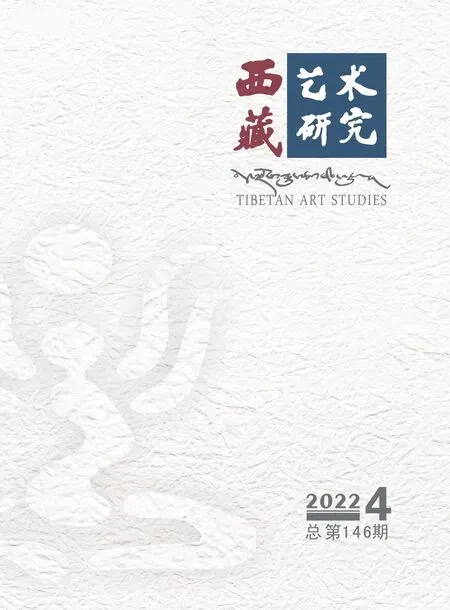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文化认同路径与艺术实践向度
——以群舞作品《欢腾的高原》《雪域暖阳》《康鼓弦音》为例
2022-03-06红星央宗
红星央宗
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累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凝聚于政治认同、经济互惠、文化自觉的整体追求下,根植于多元一体格局辩证和合的事实基础上。在这一民族实体的形成和演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铸牢国家统一之基、夯实民族团结之本、振奋精神力量之魂的情感本原与思想根柢,提供了各族人民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原生动机和内生心态,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历史阶段和社会需求下的自主发展与自为实现。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试图用“场” 的概念来补充“差序格局”的结构形态①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7(3).,以描摹地方性区域内部及各民族单元间的文化互嵌、互构过程。一如由不同中心扩散的文化同心圆,其在不同空间层次的交汇、融通形成了“多元”的节点,这些节点则在历时性发展中进一步联结为一个个“多元”的实体,继而呈现出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间交往互惠、体认互觉、共生互融的复合形态。换而言之,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实践经历了从“自在的文化表征”到“自觉的文化实体”的转型。这一过程以对自我文化的觉知和认同为基础,随后推及与他者的交流与互动,进而在对他者文化的体认和对历史心态的剖析中反思自我,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共生。即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以文化认同为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在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中寻求“多元”面向上的互惠逻辑,有助于在同一性的心理归属上重塑“一体”格局下的价值共识。
在此前提下,民族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维度的结构要素。其承载着各民族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记忆,反映了共同体成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和道德范式,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指向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进路。本文即以2021年西藏自治区藏历新年联欢晚会剧目《康鼓弦音》、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雪域暖阳》、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剧目《欢腾的高原》三部藏族群舞作品为例,从其创作理念、舞台构建和展演形态探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夯实文化认同根基的认知逻辑、实践向度与创新载体。
一、作为认同根基的多元一体格局
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赓续发展的现实样态,是各族人民建构多层次认同的理论基础。其含括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自觉民族实体的历史过程、政治经验、利益诉求和社会记忆,模塑着共同体成员在寻求价值共识中的文化心理层次和知识生产逻辑。如何星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①何星亮.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一性与互补性.思想战线,2010(1).——作为各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多样性以风俗习惯、岁时仪礼、工巧技艺、景观遗迹等符号表征涵养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事象;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同一性则以语言文字、法制俗约、价值规范、社会秩序等认知载体聚合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观念——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从“华夷之辩”“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多元一体”既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差异性和互补性,又引导着各民族单元、地域群体间的交往互惠和交融共生。在以民族艺术为实践向度的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其行动策略即立足“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和叙事逻辑,充分运用各类文化事象和民族艺术形式,以具体呈现共同体成员的心智结构与心理归属;通过挖掘隐喻在其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趣中的共性表达,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表述媒介和话语机制。
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文艺育德”实践经历了孕育奠基期(1951-1956)、曲折探索期(1966-1976)、全面繁荣期(1978-2012)和创新发展期(2012-至今)四个阶段②刘云卿、刘晓哲.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在西藏的实践及经验.西藏大学学报,2021(2).。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应具有“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历史责任;到邓小平要求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将文艺战线作为思想战线中的重要环节,坚持文艺为社会和人民服务,坚持用文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再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在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将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与文艺创造结合起来,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OL].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12/14.。“文艺育德”在党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民族性与开放性“三个相统一”的原则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文艺事业发展中,有效处理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积极促成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对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知识生产力和创新协同力有示范引领作用。如《洗衣歌》《北京的金山上》《逛新城》《翻身农奴把歌唱》等早期作品,便通过音乐舞蹈艺术真实反映了西藏群众的心声,忠实记录了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变革进程,抒发了翻身农奴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憧憬展望和西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感恩。
至20世纪80年代,“文艺育德” 的理论完善和思想实践被进一步纳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战略目标中。作为反映审美意识、引导价值取向、模塑道德范式、协调濡化过程的社会产物,进入全面繁荣期后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创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愈发注重时代意涵的构建和美育职能的发挥。始办于1980年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即是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国家法定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迄今为止,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已成功举办六届,并涌现出了一大批题材新颖、体裁多样、风格浓郁、手法写实的优秀剧目。这些剧目既具有本民族鲜明艺术特征和地方色彩,又能反映相应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及区域社会精神风貌,从而分享了各民族在历史进程共同书写的社会记忆和自觉凝聚的情感体验,拓展了巩固民族团结、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路径。如《僜人与喇叭花》《林卡欢舞》《夏尔巴的春天》等由西藏自治区选送的参评剧目,即在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取得佳绩②刘志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文艺.西藏艺术研究,2000(2).。其不仅整理、保护、再创造了僜人、夏尔巴人等人口较少群体的艺术形式和民俗形态,还将其社会生境和文化心理寓于风格化的舞蹈动作中,以舞台为媒介映射出西藏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心灵写照和精神追求。
马克斯主义文艺育德理论中国化的全面深入与中国共产党文艺育德思想的贯彻落实,促成了西藏“文艺育德”实践的创新发展期。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更新了这一行动策略的时代语境。“两个大局”的认知逻辑和“中华民族”的叙事框架表明,推进新时代民族文艺理论构建和精品创作,已上升为“关系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③董耀鹏.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价值遵循、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中国文艺评论,2021(11).的重要举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履行新时代民族文艺的责任与担当”为主线的民族文艺发展方针,在2021年于西藏拉萨召开的第三届民族文艺论坛中得到充分体现。论坛将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加强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工作、促进各民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以期传承、保护、创新各民族文化,凝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艺力量④尕玛多吉.第三届全国民族文艺论坛举行.光明日报.2021年09月17日第08 版-教科文新闻。。
可见,“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①薛帅、刘淼、卢旭.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和强烈共鸣.中国文化报,2021(1).的价值导向和美育方针,始终贯穿于西藏的文艺育德实践中。伴随着以文化认同为路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进程,新时代民族文艺作品的创作与创新在“三个离不开” 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观下具体展开。其通过文化心理的再体认和肢体律动的典范化,实现了舞蹈作品与文化认同、理论建构与舞台实践、个体惯习与身体技术的有机统一。本文所讨论的三个藏族群舞作品,便创作于这样的艺术思维和时代语境下。
二、作为创作理念的艺术主体间性
如上所述,《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是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再提炼,及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向度释读。三部作品均以藏族民间舞蹈热巴、康谐为基础。通过解构、重组传统技艺的肢体特征和风格动律,将藏族群众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情感体验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下的精神风貌,寓于动作语汇的表达和舞台时空的流动中。继而使舞蹈艺术的感官(sensuality)、肢体(somatic)和动觉(kinesthetic)从单一的动作编程和形式语言中跳脱出来,进入到历史过程、社会记忆和国家意志共同参与的话语实践和行动范式中。反映了以“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创作母题,和以“发展、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主线的工作方针。
于平曾指出,中国民间舞蹈的生命力在于其以舞蹈为认知中介,达成了身份认同的巩固和民族精神的激发②于平.民族认同格局与舞蹈认知中介——关于“民间舞生命力之所在”的思考.民族艺术,1987(3).。“风格化动作”作为聚合技艺主体文化心理的符号表征,呈现创作主体生活体认的经验表达,实现了对自我身份认同和舞蹈结构形态的双重模塑。强巴曲杰同样认为,各个民族都在其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套能够反映自身生计模式、心智结构、审美情趣的艺术表现形式。藏族舞蹈即在工巧明的知识体系和“舞蹈艺技九”的技法理论之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符合民族审美需要与地方文化生境的美学思想和动作形态③强巴曲杰.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中国藏学,2002(2).,以结构化的动作体系描摹了技艺主体生存技能和生命体验的“可舞性”。在此前提下,“风格化动作” 是主体行为与社会建构互动及其相关过程的结果,是由特定群体共同书写、累叠和体认的历史记忆。其嵌合于行为主体的历史心性和社会结构中,包含着行为主体理解事实、演绎逻辑、阐释经验、生产意义的全部过程。
如是,上述三部藏族群舞作品对丁青热巴、芒康弦子的“风格化动作”提炼,即可视为一种知识生产。其在保留铃鼓舞、毕旺霞卓这两种主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突出芒康弦子拖步、撩腿、轻踏、微颤、屈膝、塌腰的动律特征,注重丁青热巴女子击鼓技巧的舞台呈现。多将翻身击鼓、点步击鼓、顶鼓平转等传统技巧分置于高、低两个空间层次完成,并与一点鼓、三点鼓、六点鼓、九点鼓、五十六点鼓等多种节奏类型组合在一起。以空间的对比、节奏的切分、画面的重组营造了舞蹈了形式感和动势美,极大拓展了作品的动作语汇和符号表达。在舞蹈构图上,作品则突破“围圈而舞”的基本调度,转而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空间布局。通过男女舞者队列造型的聚-合、疏-密、高-低,身体节奏的缓-急、强-弱、均衡-失序,反映出不同阶段的情绪色彩和情感内涵。三部作品对音乐的恰当运用,亦推动了舞蹈的情感递进、情节叙事和思想表达。舞台空间的适度留白无疑给予了舞者与音乐以对话契机,从而使舞者能够在对音乐的领悟与演绎中,将内在的情感体验外化为具有音乐形象的可舞性节奏,由此完成了特定场景的再现和时代主题的升华。然而,这一“传统的发明”并不意味着脱离共同体叙事的文本嫁接和心性臆造;反之,其产生于对艺术形式所根植的文化生境和社会结构的充分把握上,赓续于对技艺主体所接纳的心理构图(schema)和身份认同的充分理解中——是在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上创造、延伸、革新的文化表征与意义模式。因此,藏族民间舞蹈的“风格化动作”提炼,一方面涉及知识体系的更新和价值典范的重塑,另一方面又必然暗含于历史记忆和社会事实的连续性轨迹。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地方经验叙事同时介入当代西藏民间舞蹈创编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舞台展演中的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亦在于规训社会建构下的身体技术和阐释话语。其将编舞技法与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构建与民族振兴统合起来,勾勒出艺术向度下的社会行动逻辑与文化认同进路。
具体观之,三部作品为同一创作理念的延伸与完善。其立足于“热巴是一门以铃鼓舞为主体,兼有康谐、毕旺霞卓、韵白、说唱、折嘎、杂技、气功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综合艺术”的创作基调,将由丁青热巴、芒康弦子提取的风格特点和动律特征巧妙融入同一剧目的舞蹈构思中,实现了情节叙事与情感表达在舞蹈形态中的整合。从2021年西藏自治区藏历新年联欢晚会节目《康鼓弦音》的初现雏形,到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剧目《欢腾的高原》的日趋成熟,这一创作理念始终围绕长柄鼓和毕旺两个主题形象展开。通过三段式的舞蹈结构,将人们在击鼓而歌、踏乐而舞中情感递进逐步推向高潮。以热情洋溢、喜悦欢腾的舞蹈形象,塑造了西藏人民乐观豁达、常怀感恩的品质与直率果敢、坚韧刚毅的性格。《康鼓弦音》开场便以长柄鼓与毕旺交错排列的竖直线形造型出现。随后手持热巴鼓和弦胡的两名领舞再次于队列前相遇,通过主题动作的对称呈现,刻画了长柄鼓与毕旺的同一关系。这一关系在《雪域暖阳》和《欢腾的高原》中则进一步延伸为舞群间的互动,继而将其舞蹈构思引向对手持长柄鼓和毕旺舞者的心理描摹及其情感抒发。两部作品在主体结构上相似,其均以康谐为引,伴随缓缓而起的毕旺乐声,铃、鼓轻柔相和。一条由男性领舞抛出的洁白哈达,作为衔接热巴舞群与康谐舞群的时空纽带,将手持毕旺的男性舞者从侧幕唤出,由此营造了舞台空间前、后区域的动势对比。在《欢腾的高原》中,这一对比突出地表现为S 线型和直线型的动态结构差异——后区热巴舞群以横向流水作业,勾勒出S型的长柄鼓动势,突出了视觉上的曲线美、层次美和流动感;前区康谐舞群则以行进的横直线造型,呼应了毕旺所表达的安宁祥和、绵延不绝、宛转悠扬的深远意境——反映了作品的思想基调和情感倾向。伴随着女性舞者的热谐,舞蹈进入两个舞群的群舞阶段。男女舞者交替上演主题动作,并在舞蹈中不断变化造型、更换调度,逐步将舞蹈情绪推向顶点。在高亢的鼓点与激昂的弦胡交织的高潮中,作品戛然而止。当熟悉的毕旺乐声再度响起,舞台重归平静。全体舞者在轻声吟唱中渐渐聚于舞台中央,以深情的姿态感恩祖国、感恩党,以高涨的情绪歌颂建党百年来的高原新生活、西藏新风貌。特别是《雪域暖阳》中,由《翻身农奴把歌唱》改编的主题音乐贯穿始终。从开端的轻声吟唱,到高潮的高声歌唱,首尾呼应的音乐形象和舞蹈构思更直接抒发了当代西藏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践行民族复兴新征程的真切情感,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的时代画卷。
《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三部作品的创作理念表明,编导理论的技术解构和舞台实践的审美规训,仍是围绕社会事实展开的符号行为和知识生产。倘使“两类三层说”奠定了“原生—次生—舞台”的创作范式和逻辑进路,强调藏族民间舞蹈当代创作的科学化体系建设和典范性媒介应用;艺术的主体间性则在避免先验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主体之间的可沟通性及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纳入到艺术创作中。即从文化生境和民间技艺的集体表征中萃取核心元素,经由创作者、技艺持有者、社会典范、国家话语等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商榷,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基于记忆共享和文化共识的共同体叙事范式。在西藏民间舞蹈的当代创作中,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理念转换,实质上意味着对创作主体与技艺主体、地方性知识与在地化实践、藏族民间艺术与中华民族文化等关系认知及情感体验的深刻变革。这一创作理念的更新,确立了以艺术审美为逻辑进路的认识论,催生了以知识生产为内在动因的“社会-艺术”互构,推动了以文化认同为具体路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进程。
三、作为实践范式的“文化-艺术”共同体
《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三部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在互鉴融通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实践了“以各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巩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作为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力量、分享时代发展思想共识的具体向度和艺术载体,以上述三部藏族群舞作品为代表的民族文艺创作,反映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记忆,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模塑下的情感体验、道德典范与政治理想。其将技艺传承、文艺创作、文化认同的内生动力根植于“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的意识自觉下,从而使各民族在共同生活中书写的集体记忆、习得的生存技能、累叠的认知经验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知识来源和意义指向。
在此过程中,由文化认同和艺术实践凝结的“文化-艺术”共同体统摄了各民族成员在“无意识传承”和“有意识创造”中的全部符号行为。一系列利用原有文化遗产和现有艺术资源来建构身份认同、更新自我表述、塑造价值共识的文艺创作,不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发明”和“舞台的凝视”,还包括着动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指引与整体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现实路径。从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到吴文藻、费孝通,“共同体(Community)”的伦理秩序将人类共同生活的总体事实和心理基础寓于“包含了思维的意志”中;继而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生发的情感、依赖和内心倾向,成为整合其行动惯习、认知逻辑、历史记忆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含括本质意志、展演价值典范的实践模式,“文化-艺术”共同体反映了以审美体验激发的情感共鸣和心灵契合,促成了以符号使用推进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培育。
就《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三部作品观之,其均注重舞蹈的抒情表现。“感恩”这一主题在作品中具象为一条“喜悦-歌颂-感激” 的情感脉络,并伴随着表演过程的发展而层层递进,逐步攀升至高潮。从演员的面部表情、动作强度,到舞蹈的节奏形式、空间构图,其变化进程均置于情感的延续、激化和爆发中。从而使在特定心理状态下产生的舞蹈作品情绪和舞蹈动作创作,能够在一条真实可信、正常合理的表述逻辑下被大众接纳、认可、共情,以此最大程度地发挥文艺作品的导向机制和濡化(enculturation)作用。如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指出,艺术所展示的情感价值更多在于其“表现性形式”。那些由艺术符号表征的生命形式和普遍情感,并非仅是为制造了一种艺术幻象,而在于描摹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一如人类在感受生命、体认世界中的心理起伏与持续摆动,这一艺术与生命有机体共享的“生命力”亦催生了符号使用中的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艺术给予的始终是“一种不断地感受感性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与可能性的状态”①【美】苏珊·朗格.感受与形式:自哲学新解发展出来的一种艺术理论.高艳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385-407.——由此,涵养了“文化-艺术”共同体下的文化心理、民族情感与艺术交融。互动仪式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ory,Randall Collins,2004)同样认为,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是衔接社会团结和个人行动的重要纽带。这一经由个人而拓展的社会网络,隐含着具体情境中的个体在不断接触、延伸下而缔结的互动结构。从而使微观情境下累积的历史、民族、符号、记忆、道德等多重链条关系,成为构筑宏观模式的时空维度和情感基础。当人们在心理上存在共同认知和共同关注时,便会产生类似的情感冲动,并促使他们采用相应的符号行为表达其情感体验和心理共识,美德与典范亦基于这一共同的动机和相似的诉求而产生。之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和民族艺术创作,其“文化资本”同样生发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悠久历史中,其“情绪动力”同样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进程下。如此,“文化-艺术”共同体即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维度、行动逻辑与实践场域。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②《习近平: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讲话全文[OL].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官网-时政要闻.http://www.zytzb.gov.cn/szyw.。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守正创新在于挖掘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在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艺术创造力与中华文化价值的交融汇通,推动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的意趣结合,催生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在生命力的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旨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共识。同样地,以“文化-艺术”共同体为范式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文艺创作实践,本质上仍是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风范基础之上的形式创新与价值重塑。其不仅塑造了引发情感共鸣的中华民族文化形象,更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反映时代成就的平台。伴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传,进一步被赋予了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三部作品中,来自丁青、芒康、边坝、类乌齐的基层群众是表演的主体。昌都“县县有民间艺术团,人人能跳热巴”的艺术之乡氛围,使普通农牧民成为民间艺术团的编创主体,推动了藏族民间艺术和“丁青热巴”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赓续和传承,催生了传统文化形态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模式。在此前提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使民族地区的乡风文明焕发出时代新面貌。其通过拓展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对话路径、表述机制与合作形式,形塑了《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 三部作品中农牧民表演者的双重主体身份——其一方面是参与艺术乡建的“村民主体”,在舞蹈作品中流露出对社会结构重组和物质文明提升的强烈共鸣;另一方面又是非遗传承的“技艺主体”,于舞台展演中实践着对社会文化根基和地方民俗生态的深刻体认——从而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主体间性”的审美框架,实现了“文化-艺术”共同体下的交融互通与合作共赢。
四、结语
中华文化素有“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交融传统。其将各民族沉淀于历史过程中的知识传统、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统合在以符号行为和意义生产为主体的民族民间文艺创作中,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阐发提供了文化逻辑和艺术哲学,促成了以文化认同为内聚力、以艺术创造为实践场的情感共鸣、经验共享与利益共赢。正如李世武指出,“‘异中有同’的少数民族艺术王国之所以得以构筑,离不开各少数民族艺术相互之间的交流、互鉴。各民族通过艺术交融,为中华艺术提供了丰厚养料,在情感交流、审美交流的深层交流中,走向“艺通族心”的美妙境界,在艺术世界中共筑共有精神家园,有力地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李世武.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康鼓弦音》《雪域暖阳》《欢腾的高原》 三部藏族群舞作品的艺术形式创新、编导技巧应用和情感表达延伸,即始终围绕着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的生活感知与审美体验展开,以此体现了“三维交融”的艺术创作理念,参与了“艺通族心”的时代意趣塑造,焕活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文化动力。
由此观之,以“多元一体格局”为认知逻辑、以艺术主体间为行动惯习、以“文化-艺术”共同体为实践场域的新时代民族艺术发展与民族民间文艺创作,塑造了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表征和时代精神风貌。其通过多层次、全方位、向心性民族交往中的主体互动和文化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和情感根基,加速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文化传承、艺术创新、文艺繁荣中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