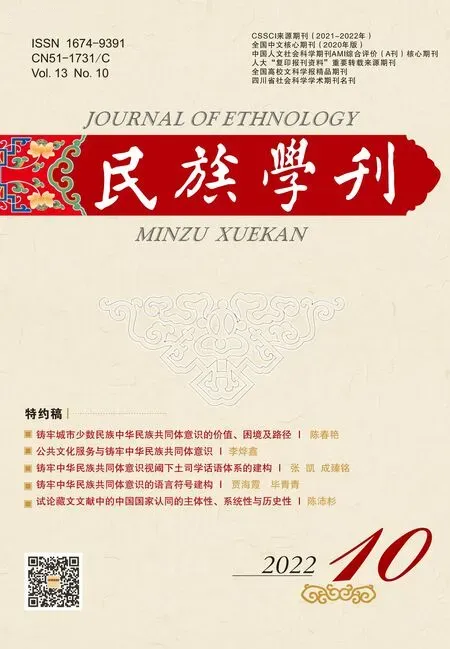从神解到药解:彝文医药经籍《此木都其》的文本历史与凉山彝族医疗思想的变革
2022-03-03摩瑟磁火
摩瑟磁火
民族医药是中华医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医药资源丰富,亟待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彝文经籍卷帙浩繁,其中与医药有关的经籍数量众多,专门的医药典籍也不少。《此木都其》是一部流传于凉山地区,具有地域代表性、学术代表性的彝文医药经籍,本文就其文本历史及其思想史意义作些探讨。
一、彝族医药文化传统
彝族医药思想起源很早,民间有许多关于先民们寻药找药、识药用药的故事,彝文经籍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流传于凉山地区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就记载了彝族再生始祖“笃慕”派遣青蛙等动物用“勒首”(麝香)“尔维”(坝子花)“素此”(刺激炎症药)“卡此”(增效药)等为天君“格兹”及其妻女治疗的故事;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也记载有支格阿龙用铜网网住雷公逼问他“什么药可治什么病”,从而获知治疗不同疾病的药物的故事。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当初神把药物平等地分给了汉、藏、彝三个民族,但只有汉、藏先民把药物收藏好了来使用,彝族先民却马马虎虎地把药草放在畜圈之上而被牲畜所啃食,所以生病时就只好拉牲畜来代替药物做治疗仪式了。至今毕摩们在仪式上追述“死因病源”时都会念诵 “用遍牛药、羊药、猪药三种药,用药也无效。”这样的经文,说明治疗仪式上所用的牺牲在彝人看来就是一种药物。此外,人们还经常用“度祖入祖界,治病于世间;扶众生之命,护众生之魂。”这样的习语来概况毕摩们的职能和作用,认为治病就是毕摩最重要的职能。这就是彝族先民长期以来为什么主要依靠祭司毕摩和巫师苏尼以各种巫术祭仪来治病的原因,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自古而然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元代以来的汉文献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如:[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五爨蛮条载:“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清]道光《云南通志稿·爨蛮》引《宣威州志》说:“黑猓猡,病不医药,用必磨翻书扣算病者生年及获病日期,注有牛、羊、猪、鸡等畜,即照所注祀祷之”;[民国]《新平县志》第十八“宗教”载:“白马,左手执书,右手摇铃,患病之家,多有延至道旁念祷驱鬼疫者”等。
对于这种治疗传统及其中所蕴含的世界观、生命观、身体观、疾病观以及治疗思想、医药知识等,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民俗学、宗教学、医疗人类学等角度进行过深入探讨。兹举几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于下:
民国时期,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在深入凉山彝区考察后指出:“罗彝至今不信疾病由于生理之失调与病菌之传染,而由于鬼神作祟。古有病者,不求教于医生,而求术于巫士;不吃药剂,而禳鬼祭神。”[1]437
之后不久,著名语言学家、民俗学家马学良在其研究彝文经籍的著作中指出:“盖倮人重迷信,遇有疾病,辄以为鬼神作祟,延巫祔除,不幸而死亡,子女则痛其先人带病以逝,到阴间不免仍受病累,以是于作祭时必举行药祭仪式,为死者医病。所以倮人患病,生时求鬼神,死后方得服药,其情殊可悯也。”[2]95
20世纪80年代,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胡庆钧在谈到彝族民间的医疗传统时认为:“……在其所进行的驱鬼治病的宗教活动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内容。例如,对于彝区流行的风湿性关节炎与疟疾等症,毕摩采取一种蒸汽的办法进行医治,以大锅一只,内置……等中草药十余种……这显然是中草药的药力通过蒸汽发挥了作用……”[3]410-411
进入2000年以后,法国学者魏明德在讨论凉山彝族宗教时认为:“我们可以从治病仪式看出团体的重要性……把病人从被鬼所干扰的生病的世界唤回正常的生活……医治社会机制的失序,如同医治社会病,与医病的道理是相同的,因为鬼破坏肉体的协调关系,同样也破坏团体内部的关系,仪式的目的在于找回关系的连接。”[4]82
作为彝族祖灵信仰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巴莫阿依在其探讨毕摩仪式医疗时认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病与治病对于凉山彝族人来讲,不仅是一种生理的过程与感受,也是一种信仰的经历与体验,疾病与心理和信仰密不可分。”[5]
因深入凉山腹心地带研究艾滋病、吸毒等问题而著名的台湾学者刘绍华在其近年出版的医疗人类学著作中认为:“传统诺苏文化认定疾病是由鬼怪或失魂落魄所引起。直至今日,这种疾病诠释对诺苏农民的日常生活影响依旧很大……改革开放时期有了更多不同疗法的选择,包括生物医学、宗教仪式疗法……虽然诺苏人同意生物医学的效益,但仍然以传统概念来解释疾病的“最初”或“真正”的原因。”[6]233-234。
另一个对凉山地区艾滋病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周如南则认为:“彝族人的传统疾病认知嵌合在当地自然和社会结构之中,形成基于地方性知识和思维模式的分类体系和治疗实践: 疾病是生活中的“失序”( disorder) ,而治疗是嵌合在整体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应对行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反常”的“他者”(鬼) 的驱除,来实现从个体到社区秩序的恢复。”[7]
此外,还有姚昌道、刘小幸、李永祥、唐钱华、蔡富莲、李小芳等众多学者都曾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对彝族的治疗传统进行过研究。
如果把这种整体的治疗传统搁置一边,单就彝文医药经籍来看,随着毕摩文化的发展,自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改土归流以降,由于毕摩社会地位、角色及职能的变化,一些专门领域如历史、文学(诗歌)、伦理道德、历算、医药等方面的知识也随之从以前由毕摩们所垄断的宗教知识体系中逐渐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相对专门的一些经籍。其中,彝医药经籍的相继产生成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自那以后,云南、贵州彝区就逐渐产生了一批彝文医药书籍①。代表性的有:贵州地区的《启谷署》(据说成书年代不晚于明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云南地区的《齐苏书》(又称《双柏彝文医书》或《明代彝文医书》,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小儿生成书》(又名《娃娃生成书》,抄于清雍正年间即公元1723-1735年)、《好药医病书》(抄于清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冬)、《医病书》(抄于清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三马头彝医书》(晚清)、《洼垤彝医书》(晚清)、《努苦苏》(意译为《医病书》)、《老五斗彝医书》(成书于清末,抄写于民国3年即1914年)、《聂苏诺期》(民国10年即1921年抄本)等[8]。与仪式治疗传统不同,这些医药经籍是彝族先民关于身体、疾病、药物和治疗方面的知识之总结,集中体现了先民们在医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凉山彝区而言,在品类众多的彝文经籍中,有相当多的部分都与疾病的预测、诊断、预防和治疗有关,甚至有不少经籍的主旨就是应对疾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类彝文经籍大约有60余种。这些经籍虽然对疾病有着一些经验性的认识,但一般停留在以命理、灵魂、鬼神等观念来解释疾病因由的阶段,认为疾病主要是来自“鬼神祖三界的非人格性力量对人间平衡的扰乱”(列维·斯特劳斯语),并在这套解释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丰富的治疗仪式,以此作为应对疾病的主要手段,尚未形成一套独立、自足、完整的医药理论。其文本的著述方式、形成过程、文化功能等都与严格意义上的医药典籍有很大不同,且大多混融在整体的宗教经籍体系之中,很难将其从中清晰地剥离开来。不过,这是彝族人民长期以来关于命理、病理、疾病、药物、诊断、治疗、预防等与医药有关的各种认知成果的总汇,反映了彝族先民遭遇疾病时进行艰难探索的历程,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彝医药传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占算经》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占卜预测书,其中的很多内容是对人生“命运”的测算。“命”主要与出生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属相时段相关,特别是与彝族特有的由其出生时母亲的岁龄决定的“命位”②密切相关。根据其特定的出生时间,每个人都有其相应的五行、阴阳、星相,并由此决定了其禄命、贫富、聪愚、盛衰、苦乐、婚姻、疾病等;而“运”则主要与其“岁位”有关,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会有不同的“运”。其中就有丰富的关于疾病测算的内容,如按生肖年、月、日、时测算病情、按朔望日测病、按命位测病、按岁位测病、女性患神怪病③测算、男性患神怪病测算、出嫁日测病、方位患病测算、患病预后测算、患病日与死期测算、寿终年测算、正寝时测算、不同季节出生者身体不同部位长势测算,等等。根据这些测算,结合鸡蛋卜、打木刻、羊胛卜等占卜的结果和通过剥鸡、剥山羊④等形式进行“诊断”的结果,以及病人的自述、症状等,毕摩们就会制定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具体的治疗实践中又会根据不同疾病、不同仪式选择诵读不同的经书。这种按照人的生辰、属相、星座、五行、阴阳及其所处时空,用天文、历算、地理、物理、生理等知识来推算人的生、老、病、死的方法,其深层内涵是对生命、人体运行规律的一种认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这些文本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医药典籍,最多也只能算是“准医药典籍”。
二、《此木都其》的版本及流传
《此木都其》一书于20世纪80年代由凉山州甘洛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的工作人员沙光荣发现,有学者说其初为“甘洛县农民木基罗卡所藏”[9]295,但据笔者对沙氏的访谈,木基罗卡(或记作“母基洛浅”[10]001,或记作“木几罗卡”)只是该书发现时的一个协助者,原藏者实际上是木基罗卡的一位叔叔,甘洛县团结乡雅什村人,彝名“尼格曲达”(或记作“黎格取打”[10]001),汉姓骆,人称骆医生,是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民间医生,常年为周边的彝、汉、藏各族百姓看病。因沙光荣与其有甥舅关系,从小与其交往甚密,后来又因工作需要发现该书有独特价值,便从其手中抄写了一份⑤,并上交了一份整理翻译稿⑥的复印件给凉山州语委。后来这个复印件被重新抄写⑦后以影印的形式收入《彝文典籍丛书》[11]6938-6951之中。这个影印件用传统彝文写成(实际上已经是整理翻译稿的一个异文),书写款式采用与传统毕摩经籍一样自右向左的横书式,无句读,不分篇章,也没有自然段,只有书名界栏和书尾用以区分本文和“抄后记”的一个段落符号。但据说“原本”共19页(出版的影印件只有14页),自右向左横书,约6000个古彝文字,译成汉文约1万字,有278个自然段落[12]32。不过这个说法似乎有点矛盾,即既然是“自右向左横书”,则应属于传统的书写款式,也就不太可能分出自然段。另外,有学者认为从“木几罗卡家发掘”的写本与目前我们所见的抄本属于“两种不同的版本”[12]32。由此来看,该书在当地可能还存有多个不同的异文,其“原件”的书写款式与目前能见到的整理翻译稿和已经出版的影印件一定有所不同。至于其外在的形式特征即装帧方式等,虽大概率应与别的毕摩经籍一致,但也不敢遽断,也不知其纸质⑧。
从收录于《彝文典籍丛书》中的影印件之“抄后记”来看,该书最初仅流传于甘洛县内有限的区域。兹将这个抄后记译录于下:
这本《此木都齐》,是由沙马毕摩硕布、马比曲都、阿尔毕摩等用来给老百姓献药的;男人有尼格曲达、阿木夫拉、木里的解、牛牛木且,女的有阿嘎金史莫、英格比乍、阿以乌箐等使用本书;现在也还在甘洛县玉田、田坝等地区广泛使用。
从这段抄后记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个信息:1.该书流传的区域主要在甘洛县田坝、玉田等地,范围非常有限;2.该书最初可能是由毕摩们所撰,且很有可能直接脱胎于《献药经》⑨;3.有女性掌握并使用该书,说明该书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担任的毕摩们对文字的垄断,从“毕摩文献”变成了普通百姓甚至女性也有资格和能力去使用的“民众文献”⑩。
再从该书的语文特点看,其语音带有明显的彝语北部方言田坝土语特征。如标准音点应作“ɡ33”的字被写为“ɡ33”,辅音从鼻冠浊音变成了无鼻冠浊音;标准音点应作“i21”(乳汁)的字变成了“ni21”,辅音从舌面前变为舌尖中。说明其祖本也应该产生于属于彝语北部方言田坝土语区的甘洛县境内。
值得一提的是,大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该书的一个抄本(抑或是一个抄本复印件)可能通过一个叫吉克曲以的毕摩流传到了美姑县拉马乡境内,现由其儿子吉克乌萨收藏,但不清楚具体的过程。另外,大致在2006年左右,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在州语委借了一本(应该是州语委新抄本)到美姑,由他们特聘的毕摩俄也拉都重新抄写了至少三份,其中一份交州语委,一份留在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一份由俄也拉都毕摩收藏。这算是该书流传到域外的一些特例。
据说该书有一个由沙光荣翻译,郝应芬、李耕冬校定的稿本[13],但未见正式出版。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有两个版本,其一是收入《彝文典籍丛书》中的抄本影印件,其后附有相应的规范彝文转写本;其二是收录于《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1辑)的阿吉拉则译注本[14]3-50,其底本依据为收入《彝文典籍丛书》的影印本。该译本完整地将原书翻译了出来,并做了大量的注释,弄清了许多与彝语药名对等的中草药名及其药性。但据笔者比对,该译本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影印件的原文,在一些细节上对原文有所增损,使原文的语气发生了轻微变化,甚至对该书“给死者献药”部分中的用药品种和药名进行了一些更改和替换。此外还有一本由吉晓丽主编的《此牧都嗪考释》,是将“原书中分散的各科疾病的内容归类集中在一起……对书中每个病的临床表现与现代中医临床验证对应,对每味药物寻找实物标本并进行鉴定,排列出对应的病名与鉴定结论……增补每个病的临床表现、诊断依据及每味药的用量、功能作用、注意事项等”[10]002,对该书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增补或删减,并非对其原本内容的完整呈现。
三、《此木都齐》的内容
从《此木都齐》这个书名来看,“此木”有“制药”“用药”“给药”等义项,“都齐”有“制毒”“用毒”等义项(但其所谓“毒”当指味苦性烈的药材,而非害人的毒品),合起来则为“造药用毒”,可译为《造药治病书》。顾名思义,该书以医药、疾病为其主要内容。书中“采用‘一病一条,按症记药’的方式罗列病名与药方,不加分类”[9]295。而对其所载疾病名和药物名,不同的研究者给出的统计和描述有所出入。兹将笔者根据影印件统计所得的数据与他们的统计数据列表对比如下(见表一)。

表一 《此木都其》所载疾病和药物数量统计表[13][14]2
书中所载疾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科、伤科、杂病及兽病”[12]32;用药方法和治疗方式有:1.内服:泡水喝、炒焦泡水喝、调水喝、熬水喝、温酒喝、泡酒喝、烤食、炕熟食用、烧喂、煮食、口含、嚼服、研沫服用、喂服、禁食等;2.外治:捣绒包扎、外敷、捣敷、烤敷、热敷、熏敷、鸡蛋滚抚、石杵滚抚、引血、放血、扯毒放血、针刺放血、拔火罐、烧熏、火疗熏烧、熏蒸、泼拍浴、洗浴、吹疗、搽擦、按摩、牵引、揉捏、滴灌、佩戴等;其药物剂型则有烟熏剂、水煎剂、食补剂、滴耳剂、泥敷剂、搽剂、散剂等7种[15]。
此外书中还记载了算命、看相、占卜、作祭献药、预防、辟邪等“诊断”和仪式治疗的方法,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卫生常识。
从其所载内容看,药方绝大部分都是单方,复方很少,说明其用药方法比较简单;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卫生常识,说明其通俗性和实用性。据说其中所载药物曾“由凉山州药检所协助进行了病种和药方的论证,对实地采集的药物标本进行了化验和科学鉴定,证明都是民间用之有效的验方”[9]295。但书中对病症只有大致的描述,没有细致的区分,没有病因的追溯,没有科学的诊断方法,没有完全摆脱神鬼致病的信仰,说明其相关知识仍处在初级阶段。
四、文本的形成及其年代
关于该书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12][15],甚至说有一个异文“至少有1176年历史,约成书于公元816年”[12]31,但因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也无人在甘洛境外发现早期与此书有传抄谱系关系的医药书籍,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些推断。如果想对该书的成书问题有个进一步的认识,还需要对其更广阔的历史、地理、社会等背景进行一些考察。
甘洛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素有凉山北大门之称。东南与凉山腹地接壤,西北与雅安市的石棉县和汉源县相望。从历史沿革看,明弘治中在海棠建镇西守御后千户所,并节制“煖带密土千户”(彝称“尼迪兹莫”,俗称下土司)和“煖带田坝土千户”(彝称“斯补兹莫”,俗称上土司),由两千户管理境内“夷务”,隶越西卫。清改卫为厅。民国二年废厅置县,在今甘洛地方设海棠区。1956年建县,名呷洛县,1959年更名为甘洛县。彝族谚语“汉区首府为大,彝区甘洛为大。”说明甘洛在彝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彝谚“石沉水塘不回还,人到甘洛不回还。”则反映了旧时甘洛山水凶险、交通阻塞、部落林立,人一旦进入便势难生还的历史地理环境。
晚近以来,甘洛彝区还形成了“曲木底”(白彝区)和“诺木底”(黑彝区)两种不同的区域。白彝区属两土司管辖,黑彝区则独立或半独立于土司的管辖之外。因土司作为官方代理人与汉文化接触较为密切,所以白彝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多;而黑彝区与邻近的越西、峨边、美姑等地的黑彝控制区连成一片,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两种区域的彝族人在居住环境、生计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清]光绪《越巂厅全志》卷六之五“土司”中说“夷人系黑白二种,生熟两分”,其中“住河内舒凶沙得地方猡夷……住煖带密地方猡夷……各支俱属白夷,半通汉语”“白夷耕田度活,半通汉语……仍照汉律惩办”,指的就是白彝区;而“住河外地罗马得瓜惹西纠地方……黑夷号生猡,不通汉语……不绳汉律”[16],指的是黑彝区。
就《此木都其》一书的主要流传区域田坝、玉田等地而言,自清康熙以来一直属于土司管辖的白彝区,理应与汉文化接触较早,但这个区域的彝人长久以来都是“病不服药,用夷僧击羊皮鼓……束草人,杀牲跳舞禳送”[16],说明他们应对疾病的方法仍然以传统的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为主。
检视毕摩的历史,因改土归流迅速瓦解了彝族传统的政治结构,毕摩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职能发生分化,从而促使云南、贵州地区的彝医药获得较快发展的情况已见前述。在凉山地区,虽然土司势力在历史大势的冲击和黑夷势力的排挤下从明代中叶起就开始衰落,但因改土归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推行,所以,直到建国前夕,仍有部分土司势力残存于凉山周边接近汉文化的地区。而且,作为土司力量衰弱的后果,是让保守的黑夷势力重新掌控了凉山的核心区域,使其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所以,在这些核心地区,毕摩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绝大部分知识,其职能的分化也不像云南、贵州地区那样明显,除了在历史、文学(诗歌)、伦理道德、天文历算等方面有所起色外,尚未在医药领域发展出更为专门的知识体系。直到清末民初,在甘洛田坝、玉田等凉山边缘地带的权力精英——土司中出现几个愿意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人物以后,才给“如封瓮中”[17]的凉山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为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道路。比如,煖带密土千户土司岭镇荣就“知汉语,略识汉文……因之了解一些新知识,以精于彝文,为传播彝族文化及外来知识,与头人共同编译出《地球志》《农作书》《工匠书》《算数书》等,并与古书《史传》《教经》本(按:应为“刊”字之误)刻印行,也派青年分别学彝文法文”[17]93,大力鼓励彝民学习科学技术。之后,作为煖带田坝土千户最后一代土司的岭光电更是认为“不破除迷信思想,彝人思想受到束缚,不仅不能接受新知识,即原有知识也会被抛却,尤其迷信消耗大,治病无效,死亡率大,是彝人前进中的绊脚石”[18]353,所以在其以田坝为中心的辖区大力提倡科学技术,改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在所办的小学内设医疗室”,“利用购置的药品,医治学生及附近彝人的疾病”[18]347,还计划“培养出十多名医务人员,供之学习呗耄经术后,带起药品器材到凉山各处巡行,边诵经作法以顺彝人思想认识,边行医以去彝人病痛”[18]342,后来又“建立医院房舍,取名叫‘斯补医院’……解除了不少彝族人的病痛……使许多人见了不得不改变认识”[18]352。为了实现在彝区推广医疗的理想,岭光电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育彝族老百姓的说辞,说“鬼使人生病死亡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毕摩苏尼祭送鬼神的方法之所以越来越没效果是因为……所以人生病了还是吃药好,药是能够驱鬼治病的”,并由此“成功地将彝人传统的观念认知方式与当时人们对世界新变化的体验感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们能够接受的疾病观”,从而“将卫生这样一种极具现代性色彩的话语体系植入彝区”[19]85。
然而,作为特别热衷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土司和彝文文献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岭光电却从未在其著作中提及《此木都其》这本书。而且,如果《此木都其》早已成书并在民间流传,作为非常适合在彝民中推广的医药书,也必然会引起曾经编译、刊刻各种工农业生产知识读本的土司岭镇荣的注意。但这两位土司似乎都不知道有该书的存在。基于此,笔者认为,《此木都其》的成书时间当不早于岭镇荣木刻印刷《教育经典》的时候(清光绪年间),更大的可能是“随着岭光电将现代的医学技术带到彝区,在当地围绕着有病时是要求医吃药,还是要祭送鬼神的选择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深刻冲突”[19]84之后,才由受岭光电思想影响,在其教育、指导下“发给药品,规定他们为病人送鬼神时,必须先给病人发药,方得再行念经念咒”[20]123的巫医毕摩们逐渐总结彝族传统的医药经验,吸收邻近汉人和藏人的医药知识而撰述成书的。当然,除了这些政治精英的努力,自清末以来,汉民们(其中必有中医)就通过租种或购买土地等手段不断地渗透到田坝、玉田等地区,与当地的彝民们有了密切的互动,这也为彝民们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医药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反映在《此木都其》的内容中,就是除传统的彝药外,其中不少药名都直接借用了汉语,如千里光(tshi55i[33]k55)、泽兰(tsɛ33la33)、藿香(bu55xu21ɛ33)、枇杷叶(phi21pa33thi34thi33)、三七粉(sa33thi33mo21)、山茈菇(ʂa33tsh21ku33)、马鞭草(ma33pɛ33bu55)等。说明彝汉人民之间(也许还有藏民)的交往、交流是该书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以电池油(tɛ21tsh33i21thu33)为药的记载,可见目前所知写本的抄写时间是在电池流传到彝区之后。而根据相关资料,中国直到1911年才自己建厂生产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作为当时的一种稀有物品,这些电池要流传到边远偏僻的凉山彝区,恐怕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若按此推测,则该书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按照彝文经籍的传承惯制和抄本的形成、演变规律,抄写时间和成书年代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要确证其祖本的形成时间,还需要找到更可靠的材料方可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凉山彝族的祭祖送灵仪式中,有一个专门为逝者献药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毕摩们或口诵“献药辞”,或诵读用文字将“献药辞”记录成书的《献药经》,意在为逝去的考妣治疗各种疾病。从书名上看,这种《献药经》彝语称为“此其”或“此其特依”,义为“献药”或“献药书”,也有称作“此其纳古”的,义为“献药治病”。这些书名都与《此木都其》的书名有着密切的关联,即“此其”一词可看作为“此木都其”一词的简化,“此木都其”一词则可看作“此其”一词的扩充,其基本词义相同,都有“献药治病”之义。再从其内容来看,虽然两种书所载的药物名、疾病名不完全相同,治疗对象也不同,一为逝者,一为生者,但目的都是为了治病。再说,《此牧都其》中还记载有算命、占卜、作祭献药、预防、辟邪等传统仪式治疗方法,说明该书还与《献药经》《占算经》等一系列旨在“诊断”、预防、治疗疾病,且流传已久的那些毕摩经籍之间有着密切的文本互涉,而如何把握这些经籍间的互文性将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其文本历史的关键。
五、文本价值小识
综上所述,从民族医药学(或医疗人类学)的视角看:首先,仪式治疗与药物治疗本是建立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疾病理解上的行为模式,其背后是不同的身体认知和疾病认知。在《此木都其》中,仪式治疗与药物治疗被杂糅在一起,其中还包含着部分传统的仪式治疗方法。说明该书是“一部在‘巫’的统治下产生,却又竭力冲破‘巫’的束缚的医书”[21],尚未完全摆脱彝族古老的仪式治疗传统,仍然处于 “神药两解”的阶段。但该书的出现也说明当地的彝族人在医疗方面已经冲破了原来以仪式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神解为主、药解为辅)的格局,进入了以药物治疗为主、仪式治疗为辅(以药解为主、神解为辅)或二者并重的阶段,其疾病认知和应对策略有了重大进步。这是凉山彝族医疗思想的重大变革,也是彝族人世界观、生命观、身体观的重大转变。这种变革为现代卫生事业在凉山彝区的推广和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凉山彝区走进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开端。从此,彝族人关于身体和疾病的固有认知发生了动摇,延续千年的观念体系逐渐瓦解,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其次,作为凉山彝区产生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书,该书是甘洛地区“彝医”们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外文化和本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下对彝医药传统的扬弃,除了在医药方面的参考和利用价值外,也为我们探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彝医药发生、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
从文献学的视角看:首先,《此木都其》专注于医药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是第一次在该地区民间自发产生以自然科学内容为主的彝文书籍,不仅突破了传统彝文经籍在内容方面的固有范围,而且在其流传使用过程中冲破了毕摩们的垄断,可以由一般民众(非宗教人士)甚至由女性来使用,这是凉山彝文书籍制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次,凉山地区的彝文经籍从文体来看几乎都是诗体的韵文,散文体的非常少见,而《此木都其》属于少见的散文体中的一种。从文本史的角度看,诗体的彝文经籍大多属于仪式文献,是将长期以口头方式流传的韵语用文字记录下来而形成的,大多是由集体创作的“文史”作品,其特点是运用丰富的修辞以“文言”的形式来表达情感、观念和思想,偏重于形象思维,使用时主要诉诸于“听觉”,由特定人在仪式语境中面向其他人大声唱诵或朗诵,处于从借助于声音的“耳闻”之学向借助于文字的“目视”之学转换的阶段,还带有许多“口语文化”的特征,其形成的年代相对较早。而散文体彝文经籍主要以“白话”的形式记录知识,重在事实的陈述和意义的表达,内容上更多“科学”的成分,偏重于逻辑思维,且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著作,使用时主要诉诸于“视觉”,由“读者”个人来阅读(默读),“把语词从声音世界迁移到视觉空间的世界”[22]92,属于“目视”之学,“书面文化”特征明显,形成的年代相对较晚。两种文本在形成途径、著述方式、涵盖内容、思维特点、语言特色、诵读形式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再从其文本结构上看,《此木都其》的内容似乎没有进行过刻意的编排,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内容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归纳在一起,而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缺乏一本成熟的书籍应有的篇章结构,说明该书还处在文本形成的初期阶段,其撰著过程还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整体性思维。实际上,该书在被学界发现之前可能还处在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之中,是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增损变异的流动性文本,而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书为我们探讨彝文经籍产生、传承、演变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文本个案。最后,由于凉山彝文经籍一般都没有明确的作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其成书过程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而要解决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除了根据经籍所载内容、语文特点及其物理特征等外在形式进行精细的文本考订外,还需要结合其更为广阔的历史、地理、社会等背景来进行综合判断。在此意义上,探讨《此木都其》的成书问题也可以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凉山彝文经籍整体的文本历史提供支持。
注释:
①据说云南地区的《元阳彝医书》成书于大理国明政七年即公元975年,若此考证无误,彝医药典籍形成的历史就会更早,但那只是孤例,与彝医药典籍大量形成于明代中期以后的情况并不矛盾。
②彝族认为人出生后,每个年岁都对应于八方中的一个方位。一般是以女孩出生之年对应于北方,男孩出生之年对应于南方,以后每隔一年就要变动一个方位,女孩按反时针方向轮转,即二岁时为西北方,三岁为西方……男孩则按顺时针方向轮转,即一岁在南方,二岁在西南方……如此每岁都相应于一特定方位,这就是所谓“岁位”。“命位”是指某人出生时其母亲的“岁位”。如其母25岁而生他(她),则其命位就属于北方。命位是一生不变的。
③神怪,彝语称为“斯色”,本义是指神,但因彝人认为他们非常神奇,甚至怪诞,难以捉摸,故将一些不明原因的酸麻肿胀、嘴眼歪斜、半身不遂、失语失聪等疾病(一般为神经性疾病和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归咎于“斯色”,并以此为这些疾病命名。
④剥鸡、剥山羊都是毕摩诊断疾病的方法。其方法大致如下:用鸡(或山羊)为病人头顶绕匝,口诵相关经文,用鸡(或山羊)抚拭病身,让病人吹气入鸡(或山羊)嘴,拂拭三次,吹气三次,诵《剥鸡经》(或《剥山羊经》),之后将鸡(或山羊)闷死,然后从鸡(或山羊)的颈项开始剥皮,逐一解剖鸡(或山羊)尸,观其各部位的形状颜色,以诊断病人相应部位有无疾病、是什么病、病重与否等。
⑤据说于1982年5月2日由“木几罗卡”解读断句,沙光荣手抄完成。参见吉晓丽主编《此牧都嗪考释》“前言”。
⑥据笔者所知,这个整理翻译稿是用当年凉山州语委特制的一种稿签纸书写,左栏誊抄已经断了句的原文,右栏为汉文翻译和注释。
⑦重抄者为当时凉山州语委语言文字科科长罗阿体,抄写时间大致在2000——2004年间。
⑧凉山毕摩经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线订卷轴蝴蝶装”和“线订卷轴包背装”。但据徐士奎,罗艳秋编著的《彝族医药古籍文献总目提要(汉彝对照)》中所载,从“木几罗卡家发掘”的《此母都齐》为绵纸,线订册页装。
⑨《献药经》是在祭祖超度送灵仪式上为逝者献药时所用的一种毕摩经书。
⑩彝文文献按其掌握文献的人群和文献使用场域的不同可以分为毕摩文献和民众文献两大部分,在凉山地区,毕摩文献在彝文文献中所占比例高达9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