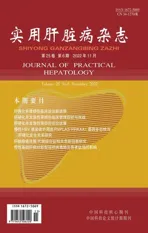慢性基础肝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结局的影响*
2022-03-03董士铭综述南月敏审校
崔 坡,董士铭 综述, 南月敏 审校
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导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全球肆虐。据WHO统计,截至2021年5月累及感染人口达1.6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定期医院就诊,较普通人群暴露于SARS-CoV-2的机会增加,报道显示2%-11%的SARS-CoV-2感染患者存在慢性肝病病史[1]。COVID-19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肝脏生化学异常,在中国1099例COVID-19患者中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 40 U/L、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 40 U/L、总胆红素升高发生率分别为22.2%、21.3%和10.5%[2]。肝损伤主要与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药物诱导的肝损伤、缺血缺氧再灌注、免疫调节障碍以及病毒的直接感染等多种因素有关[3]。研究报道,COVID-19患者肝脏可出现脂肪变性、轻度小叶和/或汇管区炎症、肝血窦充血及微血栓形成等病理改变[4,5]。不同肝病人群对SARS-CoV-2的易感性,感染后疾病严重程度及SARS-CoV-2感染是否会加重慢性肝病,进展为慢加急性肝衰竭、出现急性肝功能失代偿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阐述不同慢性肝病人群合并COVID-19的临床病程和预后情况,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 COVID-19与肝硬化
肝硬化患者感染SARS-CoV-2时呼吸道症状不明显,而以肝脏功能受损表现更显著,因此肝硬化患者出现呼吸道症状、原有肝病病情恶化及新发或再发肝功能失代偿应积极评估是否存在SARS-CoV-2感染。与慢性肝炎相比,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呼吸道症状无明显加重,但易出现更严重的肝损伤、更多的并发症和更高的病死率。
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肝损伤发生率高且出现时间早,多见于第一周内,而慢性肝炎患者肝损伤大部分发生在第三周,甚至出现更晚[6]。肝硬化患者的肝损伤主要与药物或缺氧有关,肝脏生化学主要表现为AST显著高于ALT水平、ALT/碱性磷酸酶较低、胆红素迅速升高,死亡患者的上述生化学特征更为明显[7]。另外有报道称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肝损伤可能与COVID-19相关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微血栓继发的肝脏灌注改变及肝细胞脂肪变性等多种因素有关[8]。急性肝损伤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更严重,且与高病死率相关。因此,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应在治疗中给予优先考虑,避免使用肝毒性药物,动态监测肝功能,及早发现肝损伤,加强保肝治疗及呼吸、循环支持。
肝脏相关并发症主要指急性肝功能失代偿和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肝功能失代偿事件包括腹水出现或加重、肝性脑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等。肝硬化患者存在内毒素血症、高水平炎症因子以及肝硬化相关免疫功能障碍综合征,感染SARS-CoV-2时可产生过度炎症反应,导致ACLF的发生[8,9]。一项29个国家130个地区的回顾性研究显示,386例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中,179(46%)例发生急性肝功能失代偿事件,89(23%)例出现ACLF。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肝脏合成功能及肝功能储备越差,肝脏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越高。不同肝功能等级患者之间失代偿事件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 Child-Pugh A、B和C级肝硬化患者分别为30%、56%和64%[10]。多项研究显示,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ACLF发生率约10-40%,慢性肝功能衰竭联盟-器官功能衰竭评分(chronic liver failure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core,CLIF-C)评分越高,预后越差,病死率越高[7,10,11]。
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病死率显著升高,约为30%[7,10,12,13],病死率在各年龄段相同,基础肝病严重程度是决定预后的主要因素。慢性肝炎进展到Child-Pugh A、B、C级肝硬化,病死率递增,分别为8%、19%、35%及51%,其中Child-Pugh C级ICU病区患者病死率为79%,需有创通气治疗的患者病死率高达90%。与无肝硬化的慢性肝病人群相比,Child-Pugh A、B、C级肝硬化人群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90、4.14和9.32倍[10]。来自13个亚洲国家的回顾性研究同样证实了肝病严重程度与病死率的密切相关性。COVID-19合并失代偿期肝硬化的病死率约为代偿期肝硬化的两倍(33.3%对16.3%),经肝移植改善肝功能后可使死亡风险恢复到普通人群水平[7]患者感染SARS-CoV2时的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LIF-C评分对肝硬化患者的生存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上述发现强调了肝脏功能储备的重要性以及肝硬化患者住院期间仔细监测的必要性。
另外,由于肝硬化患者肝脏解毒、代谢功能受损较重,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接受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抗SARS-CoV2治疗的比例显著降低于慢性肝炎患者。对于COVID-19合并肝硬化患者,医生需要综合评估患者病情,选择可及、可用、有效的药物的同时,需考虑药物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2 COVID-19与慢性乙型肝炎
新型冠状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共感染者临床表现为更显著的单核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转氨酶升高、前白蛋白降低及脂质代谢紊乱[14]。研究报道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感染SARS-CoV-2时病毒清除时间延长[15],且更易发生肝损伤,然而西班牙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发现,使用替诺福韦作为抗HBV治疗的CHB患者SARS-CoV-2感染发生率较低,仅0.4%[16]。抗HBV核苷类似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SARS-CoV-2发挥作用,研究显示替诺福韦能与SARS-CoV-2 RNA依赖的RNA聚合酶紧密结合,阻断SARS-CoV-2 RNA的合成[17]。大多回顾性研究显示慢性HBV感染不4影响疾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和病死率[13,18,19]。可能与慢性HBV感染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有关。慢性HBV感染后持续存在的病毒抗原导致特异性CD4+和CD8+T细胞耗竭,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受损,抗病毒功能降低,避免了机体感染SARS-CoV-2时产生过度免疫反应,细胞因子风暴减少,发生重型肺炎的可能性降低[20]。COVID-19合并CHB患者肝脏合成凝血因子能力及代偿功能相对薄弱,此类患者出现凝血功能障碍时,病程更严重,病死率更高(28.6% vs 3.3%)[21]。因此,对于COVID合并CHB患者应加强临床监测,预防并尽早治疗肝损伤、凝血功能障碍,避免发生多脏器衰竭等严重事件,改善预后。
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COVID-19时,活动性或既往感染HBV患者发生病毒重新激活问题需要引起重视。COVID-19患者过度的免疫反应可产生炎性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多脏器炎性损伤,因此免疫抑制剂应用是治疗COVID-19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包括皮质类固醇、白细胞介素-6和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以及JAK抑制剂等。研究显示,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阳性的人群接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时,出现HBV病毒复制。一周内接受20-40mg或>40mg/d泼尼松或其它等量激素时肝炎爆发的风险显著增加2.19和2.11倍[22]。Liu报道了6例HBeAg阴性、未行抗HBV治疗的共感染者,2例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COVID-19时出现HBV重新激活[23]。HBV重新激活风险较低,但仍建议加强HBV-DNA的监测及抗HBV药物的预防性应用[24]。亚太肝病学会(APASL)、美国肝病学会(AASLD)及欧洲肝病学会(EASL)建议已接受抗HBV治疗者继续治疗,未抗HBV治疗者推迟开始治疗时间至COVID-19治愈,临床怀疑有活动性肝炎发作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接受抗HBV治疗[25-27]。
3 COVID-19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COVID-19患者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比例目前尚不明确,这可能与NAFLD易合并其他代谢共病,SARS-CoV-2病毒可诱导肝脏脂肪变性引起混杂效应以及NAFLD的不同诊断标准有关。
一项最新的Meta分析显示NAFLD合并SARS-CoV-2感染患者住院期间肝功能异常率增高,病毒清除时间延长[28]。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是SARS-CoV-2的功能性受体,侵袭细胞时病毒尖峰首先作用于ACE2,前蛋白转化酶FURIN切割多元酸S1/S2位点预激活病毒尖峰,并促进跨膜丝氨酸蛋白酶(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TMPRSS2)裂解尖峰蛋白,病毒和细胞膜融合进入细胞[29]。NAFLD患者ACE2和FURIN基础表达水平较高[30],TMPRSS2在肥胖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患者中表达显著上调[31], NAFLD患者对SARS-CoV-2的易感性,和更长的病毒清除时间可能与此有关。
NAFLD患者常合并肥胖、2型糖尿病及高血压等,研究显示体质量指数较高的NAFLD患者肝损伤更严重[28],COVID-19合并肥胖及NAFLD的患者发生重型肺炎的风险是非NAFLD患者的6倍[32]。NAFLD患者体内代谢紊乱、慢性炎症状态,感染SARS-CoV2时炎症通路急性激活与慢性炎症相互影响,短期可加重肝脏损伤。慢性炎症导致的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也是加重新冠肺炎的原因[33,34]。NAFLD合并肝纤维化时肝脏功能储备降低,代偿功能有限,重症肺炎率、病死率上升,预后较差,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rosis 4 index,FIB-4)≥2.67是ICU住院、机械通气的独立危险因素[35,36]。
脂肪变性是NAFLD的基本病理特征,肝脏脂肪含量对新冠肺炎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有报告称肝脏脂肪含量增加时更易于发生症状性肺炎,脂肪含量>10%可增加重型COVID-19的风险[37]。然而,研究显示经CT评估的肝脏脂肪变性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38],目前回顾性研究较少且缺乏病理学证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体而言,NAFLD加重COVID-19疾病严重程度和相关肝脏损伤,但与ICU住院率和病死率无显著相关性,患者整体死亡风险不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感染SARS-CoV-2后NAFLD患者有可能存在持续高水平的转氨酶,远期进展为NASH的风险增加[39],因此有必要长期随访。
4 COVID-19与自身免疫性肝病
长期免疫抑制状态可能增加细菌和病毒感染机会,然而目前研究显示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hepatitis,AIH)患者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性与普通人群相似[40,41]。大型回顾性研究显示虽然AIH患者住院率较无肝病基础人群升高,但总体病程一致[42]。另有研究报道,AIH的重型新冠肺炎率、ICU住院率、全因病死率与其他类型慢性肝病无统计学差异[43]。对于AIH合并新冠肺炎患者,是否维持免疫抑制治疗、维持治疗泼尼松剂量对COVID-19严重程度无显著影响。维持免疫抑制治疗可此类人群新发肝损伤的风险显著降低,可能与该人群肝损伤发生机制有关,免疫抑制剂应用减少了药物性肝损伤或AIH复发的机会。与其他慢性肝病一致,AIH进展至肝硬化增加新冠肺炎患者不良结局的风险[42]。
目前,AASLD、EASL和APASL建议合并COVID-19的AIH患者,继续维持足量的免疫抑制剂,重型和危重型或伴淋巴细胞减少、细菌感染的COVID-19患者可依病情下调免疫抑制剂剂量,但需警惕AIH肝炎的复发[25-27]。
5 COVID-19与肝细胞癌〗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第6大常见癌症,位于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第4位,肿瘤致死病因第2位,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发性肝癌的75%~85%[44]。中国1590例COVID-19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癌症患者感染SARS-CoV-2后需要有创通气治疗的比例或病死率显著高于非癌症人群(39%对8%)[45]。与其他癌症相比,HCC患者更容易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因为在大多数HCC患者中,SARS-CoV-2引起的肝损伤可能使现有的肝炎病毒感染和肝硬化复杂化。依据肿瘤倍增时间,目前大多学者认可早期肝癌可推迟手术或射频消融等治疗2~4周,TACE治疗后病情稳定或进展缓慢的肝癌可推迟预定TACE治疗时间2~4周,中晚期肝癌可采取口服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策略。择期手术或肝癌破裂出血等情况下紧急手术采取严格防控措施[46]。此外,临床可充分利用可靠的HCC风险分层模型,筛选出HCC高危人群及治疗后高复发风险人群,制定合理的监测方案,若医疗资源和设备紧缺,AASLD和EASL建议监测时间可延长2-3个月[25-27]。
6 总结
存在慢性肝病基础的COVID-19患者面临更高的肝损伤发生率。不同类型的肝病合并COVID-19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死亡风险不同,其中合并肝硬化患者重型肺炎、肝功能失代偿和死亡事件发生率最高。对于此类患者,需在积极治疗COVID-19的基础上,注意原发肝病的变化,加强对重症患者肝功能的监测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