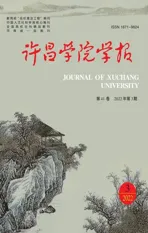儒家的自爱、爱人与受人之爱
2022-03-03付开镜董坤玉
付开镜,董坤玉
(1.许昌学院 魏晋文化研究所,河南 许昌 461000;2.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 100009)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是人生哲学的问题[1]1。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为核心,构建了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儒家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具有多个范畴,其中,仁是儒家最为核心的范畴。而儒家对仁的笼统解释就是爱人。就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而言,爱涉及自爱、爱人和受人之爱三个环节。学者对儒家爱人观念的论述甚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儒家自爱与爱人之关系或仁爱展开的,尤其是基于君主仁政思想讨论的,或未涉及儒家接受他人之爱的问题,更未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儒家接受他人之爱的思想,也是儒家仁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儒家的自爱、爱人结合成一个整体。可见,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较高的意义。
一、儒家自爱思想
儒家的自爱思想,包括自爱的本源、自爱的主要表现和自爱的目的三个方面。
(一)儒家自爱思想的本源
在人为何会自爱这一问题上,儒家强调仁者自爱,即儒家认为仁者才具有自爱的主观能动性,即本能。正如扬雄所说:“自爱,仁之至也。”[2]376儒家的自爱的概念与一般人爱护自己有着不同,儒家把自爱放在伦理范畴和政治范畴内进行考察,而不是放在生物属性上考察。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仁者自爱”所关注的则是“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What I ought to be?)的问题”[3]22-31。《论语》《孟子》中都没有直接讨论自爱的话题,但是,二人对修身的论述,其本质都是自爱。荀子对孔门弟子们的谈话涉及自爱的问题。《荀子》一书说: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4]396
据以上对话,孔子虽然把自爱当成人生之本,但似乎把“非仁者”排除在自爱境界之外了。这是否对全体民众不公?事实上,孔子强调仁者自爱,其意在于渴望社会上每个人,都要提高自我修养,都能成为仁人。孟子在这一点上比孔子有进步,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孟子的意思不是说,人都要去做天子,而是说,人都有成为尧舜的潜质,只要进行自我修炼,就能达到尧舜的精神境界。既然人人都具有成为尧舜的潜质,当然,人人也都有成为仁者的可能,当然也就具有自爱的本能了。
儒家的自爱不是自私。法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都是自私自利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所谓自爱,只有自利。在法家看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而非为了他人。
(二)儒家自爱思想的主要表现
儒家的自爱,首先表现在对自己身体的爱护上。在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是行为的主体,如果没有了生命,就不存在自爱和爱人了。因此,儒家在要求人们自爱之时,首先要求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礼记·哀公问》说:“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些都在说明爱护身体的重要性。身体是生命的根本,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因此,儒家认为重视自己的身体是处理所有社会关系的起点。
儒家的自爱,其次表现为重视心理的健康成长上。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儒家尤其重视道德修养与身体的关系,认为提高道德修养,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中庸》说:“富润屋,德润身。”所谓“德润身”,即认为心理人格与身体健康是正比的关系。
儒家自爱,再次表现在重视个人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上。思想修养的培养是儒家自爱培养的一方面,能力培养则是儒家自爱培养的另一方面。儒家设计了一套人生发展的规划,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齐家是修身的初步实践,治国是修身的中期实践,平天下是修身的最高实践。儒家重视人的能力培养,认为通过培养,人的能力可以得到提高。儒家从智力上把人分为三等,其一是上智,其二是下愚,其三是常人。孔子说:“唯上智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上智和下愚者人数不多,因此,占有人口绝对多数者,都要经过教育,方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理事能力。
儒家的自爱,最后还表现为爱护自己的声誉上。儒家的自爱为何要重视自己的名声?这是因为儒家追求精神价值。孔子强调要培养自己的君子人格,有了君子人格,就与小人有了本质区别。孟子强调要培养浩然之气,将原始生命(“体”)赋予德行的内容[5]40-48。儒家爱护名声与爱护生命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儒家认为,二者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生命。这是因为儒家认为人的身体可以死去,但是精神却可以长存。因此,为了正义,可以牺牲宝贵的生命,即如孟子所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为道而献身,并非不爱惜生命,而是因为以身殉道,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名声。
当然,除士之外,儒家还非常重视君主与官员的自爱。尤其要求君主应强化自爱修炼,把自己培育成亲民爱民的明君。君主既然为一国之主,理当成为全民的榜样,并承担着为国民谋求幸福的义务。孟子特别指出,如果君主一旦成为独夫的话,人民完全有理由杀之。孟子讲这样的话,不只是对君主的警告,而且还是对君主自爱标准的定位。儒家对君主自爱的定位,有其历史依据,即用历史上出现过的贤明君主作为标尺。同理,儒家对官员自爱标准的要求也很高,认为官员理当爱民,要选用贤能之人为官。也就是说自爱做得好的人,方有资格做官。
(三)儒家自爱的目的
儒家自爱的直接目的,是为爱人储备资质,而终极目的则是积累平天下的资质。儒家要求人人自爱,缘于儒家具有关怀社会的情怀,和为天下众人谋幸福的思想。儒家认为,人生要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就要一步一个脚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自爱思想,充满了集体主义的精神,认为集体的幸福远大于个人的幸福,与法家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完全不同。当具有修齐治平的资质时,也就达到了仁人的境界,“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可见,儒家自爱始于修身,终于平天下。
二、儒家爱人思想
儒家的爱人思想,包括爱人的理论基础、爱人的等级区分和爱人的终极目标等内容。儒家的爱人思想,在其核心范畴概念仁的含义中就体现出来了:“以仁为核心、以同心圆层层扩展的方式向外推衍,形成了由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敬、诚、勇、直、廉、耻、温、良、恭、俭、让 等众多价值(德目)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6]31-38“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解释仁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孔子与孟子的解释,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善性特征。故许慎解释仁说:“仁,亲也。”[7]161因此,“仁者爱人”处于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也是赖以存在的终极根源”[8]33-37。
(一)儒家爱人思想的基础
孔子对人性的探讨停留在性相近的阶段,但孔子尽管没有直接说明人性善良,却存在人性善良的思想。孟子直接提出了人性善良的理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熹解释孟子这句话时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9]238朱熹的意思,就是认为人之善良,源于天地善良,即人之善良,源于天性。孟子又把他的人性善良理论具化为“四端之心”说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用人的四体来解释其“四端”说,强调了人性善良的本能特质。人性既然善良,当然会去爱人。
(二)儒家爱人思想的前提
儒家认为,社会上所有人都需要有人去爱。因为无论从人的自然属性还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讲,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属于社会的弱者,需要他人的关爱方能生存下去。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时(《礼记·礼运》),这个社会才算和谐。而社会上的强者,他们是向弱者施爱的主体,但是,他们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即得到他人的爱戴和敬重,方可以享受到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意义带来的心理的快乐。
(三)儒家认为爱人是义务和修身的重要方式
儒家认为爱人不仅是人生的义务,而且也是实现自爱的手段和目的。首先,儒家把爱人当成人生的义务看待。儒家认为血亲之间的爱,完全出于义务。如子女对父母尽孝就是天然的义务:“夫孝,始于事亲。”(《孝经·开宗明义章》)当然,把血亲之爱拓展到社会领域,也就有了主政者对子民的爱和子民对主政者的爱,以及普通民众人之间的爱。主政者把子民当成了自己的子女而施以爱护;同理,子民主政者当成自己的父母而施以爱戴。如此,就完成了爱从血亲到非血亲的传递过程。其次,儒家之所以主张爱人,在于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完人的使命,即爱人是其天然的职责。如果不能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人生便不完满:“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
(四)儒家爱人思想的等级差异
“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10]82。墨家提出的兼相爱思想,是一种社会的大爱。远古时期,人们只知母而不知父,天下一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兼爱当然可以大行其道。但是,到了家天下的时代,兼爱便与血亲关系相悖起来。如所周知,血亲之间建立了互相帮助而得以维系家庭成员生存和延续的关系,因此,在家庭内部,血亲之间的关系必然比非血亲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为地要求非血亲之间做到兼爱,很难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孟子批评墨家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儒家要求“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强调爱分等差。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孟子也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儒家认为把最多的爱,首先奉献给父母,属于天经地义。这就是儒家的爱有差等观,也是“儒家的伟大发现”[11]1-5。事实上,儒家并没有直接提出爱有差等,但“其‘仁爱’伦理精神强调的‘爱由亲始’到‘泛爱众’的实质就是差等之爱”[12]10。儒家的等差之爱,包括所爱程度的等差和施爱时间的等差。
在家庭内,儒家的爱表现为孝悌。孝是子女对父母之爱,悌是弟对兄之爱。不过,孝的前提是因为有父母之爱在先,悌的前提是有兄之爱在先。故而孝悌是双向的互动。同理,兄弟之间的悌,也是具有爱与受人之爱的对等关系存在。
在家庭外,儒家又强调了泛爱的意义。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又曾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是赞赏(《礼记·礼运》)。儒家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也说明儒家认为对亲人的爱,完全可以推及至异姓非血亲者身上。当然,儒家的爱人以孝悌对内,以信义对外。儒家的信义观念,实为孝悌的延伸。对于没有血缘关系者,因为存在交往,故而也当有交往的规则,这就是信义。信的本质,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义的本质,是公平合理,是不贪占对方的经济利益。儒家要求在生活实践中爱人,做到言行一致。这也是儒家的“诚”。诚是言行一致的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儒家尽管承认爱有差等,强调把血亲之爱放在前头。但是,这不能说明儒家的爱具有完全的自私性,因为爱具有空间的距离性和社会成员关系远近的不同,其必然的结果是给予亲人的爱最多,给予他人的爱较少;给予亲人的爱在先,给予他人的爱在后。同理,报答的爱也因此而多少有别,先后有别。可见,儒家爱人的等差性,是“合乎正义原则的不平等”,[13]28-33是“以孝亲为普爱之基”[14]222,由内而外有所不同,即:“门内之爱,恩掩义;门外之爱,义掩恩。”(《礼记·本命》)
(五)儒家践行爱人思想的方法是“克己复礼”
儒家认为要去爱人尤其是把亲亲之仁扩大到泛爱程度,就要从自身做起,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当然要克制自己和战胜自己。克制自己和战胜自己的是不当的欲望,而克制自己和战胜自己的尺度是礼。因此,克己复礼便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志表现在其中。朱熹称赞说:“克己复礼,乾道也。”[9]134所谓乾道,即《易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了克己复礼在爱人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对于践行仁的具体方法,《论语》曾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还认为,爱人需要具有君子人格:“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六)儒家强调了主政者爱人的政治意义
儒家认为爱人并不只是个人修养之事,更是国家主政者的大事。因此,儒家把爱人的行为政治化了,甚至把爱人的重心放在国家政治核心位置之上,即君主身上。儒家认为国君是能否爱人最为重要人物。国君制订的各项政策和制度,都要以爱人为中心,即实施仁政,方才算是明君。故儒家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圣人“重社稷故爱百姓”(《礼记·大传》)。因此,“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
而官员爱民是君主爱民的延伸。如果君主和官员都具有仁爱思想和爱民行为,上行下效,百姓也就会爱戴其君主和官员了,这个社会就会充满仁爱,国家也就很好治理了。因此,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大学》也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儒家之所以重视主政者的爱人问题,在于君主和官员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拥有让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的资质,而且他们的政治行为具有社会示范意义。
相反,如果君主和官员都对百姓残酷剥削和压榨,老百姓也就不可能爱戴他们,而只会起而造反。为了让君主和官员对百姓多加施爱,儒家重视抑制“突出于庶民之上的阶层利益”[15]194。可见,儒家把基于个人自爱、爱人以及接受人之爱的理论上升到国家政治的理论境界。
三、儒家受人之爱思想
儒家政治目标的远景,是让天下所有人能够幸福生活。因此,儒家特别关注社会弱者,多从弱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和弱者接受施爱后的感恩心理对建立和谐社会意义的角度,来观察受人之爱的问题。
(一)儒家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是爱的对象,而弱者是重点
从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来看,有爱的主体,就有爱的客体。如果人人都只去爱人,而没有爱的对象,也就不可能实现“爱人”和“被爱”的整个活动。儒家认为,社会上所有人都是爱和被爱的对象,但是,儒家特别强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接受他人之爱和君主之爱的重点。
从人的生理发展来看,人的一生有幼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五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人的生存能力是不一样的。人在幼年和老年时,基本上都需要接受他人之助方可生存。人在没有能力给予他人施以物质之爱时,只能以接受他人之爱为主,尤其以接受亲人之爱为主,方可生存下来。而人在处于青壮年时期,一般都具有了完全的自我生存能力,并且具有了充足的帮助弱者生存的能力。在这样的时期,人一般都能帮助他人,即实施爱人行为。
从人的智力和体力来看,不同人的智力和体力存在明显差异。智力高者和体力强健者,多是社会的强者,因此,他们可以多付出,也就是能够在爱人方面超过普通人爱人的程度。相反,多数人的智力和体力并不突出,因此,他们付出的爱当然要小于智力和体力超常者的付出。只有智力高者和体力强健者的多付出,社会上的弱者方可得到较为充裕的爱。
从影响人的身体的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来看,有些人是天然的残疾者,有些人是后天的残疾者,这些人即使处于青壮年时期,也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们也需要得到他人之爱方可生存下去。
从稳定社会秩序来看,要建立和谐社会,社会的弱者当然具有获取社会帮助的权利,社会强者当然具有帮助社会弱者的义务。而代表国家的君主,是社会强者的最高代表,其帮助社会弱者的义务最大。儒家认为爱护社会弱者意义重大。《礼记·乐记》说:“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子路曾问孔子之志,孔子的回答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由此也可说明,儒家的仁爱的视野,总离不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与法家眼睛只盯着君主决然有别。孟子与梁惠王交谈时有这样的话:“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又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又劝说梁惠王实施仁政,让“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孟子·梁惠王下》),也可说明社会存在大量弱者,是国君理当爱护的重点对象。
从人的心理需要角度来看,即使是社会的强者,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关爱。当然,他们所得到的关爱,重在精神慰藉,而非物质慰藉。所谓社会强者,上指管理国家的君主和官员等社会上层,下指具有养家糊口能力的平民百姓等社会下层。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较大。他们需要得到的,是社会民众的爱戴,或者家人的爱戴。尤其是社会上层,他们多希望通过“与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而获得身心的快乐。
(二)受人之爱的类别
从受爱的来源看,可分为三种,一是接受亲人之爱,二是接受非亲之爱,三是接受主政者之爱。
接受亲人之爱,在儒家看来天经地义。首先,父母对子女的爱,源于血缘。因此,子女接受父母之爱,具有正当性和义务性,即“为人父止于慈”(《大学》)。其次,子女对于父母的爱,也源于血缘,具有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目的,也具有正当性和义务性,即“为人子止于孝”(《大学》)。再次,接受其他亲人之爱,也具有血亲的义务成分。在父母或子女不存在时,其他亲人理当成为父母或子女的替代人。接受亲人之爱,在于促使自己的身体得到健康成长,同时提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为自爱和爱人奠定基础。因此,接受亲人之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理,一个人在年老或残废之时,也要通过接受亲人之爱,方可存活下去。
接受他人之爱,也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接受亲人之爱,足以保障人的身心的成长和安全。但是,人们在社会中,有时也需要接受非亲人之爱,方可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儒家认为接受非亲人之爱,也具有社会合理性。这是因为,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扩展到血缘成员之外,这就是儒家的义。通过非血亲(如乡邻)的施爱,弱者也可获得生存的基本物资,而得以生存下去。
接受主政者之爱,最受儒家重视。儒家认为,社会下层民众,都是主政者施爱的对象,主政者都具有施爱于民的重要义务。尤其是君主,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可以通过制订国策,让普通人得到政府的关爱。《礼记·王政》载:“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周文王因为“善养老”受到伯夷、太公的追随,孟子对他赞扬不已。在儒家仁爱思想中,民众与主政者的关系,如同子女与父母。如果主政者亲民爱民,民众就以父母亲之爱之,即:“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泂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大学》)。
四、儒家自爱、爱人、受人之爱的关系与意义
当儒家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之时,就已指明了所爱的对象。因此,儒家不只是要求人们自爱和爱人,还同时主张接受他人之爱。
(一)自爱是爱人的基础
儒家认为,自爱是爱人的基础。梁启超说:“仁义二字,为孟子一切学问总宗旨。”梁氏又引用董仲舒的话说:“仁者人也,义者我也。”[16]433可见,儒家的爱人之“仁”,与有“我”存在的“义”,合为一体。义是处理“我”与他人关系应尽的准则,即处理如何“爱人”关系的准则,而“我”是主宰身体的主导,“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我们凭借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17]123。
(二)爱人是自爱的手段和目的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可见,儒家认为人应该把爱人和自爱当做一件事情来对待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只有通过不断的爱人的实践,方才可以成为完人,方才具备了平天下的资质。因此,爱人就成为自爱的手段和目的,正如北宋张载所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18]32事实上,儒家的爱人,也是“变相爱己心”的体现[16]433,因为自己能够爱人,才会得到他人之爱。这是爱的互相传递的必然结果。
(三)受人之爱具有积累自爱和爱人资质的目的
儒家的自爱与受人之爱并不矛盾。儒家的自爱,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受人之爱,当是自爱的必要补充。如前所述,人都会存在一个需要他人关爱和帮助才能生存和成长的阶段,或者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身体遭受破坏而不能自存,在这样的情形下,都需要接受他人之爱,方可积累自爱和爱人的基础。儒家强调了爱人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证明了接受他人之爱的合理性。在爱人和受人之爱这一对关系体中,儒家特别强调爱人的意义。这是因为,爱人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爱人的一方,总体上处于社会强势地位,而受人之爱的一方,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在爱人和受人之爱的关系上,儒家强调爱人的重要意义,意在倡导以强助弱,展现社会正义。
(四)儒家用自爱、爱人和受人之爱构建了一个互为因果的统一体
儒家的自爱、爱人与受人之爱,本于天性,同时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通过修身,可以提高自爱、爱人和受人之爱的境界。
儒家的自爱、爱人、受人之爱不可分割。没有自爱,就没有爱人;没有爱人,自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受人之爱,也就难以积蓄自爱和爱人的潜质。
儒家自爱的直接目的是为爱人奠定基础,爱人是自爱的必然结果。没有人接受他人之爱,爱人也就没有了对象。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爱的对象,而弱者是接受社会之爱尤其是主政者之爱的重点。接受他人之爱,有助于自爱的健康发展,也是对自己爱人行为的回报。
儒家的自爱、爱人与受人之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个人来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存在自爱、爱人和接受他人之爱的不同阶段,或者同时出现自爱、爱人或接受他人之爱的状况。因天赋和所处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自爱、爱人和接受他人之爱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每个人都具有自爱、爱人和接受他人之爱的权利和义务。做好了自爱,方可去爱人;做好了爱人,也就有了受人之爱的充分理由。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运行,在血亲家庭爱的循环中表现极为显明:第一环节:父(母)之施爱于子,子之受爱于父(母)。第二环节,父(母)年老,必将得到子之尽孝回报。第三环节:子又为父,子又生子,子开始承担起父慈的义务。第四环节:子年老,开始享受其子尽孝的义务。因此,儒家的自爱、爱人和爱人之爱,就是如此循环,没有穷尽。而在家庭之外,儒家通过“义”等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无血缘关系人族群中构建出与家庭内部相似的自爱—爱人—受人之爱的循环关系。儒家希望通过全民自爱、爱人和受人之爱,把整个社会打造成一个无时无刻都充满了“仁者爱人”的乐园。
就国家来说,这种自爱、爱人、受人之爱的过程主要通过君主的主导行为表现出来。儒家特别重视国家层面君主的自爱和爱人,总希望君主通过自爱的品格修炼,践行爱人之德,在全国推行仁政,达到君民的共赢和社会的和谐。如果实施了仁政,就会出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的和谐局面。百姓接受了来自君主的爱护,便成为支持君主的铁杆拥护者,君主因而也获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如此一来,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可享受到社会和谐带来的福祉。因此,儒家自爱、爱人和受人之爱思想的最大落脚点,在庙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