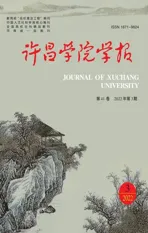“太子畏之”究竟畏何?
——兼论“白虹贯日”在荆轲故事中的内涵
2022-03-03张文东韩钦羽
张文东,韩钦羽
(1.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2.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汉初文学大家邹阳在其名篇《狱中上梁王书》中曾用到荆轲刺秦的典故,其中“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一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后世读者不同程度的误读,即对该句中“太子畏之”——燕太子丹究竟所“畏”何事,历代注家乃至当代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由于邹阳的这篇上书见录于《史记》《汉书》《文选》等巨帙,是以对“太子畏之”意见的分歧多体现在对这几部巨帙的注解之中,尤以应劭、如淳、裴骃、王劭、颜师古、李善、司马贞、李周翰、王先慎等为代表;当代学者中,则除了李学勤先生对该问题有所关注外,就笔者目力所及,各注本尚未见相关讨论。古注纷纭莫一,学勤先生对该问题的说明有所未照,今不揣浅陋,拟就历代注家及当代学者对“太子畏之”的两种理解进行考察、厘定,并从“白虹贯日”的星占学内涵及读者对天文叙事的接受来探讨理解致误的原因,庶望有助于读者对邹阳上书的透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较清晰地看到荆轲故事相关情节的发展脉络。
一、问题缘起:“太子畏之”歧义的产生
邹阳为西汉文景时期名士,初事吴王刘濞,后吴王阴谋叛乱,邹阳谏阻而吴王不听,是以离开吴王,成为后来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在梁期间,邹阳因“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1]2343遭忌于梁王宠臣羊胜、公孙诡,并被二人谗害下狱,因此在狱中写下这篇著名的《狱中上梁王书》。其篇首云: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2]2993
该书篇首特意用反语刺激梁王,然后列举荆轲、白起两个典故,并将二者与邹阳自身当时的处境对比,反复陈说自己的忠诚同荆轲之于太子丹、白起之于秦昭王一样,“尽忠竭诚,毕议愿知”,恳求梁王不要因为谗言的蒙蔽怀疑自己的忠心。梁王看到这封上书之后,立刻让人将邹阳从狱中放出,并奉为上宾。
如果读者对邹阳所列举的两个典故比较熟悉,那么这段文字其实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邹阳用典时对两个故事做了高度简洁的概括,造成后来读者不同程度的误读。尤其是“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一句,其中“太子畏之”,就引起后世诸多注家和学者的误会,以致对其解释众说纷纭。如李学勤先生便提出这样的疑问:“《史记·邹阳传》的文字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白虹贯日为燕丹表可克之兆,他见了应当大为欣悦,何以‘畏之’?”[3]即:既然“白虹贯日”这一天象预兆着荆轲刺秦王的成功(详后),为何太子丹见到“白虹贯日”不是高兴反而是担心害怕呢?这个疑问若想得到解决,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太子畏之”究竟畏何?
邹阳所用荆轲典事,裴骃《集解》引应劭之语有所说明:“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2]2993也即是说,由于荆轲的精诚感动了上天,上天便以“白虹贯日”之象昭示荆轲的忠心。而所谓“太子畏之”,是指当时燕太子丹厚养荆轲,却久不见其有行意,于是对荆轲是否真的愿意去行刺秦王产生了疑虑,其所“畏”,乃畏荆轲不能诚心用事也,是对其忠诚度的怀疑。正如《索隐》引王劭的说法:“轲将入秦,待其客未发,太子丹疑其畏惧,故曰畏之。”[2]2993荆轲刺秦的故事已为人所熟知,燕太子丹厚养荆轲欲其西刺秦王,而荆轲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寻找信物和等待帮手)没有立即行动,结果引起太子丹的怀疑。这一情节在荆轲故事文本中记载甚明,如《战国策·燕策三》载:
荆轲有所待,欲与(秦武阳)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4]1790
太子丹对荆轲的怀疑和荆轲因太子丹的这种不信任而带有愤怒情绪的回答被刻画得非常细致,“太子畏之”的“畏”明显对应的是“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这一情节。《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2]3073与佚名者撰《燕丹子》“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5]42等记载与《战国策》一致。
邹阳用荆轲典事的本意,我们从与之并列的“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昭王疑之”也可以得到证明。《汉书·邹阳传》颜师古引苏林注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昴。”又引如淳注曰:“太白,天之将军。”[1]2344《史记索隐》引如淳注作“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2]2994。二十八宿中的昴星是赵国的分野,“太白蚀昴”的天象昭示着白起“欲遂灭赵”的计划将获得成功,然而即使白起的忠诚能令上天垂象,却仍被秦昭王怀疑,乃至最终被赐死。
唐人颜师古对邹阳取荆轲典故的用意其实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其曰:“精诚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义亦如之。”[1]2344同秦昭王怀疑白起一样,太子所以“畏”,正是因为“不信”,而非其他。
通过荆轲、白起的故事所本,结合《狱中上梁王书》上下文,邹阳的意思已经十分明了:昔日荆轲、白起对太子丹、秦昭王的忠诚即使感动了天地尚不能使燕、秦二主完全信任,现在自己的忠心又怎样才能让梁王明白呢?其本意是借用古人的故事向梁孝王表明自己“尽忠竭诚”,希望梁王“熟察之”,不要因为旁人(羊胜、公孙诡)的谗言怀疑自己。
如上所述,弄清楚了太子丹所“畏”何事——“既然白虹贯日为燕丹表可克之兆,他(太子丹)见了应当大为欣悦,何以‘畏之’?”——这个问题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行文至此,“太子畏之”的歧义——“认为太子丹担心刺秦不能成功”尚未完全抛出,这种歧义盛于唐代的注释家并呈后来居上之势。歧义的源头来自相传为刘向所编《列士传》(或作《烈士传》)中荆轲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集解》最早引用这个版本的故事为“太子畏之”作注脚,《索隐》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解释,其云:
《烈士传》曰:“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后闻轲死,事不就,曰‘吾知其然’。”是畏也。又王劭云“轲将入秦,待其客未发,太子丹疑其畏惧,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2]2993-2994
司马贞“是畏也”,认为太子丹“畏之”的原因是太子丹“见虹贯日不彻”,“不彻”即意味着刺秦不会成功,所以太子丹在荆轲失败之后才说“吾知其然”。司马贞稍前的李善和大略同时的李周翰在注《文选》时持同样的观点,李善曰:“畏,畏其不成也。”[6]727并引《列士传》为证。李周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往刺秦王,使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而畏其事不成。”[6]727李学勤先生也认可他们的观点,他在提出“既然白虹贯日为燕丹表可克之兆,他见了应当大为欣悦,何以‘畏之’”的疑问后,认为《史记》《汉书》的注释家提出的种种解说“都难满意”,《史记索隐》给出的解释才是“惟一合理的”,并总结说:“据此,燕丹相气,看到白虹贯日而不彻,是荆轲谋刺不成的征兆,这样解释,便使故事前后合乎逻辑了。”[3]
由上可见,正是刘向《列士传》有关燕丹相气,见到“虹贯日不彻”的相关记载,才造成了后来注释家在解释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的“太子畏之”时产生歧义。与前文我们理解的“太子畏之”是“疑荆轲改悔”,畏荆轲不去刺秦不同,李善等人认为“太子畏之”是“畏荆轲刺秦不能成功”,且司马贞认为前者“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后者才是“惟一合理”的解释。本来文意甚明的典故何以产生如此歧义?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白虹贯日”的内涵做一探究。
二、误读溯源:“白虹贯日”星占学内涵的影响
“白虹贯日”是我国历代天文志、律历志和星占类著作记载颇多的一种天象。与“彩虹”无关,“白虹”是日旁的一种云气,《史记·天官书》将白虹置于“日晕”之属,并称:“白虹屈[尾]短,上下兑(锐)。”韦昭注曰:“短而直。”[2]1586-1587《尚书考灵曜》郑玄注曰:“日旁气白者为虹。”[7]38蔡邕《月令章句》云:“蜺常依蒙浊见日旁,白而直,曰白虹。”[8]72《后汉书·郎传》释“白虹贯日”之“虹”曰:“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9]1064可见白虹是太阳旁边颜色纯白、短而直锐的一道云气。而将君主喻为“日”则是古人的普遍观念,所谓“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10]317。由于君主与“日”对应,在星占学上,“日占”往往与君主之休咎密切相关,《天官书》云:“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2]1594白为丧色,在五行理论中又对应西方兵相,“色纯白”和“短而锐”是“白虹”最主要的两个特点,短、锐以“贯”日,已经基本奠定了“白虹贯日”天象为不祥之兆。事实上,星占学中“白虹贯日”的占辞对君主而言确实极为凶险。如:
白虹出,邦君死之。(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11]128
虹贯日,天下悉极,文法大扰,百官残贼,酷法横杀,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狱多怨宿,吏皆惨毒。国多死孽,天子命绝,大臣为祸,主将见杀。(《春秋感精符》)[12]523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晋书·天文志》)[10]334
虹霓近日则奸臣谋,贯日客伐主。(《开元占经》引《京氏对灾异》)[13]980
白虹贯日,臣杀主。(《开元占经》引《荆州占》)[13]981
类似的占辞在史书《天文志》及星经类著作中不胜枚举。从这些占辞足以见出,“白虹贯日”天象的出现,基本上兆示着“客伐主”“臣杀主”事件的发生,将会产生“邦君死之”“天子命绝”“主将见杀”的后果。
回到《狱中上梁王书》,显然,邹阳使用“白虹贯日”正是基于其星占学内涵,这与后面的“太白蚀昴”形成对称。而恰恰正是白虹贯日这种星占学内涵造成了后来读者理解上的歧义。前面提到,邹阳用典是对整个事件的高度概括,其“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表述极容易令人断章取义,认为“白虹贯日”是“太子畏之”的原因,从而产生“既然白虹贯日为燕丹表可克之兆,他见了应当大为欣悦,何以‘畏之’”的疑惑。或许有人会问:同样的用法,“太白蚀昴,昭王疑之”为何没有引起后人的疑惑?解释这一问题,还必须回到荆轲刺秦和白起灭赵两个故事本身:“太白蚀昴”虽然预兆白起灭赵定能成功,但事实上,白起“欲遂灭赵”的想法从未得到实施;反观荆轲刺秦,则是在事实上付诸行动的。所谓“占验”,既要有“占”,即事前根据某个征兆进行预测;又要有“验”,即基于事实的事态发展与事前预测吻合。在占卜体系中,“占”“验”无疑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不可或缺:有“验”无“占”,则失去了人们赋予占卜的预判事态发展的功能;有“占”无“验”,则缺乏事实根据,“占”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乃至消失殆尽。作为星占的“白虹贯日”同样如此,它对君主极为凶险的占辞需要事实的验证,这从历代史传作品的天文叙事(天文占卜的预叙模式)中能窥其壸奥,如:
(汉孝献帝初平元年)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壬辰,白虹贯日。……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后汉书·献帝纪》)[9]369-370
(晋孝怀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帝遂见虏。(《宋书·五行志》)[14]1018
海西公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日,日晕,五重。十一月,桓温废帝。(《晋书·天文中》)[10]344
(后唐)应顺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贯日,是时闵帝遇害。(《旧五代史·天文志》)[15]1857
类似的记载不一而足。从叙事模式可以看出,凡有“白虹贯日”天象发生者,君主或遭兵叛,或遭大臣胁迫,甚至被废或者被杀。当然,以现代人看来,这自然是无稽之谈,所以不得不说,叙事者的这类记载有意牵合天象与人事,以求得历史事实与星占占辞一一对应,使其若合符契。在这种叙事者叙事意图和阅读者心理期待互动的背景下,当读者接收到“占”的信息时,必然产生对“验”的预期。而在邹阳所用的两个典故中,“白虹贯日”和“太白蚀昴”这两个星象都没有在现实中应验,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白起之事因从未实施,所以读者的期待被打断;而荆轲刺秦则已经付诸行动,如果再不能与天象对应则似乎显得不符常理,是对“占”—“验”叙事模式下天命观的挑战。所以,在多数读者看来,荆轲刺秦既然有“白虹贯日”预兆其成功,那么他后来的失败则与星占结果相违,读者的预期无法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列士传》所载荆轲故事版本中“白虹贯日不彻”的天象却正好是“荆轲刺秦未果”的预兆,能够完全满足读者期待,也能够完美解释星占征兆与历史事实的对应关系。这样也就无怪乎注释家们对“太子畏之”产生歧义,甚至认为《列士传》所载版本的解释优于“太子丹畏荆轲不发”了。
三、折辩结论:太子丹实畏荆轲“不去刺秦”而非“刺秦不成”
正如我们开篇所论,若真如李善、司马贞等人所释,那邹阳用这一典故其意何在?其与白起“太白蚀昴”事又如何联系?这样理解只会造成文章前后文意的龃龉,正如《汉书补注》中王先慎所言:
先慎按,荆轲未去,太子屡疑之,事详《国策》。畏之者,畏其不去也。白虹贯日,乃轲发后事,阳特举以见轲之精诚达天,取与卫先生之事为配。如、李泥于正文,以“见虹贯日不彻,知事不成”释此文畏字之义。小司马转谓说长于王,不思与下文“信不谕主”情事不合也。[16]3809
虽然王先慎将如淳的注释同李善等归为一类欠妥(如淳仅注“白虹,兵象,日为君”,并未以“白虹贯日不彻”或“畏其不成”为释),称“白虹贯日,乃轲发后事”同样坠入《列士传》的叙事模式而有自相矛盾之处(王氏所云“白虹贯日,乃轲发后事”源于《列士传》“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的记载,矛盾之处在于王氏既然认为“畏之者,畏其不去”,就应该将“白虹贯日”视作荆轲“去”之前的事,如果认为白虹贯日是荆轲出发之后的事情,那么太子丹所畏同样指向“畏事不成”,所以王先慎这里用《列士传》文字不当),但他所说的“畏之者,畏其不去”、“阳特举以见轲之精诚达天,取与卫先生之事为配”、李善小司马的解释“不思与下文‘信不谕主’情事不合也”却得其大端,是邹阳用典的本意。
考《战国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刺客列传》,荆轲刺秦均无“白虹贯日”之说,而《列士传》传为刘向所编(有别于《战国策》,是对战国时期典籍的整理),刘向于邹阳较晚,《列士传》所载“荆轲发后,太子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之事或另有所本,其于荆轲故事本身则增其奇趣,而注释家若用之解释邹阳书中所用之典则成画蛇添足了。
综上所论,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的“太子畏之”,畏的是“荆轲不去刺秦”,而非“荆轲刺秦不能成功”。之所以众多注释家产生后一种误读并认为其优于前者,主要是在天文叙事“占”—“验”模式下,对“白虹贯日”(或“白虹贯日不彻”)星占内涵产生阅读期待而未细究文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