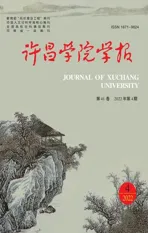《秦王破阵乐》在古代日本的传播及其变革
2022-03-03王文清
王 文 清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作为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秦王破阵乐》曾经在东亚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截至目前,国内有关《秦王破阵乐》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创作来源、历史变迁以及乐曲本身,较少论及对外传播的具体情况(1)目前学术界有关《秦王破阵乐》创作来源与历史变迁的研究居多,历时性研究如欧阳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杨宪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寻根》2000年第1期;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怡康:《唐〈破阵乐〉考释》,河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另有程雅娟:《“军权”与“戏饰”之融合——〈信西古乐图〉中的唐代武舞服饰研究》,《装饰》2011年第10期,从服饰构成角度分析《秦王破阵乐》的舞蹈服饰;李丹婕:《〈秦王破阵乐〉的诞生及其历史语境》,《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结合《秦王破阵乐》的由来、特色与功能,考察其诞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环境。而有关《秦王破阵乐》对外传播史少有专门研究,但在部分古代乐舞交流史的研究专著中有所提及,如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王克芬、江东:《日本史籍中的唐乐舞考辨》,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本文将视角扩展至古代日本,从唐代乐舞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秦王破阵乐》在古代日本的传播情况,初步展示古代日本对唐代《秦王破阵乐》的接纳及产生的衍变,以期对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古代日本乐舞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秦王破阵乐》的初创
有关《秦王破阵乐》产生的时间,通常认为在武德三年(610)左右秦王破刘武周时,地点在破刘武周所在地河东(今山西)。谈及《秦王破阵乐》的最初创作者,虽有争论,但学界通常围绕“军中将士”和“民间百姓”这两个行为主体展开论述。在笔者看来,对于此类具有政治内涵的创作作品而言,不同阶层的创作者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同。就此曲而言,若由将士自发创作,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将士的忠心、军心的稳固、士气之盛;若是百姓自发创作并传唱于坊间,便可体现百姓当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对政治形势的态度。因而笔者现以此曲创作者身份为划分,做一分析。
持“军中将士论”者认为此曲最初流传于军队中,是军中将士为太宗所作。如学者王安潮认为,这部作品是为表现李世民于武德三年在山西谢州、并州一带大败叛军刘武周,军中士兵中相颂秦王军功之歌,这是“破阵”之乐的源头[1]。持此观点者所据史料是最早记录《秦王破阵乐》的《隋唐嘉话》:“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曲,后编乐府云。”[2]18另《新唐书·礼乐十一》中载:“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3]467-468若论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可见《音乐百科辞典》中《秦王破阵乐》的条释:“《破阵乐》原是隋代(581—618)军歌。唐武德庚辰年(620),秦王李世民(627—649在位)击败叛将刘武周,将士们把新词填入《破阵乐》旧曲,以歌颂秦王功德,在庆功之际唱出,名《秦王破阵乐》。”[4]487即《秦王破阵乐》最早源于隋代军歌,是在隋旧曲《破阵乐》基础上填词改编而成的。
持“民间百姓论”者则认为《秦王破阵乐》为唐代民间所创的歌谣,是百姓歌颂唐太宗丰功伟业而传唱的。这种观点所据史料如《唐会要·中·破阵乐》:“贞观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之曲。太宗谓近臣曰:‘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民间遂有此歌。’”[5]612《旧唐书·音乐志二》曰:“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6]715以及《通典·乐六》载:“太宗为秦王时,征伐四方,人(民)间歌谣有《秦王破阵乐》之曲。”[7]3718据此推断《秦王破阵乐》最早为百姓所作的民间歌谣。
除以上两种传统说法外,杨宪益先生的“外来传播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在著作《译余偶拾》中提出《秦王破阵乐》很有可能从突厥传入中国,其源头是古罗马的武舞——“突罗戏”。他认为,因古代称罗马为“大秦”,所以“秦王”非唐太宗而是罗马皇帝,而“破阵”是“突罗戏”别称“霹雳戏”的音译;又因古代我国与东罗马存在文化交流,而突厥又是重要媒介,所以罗马武舞很有可能经突厥传入中国[8]19。
就上述观点而言,第三种说法虽新颖,但仅是简单论证了其可能性,史料依据太少,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在笔者看来,据《唐会要·中·破阵乐》中太宗对近臣所说的一席话,“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民间遂有此歌”,可推断出唐太宗在武德元年(618)挂帅出征到武德九年(626)登基称帝这段时间内,此曲已在民间创作传唱。另据《新唐书·礼乐十一》记载:“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隋唐嘉话》也称:“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曲》,后编乐府云。”可知在武德三年左右秦王攻破刘武周平定北方后,军队中已存在此曲。若论此曲最早的创作者是民间百姓还是军中将士,现有史料还不能确定。但据现有材料可以推测,在武德三年至武德九年这段时期,已存在此类时事政治题材的乐曲创作,并且这些乐曲是由百姓和军士创作的主题一致的不同乐曲。
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秦王破阵乐》并非一种乐舞,仅仅是民谣形式,而最初的这种只歌不舞的《秦王破阵乐》也非唐太宗本人所创[9]4。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之曲。”可知,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即位后此曲便在宫廷首次演出。既然这时《秦王破阵乐》已成为在宫廷展演的侍宴乐曲,必然不可能仅是简单民谣,而是由宫廷乐工加工而成的内容更加丰富、规模更大的《秦王破阵乐》。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展演的《秦王破阵乐》还没有舞的部分。在唐太宗结合战争形势绘制《破阵乐舞图》之后,《秦王破阵乐》才加入了舞的部分[9]5。可见唐太宗对这一歌功颂德的武舞极为重视,《秦王破阵乐》也从此逐渐具备了唐代大曲的规模。
二、唐乐东传与日本对《秦王破阵乐》的接纳
早在日本飞鸟时代,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刚刚建立,政权不稳,文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而这一时期的中国隋朝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其强大的国势引起日本统治者关注。圣德太子确立文化立国政策,并恢复了与中国的交流,以摄取新文化。到了奈良时代,日本更是大量吸收并模仿中国唐代文化,自630年舒明天皇第一次派遣遣唐使,至895年的二百六十余年间,日本朝廷曾计划向中国派出20次遣唐使,其中成行的有13次。可见中日交流之频繁。虽然遣唐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组成,但都是经过日本朝廷严格筛选的学问渊博或有一技之长之人,其中便有专业的乐师和舞者。此外还有漂洋过海的商人和前往日本的中国人,他们都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高度繁荣、形式丰富的唐代乐舞随之东传,在日本的艺术土壤上生根发芽,其中便有被称为唐初第一部大曲的《秦王破阵乐》。
据笔者研究,在大多数有关《秦王破阵乐》的研究专著或论文中,谈及《秦王破阵乐》传入日本者,多引《大日本史》对《皇帝破阵乐》的记载,认为《秦王破阵乐》是文武天皇时,由遣唐使者粟田真人传入的[10]10。如《山西音乐史》:“《秦王破阵乐》在当时名气很大……武则天时期日本遣唐使节粟田正人将其带回了日本。《秦王破阵乐》传入日本后,被译为《皇帝破阵乐》。”[11]138若论此观点是否成立,我们就先要讨论《大日本史》所载的《皇帝破阵乐》和唐代歌颂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是否为同一乐舞。
持两者所指为一论者,主要有以下两种逻辑:其一,认为《秦王破阵乐》传入日本后,被译为《皇帝破阵乐》;其二,认为《秦王破阵乐》和《皇帝破阵乐》所指相同,因传入时唐太宗为秦王,故称《秦王破阵乐》,后来太宗即皇帝位,改称《皇帝破阵乐》[12]154。也有学者认为两者所指并不为一。如王克芬认为《皇帝破阵乐》与唐代歌颂唐太宗的《破阵乐》非同一乐舞,应为唐燕乐中“立部伎”八部之一的《安乐》,而《信西古乐图》所录的另一个《破阵乐》,即《散手破阵乐》也似为《安乐》[13]343-344。
据笔者搜集到的史料,日本方面有关《皇帝破阵乐》和《秦王破阵乐》的直接文字记载可见《大日本史·礼乐志》和《乐曲考》。另在《信西古乐图》和《舞乐图》中大量保存着先后传入日本的唐乐舞图文资料,从中可见《皇帝破阵乐》和《秦王破阵乐》的部分舞蹈形态。综合分析后,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尚且存疑,后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有以下三个理由:首先,就翻译本身而言,《秦王破阵乐》中的“秦王”和《皇帝破阵乐》中的“皇帝”的日语发音并不相近反而差别很大,且写法上也有很大差别,很难想象是翻译本身的原因使同一乐舞产生不同名称。其次,当时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乐小调有48种,其中有归入壹越调曲的《皇帝破阵乐》和归入乞食调曲的《秦王破阵乐》(2)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植村幸生校注,日本平凡社2015年版,转引自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最后,日本《乐曲考》载:“(皇帝破阵乐)此曲或言唐太宗所作,又言唐玄宗所作,不确切。其名亦称《武德太平乐》,又称《安乐太平乐》,在唐朝不闻此名。”[14]25在《大日本史·礼乐志》中有关《皇帝破阵乐》的记载为:“皇帝破阵乐……后周宇文邕平齐所作,即唐立部伎也,新乐,大曲,有舞,文武帝时遣唐使粟田真人道麻吕传之。”[10]10可见《皇帝破阵乐》是后周武帝宇文邕平齐所作的乐舞,在中国古籍中称作《安乐》,又称《城舞》,而并非唐太宗所作的《秦王破阵乐》。实际上,在《大日本史·礼乐志》中载有三种“破阵乐”,即《皇帝破阵乐》《散手破阵乐》和《秦王破阵乐》。日本《舞乐图》中的《皇帝破阵乐》和《信西古乐图》中的《皇帝破阵乐》所绘舞者并非“披甲持戟”,与《旧唐书》所记《秦王破阵乐》的演出服饰不同,且“拔剑而舞”的动作也与歌颂太宗的《秦王破阵乐》不符。而《舞乐图》中的《散手破阵乐》舞者服饰姿态颇具“胡风”,确实更似《安乐》。
综上,日本典籍中所载的《皇帝破阵乐》和《秦王破阵乐》虽同为日本文武天皇时,由遣唐使者粟田真人(粟田道)传入的,但两者实则非同一乐舞,且唐代典籍中并无《皇帝破阵乐》这一乐舞名称,而是传入日本后出现的称谓,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安乐》《城舞》相对应。日本《乐曲考》所载《皇帝破阵乐》这一名称应是沿用了日语的称呼,至于部分中国研究者认为《皇帝破阵乐》和歌颂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为同一乐舞,应是混淆两者所致。
日本人从飞鸟时代晚期至平安时代初期曾大量引入中国唐乐,但也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在主观上有选择性地接纳,如唐代用于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大典的仪式音乐——雅乐便不在其中。究其原因,一如他们认为中国雅乐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音乐;二如雅乐规模太大,难以引进。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王权性质的不同。日本和中国王权的由来、正统性的说明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皇帝权力来源于天的受命和委托,自诩为天子。因此,就有必要祭奠天地,祭奠自己权力的根源——天地、四季、各种自然现象,祈求宇宙的和谐和地上世界的安定。而日本天皇由天孙降临来说明权力的正统性。因为与天神有直接的血统联系是前提,所以天地祭祀是无用的,以天地祭祀为中心的礼乐制度并不为日本所接受。可以说日本学习吸纳唐朝的雅乐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日本古代宫廷接受的是礼仪、祭祀结束后用于筵席的燕乐和散乐[15]。唐《秦王破阵乐》等大曲及宫廷燕乐传入日本后,常在其宫廷宴会和宗教等重要仪式活动中时有上演,可见日本积极接纳大曲及宫廷燕乐亦用于其礼仪服务。
三、《秦王破阵乐》在日本的衍变
唐代“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不在,对日本的吸引力锐减,而日本自平安朝开始政治社会发展趋于稳定,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日本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不再如之前那样遣使学习中国文化,中日之间官方的乐舞文化交流也渐趋停滞。不同于奈良时代的“唐风热”,进入平安时代后日本“国风化”渐盛。从仁明天皇开始到平安中期(10世纪中叶)的乐制改革,根据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并结合日本固有的乐舞,将外来的乐舞改造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乐舞,推进了唐乐日本化的进程。
日本著名音乐家田边尚雄认为,“从中国传入的隋唐音乐,多少按照日本的风格改变了形式,缩小了规模,称为雅乐,以后世世代代在宫廷中相传至今”(3)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在日本》,载《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2日,转引自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第217页。。中国学者金秋曾简要归纳了《秦王破阵乐》东传日本后发生的几个变化:第一是演员人数锐减为4-6人;第二是舞乐调式由“大食调”变为“壹越调”;第三是演化出了“六策上将乐”“齐王破阵乐”“大定太平乐”等别名;第四是舞容改变;第五是舞者加上了面具[16]229。除了上述几点外,对比日本《乐曲考》对《秦王破阵乐》演出盛况的记载,可见传入日本后的《秦王破阵乐》在表演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乐曲考》载,《秦王破阵乐》词曲表演时舞者128人,全部披甲持戟进行舞蹈,队伍随着音乐节奏共变化三次,每次换成四种阵势,舞者持戟来往疾呼击刺[17]2-3。但传入日本后,《秦王破阵乐》人数锐减为4-6人,且舞容后来被吸收进了《太平乐》之中。由于演出人员及规模的限制,“左圆右方”的舞蹈队形和“先偏后伍”(古阵法:二十五乘为偏,五人为伍)的队形变化也是无法实现的,也很难有如唐《秦王破阵乐》“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般震撼人心的演出效果。由此可知,日本的乐舞虽直接学习唐舞,但因地狭人稀、空间限制和人才缺乏,即使在日本宫廷也很难达到和中国唐朝一样的阵势规模,而形成一种“缩小版”的乐舞。除此之外在中日文化交流之前日本已形成了自身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受到日本人审美心理和对异文化接受程度的影响,必然会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选择性吸收并有所加工再创造,使之符合日本民族的审美,并与其文化符号体系相适应。再者,作为一种身体文化,舞蹈表演是历史文化的艺术加工的同时也是舞者情感的艺术表达,很难始终保持一种固定的范式,因而势必会随着时间的流动以及主体客体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衍变。
四、结语
在日本飞鸟时代后期便有了早期唐乐舞的东传,到了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学习吸收以唐乐为主的外来乐舞,至平安时代在消化吸收外来乐舞的同时进行本土化的加工创造,孕育了日本的乐舞文化。可以说,在古代日本乐舞是在直接借鉴唐乐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并在接纳的基础上发生了些许变化。唐《秦王破阵乐》在日本的传播及衍变不仅是唐乐高度繁荣的体现,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其传入日本后有了多种别称,且规模缩小、人数减少、队形简化,形成了“缩小版”的《秦王破阵乐》,而其舞容的变化则体现出日本的审美选择和本土创造。
(指导老师:周海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