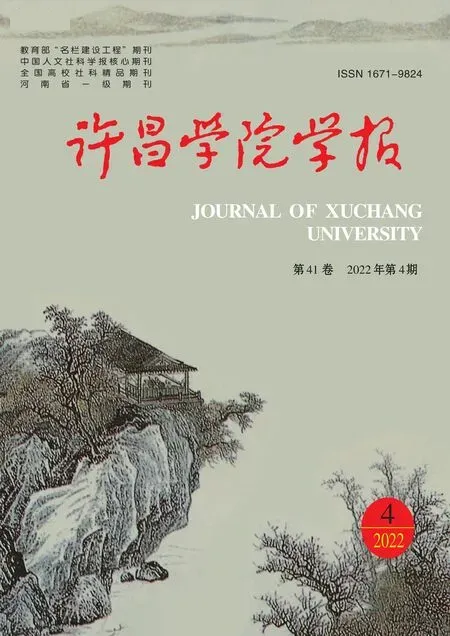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安尼尔的鬼魂》中道家与尼采思想共存现象探究
2022-03-03周也琪
周 也 琪
(香港浸会大学 文学院,香港 九龙 999077)
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是深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共同浸润的离散作家,他曾自我评价为“不同地域的、种族的、文化的‘杂糅’”[1]。其小说有两个现象引起了关注:一是主人公全都是有专门技能的人[2],并且小说深入描写了这些不同的专业技能;二是艺术的救赎力量是其一贯的主题(1)李·斯平克斯(Lee Spinks)曾在专著《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中指出,艺术的救赎力量是翁达杰诗歌的一贯主题。实际上,不止诗歌,翁达杰的小说亦如此。。这两者的结合在翁达杰的千禧年小说《安尼尔的鬼魂》(Anil’sGhost)中达到一个峰值,而这并非巧合。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斯里兰卡内乱时期,五个“匠人”式的主人公都专注于各自的技能,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用中国传统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来剖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小说主人公们的技能实已上升至艺术的境界,从而使其在艺术中感受到慰藉。而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有关艺术的思想在翁达杰小说中也经常被提及,如《遥望》(Divisadero)的题记里就引用了尼采的话:“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2)在小说《遥望》中,翁达杰注:“从J.M.库切接受耶路撒冷奖的致辞里得到尼采这句话,原句为德语。”通过梳理道家与尼采的艺术观、人生观等思想在《安尼尔的鬼魂》中的体现以及它们的交融与碰撞,并尝试分析其中的原因,本文旨在说明翁达杰力图通过艺术为人们提供精神自由的途径,并且把艺术作为东西方互通的桥梁,以此消减东西方之间的隔阂。
从翁达杰的小说里可以读到对各种各样显性艺术的描写,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安尼尔的鬼魂》也不例外。然而鉴于作家的离散身份,对其作品的分析大多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探讨身份认同、创伤、暴力等主题(3)对此,以小说标题搜索相关研究文献即可知。安尼克·希尔格(Annick Hillger)研究翁达杰的专著《无需所有言语》(Not Needing All the Words)是个例外,此书第四章从尼采的“酒神”艺术思想出发,分析了翁达杰诗歌《红岸的孩子们》(“The Kid from Red Bank”)和小说《经过斯洛特》(Coming Through Slaughter),但未涉及《安尼尔的鬼魂》。,在艺术方面往往浅尝辄止,或者只是作为论证其他主题的陪衬。又因斯里兰卡是信仰佛教之国,对翁达杰这唯一一部讲述斯里兰卡故事的小说的批评大多放在佛教的视阈下,甚至提到艺术时也只局限于佛教艺术(4)如徐怀静在《〈安妮儿的鬼魂〉中的身份认同与佛教“缘起”论》(载《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一文中的论述。,笔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翁达杰小说的一种降级解读。翁达杰曾在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呼吁读者把《安尼尔的鬼魂》看作是传递和平与和解信念的作品[3]173,而他在其诗歌和小说等作品中对艺术的书写也有力地传达出其对艺术的致敬。因此,从无国界的艺术的角度来探讨这部小说不仅恰当,或许还是使作家的真正用意得以彰显的必要途径。在道家与尼采的哲学中,艺术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本文用这两种思想来观照《安尼尔的鬼魂》这部小说的根本原因。
小说中五个主人公乍一看跟艺术关系并不大,但他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或技能都是以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以之“安身立命”——从中获得慰藉和解脱,以抵挡外界环境的动荡。这与道家的最高理念——“道”实有相通之处,与庄子为释“道”而讲的一系列精进技艺的小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梓庆削木、佝偻者承蜩等异曲同工。庄子追求在精神上通过“心斋”“坐忘”,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与道合一的自由境界。徐复观曾指出,老、庄之道实则蕴含了艺术精神,并且是就艺术精神的最高意境上说的,而“道与技是密切地关联着”,庖丁解牛的寓言就说明了技术何以进乎艺术的过程[4]30-31。“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4]30这段阐释老庄的话,用在《安尼尔的鬼魂》中五个主人公身上也恰如其分。
小说里的中国元素与时代背景也为用道家思想和尼采思想来分析这部小说做了铺垫。小说刚开篇就提到中国山西的佛窟艺术[5]8,中间还以两三页的篇幅讲述其中一个主人公、考古学家塞拉斯(Sarath)在中国的考古经历,明确提及中国古代道家、儒家以及礼乐等,并且将塞拉斯日后成为考古学家归因于此次经历[5]229,可见中国元素在该小说中的重要性。同时小说在开篇不久,描述斯里兰卡内战情景时用了希腊悲剧做对比——“和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最黑暗的希腊悲剧都显得天真”[5]7——似乎也暗示了这部小说将向尼采思想靠拢。众所周知,尼采的“艺术是最高使命”[6]18“用艺术拯救人生”[6]60等有关艺术的观点正出自他对希腊悲剧的研究著作《悲剧的诞生》。除此之外,道家思想与尼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斯里兰卡内战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兴国曾指出庄子和尼采二人的时代都具有“过渡性”:前者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后者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7]107。而持续时间长达20年的斯里兰卡内战对该国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政治体制和人民生活境况的过渡。纵然时代变迁,但战争的一些本质不变,脱胎于中国古代战乱时期的道家思想对于分析斯里兰卡内战中的人民的思想,或许仍有参考意义。综上,从艺术的角度,借助道家和尼采的思想来剖析《安尼尔的鬼魂》是合理且恰当的。这两种哲学思想虽然跨时代、跨文明、跨国界,但因“老庄哲学经过叔本华而历史地积淀在尼采的思想中”[7]100,故两者具有一定的“同态关系”(5)尼采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而叔本华曾受老子《道德经》影响,有《汉学》一文为证。,并在多个层面上相通。后文便将围绕此展开。
一、小说中道家思想与尼采思想的交融
小说中碑刻专家帕利帕纳(Palipana)的人物形象几乎是道家思想的完美呈现(6)不少学者指出道家与佛家有一定相似和相通之处,本文无意专门对佛家和道家做比较,仅欲从艺术层面分析小说人物情节,因此为论证主题之需要,后文将佛家与道家之表现的重合之处统归为道家。。身为“全国最优秀”的考古学理论家,帕利帕纳从不受其声名、功勋的影响,始终以极简的方式生活,以“猎犬般执着的注意力”专注于历史研究,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5]70。可见他几乎与庄子本人一样安贫乐道,“视荣华富贵如敝屣”[8]3。帕利帕纳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学习、调查和研究,对历史文本和实地考察得来的各种线索了然于心、融会贯通,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自我认知”,往往在去往遗址的路上就已知晓会发现什么[5]72。这相比解牛的庖丁或削木的梓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可谓“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8]45。这其中有庄子之技艺的无法言传,“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8]222,也有老、庄之道的“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名”[8]373。帕利帕纳通过拼凑起各种线索得到历史发现,却因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而名誉受损,但他不试图辩解,而是归隐山林,“遵循日月的作息”[5]93,向大自然“俯首称臣”[5]74。这其中的“无为”“不争”和“顺应自然”都是道家所提倡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将道家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杨朱、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而三者又分别以被动逃避、以不变应万变和以超脱生死的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世事这三种态度为特征[9]73。这三种态度在帕利帕纳身上皆有体现。他总结出的“归隐的悖论”——“你摒弃社会种种,但又必须先成为它的一份子,从中学习并做出判断”[5]90——某种意义上正是斯里兰卡人在内战时期的生存之道。“无为”并非无所事事,已至耄耋之年的帕利帕纳仍投身于山林钻研历史,只在乎“将所知真相尽数道出”,因此他与大自然之间有了愈发深厚的联结[5]73。最后他在林中死去,几乎不着痕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8]3帕利帕纳泯灭物我之见,顺天应时,且“无所待”,真正做到了逍遥游,这正是庄子笔下“至人”“神人”“圣人”的写照。帕利帕纳作为小说中最年长的人物,同时也是塞拉斯的老师,并为安尼尔和塞拉斯的人权调查指引方向,进而决定了小说故事走向——这一智者形象为整部小说打上一层道家底色。小说中其他人物虽不具有帕利帕纳这样的道家风范,却或多或少秉承了一些道家理念。如塞拉斯,同样投身于荒野,只有自然和岩刻是他的“欢愉之源”[5]246;其弟外科医生迦米尼(Gamini),桀骜不驯、与世无争,不分敌我地救治伤患,对于陌生人侵占自己的家不置一词,同时追求“自由和隐遁”[5]195,“不与人接近”[5]185,俨然一副道家做派。
如果说庄子物我合一的忘我境界强调的是顺应自然、反对人为,摆脱痛苦只是得“道”的副产物,那么尼采则是旗帜鲜明地要用艺术去对抗苦难、拯救人生。对尼采来说,生命本身即是痛苦的,但他提出艺术具有“拯救和医疗的作用”[6]60,而且人唯有通过艺术才能把对世界的恐怖和荒谬的厌恶转化为活下去的意念,也唯有将世界作为审美现象来看待才是合理的[6]174。小说中的点睛画匠安南达(Ananda)正是尼采这种艺术观的直接代言者:“如若不坚持当一名工匠,就将成魔。”[5]269安南达“坚信工匠的创造力”,长久以来栖身于“艺术旧眠床”,因为他深知那里“蕴藏某种慰藉”[5]268。尼采用“梦”和“醉”来分别指代产生出希腊悲剧的两种艺术力量,即以阿波罗为代表的“日神”倾向和以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酒神”倾向[6]20。前者已进入艺术的境界,人在梦境中看到“内心幻想世界的美的假象”,获得“与日常现实性相对立的状态的完满”[6]22,即从现实中解脱出来。此与“庄周梦蝶”相通。后者则更进一步,打破前者的“个体化原理”,此时,个体被消灭,人将自身完全遗忘,从内心深处或者本性中升起一种“迷人陶醉”,这种神秘的统一感令人得到解脱[6]24。小说中五位主人公都从各自的技能中获得了这样的艺术力量,他们时常游走在“梦”与“醉”两种状态之间。帕利帕纳在考古遗迹间穿行,“踏上想象中的台阶,即刻置身一个古老的世纪”,现实与远古融为一体;他踏足的“下一个台阶”则是“去除所有的藩篱与界限,在大千世界里发现一切,以此探知他未曾目睹的故事”[5]169。两个台阶正对应“梦”与“醉”两种状态。塞拉斯因“喜欢与那些背景融为一体的感觉。如同置身梦境”,所以喜欢历史[5]227。他在海边“用双手描摹着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刻画出它的样子”,那种“几近狂热”的状态也已超越“梦”而接近于“醉”[5]24。迦米尼则一直以急诊室为“最好的栖息地”,生活在等同于梦境的、“须时刻动用你第六感的地方和情境中”[5]202;他从工作中寻求“秩序感”,在急救病房里“忘却自我,如同醉心于舞蹈于过分沉迷于技巧”[5]195。小说用“熊”和“鼠”来形容这对兄弟[5]256,与尼采提出的通过艺术将对生活的恐怖和厌恶转化为生存动力的两种方式——“崇高”和“滑稽”——相呼应,前者“以艺术抑制恐怖”,后者“以艺术发泄对荒谬的厌恶”[6]60。哥哥把希望寄托在考古上,愿为岩刻牺牲生命;弟弟以“从这一切中看出滑稽之处来”为信念,奔忙于野蛮的急诊室里[5]165。
在法医专家安尼尔身上也体现了尼采的艺术观。她沉迷于实验室,对工作投入很深的感情,在向人讲述其工作时“闭着眼睛,(好似)神游在另一个世界”[5]26;她在睡梦中,“手(还)不停移动,仿佛在刷走(尸骨上的)尘土”[5]27。有段关于安尼尔的插曲占据了整部小说中描述“醉”的状态的最大篇幅,她当时在农庄里,与塞拉斯和安南达一道,为被命名为“水手”的尸骸复原头骨以揭晓其身份。月光下,安尼尔跟随令人振奋的音乐节奏,旁若无人,尽情舞蹈,“蒙住每一条她曾遵循的规则”,“抵达极限与轻灵”,如同“一个陷入魔障的女孩,月光下的祭司,抹着油脂的盗贼”,此时的她“回归真我……是原原本本的她”[5]160。安尼尔此刻以一种“毁灭的姿态”对待自己和周围及过往的一切[5]160,她几乎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身。
由上述可见,小说主人公们身上体现出道家与尼采思想的交织并存,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掌握一项技能并趋于艺术境界所决定的,其中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7]108,非理性逻辑所能解释。道家是“无心插柳”,从天然、无为出发达到物我合一;尼采是“有的放矢”,将艺术拯救的信念付诸实践,达到忘我和解脱。因此,道家和尼采在应对现实困境时,虽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即都通过艺术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正如老庄的哲学思想可以归为“道”,尼采的艺术观也服务于他的“权力意志”论。尼采和道家本不是两条平行线,他们时而相交,如在艺术上,时而渐行渐远,如在为人处世之道上。这在《安尼尔的鬼魂》中均有体现。
二、小说中道家思想与尼采思想的碰撞
“真相”是否存在,是探析这部小说时绕不开的一个命题。表面上看,小说以安尼尔这一“外来者”和帕利帕纳等本土人物分别映照了两种基本观点:前者认为真相清晰、可得,后者认为真相复杂崎岖、不可得。服务于西方权威人权机构的安尼尔,此行回到故乡的目的就是寻找真相[5]137。在西方世界学习生活了十五年,她“习惯了会有标示明确的道路指向绝大多数谜案的根源”,以及“讯息总是清晰明确,发挥作用”[5]46。因此当她以西方的理性思维去思考斯里兰卡问题,并坚信“可以利用骨头来探寻真相”时,帕利帕纳给了她当头一棒:“我们从未拥有过真相,即便仰仗你对骨头的研究也是徒劳……在我们的世界里,真相往往不过是臆断。”[5]89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东西方哲学比较中可以窥知一二。冯友兰曾指出,西方哲学家多从假设观念出发,喜欢明确的东西;中国哲学家多从直觉出发,重视不明确的东西[9]28。帕利帕纳与安尼尔对于真相的不同见解便可为例。但这两种真相观的对立,不能被笼统视作道家与尼采这两种中西方思想的对立。恰恰相反,老庄与尼采同为反理性主义者[7]104,在他们的观念里都不存在明确的真相。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在终而复始地变化着:“道无终始……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8]262尼采则用“永恒回归”表达了类似观点:世界是“奔流的力的海洋,永恒变化、回落,无限反复,如潮涨潮衰”[10]550(7)此为笔者翻译,原文为:“A sea of forces flowing and rushing together,eternally changing,eternally flooding back,with tremendous years of recurrence,with an ebb and a flood of its forms.”。庄子在《齐物论》中还阐述了相对主义的观念:居处的好坏、人的美丑、食物的可口等,以不同的标准评判,会有不同的结论[8]37。而尼采的透视主义也认为,世上没有所谓事实或真相,只有基于个人需求的“阐释”[10]267。按照尼采与庄子的思路——世界变动不居,而人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又都从主观立场出发,绝对真相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尼采与庄子的思想对小说中本土人物的真相观有一定的支撑。
小说透过塞拉斯和迦米尼的言语展现了真相之复杂的三个层面:1.主观性。真相背后有“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5]37,它不仅存在于客观事物中,还“存在于性格、表情和情绪之中”[5]227。2.危险性。其与无效性相连,揭示真相“就像一簇火苗接近整片死寂的汽油地”,所以“恐惧将真相掩藏”[5]138。3.片面性。其与误导性相连,西方世界对亚洲所发生事件的“无关痛痒的态度”导致外国媒体将真相“肢解成适宜的碎片,和不相干的照片”放在一起报道,继而“引发新的报复和屠杀”[5]137,同时西方人利用所谓的真相撰写著作,谋取利益,继而导致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误解进一步加深[5]254。基于这三点,小说中的斯里兰卡本土人物都选择了归隐、逃避、另寻寄托,不执着于真相,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拒绝与战争中任何一方的所谓“正义”做正面对抗(尤其在安尼尔到来之前)。
安尼尔虽然去国多年,但她对真相的复杂和危险并不无知。并且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政局动荡时期的法医调查……涉及多方的明争暗斗和内幕交易,还有不少因‘国家’利益而被压制”[5]23。在调查“水手”尸骸身份的过程中,她逐渐更深入地明白,在这个国家,“真相在流言与复仇之间反复”[5]46,“那些抗争的生灵只会自取灭亡”,死亡和失去“无法了结”[5]47。她甚至向塞拉斯坦言:“我知道你认为真相的作用要更为复杂,有时候在这里说出真相反而更加危险。”[5]45但安尼尔强调:即便如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5]45。比如,“拆解分析,弄清来龙去脉……可以消解紧张和危险的气氛”[5]227。安尼尔对待复杂无解的真相的态度已很明确:既然“没办法不闻不问,或是草草了解”,那就尽力去做点事情[5]116。可见,安尼尔在知晓真相本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迎难而上。这与其说是她的真相观,不如说是她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所以,安尼尔与本土人物对真相态度的差异,绝非简单的对于真相有无的思想分歧,而是如何面对真相的行动差异。若将这二者混为一谈(8)刘丹在《从〈阿尼尔的灵魂〉看东西方文化碰撞及其“协调者”》(《外国语言文学》201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安尼尔对人权问题了解不足,把安尼尔追求真相的行为简单归究于她的西方理性思维,强调两种真相观的东西方对立。,就容易将东西方文化做简单的二元对立,忽视小说人物思想差异的深层原因,甚至误解作者的本意。
本土人物与安尼尔的行为准则,正分别与道家和尼采所推崇的处世准则——“无为”与“权力意志”相对应。道家的“无为”是要“顺从生活,不去忧虑,不为过多的志向所困,珍惜并尽力过好当下每一天的生活”[11]406(9)此为笔者翻译。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在其专著《中国思想》(Chinese Thought)中的原话为“Not to worry but to take life as it comes,not to become entrapped by soaring ambition,and to savor and enjoy as much of one’s life as one can,day by day.”。帕利帕纳、塞拉斯和迦米尼都是如此,他们接受苦难的社会现实,在技能或艺术中得到“补偿”。而尼采认为世界和生命的“终极真相”就是“权力意志”:人需要释放能量(并再造),运用自己的权力意志,去尽可能地与自然、周围的环境和人相抗衡,甚至“对真理的意念”(will-to-truth)本身就是“权力意志”[11]406-407。安尼尔在农庄的那段舞蹈,“控制体内的能量……每一个肢体动作”,坚定“过去不曾以后也永远不会”为任何人或事改变自己[5]161,正是她“权力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而她对“真相”的执着追求,更是其“权力意志”的持续体现。
有趣的是,这两种行为准则对立、碰撞的结果,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安尼尔纵然有很强的“权力意志”,最终还是被改变了,或者说从思想上回归了东方。两次沉重而又充满温情的事件促成了她的转变:一是为“水手”重塑面部的过程中,安尼尔与安南达从言语不通、冷漠相待到达成默契、心有灵犀,她逐渐理解、关心并救助了安南达,她在打开封闭自我的同时获得了“归属感”,并“下定决心要回来”[5]176。二是小说临近结尾处(亦是高潮),塞拉斯为保护安尼尔并成全她所追求的“真相”,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东方的价值观以极端的方式展示在安尼尔面前,作用在她的身上,胜过一切言语说服,也唤醒了她深埋心底的故国情愫和与生俱来的东方底蕴。用塞拉斯的话讲,“去国十五年,如今她终于又成为我们”[5]239。改变安尼尔的力量,不是对真相的恐惧,而是与塞拉斯和安南达之间的“友谊”以及它带来的“归属感”。而原本“无为”的塞拉斯,却转变为愿以生命为代价为正义和真相而有所为。“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在小说结尾部分模糊起来,但塞拉斯的死亡对安尼尔产生的巨大影响宣告了(如果一定要做东西方对比的话)东方的“胜利”——东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相较西方,在斯里兰卡这片东方国土上占了上风。这似乎也呼应了小说中帕利帕纳始终认为的:亚洲历史更加古老[5]69。
三、小说中道家思想与尼采思想共存现象的原因探究
(一)用艺术提供慰藉
“人都需要仰仗谎言。”[5]92帕利帕纳在生前最后几年发现“被掩盖的历史”[5]92,其黑暗程度颠覆了从前的认知,因此感慨道。翁达杰似乎想表达:人们长久以为的“真相”可能会在顷刻间瓦解,又被新的所谓“真相”替代,如此反复。就如小说结尾,佛像因历史的偶然被炸碎,而新的佛像很快又在不远处、尸横遍野之上矗立起来,反讽意味颇重。旧的佛像,或者说佛教信仰便是一种“谎言”,为斯里兰卡人民带去精神寄托。而旧佛像的支离破碎,象征斯里兰卡人的信仰受到冲击,生命的残酷真相也即刻毕现:不过一堆碎石,无可寄托。即便佛像被(安南达)修复并重新屹立,裂痕也永久存在,成了斯里兰卡人心中无法磨灭的创伤。小说里呈现的本土人物的佛教信仰也确实风雨飘摇:画匠安南达“不再敬奉信仰的不可思量”,转而投奔艺术,坚持做一名工匠[5]269;迦米尼的信仰“荡然无存”,仅能从行医中获得安宁[5]190;帕利帕纳的兄弟、好心为无业青年建设社区的苦行僧纳拉达,遭遇政治谋杀,甚至可能就是为另一僧侣所害[5]42。内战当前,宗教信仰的无力和生命的残酷本质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翁达杰不忍揭示,却也无计可施,他便转变思路,致力于为人们寻找另一种“谎言”作为替代。他将目光转向东方的其他国家和他长期居住的西方世界,他从道家和尼采的思想得到启发,这与他本人注重艺术的性情不谋而合,他寄希望于用艺术为人们构建精神上的庇护,让人通过艺术感受到如安南达在小说最后收到的“一抹温柔”。
(二)用艺术表现真相
“真相”的世界或许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达,但让人们看清“真相”却有重要意义。翁达杰试图用小说这个艺术的世界来展现真相的复杂,在《安尼尔的鬼魂》中他展示了包括斯里兰卡时局的真相、正义的真相、西方所宣扬的所谓真相的真相,以及本土人物与外来人物眼中不同的真相观等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真相”的组成部分。翁达杰不满于西方世界对亚洲无关痛痒的态度,或者站在西方立场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或者刻意将东方问题做简单化处理,于是借由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出来。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在《报道伊斯兰》(CoveringIslam)中曾指出:“不实陈述和歪曲事实并非真诚地想要理解,也不是真正想要去听去看那些应当被听到看到的东西。”[12]30小说中塞拉斯和迦米尼这对兄弟坚定地表示:“尽管身边发生着这一切……(仍)深爱自己的国家……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5]253这几乎是翁达杰自己对东方故国的表白。但他明白,东西方之间的隔阂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赛义德早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就论述了东西方之间误解的根源和形成机制:西方世界通过掌握话语权,创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不断加以“巩固”[13]12。翁达杰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真相”的复杂世界,使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可以从中互观,引发思考,从而消解东西方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同时,他也想提醒人们,只有设身处地并投入一定时间精力去认识和感受异国的风土人情,才能够对别国真正有所认识,从而避免隔阂和误解的加深。就如塞拉斯对安尼尔所说:“(只有)你生活在这里,我(才)会更接受你的观点。”[5]37艺术无国界,这或许是翁达杰这个情系东西两端的离散作家为实现东西方相互理解、尊重而做的努力——当真相不再片面,和平、和解就有希望。
(三)回归东方
关于艺术这个“谎言”,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就毫无希望吗?普通人除了逃避,就什么也做不了吗?翁达杰用安尼尔这一人物回答了这个问题。安尼尔带着西方的先进技术、理性思维和“权力意志”回到东方的故乡,强行以一种不同的生存准则去追求“真相”,如蚍蜉撼树,未能改变太多,反而让塞拉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实际上无所谓对错,只是人物因各自的价值观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如塞拉斯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中国古代女乐官自愿殉葬的现象)。但即便只是让“大树”稍微晃动,安尼尔的所作所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犹如在污浊的泥潭中射进一束光,并且实现了她所希望的,为无辜的受害者“正名”,揭示内战中罪恶的万千分之一。这是西方价值观积极意义的体现。但安尼尔最终“回归”东方,并且永久地背负着塞拉斯的魂灵,印证了冯友兰曾指出的,西方的思维方法尽管可以改变东方人的心态,却无法取代东方的思维方法,只能是加以补充[9]362。同时这也体现了翁达杰自己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宿命般的倾向:让东方人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东方的问题。
四、结语
本文借用道家与尼采的艺术观,展示了《安尼尔的鬼魂》中的人物在极端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美学:将技能升华为艺术,以艺术对抗苦难。东方与西方,或也如中国古代编钟的每只悬钟,都有两个音阶,“相生相克”[5]229,在艺术中融为一体。翁达杰也用艺术的手法,让人们摆脱认识的局限与片面,让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和偏见在潜移默化中消减,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得以实现成为可能。
在《迈克尔·翁达杰》一书中,作者李·斯平克斯表达写作此书的目的,即想要探索翁达杰的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和创造性的来源[14]17。阅读翁达杰的作品不难发现,作家本人就如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追求技艺的精进,率先深入钻研小说人物的技能并达至高超的境界,并在写作中顺应这些人物自身的发展[15]252。如果以道家与尼采的思想来看翁达杰的写作,其中的艺术精神与随之产生的力量和美感也将有所显现。结合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来评析翁达杰这样兼具东西方文化背景的离散作家的作品,不仅有助于发掘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为东西方的相互理解与融通搭建桥梁,可谓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