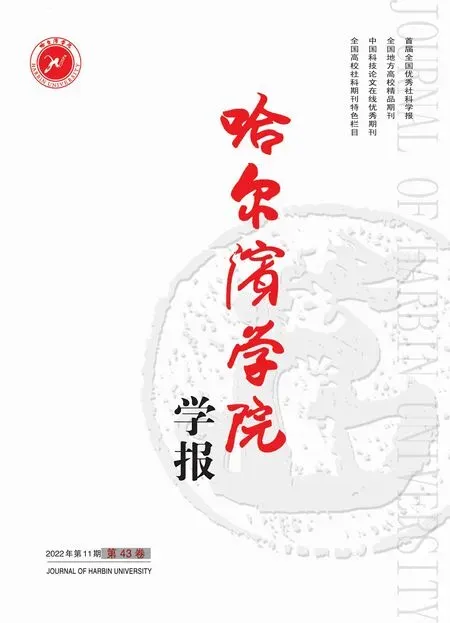复调中的具像、群体与合唱:《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他者”意识
2022-03-03陈钰冰
陈钰冰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白俄罗斯作家、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毕业于明斯克新闻学院。她历时数年完成了“乌托邦之声”系列,主要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等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她的作品在多国出版,被翻译成35种不同的文字,获得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88),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文学领域的世界著名奖项。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这样形容她的作品:“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显而易见,复调创作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作品中的突出特色。这一创作技法起源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复调作为音乐术语,起初用来形容两种或多种并行的旋律,它们交织出和谐又富有层次的乐章。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借助了这一音乐术语,说明复调在小说中指的“不是众多性格与理论”,而是一部小说“有着众多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通过小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穿插,展现了复调的对话精神。
作为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深受复调传统的影响。“乌托邦之声”由多人的采访编汇而成,容纳了各种不同立场的声音,也将记述的主人公从边缘化的他者转化为表达自我意识的主体。
“他者”的概念存在已久,在现代伦理学的范畴里,他者是被放逐、被忽视的。然而,当追求个体本位的现代性被后现代浪潮冲撞后,“他者不再是一种牺牲品”。[2](P99)重新确立“他者”和“自我”的关系成为后现代伦理学中倡导的子题。“我总是比他者有更多的责任。”[3](P88)感知他者存在,聆听他者声音,成为后现代伦理创作者一个重要的书写方向。
阿列克谢耶维奇虽未直接提及“他者”这个概念,但她始终将关注点放在传统价值观下的弱势群体上。她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声明:“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想关注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而她的每一次访谈和落笔,也遵照着这样的表述。《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乌托邦之声”系列的开山之作,阿列克谢耶维奇关注苏联卫国战争中女兵群体的战时经历以及战争后的生存状况。借助复调技法,她不仅消解了作者的权威,也凸显了他者的声音。复调既是每个人物自身矛盾性的个体复调,又是整个女兵群体的声音和其他群体间构成的群体复调,更是作者与讲述者之间构成的复调。
与此同时,她在作品中流露的后现代伦理关切也和复调技法相得益彰。作品从描摹他者的具象,亲近他者的苦难,再到引领他者合唱,层层递进,对和平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喊,令整个人类社会感受到力量的震颤,也体现了重建后现代伦理系统的价值所在。
一、个体复调:描摹他者具像,关注个性矛盾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重点讲述了二战时期苏联女兵以及她们的战后生活。她采访了161位女兵,用了数百盒的录音带来记录。故事全部来源于真实的采访素材,但采访本是对话形式,最后在书中却以独白呈现。通过隐去作者部分的语言,整本书对他者的描摹显得更加清晰和具体。复调最显著的特性也体现在这里:不同女兵迥异的经历未被一概而论,他者具象得以描摹,每个形象都鲜活地立于纸上。
战争消磨了个体意识。在整齐划一的军队群体里,女兵们只是一个被同化的符号,每个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不堪。胜利会归结于群体,而所受到的伤害因被归结为群体伤害也随之模糊淡化。“苏联女兵”这一笼统的称呼概括,掩盖了每个人血淋淋的刺痛和创伤。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下,每个女兵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展现出不同的形象。文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是直接引用女兵的口述内容,用第一人称叙述,文本中最后标注上女兵的姓名和兵种,记录她们每个人的故事。
根据女兵兵种,战争的伤害折射出不同的版本。对护士而言,在抢救伤员却又没有必要器械的危急关头,就意味着“我硬是用牙齿把伤员的烂胳膊啃了下来”。[4](P159)不上前线的炊事员,也在后勤保障上为打赢战争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力量,“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4](P189)她们承载着超过自己几倍重量的大锅,连长官看了都心疼地想把所有的大锅都打穿;对洗衣工来说,她们对战争的体会是前线士兵换下来的衣服。“第一遍水时没法下手洗的,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4](P190)卫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枪林弹雨,“要把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4](P400)
即使战争结束,每个女兵依然承受着难以磨灭的创伤应激障碍(PTSD)。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在接受采访时说,听见爆破的炸药声,就觉得自己重回到战场上,“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4](P10)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因为在战场上见了太多的血,战后只要一碰到红颜色的物品,身体上就会起红疹和水泡。“无论是红色的棉布或红色的花朵,不管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我的身体都不能接受。”[4](P388)又或是在战后回归家庭时,她们从来都“不敢触碰军事用具,从来不给孩子们送军事玩具做礼物”。[4](P399)
再者,复调的运用也体现在女兵矛盾的个性里。面对战争,女兵们在战前战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她们起初想变得和男孩子一样,跃跃欲试地加入到战争中,“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4](P233)到后来却截然不同,“最好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4](P234)战争将人心渐渐磨硬,女兵们起初连杀动物都不敢,克拉芙季娅因为食物不够杀了一匹小马而流泪。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对死亡麻木了,就在尸体旁边抽烟、吃饭、聊天,看到尸体也没有恐惧。
在庞杂的战争史中,英雄故事是其中的主旋律,而每个女兵渺小的情感和挣扎却被罔顾。除了正常的对话记录之外,有几位女兵的生活得到了着重聚焦。但她们对采访并非被动配合接受,而是有着自己的反应,有时甚至会发出抗议。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是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位受访者。在面对作者采访时,起初她显露出极大的反感和抗拒:“不,不!我不想去回忆。”接着又反问作者:“干吗要来找我?为什么不去问我的丈夫。”即使同意接受采访,也只称自己是“普普通通的故事”。[4](P2)
同样挣扎的还有尼娜·雅柯列夫娜,相谈甚欢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不少动人的细节。她遵照受访者的请求,将“最令人感动和震撼的故事”给她寄送回去,[4](P100)可收到的回信却让她分外吃惊。从尼娜那里寄回来的,是她在各个学校公开演讲时所采用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报告,而作者撰写的故事,几乎被删除得差不多了,不少苦中作乐的部分着重划了三个大大的感叹号。她对待采访的前后态度大相径庭,让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叹:“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4](P100)这是复调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他们反复审视自己,再次认识自己。他们往往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当时的人和现在的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战争时期的人和战争之后的人。”[4](P152)
在阿列克谢维奇的笔下,战后女兵们不是异类,而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女儿、一个母亲。战争过后,她们依然是愿意做好樱桃馅饼等待作者采访的普通女人。作者亲近平和地对待每一位被采访者,还原了她们的笑声与泪水,使得每一个女兵形象鲜活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二、群体复调:聆听他者声音,亲近他者苦难
在另一本纪实作品《锌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手段:“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5]他者长期处于“失语”的困境下,每一次微弱的发声也应当被仔细聆听。她们才敢于继续叙述。
列维纳斯提出“亲近”(Proximity)的概念,来形容人们对待“他者”应该拥有的态度,亲近重要的不是物理空间上的距离。而是“代表伦理情景独一无二的品性”。[2](P102)亲近意味着将曾无限给予自身的注意放置到他者身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出色,她通过亲近他者的苦难,还原女兵群体的生存状态。
对于群体,大多数人的观点与鲍曼相一致。认为“群体是对异物的窒息,对差异的废除,对他者中相异成分的消除”。[2](P112)但群体复调的使用,却在共享同一性的同时求同存异,将每个女兵的差异也保存下来。
整个女兵作为群体,同享苏联女兵的身份,凝聚在一起共同承担与消化苦难,这些如实地被作者记录下来。但与此同时,她们叙述中也夹杂着来自其他群体的诘难和询问,不同的声音汇聚在这里,清晰地构成了作者所要描述的苏联女兵群体面对的多重苦难。
首先是严酷的战争带来的生理创伤。女兵们身体上迅速苍老,“才二十一岁,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我负过重伤,脑袋也震伤了”。[4](P10)又或是女性特征的丧失:“身体像死了一样,没有月经,也没有欲望。”[4](P410)
其次,她们遭受到的是来自男性群体的质疑。战争和战后,女性在男权社会始终都是他者,是客体,站在阴影之下。书中的回忆里也充斥着男性的话语,构成另一种类型的声音。“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嗯,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然后是美丽的太太。”[4](P83)他们同时质疑女兵的能力,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弱性别”担任军职的怀疑,认为护士职业她们或许能够完成得很出色,但是怀疑姑娘“能在高炮部队里做些什么”担心她们怎么“吹干头发”;长官怜惜她们,称呼她们为“丫头们”,一看到分配的是女孩就生气了,说军队“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4](P7)面对他们的种种态度,女兵们则显得很愤慨:“我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4](P6)
更矛盾的是,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心中的柔软即便面对着残酷的战争也无法磨灭,也给她们的战争生活带来了影响。有人喜欢吃糖,在奔赴战场时也带着糖果;有人会在枪刺上带着紫罗兰,甚至因为这几朵紫罗兰,心甘情愿地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还有人“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4](P225)甚至在敌人突然开炮轰炸的时候,还在犹豫如何卧倒才不会弄脏衣服。一位年轻的狙击手,萨莎·施利亚霍娃,因为喜欢一条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因而暴露了自己的伪装。
通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生动的记述,我们全方位地感受到战后女兵延续的苦难。战后她们回归本位,因为“战争强加的后致身份与其先赋的性别身份产生了冲突”,[6]使她们遭遇到严重的身份危机。首先,她们难以适应正常的女性生活,结婚时来到服装店面对店员的询问,不知道想要什么样式的礼服,永远不想再穿高跟鞋走路。在战后的生活中,从来都不敢触碰军事用具,也不给孩子们送军事玩具做礼物。
“男人可以佩戴勋章、奖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们上过战场是一份荣誉,但人们却用完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女兵。”[4](P126)同为女性,其他留在国内的女性无法理解她们,在女兵们战胜归国的时候,指责并辱骂她们“用你们的年轻身体去勾引我们的男人”。在他人眼里,参加过战争的女兵是丢脸的,这段经历最好被永远遗忘。连曾经在战争中亲密的男性战友,当初愿意挺身而出挡子弹,共同分享外套和砂糖,似乎也在战后背叛了她们。“男人都抛弃了我们,毫不掩饰地走了。”[4](P397)一位丈夫更是将背叛的所有责任都推卸在妻子身上,说:“从她身上飘出的是香水味儿,而你身上是毡靴和绑腿布的味儿”。[4](P281)就算是没有离开她们的丈夫们,也在干涉她们的回忆。一位女兵说:“昨天一整夜他都拉着我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史,就是怕我乱说话。”[4](P417)
“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4](P20)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女兵群体的描述是一部对群像苦难史的书写。她亲近女兵们的苦难,倾听每一次“他者”之声。
三、作者与作品复调:引领他者合唱,引发和平震颤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长和学习背景,也极具有复调的特性。她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说:“我有三个家庭:白俄罗斯的土地,那是我父亲的家乡,那儿有我的整个人生;乌克兰,我母亲的家乡、我出生的地方;以及所有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不能想象自己。”这样复合多元的背景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个人保障。与此同时,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让她具备新闻写作的气质,创造出虚构与纪实交界的作品。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所写的一系列纪实作品,统称为“乌托邦之声”,从宏观来看,这一系列的作品,都将采访者放在中心地位。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通常位于权威地位,笔下的人物符合作者的意志。而纪实文学的客观,消解了作者权威,阿列克谢耶维奇主动从文本的中心位置走下来,直接将女兵们口述的内容如实地呈现给读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直接出现在故事里,甚至对女兵们叙述的故事也没有多余的评价,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倾听者的状态。“她们说的时候,我在倾听……她们沉默的时候……我也在倾听。”[4](P419)她将“自我”最小化,给“他者”提供最大的文本空间,主要的记述都留在书的开头和结尾,偶尔也会简短地用第一人称在结尾进行一部分述评。
作者尊重每一位女兵,愿意见面的,她便长途跋涉去见;拒绝会面的,她就通过电话或者信件交流,她会按照修订的意见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作者在创作手记中谈到自己是怎样进行采访的:“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试穿新买的衬衫,一起聊发型和食谱”,[4](P407)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平等的姿态去拥抱每一位女兵,以真心换真心。
而她这样平等与真诚的交流,让处于遗忘边缘的女兵深深感动。在和那些女兵们交流的时候,她们叫我“姑娘”“闺女”和“孩子”,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么记述道。女兵们从前在角落里舔舐伤口,现在终于小心翼翼地敞开了内心世界,愿意将自己的战友的联系方式分享给她。她获得了女兵们的信任,也收到了四面八方的来信。
“我为他者负责并不是在等待互惠。”[3](P86)同样,阿列克谢耶维奇积极描述他者的苦难,并非期待她们回馈给自己什么等价的回报。她时常感到遗憾,觉得录音机的功能“不能录下对方的眼神和手势,不能录下她们说话时的生活,她们自身的生活、独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们真正的原文所在”。[4](P317)
作者虽然隐去,但作者的作用却没有完全消失。第三种复调形式通过作者之声和人物之声相互牵连,人物在明处,作者却藏在暗处。却又在作品中时隐时现。虽然作者本人没有过多地参与到的对话当中,但写作的素材也经过了作家本人的精心挑选和判断。
描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作品时,“合唱”是一个常见的比喻。合唱强调和谐,尽管众声喧哗,却始终有一个永恒而稳定的主题。正如复调以独立的旋律交织融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也是如此,最终凝结成极具代表性的“乌托邦之声”。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也多次出现了合唱的描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4](P1)《伦敦时报》在评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时也说:“如同古希腊悲剧表演的合唱团。”阿列克谢耶维奇像是个指挥家,在她的精心调配下,女兵们的内部声音,女兵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声音,高低交织引领了一曲震撼人心的“他者”合唱,振聋发聩,反映了对和平的呼唤,也让人们将目光聚焦在重建后现代伦理的重要性上。
四、结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纪实文学创作的初衷,是通过它呈现出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展现人道主义关怀。她通过三种不同形式的复调应用,将所有个体的苦难和情感交织,构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合唱。虽然作者并不是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但她的纪实作品却成为一部“他者”的书写,从具象、群体到引领合唱,层层递进体现出对“他者”的特殊关切,用极具后现代伦理的话语,有意识地体现出在战后重建伦理体系的重要性。唯有正视历史,承认战争带来的伤害,倾听他者群体的声音,积极对他者群体负责,我们才能真正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构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