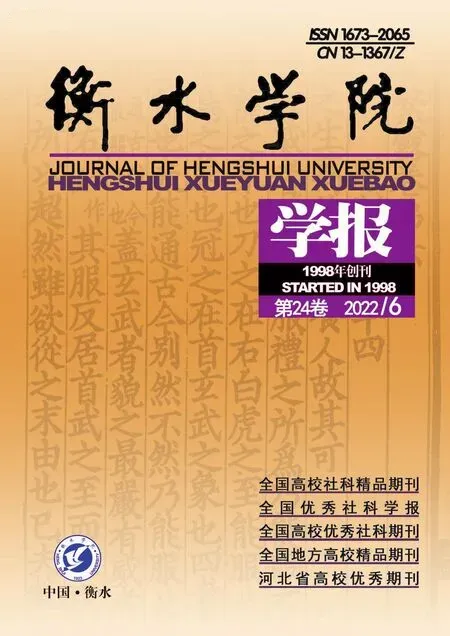周敦颐的定静工夫医学实践之可能
——以朱丹溪治郁思路为视野
2022-03-02施中阳
施中阳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 桃园 32001)
本篇论文旨在讨论业师黄崇修教授在其定静工夫研究中,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定静工夫新诠释》系列文章中有关朱丹溪三重郁说之思维,以中正仁义对治思、忧、怒三郁之可能。由于行仁对治忧郁,已在拙作《周敦颐定静工夫之医学应用——以朱丹溪援儒入医策略为视野》一文中已有论述,本文不再重复。
本文借由朱丹溪“情志三郁”(忧郁、怒郁、思郁)思维结构与周敦颐“定之以中正仁义”工夫之间的义理亲和性,试图从中找出一条“以定治郁”之身心论述脉络。鉴此,笔者对业师所提出的“集义以定止怒郁”“中正以定止思郁”之配置形式以医学伦理之方法进一步论证。最后则经由对此对应架构之探讨,笔者发现朱丹溪情志三郁思维结构与宋学义理有相呼应之处,且对现代社会有重大价值。
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诠释之反思
在《太极图说》中,面对五性之动,是以“仁义中正而定之”来对治。因此,业师黄崇修教授认为忧、怒、思一组概念与仁义中正相对应时,就能以中正仁义来代替多种而复杂的德性对应。
而“中正仁义”之概念,周敦颐只是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便再无表述。业师黄崇修教授借由周敦颐在《通书》中的说法为依据。再从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依自注观之,此句同于《道章》及《圣学章》,是此两章之简括也[1]。认为“中正仁义”有新的理解可能性。
一般学者基本依循朱熹《通书注》中的方法把“中正”拆分开来解释:中,即礼;正,即智。图解备矣[2]109。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有所对应: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2]32。此处朱熹将“中”与“正”各自解为“礼”与“智”,正回应了《通书》“慎动”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2]108
然而周敦颐并未直接就沿用其《通书》中“仁义礼智信”概念。创发性地用“中正仁义”概念来阐述圣人之道。要明其用“中正仁义”之因,就必须将焦点锁定到“圣人之道”的相关概念上来解读。而就根据《通书·道第六》来看,牟宗三先生认为朱熹诠释系统之外中正应有新的解释方式: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守之贵,行之利”是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笔者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注文内容所进行的补充。
笔者认为周敦颐对“圣人之道”的见解是与一般儒家略有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圣人”,是以孔孟为代表,除外也指历史记载中的尧、舜、禹、汤等圣君。周敦颐在《通书·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笔者认为,此圣人特指一国之君或是国家实际掌权者。且必须具备中正、明达、果断的德性,唯此才能国泰民安,这些可以对应到周敦颐提出使用了“中正”“明达”“果断”的概念。根据《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由此可见,明达、果断分别是仁、义在于应对具体事物的表现。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中所谓“守中正”“行义”“廓仁”的工夫便是内圣而向外推之的道。那么,“中正仁义”一词的断句,除了将“中正”各自解为“中”与“正”之朱熹解法之外,还可以将“中正”视为一词而与“仁”“义”工夫搭配的解法。
程颐有以“中”包含“正”之概念诠释。在《伊川易传》对《易》恒卦九二爻辞之解释内容中:“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未必中也。”程颢亦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有所说明:“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碍,左右逢其原也。”[3]360
“操持之正”与“断舍之忘”之过与不及皆不得正。因此这也呼应了程颐所强调的,得其“中”而得其“正”之解释观点。甚至是朱熹亦有类似说法:如慈爱底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义。问:“所以妇人临事多怕,亦是气偏了?”曰:“妇人之仁,只流从爱上去。”哪怕是朱熹也认为仁义不是偏守其一便可,还是要和于中道(中正)才行。
黄崇修教授基于此“仁”“义”“中正”之诠释模式之成立,其便可于形式上与“忧郁”“怒郁”“思郁”形成三对三的对应论述。笔者在此提出对这种可能性的补充解释。虽“仁义中正”联用确实是出自周子的《太极图说》。但若分成仁、义、中正来看,其实一直都是中国哲学固有概念,或者说这三组都是常用的概念。
但是就先秦儒学来看,仁义似乎并非是两组能分清楚的概念。余治平教授认为孔子讲的仁和义不是并列的两德,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于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4]。而孟子区别了仁与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只是把仁与义做了一个内外之别,即仁内义外,但并不是对象上的区分。可见,就孔孟而言,仁既爱自己又包括爱他人;义既是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又是对社会大众的道德要求。
而把仁义概念正式分开的第一人应该是董仲舒。董仲舒并不同意“仁内义外”的说法,对仁义以人我来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仁之于人,义之于我”“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仁是指对待他人的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其核心是爱人;义是自己对待自己的伦理自律,实质是伦理的自觉体认和自我审视,其核心是自省”[5]。
董仲舒把仁和人、义和我联系起来,明确了仁义的对象和要求。仁诉诸的是人,义诉诸的是我。仁是对他人的爱,是爱人;义是对自我的道德要求,是正身。
但是也不难看出,董仲舒的仁义二分,并非是把仁义在存有层面进行分别,而是在工夫实践层面之分别的区别。尤其是其“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可见一斑。仁义法,即是仁义之工夫。可见,董仲舒也只是在工夫论上对仁义进行了区分。
由此,笔者姑且把仁义之别认为是内外之别。而中正一词,沿用上文所表述的,是持中守正之意涵。那么仁义中正是否能直接对应上存有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三角关系?仁在内为体,对应存有论;义在外对应心性论;而持中守正的中正对应工夫论。但具体情况是否符合需要另行文进行论证,笔者在此只是提出一个可能性的表述。
二、仁义中正义理如何对治“情志三郁”
这一部分将以业师黄崇修教授之《周敦颐〈太极图说〉定静工夫新诠释——以朱丹溪三重郁说思维结构为视点》一文为思维主轴,并对其文章进行评述和补充。
(一)中正仁义与情志之对应
朱丹溪在《相火论》中之思想可追溯至周敦颐《太极图说》,因此,黄崇修教授认为朱丹溪《相火论》中“火致郁”理论,与周敦颐说的“中正仁义以定之”的工夫,可以作为防治五火之妄动的工夫,甚至可以作为防治情志三郁病症的最为根本的指导原则。
黄崇修教授把“中正仁义”与“忧怒思”两组理学与医学之概念相并研究,开学术界研究之先河。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2]30
程颐阐释为:“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3]577五性即是对应于五行之物性所提出的。程颐称未发之时五性为仁、义、礼、智、信。一旦感外物动而发之则称之为七情。更是指出情炽而益荡时,是对本性有害的。这种论述也是十分符合医学对人欲之发动的思考。朱丹溪认为周子所谓的“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之五性,就是《黄帝内经》中“五火”概念。中医学认为,五火是五志——喜、怒、忧、恐、思——感动而生。若“有喜怒思悲恐五志过极而卒中者,五志过热甚故”,则会“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煎熬真阴”,结果将会因阴虚而气郁以致病,严重者阴绝则死。朱丹溪认为这也就是忧、怒、思三郁等病症之根源。
在《礼记》之中就已有出现的强调正心慎动防止身体出现状况的说法:“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由此可见,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有所过当,都会使修身不得其正。因此,作为理学后学的朱丹溪在其思维之中,必然也会有先正其心,从而防治情志问题的思路。从朱丹溪的思想中也不难看出,理学中所探讨仁、义、礼、智、信的概念与医学中所讨论的喜、怒、思、忧、恐等情志问题间存在着一套可以相对治的可能性。
黄崇修教授认为此结构性的链接关系,在探寻忧、怒、思三郁之存有式的意义治疗时,能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与之相对应,则可为现代忧郁症防治提供新的思路与发展方向。这一点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意义治疗(logotherapy),是维克多·法兰克(Victor Frankl)所创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指协助患者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义,借以改变其人生观,进而面对现实,积极乐观地活下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这种治疗思路本身与中医学的理解和治疗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现代心理学认为郁症起因和治疗之复杂,各学派之间又互不认可。相比起中医认为郁症可以简化为之,其中就有用治心之法以治其身的儒学思路。朱熹式的“时拂拭”,勿使尘埃掩盖了天理。这种思路也与中医所认为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阻碍道德行为的自然流露相符合,如肝郁则不制怒,气虚则自画等。但这种思路是否真的可以在现代医学实践上得到验证,本身还是一个新的议题。
1. 医学上“行义止怒”是否可能
医学上所认为的肝之志为怒,即怒的情绪是由肝脏所管理的,不健康的肝脏状况是会影响到对怒的管理。一般的易躁易怒的状况,都是肝功能有所缺陷的表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鹰,义禽也。秋令属金,五行为义,金气肃杀……不击有胎之禽,故谓之义。”义归五德属金,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在地为木……在志为怒。”怒属五志属木,从五行上来看,金胜木。如此看来在五行生克层面义实能克怒。那么行义止怒之内在逻辑是如何?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3]53。——程颢
义者,克己也[6]。——张载
也因此,吴启超先生把克己解释为去私心[7]。而在朱丹溪的思维中,选择张载以“义”的角度来联结“克己”之内在实践逻辑也不无可能。如此一来,“义”字便可以与“克己”相互关联。
至于“义”之概念使用,《礼记·中庸》中:“义者,宜也,德之则也。”《礼记·礼运》中有“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而《荀子·强国》中有“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至于朱熹则兼述二义而有“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业师把“义”的含意解释为:在内,心有节制;在外,合乎公理。面对人心之欲时,则更显现出其中一来一往之张力。更是创发性地用兵家书籍中的言说来阐释这种理欲交战的论述:太公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由此看来,“义”的实践内涵的确符合程颢“克己”中自我克制情绪以治怒的说法。
业师还列举提取了《礼记·礼运》之内容,将十人义中之夫义与妇听,做进一步分析。他认为,丈夫必须对自己妻子有相应的夫妻情之外,还要有义。而丈夫却背叛妻子而有“不义”之行为,如此一来则可能造成关系撕裂而伤害对方。此种概念完全符合朱丹溪医学上关于“夫之无情无义”而导致“妇心愤怒”之治疗记录内容:“若妇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格致余论·乳硬论》)“丹溪治一妇病不知人,稍苏即号,抖数四而复昏。朱诊之肝脉弦数而且滑,曰此怒心所为,盖得之怒,而强酒也。诘之,以不得于夫,每夜必引满自酌解其怀。朱治以流痰降火以剂,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郁,立愈”[8]。
2. “行义对治怒”与高血压治疗
高血压作为现代常见的三高病症之一,在中医看来,其形成原因有二:肝阳上亢与肾阴不足。其中肝阳上亢血压高最为常见,而老年群体的高血压大多因肾阴不足。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易焦易躁、怒发冲冠等,即是肝阳上亢的具体表现。
肝阳上亢证,是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亢扰于上,所表现之上实下虚之症候。病因病机多样,多以恼怒焦虑,气火内郁,久之而耗阴,阴不制阳所致;或房劳所伤,或年老则肾阴亏虚而致。其临床表现有眩晕耳鸣、头目胀痛、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梦等。
肾阴虚证,指肾精不足失于滋养,虚热内生。久病伤肾,温热病后期伤阴,肾阴亏损,滋养失职,或因房事过度,阴精内损。临床表现:腰膝酸软灼痛,眩晕耳鸣,齿松发脱;男子阳强易举,遗精,阳痿;妇女经少、经闭,或见崩漏,失眠健忘,形体消瘦,潮热盗汗,五心烦热,或骨蒸潮热,咽干颧红,溲黄便干,舌红少津。
朱丹溪在《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对此已有论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夫当壮年便有老态,仰事俯育,一切隳坏。……古人谓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
笔者认为,其义涵之主旨又回归到宋明理学之关切话题——灭人欲上。朱丹溪似乎认为灭人欲工夫是为收心养心之必然要求。如此看来心不为之动,或不动心,是为灭人欲工夫之核心。孟子曰:“四十不动心。”朱熹解释道:“养气一章在不动心,不动心在勇,勇在气,气在集义。”
将朱熹之解释做一个医学思考上的解读,可以认为,是把肝气之不调达与义做一个紧密连接,身体的不健康是一种对人自身道德行为之发动的阻碍。不论是肝阳上亢还是肾阴不足,都是由一个心岂能为之不动的原因为开始。而朱丹溪指出,暴寒暴热、忧愁愤怒、惊恐悲哀、醉饱劳倦、谋虑勤动,皆为一日之虚,都是在损耗本体之阴,从而损耗身体。现代社会远比当时有着更多的外界刺激和诱惑,但人们并没有做出更为刻苦努力的定静工夫,甚至在声色犬马之中放任自流。如此,近代三高频发,且逐渐趋向年轻化,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
若把义的工夫,即行义,理解成一种高级的情绪管理,确实在很多时候可以限制自己不当的情绪。但是若没有把义内化,只是作为一个外在的标准和要求,并不能确实有效的对制怒进行实质性帮助。只是一味地提行义,而不断地勉强,只会让自身觉得委屈。其结果不但得不到止怒,更是会影响到其他情志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都是医家所关切的怒之发动中节不伤其本体之概念。因肝气盛而杂,感外物而妄动,情志过度,过怒则伤肝。伤肝则肝气失于条达不得疏泄,致肝气郁结。气郁日久化火,则为火郁;气滞血瘀则为血郁。这些对身体情况变化的描述,所指向的要求是让人减少私欲,从而达到减少对本体阴之消耗。
由此可以得到这么一条结论:要避免阳有余而阴不足,首先需要维持肝脏之阴阳平衡,保证身体的气血通健;气血通建,则肝气清纯,感物不会妄动而生怒,从而不会伤害到肝之本体。医家是从身体自然之状态去推理出道德义理之自然流露。而儒家之教育更多时候是让人“明知不可而为之”,不去刻意强调外在的客观条件限制,而是把道德内化。把义的工夫的行义(仁义),转化成义(仁义)行。并非是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去符合那个外在之标准行动。而是内心有一个标准,行为规范处处都符应内心之道德。
(二)守中正以定止思郁之症发
思,有思虑、思考之意。中医认为脾为思之官,人的思考能力需要处君位之心脏与思之官脾脏共同配合。孟子也说过:“心之官则思。”而思郁之产生,即邪思与过思所产生的气久郁结于脾胃,导致脾胃失衡所产生的情志之问题。
1. 中正之实践内涵
《周易》崇尚中道,因此二爻多誉,五爻多功。“正”指阴阳得位,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即谓之“正”,又称“当位”。九二,阳爻居中,则为不正;六五,阴爻居中,亦非正位。如果阴爻居内卦之中,阳爻居外卦之中,如六二和九五,则是既中且正,谓之“中正”。在《周易》的话语体系中,“中”与“正”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二者各有不同的意涵。“中”是从“爻位”上来讲的,象征守持正道,处事庸和,行为不偏,这与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有相近之处。“正”则是从阴阳配位来讲,象征阴阳各得其所,各得其宜。
“中”与“正”相比较,“中”德又优于“正”德。程颐曰:“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具备了“中”的品格,则自然不离“正”道,是故一卦之中的二爻和五爻,不管是阴还是阳,总是吉者居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道又可以规约为“中”道。另一方面,中道与正道又是相通的。赵岐《孟子注疏》云:“中道,中正之大道也。”中道和正道相含相摄,中道包含着正道,正道又蕴含着中道,二者互为补充,有机统一。
《周易》有尚中崇正的价值取向,如无妄卦卦辞:“其匪正,有眚。”也就是说,行为有失正道,则有灾患。这说明在《周易》古经中已经开始用中、正二字来描述人的德性,但尚未见“中正”二字连用,而与之意义相近的是“中行”,共有五处。在《易传》中,“中正”二字连用共有十七处,“正中”有五处,如“位正中”“龙德而正中”等,而分述“中”与“正”的记载则多达四十余卦,如“龙德中正”“刚建中正”“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等。可见,在《易传》中,“中正”的概念已经使用得相当普遍。
来知德认为:“圣人一部《易经》,皆利于正,盖以道义配祸福也,故为圣人之书。”[9]钱大昕也指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10]这些说法也许揭示了“中正”思想在《周易》中的重要性。概而言之,“中”“正”之本意,均是从卜筮符号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概指卜筮结果好的一面,并不具有纯粹的道德意义。但在《易传》中,“中正”二字显然已不局限于卜筮层面,而具备了道德的意涵,如《彖传》无妄卦辞:“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中正”用来描述天命的特征,显然已经超出了卜筮的范围。
实际上,《易传》常以“中正”作为解释卦辞、爻辞的普遍法则而加以运用,如《彖传》同人卦:“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又如《彖传》观卦:“中正以观天下。”如此看来,“中正”的道德属性在《易传》中是十分清楚彰显了。
2. “中正止思”的医学证据
医学角度来看此病起初多为实症,日久则转虚。或因气郁化火伤阴而导致阴虚火旺,心、肾阴虚之证;或因脾伤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而导致心脾两虚之证。
朱丹溪在其医书中已有以木之“怒气”克土之“思郁”而获得治疗效果的记载:一女许嫁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无他病,多向里床睡。朱诊之,……曰,此思想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怒则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令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时许,令慰解之,与药一服,即索粥而食矣。朱曰,思气虽解,必得喜,则庶不在结。乃诈以夫有书,旦夕且归。后三月,夫果归而愈。
这个病案中采用的就是“以气治气”“以情胜情”的权宜之计。
《黄帝内经》认为思伤脾。食物在人的胃中转化成为精气,之后透过脾使精气向上、向外输送,从而滋养人全身: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思虑过多,会使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出现气结,即气机郁滞,那就会使“脾气散精”受到阻碍。有些人即使吃很多东西仍然身体瘦弱,就与此有关。
假如食物吃下去却无法转换成自身的养分,久而久之,就会气血两虚。思伤脾之后导致气血偏虚,人体就容易感受邪气,各种疾病继而产生。此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如《论语·为政》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认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11]故在此儒学之观点下,“思”之情性活动必须与“正”之内涵相应才能成就其正面之价值而得其诚,而此种乃是对“正思”之内在要求。
然而根据前文所述程颐有“中则正矣,正未必中也”的说法,即便是得其“正”也并不必然保证一定能得其“中”。业师指出若是得正而不得中,也可能会因个人情感等因素而有所偏倚,即便是合于人情礼法之正,但发用过度,依旧会思虑过度致病。
若只得正,会因私心而有所偏移,终不得中。那是否在得正之后,再做到无私,即是达到了中正呢?《黄帝内经》“刺法论”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这似乎能与孟子所谈的:“浩然之正气”有着义理上的相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那么保持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正气,又做到了勿助长,就是符合了即得正又守其中之意。
根据《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治国如同修身,若善修其身则善治其国,修身与治国之间是可以相互对应诠释。《尚书·洪范》中,言圣王之道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2]笔者认为其中阐述圣王的治国之道,也正是周敦颐所强调的“圣人定之中正仁义”之“中正”,然程颐诠释“中正”与“思”之义理关系时也提道:“中正而诚,则圣矣。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通道笃。通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3]577“中正而诚”“邪僻之心无自生”,说明了圣人通微知机而成己成人之义在内。所以就个体养生而言,其自然不会有积疑生怨,或因个人功名、情感不遂之事纷然妄动其心而使自己罹患思郁之疾,而在主体自我走出之道德实践层面,亦可因其中正之德而使他者安心不疑而显其泰和之风。
朱丹溪在《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中指出:“凡言治国者,多借医为谕,仁哉斯言也。真气,民也;病邪,贼盗也。或有盗贼,势须剪除而后已。良相良将,必先审度兵食之虚实,与时势之可否,然后动。动渉轻妄,则吾民先困于盗,次困于兵,民困而国弱矣。行险侥幸,小人所为,万象森罗,果报昭显,其可不究心乎?”治国如同治病,其原理相同,解决问题不但要考虑是否正,同时关键也要把握住中。妄动而不得中,反而会造成身体或是国家虚弱的结果。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思郁”也是在面对复杂的外在环境,内心世界的妄动而不得中的结果。内不得静则不中,且外不得正。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表现出一个自我身份在社会中所应表现出的恰当状态。由此必定复加情志的刺激,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肝郁抑脾,会影响人的食欲及对食物的消化能力,日久必气血不足,心脾失养。而坏的情绪和思维久久不得抒发会消耗人大量的精力,对其肾脏也会造成巨大负担。除了精神上郁郁寡欢,身体上更是会有心肾两虚的情况。正是:七情内起之郁,始而伤气,继必及血,终乃成劳。
三、结论
宋儒之“存天理,灭人欲”命题实践之合理性,自清以来在学术界便饱受争议。元代金华朱子学者朱丹溪,对此问题早有所警,以医学之理论为此命题做出合理性解释。其革命性地提出相火论,明确指出欲望在身体中产生的逻辑,并造成结构性影响。
在思想研究上,由于《格致余论》被视为医书因而一直未受到哲学思想界的关注。但经本文研究得知,本书有别于一般之医籍,因其在思维结构及内容上大量引用了儒学经典诸如《易》《礼记》,以及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正蒙》等著作内容,所以本书内容经由朱丹溪之思维转化,从而形成了一具有儒学深度之医学书。换言之,正如朱丹溪本人在该书序言之说法来看,《格致余论》就是一本具有身体观论述之儒学思想专著。
一方面,此书革新了传统气郁说之局限而开展了多层郁说结构之可能;另一方面,其又为儒学天理人欲之命题在相火郁说之论述下,找到一个具有身体论述基础之道德实践理据。此在医学史或儒学史上都是一件盛事,是在此意义下成就其横跨儒学医学而扩大人类思想格局之使命。
而本研究在此观点下,从儒学之观点首先发现《格致余论》之首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之论述主题与本书序文之后所出现之《饮食箴》《色欲箴》有相呼应之处,而且三者之基本关怀都可指向到《礼记》对饮食男女之欲之命题上。除此之外,朱丹溪亦将议题引导到朱子“理欲之辨”之论点上,从而使得朱丹溪在此思想背景下,得以巧妙地运用朱子“阳有余阴不足”之概念,以说明《内经》“天道实,阴道虚”之说法着实已具涵摄人身中“阳有余阴不足”之特质。而为了说明人欲容易妄动而必须统以道心之义,朱丹溪重新诠释了医学中君火相火之关系,以建立起儒学义理与医学养生之联结之可能。因此如何令原本属于天地六气之相火概念,一转成为朱丹溪医学中论述身心互动关系重要之基础,此课题实是朱丹溪所必须面对解决的。基于此,朱丹溪于《相火论》中秉持类似《易传》象天法地之观念,于是划时代性地将周敦颐《太极图》之宇宙论述形式转变为与人身对应之思维模式,并借由此种天人之对应关系,从而建立起人身内部相火存在之合理性。此后其又于《相火论》中引用王冰、刘河间对《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之气郁现象解释,改以相火概念重新诠释传统气郁产生之观点,此一革新使得传统仅以天气变化以解释气郁现象之形式之外,又开启了另一以脏腑之火而诠释气郁现象之理论。朱丹溪此种诠释系统不仅可为中医郁病治疗提供更完整的论述基础而与当代西方医学对话,同时亦可为儒学义理或理欲之辨等命题提供具有身体论述之道德实践理据,从而建立起儒学之工夫论述与医学之身体论述相互成全之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