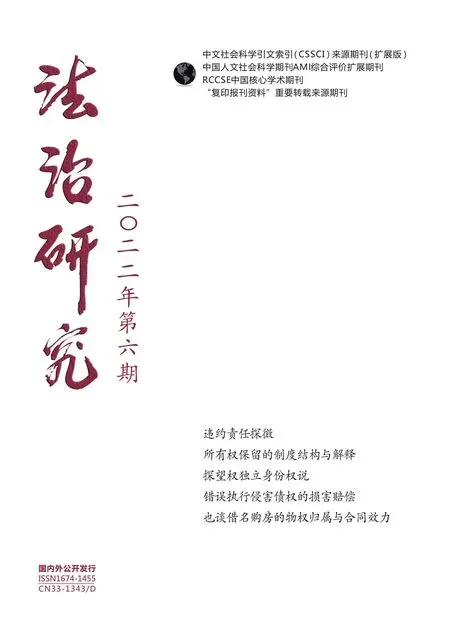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扩张解释与法律适用
2022-03-01陈霖
陈 霖
一、引言
民法现代化实现了人格去身份化。在古代社会,身份曾与人的法律人格紧密关联、被用作区分高低贵贱的衡量标尺,并依此进行社会资源分配,此身份差异被近现代人评判为不平等、非正义。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然法理论的发展,罗马法上生物人和法律人区分的人格构造被摒弃,人人平等的私法人格概念逐渐确立,现代婚姻家庭法亦基于夫、妻人格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配偶双方于意思自治下调整婚内财产关系的自由,甚至有时,这种合意在婚姻关系内部能够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之效果。在“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分居协议书》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将其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区分,承认其有效性;又进一步认可该协议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规定,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情况下在夫妻间直接发生不动产所有权变动效果,是一种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12 期(总第218 期),第 31-35 页。但是,针对此案件,无论司法实务抑或学术观点都有所争议,其中最大的难点即为:如何区别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与夫妻间赠与?诚然,两者的区分会产生“协议能否被任意撤销” “不动产所有权是否直接发生变动”之效果差异,因此本文欲在梳理此二者协议相关判例、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讨论现有法律解释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与夫妻间赠与二元对立是否必要,并假设将夫妻间赠与归至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下,论证其是否可行,进一步厘清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之法律效力,以期能够解决前述争议。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类型开放下的司法裁判分歧
现代婚姻生活的多样性带来了夫妻财产关系的多元化。虽然法律介入时曾试图固定夫妻间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类型,例如,曾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1065 条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仅限于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②参见田韶华:《夫妻间赠与的若干法律问题》,载《法学》2014 年第2 期。但是,司法实践逐渐认可了夫妻在意思合意下对特定婚姻财产所作的安排。换言之,司法实践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类型不再封闭,已然呈现出一定开放性,但是,这亦因法院立场不一造成了司法裁判结果不统一或者称之谓“同案不同判”现象。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与夫妻间赠与界定模糊
如前述“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中,法院将夫妻间的分居协议定性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但如若严格遵循《民法典》第1066 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法定事由,该分居协议的有效性将因悖于法律规范而被质疑,因此,该案二审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此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肯定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开放的前提下进行了“法律续造”与解释,此处类型法定的松动填补了法律规范的漏洞。但是,夫妻约定财产契约类型开放后给司法裁量带来的最激烈争议焦点之一为:夫妻就某项特定财产达成的分配协议究竟是夫妻间就该项财产所作赠与,抑或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 条规定的夫妻间赠与为“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一方所有的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即只要在外观上符合“约定为另一方所有”就导向《合同法》中一般赠与的任意撤销权规则,从而排斥婚姻家庭法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适用可能。然而,并非全部法院皆完全遵循此裁判规范。在“魏某与张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中,③参见“魏某与张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2019)京03 民终12087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2021年10 月22 日。婚后魏某将由其出资购买的房屋使用权约定为魏某所有,一审法院将此约定认定为夫妻间赠与,而二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因此,仅以“约定另一方所有份额为100%”为夫妻间赠与的划一式判断标准遭到质疑。而在“张某、魏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中,④参见“魏某、张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2019)鄂民申336 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2021 年10 月22 日。魏某与张某于婚前签订的《协议承诺书》载明,自魏某与张某合法登记结婚之后,魏某将自己婚前购置房屋产权中的50%划到张某名下,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二审法院则认定为夫妻间赠与。此案裁决再次印证对此两种协议定性的标准不再局限于“所有份额区分论”,而是逐步参考“协议成立时间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 条对夫妻间赠与的规定增加了“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一方房屋约定为共同所有”之情形,而《民法典》第1065 条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表述亦包括“将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财产归为共同所有”之情形,法律表述上的重合进一步模糊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一方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是夫妻间赠与抑或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界限,此种法律设计并未在原有法律规范导致的前述司法混乱中发挥定纷止争之效果,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此种裁量分歧。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与夫妻间赠与“拘束力”的差异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明文界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故司法裁判重点在于对该类财产协议的定性。各地法院一般将其与以离婚为目的订立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区分,而判决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抑或夫妻间赠与?此种界定差异将导致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效力的不同。
若认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夫妻间赠与的,则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 条,该条规则由于并未特别区分夫妻间赠与和民事平等交易主体间的一般赠与,参照合同编规则,夫妻间赠与在完成不动产登记前可以撤销,表明了夫妻间赠与不直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之立法原意,司法实践中亦基本遵循此裁判规则。如若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认定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根据《民法典》第1065 条第2款,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由于法律并未细致规定,导致引发如下一系列争议性问题:此种法律拘束力在夫妻间的具体内涵为何?是一种仅为债权性质的约束力,抑或兼具物权性质的约束力?如果认为仅具备债权效力,那么该种协议是否可以任意撤销?如果认为兼具物权效力,那么夫妻双方在意思一致的合意下是否认为该协议所载之不动产所有权未经登记即可发生变动?
为检验上述问题,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拘束力性质”以及“是否可以撤销”为统计要素,现行法院的基本裁量观点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可以依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直接发生所有权变动效果,且不可以任意撤销。⑤参见江伊:《夫妻财产协议之性质与效力——从我国四则司法判决的比较出发》,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1 期。只是关于此契约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依据,法院的裁判依据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在不涉及市场交易第三人时物权变动遵循意思主义模式,⑥参见“贺某6 等与贺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 民终1105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2021 年10 月22 日。有的认为其属于物权编所规定的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⑦同前注①。
三、关于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类型化区分的学术争议
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种类繁多,但皆因不同程度依附于夫或妻之配偶“身份”,且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应当与一般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进行区分,夫妻财产关系不适用冷酷的商品交易法则,不适用自私自利的计算理性,⑧参见李洪祥:《亲属法规则财产法化趋向论》,载《求是学刊》2016 年第4 期。夫妻财产关系的设计应该考虑以人伦秩序为基础,体现身份法与团体法属性的婚姻法的特质。⑨参见裴桦:《夫妻财产制与财产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4 期。但由于夫妻财产关系大多依附于身份关系,基于对“身份价值”或“财产价值”偏向之不同,学界对具体类型的夫妻财产协议定性与法律效力认识不尽一致。此处主要梳理归纳了对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不同类型区分的四种观点。
其一,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彼此区分独立。此种观点将夫妻约定财产制界定为一种封闭类型,当事人可供选择者有且只有三种类型,即分别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和部分共同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是对夫妻法定财产制排除适用的正当性依据,⑩参见高凤仙:《亲属法理论与实务》(增订七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版,第 115 页。其安排的为夫妻间概括性的财产关系,而非专门针对某个特定财产的处分合意。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之不同,可以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财产作出权属约定,只是面向未来在夫妻财产关系上没有拘束力。⑪参见程啸:《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与不动产物权变动——“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评释》,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不过,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都是夫妻基于各自配偶身份才能订立的财产协议,其与夫妻间赠与有本质上的不同,赠与不独为在配偶间,在其他人之间亦为可能。⑫转引自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341 页。
其二,夫妻间赠与区别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归类于后者。与前述观点类似,夫妻间赠与是普通民事主体间也可以缔结的财产协议,由财产法调整,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本质上虽为财产行为,但由于附随于身份,由婚姻法调整。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被认为是一种独创式的立法模式,法律规定允许夫妻约定任意财产制协议的所有情形,因此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即使是围绕特定财产订立的协议也被认为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⑬参见许莉:《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基于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考察》,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 年第1 期。
其三,夫妻间赠与区别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归类于前者。夫妻间对特定房产分割的约定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中的“约定”不同,是一种基于婚姻关系发生的特殊赠与,“实践中,还存在夫妻双方约定将原本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转为一方所有的情形,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方将自己在共有财产中的潜在财产份额无偿转让给另一方的行为,也应当界定为赠与”。⑭同前注②。
其四,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都可归类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该种观点着眼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间赠与的夫妻身份属性,甚至为回应婚姻家庭在现代社会萌生的新问题,将《民法典》第1065 条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视为夫妻财产约定的一般性规定,从而得以融入其他类型的夫妻间合意,如此,夫妻间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自然包含其中。⑮参见曹薇薇、黎林:《民法典时代夫妻房产赠与纠纷中的司法判决冲突及解决》,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 年3 月第2 期。只是,如果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作为夫妻婚内无名财产关系协议参照适用的万能钥匙,不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区分,是否在法律解释上过于泛化。
综上,即使学理分类上观点纷呈,但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法律效力仍然容易形成通说,上述观点皆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不可任意撤销且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至于夫妻间赠与的法律效力,相较于在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上达致的基本共识,学术观点则呈现出明显分歧,在上述第一、二种分类下,夫妻间赠与并没有在“质”上与合同编的一般赠与区别,因此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且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第三种观点较为折中,将夫妻间赠与和一般赠与联系却又区分,在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上两种赠与具备同一性,但夫妻间赠与是以“婚姻为基础的赠与”,因此又与一般赠与不同,它不能被任意撤销。第四种观点则将夫妻间赠与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框架内,将前者视为后者的下位概念,不仅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而且不可任意撤销。而关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除去第一种观点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财产复合协议类型,当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具备物权拘束力以外,其余观点将其归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或夫妻间赠与,从而在法律效果上有所不同。毋宁说,恰是为了论证哪些夫妻财产协议具备物权拘束力,学说才基于不同原理立场出现了上述分类,有的观点扩大财产编规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适用空间,将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既有“身份因素”又有“财产因素”的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导向一般赠与合同法律规则的适用;有的观点则为了强调“身份性”因素在夫妻财产协议上的重要性,为保护夫妻双方的高度信赖利益,而将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等都定性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从而在当事人之间优先适用婚姻家庭法规则。
四、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扩张性解释
夫妻关系由夫妻人身关系与夫妻财产关系构成,根据《民法典》第464 条,夫妻身份关系协议在婚姻家庭编未有规定时,可以参照合同编规则适用,实现了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的融合贯通,亦昭明夫妻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的特殊之处。⑯从法条表述角度而言,立法者似乎指的是纯粹性身份关系协议。下文所言身份关系协议,在意义上也作此狭义解释,特别与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区分。针对夫妻间一般财产关系协议,⑰根据前文学术观点论述,这里的夫妻间一般财产关系,指代夫妻间赠与、买卖等法律关系,即不只在夫妻之间,在一般民事主体间也可以成立的财产法律关系。虽然在法律适用上学者观点不一,但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依旧秉持了直接参照适用财产法规则的立场。只是夫妻间身份关系协议与夫妻间一般财产关系协议有时又非完全分离,于二者的模糊交界处存在着一种身份财产复合型协议,⑱即依赖于夫妻身份关系才能形成的夫妻财产关系,如前文所述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等。加之意思自治在现代婚姻家庭领域的进一步渗透,夫妻在真实意思表示一致下订立的婚内财产协议类型呈现出“无名化”趋势,如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等,这已超越了婚姻家庭编既有的法律规定,前述司法与学术中的争议即聚焦于此类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如何嵌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在具体适用时是以身份关系法偏向为主,还是财产关系法偏向为主。
(一)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开放性立法模式
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是一种典型的身份财产复合协议,附随于结婚这一法律事实,具备较强的身份专属性、伦理性,其他一般民事主体不得代理亦不可为之。关于其立法模式,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有自由约定式与选择约定式,前者如日本、英国,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规定、不抵触善良风俗,当事人即可在意思自治下自由约定夫妻财产的具体类型;后者如德国、瑞士,为强调对债权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的维护,当事人不可自由约定协议的内容,由法律预先规定可供选择的财产制种类。⑲参见戴东雄、戴瑀如:《婚姻法与夫妻财产制》,三民书局2009 年版,第136 页。我国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类型是封闭式的,还是开放式的,亦存在对立观点。坚持封闭式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有限,赞成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有且仅能遵循类型有限原则,⑳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6 页。认为此是衡平婚姻关系内部当事人自我决定与婚姻关系外部交易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合适立法选择。并且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封闭性是其与夫妻间赠与区分的重要标准,21同前注⑪。如果开放将会带来两种夫妻间财产协议认定的混乱。主张开放式观点者提出,将夫妻对婚前、婚后财产的约定概括为共同所有、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夫妻双方财产归属可以约定的所有情形,即使是夫妻间针对特定房产的约定,亦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范畴。22同前注⑬。
在婚姻家庭现代化变型之际,个人主义已经在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类型法定空间以外滋养出各种事实类型,如果继续僵化地对待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将进一步加大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分离。而所谓类型“封闭性”带来的便利,反倒成为加剧现实司法裁判混乱的祸根,仅通过形式化地判断某项夫妻财产协议是否具备“要式性”从而界定是否受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调整,并不符合家事诉讼中的实质正义。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扩张下婚内财产协议的纳入与区隔
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类型开放是其得以扩张适用的论证前提,本部分进一步探讨广义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作为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上位概念的可行性。
其一,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纳入之可能。立法上,针对夫妻间一般财产关系,总聚焦于“财产”因素上,而忽略了因为“夫妻”身份在先而带来的异质性。参照人格权在夫妻间行使的界限,对此权利的保护相对于其在一般民事主体间而言,前者更强调在婚姻关系中的合理期待性,从而论证了人格权在夫妻间的有限保护。那么,是否可以类推认为夫妻间一般财产关系也应与平等民事交易主体间的财产关系有所区别呢?学界已关注到此问题,亦不乏对夫妻间赠与任意撤销性的批判,却又因夫妻意思自治在物权变动效果上的差异,多数观点建议将夫妻一般财产协议与夫妻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区分,进而将夫妻间赠与归属于前者,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归属于后者。
但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夫妻间赠与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却可以,此种差异性的法律依据何在?无论是夫妻间赠与,还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签订协议的夫妻双方均没有进行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大概率源于夫妻身份上产生的高度信赖。如果是为了保护婚姻关系外的交易第三人,而否定夫妻间赠与的物权拘束力,那么,为何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可通过婚姻关系的内外部区分证成其在夫妻间直接产生物权变动效果?23同前注⑪。既然如此,夫妻间赠与的物权效力是否可采取同种论证逻辑?在德国法中,较少将夫妻间的给予行为认定为赠与,而是视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从而不适用有关于赠与的规定。2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9 页。如此将“身份伦理性”同时作为夫妻间赠与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价值偏向,将两类财产协议的法律效果在婚姻关系内外部进行统一,是否反而能够解决司法实务中不知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定性为夫妻间赠与还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之困惑呢。概言之,在既有法律体系中,可以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进行法律上的扩张解释,建议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可以涵盖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其二,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区隔。虽然同属夫妻间财产分割协议,但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并不相同,在前述“ 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案件中,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时签订的分居协议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被认为有所不同,正如审理法院之观点——“分居协议离家不离婚”,这与以婚姻关系解除为目的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存在微妙却本质的差异。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而言,我国学说中有赠与说、附条件法律行为说、附随身份说等观点,25参见叶名怡:《离婚房产权属约定对强制执行的排除力》,载《法学》2020 年第4 期。甚至有学者将其归为一种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26参见李洪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类型、性质及效力》,载 《当代法学》2010 年第4期。但是,在功能上,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中当事人对婚姻共同生活期待或维持的意愿不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婚姻关系结束后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清算。从生效时间而言,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一般情况下,一经成立即生效;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一种附生效条件的身份财产复合协议,这与人身关系的变动附生效条件不同,此种条件是否成就仍受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控制,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69 条,主要表现为双方同意离婚且对财产分割无异议,否则,人民法院将认定其无效。从法律效力而言,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物权变动以及是否可任意撤销上存在较大争议,与此问题上的莫衷一是相反,在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能否直接产生物权变动这一问题上,学界普遍持否定意见。27同前注。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适用可以推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但是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却不能涵盖于其中。
五、婚姻关系内外部视角下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效力构造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财产协议大多是与亲属“身份”交织的财产行为,婚姻家庭内部“人”的利他性异于财产法中“人”的利己性。《民法典》背景下,财产法原理的过度适用有可能淡化家庭内部的感情信任,因此身份法偏向者始终秉持这样的立场:婚姻家庭中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因具备伦理性,应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但是,为与《民法典》其他编在法律体系上保持融洽,婚姻家庭编的规范适用又不可完全与财产法规则相抵触。为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法律效力在婚姻关系内外之区别对待。设想若能将这种效力差异视角也适用于夫妻间赠与之情形,将能照顾婚姻关系中夫妻间在情感上的高度信赖感,亦能兼顾婚姻关系外市场交易第三人的民事权益。
(一)债权效力: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非任意撤销与法定撤销
婚姻家庭法的现代化促进夫妻一体主义转向夫妻别体主义,夫妻的人格独立消除了人身关系之依附,实现家庭内部夫妻人格平等,保证意思自治下夫妻间身份财产契约的自由与公平,夫妻间约定财产协议的有效性因此得到肯定。至现代社会,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种类已经超越了既有法定类型,如“分居协议”中涵盖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形式上因不符合《民法典》物权编共同共有财产分割的法律构造,其有效性遭到质疑。推崇“婚姻法私法化”的美国法院从20 世纪后半期开始,已经在司法裁判中逐步肯定分居协议的效力;近年来美国学者进一步提出如果仅依据财产契约效力判断规则在诉讼中进行程序上之公平审查,将难以真正落实分居协议的实质公平理念,应考虑身份关系伦理性,给予特殊的审查机制及判断标准从而衡平身份财产关系的公平性需求。28Sally Burnett Sharp,Semantics as Jurisprudence:The Elevation of Form Over Subst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Separation Agreement in North Carolina[J].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1990,69 (1):319.我国《民法典》第1066 条虽限定性规定了婚内财产得以分割的两种情形,但其适用前提为请求法院分割,并未完全否定当事人意思自治下所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效力。另外,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基于《民法典》第1065 条所为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并不限于对当事人所有财产的概括性约定,现实常态恰是多为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权属约定协议,29同前注⑬。因此夫妻间围绕某项财产订立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有效,亦可受第1065 条法律规范调整。
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效力在债权法上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是否可以被任意撤销?《日本民法典》第755 条、758 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关系类型需在婚姻成立时确定,结婚后不可随意变更,在立法上原则性否认了夫妻一方对约定财产协议的任意撤销权。而学者担心如果此种协议可以被任意撤销,可能造成夫妻中一方为谋取自己利益而欺压对方之现象。30《日本民法典》第755 条规定:“婚姻申报前,夫妻未就其财产另行订立合同时,其财产关系依下一分节之规定”。同法第758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一方管理另一方财产之情形,因管理不当而危及其财产时,另一方得向家庭法院请求自己作出其管理;就共有财产,得与前款之请求一同,请求其分割”。参见王融擎:《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新华书店2018 年版,第704-705 页。《法国民法典》第1396 条、1397 条则采取了有限认可之立场,即在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成立且生效两年以后,考虑到家庭的利益或存在侵害债权者利益情形时,始认夫妻间约定财产协议的任意撤销性。31参见二宮周平『新注釈民法(17)親族(1)』(東京有斐閣,2017 年)233 頁。我国的婚姻家庭长期以来受婚姻共同体主义的影响,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订立大多为保证未来婚姻生活之和谐而进行夫妻财产关系的安排,即使是分居协议也并不想解除婚姻关系,这亦是其与离婚协议在订立目的上的本质区别。婚姻家庭领域对意思自治的有限认可排斥了夫妻财产关系完全照搬《民法典》财产编规则,如果坚持只要不动产登记之前夫妻一方都享有任意撤销权,那将有可能消释婚姻关系中的脉脉温情。
夫妻间赠与亦同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 条之“夫妻赠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前可以参照合同编赠与合同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忽略了夫妻间赠与和一般赠与的本质区别。两者虽都为无偿合同,但是多数情况下,夫妻间赠与的动机在于回报、感谢另一方在婚姻关系中所作的贡献。即使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658 条第2 款之“赠与人不可任意撤销道德义务性质赠与合同”,夫妻间赠与亦可能不被任意撤销,但这需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有较大的不稳定性。现有的法律体系在适用上将夫妻间赠与导向一般财产关系,无疑忽略了前者的伦理身份性,又将其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刻意区分,反而徒增司法裁量中甄别两者的困惑,莫不如将夫妻间赠与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范畴下,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否定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此种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若存在总则编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以及合同编赠与人法定撤销权行使之情形时,可以在尊重婚姻家庭法伦理特性基础上再选择性地参照适用。譬如,夫妻间赠与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后,将排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 条“任意撤销权”的行使,那么是否意味着《民法典》第663 条32我国《民法典》第663 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规定的一般赠与合同中出赠人的“法定撤销权”完全无法影响夫妻间赠与或者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从《民法典》第464 条规定的身份关系协议可以有限参照合同编规则的立法原意观之,似乎并未完全否定财产编规则对婚姻家庭法的反向影响,即吸纳了夫妻间赠与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并不彻底与合同编赠与合同规则绝裂。对赠与合同第663 条第1 款第1、2 项合情合理地参照适用恰能填补现有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可否撤销上的立法模糊,也可给当下司法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过于绝对的不可撤销增加灵活解释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在参照第663 条第1 款第3 项的“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如果夫妻一方将维系婚姻关系稳定作为不动产赠与的附加义务,一方离婚时以对方没有履行此义务为由,可否行使法定撤销权?虽然有学者从法律不应保护未遵守赠与中承诺的一方保有此受赠财产的权利之角度论证了此种情形下赠与的可撤销性,33同前注⑬。但是离婚或结婚是婚姻家庭法所保护的当事人自由之一,将这种人身行为作为赠与合同所附之义务本身即为不妥,所以在参照第663 条第1 款第3 项,判断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可否法定撤销时,需明确此种附加义务不可为人身性义务。
(二)物权效力:债权意思主义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有限性
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能否直接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键在于,对此协议的定性是“财产性”的,抑或“身份性”的;前者将其置于《民法典》第209 条规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之登记生效主义下,后者将其视为同条的“法律另有规定”从而不适用该条的物权变动规则。我国相关学说与实务虽有分歧,但是多数立场为:当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能够直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34参见本文前述第二、三部分的论述。与此相悖,夫妻间赠与通常被认为单纯发生债的效力,作为其标的物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仍需遵循公示原则。35同前注②。只是此种概念定义上的明确区分恰是导致司法裁判分歧的直接原因,多数法院在认定夫妻间某个财产约定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或是夫妻赠与合同时较为随意。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祛除这两种夫妻间财产协议在是否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上的效果差异,基于二者本质内涵上都有“身份性”因素的特殊性,统一肯认它们在引起不动产物权直接发生变动时的积极效力。虽有观点也将夫妻间赠与包含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但认为这是一种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36同前注⑮。重要的不是当事人订立财产协议时的意思表示,而是婚姻关系本身所具备的公示性,才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可以不完全遵循物权编的一般规则,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之物权对世性,认为其亦可对抗婚姻关系外之第三人。实质而言,此种物权变动仍是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其正当性基础在于这是一种债权意思主义下的物权变动模式,且仅在不涉及第三人时发挥效力。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并非采取单一的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如第333 条第1款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的规定也认可了债权意思主义。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由于包含伦理情感因素,采取免于程序性登记的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更为契合。
如果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扩张后,将夫妻间赠与纳入并认可其物权变动拘束力,是否会带来混乱?此种担忧实无必要,反倒可利用此种扩张的法律解释路径减少司法裁判分歧。夫妻间赠与和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法律关系成立目的上具备一些相似性,而《民法典》第 464 条关于“夫妻身份关系协议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时可以根据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更是加强了夫妻身份财产复合协议、夫妻一般财产协议和一般财产协议的参照交互性。因此,如果认为赋予夫妻赠与合同物权效力会引发混乱,何不忧虑具备物权拘束力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亦具备负面影响。所以,此种理论窒碍不独针对夫妻赠与合同,在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中亦存在,概言之,问题根本为: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是否会增加婚姻关系外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受侵害的风险。如果将婚姻家庭视为完全封闭的团体,配偶间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财产只在夫妻之间流转,并不涉及市场交易第三人,自然不存在交易安全保障。但婚姻家庭中的“人”亦为市场交易平等民事主体中的“人”,当作为名义物权人的配偶一方将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时,另一方仅依夫妻赠与协议或约定财产协议可否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此时再坚持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之物权拘束力,无疑增加了第三人的交易风险,为解决此问题,建议可从两个方面进行限制:
其一,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效力限定在婚姻关系内部,不能对抗婚姻关系外的善意第三人。虽然婚姻家庭编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需采取书面形式,具备要式性,但是并未要求进行登记,造成夫妻关系内部的意思合意无法对外公示,第三人将难以知晓,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在现有立法规范上,实质已经表明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无法对抗婚姻关系外第三人之立场。根据《民法典》第1065 条第3 款规定,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除非能够证明债权人知晓夫妻间的约定财产制契约,否则依旧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8 条规定,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所有房屋,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取得房屋所有权,参照此条规定,在婚姻关系内部基于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可能造成事实物权人与名义物权人的分离,但是这种法律效果无法对抗婚姻关系外的善意第三人。
其二,在婚姻关系内部,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有限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则。除去存在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之情形,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夫妻间是否绝对有效?在《民法典》第663 条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行使的法定情形中,除了“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因与人身行为不可作为附加义务相关联而需谨慎参照适用以外,其余两项“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以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几乎可以直接作为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法定撤销的情形。婚姻家庭法的现代化变革保障婚姻关系完全破裂后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同时也尊重这段婚姻关系中当事人曾经在意思一致下所作的夫妻财产关系安排,但这并不意味因夫妻关系的亲密即放任此种意思自治在婚姻内部的绝对优势。法官在面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时,不能仅止步于程序性的裁判,更应发挥家事诉讼中的职权主义探究订立此种协议时配偶一方是否存在占有财产的恶意,并参考前述赠与合同法定撤销的情形,决定是否支持夫妻一方撤销上述契约,因为一旦判决撤销,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那么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物权拘束力将随之消失。如此,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约束,扩张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之效力将能与《民法典》各编在体系解释上保持和谐一致。
六、结语
若将夫妻视为市场交易中的平等民事主体,当然可以互相缔造一般人之间的财产法律关系,但是,基于配偶身份的伦理特殊性,此种财产法律行为不得不遵循婚姻家庭法的团体逻辑。夫妻间赠与即因身份财产的复合性,被认为应当与一般赠与合同有所区分,其在现有法律规范中的任意撤销性亦饱受学界中支持婚姻财产关系特殊自治原理者之诟病。加上私主体个人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领域不断渗透,夫妻间财产关系的法定类型不断解消,诸如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一类的夫妻财产协议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涌现,又因司法裁判中存在将其界定为夫妻间赠与抑或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分歧,导致该类财产协议在“能否被任意撤销”“是否直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上呈现效果差异。为实现既有法律规范对夫妻财产关系协议多样化的周全调整,法官在进行法律续造时,往往从夫妻间是否具备赠与真意切入,继而再对夫妻无名财产协议进行定性,但如此大费周折的实质判断却又未必效果如意。建议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进行解释论上的扩张,将夫妻间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等夫妻身份财产复合协议一并纳入。在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进行效力界定时,既要坚持夫妻不完全共同体“伦理秩序”的价值优先性,又要避免这种特殊性与财产规则过度分离造成的民法典体系紊乱。因此,在价值论上,可有限承认财产法中意思自治原理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反向渗透,同时谨防个人主义对婚姻家庭中利他主义的完全替代。在方法论上,以功能主义为进路,交替使用婚姻法与财产法规则,在婚姻关系内部,坚持身份法团体性之主轴,肯定此种契约的物权拘束力与非任意撤销性,在婚姻关系外部,遵循《民法典》财产规则的“意思自治”与“物权公示”逻辑,辩证地对待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在婚姻关系内外部有所差异的效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