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功能
2022-03-01夏元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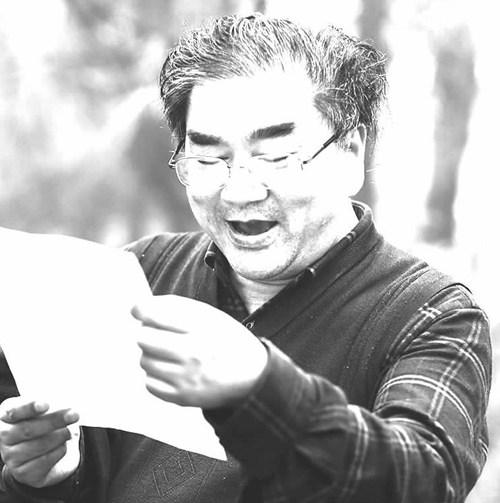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一个血肉丰满、生动有趣的形象,其在《红楼梦》中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曹雪芹之所以要塑造这么一个形象,是基于很多种考虑的。首先,刘姥姥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大观园内外许多人物的性格。第二,刘姥姥也是一个极好的见证人,正是这个乡妪见证了贾府的荣枯。第三,刘姥姥还是一个绝佳的视角,正是透过她,大观园另一番图景才得以显现。
刘姥姥这个形象,有说是正面的,有说是反面的。喜欢她的,赞其智慧;讨厌她的,斥其圆滑。其实这种好坏二元思维并不可取。鲁迅曾说过,《红楼梦》一书的好处在于它叙好人并非全好,坏人也非全坏,即《红楼梦》中人并没有脸谱化。见仁见智固无不可,要紧的还是从这个形象本身看世态,体会作者的用心,还其艺术形象的本来面目。
刘姥姥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其多维性格,正是通过她与周围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物塑造离不开关系,孤立写人很难成功。现在仅就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来谈。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可以分成三节。第一节刘姥姥家中定计,即与女儿女婿商量如何到贾府找王夫人,寻求王夫人的帮助,以解燃眉之急。第二节刘姥姥带着外孙板儿见贾府仆人周瑞家的,请求其引荐。第三节刘姥姥见王熙凤。这三节刘姥姥分别与三个人物打交道。第一节与女婿狗儿,第二节是周瑞家的,第三节是熙凤。刘姥姥在这三个人物跟前表现完全不同,展现了性格的不同侧面,层次分明,又不失其统一性,充分显示出曹雪芹刻画的深细。
本来,第六回写刘姥姥,真正落脚点是王熙凤,第一次正面展示王熙凤当家管事的才干,刘姥姥其实不过是穿针引线的人物。但就是这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在这一局部竟然成了主角,大有抢凤姐戏的嫌疑。凤姐在这一节固然精彩,而刘姥姥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比一般小说的敷衍。
刘姥姥是个什么人物?书中只给了一句话的交代:“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意思无非是说刘姥姥非等闲乡妪,她是见过世面,有很多人生经历,其见识不可小觑的人物。正因其年高,又是一个寡妇,人生的许多艰难苦涩见得多,体会得深,是一个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老人。所以这个刘姥姥就不是一般的刘姥姥。她是村妪,但她并不缺少幽默,甚至颇富智慧。到后来,她知道了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贾母眼中的意义,最初见凤姐的局促惶恐就不复存在了,而成了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即用自己装疯卖傻的表演,赢得贾府上上下下几十口的欢笑。
有人将这看成是刘姥姥的逢迎,而我却要将之定位为智慧。我以为,与其说贾府中人在捉弄她,不如说她在捉弄贾府中人。刘姥姥在她的成功表演中,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相反,她找到了与这个豪门世族对话的资本。她带来的时鲜瓜果可以解馋,她的表演可以博得贾母的欢心,她从贾府中得到的一切是她付出的回报,她根本用不着拘谨。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她的经见,不是她的胆识和智慧,都无从谈起。这也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因素。
刘姥姥作为一个富于智慧的鄉妪形象,她的幽默,甚至她的行为艺术,都绝对一流。她没有其他资本,只能凭自己的一张嘴,既迎合了贾母,也感动了宝玉这样的公子哥儿,甚至还赢得了王熙凤的信赖。语言为她赢得了一切,使她从一个向贾府打秋风的可怜虫,变为给巧姐提供保护的义媪!所以只看到这个形象滑稽可笑的一面是错的,这个人物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们还是来说第六回中刘姥姥的精彩表演。说了,这一回有三节,三节中刘姥姥分别与三个人物对话,三种对话各各不同,显示出刘姥姥性格的不同侧面,精彩纷呈。
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刘姥姥面对的是他的女婿狗儿,一个无多大本事,光知道“闲寻气恼”的庄稼汉。刘姥姥对她的这位姑爷,可谓知根知底,所以说出来的话,理直气壮,居高临下。她认为作为一个庄户人家,最要紧的是本分,“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言下之意,这位姑爷有点逾越了庄家人的本分。她批评姑爷:“你皆因年小的时候,托着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这言语不可谓不尖锐。
但仅能批评不够,难得的是她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让狗儿到贾府寻找机会。她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这不仅是一种见识,还是一种主动的生存策略。而且她向狗儿提出如此建议,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而是基于对两家过去的关系以及王夫人的分析和了解。特别是王夫人,如今是贾府的当权派,“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何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话说得不是很肯定,但有理有据,并不是心血来潮,显见得她对这件事是深思熟虑的。
从她对姑爷的批评,到提出建议,到分析成功的可能性,有条有理,没点见识的老妇是断断做不到的。这时的姥姥可是站得高,看得远,说话没有半点忸怩,令人佩服。
第二节交涉的对象是周瑞家的。周瑞家的虽然是王夫人的陪房,是贾府有头有脸的仆人,但比起刘姥姥来,那可是不能同日而语。可是刘姥姥见了周瑞家的,并不怯场,而是不卑不亢,得体大方。刘姥姥对周瑞家的以“周嫂子”呼之。“好呀,周嫂子!”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而刘姥姥之所以不怯周瑞家的,是因为她了解周家与他们王家的历史,当年周家与人争买田地,得到过狗儿的父亲的关照,王家有恩于周家,故刘姥姥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周瑞家的说话,并不觉得低人一等。
由于没有心理障碍,所以当周瑞家的问她“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时,她答得十分得体:“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面面俱到,既抬举了周家嫂子,又没有降低自己的身份;既道明了目的,又表达了对周家的亲近。
而当周瑞家的说起王熙凤,她也不失时机地发表评论:“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自己竟成了识千里马的伯乐!夸了别人,也没忘了抬高自己。但这番对话与前相比,平等中透着亲近,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训。这也是她的真聪明。
第三节是面对王熙凤。还是这个刘姥姥,在女婿面前可以侃侃而谈,在周瑞家的面前也不失风度礼数,可到了王熙凤跟前就拘谨起来了,话也不会说,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见了自鸣钟不识何物,听其声,居然以为是打箩柜。而见了平儿,竟然以为就是凤姐,才要称“姑奶奶”,被周瑞家的一语给救了。开口就不得体,什么“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话是实话,却太过直白。所以凤姐要说“这话没的叫人恶心”。当周瑞家的让她说出此行的目的,她几乎有点张口结舌了,一面推出板儿:“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弄得凤姐以为她不会说话。其实刘姥姥何尝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她在女婿面前,在周瑞家的面前何等伶牙俐齿!关键是她面对的对象变了,还有就是那种向人开口的难堪。
首先看凤姐的威仪气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俨然是老佛爷。刘姥姥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先是居室里的陈设,再是平儿的打扮,让刘姥姥先怯了三分,再出来一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凤姐,就是再会说话的刘姥姥也没法开口了。这就是气馁。此时的刘姥姥完全没有找到她与眼前这位少奶奶交接的支点!在女婿那里她是出谋划策,在周瑞家的那里她可以叙旧寒暄,可她如何对凤姐?一个人,当与另一个人失去了交往的支点,身子一下子矮了下来,只能仰视,两股战栗,还哪来的从容睿智。这是一。
第二点更关键。人常说人不求人一般高,偏这姥姥今儿要求人。这求人的滋味是何等的难受,不说吧,达不到目的,说吧,难堪尴尬!所以刘姥姥还没开口就红了脸,而作者给的一个词竟是“忍耻”!我不知道家道败落之后的曹雪芹有没有求乞的经历,他的朋友说他“举家食粥酒常赊”,想来他对这种求人的滋味定不陌生。杜甫有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我觉得曹雪芹通过刘姥姥传达出来的屈辱的滋味,甚至比杜甫的悲辛更沉痛。
还是说“关系”。一进荣国府,是刘姥姥第一次亮相,却如此鲜明生动,关键在于作者展现了刘姥姥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刘姥姥的多元性格,含蕴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三个关系,由俯瞰,到平视,到仰观,对象逐渐抬升,刘姥姥却一步步变小,最后小到几乎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人物语言由丰富健朗,到不卑不亢,到语无伦次,步步与人物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处处体现出作者对人情世态的精密观察。
在《红楼梦》中,刘姥姥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叙事,这在第六回上可以集中体现出来。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有一段“元叙事”。
所谓“元叙事”,简单说就是关于叙事的叙事,也就是将作者写作构思的过程当作了叙述的对象。第六回的这段叙述,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信息,仿佛作者写到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与袭人初试了云雨情之后,一时之间没了叙述头绪,不知写什么好了。因为贾府之大,人事多繁,从哪一处叙述才是头绪?作者遇到了叙述的瓶颈,感到困惑。所幸有了一个刘姥姥,这才茅塞顿开,叙述才得以接续下去。那么,第六回刘姥姥的故事,对于全书的叙述来说称得上“起死回生”了,有着非凡的意义。
第六回刘姥姥的故事,等于又一次为《红楼梦》开头。其实《红楼梦》有好几次开头,但第六回之前都带有“楔子”的性质。
第一次開头是第一回:“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讲述的是《石头记》的来历,亦即本书的来历。原来本书都是刻在石头上的故事,是那块经过锻炼之后又无才补天的石头,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帮助下,幻形入世,于红尘走了一遭,经历了人世的繁华与悲惨之后,复归青埂峰的故事,即所谓“石头记”。记于石头,亦为石头所记。这种神话式的开头,既为全书的故事带上了魔幻色彩,同时又为全书的叙述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既不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又不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是一种自由出入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第二次开头是甄士隐的故事。甄士隐与《红楼梦》的主体故事既有联系,也有分别。联系表现在,甄士隐是小说中另一悲剧人物香菱的父亲,又与贾雨村有旧。分别在于他并不是《红楼梦》主体故事中的重要一员,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其实甄士隐的意义在于,他既是贾宝玉人生的缩影,带有象征性,又在现实的层面上回应了小说主题:“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甄士隐在叙述上有引出贾雨村的便利,而贾雨村与黛玉和宝钗都有瓜葛,这一带就可以带出一串。但这并非关键,关键还在于他的隐喻性,是关系到小说的整体思想的,与石头的故事异曲同工。第三次开头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四次开头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这算是对贾府的宏观交代,以及对《红楼梦》中女性命运的预告,为的是让读者能够理清小说人物关系,也对众多女子的人生悲剧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也是作者写作的蓝图。而进入事件性的开头,一个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个是贾雨村乱判葫芦案,《红楼梦》的故事似乎开演了。其实这两个开头还是带有介绍的色彩,就像下围棋中的布局,真正酣畅的叙事还是没有打开。而真正打开叙事,便是第六回了。所以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一至五回全部是“楔子”,第六回起方入正文。
为什么第六回有如此巨大的叙事功能?让我们细细分析。第六回写的是什么?两件事。一件是承上回神游太虚境而来,写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情,表明宝玉和袭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写宝玉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只是略写,真正详细叙述的却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为什么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一个很好的叙事头绪?我想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是《红楼梦》的核心内容。《红楼梦》的真正主体,还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以及作为“末世”的贾家的败落。特别是前者,《红楼梦》开篇就说得清楚:“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为金陵十二钗立传,才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内容,虽然黛玉、宝钗是其中最重要者。
要想写出众多年轻女子的悲剧命运,写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单靠宝、黛这条爱情线远远不够,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支柱。这个支柱是谁?我以为是王熙凤!只有王熙凤向内可以链接大观园及府中上上下下的主子、奴才,向外可以辐射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王熙凤既是荣府的管家,又是一个年轻泼辣的媳妇,视野更加开阔,几乎可以全方位辐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熙凤才是《红楼梦》中的头号角色,也是刻画得最精彩的一个形象。第六回表面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而真正的戏是落脚在凤姐头上的。凤姐作为全书的杠杆,第六回才开始撬动。第六回之前王熙凤就出场了,黛玉进贾府时她就有精彩表演,但那不是她的主场,故事不好从她那里展开。只有到了第六回,王熙凤才真正成为主角,后面的叙述很自然地就流淌起来了。这便是第六回结构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是《红楼梦》的叙述风格。《红楼梦》不同于四大名著的其他几部,既非神魔,也非历史,亦非英雄传奇,而是所谓“世情小说”。用现在的观点,《红楼梦》的叙事是颇“生活流”的,虽然匠心经营,却又随物赋形,不以情节的跌宕见长,而是凭细节取胜,所有精神尽在家长里短的日常叙述之中展现。前面几次开头,故事性强,传奇色彩浓厚,而没有真正进入日常的生活细节。黛玉进贾府写得很生活化,但顺着写下去又太漶漫,没有头绪。只有刘姥姥进府,才打开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才使小说的世情化风格得以顺风顺水,才是个头绪。既细密,又不支离漶漫,所以才是头绪。顺着黛玉进府,接着来个宝钗,接着三人口角争斗,很明显走的是故事的套路,事件胜过生活细节,《红楼梦》就不复存在了。叙事必须得有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是从第六回才开始建立的。
夏元明,1957年出生,湖北浠水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喜欢阅读废名、汪曾祺等人的抒情小说,撰写过数十篇论文,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爱好诗歌及古典小说,出版过《中国新诗30年》《田禾新乡土诗鉴赏》及《小说红楼梦》等专著。偶写散文,有散文集《满架秋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