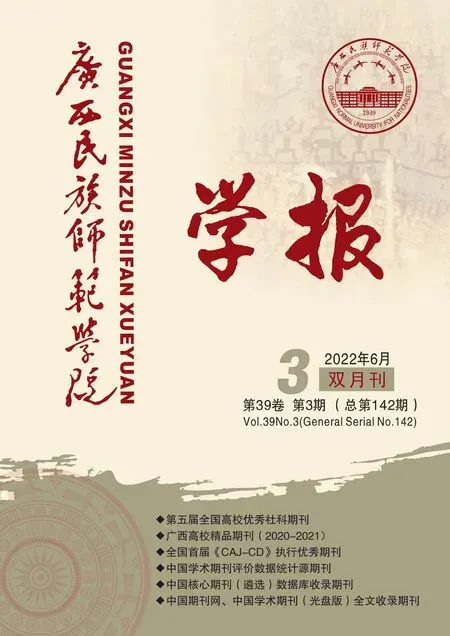“顶牛爷”人物塑造方法
——兼谈凡一平“上岭村”长篇系列的叙事策略
2022-02-27杨勇
杨 勇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凡一平是文学“新桂军”的主力成员。评论家温存超曾提出“凡一平的短篇小说创作,前期多为农村生活题材,1992年开始出现城市生活题材,1993年以后以城市生活题材为主”[1]103。虽然这是据其短篇小说的创作主题进行分期,但凡一平似乎是在此后的很长时间才将他的视线再度转向农村。他以故乡上岭村为背景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2013)、《蝉声唱》(2019)、《顶牛爷百岁史》(2021)。与凡一平前期的小说相比,这三部小说在叙述表达上更为凝练简洁、技法结构更加精巧成熟,在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的同时,试图从更深层次揭示幽微复杂的人性。正如《上岭村的谋杀》中派出所所长田殷评价警员黄康贤说的那样:“他虽然没有后台,没有钱,但是他有非凡的气质和品格,更有一颗王者之心、仁者之心,这些富贵相、帝王气我们没有,都没有。他是龙,我们是虫。”[2]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蝉声唱》中的蓝必旺,33岁突然从大富大贵跌入贫穷的境地,但我们知道,在浴火重生通往成功的路途上,“命运一定要将他在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3]193,不过只要有非凡的气质和品格支撑,蓝必旺一定会再次成就一番事业。“非凡的气质和品格”就像是凡一平上岭村人物塑造秘诀,贯穿着他的创作。
一、顶牛爷“非凡的气质和品格”
《顶牛爷百岁史》的主人公是顶牛爷。乍一听“顶牛爷”这个名号,会以为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厉害人物,作者巧妙运用了一词多义,“顶牛”在方言中,既可解释为与人抬扛、坚持己见,也可解释为对人的夸赞,“顶牛”就是“非常牛”的意思。而顶牛爷名号的来历显然更多的是因为“喜欢处处与人顶撞、斗狠”[4]64。比起上述两个年轻人黄康贤和蓝必旺,顶牛爷终其百岁生涯都只是个最平凡的普通人,“他困苦可怜、孤苦伶仃,像一棵被雷劈过、被刀砍过、身上满是鸟屎的残损肮脏的树”[4]232。甚至可以说,他过着贫困潦倒的一生。
年轻时的顶牛爷给团长老乡当勤务兵,团长嘱咐他:“一旦饭点我还没回来,你就跑,说明我被抓了。”已经提前得到这样的忠告,顶牛爷却没跑,他也因此被抓、被逼迫做了假口供,被强行用他的右手拇指摁了手印。开庭审判团长时,判官拿出证词,让顶牛爷承认,但他矢口否认。判官说,你还想抵赖,你的手印可在上面。这时,顶牛爷举起右手,说,大家看,我右手有拇指吗?原来,顶牛爷因为不愿做伪证,砍掉了自己的大拇指,“丢车保帅”。因为他不肯在庭上作伪证,最终团长得到从轻发落,这是传统价值观中的忠义,也是一种守节。
在台儿庄战役中,顶牛爷被派去督战,所谓督战,就是督促战士英勇杀敌。督战之人,有权射杀逃兵。当旅长的小舅子带领士兵逃跑,顶牛爷恪尽职守、铁面无私将其枪杀,而后顶牛爷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其他逃兵重上战场与日本兵殊死搏斗,“面对凶狠迅猛、拼死一搏、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中国军人,日本鬼子惊呆和吓坏了,最终无法招架,弃炮而逃”[4]25,中国军队一个营,最后拼杀至只剩三人。但顶牛爷并不愚忠,面对战争,他也有判断的智慧。到1949年面临与解放军的战斗,顶牛爷又被派去督战,同样面对逃兵,这一次,顶牛爷却让逃兵跑了。他认为,“这种对死难同胞的心疼与抗日的牺牲大不一样。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心疼中犹然有一种尊敬。而这却是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不值得,除了心疼,还觉得可怜”[4]28。他果敢地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顶牛爷也有过可以发迹的机遇。1949年,全国即将迎来解放。29岁的顶牛爷和同乡韦正年作为国民党兵被解放军俘虏。但韦正年抱着投机的心态转而参加解放军,他劝顶牛爷跟他一起,这样的话今后“肯定不会只是一个平民”[4]35,但顶牛爷还是决定回家务农。多年后,韦正年官至地委书记,又因贪腐犯罪入狱,这时他反倒羡慕顶牛爷的生活:“他现在活得健健康康的,多好。”[4]35顶牛爷年轻时,虽然不得已加入国民党军队,但抗日杀敌他毫不畏惧。当同乡希望他同作投机选择,他予以回绝,这是一种内心的坚守。
顶牛爷在回村的路上,收留了落难的覃小英,他对外假装覃小英是自己老婆,带她回村里避难。到了年三十,两人喝了酒,情绪很好,差点要行夫妻之实。关键时刻,顶牛爷控制住了自己,他心想,自己不能毁了覃小英,她以后“还要有头有脸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事”[4]117,君子不乘人之危,这体现了他正直的品格。
以上所指出诸如忠义、守节、果敢、正直等传统美德,是顶牛爷“非凡的气质和品格”的具体体现,但是,当他面临选择、做出行动之时,并不会先用这些品质去衡量,他只是凭借骨子里最朴素的价值观去判断,也正是这份纯粹,使他的品格更显非凡可贵。当然,这种“顶牛”的非凡品质也不能保证他总是“绝对正确”。
在两夫争妻事件中,他就曾为自己的裁决“感到不安和愧疚”[4]78。可怜的覃桂叶,她一生悲惨流离,从小就和蓝茂订了娃娃亲,后来被人贩子拐卖给韦加财,并生下了儿子韦仲宽。及至蓝茂找到并希望覃桂叶再做回自己的妻子,蓝茂和韦加财之间便产生了纠纷,这一纠纷的裁决人便是顶牛爷,在详细调查后,他把覃桂叶判给了韦加财。不成想,十年以后,韦仲宽意外受伤,输血时发现他的血型和韦加财不匹配,很明显,他不是韦加财的亲生儿子。韦加财首先怀疑他是蓝茂的私生子,并要求他俩做亲子鉴定,结果是,韦仲宽和蓝茂也无血缘关系。原来,韦仲宽是覃桂叶被人贩子强暴后所生。最后,养父韦加财赶走韦仲宽,他变成了无依无靠的野孩子。这样的结果让顶牛爷沉闷自责,他认为自己的裁决给覃桂叶造成了不幸。又过了16年,79岁的顶牛爷大病一场,他自以为行将就木,念念不忘26年前两夫争妻的事情,要求重新裁决,这一次,他判蓝茂和覃桂叶是夫妻,这当然是更合情合理的裁决。或许是良心得到安慰,没过多久,顶牛爷竟然痊愈了。至于韦仲宽,他被养父韦加财撵出家门后不久,就被蓝茂收养,多年后已是在读博士生。曾经的悲剧故事,好像又迎来皆大欢喜的结局。那么顶牛爷26年前的裁决是错的吗?好像谁都说不准。所谓对错,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是非曲直、教条式的标准,而是在综合考量内心与现实、道德与欲望、感情与法理等因素后,凭良心做出的决断。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叙事的张力中,才得以窥见顶牛爷高贵的人格。
二、“非凡的气质和品格”是否真实?
对于《顶牛爷百岁史》,凡一平曾指出:“其实这些故事不光是顶牛爷一个人的,而是上岭村人故事的结合和综合。他的身上满是上岭村男人的性格和气味。他的经历中有我曾祖父的冒险和神秘,有我祖父的坚韧和大气,还有我父亲和叔父的善良和忠诚……”[4]233或许有必要追问,这种“非凡的气质和品格”真实吗?
其实,在凡一平作品中具有“非凡的气质和品格”的人物,并不占大多数。概而言之,他上岭村系列笔下的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真实的普通人,他们过着平凡的有酸甜也有苦辣的生活,性格存在怯懦、贪婪、虚荣等弱点;第二类是不幸的人,如《顶牛爷》中的覃小英、韦香桃,她们逆来顺受、善良坚韧,但却频遭命运的重创,作者对她们的遭遇心怀悲悯;第三类是品质恶劣者,这一类是极少数,但在作者看来,他们并非十恶不赦之人。比如《上岭村的谋杀》中的恶霸韦三得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后来当兵未遂,他怀疑自己被村支书儿子顶替,由此开始“破罐子破摔”,成了村霸。作者对其恶霸行径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透露出对韦三得命运转折的无奈——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好青年;第四类是具有“非凡的气质和品格”的人物,他们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尤其是那些幻想以暂时妥协来挣脱命运的主人公,却在悲惨的境遇里泥足深陷,“被社会偏颇的铁锤砸向不幸”[5]。如《上岭村的谋杀》中的黄康贤、《天等山》中的龙茗,虽然他们也曾妥协,甚至干过错事,但一直在和命运抗争,追求正义,在妥协和斗争之中,他们还是逃不掉“杀身成仁”的结局,最终实现了人性的救赎。或许凡一平对笔下人物“倾注足够的温情”[3]200的同时,也在寻求如何书写最高意义的故乡品质。
上岭村是凡一平的故乡,也是他创作灵感的宝库来源。村庄的气度是历史的积淀,它不仅影响到凡一平本人,同时也浸润滋养着他所塑造的人物。身为壮族子弟的凡一平曾经说过:“如果说少数民族文化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在为人上,我乐观,容易知足,对人友好、宽容。”[1]294在凡一平心中,“乡亲个个善良,善良到纵使掌握或唾手可得你天大的秘密,也绝不出卖或勒索你”[6]188。而且对凡一平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最洁净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抵抗——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再天真,不再干净了。”[6]186如何寻找自我,完成“心灵救赎”呢?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淳朴、厚道、善良,富有温情。但作者还希望通过塑造故乡人物最高贵的品格来书写故乡品质,以此实现其对历史的跨域想象,实现文学对心灵的救赎。
回到上一个问题,“非凡的气质和品格”真实吗?这个问题可以借凡一平在《顺口溜》中对彰文联的评价来回答。在《顺口溜》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极具气节和操守的学者型官员彰文联,当记者问及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时,凡一平回答说:“假如生活中没有像彰文联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么写这部小说岂不是没有意义?假如这部作品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作品,那岂不是共鸣者寥寥?”[1]148毫无疑问,人物的塑造、经典的诞生,必然经过创作者对生活的悉心观察和提炼,艺术化地加工与整合。我们应当坦然承认,这种“顶牛”的“非凡的气质和品格”寄寓了作者的文学理想,他在多年的创作中,有意赋予上岭村人物“顶牛”式的人格,从而将上岭村转化为其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三、叙事策略及“套路”介入
凡一平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认为,“一个好故事比一个深刻的思想要难得得多。好故事可遇不可求”[7]163。如何讲好故事呢?在他看来,“巧妙是艺术创作的法宝”[7]252,为了架构传奇故事,他有意借助独特的叙事结构来编排。从阅读效果而言,他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好看又耐看。然而,有时候只专注于故事的传奇性,就会遮掩小说更深层意义的思考,这一问题在凡一平创作中偶有体现。
相较于凡一平的早期创作,《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顶牛爷百岁史》在技巧上更加圆熟,早期小说那种明显的电影手法在这里被更细腻深刻的思考收编,匠心独用的艺术结构能服务于严肃的创作主题,这让作品既精彩好看,又引读者回味深思。
《上岭村的谋杀》就是这样一部巧妙结构和人性探讨浑然交织的典型作品,凡一平在小说前的题词是“一场人欲与道德的鏖战”。这一主题看似严肃,但小说读来却紧张刺激。作者将故事分为三部,采取“过去—过去的过去—现在”的时间策略展开叙述。故事先从中间的2010年讲起。村霸韦三得被杀害,警察经过调查,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韦波。故事大致交代清楚,却留有伏笔,如被韦三得强暴的唐艳后来遭遇了什么?吊起读者胃口,作者这才开始第二部的讲述,叙述2008年以来的故事,这才使读者全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韦三得是被黄康贤、唐艳、韦波、韦涛一伙人精心设计杀害的,韦波承认自己是凶手,只是为了赶快了结此案保护其他人。故事讲述至此还未结束,警察一直怀疑这是一起团伙作案,只是没有证据,这就引发了第三部2011年到2012年的故事,黄康贤大学毕业当上警察——是的,凶手当了警察!只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黄康贤设计杀人的罪行,村民苏春葵早就得知,她借此威胁黄康贤,这使得黄康贤为此烦躁不已。黄康贤的父亲了解这一情况后想帮助儿子,设计杀害了苏春葵。巧就巧在,调查苏春葵被杀案的警察正是黄康贤自己。在搜寻证物之时,他发现作案的锯子正是父亲的,恍然明白了他的苦心,便将证物藏匿起来。案件调查没有进展,直到苏春葵丈夫拿着黄康贤买给她的漂亮衣服找上派出所领导,眼看着说不清、道不明,黄康贤选择自杀,带走了所有的秘密。
有人注意到凡一平这种独特的艺术结构,并将之归结为“嵌套的叙述结构”,“即在一个故事中穿插另一个故事、一条线索引出另一条线索、一个人物带出另一个人物”[8]。正是在紧张刺激、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的叙述中,凡一平注入自己对人性的思考,让读者在阅读中直面人性的复杂。
相比《上岭村的谋杀》的倒叙,《顶牛爷百岁史》是线性的叙事,故事情节随着顶牛爷从年青到年老一步步展开,但仍有很多巧妙的设计,比如顶牛爷的金牙。小小金牙贯穿作品始终,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一是探寻顶牛爷长寿的秘密。在作者看来,顶牛爷的“金牙之谜就是他的长寿之谜”[4]233。战友临死前托付顶牛爷将金子转交战友妹妹,为便于保存,顶牛爷把金子做成金牙,而顶牛爷找了一辈子也没找到战友妹妹。金牙象征着信义和使命,活着的使命还未完成,当然不能轻易死去。这种情况在小说《蝉声唱》中也有体现,樊家宁活着的时候,最大愿望就是把因救自己而中弹身亡的七个兄弟的坟墓迁回老家,直到这项使命完成,樊家宁才觉得完成了自我救赎,几天后撒手人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份信念就是顶牛爷长寿的秘密。
二是金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虽然金牙在前面的故事里多次出现,但直到最后,作者才交代金牙的来历,此时,读者再回过头来复观全局,就更能体会金牙是如何统筹推进《顶牛爷百岁史》的故事情节的,也更能体悟到顶牛爷这种“因信称义”的非凡品质。顶牛爷一生中,无论多么困难,都从未打过这几颗金牙的主意,“穷死我都不用”[4]228,因为这坨金子不属于他。
三是金牙的巧妙之处还在于它像一根针,将顶牛爷一生的故事严丝合缝串联起来。比如,战友把金子托付给顶牛爷,才引出顶牛爷找战友妹妹,然后顶牛爷在路途中拾到覃小英,为了覃小英的清白,顶牛爷严苛控制自己,从未和覃小英发生过夫妻之实,而后才有覃小英报答顶牛爷,才有顶牛爷和韦香桃的恋爱故事……纷杂的故事、线索、伏笔和人物,在金牙的统摄下清晰明了,体现了凡一平化繁为简、以小见大的叙事能力。
金牙的巧妙设计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传奇性,叙述技巧“无迹可求”。当然,有些情节难免露出斧凿的痕迹,如覃小英从“落难公主”复位为“珠宝富婆”后,给了顶牛爷丰厚的经济支持,他先是大修祖坟、又是给族人发钱,还替韦香桃出钱看好二儿子的脑瘫病。眼看就要和韦香桃谈婚论嫁,她的大儿子却提出,让顶牛爷出钱为他买官,顶牛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婚姻。这一段“麻雀变凤凰”的情节就传奇得有点离谱,当然,无巧不成书,读者本来无须挑剔,只是纵观凡一平的全部创作,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多见这种由巨额财富,或因财富的得与失来推进情节的情况,相比于凡一平笔下真实可感的普通人,这类人或可直接地称为“有钱人”。如《保镖沉落》写一个富商回乡考察投资,《韦五宽》中主人公和叔叔偷盗高官贪污的巨额财产,《丁酉年记》里蒙冤入狱的韦宝路获赔巨额资金出狱后大手大脚花钱,《天等山》里富商林伟文之死,《戊戌年记》中大老板唐文武破产后被人索债,《蝉声唱》里三十三岁大富大贵的罗光灯突然变为贫穷的蓝必旺……诸如此类的故事奇则奇矣,但也易令读者心生“套路化”之感。而如何不自我重复而实现突破,也正是许多创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