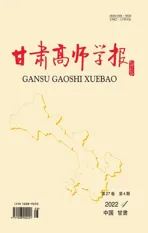妙在得意可忘言
——古代诗文中的数词辞趣研究
2022-02-27周奉真
周奉真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屈原《远游》 有句:“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1]152汉代王逸在其《楚辞章句》 中对“餐六气而饮沆瀣” 一句注曰:“远弃五谷,吸道滋也”[1]152,意为有人不吃五谷食品,靠“餐气”“饮沆瀣(露)” 而活着。按:这里的 “道滋” 的 “道”,即指宇宙本体自然的产物 “气”“沆瀣(露)”。对“漱正阳而含朝霞” 的注,王逸另引 《陵阳子明经》:“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秋食沦阴。沦阴者,日没以后赤黄气也。冬饮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夏食正阳。正阳者,南方日中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是为六气也。”[1]153《陵阳子明经》 佚文除《楚辞·远游》 王逸《楚辞章句》所引外,还有 《文选·甘泉赋》 李善注 “历倒景而绝飞梁兮” 句引张揖曰:“陵阳子明 《经》 曰:‘倒景,气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2]113但 “倒景” 是物理现象,任何景物在水中的投影都是倒景,完全没有不知所云的“气去地四千里” 的条件。晋代李颐对《远游》 注:“平旦为朝霞,日中为正阳,日入为飞泉,夜半为沆瀣,天玄地黄为六气”[1]153;司马彪曰:“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3]964两者大不相同。到后来《抱朴子·释滞》 有“于云端食六气”[4]149说,其源于《远游》。之所以如此分歧,关键问题出在对“六气” 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上。
一、“六气” 是一个修辞概念而非数目实指
“六气” 本来是关于气候的一个说法。《左传·昭公元年》 记医和为晋侯看病,医和言:“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5]1217对这一说法需要分辨的是,其中内容分为很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固定正常具体有所指的,如四时、五味、五色,都有相应的客观存在;另一类是临时的拼凑,如六气、六疾、五节,它们都没有相应的客观实际。以“六气” 言,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并非截然不同。如 “阳” 与 “明”、“阴” 与 “晦” 又有多少区别?所谓 “六疾” 的寒、热、末、腹、惑、心,也似拟于不伦。这实际是古代拼凑数词序列的一种趣味修辞。如 《左传·昭公二十年》 记载晏子论述事物之间的“和协” 与“相同” 并不是一回事时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5]1419而《国语·楚语》记观射父论祭祀时说:“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以先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畡数以奉之……。”[6]597这里就是因追求意趣修辞而拼凑了一组从一到十的连续数列。“一纯”即精诚专一,“一” 是形容词,非数词,“二精” 指玉和帛,“七事” 指天、地、民和四时之务,此已兼含前文“四时” 一目。就此可知这纯是一种为求排列整齐的修辞手段,并非按严格的事理或物量的多少排列。后面从百到兆又是另一组大数成级数的排列,实际都是指官吏和人民,其间也并无必然的数量规定,也只是在一些常用词语的基础上附着上数词作扩充搭配,形成一个貌似的数列。
这些情况说明“六气” 并非科学的有具体内涵具体指称的概念。《庄子·在宥》:“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7]194其中 “六气不调” 也是没有具体所指的含混说法,实际是对“天气不和” 换了个表述复说而已。各种气候不正都是天气不和,而并没有什么 “地气”,也没有什么“六气” 不调与“六气” 调的对比。《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7]12所谓“御六气之辩” 就是适应气候的变化。
那么屈原为什么说“餐六气而饮沆瀣” 呢?还是回到王逸《离骚序》 看:“《离骚》 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1]382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就是屈原用浪漫主义的艺术写法来表明自己的纯正清高。如 《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1]14,绝非具体地用菱叶、荷叶去制作衣裳,而是把自己比喻为荷花。同样,“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1]1,也绝非用香草佩饰。在现实生活中,除小女孩有时将采摘到的鲜花插在头上作玩耍外,成年妇女也没有以鲜花作头饰或佩饰的,一方面插不稳,另外鲜花也会很快萎缩而失去美丽。应该说王逸在对屈骚的总体理解把握上是正确的,但对《远游》 二句的注解却出现了偏差。所以屈原的“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 与《庄子》 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都是取譬,表明不同于凡俗庸众的汲汲营营,人品纯正高尚罢了,并不是真的去“餐气”,去“饮露”。
二、古代诗文中数词辞趣之归纳研究
正如王逸注楚辞《远游》 两句一样,因为对数词修辞的本质未作宏观深入的研究,眼中就只拘泥于诗文中的数字,按数字提供的表面信息与实际的事理作联系分析,而不去联系数词修辞的语言社会性或历史性的广阔背景,就不明白数词后面欲传之思想精神。正如黑格尔说:“这些数的本身并没有性质足以表示这些特定的思想。人们愈是进一步采用这种附会的方法,特定数目与特定思想的联系就愈会任性武断。”[8]232黑格尔已区分得十分明确。对数词任性武断的附会,使许多注解家对古籍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误解,这提示我们对诗文中呈现出的这些特殊数词应予以关注研究。
1932 年,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刊行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被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陈先生在“积极修辞五” 提出了“辞趣” 这一新命题。他解释说:“关于语感的利用,大体可以分作三方面,就是: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这三个方面大体同语言文字的意义、声音、形体三方面相当。我们在辞趣论里所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上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的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语言文章的情韵的问题。利用语言文字的风致来补助语文情韵的手段,虽然普通并不计及,但是应该讨论的项目也不少。”[9]70
结合陈先生的具体例证以及所言的“附着的风致”“情韵” 来细致考虑,所谓“辞趣” 就是趣味修辞,就是在表达的文义之外另外增添一种趣意。一般的修辞,如比喻、拟人、夸张等,目的是要表达的思想更加清楚明白、形象生动、深刻有力,不是另要增加新的内容,“辞趣” 却正是要增附情趣。陈先生说,一般修辞论著对辞趣 “并不计及”,但他却说在“辞趣” 一说里,“应该讨论的项目也不少”。他草创了这一辞格,但也未及详论深说,仅就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粗略而言,有的例证或解说也未必恰切。从陈望道先生提出这种修辞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语言文学界研究辞格有不少创获,但陈先生提出的“辞趣” 说,除了钱钟书先生较早言及这种语言现象,刘瑞明先生对数词辞趣进行过探讨外,再罕见有学者对此继续深入研究。我们由 “六气”的释义问题,研究数词辞趣,就是从数词这个场域为陈先生的“辞趣” 说进行深入讨论。
最早注意到趣味数词的是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篇》 第三册 《全后汉三国六朝文》 第三七条“合两虚数成四言之三式” 中,注意到了各种文体刻意用数词求趣的例句,且指出了前人因为不明白这种修辞而误改前代文献或错误地理解语句的情事,兹引如下:
《樗蒲赋》:“精诚一叫,十卢九雉。”按即后世所谓“呼卢喝雉”“呼幺喝六”,岳珂《桯史》卷二载李公麟画《贤已图》中景象也。“五木”而言“十”与“九”,似不可通;宋本《艺文类聚》作“入卢”,则“九”疑“凡”之讹,“凡稚入卢”以押韵故,句遂倒装,谓雉都成卢,获全采耳。顾即以“十”“九”为汪中《说三、九》所谓“不可执”之“虚数”,亦颇无妨,求之今日常谈,会心不远。合两虚数以示“多”“都”之意者,惯式有三。第一,数相等,如常言“百战百胜”,词旨了然;《北梦琐言》卷一七李克用曰:“刘鄩一步一计”,是其类。第二,后数减于前数,如常言“十拿九稳”,语气仍正而不负,夸“九”之多,非惜“十”之欠一。《焦氏易林·履》之《履》:“十鸟俱飞,羿得九雌”,《魏书·序纪》孝武皇帝“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江淹《泣赋》:“魂十逝而九伤”,又《杂三言》:“山十影兮九形”,《皇朝类苑》 卷六〇引杨亿《谈苑》载党进斥优人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 ”(《说郛》卷五李义山《杂簒·愚昧》:“三头两面趋奉人”),是其类。第三,后数增于前数,如常言“一猜两着”。《参同契》上篇:“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易林·蒙》 之《复》:“獐鹿雉兔,群聚东囿,卢黄白脊,俱往趋逐,九齗十得,君子有喜”,《睽》 之《随》:“五心六意,歧道多怪”,《艮》 之《颐》:“八面九口,长舌为斧”,《蹇》 之《损》:“脱兔无蹄,三步五罢”,《西青散记》卷一:“心神凄陨,记三讹五”,是其类。《易林·贲》之《干》又曰:“八口九头,长舌破家”,夫既主“长舌”,则着眼亦在“口”,而“九头八口”,指归正同《艮》之《颐》:“八面九口”,复正同《通俗编》卷一 六《涑水家仪》:“凡女仆两面二舌”;犹《睽》之《随》;“五心六意”,指归无异关汉卿《救风尘》第一出:“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复无异《论衡·谏时》:“天地之神……非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也。”“刘鄩一步一计”,而《通鉴·唐记》八〇天复三年胡三省注作:“刘鄩用兵,十步九计。”史惇《痛馀录》载《退婚卷》程序:“一离二休,十离九休”,元阙名《刘弘嫁女》头折王氏以“寸男尺女皆无”,劝夫纳妾,夫曰:“你待赔千言万语,托十亲九故,娶三妻两妇,待望一男半女”;后数于前数或增或减,词旨无殊。盖得意可以忘言,不计两数之等(=)或差(+/-)也。“九雉十卢”倒装而为“十卢九雉”,如曰“尽雉全卢”,若是班乎?“十”有全义,《说文》:“十,数之具也”;“九”有尽义,《易纬干凿度》《列子·天瑞》:“九者,气变之究也。”[10]984
钱先生上列的读其 “不可执” 之” 虚数” 却“会心不远”,“盖得意可以忘言”,并言“尽雉全卢”岂若 “十卢九雉” 之另有异趣,这 “异趣”,正是陈望道所言 “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继钱钟书先生之后,刘瑞明先生就数词辞趣著文进一步论述道:“利用数词修辞是一种积极修辞,它的基本特点是由于数词用得华巧,便在基本意义表达之外,附随了一些奇趣雅兴,增加了语言的优美,耐人寻味。”[11]26他认为,经过历代文人的实践,这种巧用数词的修辞,已经发展完善为多种形式的一整套格式,并按照自己的观察研究将这种格式进行了归类表述。钱先生此说虽为札记,然则导夫先路,足见卓识,刘瑞明先生慧眼识得这种数词修辞的价值意义,继作求索,难能可贵,现拟踵武前贤,征引众多的例证就诗文中同时使用两个或更多的数词的修辞观象,进行归纳分析研究,探讨经过历代文学家长期实践,业已发展完善形成的数词修辞格式。
(一)重复使用数词
这里说的重复使用数词,是指同一数词在句内间隔重复或在同一篇诗文里不同文句中重复运用,有两重三重甚至多到十重的。这种格式又分为一篇(首)诗文里一数重和两数重,先看一数重,我们以“一” 字为例。
阮籍《咏怀·其六十三》:“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及《咏怀·其六十四》:“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12]215两首诗中各有四个“一” 字的重复运用,无非是想表达朝朝暮暮日日年年时光的迫催,对人容颜精神的摧毁,使人哀伤心焦,但作者却舍弃平淡的表达而求辞趣,两首诗各连用四个“一”,在绵密的重复中,让人感受时光流逝的紧促,人生易老的无常。白居易《山石榴寄元九》:“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无闲事,山下斫得庭前栽。烂漫一栏十八树,根株有数花无数。千芳万叶一时新,嫩枝殷红鲜曲尘。”[13]2859诗中连用了四个 “一” 字。其中 “一声催得一枝开”“千芳万叶一时新” 两句中,“一” 字必须用,而“烂漫一栏十八树” 句中的“一” 则完全可以替换。从表达效果看,“栏内”“满栏” 之类,则词义更显豁明朗,但诗人舍寻常而求新趣,“一” 字之用由“三迭” 增至 “四迭”,正是诗人的刻意追求。一般说来律诗要尽量避免用字重复,但任何事物的形式都不会绝对化,形式的美是多种多样的,诗家之匠心可以打破常规别出新趣。如唐戎昱《送李参军》:“好住好住王司户,珍重珍重李参军。一东一西如别鹤,一南一北似浮云。月照疏林千片影,风吹寒水万里纹。别易会难今古事,非是余今独与君。”[13]1812诗人在格局上着眼于求新,“一东一西如别鹤,一南一北似浮云”,一联四个 “一” 迭用,指向四个方向,显示出对称整齐的回环错落之美,这是数字迭词修辞的生命之所在。
在一首诗里将 “一” 字九迭,最有名的当是清代王士祯 《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14]492单纯从一首绝句用了九个“一” 字看,这自然是有意为之,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但从表达的意境思想看,全诗将垂钓者的潇洒逍遥又有几许萧瑟和孤寂,刻画得活灵活现,让人叹为绝妙,正是对这种修辞的肯定。
不仅仅是“一” 字多见复用,“三”“六”“九” 甚至十位以上的数词也有重复运用。“三” 字复用如明王世贞 《弇园杂咏》:“三弇此三夏,三产三秀草。吾亦有三儿,宁馨似芝好。”[15]235“六” 字重复用如宋郭应祥《鹊桥仙》:“六人欢笑,六姬讴唱,六博时分胜负。六家盘馔斗芳鲜,恰两月、六番相聚。”[16]8又,《鹊桥仙》:“六丁文焰,六韬武略,那更六经心醉。六人相对座生风,继六逸、当年旧事。六州清唱,六幺妙舞,执乐仍呼六妓。大家且饮六分觥,看宾主、迭居六位。”[16]9“九” 字复用如明湛若水《即席和九山翁天阶之作》:“九德山中有九峰,九峰元是九山峰。汤翁肯步陈翁武,便是乾坤第一峰。”[17]473十位数以上的如宋汪莘《水调歌头(雪中篘酒,恰得三十六壶,乃酹黄山之神,而歌以侑之)》:“黄山图就,旧日境界喜重新。三十六峰云嶂,三十六溪烟水,三十六壶春。”[18]826清周之琦《眼儿媚》:“南朝驻跸爱杭州。直为圣湖留。十三门外,十三椄畔,占尽风流。”[19]41上列数词的重复使用,不仅毫无冗赘重复的感觉,反而使人觉得迥乎寻常,眼前一新。
再看两数重复用。两个数词复用多表达的是两个数词重复的对比,在对比中诉诸人以美感。多见两重或三重,也有多重。唐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13]717宋李廷忠《鹧鸪天·九日南楼和范总干韵》:“槛外长江浪拍空。萧萧红蓼白苹风。三秋告稔三农庆,九日追欢九客同。烟渚北,月岩东。莫嫌光景太匆匆。登龙戏马英雄事,都在南楼一啸中。”[20]48李白 《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啼,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声一断肠,三春三月忆三巴。”[13]1121其中“一叫” 与“一声”,“三春”与“三月” 表达的是同一意义,但作者为追求三重而刻意为之,足见诗人追求辞趣的强烈愿望。又如李白 《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13]1109我们只有从修辞的角度对诗人表达的思想情感进行理解,才能发现其美学价值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体会重复用的数词,曲折铺排,回环宛转,精工雕琢,极尽文学之妙用。
(二)按固有的数字次序连用数词
按约定俗成的数字次序,相邻的两个或者更多个数词依次或者间隔用于诗文之中,是文人诗客追求的又一种数词修辞意趣。白居易 《春去》:“一从泽畔为迁客,两度江头送暮春。”[13]2951“一从” 意即“自从”,“一” 在这里不作数词用,但诗人却弃“自” 字不用,刻意用了 “一”,与下一句中的“两” 成为依次邻数,增添数词连用的辞趣。再看白居易 《勤政殿楼西老柳》:“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13]2977从字面看,这两句诗跳跃大,意不连贯,“一” 与“二” 作为依次邻数拟于不类,但诗人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即开元年间栽的一棵柳树,一直活到了长庆二年的春天,是说这棵老柳太年高了,但如此说,就平淡直白,少了意趣。所以诗人宁取邻数连用的不类,也要追求意趣。这种追求在他的另一首 《放旅雁》“九江十年冬大雪”[13]2895句中就更明显了。九江的“九” 与长庆十年的“十” 两个数词毫无事理关系,但诗人却要着意“拉郎配”,笔下生华,达到新的艺术效果。唐熊孺登《寒食野望》:“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13]3267贾岛《题诗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13]6746韩愈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因题门楼》:“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13]674杜甫《恨别》:“楼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22]311陶渊明《归田园居》:“方宅十余亩,草庵八九间。”[23]78王维 《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13]752
以上诗中所示依次序用数词有一、二(两、双)、三;三、四、五;四、五、六;八、九、十;百、千、万。而张祜 《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十二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24]21这首感情深挚的名诗,数词的意趣产生了极大的辅助作用。“三千”“二十” 皆非实指距离和时间,而是在表示多量意义之外,使“一声”“双泪” 这两个表达情感的重点词语得到了支持与烘托。三、二、一,是三个相邻递降的邻数,一、双(二)又是两个一组的回升邻数,在邻数的递降与递增的回环对比中,让读者感受到了诗里情感起伏跌宕的波澜。
如果说两个依次数或三个依次数的连用对这种修辞表现得还不够显著,那么下面三个以上的多个依次数的铺排连用,就使我们对这种修辞手法看得更真切了。鲍照 《寄行人》:“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是时君不归,春风徒笑妾。”[25]102杜甫 《南郊》:“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渡两三人。”[22]561韩愈 《河南令舍池台》:“灌池才盈五六丈,筑台不过七八尺。”[13]3755唐吴融《李周弹筝歌》:“闻君七岁八岁时,五音六律皆生知。”[13]2147唐史思明《石榴诗》:“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作刀割破黄胞衣,六七千个赤男女。”[13]2433白居易 《耳顺吟寄敦诗梦得》:“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13]244
这些依次序连用于诗文之中的数词,犹如在质优的器皿上附着了黼黻纹饰,精良华美,令人称赏玩味不已,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求新、求雅、求趣的美学理念在语言中的生动运用。
(三)连续运用数词形成数词流
上述为固有数字次序依次连用于诗文,还有一种数词修辞意趣,是从一至九或十,甚至再向后延及的系列,我们姑称之为 “连续数词流”,就有更难得的意趣。这种连续数列修辞,为时甚早,可上寻其源,始于散文,如前文所示 《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子论事物的 “和协” 与 “相同”,从“一” 罗列至“九”,《国语·楚语》 记观射父论祭祀,从 “一” 排列至 “十二”,延及百、千、万、亿、兆,但此并非严格按照物量或事理的逻辑排列,只是在一些名词上搭配上数词,在表象上形成一组数列,而实际追求的是排列整齐有序的修辞效果,数字本身并不表义。又如 《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25]245由此也可知那时的文史家们已感觉到了这种数词铺排修辞的效果并积极追求。这种修辞方法在后世更多地被诗家继承,形成了一种诗体叫“数名诗”。数名诗又叫数字诗,它是以数为题,把一至十这些数分别嵌入一首诗中连续数列。最广为传播的有元徐再思《无题》:“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26]199这首“数名诗” 类似儿歌,传播极广,说明连续数列修辞有雅俗共赏的意趣和美感。
从《文选》 的收录看,写数名诗最早的是南朝鲍照的《数诗》 :“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2]389诗从一至十按顺序用在每联首句,了无牵强之感,借助这一连续数列,将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之下豪门子弟轻易得官、平步青云、一宠百荣,与出身寒微,十年苦读,却仕进无门的鲍照形成鲜明对比,揭露了门阀制度的荒谬,极具讽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际写 “数名诗” 的还有虞羲:“一去濠水阳,连翩远为客。二毛飒已垂,家贫无所择。三径日荒疏,徭人心不怿。四豪不降意,何事黄金百。五日来归者,朱轮竟长陌。六郡轻薄儿,追随穷日夕。七发动音容,宾从纷奕奕。八表服英严,光光满坟藉。九流意何以,守玄遂成白。十载职不移,来归落松柏。”[2]472与鲍照诗表达的思想相类,也是揭露社会不公,为国效力者不得升迁,轻薄之徒却富贵荣华,抒发了诗人的悲慨之情。此后连续数列的“数名诗” 代有之。唐权德舆《数名诗》:“一区扬雄宅,恬然无所欲。二顷季子田,岁晏常自足。三端固为累,事物反徽束。四体苟不勤,安得丰菽粟。五侯诚晔晔,荣甚或为辱。六翮未骞翔,虞罗乃相触。七人称作者,杳杳有遐躅。八桂挺奇姿,森森照初旭。《九歌》 伤泽畔,怨思徒刺促。《十翼》 有格言,幽贞谢浮俗。”[13]2497一位甘于平淡耕读自乐怡然自得的读书人形象站在了我们面前。诗劝诫世人不要汲汲于功名利禄,要远离世俗名利的束缚和烦扰,颇富哲理。及宋有欧阳修的《数诗》:“一室曾何扫,居闲虑俗平。二毛经节变,青鉴不须惊。三复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 宁敢拟,高咏且陶情。五鼎期君禄,无思死必烹。六奇还自秘,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雾,彪文幸有成。八门当鼓翼,凌厉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问,从此卜嘉亨。”[27]109诗亦富有哲理,表达了人生有限,无须追求功名,而应安于归隐的思想。
(四)历史形成的特定表示多的数词
数字词本是计量表示数目的,古人却在一定的语言背景下,在诗文中用数词表示泛指的多数,这是汉语语言中特有的趣味修辞及语言现象。而前人因不了于此,胶柱鼓瑟,循数以较其实,制造了不少笑话及笔墨官司。事实上,正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编》 概括总结有数词修辞 “合两虚数以示 ‘多’‘都’ 之意者,惯式有三”[10]367。这种数词泛言多数不仅存在,而且在具体用词上还有不少相对固定性的“惯式”,下面试再作探讨归纳。
1.三、六、九及相应的倍数表多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 是一个最古老的数额最小的表示多的概念,由“三” 作为多数这个概念滋乳至于用三、六、九泛指多数,人多熟知,不赘。九的九倍是八十一,故八十一也表泛指多数。唐僧取经有八十一难,古时分天空为八十一域。《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八十一首。”[28]950言蒯通最善分析离合变化出谋定计,可知在汉时 “八十一” 已表多了,后在诗文中代有以“八十一” 言其多的诗句。李白《上云乐》:“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13]279白居易 《骊宫高》:“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13]147这些句中的 “八十一” 都言其多。
2.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表多数
古人认为十二为 “天之大数”。《左传·哀公七年》 载:“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5]478这是因为先民发现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寒来暑往一年正好是十二个月,岁星一周天是十二年。及至十二再回复到一,十二是天体运行的最大数,所以 “十二” 就有了泛指大、多之意。《礼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礼记》又曰:“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之数……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地,天垂象,圣人则之。”[29]459《后汉书·荀爽传》:“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30]2496可知“十二” 是帝制时代不可僭越的最大数了。这种观念传至唐宋,在诗词中 “十二” 成了泛指多的数。如陈陶 《赠容南韦中丞》:“十二铜鱼尊画戟,三千犀甲拥朱轮。”[13]1975慕幽《三峡闻猿》:“七千里外一家住,十二峰前独自行。”[13]2077从上面诗句中见,十二,无论表何事何物,都是多、大、高之义,且多与泛表多的数对举。三十六是十二的三倍,故亦表多。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在全国设了三十五郡,将“内史” 也凑作一郡,成三十六郡。言职业有三十六行,江河有三十六滩,帝王有三十六宫,道教有三十六洞天,皆泛指其多。由三十六泛说多又扩大十倍百倍再表其多。李白 《梁父吟》:“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通。”[13]1693三十六的两倍为七十二,也泛表多。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孔子有高足七十二人,明堂有七十二窗。三十六的三倍是一百零八,也泛表多。佛家称人有一百零八烦恼,水浒一百零八好汉,等等。
3.三百、三千、三万表不确指的多数
一百已经表多数,如“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百的三倍、三十倍、三百倍,仍作同义表述。《毛诗注疏·伐檀》“胡取禾三百廛兮”[31]336,《礼记·中庸》 有 “礼仪” 三百,李白 “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 《秋浦歌》 之二:“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13]1703《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13]1715白居易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三千里外故人心。”[13]2433杜甫 《观曹将军画马》:“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21]432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13]2703可见三百、三千、三万是又一个表示多数的系列。
4.八百、八千、八万表不确指的多数
西周有八百诸侯之说,后用为表不确定的多数,并衍至八千、八万。彭祖寿八百,《神仙传》 载李八百即系于此。《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7]36八千岁也是取原八百之十倍,在后世它比八百使用得更为习见,如项羽有江东子弟兵八千等,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21]422都属此类。
5.四百八十、四万八千表不确指的多数
《南史·郭祖深传》:“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32]762杜牧嫌五百有实指之嫌,易说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使句意增出虚夸情调。后有继之者如李白 《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13]1774《文选·蜀都赋》 刘注引扬雄《蜀王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2]1251“三万四千” 也是难以核实的不确数,但李白为避免别人以实数理解,故意改写为四万八千,避实以就趣。陶弘景 《真诰》、宋 《云笈七签》 皆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而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说:“天台四万八千丈”[13]1755。清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引用《云笈七签》 说,言 “四当作一”[33]1687。今朱金城等作《李白集校注》 对此歧说未作分辨,皆不明“四万八千” 是修辞之笔。另有苏轼 《游法华山》:“谁云四万八千顷,渺渺东尽日所洒”[34]1943均应作李白诗句一例解。
除了表示多的系列数词外,还有零星表多的数词,譬如九十九。《东坡志林》 言:“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35]251江陵有九十九洲,贵州有九十九陇,黄河九十九道湾之类语句也多见。“八万四千” 本为佛教表事物众多的数字,佛经《法华经·宝塔品》:“若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 后用以言极多数。黄庭坚 《观世音赞六首》 其一:“八万四千清净眼,见尘劳中华藏海。八万四千母陀臂,接引有情到彼岸。”[36]61
汉语泛表多数的数词极其丰富,其诉诸人的信息意义并不是数词本身的计量多少,而是经历代文人诗客在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一种修辞方法。貌似不伦的一组数词,因为修辞手段的运用而同归于一种逻辑意义的表达,这显示了语言的规律性、社会性及民族性。如果不这样分析问题,仅拘泥于数字本身去计较,就难以理解“三” 可表多数,四、五何以不能表多数。同理也不能理解杜牧为什么不用“四百七十”“四百九十” 去表述南朝佛寺之繁盛。这种基于数词及其倍数关系的修辞,恰恰体现了作家诗人用词的习惯及其鲜明的风格。
三、结语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第九篇 《积极修辞五》曾提出“辞趣” 的命题。他认为辞趣是“关于语感的利用,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具体指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即是利用语言文字的风致来补助语文情韵的手段。本文探究的各种数词的别致使用,正是数词 “辞趣” 之“风致” 和“情韵” 的充分展现。
在诗文中巧用数词,并非所述事物的机械罗列,属类举而非确数,属于修辞范畴而非逻辑范畴,旨在激发读者关于量的遐想。正如刘瑞明先生所说“人们惬意其中各数字间的倍数关系”,忽略其量之确凿,实为 “修辞陪衬之趣设”[37],这种 “辞趣” 当为数词所独有。
就技术层面而言,数词在诗文中的排布,可以分为数词叠用和数词连用两种。数词叠用,是在一首诗中将同一数词反复使用,以清代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 为代表,将数词“一” 九次叠用,简洁明了,读者不觉繁复,而是通过明快的节奏,感受到的是抒情主人公怡然自得、享受独钓的美好意象。数词连用,构成 “连续数词流”,以欧阳修的《数诗》 为代表,由一到十的间隔连用,使描述的事物或意象散珠连缀,聚零为整,浑然一体。若果没有数词,这首诗就抽了筋骨,散为碎片了。
创造美正是历代文人墨客追求数词趣味修辞的内生动力。数词原本意义最明确最确定,同时又最抽象最无生气,但文坛雕龙圣手却匠心独运,既用数字而又不实用数字,如此在数字之外新增了语义信息,在表达句意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完成了数词间妙趣的结合,诉诸于人的是一种美感的赏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