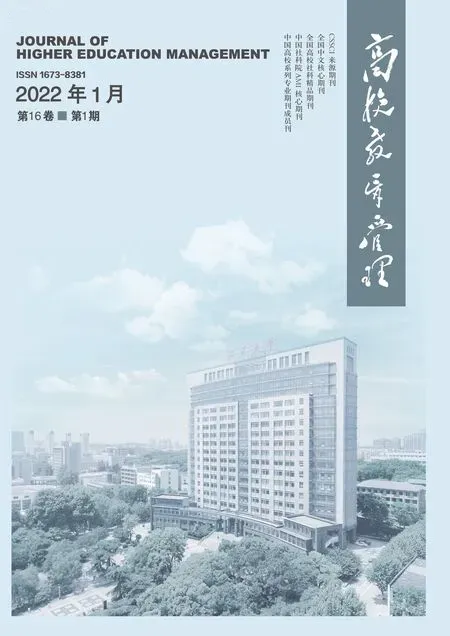雪山的雪线与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
2022-02-26邬大光
邬大光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021年,我们课题组承接了四川某高校的一个横向课题,暑假期间多次飞往成都进行调研。课题完成之后,校方邀请课题组游览了位于四川甘孜州康定、道孚和丹巴三县交界处的雅拉雪山。此次雪山之行让我有了一个意外收获——雪山的雪线让我联想到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
雅拉雪山,藏语全称为“夏学雅拉嘎波”(意为东方白牦牛山),海拔5 820米(也有资料说是5 884米),被康巴藏区的牧民视为心中的一座神山。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承载了千万藏民的希冀和梦想,给予他们神圣的信仰,因此雅拉雪山不仅是一处风景旖旎的旅游胜地,更是人们灵魂栖息的圣地。在世界变得日益拥挤、心绪变得日益烦乱的时代,游览一下那耸立于云霄白雾之中的雅拉雪山,也不失为一种洗涤心灵的选择。
当地藏民把雅拉雪山叫作“大炮山”,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看雅拉雪山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美景:或如皇冠、或如莲花,或与金塔争辉、或与冰川相印,让人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大自然强大的生命气息。“品”字形的雪山顶终年积雪,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冰川、瀑布与湖泊交相映衬,不乏灵动秀逸之态;澄明的湖水轻轻涤荡略感疲乏的身心,让人仿佛进入“万物皆隐,唯余空灵”之境。当然,最引人入胜的还数金字塔形雪峰下的高山湖泊——友措神海(也叫玉石海)。放眼望去,微风拂过开阔的湖面掀起阵阵涟漪,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皎洁中透出淡绿色的光辉,宛如晶莹剔透的碧玉一般。湖的周围错落分布着古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滩。石滩之旁温泉四布,古驿道依稀可见,与森林、草场、海子等共同构成了一幅绝妙无比的奇美画卷。雅拉河即发源于此,涓涓流水,绵延细致,不被狭窄的河岸所束缚,越过山石、穿过险滩,向远方奔流而去。在藏传古籍《神山志易入解脱之道》中雅拉雪山被称为“第二香巴拉”。
于我来说,进入藏区欣赏草原已有多次,2020年暑假就曾两次游览甘南草原。甘南草原与川西的阿坝、甘孜草原接壤,风景一脉相承,只是隶属于不同的省份罢了。此次之所以赴甘孜州的康定,主要是想一睹雅拉雪山的旖旎。川西风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们无须驻足观景,所映眼帘处处皆景,在车上观景与下车观景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坐车观景也不失为一种享受。我们第一天从成都到康定,一路颠簸和雷同的景色不禁让人产生了审美疲劳。第二天我们又从康定到道孚的巴美,再从巴美到丹巴的甲居,途经的墨石公园倒是让人眼前一亮。如墨的石头一丛丛、一簇簇或直或斜耸立着,变幻雄奇,置身其中仿佛遨游在太空之中。舟车劳顿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圣洁纯净、遗世独立”的雅拉雪山。在218国道的观景台上,望着远处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的雅拉雪山,导游小刘的一番讲解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说:“每年我都要带旅游团来这里看雅拉雪山,如果把雪山比作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看雪山,雪线是在雅拉雪山的腰部。你们今天看到的雪线已经到了人的脖子,也不知道雪线还会升到哪个部位?也不知道你们明年或以后再来,是否还能看到雅拉雪山的雪线?”
远处巍然挺立的雪山顶上有着泾渭分明的雪线,如果不是小刘的提醒,作为一个游客,我又怎会注意到雪线的上升?小刘是一位虔诚的藏族文化爱好者,面对雪线的不断上升,她的无奈之情写在脸上,乃至一股凄凉之感油然而生。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问题。
雪线指的是在气候变化不大的若干年内最热月份的积雪下界。作为一种气候标志线,雪线反映的是一地的气候特点,雪线上升也就意味着该地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雪线不断上移,守护雪山的雪线已然成为人类的共识。那么,高等教育是否也存在这样一条“雪线”呢?如果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看作一座雪山,那么是否可以把雪线比喻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对于高等教育学人来说,难道不需要建立预警机制守住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吗?继续联想下去,是否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也如同雪山雪线上升一样出现了下滑现象,而人们却浑然不觉?
近年来,学界关于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讨论一直有两种声音:有人说质量在上升,有人说质量在下降,其中认为“质量下降”的声音较弱,只有个别学者提出了“质量底线”的概念,但影响甚微。保护雪山就是想方设法不让雪线上升;同样,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就是不让大学底线失守,乃至毫无下限,就是让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质量底线。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质量底线”的概念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质量下降的预警和朴素反思。这种反思不能仅停留在模糊的直观感觉层面,而应该用行动去落实。
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提出,教育质量标准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工程(1)https://jwc.usc.edu.cn/info/1997/5281.htm.。该《标准》就是一种底线标准,政策制定者希冀《标准》不仅能够成为衡量教育质量优劣的标尺,而且能够成为高校治理的有效手段。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质量保障与质量标准的概念源于企业界,但教育质量标准的设立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而不是简单嫁接企业界的质量标准。基于市场逻辑建立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往往会使大学失去教育的本意,也会使其与“立德树人”的目标背道而驰。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2)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建议》颁布后,学界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讨论开始升温,“高质量”也迅速成为一个高频词,但如何认识和理解“高质量”的真正含义,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教育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不单单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获得学分如此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在遵循人类心理发展特征基础上探索教育规律的过程。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也会随着人们对教育意义认识的深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无视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更不能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已经从最初的“知识标准”发展到“人的标准”,再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世界协调发展的标准”。这就需要我们摆脱教育的功利性、人的功利性乃至社会的功利性去发现教育的“无用”性。人们既要关注教育质量中可检测、可观察的一面,也要关注教育活动背后深刻的一面。教育的质量标准不是一种社会经济标准,更不是排名的标准或数字游戏的舞台,而是一个“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等,使他们自由地生成(3)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 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则主张人们应该学会“凝思”,在美的面前平静下来,去期待和聆听最美妙、最遥远的声音(4)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7.。教育的追求就是对“善”和“美”的追求,教育“不善”可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5)陈 婧,邵思源.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国家战略研究——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113-123.,教育对质量的追求如若忘记了这样的本意,不仅不会带来文明的昌盛,反而会陷入理性的疯狂。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不难发现,我国部分大学还没有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意识。2020年,我以“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为题到一所高校讲学,该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听了讲座之后毫不避讳地告诉我说:“省内的一些高校为了方便学生出国和就业,在本科生毕业成绩单上都会把绩点提高一些”。我听了之后不禁为之震惊,立刻询问这种情况是否普遍,他回答说比较普遍。从2015年开始,我们课题组做高校学生毕业前的“清考”调查,经过3年努力,教育部在2018年8月发文要求高校取消“清考”。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取消“清考”之后,竟然又有高校“发明”了提高绩点的“对策”。我们知道,现在我国许多高校都成立了质量保障部门,但为什么高校的质量保障机构却对此类现象视而不见?倘若真是这样,取消“清考”还有何意义?成立质量保障机构还有何意义?目前到底有多少高校在悄悄地提高学生绩点,有多少高校对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熟视无睹,又有多少高校早已将质量底线抛之脑后?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现象严重侵蚀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文化与质量精神,深刻威胁着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约10年前,我们课题组梳理了厦门大学建校90年来的本科生毕业率和学生成绩单,经过简单统计后发现:厦门大学本科生毕业率和成绩单的分数逐年提高,尤其是最近20年,本科生的毕业率和成绩单分数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当时我们课题组虽然没有全国百年大学的数据,但依然可以作一个大胆猜测:当代大学本科生毕业率和成绩单分数普遍高于几十年前。2020年,我们课题组曾到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调研,该校的教务处长十分“得意”地告诉我们:“本校在过去5年中,本科生毕业率为百分之百”。听到这个数据,我们一行人都十分吃惊。实际上,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学生百分之百地毕业,而且是连续5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好的大学都是以坚守质量底线著称的,大学只有长期坚守质量底线,最终才会形成自己的质量文化。我们课题组近期已经开始研究本科生成绩单,拟在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跟踪大学生分数等数据的变化情况,以此来验证之前的猜测。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有同仁分享学生成绩、绩点等数据,以从中透视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否的确存在质量底线失守的现象。
实际上,世界各国大学的许多制度设计都隐含着底线思维,既有道德层面的,也有教学层面的,例如人们熟悉的学分制、学期制、选课制等。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却逐渐忽略了这些底线设计。首先,从选课制度来看,通过分析我国大学生的成绩单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四年级时,学生基本没有课上,即使有课,通常也只有一至二门,这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大四“放羊现象”。严格来说,本科四年的教学计划原则上应该平均分配课程门数、学分和学时,即使有一定的浮动空间,也不应太大,教学计划的严肃性也就在于此。其次,再来看一下学分制,学生大学期间的学分总数无论是多少,基本上都是按照4年8个学期平均分配的,可是在学生的成绩单上却可以看到,学生的学分主要集中在二三年级。而在国外的大学,当一个学生每学期选课门数或学分过多或过少时,学校都会进行警示或提示,而我国高校基本是做不到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学的体育课。体育课原本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实践中,学生入校时进行的身体素质测试以及毕业时的体育课考试基本流于形式。或者说在我国如今的大学,已经没有学生会因为体育课成绩不合格而无法毕业。上述现象都属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范畴,都是大学必须坚守的底线标准。
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巨大的成就,也可以说我国基于规模扩张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基本完成。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这一伟大目标的重中之重。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埋下了一些隐患。但是,从目前多数大学的情况来看,高校并未形成危机意识,也没有建立预警机制,甚至对质量的理解都没有达成共识。例如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外延轻内涵、重学科轻专业等现象,大学生就业率、学生毕业薪资水平、校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等成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也成为学生上大学、选专业,高校增设热门专业、裁撤所谓“冷门”专业的重要依据。而大学生报到率、流失率、心理健康等关乎“人”的质量的现象却较少引人关注,学生、家长和社会都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教育现象也进行了猛烈抨击,号召高校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3954791711587942&wfr=spider&for=pc.,真正把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中。
实际上,高等教育界对“质量”一词从不陌生,自从有了教育就有了“质量”的概念,“教育”与“质量”两个概念是相向而行的。当下高等教育界对“质量”的认识在不断“拔高”,诸如“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原则”“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等各种表述已被大众熟知;学界对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解读也在不断深化,如质量检查、质量监督、质量保障(外部质量保障、内部质量保障)、质量评估、质量文化等词汇都已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行动框架。严格来说,质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实际起到的是预警作用,对质量认识的深化就是形成大学的质量文化。新时代,党中央又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显然是因为质量方面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某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这绝不是简单地在质量前面加了一个“高”字,仅仅从“高”的字面意思去解读质量对于解决高等教育体系的底线失守问题毫无裨益。
探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在于对质量进行何种“高、大、上”的理论解读,而在于对现实中的底线失守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理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木桶理论”切入,即决定木桶容量的根本因素是最短的那块板,这就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底线思维。我们如果对现实中的质量底线失守现象抱着任其泛滥而不作为的态度,就无法真正实现党中央要求的“高质量”。从几年前众多高校普遍采用的“清考”制度到提高绩点的做法等,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底线失守的典型案例。目前虽然“清考”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质量是否真的得以提升还有待科学评价的检验。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上限追求愈发强烈,但如果对底线的下滑视而不见,没有建立起高等教育应该坚守的质量底线,或没有对坚守底线进行积极反思,那么高等教育的质量上限也就缺乏了根基。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如高等教育质量底线无限下滑,上限无限拔高,高等教育是否可以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人们是否认可这样的“高质量”?这是否就是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应有之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更加多元,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也走向多元化。但允许多元质量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底线标准的降低,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多元质量观的本质是以“一种共同的底线或基点为前提,不然多元也只是相对主义或没有质量保证的代名词”(7)单 鹰.高等教育原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70.,这一点毋庸置疑。
令人棘手的是,高等教育质量底线的共同基点并不像雪山的雪线那样能被人为地测量和计算,它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和文化,当今“质量文化”一词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起就是对质量的最好解读。实际上,人们对质量标准的期待就是对质量文化的期待。在我国,尽管教学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认证等一系列做法规范了许多质量评价指标,但这些外部指标往往是高校的硬件标准,人们还无法简单地通过指标或数据判定质量文化。因为设置质量底线不在于设置最基本的及格线,而在于质量文化意识与教育规律能够真正潜移默化地走进每一位办学主体的思想和行动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守住高等教育质量底线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高等教育质量底线强调的是质量本身的目的性和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强调高等教育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价值和质量。当每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义无反顾地把质量作为办学的追求时,高等教育的底线就守住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质量底线的高等教育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更不是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应有特征。底线思维越是强化,高等教育才越会走向真正的“高质量”。
雪线上升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预警。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碳中和、碳达峰”的时间表。同样,“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对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的预警。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我们绝不能像人们对待雪山的雪线那样,眼见雪线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消失才去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也许为时未晚,但必定要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同理,每一个高等教育学人都应该自觉地树立高等教育底线意识,守护、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这才是“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应有之意。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底线的缺失一定会从根本上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返程路上,我把自己的一点想法与思考与同行人分享,没想到却引起了共鸣。一行人同样认为,今天大学的质量保障应该在建立底线标准上下功夫。回望身后渐行远去的雪山,一派地老天荒的深远与神秘也逐渐淡出视线。车窗外间或闪过几个骑行或徒步的“驴友”,他们背着背包,戴着骑行头盔、眼镜和手套,满身疲惫却掩盖不住内心的兴奋。这不禁令人思忖:这些“驴友”不也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吗?挑战自我极限的过程不就是认识自己毅力和体能底线的过程吗?如此看来,当一个人陷入迷茫之时,不妨进行一次“驴友”体验,这无疑也是在给自己倦怠的人生赋能,从而走向高质量的人生。
不忘初心,方能行远。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也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底线意识,悉心探寻底线内容,时刻警醒自己逾越底线的严重后果,始终警示自己坚守底线。从质量体系的构建来看,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促进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从单纯程序性、技术性的外在约束转变为主动、内生的动机需求,从而唤起教育主体的质量意识、质量责任、质量态度和质量道德。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每个高等教育学人都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且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那么全社会也就守住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雪山圣洁,恰如象牙塔般的大学殿堂;雪线缥缈,唤醒着高等教育学人的教育初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抉择与坚守。明底线,方能知敬畏;有底线,高等教育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