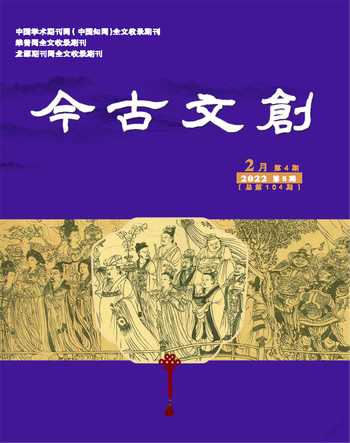原创生态舞剧《大河之源》的文化反思
2022-02-26吴少卿
【摘要】 原创生态舞剧《大河之源》作为现实题材的创作作品,用象征的手法呈现出了一场大河的生命礼赞。本文从具体的舞蹈本体出发,讨论了拟兽表演对于人性本质的呼唤;又以器物为关注点,讨论了原始器物所折射的文化成就及器物呈现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最后将视角落在大河陨落的呈现上,讨论了作品对于全球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观照。
【关键词】 大河之源;生态舞剧;舞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J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8-0086-03
继《朱鹮》之后,编剧罗怀臻与编导佟睿睿再度联手打造的原创生态舞剧《大河之源》于2021年5月上演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员们的倾情奉献中,展现了一场民族文化自觉与时代担当视角之下的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生态问题的颂歌。编剧在场刊中写道:“文艺创作,仅靠想象不行,唯有双足抵达,身心亲临……”
诚然如此,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一切的来源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进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当那些人们所熟知、熟悉的生活场景的反映同大家的心理感受发生呼应时,艺术作品的魅力和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能动性才能作用于观者、表演者其身,兼具思想性和审美性的藝术创作,势必要从充满魅力的客观世界当中汲取营养。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同时又会对人们思维意识有所影响和制约。发展到新时代的今天,在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背景之下,艺术为何、艺术何为的诘问不仅要求艺术家去真切地考虑艺术创作的能动效应,更要关注到接受群体所体悟、体会到的能动反映。
面对《大河之源》当中自然和人类、环境与资源、发展与保护的诸多现象,一场人与自然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便开始了,未来如何人们无从得知,那一个开放性的结果却留给大家无限的遐想。身处这样一个和平、发展、迅捷的时代,如何平衡好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应尽的社会义务,如何解决好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却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大河之流 ——拟兽表演所透露的人性回归
整台舞剧的串联,是由一只雪豹开始的。千百年前的昆仑山脉,一只雪豹似乎是那片空灵雪原的统治者和见证者,它徘徊在山顶的崖壁上,经历着岁月的轮回也见证着这片净土的和谐与淳朴。人类的进入似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与取舍有度的人类生存似乎又达到了一种平衡,直到那一声盗猎者的枪响,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断裂。
在这样的背景故事中,舞台上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动物群体,有霸气的雪豹、凌厉的雄鹰、矫健的羚羊、魁梧的牦牛等等,万类竞自由的动物在这里并没有呈现出追赶杀戮的生物链条,而是以拟人化的方式,相互依偎、玩耍,呈现出一片雪域高原的和谐之景。
在自然界中,以羚羊、牦牛为代表的素食动物是不可能与雪豹、雄鹰等肉食性动物如此和谐共处的,但是在舞台上的它们通过拟人化的处理,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可以和平共处地存在于舞台空间之中,相比起后期人与自然的竞争,这样动物之间的和谐就显得更加可贵和可信。
在这里的动物,似乎不再只是单纯思考如何生存的简单物种,而是雪域高原上拥有了灵智的精灵,他们懂得自然的相处之道,懂得如何修补、休整被打破的平衡,也懂得如何调节自身去更好地适应环境。高原上这些所见的动物,一方面是现实高原环境中那些可爱的生灵,另一方面它们也和当地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姚斯所说:‘接受者的心里不是真空,而是早就已经有了预置结构。’”[1]真空、空白其实都是相对于艺术作品结构而言的意义悬置部分,这一部分不仅给予了接受者极大的解读自由,也给了表演者极大的实践自由。于是在经历过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之后所带有的那些体验,便以期待视阈(期待视野)的形态进入到意义的解读当中,成为那些早就形成的印象。在这种印象形成的过程中,观者、接受者在彼此的自我暗示下,实现了对悬置意义的填补。动物们的身份,便不再是生物学视角下的那些单一的物种,而是带着当地文化、风土人情等一系列精神特质的物质载体,传达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界本身所带有的包容意味,相比起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侵略,动物身上所显露出来的人性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这些动物似乎具有了人性,又或许是编导希望人们通过对这群动物的反思来更好地反思自己。不管是舞剧当中人对于自然的改造,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舞剧中人、物、事的理解与解读,都是在进行自我确认和回归,这种舞蹈所带给人的本质回归伴随着对人性的呼唤。
正如编剧罗怀臻在场刊中所说:“舞蹈,不仅仅表现‘美’,也表现‘善’,表现‘真’,唯有经过‘真’的求索,‘善’的升华,方能抵达‘美’的胜境。而拥有了‘真’的思想内涵与‘善’的精神洗礼,舞蹈之‘美’,才会更加纯粹,更加高级,也更加‘美’。”
慕羽教授也说:“……《大河之源》则是为‘善’和‘善念’而舞。‘善’是一种良知,‘善念’则更是对良知的信念。剧中的群舞呈现出一种不经雕琢的天然之美,无论是藏族风格的‘取水之舞’,还是天人合一、日月交汇的‘圣水之舞’,整体调性都是契合的。”[2]
在《大河之源》当中的群舞,既是那高原上纯真质朴的女子,又是那大河当中若隐若现的精灵,人、水、月、情在这种整体的和谐当中带领人们进入到那个神秘的高原世界。
二、大河之源 ——原始器物所折射的文化回望
除了对于雪域动物的描绘以体现其生态的活力之外,《大河之源》还关注到了5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以显示其文化生态积淀之深。
裸露的高原,清冽的泉眼,渐渐汇拢成溪的河水。暮色降临,日月交汇,布满星辰的湛蓝夜空。星辰之亮、之近,仿佛触手可摘。早在5000年前的彩陶文明时期,在河湟地区出土的彩陶纹饰上,就描绘着先民子女曼妙的舞姿。据称那是最早记载的中国舞蹈。
原始器物所代表的物质文化,往往在认知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人们会普遍认为他们是相对简单、容易理解的器物,其实器物背后凝结着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劳动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希望。以器物为载体的人类学家其实早就开始了通过器物对于人类社会的观照。
自古以来,器物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在文化研究还是考古研究当中,器物及其背后的历史、功能、文化、技术、经济、传播、交流、贸易等方面,都在不断地丰富着由器物本身出发的各种研究。从最早地坐在摇椅上、走廊上的人类学家开始,到深入田野、强调体验的方法,器物研究开启了其残存到建构的历史功能;社会学家则致力于其作为物品的能动性研究,从创作者出发到作品、接受者,都成为这种能动性现象当中的不同角色,发挥着自身能动性的同时,又被器物的能动性所影响和改变。
现在的器物研究,不仅仅关注到这些层面,更涉及了器物市场化的交易、效益以及其所属文化的涵化、濡化现象。经历了早期舞蹈人类学研究之后,理论研究的范式也从对于物本身的关注,转移到了物对于人的塑造。“这类新探索颠覆了长期以来在物的研究中对于人们如何制造物的研究模式,而去诘问物是如何制造人的、客观之物是怎样影响到人的社会关系的、没有生命的物何以具有了其自身的能动性……”[3]
物之本身所涉及的文化界面是丰富的,从功用到审美,从材料到工艺,从功能到隐喻,它本身承载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当中的诸多意义。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制造器物的材料、技术、功用来推测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通过比较古物与新物的诸多方面来审视当今的发展进程,通过追溯当下之古物的审美根源来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物之本身,不仅仅是某一个工具、器物、道具,更是人民的智慧、文化的结晶、历史的选择。
所以,呈现在舞台之上的那些彩陶盆及各式各样的陶壶、陶碗、陶盏等,不仅仅体现着华夏文明深远的物质文化基础,其中更凝聚着华夏子孙背后的历史文化动态。
基于这样的设计,不管是再现陶盆上那些曼妙的舞姿还是表现的高原少女,以陶罐为线索贯穿的基于原始器物的观照,体现了对于族群历史文化的回望与回归。
三、大河之殇 ——全球语境下的生态问题回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4]
因此,《大河之源》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大河之源》这部舞剧作品并不是聚焦在“我”与“卓玛”之间的爱情故事,尽管剧中的大量双人舞为二人最终的关系做了铺垫,但是基于对于高原生态之大爱视角下的“我”与“卓玛”之间的情愫,却是克制而内敛的。
一方面“我”是作为一名考察水源的“他者”来到这片净土,另一方面“我”与“卓玛”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这片纯净之域的尊敬与热爱,在这种情感的共识之下,男女主人公之间更多是异域文化的交流者和传播者,又是共同文化属地的文化保护者,所以二者之间的情感更多是朋友、知己。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编导和编剧都没有着重刻画二人之间的情感,而是将这份被克制的情感,转移到对雪域高原的热爱和尊敬,以及对盗猎者的仇恨与憎恶之上。
正是这种将小情小爱的放大和转移,反而突出了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生态问题的普遍观照。不论是生态的失衡还是环境的破坏,不论是物种的灭绝还是气候的突变,都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缩影。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盗猎者的枪影下,那一具具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甚至是刚出生的小藏羚羊,都难以逃脱盗猎者的魔爪。尽管从先民的捕猎时期,人们也看到过这种对生命的掠夺,但一方是为了生存,是对生命敬畏之下克制的索取,而另一方则是为了金钱,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无尽的破坏。也正是这样的区别,编剧和编导都将视角聚焦在那大河之殇的挽歌。“天下黄河青海清——这是大河之源;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大河之浪;汹涌的气势,澎湃的涛声——这是大河之魂;河水枯竭,河床裸露,生灵遭殃——这是大河之殇。”
从源头活水到河道干枯,是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步步紧逼下造成的严重后果。《三江源生态》杂志主编唐涓在场刊中写道:“作为世界屋脊的中华水塔三江源,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地,更是生态的高地、生命的高地、文化的高地。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明天。”
“舞剧《大河之源》是一部倡导生态保护的‘生态舞剧’……”[5]生态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中之重,也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导向。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大河之源》与《朱鹮》的同质在于它们对于人类的明天、生活环境、物种多样的普遍观照,所聚焦的不仅仅是人类情感当中的男欢女爱、情爱纠葛,而是将视线放大于全人类的共同感受,即是对自身生存空间、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反思与讨论,通过将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揭露于舞台空间,从而在这一具体的时空中,唤醒处于异时异地的那些冷漠、残酷的人们,从而更好地反哺当下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
四、结语
《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龙仁青在场刊中写道:“世居青藏高原的人们,目睹了黄河成长的过程,看到了她蹒跚学步的可爱模样,见识了她出落成窈窕少女的惊艳与美丽。在我看来,《大河之源》便是讲述和演绎了黄河少女的故事:当父亲般的青藏高原岿然不动守候着故土家园的时候,美丽的黄河少女离开了父亲的怀抱,走上了一条造福人民开创未来的道路。《大河之源》带着青藏高原上的大山和众水塑造和淘洗出坚毅与清新,承载着‘深耕黄河文化、厚植青海故事’的美好夙愿向着世界走来。”
在作品中,卓玛的形象和父亲的形象,不仅仅是那位世居高原的少女和父亲,他们对于大河之源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见证,恰恰使他们成了这条大河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这种精神纽带的连接下,父亲就是那座大山,她仿佛就是那条大河,正印证着她最终的归宿,呈现出她无私的反哺之举。
参考文献:
[1]于港.从“蓝蓝的天空”看当代的内蒙古舞蹈[J].艺术品鉴,2020,(30):129-130.
[2]慕羽.生态舞劇《大河之源》:为善念起舞[N].中国艺术报,2021-05-28(3).
[3]王建民.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J].思想战线,2014,40(05):1-6.
[4]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EB/OL].2018-06-24.http://www.gov.cn/zhengce/2018-06/24/content_5300953.htm.
[5]于平.生态舞剧创作的文化自觉与时代担当——青海省演艺集团大型原创生态舞剧《大河之源》观后[N].中国艺术报,2020-12-16(7).
作者简介:
吴少卿,天津音乐学院舞蹈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舞蹈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