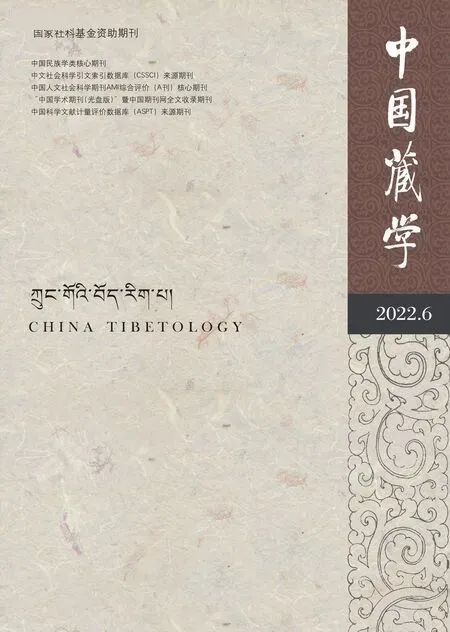论《格萨尔·贵德分章本》的同属抄本系统及其汉译文本的情节变异特色
2022-02-24李连荣
李连荣
引 言
《格萨尔·贵德分章本》①“贵德分章本”一名,源自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为便于叙述,本文中笔者沿用此名简称并仿此为其他抄本取了名号简称。在我国《格萨尔》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大约自1964年以后,《贵德分章本》的藏文抄本原文已不知去向,其汉译文本却在《格萨尔》史诗传承、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后来《格萨尔》史诗在中国学界得到“高规格的学术待遇”并取得如今的辉煌成就,都与这个汉译文本的“影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其藏文原文散佚为我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比较研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诸多与该抄本同属一个抄本系统的藏文抄本陆续被发现,从而为我们展开比较研究乃至于还原该抄本的藏文“原貌”提供了可能。
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参照与该文本具有密切关系的几个藏文抄本,尝试讨论该汉译文本在情节结构上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一、《贵德分章本》的同属抄本系统
所谓的“同属抄本系统”,是指一个从口头传承记录而成的书面文本或艺人自己撰写而成的文本(即抄本),经过历代或不同地域的传抄而出现了的多个类似抄本。这些抄本之间,虽然在故事情节与文字表述上存在些微差异,但从整体故事情节结构和语句表达方面来看几乎是一致的。它们之间“长得非常相似”,乃至于“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极其雷同。《贵德分章本》正是同属于这样一个具有许多“兄弟姐妹或子孙后代”的抄本家族或系统。因此,我们把这些产生微小变化而且相互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抄本”,称作“同属抄本系统”。
同一个抄本发生这种变异,或者说这些抄本之间出现这种微妙的相似现象,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传抄者的“纠正”和“校订”导致的。由于对经过历代传承下来的原抄本中的古词、方言或语句表达理解不够,或者能够理解但却认为原文表达不够完美从而予以“纠正和校订”,就会造成新抄本与原抄本之间的些微差异。另一种可能是,传抄者非常熟悉其他文本的《格萨尔》史诗,因而认为原抄本“讲述错误”,从而主动对相关情节作微小的修改,等等。总之,这种因传抄而在传播、传承过程中发生微小变化后形成的多个不同抄本,就如同同一位艺人在不同场合讲唱同一个故事所产生的微小差异一样——即口头诗学中所谓的多个“特指的歌”(the song)①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页。,表明它们既属于“同一个作者”(具有共同母本),但各自又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和价值。
就目前所知,与《贵德分章本》同属于一个抄本系统的藏文抄本有《民和分章本》《化隆分章本》《北京分章本》和《强曲艺人分章本》。
《民和分章本》②其藏文名称为(《岭雄狮王的本生传》);此外,西北民族大学的学者称此抄本为 “俄罗斯藏分章本或俄藏分章本”,也是非常贴切的称呼。发现最早,于1885年由波塔宁与其土族助手从三川 (青海省民和县)“贡刹寺”获得。波塔宁后来对其做了补抄工作,最后收藏于列宁格勒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1961年,策·达木丁苏伦将其转抄带回蒙古国后以手写体出版。但是,不知是原抄本本来就“破损严重、字迹模糊”,还是抄录者的工作态度、藏文水平等原因③从该手写体出版本字迹可见,它可能是多个人采用楷体、草体等多种字体抄写而成,而且字体潦草、缺少规范、错误较多。,总之该手写体版本出现了连篇的错别字、语法错误、字体不同和大量文字遗漏等现象,几乎“不堪卒读”。最近,该手写体出版本经角巴东主和娘吾才让整理,以汉文名《格萨尔·分章本》(藏文名为:意为《简略史诗·珍宝璎珞》)在国内正式出版④角巴东主、娘吾才让整理:《格萨尔·分章本》,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177页。。
笔者对策·达木丁苏伦出版本与角巴东主和娘吾才让整理本进行了初步的比对,发现《格萨尔·分章本》的优点在于,整理者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藏文原稿的特色,相信其中发挥了整理者的艺人品质①娘吾才让不仅是一位青海《格萨尔》史诗保护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吟诵艺人”。他的讲唱音色浑厚嘹亮、吐字清晰鲜明、曲调婉转悠扬、曲风典雅抒情,是继著名优秀吟诵艺人尕藏智华之后又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用安多方言讲唱的杰出史诗艺人。迄今为止,他已经讲唱超了100多个小时。其讲唱的《格萨尔》史诗经常在青海藏语广播电台中播送。以及对《贵德分章本》汉译文本的借鉴和还译。特别是修改了错别字和语法错误,并补充了情节方面的阙疑,比如依据《贵德分章本》汉译文本对其“魔之章”结尾残缺部分的补足等。但是,该整理本“明显的不足”也在于“整理”。因为整理工作本身,就如将口头讲唱的故事记录成文字一样,历来众说纷纭,饱受质疑。但不管怎样,对于研究者来说,该整理本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相关文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是《贵德分章本》同属抄本系统的新成员。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则是另外一个“特指的歌”(the song)。
此外,波塔宁在《中国唐古特—西藏地区和中央蒙古 (第二卷)》中,将此抄本称作是“欧洲第二部《格萨尔》书稿”②张艳璐:《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晚清青藏及安多地区考察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36页:“……而这部手稿据其本人考证应该是欧洲第二部《格萨尔》书稿。”第一部可能指蒙古文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国内有两个汉译本:桑杰扎布译本 (1960年)与陈岗龙、哈达奇刚等译本 (2016年)。,可见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发现”。但非常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学界尚无一人亲眼看见过该藏文抄本的原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策·达木丁苏伦先生出版的转抄本。尽管我们说该转抄本如何如何“不堪卒读”,但内心却保持着对转抄者和出版者的深深敬意。若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就根本无法得知该藏文抄本的丁点信息。
《化隆分章本》③该抄本的藏文书名为:(岭雄狮王的黄金史)。是徐国琼搜集到的,从其早年调查笔记和晚年回忆文章可见,该抄本搜集于1959年。最早探知该抄本的情况是1958年,当时徐国琼与华甲在去往青海南部的调研路上途经化隆县城(当时位于巴燕镇,现为群科镇),其间拜访副县长却吉时得知若索寺格鲁派)的合尔纳活佛 (当时为县政协委员)处藏有多册《格萨尔》手抄本④徐国琼:《〈格萨尔〉考察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页。。在徐国琼后期的追忆文章中提到从合尔纳处搜集到了《霍岭大战 (上)》⑤实际是 《霍岭大战》之下册。该抄本封面原藏文题名为:,意为 “世界王的传记·降伏霍尔简略本·天铁 (霹雳)宝剑”,封面题名与正文均用藏文柏簇字体抄写。在封面与封底有汉文题记为 (估计为当时抄本校阅者杨质夫先生的笔迹):白帐王下部 (化隆本)。在该抄本的最后两页和封底即原藏文页码第200页b面、第201页a面与b面上,留有徐国琼笔迹:“徐国琼经催毛借来,待还。”该抄本原藏文后记中提到了作者著作此部史诗的情况:“此简本著于2月2日,北方郭密地方附近的吉谷 (音译为吉谷,《毛兰木词典》中写作音译为吉盖)的密咒师 (即达贤巴)在长官 (部落王)的衙门完成。……老密咒师达贤巴的幻觉中显现”;封底用藏文正楷题为:(康·达贤巴讲述了)。由此可知,此达贤巴应该是第四世达贤活佛,即18世纪的达贤杜德多杰 ,该活佛还著有史诗 《阿达拉姆》(即 《地狱救妻》)。等多部史诗,其中提到了3部史诗的名称,并未提及该抄本的名字⑥徐国琼:《〈格萨尔史诗〉谈薮》,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8页。徐国琼回忆搜集该抄本的情况时写道:“次年春,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一人专访了远离县城的一个偏僻山村德恒隆乡甲加村,拜访了县政协委员合尔纳老人。从这位老人手中搜集到了《霍岭大战 (上)》《安定三界》《分大食牛》等部抄本。”。但在笔者翻阅其搜集的其他抄本中,包括此部抄本与上述所谓《霍岭大战 (上)》⑦此抄本以《霍千莲牧场》(达贤仁波切述录、久美多杰整理)之名,于2021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等抄本内,均可见到徐国琼留下的笔迹:“徐国琼经催毛借来,待还”⑧本文所说《化隆分章本》之封面、首页上均有类似此意的徐国琼的笔迹。等字样。从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①原名称为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研究所,2020年7月15日更名为现在名称。的登记目录中可见,该抄本登录名为《英雄诞生》②李连荣:《〈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解题目录 (1958—20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4—96页。。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2019年笔者曾前往化隆县德恒隆乡甲加村作调研③此次调研中得到了青海省民协主席索南多杰先生、化隆县文联李成虎主席、化隆县文联的马继萍秘书长、德恒隆乡的马冠毅书记、甲加村的第一书记曹文生先生、甲加村书记兰州先生、村长夏吾才让先生、原甲加村百户后人僧人彭措加措、研究生彭毛才让等人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在此致谢!特别是第一书记曹文生先生亲自陪同、马继萍女士驾私车护送,攀越崎岖险峻山路,此情此义,感铭于心!,了解该抄本的传承情况。经向当地老人、村书记兰州 ()与原百户拉加 ()的后人了解,得知该抄本系由已故若索寺活佛合尔纳家族传承,合尔纳活佛祖籍青海省同仁县合尔纳村 (现今为黄乃亥乡)。由此可知,该同属抄本系统传承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隆务寺 (格鲁派)为中心的河湟谷地的最南段。
据王沂暖先生介绍,《北京分章本》抄本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不知何人搜集。故事内容除了第五章即《征服霍尔》与贵德分章本稍有差异外,其他章节几乎与《贵德分章本》一模一样④王沂暖:《关于藏文 〈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229页。就像“俄罗斯藏本”一样,将该抄本取名为“北京藏本”可能更准确一些,因仅收藏于此,而不像其他抄本那样长期传承于某个地区。。关于这一抄本,除王沂暖作过介绍外,其他学者似乎没有过多关注。
最后介绍一下《强曲艺人分章本》⑤该抄本取名为《强曲艺人分章本》,是由于该抄本后记中提到了该作者的名字 (第404页):“强曲著于土虎年长期静修合意之际”,因此就以此艺人的名字作了区分,并没有采用出版地的名字来取名。。笔者在近年阅读中,看到一部手写体出版的《格萨尔》,藏文全名为(《岭·雄狮王的史诗降伏北魔与霍尔之极简经过》),简称为(《霍岭简本》)。该出版本用藏文乌金字体 (正楷)抄写,1979年出版于印度德里,正文共404页,之后附有61岁的抄写者桑杰多吉的一篇长达16页的祈愿文。经过比对可知,此书也属于该同属抄本系统。该抄本在章节划分方面,除了在“魔之章”⑥第36—37页:(意为现在简述一下 “魔章”)。开头点明了下面所要讲述的内容以外,其他章节开头并无显明的章节说明,只是在另起一章时,用六字真言开头作为特别明显的区别。可以说,该抄本开头部分 (缘起)与其他抄本有明显差异,其余部分除了文字与情节比较精简扼要 (即书面化倾向鲜明)以外,内容情节和文字表述等方面基本上与其他抄本相似无疑。
二、《贵德分章本》的“冗余”与“俭省”情节
在上述同属抄本系统中,每个抄本或多或少都有各自不同于其他抄本的情节,但《贵德分章本》汉译文中的有些情节看起来却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新创作的”和“搬运来的”。比如,在“征服霍尔”(即“霍尔之章”)的开头部分说到派4只鸟儿外出为黄帐王寻找王妃时,讲述黑老鸹 (乌鸦)到岭国见到正在梳头的珠毛 (珠姆),唱歌表达了作为黄帐王使者前来求娶王妃而惹怒珠毛的情节⑦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104页。,不见于其他抄本,说明这个情节可能是华甲艺人新增加的。因为这部分内容几乎“原模原样地”出现于由他译意、金放整理且早于《贵德分章本》发表的《南瞻部洲的雄狮——盖舍尔》⑧华甲译意、金放整理:《南瞻部洲的雄狮——盖舍尔》,《青海湖》1957年第7期,第4页。的开头部分。而其译意的《南瞻部洲的雄狮——盖舍尔》,实际上讲述的是以白帐王为主人公的《霍岭大战》,属于另外一个传统的抄本系统 (笔者称之为南传本)。这一点可以作为华甲艺人对《贵德分章本》“搬运”和“增添”内容的一个鲜明凭证。实际上,这种“新增添”和“搬运来”的内容,在《贵德分章本》汉译本中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其他抄本。这种现象,除明显反映了华甲作为艺人发挥了其“独具个性魅力的阐释和创编”作用外,可能还包含了“翻译、整理”①该汉译文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种文本形态:即1958年《青海湖》杂志发表和1959年青海文联内部编印时,均以“华甲、王沂暖翻译、整理”署名。该抄本时出现“误记”或依据时势需要增添的内容。
这种在“翻译整理”该抄本时出现“记忆错误”的现象,同样也见于王沂暖的文字表述中。比如在正式出版该抄本的“译者前言”中,他解释当时“翻译整理”的确切含义——“整理过”的内容时说:“原文第一章中,与白梵天王商量派一位神子下凡,降妖伏魔的,是观世音菩萨。旧译把‘观世音’改译为 ‘天神’,现仍按照原文译为 ‘观世音’。”②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第2页。实际情况是,该同属抄本系统的其他几个藏文抄本中,在此处根本没有提到过观世音菩萨。这可能是王沂暖先生“记忆错误”造成的,因为这个“译者前言”是该藏文抄本散佚约15年后才写成的。事实上,关于观世音菩萨与白梵天王商议或者劝其派神子下凡这个情节,是林葱木刻本《天岭卜筮》(《天界篇》)中的内容。林葱本《天岭卜筮》述及故事缘起时讲道:吐蕃末期,佛法入灭,战争兴起,边魔窜入中央,人民痛苦,尊圣大悲主(即观世音菩萨)③大悲主是观世音菩萨的主要名号。此外,为突出讨论重点,本文中重点内容文字部分笔者添加了下划线。悲心不忍,祈祷无量光佛指示救度方法④Kunzang Tobgyel,The Epic of Gesar,Volume I,Druk Shering Press,Thimphu,Bhutan,1979 年,第 2—3 页。。王沂暖先生很可能将此情节误记为是 《贵德分章本》的内容了,这可从 《贵德分章本》本身文字内容的变迁和其他同属抄本系统的文字表述得到印证。
首先,我们来比较3个汉文版本的《贵德分章本》对此内容的描述。
(1)1958年版:“……大慈大悲的佛祖菩萨们,看到这种情形,顿生不忍之心,于是就和白梵天王商量,想法拯救人间灾难。后来决定,派遣一个能降伏妖魔的天神下界……”⑤化甲 (华甲)、王沂暖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青海湖》1958年第6期,第2页。“华甲”艺人的名字,当初有两种汉字写法,华甲或者化甲,后来固定为了“华甲”。
(2)1959年版:“……同情人民百姓的天神们,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实在不忍。于是大家就商量,要想法子拯救人民百姓的灾难,要派一个善良勇敢的天神,到人间去降魔除害……”⑥华甲、王沂暖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 (草本一)》,西宁:青海省文联编印,1959年,第1页。
(3)1981年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到这种情形,顿生不忍之心,就和白梵天王商量,想什么法子去拯救人间灾难。商量的结果,决定派遣一位能降伏妖魔的天神下界……”⑦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第1页。
关于这一内容,藏文《化隆分章本》和《民和分章本》一致,几乎一字不差。按《化隆分章本》译出:“中界人间时值恶世末期,恶魔兴盛,唯有恶魔掌控人间。佛陀与一切菩萨商议认为,需派一位降伏边地四魔的化身 (下凡),顿珠噶布英勇高超,派去合适。”⑧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藏:《英雄诞生 (化隆分章本,藏文长条)》,1959年,第2a页;Ts.Damdinsuren ed.,Corpus Scriptorum Mongolorum Instituti Linguae et Litterarum Comiteti Scientiarum et Educationis Altae Reipubligae Populi Mongoli,Tomus VIII,Fasci ulus 3,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Chapter I-III.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хэвлэл,1961:16.《强曲艺人分章本》的开始略有不同,另外也未提到观世音菩萨而是提到了佛陀。该版本首先讲述了吐蕃时期王国强大,佛法传入,晚期灭佛而造成妖魔兴起,释迦佛祖慈悲关照,此时须弥山山顶中央帝释天王四周尚有4位小帝释天王,看到人间恶魔兴盛,通过明镜查看派谁下凡降魔合适时,得知是南方的帝释天。他有3子,此事最终落到了其最小的儿子顿珠噶布身上①Jamyang santen and Tashi.Hor gling bsdus pa.Delhi:Lakshmi press,1979:3—6.。由此可见,《贵德分章本》的第一版即1958年版中提及的“佛祖菩萨们”,其实最接近其他藏文抄本。也即此版可能在翻译时,对原藏文抄本此处的内容“修改”最小。
事实上,包括《贵德分章本》在内,在其同属抄本系统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观世音菩萨”,至少也出现过两次。不过,华甲与王沂暖的译本中,一次给予了保留,即“我的北库房/有个白螺大悲观音像,……”②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第303页。。另外一次完全没有翻译,即霍尔女卦师怯尊 (曲珍)根据卦象得知弟弟此次出征有生命危险,劝他别出征而不听劝时,只好赠予自己的戒指 (或手镯)并告诉他,若在战斗中出现危机时要修念观世音明咒、平寂怨恨,以便死后步入善趣。此处藏文原文,其他几个抄本均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似的含义。
比如,《化隆分章本》:“……军队前行别冲前头,/返回之时别殿后。//别骑乘小黑骏马!//军队交战之时刻,/心头修念观世音菩萨咒!/心中平寂怨恨念诵六字真言!//请戴上姐姐的这枚金手镯 (或金戒指),/来到中阴道路关口时,/那法王 (阎王)主仆太凶暴,/别随业力说谎言!//将此黄金手镯交付 (阎罗)国王之眼前,/虔诚禀报道明 (自己)是噶尔萨曲珍的兄弟。//请让前往吉祥道路的地方,/心中不要犹豫去往天界。//此生再与兄弟相会难,/来世愿在空行界中相会!//”③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藏:《英雄诞生》(化隆分章本,藏文长条),第98a—99a页。强曲本更进一步指明了选择“善趣”的方法:“……别 (站)在军队前行之前头,/和收回之时之后方。//别骑乘黑色小骏马!//如果非得冲杀时,/心头修念观世音菩萨,/心中别放逸诵六字真言。//戴上姐姐我的这枚戒指,/步入中阴坡路时,/那国王 (阎王)主仆太残暴。//业之明镜,别说谎言;/将此戒指交付国王 (阎罗)眼前。//禀告是噶尔擦的兄弟,/恶趣在右善趣在左,请求踏上吉祥之道 (善趣)!”④Jamyang santen and Tashi.Hor gling bsdus pa.Delhi:Lakshmi press,1979:144—145.《民和分章本》中说:“……军队前行别走在前头,/返回之时别呆在后面。//别骑压在小黑骏马上!//与军队交战之时,/心头修念观世音菩萨,/心中舍去怨恨念诵六字真言。//姐姐这枚金镯 (戒指)(送)给你,/去往中阴关口时,/那法王 (阎王)主仆太凶暴。//业之明镜,黄金手镯穿过国王 (阎王)之眼路。⑤此处原文中自 “业之明镜”至 “……国王眼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诗行,而其他抄本中用两个诗行来表达。从史诗格律上看,它破坏了7或8音节的音节限制,达到了11音节;再者,它也不符合藏文语法规律,表义不明。由此,通过与其他抄本对比,显而易见,这里抄漏了半句即 “别说谎言”。/禀告是噶尔萨曲珍的兄弟,请求步入吉祥道路之天上。//心中不要犹豫去往天界,/此生再与兄弟相遇难,/愿来世相见于空行界。//”⑥Ts.Damdinsuren ed.,Corpus Scriptorum Mongolorum Instituti Linguae et Litterarum Comiteti Scientiarum et Educationis Altae Reipubligae Populi Mongoli,Tomus VIII,Fasci ulus 3,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Chapter I-III.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хэвлэл,1961:60.
但在该汉译《贵德分章本》中,却将此段译为了:“……冲锋别在最前列,/退却别在最后边,/要骑那匹小黑马,/临阵能保主平安。//再带去姐姐的金戒指,/万一不幸献到阎王前。/阳世阴间一个理,/当官的哪个不爱钱。/阎王得了金戒指,/定能让你升西天。/今天姐弟永别了,/发愿来生再相见。//”①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第118—119页。由此可见,此处《贵德分章本》除“删去了”观世音菩萨的内容外,也可能错译了“别骑乘小黑骏马”的内容。而且在上述3个藏文抄本中,“戒指 (或手镯)”仅仅作为姐姐这位“法师”的“信物”,而并非作为“行贿之物”。可以想见,进行如此“修改翻译”,完全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要求而作出的选择。
通过上述例子,也可以发现各抄本藏文原文在语句表述细节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和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抄写者对待原文的工作态度和史诗知识的储备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文学鉴赏能力。正是这些变化,造成了内容些微差异的“同属抄本系统”——也即“兄弟姐妹或子孙后代”抄本的大量出现,或者说这一“抄本家族成员”的兴盛。同时,正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确立了各抄本能够独立存在于世的价值与意义。
三、《贵德分章本》的影响与误译
通过“同属抄本系统”内几个抄本之间的对照,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其中某一个抄本“所选道路”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检验这条“道路”的准确性或偏离“该抄本家族”的距离远近问题。我们通过《贵德分章本》本身前后的汉译文,可以看到其“整理思想”的变异,而且参照其他同属抄本系统中的抄本,也可以确认这种“整理思想”的准确与否,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观察这种“整理思想”产生的影响。
关于这种“整理思想”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别音译词汇的变化对日后《格萨尔》史诗在汉文化界中的接受与传播问题;二是汉译时对原藏文抄本词汇的“修订”对《格萨尔》学界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音译词汇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汉文译文本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两个关键词语的变化:一个是从“盖舍尔”向“格萨尔”的变化,另一个是从“胡儿”向“霍尔”的变化。这两个音译词汇,对以后的汉译史诗和《格萨尔》史诗在汉文化圈中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然,华甲与金放在译意、整理“盖舍尔”之前,可能并不知道已经有任乃强等在40年代音译的“格沙、格萨”,也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等人在报告中提到过“格萨尔”。但是,种种迹象表明②任乃强先生1940年代的论文《关于 〈蛮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 〈蛮三国〉》等中称为“格萨”或“格沙”、老舍先生1956年的文章《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称为“格萨王”,王沂暖先生与华甲合译之《格萨尔王传》在1958年《青海湖》杂志上连载时,他将此前华甲等人所用“盖舍尔”修改为了“格萨尔”。可见,他对前人的成绩是比较熟悉的。,王沂暖先生显然是知道任乃强、老舍等人有“格萨”“格沙”“格萨尔”等音译名称的事。因此,在他们合作翻译整理的《贵德分章本》中,不仅摈弃了“盖舍尔”一词,而且将“格萨尔”一词固定了下来,并得到当时众多翻译者的确认与大量使用,使“格萨尔”一词成为通用词汇,沿用至今。与此相反,他们在早期译文中使用的另一音译词汇“胡儿”,却由于同时期其他人都音译为“霍尔”,所以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贵德分章本》本中“不得不”修改为“霍尔”。实际上,不论从汉文化传统对北方乃至西方民族的称呼,还是从藏族历史上以及《格萨尔》史诗中可见,他们对“胡儿”民族的音译名称可能更符合传统或更准确一些。但遗憾的是,这个译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承。
其次,我们来看对原藏文抄本中一些专属词汇的修订问题。举两个例子:一是从“写姜珠毛”到“森姜珠毛”,二是从“交惹”到“台贝达朗”。
严格意义上来说,从最初将“台贝达朗”修改为“交惹”,到后来再将“交惹”修改为“台贝达朗”(即该汉译文的3种文本采用该词的变化,详见下文),仅仅是《贵德分章本》汉译者自身认识《格萨尔》的“正确性”的反映,与该藏文抄本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当然,从“写姜珠毛”到“森姜珠毛”,再到后来王沂暖译其他《格萨尔》中统一为“珠牡”的变化,也属于这种情况。稍有不同的是,从“写姜珠毛”修改为“森姜珠毛”,实际上忽视了对原藏文抄本内涵变化的理解,也就是这种变换可能反映了抄本的时代更迭现象和地区文化的强势影响。
最初的汉译文1958年在杂志上发表时,主人公格萨尔幼年的名字是“台贝达朗”①华甲、王沂暖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 (二)下界投生》,《青海湖》1958年第7期,第25页。。但是到了1959年内部编印本,两位译者将“台贝达朗”()修订为了“交惹”(),并且注释为“是苦孩子穷孩子的意思”②华甲、王沂暖翻译整理:《格萨尔王传 (草本一)》,第22—23页。。修订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从民间的口传史诗和广泛发现的史诗抄本可见,主人公幼年时期的名字一般都叫交惹 (现多音译为“觉如”),而“台贝达朗”之称仅见于该同属抄本系统中的几个抄本,并不具有“广泛性”。因此,两位译者可能依据“大趋势”进行了修订。后来,王沂暖先生为了尊重原文,依据自己的“记忆”③可能依据的是其保留的初译草稿。因为从该出版本可见,其他众多“修订处”也比较靠近该“同属抄本系统”中其他抄本的藏文原稿。,矫正当时“整理过”的内容,恢复了原文内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对我们研究史诗的创编历史,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从当下的研究可知,不管是“台贝达朗”还是“交惹”,这种取名在史诗中都具有深意,并非作者 (艺人)一时兴起随意取的。“台贝达朗”的含义是“乘之马道”④对于该词,有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中写作(意为乘之马靴)等,有多种拼写方式。笔者从该同属抄本系统的整体风格,认为“乘之马道”(即大乘道)可能更符合“作者原意”。,其中隐含着“大乘之道”的含义,具有佛教思想。而“觉如”的含义,学界争议较多。有说是“双耳竖起”()的记音;有说是从“佛子”“王子”或“菩萨”()变音而来;也有说是从肉球形反刍袋 ()的变音而来,以及具有“哥哥的可爱弟弟 (小兄弟)”()的含义,等等。但从该词广泛流传于康区的通识来看,一般被解释为“佛子”和“小兄弟”之意比较常见。
笔者揣测,上述对“觉如”一词含义的众多解释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中一些含义也打上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即便是被认为具有侮辱或诅咒含义的“双耳竖起”,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驴耳王”或者“牛角王”(如酒神狄俄尼索斯形象)之类流传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古老英雄或恶魔的故事 (艺人帽上的驴耳特征也可增加这种含义的“可信度”)。而佛子、王子乃至吐蕃赞普的小名 (如勇猛到能用铁索捕获野牛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小名野祖如)和小兄弟等含义,具有鲜明的藏族特色。由此可见,各抄本选择怎样的名称,不仅反映了不同传承地区的特征,而且也可能与历史时代具有密切的联系。使用“台贝达朗”(大乘道)之名,不用说与佛教后弘期噶当派、格鲁派等宗派中推崇显宗大乘道之作者们参与史诗创编工作有密切关系。相反,“觉如”之名的使用,从其最初含义来看或许时间更加悠久,可能是早期苯教时期象雄文化中崇拜“鸟角王”()和具有神通的“驴耳儿童”等的文化遗留。
从“写姜珠毛”变化为“森姜珠毛”,其中有无可循的线索呢?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比如艺人热古阿尼的《降魔》就可以作为其典型例证。在热古阿尼的《降魔》中,似乎也为处理这两种情况左右为难。但也为这种变换给出了自己的“合理解释”,即将“雪山”与“狮子”联系在一起,为二者的顺利过渡铺平了道路。因为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经常使用“水晶”一词来修饰雪山,再据“雪山上居住着具有甘露般狮奶的神圣狮子”传说,就自然而然地将“写姜珠毛”(水晶/雪山夫人珠姆),修改为了“森姜珠毛”(雪山/狮子夫人珠姆)。
这里,引用其中诗句作一说明。首先,该文本中存在“写姜珠姆”和“森姜珠姆”两种写法混用的现象。比如称呼为“写姜珠姆”的歌词:“……若不唱三次塔勒调,/写姜珠姆夫人不明白,/……”②1981:13.又如称呼为“森姜珠姆”的歌词:“若不了解夫人我,/在白岭国,六条山谷加上第七山麓,/第八是伟岸的黎明曙光崖,/第九是波浪翻腾的洁白海螺湖,/第十是雄伟庄严的虎峰宫,/在 (此)吉祥如意十全的院落中,/(我)是噶嘉洛 (部落的)森姜珠姆。”③同上,第27页。
那么,怎样理解这种转换呢?我们从该文本中对于水晶雪山的修饰中可见其端倪。“古代藏族谚语讲,/洁白雪山山边有两只健壮狮子,/那绿松石鬃毛的雄狮巡游雪山 (时),/另一只则守住洁白水晶凉亭。//”④同上,第76页。。另一首歌中:“绕转洁白水晶雪山边上时,/洁白雄狮独自绕转则美丽。//”⑤同上,第88页。从上述“洁白水晶凉亭”()和“洁白水晶雪山边”()可知,“水晶”一词是专门修饰雪山的,也可看作是“雪山”一词的专属名词性修饰词 (epithet)。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从“写姜珠毛”到“森姜珠姆”转变的原因了。实际上,这种转换中其含义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是更加确切而已。
此外,笔者认为《贵德分章本》汉译本中还有一处错误翻译,即将“家友七兄弟”译为“梵天之友 (或七梵友、梵天七友)”⑥王沂暖、华甲译:《格萨尔王传 (贵德分章本)》,第16、263页。。从笔者所掌握资料可知,“梵天七友”的说法,无论是藏族史诗还是佛教经典都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家友七兄弟”(或家友黑蛇)之说倒存在于传统藏族文化中。比如多罗那他的《后藏志》中,讲到岭国神祇时也提到了“家友黑毒蛇”[]的说法①1983:125.。而且,史诗中也多次提到了“家友七兄弟”②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藏:《英雄诞生 (化隆分章本,藏文长条)》,第63b页;Jamyang santen and Tashi.Hor gling bsdus pa.Delhi:Lakshmi press,1979:88.或“家友九兄弟”③青海文联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藏:《英雄诞生 (化隆分章本,藏文长条)》,第279b页。的说法。藏族民间传说中,认为进入家中之蛇是“龙神”,是保护家族兴旺之友,据此,可能将它们称为了“家友七兄弟”。唐代敦煌文献句道兴著《搜神记·刘安》中,也记载了挖出家中蛇 (赤物/龙)飞走而家道中落的故事④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编:《敦煌变文集 (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69页。,可作为这种传说风俗的旁证。尽管手抄本《格萨尔》中文字的规范并不严格,但在此处应该是“家友”()而非“梵友”()。
由上可见,《贵德分章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创编特点。虽然该抄本有“过分修订”的问题,但华甲艺人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作为一位艺人,华甲充分发挥了他的“阐释”与“创编”的能力与作用,并为《贵德分章本》这样一部文字古老的史诗的正确翻译提供了保证。
四、小 结
《贵德分章本》汉译文本较早以“片段”形式 [(1958年)在《青海湖》杂志连载]和内部征求意见稿形式 (1959年)与读者见面,慢慢被文化界所熟知。新时期,它被认为“较完整地”呈现了《格萨尔》史诗的全貌,加上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民间文化特色 (比如浓厚的神话色彩),多年来深受读者和研究者青睐。但实际上,从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格萨尔》史诗的一般情况来看,它并不具有该史诗的“典型性”,而仅仅是一种比较“古老”或者“边缘”的史诗形态而已。
但是,《贵德分章本》及其同属抄本系统,在《格萨尔》史诗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却是空前的。自这部史诗“被发现”以来,便以“欧洲第二部”《格萨尔》史诗和第一部藏文《格萨尔》史诗而得到世人的认可,其影响是深远的。同时,该同属抄本系统被全文或部分翻译为多种文字,如俄文、蒙古文、法文、日文,得到世界各国学者如石泰安、达木丁苏伦等人的重点介绍。当下,它还以绘画刺绣、影视作品等形式得到延伸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从该同属抄本系统“具有较早时期《格萨尔》史诗”的特点来看,它在早期《格萨尔》史诗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名称,在较早传入该史诗的其他民族中,被称为“格赛尔”或“格斯尔”。出现这种现象,过去大多认为是传入民族自身的语言与文化特点造成的。但是,通过该同属抄本系统中的诸多“错别字”可知,这或许与该词本身的多变性或不固定性有关。我们从化隆本、民和本和强曲本中可以看到,藏文(格萨尔)和(格赛尔、格斯尔)⑤实际上在藏语安多方言中,的发音基本上均近似 “格斯尔”;而 “格赛尔”一词在青海汉语方言中发音近似。“格萨尔”这种汉语书写,实际上是先有任乃强先生等人记录藏语康区方言的 “格萨、格沙”,后又有王沂暖先生等注重卫藏方言者,加上该词外语书写的汉译而造成的 “新词汇”或新音译。这两个词汇在行文过程中,“前后并不矛盾地”频繁出现。这表明,除了该文本是“真正”来自口头讲述的记录外,在书写者或抄录者眼中,这种“无法固定该名称”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此才出现了两种发音和两种记录的情况。这也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格萨尔”(或格赛尔、格斯尔)这一词汇最初可能就是个外来词,后来才被本地化了。当它与凯撒 (ke sar,or césar)联系在一起时 (比如8—9世纪的“大神通的凯撒噶”[①巴桑旺堆、罗布次仁编:《当许噶塘蚌巴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 (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9、176页 (影印原文献见第46页第11行)。],就表示“国王、狮鬘、狮子王、王中王”;而它与从莲花花蕊中化生的莲花生大师 ()联系在一起,则表示“莲花花蕊、慈悲、空性、菩萨和法王”。至于后来史诗本身将该词解释为“今天如此新突出拔群 (新立、新晋)”()②1981:272.,以及象雄语词汇与藏语词汇结合的“驱魔怙”()③1994:87.等,则如其另一常用名称“伏敌珍宝”(音译为诺布占堆)一样,明显是藏族民众本土化的传统思想与愿望的体现。
从《格萨尔》史诗在藏族内部传承情形来看,《贵德分章本》及其同属抄本系统也在其中承担着非同一般的“角色”。首先,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明显的下安多 (半农半牧区)史诗特征以外,更重要的是《强曲艺人分章本》所体现的卫藏文化与安多宗喀地区 (即河湟谷地)及河源闷摩黎山(花石峡地区)有密切联系的特征,不知与宗喀巴大师等沟通两地文化学者们的努力是否有关。这虽然仅仅是一种猜想,但该文本所具有的安多方言、卫藏敬语词汇、13—14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古词等,着实让人对这种猜想产生附会与遐想。另外,该文本所具有的典型下安多地区传承的史诗特征(如歌词短小、常常突破诗歌格律、故事化倾向鲜明等),也为我们深入比较康区和藏北传承的“正宗”《格萨尔》史诗提供了可能。或者说,《贵德分章本》及其同属抄本系统在故事类型和情节结构上反映的特征,也为划清安多本与康区本的分界提供了一种可能。
最后,从该“同属抄本系统”的几个抄本来讲,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同一个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统一且个性鲜明,既具有共性鲜明的“一般的歌”(a song)的特点,也具有各自特征的“特指的歌”(the song)的意义。因此,它们各自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有相互同属的特点。这就是目前这类“同属抄本系统”展示给我们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