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464窟首次重修年代再探
2022-02-24张丽卉
□张丽卉
考古资料显示,莫高窟第464 窟现存壁画为后期两次重修时所绘[1]108。从该窟两次所绘壁画相互叠压的层位关系来看,前室和甬道壁画位于后室壁画层之上,可知后室壁画绘制时间早于前室和甬道壁画,为首次重修时所绘。有关第464窟后室详细的考古信息及壁画内容,沙武田先生在其《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2]。关于第464窟首次重修的年代问题,因缺乏相关文献的明确记载,所以对其后室壁画艺术风格的研判就显得尤为重要。张大千先生认为该窟后室壁画属“西夏人画”[3]628。宿白先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亦认为该窟主室壁画为西夏遗迹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夏说为学界普遍接受。谢继胜、沙武田、王慧慧亦支持西夏说②,并从多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进一步得出该窟后室壁画绘于西夏前期和西夏中后期的不同观点。杨富学则对西夏说提出质疑,主张后室壁画应绘制于元代早期[4]。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对第464 窟首次重修的年代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在对该窟后室壁画和前室游人题记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前人所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故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后室壁画中所蕴含的“西夏元素”
1.后室壁画中出现的西夏人物形象
在后室所绘的20幅方格式屏风画中,每一幅均有2—4 个数量不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及其所着服饰,大多数并无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有一幅画面较为特殊,即南壁东侧下方第一幅方格画中所绘人物较其他画面有很大不同。此画面表现的是一位坐于方毯之上的上师及其侍从形象。上师头戴莲花帽,着右袒式袈裟,右手作说法印,正在讲经说法;其身后站一僧人,身着袈裟,僧人旁边为一小侍从,手持伞盖,二人作低声交谈状;上师的左手边还立一女性侍从,着圆领窄袖长衫,右肩搭有一长巾,双手置于胸前(图1)。

图1:第464窟后室南壁上师及其侍从[2]
谢继胜先生较早注意到了此幅画面中的上师像,他认为此上师所戴莲花帽样式与榆林窟及河西石窟所见西夏上师帽冠样式为西夏藏传绘画中流行的上师帽子样式,这种帽式最初来源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莲花帽,是西夏上师的典型帽冠[5]。沙武田认为画面中的上师形象、男女侍的发式和服饰均具有典型的西夏元素。他还特别注意到上师左手边女侍右肩上的装饰物在武威西郊西夏墓所出土木板画的男侍身上也有出现,且十分相似。[6]这种类似于长巾的装饰物在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中共出现两次,均出现在五女侍(图2)和五男侍(图3)木板画中最后一位侍从的左肩上。与前4 位侍从相比,最后一位男、女侍从均未持物。无独有偶,在俄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水月观音》麻布画右下角出现一头戴软脚幞头的西夏官员及侍从形象,在该侍从的左肩上也出现这种长巾(图4)[8]202。另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卷轴丝质画《玄武大帝》中也出现一位左肩披白色长巾的男性形象(图5)[8]247。

图2:武威西夏墓五女侍木板画[8]9

图3:武威西夏墓五男侍木板画[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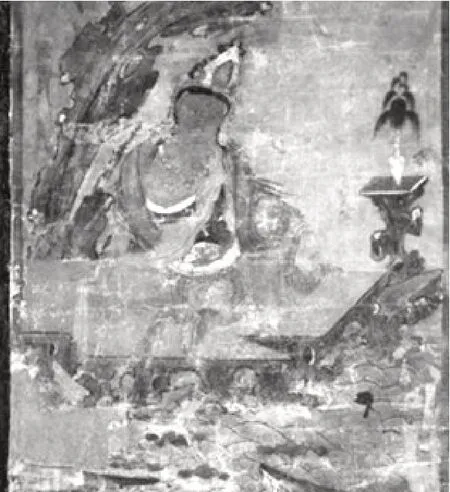
图4:西夏绢画《水月观音》[7]247

图5:西夏绢画《玄武大帝》[7]202
笔者发现在辽宋墓室壁画和唐宋辽金元绘画中,此类持物普遍置于侍者的手中,而在武威西夏墓和有关西夏绘画中,这种持物的位置发生变化,置于侍从肩上。此类长巾持物在西夏时期所绘人物肩上多次出现,而未见于其他时代,可认为具有明显的西夏时期特征。第464窟后室南壁绘画中女侍的长巾亦置于其肩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绘制时代指向西夏时期。
2.后室壁画绘画元素与莫高窟第465 窟壁画的一致性
谢继胜先生认为,第464 窟后室藻井所绘大日如来像颇具藏传绘画风格。谢先生经仔细比对发现该窟大日如来像背龛的卷草纹装饰、龛柱中央的珠宝装饰和龛柱外围的白色饰带,尤其是大日如来像外围所绘的花朵等细节,都可以在与第464 窟毗邻的第465 窟的西夏壁画内找到相对应的细节,从而认为第464窟和第465窟壁画属同一时代的作品[5]。笔者对两窟壁画进行比对发现,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第464 窟窟顶藻井所绘大日如来像的背龛装饰和其周围分布的花卉图案都可以在第465 窟的壁画中找到多处对应,两窟壁画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两窟壁画之间这些绘画细节的一致性显示,此壁画绘于同一时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并非是简单的对西夏绘画技法的传承。
除此之外,第464窟和第465窟窟顶均绘牡丹花卉纹,且绘画风格十分相似。第464 窟中出现的此类牡丹花卉纹并非只出现于壁画中心内容的边角装饰位置,也大面积地出现于后室窟顶四披所绘四方佛的周围。从整个装饰的视觉结构来看,卷草纹饰不是依附于圆形坐佛,不以装饰圆形坐佛为主,坐佛反而成为整个窟顶装饰的点缀,和卷草纹一并组成统一的视觉整体,形成了井然有序、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9]。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在整个敦煌石窟中并不多见,仅东千佛洞的部分西夏洞窟中有所表现,沙武田也认为,在佛周围出现大量花枝纹的绘画特征不仅多见于西夏时期的壁画中,还多见于黑水城的西夏时期唐卡绘画中,故可认为具有明显的西夏时代特征[2]。
牡丹花卉纹是西夏艺术品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在西夏瓷器中尤为多见,如宁夏博物馆藏褐釉剔刻花牡丹花梅瓶、宁夏海原文物管理所藏的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宁夏博物馆灵武磁窑堡出土的两件黑釉和一件褐釉四系瓷扁壶上均在扁壶腹部剔刻风格迥异的牡丹花纹等③。
除瓷器以外,西夏时期的壁画中也多见牡丹花卉纹样。最典型的是瓜州东千佛洞第2 窟,在该窟前甬道窟顶绘制凤凰图案,凤凰的周围杂饰各种花卉纹样,其中就有牡丹纹。另外在东千佛洞第2 窟后甬道水月观音画中也出现牡丹花纹。牡丹花纹在西夏艺术品中如此广泛地被使用,体现了西夏人对牡丹花的钟爱。[10]莫高窟第464 窟和第465 窟出现相同式样的牡丹花卉纹,再加上第464窟牡丹花卉纹样大量出现于佛周围的绘画特征与东千佛洞西夏洞窟的特征一致,均将其绘制年代进一步指向西夏时期。
二、前室两则汉文题记的年代指向
第464 窟前室现存的两则汉文游人刻画题记,对该窟首次重修年代判定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沙武田先生介绍,这两则游人题记分别位于第464 窟前室南北两壁的西侧,且均位于北朝多室禅窟的素壁上,首次重修时,被涂抹的白色粉层所覆盖[2]29。这些考古层位信息均说明题记书写于首次重修之前,故而,这两则题记的书写时间成为判定首次重修年代上限的重要参照。由此亦可知,首次改建并未敷设新的地仗层,而仅是在原多室禅窟的地仗层上涂白色粉层,否则这两则汉文题记今天是无缘得见的。
伯希和最早注意到这两则游人题记,此后不少学者均有关注并引以探讨。谢继胜和沙武田二位先生分别认为题记的书写时间在“西夏据有瓜州的前50年之内,大约是1032年至1072年,至迟到北宋末年”[5]和“西夏统治敦煌之前或早期阶段”[2]。笔者对此二说持不同看法,故在此作进一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两则汉文题记今局部已漫漶不清,相关文字释录主要有伯希和、敦煌研究院、梁尉英、沙武田四种,兹列于下。

第464窟前室汉文刻划题记录文

续表
通过仔细比对图版,上表中以沙武田文中给出的录文最为准确。关于题记中所出现的阆州(今四川省东北部)和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在宋时的归属问题,谢继胜、杨富学均认为二州在宋时同隶属成都府路,故将题记南壁中的“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补为“大宋成都府路合州赤水县”。笔者检核史料,上述复原难以成立。据南宋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记载:
(阆州)初隶西川路,开宝五年,分蜀为川、峡两路,阆隶西川。后隶利州路。咸平四年,分益、利、梓、夔四路,而阆隶利州路。中兴以来,隶利东路。绍兴十四年,郑刚中乞分利路为东、西路,阆隶东路。[12]5381
据上引文,阆州从未隶属于成都府路。故上述谢继胜和杨富学二位先生的复原是与史实不符的。关于南壁题记中合州的建置沿革,《舆地纪胜》中亦有详细记载:
国朝平蜀,乾德三年。仍为合州。分蜀为东、西川、峡路,而合隶峡路。及分川、峡为益、梓、利、夔四路,而合隶梓州路。咸平四年。[12]4811
诏梓州复称剑南东川,《图经》及《国朝会要》在元丰三年。升为潼川府,《国朝会要》云:“重和元年,剑南东川奏:昔元丰中,神宗皇帝正剑南东川之名,而监司移文尚以梓州为称,欲望睿断,依剑南西川例赐一府号。’诏梓州赐名潼川府。”以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国朝会要》在重和元年。[12]4617
据上引文,合州在北宋初隶属峡路和梓州路,梓州路在重和元年(1118)改称潼川府路。直至南宋灭亡,合州一直隶属于潼川府路[13]288。不难看出,合州也从未隶属于成都府路,且宋朝政区曾有多次调整,在合州先后隶属的峡路、梓州路和潼川府路中,唯有“潼川府路”可补南壁题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阙文,故沙武田先生复原为“潼川府路”无疑正确。不过,据上引《舆地纪胜》记载,潼川府路始置于北宋重和元年(1118),故题记书写时间只能在1118 年及其以后,以此看来,上述谢继胜和沙武田二位先生的判定难以成立。至于题记书写年代下限,谢继胜认为南宋时因吐蕃与金的阻隔,宋夏已不再接壤,且宋金之间战事连连,故四川阆中和合州人此时不大可能前往河西地区[6]71-72。确如谢继胜所言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事及金对西北边防的重视而在宋金边界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14],此时的南宋人要想前往河西确实很困难,但谢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他认为这两则游人题记“都是一波同乡游人所留”,并认为题记中的“宋师父”住在西凉府,而“杨师父”居住在沙州,是杨师父邀请住在西凉府的宋师父来沙州礼佛[7]。既然题记的书写者均居住在西夏境内,那就不能排除他们是重和元年(1118)以后自宋来西夏且因战争的爆发或其他原因而滞留在西夏境内宋人的可能性,所以这两则题记的书写下限目前还无法做出判断。是故,第464 窟后室壁画的绘制时间最早可上溯至1118年。根据刘玉权先生早年对莫高窟西夏洞窟的分期标准[15]312-316。1118 年属西夏中期,所以第464窟的首次重修年代当在西夏中晚期。
三、小 结
综上所述,莫高窟第464 窟首次重修所绘后室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绘画内容等确实具有明显的西夏时期艺术特征。通过对该窟前室壁面上遗存两则汉文游人刻画题记书写年代的进一步考察,可知其书写上限为1118 年,再根据考古层位信息可知该题记书写于首次重修之前,据此可判定第464窟首次重修年代当在1118年之后的西夏中晚期。
注释:
①参见宿白《敦煌七讲》未刊讲稿,敦煌文物研究李永宁、施萍婷、潘玉闪记录整理,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②参见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第2期;沙武田、李晓凤《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时代探析》,《敦煌学辑刊》2019第4期;王慧慧《莫高窟第464窟被盗史实及被盗壁画的学术价值——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20第4期。
②参见李进兴《尘封的文明——西夏瓷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