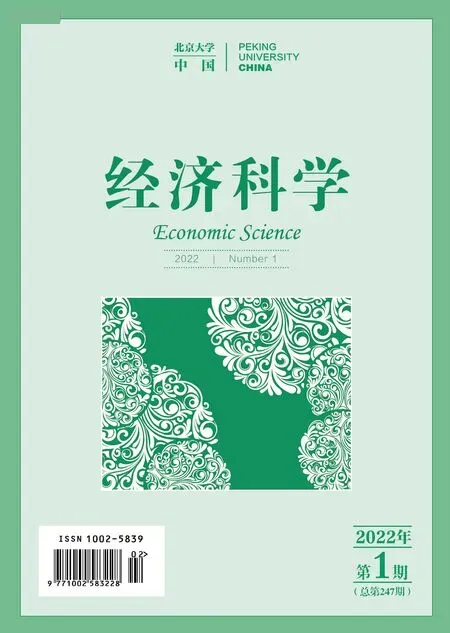企业杠杆率分化、资源错配与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2022-02-24谭小芬王雅琦李松楠
谭小芬 王雅琦 李松楠
(1.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北京 102206)
(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在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将“去杠杆”确定为五大经济工作任务之一。自此,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解决开始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结构,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做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根据BIS的统计数据,从2008年底到2017年初,我国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从93.9%迅速攀升至161%,远高于同期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水平;而后随着“去杠杆”工作的开展,这一统计数字到2019年末降低至149.3%。由此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水平确实曾呈现出过高且增长过快的态势。但钟宁桦等(2016)借助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的微观杠杆率(负债/资产)整体上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攀升,反而从1998年的65%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51%,这表明非金融企业整体并不是在加杠杆,而是在降杠杆。在此期间内显著加杠杆的企业主要为大型、国有、上市企业。但无论是个体数量还是总体规模,这些企业在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占比并不高。那么,既然微观个体企业的杠杆率整体上不断下降,为什么整个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却出现了攀升呢(见图1)?

图1 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与微观杠杆率的背离
我们认为,两者背离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定义相差一个“资产效益”(增加值/总资产) (纪敏等,2017)。宏微观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为:宏观杠杆率(总债务/增加值)=微观杠杆率(总债务/总资产)/资产效益(增加值/总资产)。因此,企业部门微观杠杆率下降的同时宏观杠杆率在飙升,是由于资产效益恶化的幅度超过了微观杠杆率的下降幅度。图1展示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与微观杠杆率的背离及资产效益的变化。可以看到,2004年之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下降是微观杠杆率下降与资产效益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2005年之后,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在微观杠杆率变动幅度很小的情形下,宏观杠杆率的飙升主要来源于企业部门资产效益的大幅滑坡。换句话说,相同规模的债务扩张带来的增加值越来越低,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导致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攀升。这与陆婷和余永定(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由于资本使用效率和企业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为了维持给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将持续增长而不会趋于稳定。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微观杠杆率在2005年之后基本平稳而整个部门资产效益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高效益企业杠杆率下降而低效益企业杠杆率保持平稳甚至上升。我们将所有企业按照资产收益率(ROA)在样本期间内的中值分为五组,发现在2004年后微观杠杆率出现上升的企业确实主要为低效益企业(见图2)。具体来说,对于ROA在20%分位数以下的企业,其微观杠杆率从2004年的65.98%上升到2013年的68.51%,而ROA在80%分位数以上的企业其微观杠杆率则从2004年的46.41%下降至2013年的38.98%。加杠杆的微观企业更多集中于效益较差的“坏企业”而不是高效益的“好企业”,这意味着金融资源投向出现错配。实体经济中的“好杠杆”下降而“坏杠杆”上升、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效益低的企业,降低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最终导致企业部门整体经济活动效率的下降。

图2 各ROA五分位企业杠杆率均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那么,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的背离,为何在次贷危机后愈演愈烈?我们在本文提出的解释为次贷危机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是指经济主体由于无法确切预知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经济政策而面临的不确定性(Gulen和Ion,2016)。为避免次贷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纷纷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而这种做法也提高了各国的EPU水平。EPU上升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抑制企业投资(Gulen和Ion,2016;Kim和Kung,2017;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影响企业的资产配置方式(王红建等,2014)。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也会受到宏观层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杠杆率往往会出现下降(Baum等,2009b;Baum等,2010)。
本文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EPU的视角探讨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化与资源错配。结果表明,在EPU上升时,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分化扩大,高效益企业的杠杆率降幅是低效益企业的3.06倍。进一步地,我们对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扩大的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充裕的现金流能够抑制高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下降,从而表明相较于避险能力差异,融资约束差异对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分化影响更大。随后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external financial dependence)和地区信贷环境两个维度的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差异的确是EPU上升导致高效益企业相较低效益企业杠杆率降幅更大的重要原因,且低效益企业的融资优势与国有所有制、抵押品相对较多和行业垄断程度较高有一定的关联。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的检验结果则表明,避险能力差异对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分化的影响比较有限。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结合了三类研究文献。第一类文献关注EPU对微观企业行为如投资活动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EPU的上升会抑制企业投资,且抑制效应在资本不可逆程度较高、沉没成本较高的行业中较强(Gulen和Ion,2016;Kim和Kung,2017;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这与实物期权理论(McDonald和Siegel,1986)相一致,即不确定性的上升能够提高投资的期权价值进而带来边际投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抑制企业投资。此外,EPU还会对企业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例如王红建等(2014)发现EPU上升会使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增加。
第二类文献就融资约束对微观企业决策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已有文献中有丰富的利用企业层面财务数据构建融资约束指标的方法(如KZ指数、WW指数等),但利用这些度量方式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Rajan和Zingales(1998)借助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刻画行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发现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且相对于金融不发达的市场,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的行业在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市场上增长更快。Manova等(2015)则采用了包括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在内的四个指标刻画行业的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vulnerability),并基于外资分支机构可以通过海外母公司进行内部融资这一事实,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中国的外资分支机构比内资企业有更好的出口表现,且这一优势在金融脆弱性高的行业里更明显。谢军和黄志忠(2014)则通过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证实了传统的融资约束理论,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
第三类文献结合融资约束研究了经济金融双轨制下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问题。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双轨制下,国有企业享有垄断优势,并有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因此资金筹集阻碍更小,而效率更高的私企则面临着更强的融资约束,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企(Song等,2011),已有诸多学者围绕国企所有制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展开了探讨(Huang等,2011;陆正飞等,2015)。此外,钟宁桦等(2016)从时间序列上考察了在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我国企业负债率的变化,发现从1998年至2013年,我国企业杠杆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融资约束较弱且缺乏硬预算约束的数千家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则显著加杠杆。申广军等(2018)关注增值税转型对非金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减税效应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负债率、降低了企业的短期负债率,且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内销企业中更为明显。纪洋等(2018)以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发现EPU的上升对私企杠杆率的降低和国企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影响,且金融市场化对于缓解私企的融资约束、改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杠杆率分化有积极作用。
本文将上述三个方向的文献结合,从EPU的视角探讨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化与资源错配。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以往研究中国企业杠杆率的文献大多采用上市公司数据(Huang等,2011;陆正飞等,2015;纪洋等,2018)或2007年及之前的工业企业数据(申广军等,2018)。上市公司普遍规模较大,能够使用的融资方式也较多样化,其面临的融资环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非上市企业的真实状况。另外,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问题在次贷危机以后更加突出。因此,我们采用1998—2013年(2010年除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既能克服上市公司样本缺乏代表性的不足,又能分析和检验2007年之后EPU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第二,与以往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文献相比,本文不仅研究了EPU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而且重点关注了EPU上升时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分化。不同于讨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的杠杆率背离涉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结构问题。这一结构问题直接关乎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最终对企业部门的资产效益乃至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因此相较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绝对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这一部门内部的杠杆率结构性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且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既然宏观杠杆率的高企并非由微观杠杆率的上升所致,而是与资产效益的下降、金融资源的错配有关,那么仅仅依靠减少债务总量绝不足以完成稳定宏观杠杆的目标。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高效益企业、淘汰低效产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结构,对于宏观杠杆率的稳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和供给体系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
第三,相较关注企业部门内部杠杆结构问题的文献,本文研究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视角更具一般性,在机制探讨和现象解释上的维度也更加全面。具体来说,针对企业部门内部的杠杆结构问题,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杠杆率差异(Huang等,2011;陆正飞等,2015;纪洋等,2018),并从银行信贷融资的所有制歧视角度(Johansson和Feng,2016;纪洋等,2018)对国有企业相较民营企业杠杆过高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则直接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更为一般地关注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分化问题,且在融资约束机制外,从企业风险规避的视角讨论了另一种可能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避险能力机制。此外,针对高效益企业面临的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我们发现除陆正飞等(2015)、Johansson和Feng(2016)、纪洋等(2018)所关注的所有制歧视外,抵押品和行业垄断程度差异也是高效益企业融资更难,进而导致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分化扩大的重要因素。
(二)理论机制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Myers和Majluf,1984),相较于低效益企业,高效益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现金流,用于投资的内部资金更充裕,因而对外部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小,负债比率相对更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EPU对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影响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首先,Acharya等(2007)表明,在企业避险需求较高时,企业以内部资金替代债务融资以规避风险的偏好会更强,而高效益企业盈利能力更强、内部资金更加充裕,因此可以在EPU上升时,以内部资金偿还债务、收缩资产负债表从而降低杠杆率、规避风险,低效益企业则由于内部资金不足以替代债务融资、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无法实现杠杆率的降低。EPU对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差异,是在两类企业都有避险需求的前提下,由两类企业内部资金充裕程度的差异所致。基于这一分析,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H1a。
H1a:(避险能力差异机制)EPU上升会导致高效益企业相对低效益企业更大幅度的杠杆率下降,且高效益企业现金流越充裕,其杠杆率降幅在EPU上升时越大。
考虑到中国经济双轨制的现实,高效益企业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也会使得EPU对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影响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竞争行业、抵押品较少的非国有企业,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往往规模更大、有更多的抵押资产,且通常可以获得政府的隐性担保(Song等,2011;纪洋等,2018;王彦超等,2020),因而在银行信贷融资上更有优势;但这些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经营效率相对低下(Hsieh和Klenow,2009;于良春和张伟,2010;Song等,2011)。而在EPU上升时,银行放贷的风险增加,因此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银行会更加谨慎(Baum等,2009a;Talavera等,2012)。当银行筛选贷款对象的标准更加严苛时,在缺乏政治关联或抵押担保的非国有企业中,只有资质更加优秀的企业才可能继续获得融资,维持现有的杠杆水平和资产负债规模。据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H1b。
H1b:(融资约束差异机制)EPU上升会导致高效益企业相对低效益企业更大幅度的杠杆率下降,且高效益企业现金流越充裕,其杠杆率降幅在EPU上升时越小。
在以上两种机制下,EPU上升均会导致高效益企业相对低效益企业更大幅度的杠杆率下降,但现金流充裕程度对EPU上升时高效益企业降杠杆的影响是相反的:如果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分化是由于两类企业避险能力的差异,那么现金流更加充裕的高效益企业杠杆下降的幅度会更大;反之,如果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分化是由两类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所致,那么现金流更加充裕的高效益企业杠杆率降幅会更小。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企业现金流充裕程度,通过观察EPU上升时现金流更充裕的高效益企业杠杆率的变动方向,识别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主导渠道。
进一步地,如果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变动的差异的确与企业主动风险规避有关,则可以预期企业所属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越低,EPU上升对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之间杠杆率分化的影响会越小。这是由于资本不可逆程度较低的行业内因投资失败所致的潜在损失较小,因此企业的避险意愿相应下降。若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变动的差异的确与融资环境的恶化有关,则可以预期企业所属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所在地区信贷环境越低迷,EPU上升对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之间杠杆率分化的影响会越强。这是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对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信贷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融资渠道和银行投放的信贷资金数量更加有限,使得高效益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加严重。据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说H2和H3。
H2:(避险能力差异机制)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越低,EPU上升对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影响越小。
H3:(融资约束差异机制)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地区信贷环境越低迷,EPU上升对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影响越大。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介绍
(一)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钟宁桦等(2016)、纪洋等(2018),本文构造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企业,表示年份。Lev为企业的杠杆率,EPU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ROA为高效益企业虚拟变量,若企业在样本期间内的中值高于所有企业中值的中位数,则ROA为1,否则为0。X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效益水平(ROA)、规模(Size)、有形资产占比(asset)、企业成长性(Growth)以及税率(rate)五个控制变量。GDP为实际的年度增速,用来反映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φ为企业固定效应,ε为回归残差项。之所以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特征变量与水平,是为了降低这些变量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回归系数中,是截距项;反映了的上升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我们预期该系数为负,即的上升会带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性下降;则反映了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在上升时杠杆率变动的差异。
(二)数据介绍
1.EPU指数
本文采用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EPU指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进行度量。该指数的构造运用的是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南华早报》()中每月探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文章数量占该报纸当月文章总数量的比重刻画该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实证检验中,为与企业层面的年度数据相匹配,我们以每年12个月度EPU指数的中位数作为该年度的EPU指数值,并对其进行标准化,用来衡量该年度的EPU水平。
2.企业层面变量
本文使用的企业层面数据来自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首先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样本缺省值、异常值的删选,进行的处理如下:(1)删除“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实收资本”、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产品销售收入”、“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本年应付工资额”小于等于零的观测值;(2)删除“出口交货值”、“长期负债”小于零的观测值;(3)删除“应收账款比例”、“有形资产净值比例”小于等于零或大于等于一的观测值。
鉴于2010年的企业数据质量可能存在问题(钟宁桦等,2016;谭语嫣等,2017),我们没有使用2010年的数据,因此最终得到了1998—2013年(不含2010年)由847722个企业、3 623 220个观测值组成的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此外,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使用到的企业层面变量进行了上下2.5%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在样本期间内,样本企业平均负债资产比率为55.98%,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7.16%,而负债最高的企业债务与资产比率高达109.06%、盈利能力最差的企业ROA低至-11.31%,表明部分企业在样本期间内出现过巨额亏损或资不抵债。

表1 关键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3.行业、地区层面变量
在检验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两种机制时,我们借鉴Kim和Kung(2017)、盛丹和王永进(2012)、谢军和黄志忠(2014)等的研究,通过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验证避险能力差异机制,借助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地区信贷环境检验融资约束差异机制。机制检验过程中涉及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变量的具体设定如下。
(1)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我们以Kim和Kung(2017)计算的行业资产再配置程度(asset redeployability,AR),作为资本不可逆程度的度量。对于某一行业而言,资产再配置程度越高,资本不可逆程度就越低。
(2)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借鉴盛丹和王永进(2012),我们采用各2位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自筹资金以外的资金来源在该年资金来源中的比重(_)度量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为消除数据波动的影响,我们计算了2003—2011年9年的平均值。
(3)地区信贷环境:借鉴谢军和黄志忠(2014),我们采用各省份各年度的信贷余额增速(_)衡量企业面临的信贷环境宽松程度。
四、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第(1)、(2)列所示,可以看到EPU的上升会带来企业杠杆率的降低,且高效益企业的杠杆率降幅更大。根据表2第(1)列的回归结果,EPU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企业杠杆率整体上会出现0.73%的下降。根据表2第(2)列的回归结果,EPU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低ROA企业杠杆率就会出现0.36%的下降,而高ROA企业的杠杆率降幅更是达到1.10%,约为低ROA企业杠杆率降幅的3.06倍。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所有企业的平均杠杆率水平从1998年的62.02%持续下降至2013年的52.21%,其中高ROA企业的平均杠杆率水平从1998年的54.41%持续下降至2013年的45.33%,因此EPU指数一个标准差的上升所带来的企业杠杆率整体上0.73%的降幅,相当于所有企业平均杠杆率在整个样本期间内降幅的7.44%,而EPU一个标准差的上升所带来的高ROA企业1.10%的杠杆率降幅,则相当于高ROA企业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杠杆率降幅的12.11%。以上结果表明,EPU上升对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影响不容小视。

表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① 稳健性检验的相关变量测度和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页面“附录与扩展”。
(1)控制经济因素不确定性的影响。除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外,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还面临着各个层面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为了说明EPU与企业面临的经济因素波动不相互重叠,我们进一步引入宏观、行业和地区层面经济因素不确定性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经济因素不确定性的干扰。在控制经济因素不确定性的影响后,EPU对企业杠杆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高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在EPU上升时降幅更大的结论仍然稳健。
(2)样本删选。在基准回归已剔除2010年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剔除2008—2009年的样本,以排除次贷危机期间工业企业数据统计质量可能存在问题的潜在影响。在剔除危机期间样本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仍然成立。
鉴于低效益企业样本中有一部分企业效益常年为负,我们根据企业ROA在样本期间的中值是否为负将其定义为负效益企业,并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后,再对基准回归的结论进行检验。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剔除“僵尸企业”样本,持续亏损是确认“僵尸企业”的重要标准之一(谭语嫣等,2017)。在剔除负效益企业样本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仍然成立,表明EPU上升时相较高效益企业而言杠杆率降幅较低的低效益企业并不仅仅是“僵尸企业”。结合引言所述,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扩大,意味着银行体系信贷资金投放的错配,这一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当EPU上升时,在流入“僵尸企业”的错配信贷之外,低效益的“非僵尸企业”与高效益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信贷错配。
(3)工具变量检验。尽管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层面的企业杠杆率不太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但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借鉴王义中和宋敏(2014),以美国的EPU指数作为中国EPU指数的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表明,EPU对企业杠杆率整体上存在负向影响,且高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降幅更大的结论比较稳健。
(三)机制检验:避险能力差异与融资约束差异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EPU上升会导致高效益企业相对低效益企业更大幅度的杠杆率下降。结合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在计量模型(1)中引入现金流充裕程度()变量,以识别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的主导渠道。根据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EPU、高效益企业、现金流充裕程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更充裕的现金流能够抑制高效益企业相对低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下降。这与待检验假说H1b相一致,说明相较于避险能力差异,融资约束差异对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分化影响更大。
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融资约束差异在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扩大中的重要性,但并未体现避险能力差异影响的大小。因此,我们借鉴Kim和Kung(2017)的研究,通过行业资本不可逆程度对避险能力差异在EPU上升导致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扩大中的效应进行检验。在表2第(4)列的回归中,EPU、高效益企业、行业资产再配置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说明资本不可逆程度越低,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分化程度越小。这与待检验假说H2相一致,但这一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整体而言,避险能力差异在EPU上升导致不同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扩大中的效应比较有限。
表2第(5)、(6)列则借鉴盛丹和王永进(2012)、谢军和黄志忠(2014)等的研究,通过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地区信贷环境,对融资约束差异在EPU上升导致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分化扩大中的效应进行了识别。EPU、高效益企业、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EPU、高效益企业、地区信贷环境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EPU上升时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分化,在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地区信贷环境较差时更加明显。表2第(5)、(6)列的实证结果整体上与待检验假说H3相一致,即融资约束差异是EPU上升导致高效益企业相较低效益企业杠杆率降幅更大的重要原因。
(四)高效益企业的融资约束来源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融资约束差异对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分化的重要影响。但是,如理论机制部分所述,以上结论成立还有一个前提,即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关于高效益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的潜在原因,我们从所有制、抵押品和行业垄断程度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1.所有制
我们首先从所有制的角度,对高效益企业是否面临着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一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所有制变量()与企业效益()显著负相关;表3中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在所有制分布上的差异也表明,相较于低效益企业,高效益企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占比更高(Hsieh和Klenow,2009;Song等,2011)。此外,我们还在基准回归中引入了EPU与国有企业的交互项,从表4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看,EPU与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从而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的降幅更大。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往往更加严重(Song等,2011;纪洋等,2018)。结合表3和表4的实证结果整体来看,所有制歧视可能是高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融资约束更严重,以致杠杆率降幅更大的原因之一。

表3 不同效益企业的所有制、抵押品与行业垄断差异

表4 高效益企业的融资约束来源:所有制、抵押品与行业垄断
由于无法获得银行对单个企业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的数据,我们进一步借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债券发行利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EPU上升时融资约束的变化差异进行分析。图3显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债券发行利率以及EPU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短期债券还是中长期债券,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发行利率都在EPU上升时出现了大幅的飙升:在数据期间内EPU水平最低的时期,民营企业的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仅比国有企业高出0.72%,而在数据期间内EPU水平最高的时期,这一融资利率差额达到了1.94%,这表明在EPU上升时,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变得更困难。

图3 EPU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利率差额
2.抵押品
除所有制歧视外,我们发现高效益企业和低效益企业拥有的抵押品差异,也可能是高效益企业融资约束更严重的原因之一:通过表3可以看到,低效益企业相较高效益企业拥有更多的抵押品;通过表4第(2)列我们发现,抵押品多的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降幅更小。在EPU上升时,银行放贷的风险增加,因此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银行会更加谨慎(Baum等,2009a;Talavera等,2012)。据此,低效益企业可以凭借更多的抵押品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而高效益企业抵押品不足,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从而出现高效益企业与低效益企业杠杆率的背离。
3.行业垄断程度
不同效益企业的行业垄断程度差异,也可能是高效益企业融资约束更严重的来源之一。通过表3可以看到,相对于高效益企业,低效益企业的行业垄断程度更高。通过表4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降幅更小。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垄断行业,垄断行业的经营效率往往更低但在外部资金获取上存在优势(于良春和张伟,2010;王彦超等,2020)。因此,高效益企业相较低效益企业面临的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也可能与不同效益企业的行业垄断差异有关。
基于表3、图3和表4第(1)—(3)列的结果,我们发现高效益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可能与所有制、抵押品和行业垄断程度三个因素有关。那么,除这三个因素外,高效益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是否还有其他解释?我们作了进一步分析。在表4第(4)列中,我们发现在同时控制EPU和所有制、EPU和抵押品,以及EPU和行业垄断程度的交互项之后,EPU和高效益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从而表明除所有制、抵押品和行业垄断程度三个因素外,高效益企业面临的更严重的融资约束可能还有其他解释。至于其他导致不同效益企业在EPU上升时杠杆率分化加剧的原因,可留待未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了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化与资源错配,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分化扩大,高效益企业的杠杆率降幅是低效益企业的3.06倍。第二,避险能力差异对不同效益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杠杆率分化的影响比较有限。第三,融资约束差异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高效益企业相较低效益企业杠杆率降幅更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相较于低效益企业,高效益企业中非国有企业、非垄断企业更多,且抵押品比例更低,因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其融资环境相对恶化;另一方面,当高效益企业的现金流更加充裕、所属行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较低、所在地区信贷环境较为宽松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企业杠杆率分化会缩小。
以上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第一,由于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恶化高效益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因此要尽量避免经济政策频繁、大幅调整,保持经济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降低信贷资源错配的程度。第二,在以去杠杆为目标进行宏观调控时,应注意不同效益企业的融资约束差异,避免“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否则金融资源在紧缩期间更多地流向低效益企业,会造成资产效益的下降和宏观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第三,不同效益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的杠杆率分化扩大与融资约束密不可分,因此应当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第四,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高企与不同效益企业的杠杆率分化和资源错配紧密相关,因此应当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思路,努力减少低效益企业的债务,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优质的企业。这就要求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体系质量,从而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