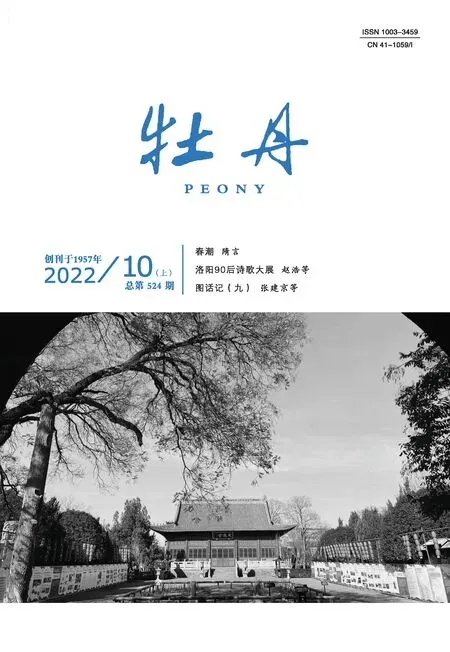加缪《局外人》的传播符号学理论解读
2022-02-23王姗姗
王姗姗
一
传播符号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它用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人类的传播方式,阐释传播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虽然什么是“符号”的问题,复杂难辨,但赵毅衡先生给出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他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之,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尽管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仍然处在不断丰富完善的初期,但作为起始于语言学的符号学,在文化多媒体、全球化传播的语境下,其解读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生成和价值认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阐释力不断彰显。
《局外人》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加缪,于1942 年创作的作品,作品也为加缪赢得了崇高的赞誉。在今天多媒体跨文化传播环境下,研究界公认,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认知。作品显示出作者、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各种根本性问题的伟大思考。《局外人》也被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
加缪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描绘的场景,是充满意味的形式,是可以广泛解读、具有巨大阐释空间的文化传播符号。这些文化传播符号使《局外人》作为欧洲大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今天仍然在全球传播。作品不单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上,给读者和作者深刻地启迪,在社会学、哲学上也引导读者反思社会人生。小说中的人物符号有默尔索、默尔索的母亲、葬礼上的宾客、默尔索的女友玛丽、邻居雷蒙、雷蒙的情妇、默尔索的老板、雷蒙的“对头”、预审法官、检察官等共10个。场景符号有:葬礼上、法庭上、行刑前的夜晚等3个。
二
这13个符号彼此关联,编织了一个故事,组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认为的荒谬世界,这个世界里,人生是痛苦的。《局外人》塑造了一个面对母亲去世表现平淡、面对陌生人的死亡毫无怜悯的主人公默尔索形象。默尔索面对亲人和周围环境都是一种疏离、不带情感的注视的态度。默尔索用枪打死朋友的仇人,并不是因为死者和朋友有仇,而是当天的太阳太过刺眼。杀人的理由如此轻率,令人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存在的人,他也有着对死亡的本能害怕,和对生的本能渴望。但是在庭审过程中,他又无法讲述出能帮助减刑的理由,也无法解释杀人过程中,他为何先开一枪,停顿之后又连开四枪。因为无法给荒谬的行为一个恰当的理由,而坚持真实的荒谬动机,这样正是加缪精神的高度体现:反抗荒谬,无论是用真实,还是用荒谬本身。加缪在《局外人》的后记中阐释了默尔索的真实:“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的内心被一股坚韧不拔而意蕴深厚的激情驱使,驱使他追求一种‘绝对’和‘真实’。”
主人公默尔索在面对母亲去世以及下葬的过程中,有一系列异于常人的表现。例如养老院的院长问他是否想在盖棺前再看母亲一眼,他直接回答不。作者将默尔索拒绝的过程简略到连一句完整的对话都不必要被呈现。在默尔索回答之后,加缪也没有对院长听到回答后的反应加以任何描述,但院长在默尔索的庭审中就此事给出了关于默尔索的“判断”。这种“无理感”的真实,不仅得益于加缪在故事中将人物的真实与荒唐塑造地如此对立又和谐,同时也因为加缪深厚的文学功底:用第一人称来交代主人公视野中的信息缺失与错位,更进一步体现出默尔索对世界的感知上的隔离与疏远。在同一件事情上,当院长的反应并不能与他产生实际联结时,默尔索便不“感知”它;当院长的判断影响到法院对默尔索的判决时,默尔索便“听到了”院长对他的看法——冷漠无情,于是默尔索被判处死刑。
现实中人们用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一些所谓的普遍的大众的理由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约定俗成。这并不意味着拥有这些表现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情感是不真实的,只是这样会将不表现的人放在这种社会性规律的对立面,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非常规的“真实”味。
这种消极感同样体现在默尔索对待周围人的“要求”的“无拒绝”。无论是默尔索的女朋友玛丽说要和他结婚,还是邻居雷蒙说要和他成为朋友,他都不考虑、不反对,也不拒绝。后来玛丽问他是否爱自己,默尔索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并承认不爱她,但也没有因此拒绝和玛丽结婚。雷蒙在委托默尔索写完给雷蒙女友的恐吓信之后,才表示默尔索是他“真正的朋友”。默尔索“没有理由拒绝”帮忙写信,同时对交朋友又感到无所谓。但他并不是主动想要做这些事情,也不是被迫接受这些事情,而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他也无法预测自己的“无理由”行为在日后会成为审判他的主要证据。
在《局外人》的故事中,主人公是通过一个个行为的选择,导向了一种有罪审判。默尔索拒绝临死之前对着天主教神父忏悔,不仅是因为他对周遭以及自己的杀人行为感到厌烦,还有着他对自己的行为的“负责”。他“不习惯”自己的罪犯身份,是因为他感受不到法律和道德的审判,但是他在判决之后还是放弃了上诉。加缪笔下的默尔索有罪吗?当然有罪,因为他确实杀了人。默尔索真的冷漠到没有人心的基本反应吗?在法官问他爱不爱自己的母亲时,他回答“爱,和所有人一样。”他跟法官解释“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在母亲的葬礼上,疲惫和困乏使默尔索的情感反应迟缓,但是他也能肯定“我更希望妈妈没有死”。基于真实的回答和人们看到的他的反应,是“不统一”的,但是这能证明他不爱自己的母亲吗?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看到,默尔索关于母亲和玛丽的美好回忆,是因为我们从默尔索内心的视角来看他,但是他身边的人只能从外部观察他。
三
作为荒诞文学的巅峰,最荒诞的地方在于,默尔索被判处死刑的过程,不是用法律审判,而是用道德良心来判处他的死刑。这里的荒诞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主流价值之外的东西,除了杀死,别无他途。世界的荒诞之处就在于,所有一切,就像是一场滑稽的喜剧。世界只是存在,并不管人的理想和价值、希望及意义。荒诞的是人对世界的期望和世界本身不会按照这种方式存在的对立。加缪的《局外人》展现出一个无法解释因果、充满矛盾与和谐共存状态的世界。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物形象符号是突然有一天变成了虫子了的“我”。“我”以肉体变异的形式与周身的世界隔绝,但还保留着人的思想和情感。当某天意识到作为实感存在的人和情感都远离和拒绝他时,“我”便突然的死去了。卡夫卡的作品里,主人公面对荒谬世界的态度是忍耐和走向死亡。从“我”这个符号中,解读出的自我压抑,某种程度上,与存在主义核心观点所提倡的对人感性的尊重是相违背的。而加缪的《局外人》则倾向于反抗,倾向于以个人的真实回应世界的荒谬。这就是我们解读13 个符号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主要意义。
传播符号学的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考,并展开对传播人类生存价值的现实关切。我们以符号学理论,解读《局外人》这13个符号的意义生成,表达对共同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基础上的整体正义,替代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这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基本原则。由此,传播符号学形成了富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新兴学科,它关注大众文化建设,研究传媒时代意义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规律。使具有存在主义浓厚色彩的《局外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生成新的解决现实文化困境的当前价值。
符号具有象征性和隐喻特征,加缪的“局外人”是一个可以全球化传播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表征着: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对自己荒诞的审判,最后才能以“局外人”的姿态超越荒诞。由此《局外人》产生了穿越时空的、震撼人心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