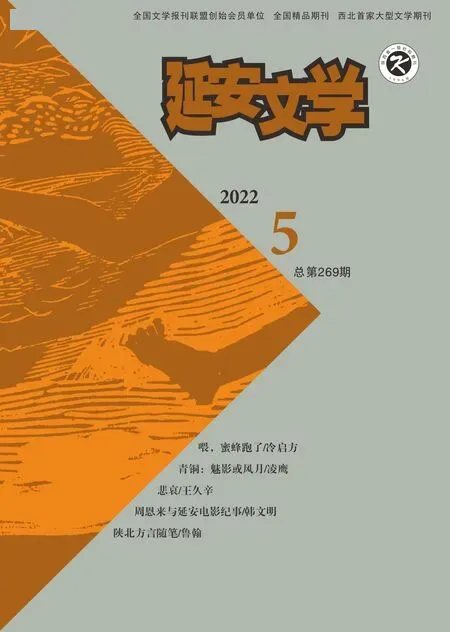余烬
2022-02-23胡静
胡 静
她踩着渐渐变冷的阳光从办公室回到家里,鞋也不换走进卧室,“啪嗒”扭转门锁,把自己关了起来。人在遭受身心重创后往往如此。葬礼未结束,她的眼泪就流干了,脸色发青,双腿发软,神思恍惚,听不清别人说的什么。哪些人来了,哪些人离开了,她也无心顾及。人到中年,她已懂得,人天性喜欢圆满和幸福,讨厌苦难和灾祸。面对深陷痛苦或者不幸中的人,绝大部分人唯恐避之不及,生怕遭遇同样的厄运。她虽然相信有些人是真心替她难受,但在她经受的痛苦面前,再动听的语言都显得苍白和廉价。那些人许是明白这一点,说话时期期艾艾,欲言又止,仿佛喉咙卡了一根鱼刺,讷讷几句,就找个借口走开,边走边轻抚胸口,暗暗嘘出一口长气。她不想见任何人,听任何话,她只想静静地,没有任何人打扰地待着,没有发现家里除了小狗欢欢,并无其他活物。
房子是小高层,贪图五楼的大平台,她不顾十字路口商住两用楼的喧嚣,说服丈夫买了下来。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有了私家小花园的气象。沿着墙根摆放着一排多肉,其间间杂种着玫瑰、风雨兰、鸡冠花这样的花卉。靠近墙角的葡萄架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秋千。儿子练习吹笛时喜欢坐在上面。眼下花事凋零,深秋的露水浮在上面,像一枚枚小小的、泛着泪光的眼眸。
她的卧室正对着小花园,刚擦黑的天色一片灰蒙。卧室在暮色的湖水里晃晃悠悠地摇动,突兀响起的手机铃声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枯草。儿子离开后,她的电话老是没电。有电时,电话响了,又常常懒得接。偶尔接了,也不明白对方说的啥。主动联系她的人已经寥若晨星。她任由铃声响到自己挂断。亮光熄灭的刹那,她看见手机屏幕上自己松弛的面容,鼻翼至嘴角有两根明显的纹路,抿嘴时更深了。
她起身揿亮台灯,双手塞在大腿形成的缝隙里,愣愣地看着窗玻璃上愈加暗沉的天空。未被秋风扫尽的蚊蝇飞过来,她没有伸手驱赶,放任长针般的蝇嘴深刺进裸露的肌肤,体内升起一种被虐的快感。
一夜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梦,与她的痛苦全不相干。第二天早晨,她走出卧室,走进黑沉沉的封闭楼道里,感应灯在脚步声和开门声的双重冲击下发出灰白的光亮。保洁刚拖过地,水迹闪着冰冷的反光。电梯按键亮了许久才停留在她站立的楼层。电梯走走停停,铝合金梯箱面板映照着进出电梯的身影。出口处下行两级台阶是人行道,石青色的地砖像公园的甬道。卖鸡蛋、柑子、白菜、萝卜、野蘑菇、麻糖的商贩把货物盛在篮子、背篼、塑料布上、小推车里,沿着人行道一字儿摆开,把对面的银行,连同这栋高大的楼房包围在里面。银行方便老残者取钱修建的坡道上,一个卖小葱的老太太抱着篮子坐在入口处,取钱的人经过时得把身子偏向一边。经过一个春夏的生长,利剪修剪过的行道树又探出了人行道。深绿的枝叶浓密得像要掉下来,落在行人的肩头。
她赤脚套着一双白色的平跟软皮鞋,身着棉布圆领灰色长裙,沿着右边的人行道缓缓前行。这条路通向上面的另一个商场,也通向那间沿河而建的学校。两旁有不少早点铺,赶着上班上学的人已经在铺子里坐下,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大快朵颐,乳白的水汽如同云雾掠过耳际。她奇怪自己还活着,还能嗅闻到早点铺里酥肉绿豆粉的香气,还能捕捉到端碗站在人行道上吃豆花面的男人脖子上鼓起的青筋,还能感知到河风如同钉子往骨头里钻。她甚至注意到树荫上面的天空阴得能挤出水,其间栽种的桂花树余香未消。再往前一点,便是学校的大门,是不锈钢材料做的伸缩门,偶尔有车辆进出,才像钢刀入鞘一样徐徐缩回去。她在门前停住了脚步。此时正在上课,校园里空无一人,远处的教学楼里隐隐传来读书声。她看着闪着寒光的铁门缓缓打开又缓缓合上,又伤心,又不解。这个门前的夜晚历历在目。晚自习结束的铃声拉响,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鱼贯而出。灯光微弱得如同夜的叹息。儿子挤在一大群孩子中间,她还是准确地找到了。突然疯长的身体像被巨手野蛮拔高的稻秧,不到十四岁就一米八五,与身高不成比例的脸尖得像几何课用的三角板。看见她,儿子远远招了下手,加快脚步,用永远消失的声音喊着妈妈向她跑来。母子俩一高一矮并排着,随着人流向前移动。没有家长接的男孩三五成群,儿子丢下她蹿过去,和男孩们勾肩搭背。她索性放慢脚步,放任儿子走远。直到儿子掉头蹿回来接她。刚走近,经过的同学扬声喊他的名字,又打闹着跑远了。从偶尔听到的片言只语中,她了解到他们正在组建乐团,谁弹钢琴,谁吹笛子,谁弹吉他,谁做歌手。儿子自告奋勇担任吹笛手,钥匙刚从锁孔里拔出来,就催促她在淘宝上下单买长笛。在这之前,儿子只学习过葫芦丝。吹笛子和吹葫芦丝是两回事。葫芦丝是包吹法,吹出来的气息全部进入乐器内,不管怎么吹,都是一样的发音,简单易学。笛子需要控制嘴形和舌头,两者的变化控制声音的变化。儿子的舌头在口腔里“吐噜”一个多月,笛子才慢慢出声。儿子移动手指,流畅地吹出花舌音,屋子里热闹得像养了一窝小鸟。谁也想不到,儿子会突然离去。她抱着小棺材走进设在郊区的公墓,葬进了一块墓地。小小的棺材似乎带走了儿子的整整一生。
一片冷寂,只有在深秋迷蒙凄冷的日子里才有的冷寂。她缓缓掉转身子,沿着来时的方向逆行,身后的水泥地留下一串沉闷的脚步声。远山空蒙,树木挂着寒霜,又斑斓得令人惊奇。她离开学校,经过寺庙和农田,来到一块临近河边的林地上。林地是农田改的,栽种着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水柏杨。落叶如同一床金色的地毯铺在上面,靠近河边的地方稀薄些,有几片随着河水缓缓地荡漾。河对岸有几户农家。她矮下身子,缓缓蹲坐在落叶上。山背后传来车辆行驶的声音,喇叭声沉沉地传向远方。雾气笼罩的河水前方,缓缓爬上高坡的太阳虚弱得只剩一个浅浅的灰白影子,像炉火燃烧后的余烬。
午后,她打开“花小猪”叫车软件,叫了一辆快车去墓地。白色的大众在沥青道路上驶行,发出“嚓嚓”的声音。横逸而出的枝条像轻轻地哀泣擦过车窗。蒙蒙秋雨似乎给群山蒙上了一层白纱。她在墓前坐了小半天,用枯瘦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黑色墓碑上镶着金边的名字,一如抚着那张消失了的小脸,回家后感到一阵魂魄丢失了的空虚,好像刚才在墓地里反而比家里离儿子更远。这是因为在家里,儿子手扶长笛启唇吹奏的笛声仍然回荡在屋子里。
黄昏时分,一阵心脏被揪紧的感觉袭来,她起身去推儿子卧室的门。门带着一声嘶哑的闷吼声打开了。卧室窗子朝北,吹进来的风挟带着寒冬的凛冽。她没有觉得冷,还听到了一个变声期的嗓子喊妈妈的声音。她移步进屋,仿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巴掌拍击的声响。她伸手揿开门侧的开关,青白的灯光照亮了房间,叠得整整齐齐的榻榻米显得如此陌生。她枯瘦的身影投射在右侧的墙壁上。她看见身影伸出一条胳膊,停在墙边的书柜上。书柜里摆放着书,还有闹钟、水杯,和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有的贴着书本放着,有的放在书架的边缘……
这个房间既是儿子的卧室,也兼作书房。书桌临窗摆放。随风飘进来的雨粒溅落在书桌上闪着珍珠跌落的光亮。她扯纸巾擦拭,用力过猛,不小心刮破了手指。她关了灯,疼痛的感觉没有消失,窗外的茫茫夜色侵占了整个房间。她感觉喘不过气来,再次揿开台灯,柔和的光线重新照亮房间,圆圆的灯帽映在窗玻璃上,她顶着一头乱发的脸凸显出来。
她坐在空无一物的书桌前,空洞的目光从纹路深显的额头上抬起,打量屋里的陈设:席梦思对面的壁架上,从左到右摆放着长长短短的乐器,一张特意裱糊的名师书法条幅悬挂在最上面。突然间,她的脸俯向书桌,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先是将嘴唇贴在被雨粒打湿的冰冷桌面上,随后又将泪水浸湿的脸颊贴上去,双手紧紧抓着书桌靠近窗户的两个角。
她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几个小物件,几块用了一半的橡皮擦,一叠没有做完的卷子,一个音乐盒。音乐盒里面放着一张乐谱,这是儿子准备排练后在学校体艺节上表演的节目。乐谱抄在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字迹稚拙,像刚学步的孩子歪歪倒倒的足迹。临离开的头几天,儿子还在苦恼自己肺活量小,无法流畅地吹奏出乐谱里的滑音,央求她买哑铃。临近中考,她担心影响学习,答应考试后再买,还许诺给他请笛子老师。抽屉里还发现一支废弃的黑色短笛,套在一只袋口系着松紧绳的布套里,一根绳子被她抽出来系了装黄豆的袋子。
她伸手拂拭乐器表面的尘灰,身子越弯越低,眼泪滴落在上面,发出雨打枯叶的声响。乐器架上不但摆放着长长短短的笛子,还摆放着儿子喜爱的一些小东西:土黄的葫芦丝、像琵琶一样的口琴……就是在这间屋里,在书桌前的那把椅子上,她的儿子曾经练习过乐器。儿子最先学会的是葫芦丝。那时还在上小学,吹的是《喜洋洋》这类欢快而活泼的曲子。儿子喜欢坐在花园的秋千架上,晃荡着小短腿练习。曲调断续、刺耳,爷爷奶奶却觉得比电视上那些著名的音乐家还吹得好。儿子是她和丈夫婚后五年才出生的。儿子未出生前,公婆以为她不生,经常找她的茬子,还让丈夫和她离婚。儿子出生后,态度才转变了。她和丈夫吵架,还会训斥丈夫。她也没有了恋爱时的小性子,对丈夫的要求降到了最低。半夜打麻将回来,记得给两娘母带份夜宵,哪怕是两元钱一份的卤豆腐干,她都会开心得像买二十元的彩票中了三十元的大奖。
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她搬出闲置的茶具陪在儿子旁边,习惯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丈夫也把客厅的躺椅搬出来靠在她身边。有时候,还会朗诵两句篡改的顾城诗歌:儿子在秋千下吹他的笛子/老婆在花丛里烫她的杯子/我躺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她笑得捏不稳手中的茶杯,溅落的茶水洇湿了白色的茶服。上中学后,葫芦丝换成了笛子。儿子习惯躲在自己的屋子练习。拗不过爷爷奶奶的请求到花园里,吹奏时懒心懒肠的,欢乐的曲调听起来也蕴含着淡淡的忧伤。她坐在客厅里,隔着厚厚的墙壁,听着会突然纳闷:十四岁的孩子哪来的这些愁绪?儿子脸色苍白,不思茶饭时,她一点也没想到是得了那种要命的病,觉得是笛子曲调太幽咽,好好的男孩谁会像女孩一样弱不禁风,威胁要把乐器当柴烧了。此刻,距笛声最后一次响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烟蓝色的夜空薄云密布,月亮偶尔才露出真容。冷冽清辉中的楼房在大地上投下沉沉的暗影,花园里的花木像敷了一层薄霜,时不时像冰碴一般闪烁。
她刚走出卧室,手机忽然发出急促的呼叫声。已经许久没有人联系她了。就连曾经说过要过一辈子的丈夫,也再未主动打过一个电话。烧七时,家人、亲戚们都帮着翻找儿子用过的东西,卧室、客厅、花园里,甚至走廊上都有儿子骑过的小童车。他们把这些东西聚集到一起,说是烧给儿子,免得他在另一个世界寂寞。爷爷奶奶也把相片脸朝下扑在桌子上,劝她趁着年轻赶快备胎。突然消失的身影好像不是一个人,不是他们口口声声的心肝,而是一件损坏的物品,比如车坏了,电视机、洗衣机坏了,扔掉或者处理给收旧货的,清扫干净遗留的痕迹后,再购进一个。她拼命护着,才保留了原样。
手机一连响了三次。第三次,她才慢腾腾放下包裹,摸出手机,扔到旁边的沙发上。她两眼通红,一边脸颊上还贴着湿漉漉的短发。
她把儿子的东西收集起来,放在了一个大口袋里——有短笛、长箫,葫芦丝,擦拭笛子的软布,断了的琴弦,儿子戴过的表,玩过的篮球,还有藏蓝色的平板电脑。她撸起衣袖,拿起手表戴在左手腕上。她抬起手腕,把表贴近耳朵,指针轻轻的走动声如同鼓点敲击着耳膜,一缕熟悉的体香钻进她的鼻翼。她放下衣袖,拿起平板电脑,长按开机键,发现电早就消耗殆尽了。她在茶几下面的抽屉里找到充电线,插上电源片刻后重按开机键,天蓝色的屏幕下端出现一个输入框,下面有一串小字提示输入密码。她输入自己的生日,锁就开了。屏幕封面是一个在夜空中静坐的少年。少年坐在夜色一般墨黑的草地上,双腿略略弓起,尖尖的脸对着夜空,眼睛在长长的额发间闪着微光,看上去忧伤又神秘。她漫无目的地划动手指,无意中点开了桌面上的文件夹。文件夹存满了视频和相片,都是儿子的身影,坐着的,站着的,微笑的,吃东西,在台上表演的,在家中小院演奏长笛的,有小跑着前行跑远的背影……平板电脑是儿子学习吹笛子时买的。笛子吹奏的布谷鸟叫设置成了闹铃。黎明刚刚刷白浅蓝色的玻璃窗,布谷鸟的叫声响了起来。儿子开门起床洗漱,直到客厅大门打开,又重重关上,布谷鸟的叫声才慢慢消失。她看着那个已经消失的身影屏息许久,眼泪重新溢满了眼眶。泪眼模糊中,手指双击点开了一个文档:
“明天去贵阳参赛,以后我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参加更多的比赛……”
“今天周末,天气晴好。我在院子里练习笛子。妈妈端茶具泡茶,爸爸躺在葡萄架上晒太阳。爸爸周末难得没去打麻将。”
“放暑假了,几个同学约我打篮球。本来不想去的,听说她也要去,我才答应了。从中午打到下午,都没有看见她……”
她抬起头,脑壳飞速旋转起来,儿子有喜欢的姑娘了?
“又去学校打篮球,”她继续往下看,“我举球投篮的时候,她沿着球场外侧的跑道走了过来,眼神朝着我站的位置,我确定她也喜欢我。”
“是谁家的女孩呢?”她喃喃地说,“他离开的最后一刻想念过她吗?”
她机械地移动着手指,贪婪地阅读着这些如同呓语一样的片段……
“今天新买了一支长笛。前天,听说她转学的消息后,就一直没有看见她。她可能已经走了,我们还未曾说过话。别了,我的宝贝,不知道哪天才能再见!”
儿子才读九年级,临走的前几天还问我要钱买棒棒糖。她用拳头重重地搓揉着太阳穴,竭力思索。
儿子是在和谁说话呢?长时间不滑动,屏幕已经暗了。她重新点亮屏幕,试着在电脑里找到蛛丝马迹。她点开QQ,自动登录上去,一连串新消息蹦了出来。她点开对话框,发现是自动推送的广告。聊天记录是空的,显然是怕她偷看,启用了清空聊天记录的退出模式。她试着点开好友栏,发现每个孩子的空间都上了锁,不是要求输入生日、星座,就是问自己最爱的人是谁。她进入儿子的QQ 空间,发现只有一些幼时的相片,相片发黄,分辨率也不高,还是她极力说服儿子上传的。每次,儿子都不以为然。他窥破了她想借此窥伺他内心隐秘的想法。
她站起身,摇摇头,再一次控制住悲痛欲绝的哭声。
“我……的胸口……好疼……”她抽抽咽咽地说道,“我……的胸口……好疼……”
“今天是我的生日,”她突然想起来,“我却要死了。从儿子离开那一刻,我就死了……”
她抽出一张纸巾覆盖在脸上,瞬即就被浸出来的泪水打湿了。她一连换了几张纸巾,一张脸被搓得红红的,纸巾也被搓成一个一个小小的纸团,扔在地上。
“……等等我!”她轻轻说道,好像身边有人转身离去。
一辆车子驶过远处的高架桥,桥上的灯光透过落地玻璃射过来,把屋子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阴影。平板电脑屏幕暗了下去,横放在桌子上,如同关闭了蕴藏的所有秘密。她双目紧闭,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似乎幽冥中有股力量裹挟着她匆匆向前,不容拒绝。她的悲伤显得无力,显得自找苦吃,一切努力都是虚空,无法避免那场注定的噩运。
她站起来走向阳台,手扶在栏杆上,俯身看着下面的万家灯火,手机又响了,听起来像命运的嘲讽。她刚刚伸手掐掉,短信铃声“叮叮”响起:
“黄女士你好,祝你生日快乐,你的礼物正在朝你飞奔而来!”
是同名的吧?她明确表达不想再生的意愿后,公公看她的样子像看灭门的仇人。婆婆也不再隐藏心里的不满,细小到炖排骨时,萝卜是斜切,还是切成细长块,香葱切长了、短了,都成为斥责她的理由。刚刚恋爱时,婆婆也嫌她矮,嫌她的工作不在体制内。第一次登门时,婆婆正眼也不看她。她在那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的鼓励下,小心翼翼地喊了声阿姨,婆婆勉强答应时,鼻毛从鼻孔里冲了出来。知道她要去婆家,母亲买了五百多元的礼物,婆婆给的进门红包不值这个价就罢了,居然还有零头:333 元。母亲和姨妈们说333是快散的意思,让她趁早死了心,她还强辩说自己嫁的是丈夫,又不是婆婆。丈夫那时也是真爱她。婆婆说娘矬矬一窝,担心未来的孙子。他说自己就喜欢娇小玲珑,盈盈一握刚好。婆婆嫌她不在体制内,他说夫妻俩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刚好,说明咱里外都有人。婚后的第二天,婆婆就把厨房交给了她。从来不下厨房的丈夫还特意拴上花围腰打下手。花围腰是婆婆特意给她买的。时逢炎夏,一米八的丈夫赤膊挂上像穿了个肚兜,滑稽的样子逗得婆婆忍俊不禁。儿子出生后,婆婆开始搭把手,丈夫恢复了大少爷的本性,偶尔进厨房剥几颗蒜都像立了大功。儿子的死像冬天熄灭的炉子,微弱的暖意瞬即被寒气吸没了。公公婆婆怪她没带好儿子。丈夫也整天沉溺于喝酒、打牌。偶尔,她和丈夫的眼神对上,厌恶和憎恨像混凝土里突兀伸出的钢筋,戳得她胸口疼。这次来之前,丈夫就在电话里让她离开时,把钥匙放回客厅的博古架上。双亲早已逝去,其他的亲人也像海水退潮后的沙滩,形同陌路。一定是送错了。那个人恰好姓黄,手机号码和自己只相差一个数字,或者顺序颠倒,错输成了她的。她关掉手机,扔回沙发,慢慢走到阳台上,一条腿刚跨上栏杆,门铃响了。
门铃连接着下面的大门,来客在铁门右边的按键面板上输入楼层号,主人家按开门键即可进来。常常有人按错了房间号,她看见头像不是熟人,也会热心地帮忙打开。今天,她不想理会,也没心情理会。她静静地听着门铃声,等待铃声自动消失。铃声重复响了起来,急促的声音听起来像一根绳索,要把她拽离阳台。她松开抓住栏杆的手,返身回到客厅,拉开茶几抽屉,在里面找到一把扳手,“咣”地砸碎了显示屏。门铃声消失了,屋里平静了几分钟,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指骨敲击在铁皮门上发出的声音似乎比门铃更刺耳,她甚至能够听见来客的呼吸声。她不想理会。敲门声仍然固执地响着,似乎她不开门,就会不顾一切破门而入。身体里的悲伤冲上头顶,她掉头冲到门前,握住门把手“咣”地向外推去。有硬物撞击在铁门上发出“怦”的一声巨响。紧接着,过道墙壁上又传来撞击的声响。一个身着美团服装的小伙子一手扶门,一手揉着后脑勺,从门和墙壁合力形成的缝隙里挤了出来。
她刚要厉声质问,一大束粉白的百合花递了过来,鹅黄色的花蕊在她胸前的布料上印下了一些黄色的圆点。
“这是谁的花?”
“你的!”
谁送的?
美团快递念出那个已经刻在黑色墓碑上的描金名字时,她接过花束,把脸埋在上面泣不成声。
就在此刻,只听见突如其来的一声响,一声细细的,如同风扇启动的声音,也像是长夜里黎明到来的脚步声。她抬起头,暗下去的笔记本屏幕突然亮了起来,代表着时针和分针的两根小细线闪闪地跳动,笛声响了出来,像布谷声,也像蛙鸣。就在她以为要断了的时候,又响了起来。叫声是从平板电脑里传出来的,原因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人为它接通了电源。电流如同温热的血液穿透冷冰冰的外壳输送至里面的元件,喊醒了原来设置的闹钟程序。它一直静静地待在那儿,一旦感受到电流,便迅速地启动起来。
一直默不出声的欢欢似乎听到了小主人的召唤,吠叫着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立……欢欢用狗鼻子顶着篮球滚动的时候,她的视线已经模糊成了雨夜的门帘:儿子喊着妈妈走了过来,坐着的,站着的,微笑的,背着书包的,弯腰换鞋的,在卧室的乐器架前,在花园的秋千架下。儿子擦拭乐器的时候像检阅心爱的军队,有的哈一下气,有的试一下音,有的还会吹上一小段……她伸手去拥抱,却发现怀里的是欢欢,看见眼泪如碎玉般滑过她的脸颊,便伸长狗舌轻轻舔舐。
欢欢是儿子三岁时从亲戚家抱养的。她小时候有被狗追着咬的经历,对于狗不但不喜欢,还一直心怀戒备,远远看见就设法避开,家里养狗自然是一万个反对。儿子抱着欢欢眼泪汪汪地乞求,公婆帮着说情,并承诺给狗洗澡,保持洁净,才留了下来。几年过去,儿子和欢欢好得俨如一人。
欢欢显然知道她不喜欢它,像所有为了所爱忍气吞声、低声下气的人,待在她规定的距离外,尽可能小心翼翼地讨好她。她心血来潮扬声呼喊时,亦会乖乖跑过去蹲在她面前,耸动着小鼻翼乖巧地看着她。在儿子的引导下,欢欢学会了许多小技艺:用狗头顶球,举着前爪行走……她去超市给儿子购物时,会顺便给欢欢买一袋狗粮。
公婆其实也不喜欢养狗,嫌欢欢乱跑,嫌春天换季时狗毛落得一个屋子都是,只是因为孙子喜欢,唠叨几句忍了。儿子出事后,残羹剩汁就算倒进下水道也不愿给欢欢,更别提买专门的狗粮了。
许是知道小主人离开后,家里再无自己的容身之地,儿子下葬那天,欢欢莫名其妙失踪了。大家都以为它另外寻觅新主人了。她去墓地时,发现欢欢守在墓前,看着墓碑上儿子的相片一动不动。她抱起欢欢,发现眼睑下面的狗毛黏结成了一团,像深夜里反复痛哭的人眼角凝结的泪痕。
第二天天明,她把儿子的遗物堆放在儿子墓前,取出打火机点燃时,欢欢咬着她的衣袖不松口。人和狗僵持至暮色降临,欢欢才流着狗泪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墓地归来后,欢欢一直跟在她的身边,像晚自习时,蹿远了又倒回来找她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