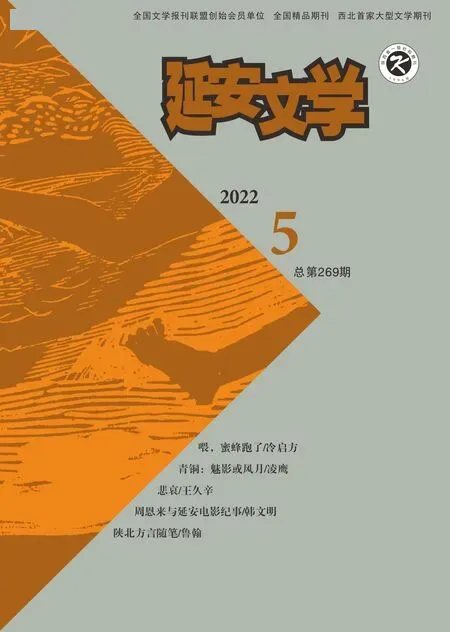卡夫卡的等待
2022-02-23刘晶辉
刘晶辉
1
此刻,小说家卡夫卡正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
由于疫情原因,他被隔离在家已经两周了。
他感觉自己生理、心理上所承受的孤独和煎熬,都已经达到了极点。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想立刻出门,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离群索居的人。但当他出门的权利被暂时、合法地剥夺后,他便觉得痛苦起来。他对于隔离的心甘情愿的配合态度,让这份痛苦变得更加痛苦,因为这注定只能他一个人默默承受。
临窗的这条小街上,每天都有很多人。这些人走了,那些人来了,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街道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但只要这条街不是完全封闭的状态,人们还是会来。有的人戴口罩,有的人连口罩也不戴。所有人都在忙着逛街,即便卡夫卡一整天都望着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卡夫卡。老人有老人的事情,女人有女人的事情,男人有男人的事情,孩子有孩子的事情。这让卡夫卡觉得惬意和安宁。反之,哪怕有一只苍蝇从几十公里以外毫无恶意地盯着卡夫卡看,他也会立刻感觉到,从而立刻关上窗户。
这段时间,忧伤而敏感的卡夫卡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
这个问题对别人来说,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对卡夫卡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卡夫卡的父亲从来不会理解卡夫卡,哪怕是一丁点的理解,都没有。而卡夫卡从来没有想过试着反抗,因为他在内心里深深地崇拜着他的父亲,这是他痛苦的根源。叙述到这里,卡夫卡面对的问题可以进一步修正为:
要不要去见自己的父亲?该不该去见自己的父亲?
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在卡夫卡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仅仅是因为告诉了父亲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父亲就冷酷地判决他跳河而死。结尾,主人公迅速而果断地执行了父亲的这个命令,就像一个士兵执行将军的命令那样,毫不怀疑,毫不迟疑。
父亲的权威高高在上,不容置疑,不可侵犯。在小说里是这样,现实中也一定是这样。
卡夫卡之所以会产生去见父亲的念头,完全是因为他被隔离了。他害怕隔离的时间太久会出现什么意外,万一父亲突然离去,自己不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吗?虽然那只是一瞬间的念头,但他觉得这种不幸变为现实的可能还是有的。思念的藤蔓,悄无声息地从脚掌爬到他的心房,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它牢牢地控制住了。他正是在自己以为不会想念父亲的时候开始想念父亲的。
他的父亲也被隔离了。当然,是隔离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我们知道,疫情期间,这种事总是常常发生的,一点也不奇怪,对不对?对于经常外出做生意的父亲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不过了。难道,你指望他老老实实地在家陪着卡夫卡研究该死的文学和小说?
按照相关的防疫政策,这种隔离不会是永久的,一般是十四天左右,没有问题就会恢复自由。就是说,他不必急着要求立刻见到父亲,因为他早晚可以见到。何必着急在这一刻?话虽如此,但敏感的卡夫卡还是感觉到不安。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说《地洞》中说的那样:
每一粒沙子的去处,我都要弄清楚,不然,我就不放心。
卡夫卡的不安来自何处?来自他对父亲的恐惧和想念,这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我相信这个并不难理解,就像爱情那样,越觉得难以掌控,就越想掌控,越想接触。一个人伤害了你,但你却总想着接近他。
2
但接近父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卡夫卡,我们试想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个场景是很可能发生的):
父亲和儿子的隔离都已经结束。两个人见面了,卡夫卡激动地上前,给了父亲一个拥抱。他父亲呢,总是一门心思忙生意,从来不知道儿子忙活的文学是什么玩意。父亲拒绝了卡夫卡的拥抱,并且冷冷地说:走开,弗兰兹!我还有事。这几天隔离,让我耽误了很多生意上的事。
卡夫卡在内心里用最饱满最热情的口吻对他的父亲说:我爱你,父亲。但是他嘴上说不出来,他父亲也不会允许他说。
被拒绝后,他会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自己的父亲,以免被父亲继续嫌弃,以免惹他生更大的气。在那天的深夜,他无法入睡。当他蜷缩在床的一角,披上被子,抱紧自己,回味着白天发生的那一幕的时候,他仍然,眼含热泪,浑身发抖,像一只卑微的、饥饿的夜鼠。但他对命运是感恩的,因为毕竟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只看一眼,对卡夫卡来说就已经足够。
但他连被拒绝的机会都没有。越是没有机会,他就越想他的父亲。
防疫人员对他很好,为他送来了各种吃的,甚至还有贴心的咖啡。他不由得想到,父亲呢?父亲那边的防疫人员会对父亲很好吗?他相信会,但他没有亲眼看到,他不敢确定。父亲平时喜欢喝两口小酒,他们会满足父亲的需求吗?他不敢想。
他的内心,涌起一丝对父亲的怜悯之心。是的,父亲对卡夫卡并不好,但他一样是他的父亲,不管怎么说,父亲岁数大了,他应该享受一个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喝点酒,抽点烟,如果他觉得快乐,那就抽点,喝点吧。当然,他也曾劝说父亲戒烟,但他知道,那是残忍的,他不想剥夺父亲最后的快乐。父亲他不会上网,不会玩智能手机,他想抽烟,就让他抽吧——
天哪!
我究竟是在说卡夫卡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该死的跑题!在短篇小说寸土寸金的地方,不应该,真的不应该。我检讨自己,但我想说,刚才,我真的想我父亲了,就是这样。
继续卡夫卡的故事,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
卡夫卡吃完了饭。
他再次忧心忡忡地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街道和行人。眼前的一切和夕阳结合起来,真是一副完美的画,让卡夫卡无法不注意到它的美。他的身体无法外出,那就让眼睛自由地徜徉吧。其实,即便是眼睛,也不能说多么自由,因为它所能看到的,也只有窗外的这一点风景而已。不过,现在防疫形势特殊,这样已经很奢侈了。
街道,行人。卡夫卡喃喃自语,街道和行人是如何美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呢?如果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街道是孤独的。如果把行人放在其它地方,放在一个屋子里,放在海滩上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他就不再是“街道上的行人”。街道和行人似乎不可分割,自己和父亲呢?也不可分割。
对,不可分割。
窗外的景色可以缓解他的心情,但是他不知道究竟是他在望着窗外,还是窗外的人在望着他?你觉得外面的行人是你的风景,但你错了,他们其实不完全是。他们作为整体是,但他们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不是。因为,你不会特别关注某一个人。他们不会时刻都让你觉得放松和舒适。当他们所有人都抬起头,注视着窗边的你的时候,当他们像你的父亲那样,对你投来好奇、怀疑、打量的眼神的时候,你立刻会变得坐立不安。
这几天,卡夫卡的思绪很乱。他不停地想很多事情,和他父亲有关的,无关的,但不管他想什么事情,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他的父亲。他绝对配合疫情期间的管理政策,他觉得隔离是有用的,是必要的,但他就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3
在被隔离的最初的几天里,卡夫卡并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永远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他觉得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几天而已,就可以出来了。但随着被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想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两天,他通过刷手机上的软件,刷到这样的一条新闻:
一名男子的父亲在男子被隔离期间去世了,由于被隔离,他未能参加父亲的葬礼。于是,当父亲的灵车经过酒店的时候,男子对着灵车跪下,号啕大哭。
这是一条感人的新闻。这样的新闻,曝出来的是一条,但并不意味着只发生了一件。就像你小时候,考完试回家,你考得很差,推门而入,你父亲随口问你这次考得怎么样。你故作轻松地说,还可以,题比上次难了点。但其实你考得很差。
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疫情牺牲了很多,值得我们为他们点赞——
你一定看穿了笔者的阴谋:卡夫卡就是笔者自己!
你会说,笔者假装在讲卡夫卡,其实他携带了很多私货,他在讲自己的故事!如果你这样说,那笔者深感惭愧,因为我真的是想为大家讲一讲卡夫卡的故事。
对于在小说里加入其它的叙述线,笔者深感不安。在笔者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北京的疫情又严重了。刚才,就在刚才,我一点也不骗你。今天是五月四号,我们依然要做核酸。我看到微信弹出来好几条信息。有一条是和我们紧密相关的,那就是我们公司附近的地铁封站了,十里河地铁封站,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平时那样去上班。你可能会说,你可以在附近的地铁站下车,但问题是,连着好几站,都封闭了。这意味着公司附近的疫情很严重,如果我们“冒死”赶过去,是不是一种危险行为呢?前几天我父亲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只是简单聊了几句,但我的内心却起了波澜。说实话,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我经常想着假期出去玩,结果我都回家了。到家里干农活,被催婚,得到了不美好的体验,但我又不能真的不回。但现在,我真的回不去了。过年我也没回去,有些人可能两年没回家了。我开始想家,真正的想家。但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思念,不然它会让我崩溃。诚然,我们不是卡夫卡,但我们可能在某一方面,和卡夫卡很像,我们的内心,也是孤独的。像我一样的,也许有很多人。这是笔者创作这篇小说的缘由。笔者如此深爱自己的父亲,笔者也是如此深爱卡夫卡,所以当两者产生奇妙的碰撞的时候,笔者的叙述也不得不在卡夫卡和自身之间摇摆。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知道。没有终点的等待是最可怕的,三年?五年?我相信只要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期限,所有人都会愿意等。国家在尽力控制,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们要做的,只有等待。笔者又一次想到卡夫卡,他在等待什么?如果他和笔者一样,被隔离,他的内心会怎么想?我们一起来接近这位文学大师吧。
卡夫卡的内心是极其封闭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在他封闭的终点,到底是什么?
4
卡夫卡试图通过研究其它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夜幕降临,街道上的人逐渐变少。很少有人研究过,街道上的人,是怎么变少的,但这几天里,卡夫卡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且颇有心得。
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街道上的人,不是一点一点变少的,街道上的人是一下子变少——甚至消失的。这是一种心理感受。
诚然,从事实的角度,街道上的人的确是一点一点变少的。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你现在站在窗边,一直凝视着街道上的行人,多一个,少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少了一个人,少了两个人,甚至少了十个人,你根本不会察觉到。因为少的人被从其它地方过来的人补位了。街上的人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恒定的数量。
但如果你在做其它事,不是一直盯着窗外看,比如,你下午睡了一会,一直到五点才醒来。你揉揉眼睛,去窗边看,你发现,哎呀,少了这么多人!如果你非常贪睡,睡到晚上八点,你再去看窗外,你会更加吃惊,因为没人了。
卡夫卡继续研究,还得出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街道上的人其实一直在增加。我说的是总人数。来过这条街的人,只能越来越多。比如说,这条街道是著名景点,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每天都不重复。来过这条街道的人,越来越多,但你在一个凄清的夜晚,看到街上没人,只是一个现象,不是它的本质。明天,它又会人满为患。
对,我差点就要说南锣鼓巷的名字了,北京的南锣鼓巷!但,我要控制,毕竟,咱们在聊卡夫卡。咱们应该聊布拉格。布拉格和北京很远,但是布拉格和北京真的很远吗?也许只是物理上的远?您说呢?笔者一定要克制!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在撕扯我,它不让我顺利完成我的叙述。我只想说,如果我们都对疫情有所感知,期待它早点结束,那么我的文章您应该继续阅读下去。
继续卡夫卡。
他想出去。
不管研究什么,他最后都得出一个荒诞的结论。只有父亲是真实的,可以感知的。他甚至感觉父亲就在眼前了。
他必须出去。
5
怎么出去?他能成功出去吗?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虽然可能性很低,但卡夫卡还是一遍一遍地在想这件事。
小区里有很严格的管控,基本上出不去。按照卡夫卡的性格,他不会硬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最可能做的,就是和防疫人员耐心地解释。他不是会写小说吗,他就按照他写小说的思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假如他和他爹距离很近,他能成功去看他爹一眼吗?卡夫卡在心里盘算这件事,盘算怎么和防疫工作者去聊。他想了一个比较好的版本:
你看,他说,你们都看那个新闻了吧?对,就是那个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新闻。对。看了吧?什么,这位同志没看?我给你讲讲。简单说,对,长话短说,就是一个男人,因为隔离,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你说,可惜不可惜?咱就说,一个人都不能孝顺自己的父母,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自己亲人病重的时候,他就得守在自己的亲人身旁,不然,他活着还有啥意思?哎呀,这位同志,你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有自己的职责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看看,隔离了这么多天,也没事吧?该做的措施,都做了,核酸也做了好几遍,对不对?结果是什么呢?阴性。你得让我看看我爹,是不是。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没人性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政府肯定有政府的难处。但是我知道了,我老爹,距离我不远,就在那个楼,对面,你让我上去,和老爷子说句话,行不?就一句。隔着防盗门,我看老爷子一眼,行不行?哎呀,你们就说,都戴着口罩呢,能出什么事?就你,是五号楼的吧,都是街坊邻居,你说,我卡夫卡平时对你们怎么样?对呀,都不错,你让我去看一眼。您受累,让我看一眼我爹,我亲爹,行不行?哎呀,我心里真是想他。那什么,我这里有烟,你抽一根呀!来,接着。哎呀,你看你这人,不抽的话,你给我拿进来呀,别踢远。你这位同志呀……
不行,谈不拢。肯定谈不拢,人家也不可能因私废公。一声叹息。
这一顿饭,卡夫卡没有吃。
他是被饿醒的,但他看到桌子上的冷饭,他没有要吃的欲望。但肚子确实很饿。没办法,吃吧。
他很快吃完了这些饭。他起身,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望着外面漆黑的夜。一阵冷风吹进来,他打了一个激灵,但他没有像以前一样,马上关上,而是继续望着窗外的世界。
空荡荡的街道,一个人也没有。
他试着回忆白天看到的街道上的那些人,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特征。不是具体的长相,那个肯定记不清。只是一些特别容易被人记住的特点。比如,哪个女孩穿的衣服很性感呀,哪个摊位跟前有很多人呀,哪个孩子当街拉屎呀,等等。只要能想到一点,他就很高兴,仿佛他和白天热闹的街道还有些联系。
但他想了半天,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
6
夜里,在睡梦中,卡夫卡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父亲的公寓。他终于要与自己亲爱的父亲见面了。
上楼,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他站在了父亲的门前。敲门,过了一会,门开了。
父亲。
他往里面望了一眼,屋里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无法想象父亲在这样幽暗的房间里,每天是怎么度过的。
他想进去,但父亲拦住了他,他不让卡夫卡进门。父亲开始用严厉的口吻责怪他,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隔离?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吗?不要提该死的朵拉了,那个女人,根本不配做我们卡夫卡家的媳妇,我不同意。
父亲的话越来越多,口吻也越来越严厉。卡夫卡觉得下起了雨,是室内下起了雨,而不是室外。雨水冲刷着他的身体,把他全身都淋湿了。他不愿意离开,他就那样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父亲,仿佛他以后永远无法再见到父亲那样。恐惧和爱,同时占据他的身心,他有多么害怕他的父亲,他就有多爱他的父亲。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父亲啪地一声,关上了门。
犹如一声炸雷,他被惊醒了。
他想,如果每天都可以在梦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7
第二天醒来,外面阳光明媚,天气仿佛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可怜的卡夫卡已经痛苦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他决定不再去想关于父亲的问题。就让他安安静静地欣赏这条街道吧。
饭菜在正午温暖阳光的照射下,仍然慢慢变凉,卡夫卡觉得,并不是饭菜的温度在逐渐降低,而是他的体温在逐渐降低。他的体温在逐渐消失。
看到了吧,读者朋友们,这仍然是一篇小说,不是回忆录或者记叙性质的散文!卡夫卡要解脱了,笔者也要跟着他一起解脱了!有些耐心,继续往下看!笔者再不结束这篇小说,就会永远迷失在其中。
继续卡夫卡。
一切,真的太痛苦了,昨晚的一切,真的太难忘了!尽管,那只是梦。梦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它总暗示你,生活中有特别的事情,就要发生。父亲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机器,又或者是一座山,单纯父亲这两个字,就压得他喘不过来气。如果他再想这两个字,那么父亲似乎就能从他的意念中来到现实,把他掐死,他给了他生命,所以他有权利夺走它。
整条街道,好像都被静音了,他什么也听不到。他越是命令自己不去想他父亲,就越是忍不住去想。
继续看这条可爱的街道吧!
一个小男孩正在缠着父亲买一串糖葫芦。小男孩的父亲人很好,立刻停下来,要买。但是小男孩很调皮,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串他不满意,比划着要换一串。只好又换一串。但是小男孩还是不满意。其实从卡夫卡的角度,看过去,他觉得这串糖葫芦已经很完美了,色泽、大小都很好。他不知道小男孩为什么一直要换。换呀换。又换了好几串,小男孩还是不满意。最后卖糖葫芦的大爷也不高兴了,不知道他究竟要吃哪一串。大爷以为他们是来找茬的。最后当爹的实在忍不住,给了他儿子一巴掌,打的屁股,很明显力气不大。但他儿子仍然立刻哭了起来。
这一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小男孩也很怕自己的父亲,但他就是想调皮捣蛋,似乎这样做能获得和父亲的深度互动。他父亲在前面走,小男孩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当然,他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最后的那串,他没有要求再更换,不然还得挨打。卡夫卡哈哈大笑,笑出了声。那个父亲猛地回头,他好像听到了,这一回头,把卡夫卡吓了一跳。这个人和他的父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一模一样。
父亲!
父亲!
所有的梦魇要变为现实了。
卡夫卡大感惊骇。难道父亲要骂自己了?但他没做错什么呀。他鼓足勇气,和那个男人对视,好像在说,来呀,你看你能够得着我吗?男人似乎听到了卡夫卡的心声,他嘴角轻轻地翘起来,张开两只手臂,像鸟一样上下扇动。他竟然飞起来了。他微笑着,朝着卡夫卡的方向飞过来。街上的人看到有一个人飞起来了,纷纷抬头观望。然后又有一个人像那个男人一样,也扑棱棱飞起身,朝着卡夫卡的窗户快速袭来。卡夫卡定睛一看,这个人也长着一张和父亲一模一样的脸。危险。
卡夫卡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猛地关紧窗户。再打开,他发现男人还是男人,不再像鸟一样飞了。
无处可躲。卡夫卡选择和街道上的人对视。对视就是对抗。卡夫卡决定反抗。
他们看着卡夫卡,他们所有人看着卡夫卡。父亲?是你吗?卡夫卡忍不住问出了声。很快有一个人回答,是的,我是你的父亲。卡夫卡瞬间热泪盈眶。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自己的父亲。但很快第二个人也开始说,我也是你的父亲,亲爱的弗兰兹。第二个人是一个女人,她怎么会是自己的父亲呢?卡夫卡觉得这真是搞笑。他把脑袋伸出窗外更多一些,让半个身子也探出去,大声吼道:滚开!那个女人就开始捂着嘴笑,很快,她消失在了人群里。卡夫卡看不见她了,又开始找刚才回答自己的那个人,那个“父亲”。但那个男人不见了。卡夫卡变得紧张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的视线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扫来扫去,希望可以重新找到刚才那个男人。没有找到。卡夫卡沮丧地低下头,等他再次抬起头,准备关上窗户的时候,他忽然又看见了刚才那个“父亲”。父亲!卡夫卡大声叫着。对方也热情地回应卡夫卡。但卡夫卡很快就发现,那个人和刚才那个“父亲”,模样不一样。天哪!究竟哪个才是自己的父亲?卡夫卡努力和对方沟通,他问对方,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父亲?对方说是,他说出了卡夫卡小时候的生活习惯作为佐证,这下卡夫卡放心了。对方说,你爱你的父亲吗?卡夫卡说爱。对方说,那快来拥抱你的父亲吧。卡夫卡把窗户打开到最大,打算迎接自己的父亲。男人开始缓缓朝卡夫卡走来。他不是在平地走,而是直接在空中走,一步一步接近卡夫卡的窗户。但更加诡异的是,他身后,整条街的人都在跟着他。
弗兰兹!我爱你!
弗兰兹!父亲爱你!
弗兰兹,我们都爱你!
卡夫卡急忙关紧窗户,但已经晚了。整条街的人像鸟扑棱着翅膀一样,挥动自己的双臂,朝着卡夫卡冲了过来。
他们温柔可亲,他们来势汹汹。
他们笑容可掬,他们笑里藏刀。
卡夫卡无所适从,不知道逃往何处。如果现在逃到外面,那等于是自投罗网。他决定在屋里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虽然不一定有用,但眼下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窗户啪啦啪啦地响,外面好像刮着八级大风一样。相信一会,窗户就会被窗外那一群“父亲”攻破。
卡夫卡相信,即便父亲见到自己,也不一定会在行动上对自己做出什么伤害。但是在语言上,父亲一定会把他批得体无完肤。父亲的语言会像洪水一样把他淹没,父亲会看着他在水里挣扎而不为所动。他喜欢的女人,他喜欢的文学,在父亲的眼里,都是狗屁。一个人说,还不够吗?窗外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说一遍,那简直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
他转过身去,用后背抵挡这一切。他像一个不被认可的小丑演员,默默承受观众因为愤怒丢来的苹果、番茄和鸡蛋,还有无穷无尽的谩骂。他能感觉到,番茄和鸡蛋的汁液从他的脸上慢慢地流下来,一直流进自己的心里。
他特别想让自己后背变得坚硬一些,坚硬一些,再坚硬一些,那就可以更好地抵抗所有的一切。可眼下,屋子里,除了一个发黄的老式衣柜,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先钻进去吧,钻进去,关上门。柜子门应该比他自己的身体要坚硬。这个柜子里面也有把手,他可以在里面拉紧,不让外面的父亲们闯进来。
他站在衣柜前,不忘整理一下自己的衣领。他要为一会的“战斗”做最后的准备。柜子上镶嵌的平面镜中,照映出一张惊慌失措、可怜无助的脸。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是他自己。
他盯着这张脸看,越看越觉得陌生,越看越觉得不是自己的脸。他知道这是谁的脸了,这是父亲的脸。此刻,他需要立刻拉开衣柜的门,躲进去。至于那张脸,他不能再看,于是,他闭上眼睛。他用双手抓紧衣柜的把手,用力往外拉。先拉开。奇怪,衣柜纹丝不动,门就像被最强力的胶水粘住一样。他气急败坏,猛推衣柜,衣柜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有千斤重。他双脚都用上,使整个身体垂直于衣柜,他惊讶于此刻从自己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力量。他的头用力向后仰,他咬紧牙关,用尽生平最大的力气去拉。他的身体几乎变成了一条平行于地面的直线。
砰地一声,衣柜的门终于被打开了,卡夫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疼。一阵白雾散去,他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在衣柜里,他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只巨大的、后背的壳在闪闪发光的甲虫。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甲虫。他应该恐惧,应该尖叫,但他没有,他也纳闷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恐惧。他只是觉得,眼前的这只甲虫简直太迷人了。线条、肤色、身体比例都是完美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昆虫。他看得入了神。只需瞥一眼,他就能断定这只甲虫的外壳坚硬无比,可以承受世界上最厉害武器的攻击。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变得温润起来,他多么需要一个这样的壳子呀!
只见这个铁板一样的外壳,缓缓张开,张到一定的幅度后,停下了,就像一辆车打开了主驾驶的门。
卡夫卡下意识地走上前。
这只甲虫伸出一只黢黑而灵敏的爪子,亲切地对卡夫卡说道:
你好,我叫格里高尔,很高兴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