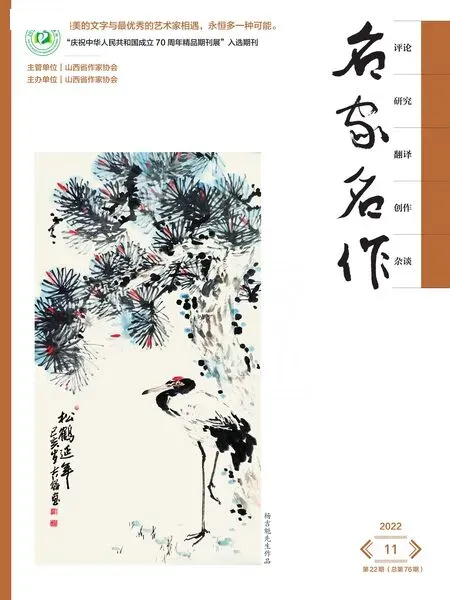存在时间与死亡未来
——以《喧哗与骚动》《尘埃落定》为对象
2022-02-23张丹琛
张丹琛
亨利·柏格森在其时空视野下将时间划分为两类——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前者一般指钟表时间,即物理意义下物质发展的客观时间,主要用于度量人与事存在长度的数字概念。与之相对的后者指主观意识上以顿悟感知到的生命“绵延”[1]。因此,心理时间没有绝对线性的顺接连承,而是强调各要素的交互渗透,指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法由他人琢磨与预测的浮光掠影[2]。
综合前人研究,在时间研究层面大多学者将目光集中于康普森家族的长子昆丁的叙述中,较少关注到痴傻幼子班吉视角下的时间流动;关于《尘埃落定》的研究中虽关注到其意识流时间书写,但较少学者将柏格森与《尘埃落定》相关联。因此,本文将从二者共有的痴傻视角出发,以柏格森的时间理论为研究基础与切入点,浅析《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中时间的“常态世界”与“非常态世界”。
一、“常态世界”中禁锢与游移的未来
(一)禁锢 :以重复叠印的“一天”建构停滞的“一生”
《喧哗与骚动》中三岁智力水平的青年班吉是第一位叙述者。虽然带有痴傻之名,但班吉对于钟表时间拥有可借助周围环境进行判断的天然感知力。以文本整体的空间时间为视点,班吉处于家族没落、父兄死亡、日薄西山的“现代”背景中。以班吉为内视角的现实来看,找高尔夫球、镚子儿和回家、吃蛋糕、睡觉构成了叙事者一天的活动格局;现实在回忆中显出寡味的同时处于记忆末端的凯蒂是他这一天始终惦念的鲜活存在,由此扭曲了班吉整体感知的时间长度。班吉作为叙事者呜咽在嘈杂中,集中感受周围浮于事象的表面[3],因此将班吉所在的1928年、1912年等分别归类,他对“一天”时间的概念十分清晰,其表达方式来源于场景再现与经由光影变换点明环境中的空间时间。
班吉拥有空间时间意识并能将其扩散至回忆中,进而展现现实的“一天”与过去的“一生”两个维度共存下的空间时间。
(二)游移:以压缩的“一生”漫过永昼的“一天”
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是《尘埃落定》中唯一的叙述主体,以不怀心机的个体叙事构建了历史与自我判断交织的空间时间。傻子少爷处于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嘉绒藏族的大背景中。从叙述者的生存来看,罂粟和现代武装的进入、宗教间的斗争渗透、饥荒和贸易的始末、战争中选边错误与最后土司覆灭构成了傻子少爷一生的活动格局。但看似清晰的事件脉络却较少针对单一固定的时间线进行连续推进,大时代空间时间的历史时间点的叙述昙花一现后隐蔽无踪,转而集中个体周围事物堆砌的多少来判断时间流速。因此,大历史视角与事件增减数量的糅杂动摇了常规事件与线性时间的推进,转而偏向时间流速、事件调度混杂的描写方式。二者的相互依存让柏格森理论下的空间时间混浊化,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时间。
傻子少爷有深刻的大历史宏观视角下的时代空间时间与纷繁的个人判断的空间时间,并且二者辨析明晰的同时又相互融合,构成独立完善的空间时间体系。
(三)班吉与傻子少爷的未来存在潜力
班吉作为福克纳笔下名副其实的、不具备生活能力与理解能力的痴傻形象,他对一切周围事物凭其气味、色彩等进行感知,不会评价与反思;而傻子少爷名为傻子,却能精准定向事物内部发展,有渴望、有虚妄的同时能够解剖反思自身。因此,二者形象建构的对比拉开差距,前者的班吉将现实一天中的昏浊夹杂于一生度过,空间时间序列只限定了何时将回忆中的碎片串起,进而辨别拼凑出与凯蒂的朝夕,以是班吉活在过去,目前的光影空间只作用于其过往的召回,并不存在现实意义,所以班吉也没有钟表空间概念的客观未来。从以“过去—现代—未来”为延伸的空间时间来看[2],班吉活在过去、以现代时间关照过去,没有关照现代的同时没有向未来依次延伸的迹象,因此班吉没有未来。后者的傻子少爷却空背痴傻之名,将一年推拉至“一天”的同时,将空间时间线划为双重辨判:一重于大历史视角下行预言之实,贯穿“过去—现代—未来”凝视土司的挣扎与崩溃;一重于个人化空间时间,虽由自身堆砌的事件多少判断时间序列,但空间时间的推进与演进仍依线性分布,处于过去—现代—未来的整体延伸中;因此即使在其大历史视角下的钟表空间与土司湮灭共同濒临崩溃,个人化的空间时间仍隐现着傻子少爷行至未来的潜在资本。
总之,二者都在打破常规概念下的时间流动的同时传递出时间难以逃避抗拒的苍白感。
二、 “非常态世界”中扩散与纵深的绵延结局
(一)班吉:流止的局限与无望
班吉从叙述开始就陷入没有中止的哭嚎,并伴随着当下的喧哗逐步迷失在过去的骚动中,他的心理时间是由自我体悟与外界刺激二者相互作用产生。从其心理时间流过的事件来看,班吉一共经历了1898年大姆娣去世、1910年凯蒂结婚等七个事件,他的心理时间在以上七个事件中反复跳跃——以凯蒂所说所做为主要线索,加之与现实周围事物的形状、气味等相关联形成独特的“非常态世界”。也因为与空间时间对比鲜明的心理时间,所以班吉的一生扭曲至短短一天,即使白驹过隙,他自始至终都处于将自己从家族边缘拉至中心的、虚无缥缈的空间中;柏格森认为心理时间表示生命的深度与广度,班吉生命的深度限于凯蒂及其给予的幸福感,其生命的广度限于与凯蒂相关的七个事件,班吉的一生也仅限于与二者相合。
班吉心理时间颠倒、事件混淆,但总体都是以自我幸福为中心向外扩散,自身的存在是整个绵延过程中最中心的长存的要素。因此班吉的心理时间是由深度与广度相交融的“自我生命之流的绵延”[1]。
(二)傻子少爷:自觉的沉沦与接纳
《尘埃落定》的叙事经历了从国民政府到解放战争胜利的二三十年,但文本内的钟表时间在创作主体借叙述者之口被定义后,转而使整体叙述时间以感悟到的生命流动的方式来呈现。
不同于班吉的流亡于过去,傻子少爷的心理时间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渗透融合,在各要素的混乱中以情感变迁为线索,将时间流速相对化实现自身叙述的陌生化,使漫长一生匆匆流过。因此,文本中事件变动如走马观花,几天后马不停蹄地奔向下一个事件的行动序列,一切由情感色彩的流变统领,将傻子少爷个人的心理时间罩落在巨幅的土司大地。创作主体在此基础上加以内视角的沉浸式叙述,跟随傻子少爷度过了似乎是仅仅一眨眼的,但清晰模糊各个分明的万灯交汇——“要是母亲像多年前那个早晨一样坐在这房间里,我就要问问她,她的傻瓜儿子有多少岁了。三十四十?还是五十岁?好多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走到窗前,外面,大雾正渐渐散去,鸟鸣声清脆悦耳,好像时间从来就没有流动,生命还停留在好多好多年前。”因此,其生命绵延的完整保留也将一眨眼的生命历程合理化,细微情感体验中的策马奔腾与轻抹慢捻相生,也将“非常规世界”鲜明化——“本来,前些时候,我已经觉得时间加快了速度,而且越来越快……土司们来了,梅毒来了,有颜色的汉人来了。只有当我妻子为了勾引年轻的汪波土司而引颈歌唱时,我才觉得时间又慢下来。”
综上,傻子少爷以相对化的心理时间对本来符合时间序列的“常态世界”进行了直觉内省,将世界拉入个体情感感受,将看似流止寻常的一生变为短短一晃。
(三)类同的预知能力与差异化的死亡维度
真假痴傻形象在心理时间方面区别最明晰的是二者于各种状态、各种要素组合下的各种事件于心理时间中的梳理。班吉心理时间下的事件混杂、不定性强烈,虽是以凯蒂为线索,但声音、马棚等都可以成为牵动其心理时间的依据,进而使事件连续、嵌套跳跃。傻子少爷则更显常规化,事件序列清晰、指向明确,以情感变动为基的浮光掠影只限于该事件在其情绪变动下的意识快慢;因此,班吉在痴傻形象的基础上增添了对凯蒂的依赖、敏感、天真、不识世事等特点,如无时无刻想起凯蒂和看似与现实不相关的事件切换;傻子少爷在痴傻形象的基础上点染的却是超常的残忍与善良,如对待桑吉卓玛与翁波意西在不同心理时间的不同的态度与方式。
但二者的心理时间在对形象进一步塑造的方面都体现了超乎寻常的预知能力。班吉能闻出凯蒂身上树的气味和死亡的味道,傻子少爷早早发觉辖日下的隐患并以画眉被雪压下、水落于地面分崩离析隐喻土司最后的结局。二者预言的成因也相同,班吉对树与死亡气味的敏感出于对自身处境的判断,凯蒂的离去与昆丁的死亡都意味着生活消极面增生,因此班吉的预言是他对自身、对未来的提前预警。傻子少爷对自身未来的预知也在小说第一章中体现——“一个月时坚决不笑。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作出反应。”因此在“我们麦其一家,除了我和母亲,还有父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是汉人”的境地下成功存活。但是傻子少爷对时代的必然趋势则抱有悲观的态度,从辖日的歌声中看见自身的命运,对土司世界的改革、用人文关怀打开土司世界大门等都是对自身命运拯救的企图,但时代纷纷、轮回的债券欠到了傻子少爷身上最后黑血流出,回望“辖日”的一切,都能发现装傻与试图救起土司都是出于自身拯救的企图、对未来的提前预警。
虽然二者预知能力无法阻止毁灭爆发,但二者结局的性质截然不同。凯蒂离去、康普森家族没落,班吉的心理时间困于时空一隅,任空间时间流动,心理时间的绵延永远停滞,凯蒂永远流窜。班吉的人生已经是一个破碎的、无可挽回的人生,他失去了幸福空间的支撑,并且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痴傻形象,只是想同记忆中与凯蒂年纪相仿的女孩说话就被康普森家族定性为恶意事件进而去势来看,其未来已经具有自身不可抗的定型模式。因此班吉沉沦于过去的喧哗,迷失在日复一日中却依旧将年复一年地承担家族灭亡。因此,班吉注定长存于黑暗,他绵延的心理时间中只有的过去作为“一团团滑溜的、明亮的”[4]被用来沉淀生命,但他的现在、未来和他生命的流动都被黑暗覆盖。
然而傻子少爷虽然从始至终都在试图拯救自己所深爱的土司岁月,但“君不见,那些想要说些什么的舌头已经烂掉了”,“百姓有时确实想说点什么,但这些人一直要等到死了,才会讲点什么”。傻子少爷透视了静态土司制度下难以阻挡的时代暗涌,浓厚的宿命色彩贯穿他对土司制度的理解并以其带动心理时间的流动。因此他从最初就回归、明定了自身命运,将家人与自己的死亡作为麦其土司家族最后终结的一个象征,作为时代暗涌冲破冰层迸流在土司大地的一个符号。因此,本是美好过去与现在的毁灭,傻子少爷却发出“整个下降过程非常美妙,给人的感觉倒好像是飞起来了”。后续得知家人死亡后也认为“麦其土司和太太的灵魂要上天去了”。他以自身的历史循环思想凝望土司制度与深陷其中的家人,与班吉没有个人选择的固化有质的区别。最后,傻子少爷以轮回、宿命的归属迎向死亡,坦坦荡荡地认命并迎接属于自己的结局。因此,傻子少爷的结局甚至谈得上个人层面的充盈希望与圆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柏格森的时间理论出发,分别从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两个维度解析二者的常态与非常态的世界,进而对两书中的痴傻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空间时间来看,二者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时段中拥有不同的本真存在与绵延潜力;自心理时间的浅析中二者因形象构建差异产生的叙述序列差异与叙述差异反响至二者形象塑造的差异与类同,因形象的异同对二者结局性质产生的差异与最后两位作家对命运深度书写的类同。种种异同使二者各保有独特的时间结局与存在,班吉于精神未来湮灭,但客观物质世界存活;傻子少爷于灵魂精神完满,但客观物质世界陨落。
二书相合即是时间力量的不可抗性,无人长久幸福地留存于世界,反映了现代以来人类的生存与情感困境的同时,以痴傻形象的失语与不同层面的陨灭对人类的未来进行质疑与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