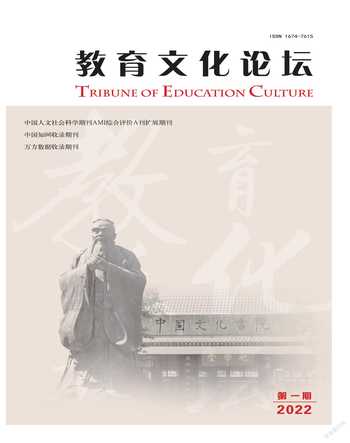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
2022-02-22何峰
摘 要: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
关键词:康乾南巡;典籍编纂;江浙地区;文化事业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1-0049-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1.009
孟森先生认为,清朝开国制度除八旗制度外,其余皆沿明制,几乎没有改变。顺治三年(1646)三月,“繙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康熙帝亲政之后,延续顺治时期重视汉文化的传统,努力稳定和收拢汉文化影响下的士人群体,其中以康熙十八年(1679)举办的“博学鸿儒”一科为典型代表。据《清圣祖实录》卷71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谕吏部,诏举“博学鸿儒”,不仅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布、按等官员可以举荐人才,其他各类官员也可向吏部或督抚推荐博学之士,此举在于全面收罗地方上的汉人士大夫。经过一年的准备,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正式开考,“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其中不少人在此后康熙朝的文坛和政坛中具有重要影响。可见康熙己未博学鸿儒之举,确实有提高汉人士大夫地位之作用。康熙初年,江南地区汉人士绅聚集,尽管清政府军事上已经稳定了江南地区,然而一些江南士绅对明王朝仍抱怀思。康熙帝此次举博学鸿儒,为“循名求士”,尤以地方上的大儒甚至不愿出仕的大儒为重点延揽对象。《冷庐杂识》卷1记载:“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人才皆以江南为极盛。己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己未王顼龄、丙辰刘纶入阁,皆江南人也。其次,则浙江为盛,己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江南士绅是康乾时期国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康乾盛世,清政府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以康熙时期《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代表,尤以后者最为繁巨。因此,从技术层面讲,清政府也需要延揽大量文人,而南巡无疑是帝王广泛接触江南士绅群体,并亲自延揽人才的最佳途径。此外,巡幸江南,除与江南地方进行人才的互动之外,江南地区收藏的一些古代典籍或时人著述,也通过收集或进献的方式,进入帝王的视野,成为典籍编纂的参考。
一、考察与延揽人才
江浙一带作为“文物之邦”,文化底蕴丰厚,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在江浙地区进行了多次“召试”。
1.特恩召试
这类召试相较于“博学鸿儒”一科更为灵活。“博学鸿儒”举行的次数非常少,且须有官员引荐之后,入京考试。巡幸地方,帝王与当地文人士绅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少文人士子在御道附近献赋献册,且在当地进行考试,有利于没有条件前往京师或进入此前引荐系统的文人进入国家的视野。当然,不仅南巡有特召考试,其他巡幸活动也曾给士人特召的机会。
南巡召试以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招取士子为最多,尚未发现康熙帝前几次南巡有大规模的召试行为,但因献赋、献册而给予恩赏的情况并不少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两次南巡,一举招取文人73人,应与康熙中晚期集中编纂汉文化典籍有关。康熙帝非常注重汉文化典籍的编纂和整理,他在武英殿造办处下增设武英殿修书处,“负责修书和刊刻图籍,并以后一任务为重。武英殿修书处总裁,满汉各一,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简任,下设提调、纂修、协修、笔贴式。设有书作、印刷作等下属机构……。武英殿印书甚多,刊有经、史、子、集,丛书595种……除收辑宋元版本的《武英殿聚珍丛书》、《十三经》、《二十二史》,多刊刻清代著作,诸如政书、方略、皇帝的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等。”王欣夫先生提到,康乾时期“编辑了许多卷以百计的大部书籍,又大量地翻刻古书,因而在官刻版本来说,不但数量上远远地超过了宋、元、明三朝,而雕刻技术和印刷装潢也可首屈一指”。京城大规模的典籍编纂工作需要大量抄写人员,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至苏州,谕江南江西总督阿山等,“内廷供奉诸翰林虽皆善书,但朕勤心典籍、卷帙繁多,见在供奉人员缮写不给。尔等出示传谕,安徽、江苏,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赴尔等衙门报名。至浙江,亦照此传谕。朕亲加考试,特谕。”即康熙帝此次大举南巡召试,乃因“勤心典籍、卷帙繁多”,“供奉人员缮写不给”,因此,要求地方督抚召试“书法精熟”之人。《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康熙帝要求江南总督、安徽巡抚、江宁巡抚、江南学院“出示晓谕上下,两江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庭供奉抄写者,星速赴尔等衙门报名,就近齐集。江宁、苏州二处俟朕回銮之日亲加考试”,此后总督、抚院立即晓谕各地,令“苏、松、常、镇、淮、扬六府在苏伺候;安徽所属并江宁、徐州,在江宁伺候”。至杭州时,传令杭州地方官:“进过册页浙江人员内举贡监生童,着速传集杭州府城听候考试,如有善书者,情愿赴考,亦着作速报名,一同考试。”
此次召试,以苏州、江宁、杭州为考点,地域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尽管此时江苏、安徽二省已经分治,但安徽布政使司仍寄治江宁,因此,苏州、江宁作为政治中心统辖江苏、安徽二地,并在文化地域上各有重心。召试以“书法精熟”为标准,参与者基本为文人士大夫。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的记载,在苏州参加考试的“举贡监生员并献册页童生人等共千名”。安徽各府、江寧府、徐州等府州的举贡监生员,及回銮镇江一路进册页的生员、童生都集聚在江宁贡院考试,“应考举贡监生童共五百余名”。除此之外,江宁八旗官员,笔帖式中擅长满汉两种字体的人员,也都需要进行考试,“由苏州迄江宁,御试士子者三。中选者给白金,令赴京入各书馆”。
与“博学鸿儒”科不同,此次考试无须官员引荐,南巡沿途或在行宫中献赋诸生,及地方官员晓谕各地之后前来应考的生员基本上都可以参加,因此苏州考试人数即有千名,江宁有五百多名,而召试的目的却主要是“赴京入各书馆”。乾隆南巡沿袭了康熙南巡召试的传统,对沿途献赋献册的文人士子进行召试。进献诗赋册页,即可获得额外召试机会,对于广大希望进入仕途的江南士人而言不啻一极简途径。“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爱戴之忱,有足嘉者。朕已叠沛恩膏,随时赏赉,缅昔皇祖圣祖仁皇帝时巡所至,优奖士类,一时硕学通才,多蒙鉴拔,方策所载,称盛事焉。”乾隆帝历次南巡,都在江浙二省进行召试,招取之人除入中央各书馆之外,有不少因此获取功名,进入仕途。《吾学录初编》记载献册、献诗诸生,考中进士、举人,取列一等的,以内阁中书补用,贡监生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或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列二等的,给缎,或可充中央各馆誊录官。为体现延揽人才之诚,对召试人员身份进行限定,即“现任京堂及翰、詹、科、道,外官府、道以上”官员的亲兄弟子侄,只准迎銮献册,不准应试。
《乾隆南巡御档》记载了乾隆三十年(1775)浙江、江苏及安徽南巡召试情况,列一等之人,直接授予职衔,二等则赏赐物品。乾隆四十五年江苏省召试,周边省份如江西省生员也可参加应考,但却有地域差异,即江苏、安徽生员列一等者直接授职,江西、直隶、山东列一等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南巡招取的文人,随个人发展的差异,一部分人逐渐升迁官职,诞生了一批在清代中期有影响力的文化或政治人物,如钱大昕、褚寅亮、沈初等人。
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钱大昕24岁,沿途进赋,后被召赴江宁考试,入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获取进士功名,改庶吉士,此后又曾任翰林院编修,山东、湖南、浙江乡试考官,及翰林院侍讲、广东学政等官。乾隆四十年(1775),因父亲病逝归里,未再入京供职,以在江南地区任一些闲散文职、游赏名胜为主。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巡,钱大昕仍与在籍诸臣前往淮安迎驾,并进南巡颂一册,后被两江总督萨载盛意请求,续修南巡盛典。以此观之,作为江南地区的知名文化人物,钱大昕的个人经历与南巡有着密切的关联,因南巡步入仕途,并成为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的官员,参与国家最高层面的文化活动,并多次任地方文化生活的领袖人物,赋闲居家之后,仍参与南巡事宜的后续工作。沈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召试,授举人,内阁中书,后入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多省学政、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期间曾兼任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最终获得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军政要职。无锡人杜诏,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以诸生进迎銮词”,驾幸惠山,“又进梁溪望幸词,召见御舟赐绫诗一幅”,后被召至京城,曾纂修历代诗余、词谱,后“钦赐进士,改庶常”。
南巡召试对于许多江南士子来说,是进入仕途的简便途径。尽管召试中很多人不能直接被授予进士,而为举人,但因此进入国家文化系统,为帝王和官员们所了解,进一步获取更高功名的机会比常规科举入仕更为容易,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学养丰厚的一代名儒。
2.官绅书赋能力测试
对于文官系统,康熙帝也曾进行考试,测试文官书赋能力。康熙帝五到苏州,谕令“有能善于诗文者赴行宫赐题做诗,随督抚、学院一同考试”;在杭州,“召抚、学二院,布、按二司,杭、温二府,杭、嘉、湖、严、台、宁七府同知,杭、金二通判,归安、东阳、仙居、临海、天台、建德、汤溪等知县,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干、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其中,江苏巡抚宋荦的书赋较好,即获康熙帝的称许与赏赐。此次杭州的考试,几乎将浙江各府、州、县主要文官都召集到行宫赋诗,是一次对文官系统官员文化素养的全面观察。
康熙帝对官员文化素养的测试,亦与他在江南地区的典籍刻印事业有关。康熙帝热爱刻书,不仅在武英殿设有修书处,于京城聚集文人编纂盛典,在江南各地也有一些名僚为其刻印各类典籍,其中尤以宋荦、曹寅等人为代表,形成清中叶江南地区的刻书风尚。康熙帝南巡时曾对宋荦以软字精刻的“皇舆表”大加赞赏。金埴《不下带编》卷1载:“江宁织造曹,公子清有句云:赚得红蕤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自谓平生称意之句。是岁,兼巡淮鹾,遂逝于淮南使去院,则诗谶也。公素躭吟,擅才艺,内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锼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书’者,自曹始也。”金埴以康版书自江宁织造曹家开始,且金氏认为“康版”刻书胜于“宋版”。如此可见,康熙帝在南巡中召江南文官集体考试,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根据章宏伟先生的研究,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到苏州,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9人分校,后又命江苏巡抚宋荦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令召纂修书史。驻跸杭州时,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进行宫做诗;在常州府,又召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朝见考诗。章宏伟先生根据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的奏折,指出彭定求、汪士鋐、汪繹、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9位,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10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彭定求也提到康熙乙酉南巡,令在籍翰林官10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可见,康熙帝的典籍刻印事业有两个重心,即京师和江浙。南巡是考察江浙官绅文化素养并委以典籍编纂重任的重要契机。
二、搜集书籍文献及画册
“召试”为国家文化事业吸纳人才资源,接受地方上的书籍、画册进献则为文化事业进行资料储备。尽管内府收藏浩如烟海,但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对地方士绅进献书籍画册予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记载,各地进献物品中,康熙帝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收取,不过古书一般都会收取,并力图在民间搜寻一些孤本书籍。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至苏州,问起原灵壁知县马骕所著的《绎史》一书,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第二年花200两白金至马骕所在山东邹平县购买,自此收进内府,民间难见。
乾隆帝对江南各地藏书及书籍流传情况非常熟悉,因编《四库全书》的需要,对收集各地书籍之事也非常急迫。乾隆三十八年(1773)谕军机大臣等,令各督抚在江浙地区搜访各类书籍,江南各地督抚及藏书之人对于收书一事抱有谨慎态度,担心书中若有不利于当朝的言辞而被牵连,乾隆帝谕令无须察看,直接送到京师,不加责于地方。《四库全书》即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编纂。由此可见,此次大规模收书工作,确实为四库所需,乾隆三十九年(1774),“催缴直省藏书,四方竞进秘籍甚众,江、浙督抚采进者达四五千种,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家藏之籍,呈进者各六七百种,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亦各进书百种以上。至是天府之藏,卓越前代,特命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著录六千七百八十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平步青言编纂四库“诏征天下遗书凡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虽收书时间并非主要在南巡期间,但以乾隆帝编纂典籍的热忱及对江南藏书情况的熟稔,南巡期间应一直注意地方上的文献状况,地方官员应也会予以配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南巡,伊龄阿进“宋岳珂原板孝经论孟三部”。
地方进献的书籍除历代典籍之外,还包括时人自己撰写或整理编纂的著述。康熙帝和乾隆帝对于捐献之人或给予召试机会,或赐钱刊刻,或直接赏赐御书匾额、物件。进献书籍中,有不少精品入编四库,或成为皇帝御定书籍。对江南士绅而言,其著述往往先是在文人小圈子里流传,若想受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需要一定的契机,“南巡”直接将著述呈送给帝王,即是一个机会。因此,进献书籍对于帝王和当地士子而言,都很有意义。毛奇龄于康熙己未科“博学鸿儒”即已在京师入职,后因身体不适,返居乡里,撰有《圣谕乐本解说二卷》,康熙三十一年(1692)五月曾想寻找机会,进呈给康熙帝,没有成功。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毛奇龄特地到嘉兴迎驾,并将此书进呈给康熙帝,后入编《四库全书》。南巡进献入编《四库全书》的代表性书籍,还有胡渭的《禹贡锥指》、龚士炯的《历代纪事年表》等。一些进献书籍获得帝王的赏识,由此有了“御定”身份,如《乾隆御定石经》为乾隆南巡时江南布衣蒋衡书呈进,存放在懋勤殿,并刻成石经。徐倬《全唐诗录》100卷“以唐诗卷帙浩繁,乃采撷菁华,辑为一集,每人各附小传,又间附诗话、诗评以备考证”,于康熙南巡时进呈,获得康熙帝嘉奖,并“由侍读擢礼部侍郎,以旌好学,并御制序文,赐帑金刊板”。帝王御制序文,并赏赐刻印费用,对当时的文人而言,应是非常尊崇的殊荣了。
三、江南地区的典籍分藏
康熙帝和乾隆帝通过南巡吸纳江南地区的人才及文化资源,促进了清中叶典籍编纂事业的发展,也以“颁赐书籍”的方式对南巡沿经的江浙地区进行文化回馈。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即曾颁赐江南各重要书院“殿板经史”,“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沿经江浙地区的文化机构主要为各大书院,因此,颁赐以书院为对象。至乾隆中晚期,于三处帝王南巡行宫所在地扬州天宁寺大观堂、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镇江金山江天寺建立“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江南三阁,以分贮《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成为清中期国家对江南地区文化输出的重要场所。除江南三阁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之外,南巡一路的诸多行宫及名胜也都曾受到帝王推行汉文化典籍的恩泽。圆明园长春园中有一轩,落成时适逢重刻宋代“淳化阁帖”,于是“于左右廊各十二楹内,每一楹嵌六石”,称之为淳化轩,重刻的淳化阁帖,“凡十卷,诸家名迹共九十九人”,刻成之后,“用蝉翼摹搨四百部,分赐皇子皇孙、王以下、文职二品以上,及内廷翰林、外省督、抚、衍圣公”,同时“直隶、山东、江、浙行宫与名胜之地,及翰、詹、国子监衙门、庶常馆、各省书院,俱分颁藏弆”。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月初一日谕内阁:“仿宋板五经着于直隶赵北口绛河,山东德州白鹤泉、泮池、泉林,江南天宁寺、高旻寺、金山、焦山、寄畅园、苏州灵岩山、江宁、徐州柳泉、浙江杭州圣因寺、龙井安澜园等处各陈设一部,其平定准噶尔回部两金川得胜图,亦着一并陈设。”如此可见,重要典籍或重大事件相关图籍刻印,江浙地区帝王南巡行宫及名胜所在地,往往与京城重要处所及王公贵族、重要官员一起,获得颁赐待遇。
四、结语
康乾南巡是清政府与江南士绅群体最直接、最广泛的接触过程。南巡过程中,许多人才受到重用,文化资源得到保护,为清政府的文化典籍编纂事业作出了贡献。清政府在京城和江浙地区进行了系统的文化典籍编纂整理工作,这种整理是对汉文化典籍的重新挑选,再通过典籍颁赐的方式,以清廷塑造下的典籍文化重新影响江浙地区。江浙二省典籍的贮藏之所,与南巡留下来的景观直接相关,亦可见南巡对江南地区文化系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孟森.明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397.
[2]清圣祖实录:卷80[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016.
[3]陆以湉.冷庐杂识[M].崔凡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4.
[4]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上[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11.
[5]王欣夫.文献学讲义[M].徐鹏,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56.
[6]清圣祖实录: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6.
[7]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丛书集成续编第27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8]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童正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9]清高宗实录:卷383[M].北京:中华书局,1986:39.
[10]吴荣光.吾学录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南巡御档[M].杭州:浙江富阳华宝斋书社,2001.
[12]清高宗实录:卷1103[M].北京:中华书局,1986:772.
[13]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钱辛楣先生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14]沈初.西清笔记: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286-289.
[15]法式善.槐厅载笔: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6.
[16]曹红军.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书印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51-53.
[17]金埴.不下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
[18]章宏偉.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85-96.
[19]钱林.文献征存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4.
[20]清高宗实录:卷929[M].北京:中华书局,1986:500-501.
[2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4 264.
[22]平步青.霞外攈屑: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3.
[23]四库全书总目:卷38[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7.
[24]英和.恩福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7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0.
[25]四库全书总目:卷190[M].北京:中华书局,1965:1 731.
[26]清高宗实录:卷384[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45.
[27]何峰.清帝南巡与江南三阁[J].江西社会科学,2013(10):123-127.
[28]钦定南巡盛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98.
The Southern Tours of Emperor Kangxi and Emperor Qianlong, Compilation of Classics and Cultural Business
HE F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48)
Abstract:During the tour of Emperor Kangxi and Emperor Qianlong to the south, they actively interacted with the literati and gentry group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inspecting and recruiting talents through the special test, the official gentry writing ability test, etc., and searching for classics or accepting books and paintings contributed by the literati and gentry. The emperor’s absorption of literati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reserved strength for the compil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centering on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in the capital and Jiangsu and Zhejiang. During and after the southern tour, the compiled cultural classics which were adjusted and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by the government were awarded to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most of the storage places for the cultural classics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are palaces or scenic spo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tour.
Key words:the southern tours of Emperor Kangxi and Emperor Qianlong; compilation of classics; Jiangsu and Zhejiang; cultural business
(责任编辑:杨 波)
收稿日期:2021-08-23
基金项目:故宫博物院2021年度开放课题经费资助项目“‘江南’与‘京师’:‘康乾南巡’影响下的景观、社会与文化”。
作者简介:何 峰,女,江苏东台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文化、景观文化、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