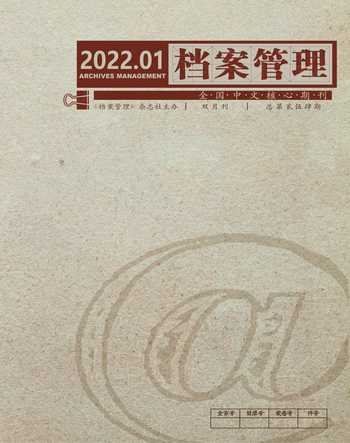从《至正条格》看元代急递铺与档案文书的递送
2022-02-22王芳
王芳
摘 要:元代急递铺是专门传递档案文书的机构。2002年发现的元后期法典《至正条格》为进一步研究急递铺提供了新的史料。元政府针对档案文书递送出现的稽迟、损坏、沉匿等问题,因时因事立法,保证急递铺的人员和设施完备,规范递送行为,对违反法律者予以处罚,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递送系统。
关键词:元代;急递铺;档案文书;《至正条格》
Abstract: The Jidipu in the Yuan Dynasty is a special organ to transmit the archives and documents. The Zhizheng Tiaoge, the code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as discovered in 2002, which provide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Jidipu in the Yuan Dynasty.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delay, abrasion, damage and loss during the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rchives and documents, the Yuan Dynasty made laws according to time and matter to ensure personnel and complete facilities in the Jidipu, regulate the transmission, punish the breach of law, thus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transmitting system.
Keywords: Yuan dynasty; Jidipu; The archives and documents; ‘Zhizheng tiaoge’
元代擁有庞大的疆域,档案文书在这极广的范围内进行频繁的、有效的传递就更为重要。元代承袭金代,有急递铺作为专门传递档案文书的机构。《元史·兵志四》云:“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1]关元代急递铺,学界对其设立、分布等已有所研究①。学者所用史料主要为《元典章》《经世大典》《元史》中所载。2002年,久已亡佚的元代后期法典在韩国被意外发现,2007年,其影印本和校注本出版。《至正条格》中关于急递铺的规定,有见于其他文献者,如《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五《职制·整点急递铺》“大德十年三月”条、《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五《职制·设立邮长》“至治二年九月”条②,也有不载于其他文献者,如《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五《职制·整点急递铺》“至顺三年二月”条、《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五《职制·禁扰铺兵》“泰定二年五月十四日”条等。急递铺设立于元世祖初年,在运行中必然存在些许问题,元政府采取相应措施,逐步完善,使其成为一个庞大而有效的传递系统,保证政令通达。笔者拟结合新的史料进行研究,敬请批评指正。
1 急递铺系统的人员和设施
元代驿站“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之外,还接待使臣,传送物质,站户不堪重负。忽必烈为了减轻站赤铺马压力,保证官府间文书传输的稳定安全,仿照金代设立了专门传输官文书和政府信息的机构,即急递铺。[2]
1.1 铺司、铺兵。急递铺的当差人员是铺司和铺兵。铺司,也叫铺书记或书手,检查铺兵递送文书的时间,以及文书的收藏和保密。[3]每一急递铺有铺兵五名。最初设立急递铺时,“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签起”。[4]先在所管民户内挑选“不能当差贫户”。挑选贫户的原因在于贫户无力承担其他需要出物质的差役,让其充当铺兵,“除其差发”。贫穷户不够时,“漏户籍内贴补”。[5]铺兵执行传递档案文书任务,有严格的时间、速度要求。至元二十八年规定,“铺兵须壮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随即易换”。[6]大德元年规定,“各处提调官选少壮人丁应役,毋令老幼不堪之人充应”。[7]
随着时间推移,铺兵“身死、在逃、老幼残疾”,则传递文件比最初设立急递铺时迟慢很多。针对这一情形,元政府多次整点急递铺。大德十一年七月,中书省要求将“不堪走递之人,取勘见数,于相应户内,依数补换”,保证“堪役人丁,正身应役”,不允许“权豪势要并一般人户,取要钱物,结揽代替”。为便于监督,“开具实补换户数,各县村庄,花名造册”。如果有的急递铺需要增加户数,则“明白议拟,保结呈省”。[8]
急递铺的铺兵,其专一任务就是递送档案文书。但是,有时过往的差使人员、权豪等,借公差之名,“强拖铺兵并镇店百姓挑担行李及牵船只”,以致“走递文字稽迟”。为禁止这一情形,大德五年,发布禁例,禁止让铺兵挑担,如果违犯,痛行断罪。[9]泰定年间,有些衙门、枝儿令铺兵递送果木,宣徽院奏请:“今后除进送上位的果木并忙文书外,各衙门、各枝儿递送的果木,休教递送。来往行的贵赤、祗候每衣服,若教担着递送的,拿住呵,要重罪过。”[10]
1.2 设立邮长。元代的急递铺“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而设立,“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11]传递文字,只是急递铺中的铺司接收文书和发放文书,具体传递由铺兵完成。铺司的担当者,都是“村野愚民,不知利害,不通文理”,加上铺兵“老幼充应,多不堪役”,州县提点人员,又不亲自整点,导致传递文书迟慢、损害,甚至丢失,无从追究。[12]英宗至治三年,元政府决定设置邮长,专门管理急递铺。《元史》载:“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13]邮长“壹周岁交替”。如果设置邮长,所含十铺属于两州县,则在“铺分多者”州县设置邮长,两州县急递铺数量相同者,轮番设置。邮长的职责包括巡视、登记和“每上下半月,开具递过文件及日时申覆”。[14]
1.3 提点监督人员。起先,急递铺由地方的宣抚司管理。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奏准,“各路所设急递铺令宣抚司提调”。[15]到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元政府在大都设置大都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一颗,设提领三员,别无俸禄。[16]由于档案文书关系到政令的通畅,元政府规定对急递铺的工作进行监督。但由于宣抚司不是路的正官,也没有俸禄,并不用心监督检查,急递铺递送的档案文书多有损坏延迟。中统二年七月,元政府改换提调官员,“令总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总行提调,州县依委有俸次官往来刷勘”。[17]
根据《至正条格》所载,有提点监督之责者,路总行提调,主要是府判,州县的提点官是州判、主簿。路总管府府判,每季总行提调,带领司吏一名、祗候一名,到自己所管辖急递铺清点、检查,将结果“牒报本路”。州判、主簿“上下半月,亲临提调,往来照刷”。[18]
1.4 铺马。元代传递档案文书的铺兵,必须是“善走者”。可见,铺兵是步行接力传送档案文件。北宋递铺分急脚递、马递与步递三种,“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19]《金史》载:“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20]由此可见,金代一般情况下是人力传递档案文书,但在特定情形下,如军期、河防,则可以骑马传送。那么,承继金代急递铺的元代有无凭借马力传送文书的情形呢?邱树森、默书民“倾向于肯定”,但其在大作完成时,“现存元代急递铺的汉文史料中尚未发现关于马匹使用和管理的记载,故此问题还有待于汉文史料的发掘考证”。[21]
2002年发现的元代后期法典《至正条格》中的史料,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间接的史料。《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三《职制·中买站马》“至元三年八月”条[22]:至元三年八月,刑部议得:“保宁府达鲁花赤牙忽,系提调站赤正官、将站户许聪堪充走递铺马,妄作不堪,勒令补买,却将自己花骟马壹疋,折至元钞捌拾贯。依不枉法例,杖陆拾柒下,降先职壹等,标附。”都省准拟。
此则史料不见于其他文献,故邱树森之文没有考证此史料。在此条中出现了“走递铺马”之语。“铺马”经常出现在有关驿站的条文中,在《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驛站》之下有“铺马”之目。此目下有如“品从铺马例”“军官起铺马例”“贴马在家喂养”“拜见铺马”等15细目,但文中主要是规范来往官员骑坐铺马。在“贴马在家喂养”目下,有“照勘各处所立站赤,依验驿路紧慢,设定铺马疋数,应付使臣人员走递”之语。[23]急递铺传递文书的承当者是铺兵,所传文书并非官文书的全部,一部分文书是专门官员骑坐铺马传递。“走递铺马”,是否可以理解为“走铺马”和“递铺马”?“走铺马”侧重于供来往人员骑坐,“递铺马”侧重于传递文书。这样理解,则马可波罗的记载则是可信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如果有急需传递某州之消息,或某藩主背叛事,或其他急事于大汗者,其人(铺兵)“于所在之驿站取轻捷之良马,疾驰乡于马力将竭,别驿之人闻铃声亦备良马、铺卒以待;来骑抵站,接递者即接取其所赍之书或他物,疾驰至于下站;下站亦有预备之良马、铺卒接递;于是辗转接递,其行之速,竟至不可思议”。[24]这样说来,在特定情形下,铺兵可以到驿站调用铺马来传递档案文书。
1.5 设施。各路的急递铺有铺舍。铺舍的具体样式并没有相应史料记载。铺舍的具体物件,史料有明确记载。大德元年整点急递铺时规定:“每铺什物:时辰轮子、红绰屑并牌额、铺历二本、夹板一副、铃攀一副、软绢包袱、油绢三尺、蓑衣一领、回历一本。”[25]时辰轮子,是计时工具。红绰屑,是指急递铺的门楼,上有牌额,即铺的名牌。铺历两本,一本“上司行下”,一本“诸路行上”,用来记载递送文件及递送有关情况。传递文字时,一定在铺司放置铺历,“分朗附写所受、所发相邻铺兵姓名、文字、时刻,及交递文匣封锁有无损坏。每月提点官就铺照押”。夹板、铃攀、软绢包袱、油绢、蓑衣、回历是铺兵走递时所需之物。
2 规范递送行为
有元一代,多次制定法律法规,规范急递铺的递送行为。
2.1 递送标的。元世祖时,设立急递铺,“凡有合递文字”,“严立限次递送”。[26]中统二年,在各路设立急递铺,所传递文字,“除申朝省并本路行移官司文字外,其余闲慢文字不许入递”,也不得私自夹带一毫物件。[27]中统三年,对合递文字作了进一步规定。对于下行文书,“遇有省发的文字,教转递者”,“其余官府文字”则不能由急递铺转送。对于上行文书,急递铺只能转送“各路总管府文字并总管军官文字直申省者”,如果不是上报中书省的文书,不能递送。中统五年,元代设立了宣慰司。在设立宣慰司的地方也设立急递铺。此处的急递铺除了遵守中统三年的规定外,还可以转递宣慰司、转运司文书。这说明,急递铺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转递的文书稍有不同。
至元年间,消灭了南宋,百废待兴,公事浩繁,急递铺转送标的有时有所增加。如至元八年规定,“各处造成军器,应系随路合申禀事理,今后拟令急递铺转送”,除了文书外,各路账册重十斤以下者,可以让急递铺转送。又如,至元二十年规定,功德使司文字可以转递。又如,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释教总摄所、总统所,凡行文字入递”。[28]可见,至元年间,急递铺转递的文字大大增加,但是铺兵的人数增加不多,结果转递迟缓。至元二十八年规定:“今后省部并诸衙门,入递文字,其常事皆付承发司,随所投下去处,类为一缄。其他府司同。省部台院,凡有急速之事,别置匣子发遣,其匣子入递,随到随行。”[29]将文书“类为一缄”或“别置匣子”,这就方便了转递。
急递铺递送标的、方法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提调官不为用心,加上转递时“有夹杂诸衙门不该走递文字”,致使传递速度缓慢,有的“每昼夜仅及百里”,转递文字迟滞很长时间。大德五年,御史台议得:除边远军情等事差委使臣勾当外,拟合应入递文字,责令总铺依例类缄发遣;除两都递送御膳菜果铺兵外,其余应设急递铺去处,只递公文,并不得将文册十斤以上及一切诸物入递。这一议拟得到了中书省的批准。中书省并明确规定了应入递文字的,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衙门,和不应入递的,如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衙门。[30]
2.2 递送程序。针对急递铺传递档案文书特别迟慢,大德十一年,中书省进一步规范急递铺行为。平时,准备好急递铺所需“时刻轮牌、灯堠、法烛、毡袋、油绢、夹板、铃攀”等物。遇有传递档案文书,及时在铺历上记录,分明附写,“是何衙门文字,承发时刻,相邻铺兵姓名,交递文匣有无损坏”等具体内容。然后,立刻用早已准备之物,将传递档案文书按照规定裹好保护。接着用“当时第几刻牌子”,在档案文书上拴好系好。最后,依所定的时刻,以“昼夜四百里”的速度,送到前面的急递铺,将档案文件和附历明白交付。[31]至治二年,兵部在议拟设立邮长时,强调“依元立程序走递”。[32]此处的“元立程序”,当指大德十一年的规定。
2.3 递送速度。急递铺传送档案文书,必须快速。“急递”的含义,《通鉴》中胡三省的注释为:“军期紧急,文书入递不容稽违晷刻者,谓之急递。递,邮传也。递者,言邮置递以相付而达其所。”[33]《金史》云:“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34]金代急递速度一般是一昼夜三百里,如果特定情形下骑马递送,应超过三百里。
据《元史》,元代最早在中统元年规定了递送的速度,“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35]至元二十二年,依期整点急递铺兵,发现传送的档案文书,不管是紧急文书还是缓慢文书,都递送迟缓,于是针对文书缓急,调整转递速度。紧急文书,“一昼夜须行五百里”,其余文书,还是按照原来规定的程限,“一昼夜行四百里”。[36]但是,到了至元二十八年,紧急文件的递送速度又变为一昼夜四百里。就目前史料来看,一昼夜行四百里,应为定制。元代后期的《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五《整点急递铺》“至顺三年二月”条规定:“凡有递转文字,一奏夜须及四百里。”[37]
3 处罚递送违法行为
3.1 铺司铺兵。对铺司铺兵稽迟、损坏、沉匿、私自开封文书的行为,根据行为的轻重进行处罚。[38][39]
3.2 邮长。邮长对自己所管急递铺承担重要的职责,如果急递铺“稽迟损坏文字,或附写不明不实”,则邮长可以对铺司、铺兵“就便治罪”。如果邮长不能尽职,致有稽迟者,“提调官量事轻重断罪。三犯者替罢,仍黜去籍记姓名。壹岁之内,能尽其役,略无稽迟者,即许从优先补用”。[40]
3.3 提调官吏。元代因时因事立法,对提点官的处罚,不同时期,法律规定有所不同,见《经世大典》《元典章》《至正条格》③所载。其一,对提调官的处罚,州县一级重于路一级。路级提调官也分为初犯、再犯和三犯,比起州县提调官减等处罚。如大德元年,提调官初犯是罚俸一月,则路提调官罚俸半月。其二,处罚因初犯、再犯、三犯而不同。其三,整个元代而言,不同时间,处罚大致相同。大德十年的处罚规定,在元后期的法典《至正条格》中被沿用,可推测《大元通制》中的处罚应同于大德十年规定。[4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元代断例研究与复原”(编号:17AFX006)。
注释:
①邱树森、默书民:《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②此条《至正条格》(校注本),并未标出出现于其他文献中。仔细检索,在《经世大典·政典·急递铺》中有同一史料,参见(元)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等辑校对:《经世大典辑校》第八《政典·急递铺》,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40页。
③史料版本分别为: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等辑校对:《经世大典辑校》第八《政典·急递铺》,中华书局2020年版;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
参考文献:
[1][4][5][11][13][35]〔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96,2596,2598,2596,2598,2597.
[2]李漫.元代传播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4.
[3]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168.
[6][7][8][9][23][25][28][30]陳高华等.元典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03,1305,1307,1313,1273,1305,1309-1310,1310-1311.
[10][14][18][22][31][32][37][38][40][41]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M].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216-217,216,215,195,215,216,215,215-216,216,216.
[12][15][16][17][26][27][29][36][39]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等辑校对.经世大典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20:740,718,736,718,715,718,732,732,723.
[19]〔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856.
[20][34]〔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6,276.
[21]邱树森、默书民.元代官府公文传输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4(02):176-179.
[24]冯承均译.马可波罗行纪[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47-248.
[33]〔宋〕司马光.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9102.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2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