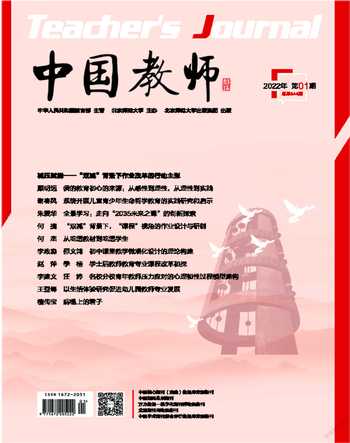病榻上的君子
2022-02-21檀传宝
檀传宝
能遇到好老师,实在是一种人生的幸运与幸福。
非常荣幸,当年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博士生几乎都是哲学大家、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萧焜焘先生的“亲传弟子”。因为萧老师与我们导师鲁洁教授的友谊,他曾经一届又一届地给我们义务讲授西方哲学流派、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课程(鲁洁老师希望我们能借此了解西方哲学,提高理论思维)①。虽然我们不是哲学专业的学生,许多内容听起来不免费力,但是每一届同学都是怀着虔敬的心理走近先生、听先生娓娓道来的。我于1993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就读,当年秋季起就和同门一起每周去先生家听课。不过我们那一届比较特殊的是,那年萧老师已经病重(糖尿病、高血压等),一半课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萧老师担任过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里给我们上的,原定半学期的课也断断续续上了一整年。所以,萧老师对我们来说,是一位“病榻上的先生”。
“病榻上的先生”
1990年,萧老师在自己的回忆录《生之欠》中说:“我一生有不少有褒有贬的称号,但最使我心醉神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师’。”在为自己的教学成就自豪的同时,他也曾认为自己作为老师“极大的缺陷”是“不少学生认为我难以亲近”。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却是:每周固定时间,无论是在先生家里还是后来在病房里,萧老师永远都是微笑着迎送我们,每一节课都让我们如沐春风。
倘若不是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看他浮肿的双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饱受疾病折磨多年,且已经来日无多了(先生于1999年3月1日离世)。在南京兰园先生的家里,尤其是后来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我们曾经多次请求先生暂停授课,希望等他好一点儿再继续,但是萧老师决绝的回答往往让我们再也无法说什么。有一次,他看我们实在着急,就说了一段宽慰我们的话:“你们不要客气。你们知道吗,你们来听课的时间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给你们讲课,至少可以让我暂时忘记疾病的痛苦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花整整半天来听一个老头唠唠叨叨,讲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呢?”
岁月流逝,加上大家都不是哲学专业,《精神现象学》的具体内容如“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伦理精神”“宗教”“绝对知识”等,我们大多已经忘记。但是萧老师的“(黑格尔的)思想是火焰。范畴像水一样是流动着的”等生动诠释带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让我们终生受益。我一直对我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们,强调概念之间的推演、文章内在逻辑的贯通等,就是深受萧老师的影响。
老泪纵横的时刻
可能因为上的是哲学课,也可能因为其儒雅的性格,萧老师上课时总是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脸上多带着温和的微笑。但是也有特别的时刻。有一次课间闲聊,感叹于一些干部严重腐败的现象,先生一下子老泪纵横。这让我们在场的所有学生都震惊不已。
平静下来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去雨花台(烈士陵园),看见的只是一些‘照片’而已。可是我去看见的,许多是我的老师、同学,活生生的人哪!我们当年拼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新中国。现在这样(腐败),我們如何对得起那么多为国捐躯的烈士?”后来我们才知道,若不是李宗仁和平谈判成功,宣布特赦政治犯,萧老师很可能早已成为雨花台上的“照片”了。
那一天,萧老师坚定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努力克服病痛坚持给我们上课,一个重要的动力是希望我们相信: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主义运动虽有缺点、曲折,但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是完全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他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能够摆脱封建主义、战胜拜金主义,也希望我们能做推进历史发展的“种子”—因为即便很多人都腐败了,但只要有“种子”在,人类就有希望!
不管人们是否认同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也不管人们如何评价社会主义运动,每每回想那一时刻,我都会清晰地记起:这个世界上,曾经岿然站立过一位真诚、理性的学者,一位满怀悲悯、大义凛然的共产主义者!
岂知问候即永别
1999年2月16日(己卯年大年初一)上午,我打电话给萧老师拜年。萧老师特别高兴,和我聊了许久。他对我说:“传宝,你知道吗,我一生最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几乎你们鲁洁老师所有的博士生我都上过课!”他还俏皮地和我说:“你这个电话来得正是时候,晚一点儿,你就打不通啦!医院只‘批准’我在家里待到10点,待会儿我就得收拾东西走人了!”我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还是非常乐观地安慰我,但也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已经无法完成他上课时和我们说过的哲学三部曲(《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论》,《精神哲学》未竟)了—眼睛起初还能模糊看见,现在完全看不见了;起初还可以口授、录音整理,现在恐怕口授也难以坚持了……那一刻,我虽在嘴上宽慰着老师,心里却是难受至极。“学术是他的生命”,鲁老师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他轻描淡写地说出恐怕完不成自己的哲学三部曲时,我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地不甘!
因为萧老师得病十多年并且一直得到了较好的医治,那天我还天真地认为,说不定春暖花开时先生还会像过去一样好起来。但是非常可惜的是,1999年秋天,一位同门告诉我,萧老师已经于春天仙逝了。我一方面为自己能在拜年时与老师有过较长一段聊天而有些许宽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十分哀痛:早知问候即永别,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多听听萧老师亲切、温暖、从容不迫的湖南腔!
谢谢您,敬爱的萧老师。虽然我们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但也都是东南大学萧先生的学生。
2020年3月23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