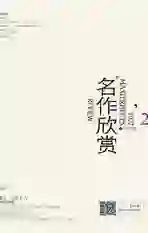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作品生成与形象塑造
2022-02-19胡喻文
摘 要:通过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人成长过程中的可塑性,即通过不同文化氛围的引导,使人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长。本文借此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加以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在传统文化语境下,塑造出的不同的作者及其作品。
关键词: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 人格塑造
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对非洲三个相对封闭、与现代人类社会习俗迥异的部落进行了田野调查:阿拉佩什人认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温良、敏感、易与人合作这些与生俱来的品性,他们是比大多数原始初民更驯顺、更被动、更能助人为乐、更忽视艺术创造和技术性职业的人;蒙杜古马人同样对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他们的理想人格是凶横、勇猛刚强和争强好胜的,并鼓励人们热衷于炫耀行为与钩心斗角,蒙杜古马的传统要求不论男女,都应该骄傲自大、举止粗鲁、喜欢暴力,他们根本不容阿拉佩什人那种温柔的特质;德昌布利人像现代社会一样,男女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但恰恰相反,在德昌布利社会中真正有地位的是女人,她们结成一个牢固的群体,群体团结,丝毫不受个人情绪影响,愉快、和睦、鲁莽、粗俗的玩笑与话语是她们生活的特征,而男人则很少有责任心,并且多愁善感,易于依赖他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的争吵、误解、发誓、抵赖。
玛格丽特·米德借此书向西方传统的男强女弱的性别思维定式发出了质疑,并得出结论:人类的天性即具有可塑性,能够应对多变的文化刺激,故而不同文化成员间的差异可完全归因于作用不同的社会条件,尤其个体发育早期的条件作用特别重要,该作用即由文化机制所决定。米德指出:“我们知道文化总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使一个新生儿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长。”a虽然米德这本书出版年代较早,但她关于文化与人格、性别、气质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作品研究亦有启发。
从人格这一层面来看,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其发育早期所处的文化环境,对于个人的人格塑造十分重要,不同的文化人格,进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学作品。以司马迁为例,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b这一段记录了司马迁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而这一时期的文化环境对于司马迁人格塑造的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在汉时属三辅地区,是当时关中核心地区。随着汉初政治的稳定,三辅以京畿之利、政治中心之便,聚集了王公世家、商贾富人、豪杰游侠等,构成了三辅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c 的特点,而这些人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他们召集门客、聚徒讲学的行为,必然会汇集各地文人前往,促使文化活动的繁荣,使得三辅地区亦成为汉时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带。自汉初,统治者在回顾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即把李斯的文化激进主张视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故西汉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在文化上主张兼收并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自由,形成了儒、法、道三家并兴的文化背景,三辅地区作为文化中心,受到的影响更甚。这一文化环境影响了司马迁自由不羁、包容广博的性格之形成,使得他的思维比较开放。反映于《史记》之撰写,则是其包容性很强,书中有一大批道德上不够“完美”的人物,如司马迁一边批评商鞅的刻薄寡恩,一边肯定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强盛的贡献;一边指出李斯的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一边赞赏他辅佐始皇卒成帝业的功绩;再如一边讲述蒙恬滥用民力、阿意兴功,一边指出他“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d。同时司马迁对于不同类型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以《游侠列传》为例,司马迁对游侠阶层基本呈一种维护态度,甚至为其鸣不平,而在同时期稍后的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则基本持一种否定、批判态度,班固对于司马迁的肯定态度也颇有不满,在《司马迁传》中即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残贫,此其所蔽也。”e司马迁热情歌颂的游侠,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这种差异,正反映出司马迁自由包容的心态。
司马迁游历时曾经过三楚地区,而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神巫性和浪漫性,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f,走遍楚地,深入地接触楚地文化。楚地的神巫传说、文学作品极富有浪漫主义精神,例如女娲、禹、舜、启、羲和、尧的传说,还有《楚辞》等文学作品,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司马迁《史记》的风格,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史记》所表现出的“把神话—史—现实打成一片”的特点,恰恰是“保存在楚文化中的那种和原始巫术、神话传说联系的热烈的浪漫主义精神”g,使得《史记》并不是以平铺直叙的方法照抄照搬,而是富有文学性。
再如之后其停留过的齐鲁地区,齐鲁文化是儒学发源地,刘跃进甚至指出“西汉儒学之兴,首倡于齐、鲁”h。齐鲁之学本质就是经学,如鲁学代表《榖梁春秋》,齊学代表《公羊春秋》,汉初济南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还有所传《鲁诗》 《齐诗》等。司马迁曾“讲业齐、鲁之都”,可见在这一地区停留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又“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i。 随武帝封禅再一次去过齐鲁地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更大。早年游历期间更是直接提到“观孔子之遗风”,足明儒学代表人物孔子于司马迁影响之巨大,《史记》三十世家中孔子是唯一以布衣身份进入该体例的,《孔子世家》更有:“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可谓至圣矣!” j本就对孔子心生向往的司马迁,通过在鲁地的实地走访,对孔子更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对于孔子作《春秋》明王道之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有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孝,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k除此,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儒林列传》 《十二诸侯年表》中亦表达了对孔子作《春秋》 的高度赞同。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与自己著《史记》联结起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l把《史记》定位于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传统,可见孔子以王道贬损现实政治的精神对司马迁产生了强烈的感召作用,而后《史记》中体现的王道德治的精神还有以史为鉴的现实批判精神都能看到《春秋》的影响。
同时因齐鲁地区临海的环境,有渔盐之利,历代重视经济,工商业发展较快,使得该地文化有开放务实的一面,这也使“开放包容”的司马迁能更为客观地看待商贾富人。《史记·货殖列传》中:“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认为当时的“百万富翁”是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又有:“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m说明当时经商者虽然没有公认的社会地位,然而实际上,他们已经能够以其实力左右一些事情,司马迁指出孔子名扬天下,子贡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社会现实,司马迁认可他们的地位和贡献,并给予他们相对客观公道的评价。
不论是司马迁的出生地,还是其青年游历停留过的三楚地区、江南地区、齐鲁地区,都对司马迁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文化刺激,并帮助其最终文化人格的形成。其著作《史记》中反映的文化倾向,正是司马迁在所处文化氛围中被塑造的结果外显。
从性别层面来看,米德指出男女的气质特性并非天生就有差异,而是在后期的社会设定中被不断塑造,如果一个社会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男子,这个社会就会主张全部男性应具备勇敢、好斗的气质,在之后社会分派的职业偏向就使这一点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最后把勇敢、蔑视懦弱、憎恨在危险和痛苦前畏缩退让等特质和态度视为男子的行事风格,而动辄公然表现怯懦、痛苦之类的特质和态度则被看成是女人气,至此不同性别的气质被标准化了。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女性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往往被要求守贞、贤惠温柔、顺从丈夫,甚至无才便是德;而男性则可以勇上沙场、参与科举、追求功名,还可以三妻四妾。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男性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难听到女性的声音,在文化作品中亦少有女性作者,因为女性鲜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并非完全没有受教育的女性,李清照即是宋代著名女词人,她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气质更多是一种柔婉之美的“女性特质”,像男词人辛弃疾作品中那种豪放气质在其作品中是见不到的。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化人格,很难否认没有当时社会文化下性别气质标准的影响塑造。而像这类受过教育且能留下“痕迹”的女性作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少数的,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塑造下的结果,女性不被期盼饱读诗书、考取功名,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下,女性作者的作品少于男性是必然结果,而非古代的文人女性不如男性。
正因女性文学书写者数量不多,了解古代女性多要通过男性的文学作品这一窗口,而出现在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很多是单一且负面的。如《诗经·大雅·瞻卯》就称周幽王之后褒姒是祸乱之首,《尚书·牧誓》则认为商王亡国是因为“惟妇言是用”n。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创造了一个几乎全是男性的世界,据学者沈加仁统计,“在这英侠传奇小说中提及人物总数共计七百八十七个”,细数《水浒传》中出现过的“女性大约有七十六位,其中具体展开描写的才有二十九人”,可真正称得上浓墨重彩描述的也只有六位女性,她们分别是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三位女英雄和杀夫通奸的潘金莲、私通和尚的潘巧云、不耐寂寞的阎婆惜三位“红杏出墙”的“品行不端”之女。这六位女性在文中的形象不是雄性化描述,就是丑化她们为荡妇。张恨水在《水浒人物论赞》中再三强调:“水浒写妇人,恒少予以善意”。《水浒传》全书女性形象塑造几乎都是为突出男性的忠义行径,处在一个附属的地位,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透露出的实际是男性的命运轨迹和价值取向,这都体现出古代男性作者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文化塑造下,内心对女性的期盼和控制。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俯视甚至轻蔑,积淀成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社会文化影响下的结果,亦非女性形象真正如此。
由上文可知,仅仅通过男性作者叙事去了解女性,是有失偏颇的。如关于武宣卞皇后的记载。王沈的《魏书》中“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还有其“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并主动以此约束外戚的相关记载。o而鱼豢的《魏略》中则记录了卞后“常对太祖怨言”“又欲太祖给其钱帛” 等为外戚争名利的事迹。p两书中关于卞后的形象塑造相去甚远,《魏书》中的卞后仁孝贤明,更具理想皇后的道德色彩,而《魏略》中的卞后则是一个具有私欲的普通人,毫无传统皇后威仪,后人很难判断哪个作者笔下的卞后更接近真实的卞后。同一人物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形象塑造尚有差别,可知作者因其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笔下不同的人物形象。同时更因在传统文化语境下,女性常被“边缘化”“扁平化”,应更为谨慎地判断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不可偏信一隅。
米德最后还提到了一类“离轨”者,他们与既定文化格格不入,致使这些个体对现有社会文化价值怀疑,并认为是不真实的、靠不住的,甚至是荒谬的,其社会顺应不良反应不归因于其天性和生理障礙,也不能归因于早期经验中的意外事物及精神不健全,而在其个体的内在性意向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裂隙。中国古代亦不乏离轨者,武则天即是典型,在武则天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传统男性气质。离轨者本身没有错,只是传统社会习惯于为男子和女子标定特有的潜能,而这实际上是相当一部分男女成员共有的潜能,从根本上与性别本身无关。中国古代男性中亦有离轨者,南唐后主李煜,志在山水,无意功名,其词中多男女情爱或伤春悲秋,体现了很多“女性”气质。李煜历来被称为亡国之君,多遭后世非议,现在看来,他的潜能并不在传统认为属于男性的统治、功业方面,想必在当时的性别气质约束下,李煜亦充满了痛苦与割裂感。即使在男性处优势地位的中国古代,规定的刻板性别气质对男性来说亦有不利。对于此类历史上的离轨者,评价应更多元和包容,不能单从传统性别分工的维度对其作品进行评价。
美国心理学家普汶在《人格心理学》里亦有与玛格丽特·米德类似的观点: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就像文化本身一样——也许不全然是不知不觉的,但确是无可指摘的。q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人格,进而产生各异的文化作品,而其中包含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正是作者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被塑造的结果,这是一个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过程,但绝不能把任何作品的出现视作理所当然。
a 〔美〕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bdfkl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册, 第3998—3999页,第4022页,第3998—3999页,第4003页,第4002页。
c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642页。
e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册,第2737—2738页。
g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h 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i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册,第1685页。
j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册,第2356页。
m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册,第3982页。
n 顾颉刚, 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册,第1098页。
op〔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157页,第158页。
q 〔美〕普汶:《人格心理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俞士玲.汉晋女德建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5] 普汶.人格心理学[M].台北: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6] 胡雅琴.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水浒传》女性形象[J].文化产业,2019 (13).
[7] 韩丽.《水浒传》女性形象分析——男权文化的解读[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 (4).
作 者: 胡喻文,西北師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至南北朝文学文献。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