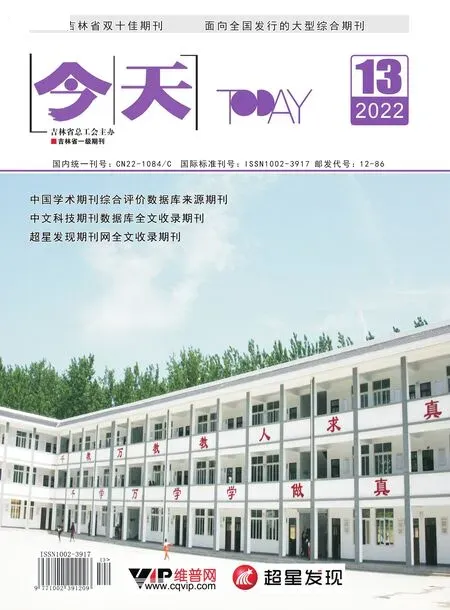绥米唢呐的传播主体与路径构建
2022-02-18明杰
明 杰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1.边陲景观与唢呐文化
自秦汉以来,陕北就属于边关要塞,这里既是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地带,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竞相争夺的生活区域,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这片古老土地金戈铁马的历史印记,也留下多方融合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要塞成为贫瘠浑厚的辽远天地,并造就了陕北人坚毅、隐忍的文化心理,继而外化为形式各异的文化符号,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传承已久的音乐,陕北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承载着黄土高原上一代代人的情感诉求和生命体悟,是古老民族的精神象征。
唢呐的管身由檀木或花梨木制作,顶端的芦苇芯子里是铜或银的芯子与其连接,末端再套上一个铜碗。在陕北的民歌文化里,唢呐吸取了大量的营养文化,唢呐乐曲得以丰富发展,在黄土高坡上埋下种子,然后生根发芽。绥德唢呐的传统曲目如《下江南》、《刮地风》,还有一大特色便是曲牌,如《摆场》中有碗碗腔的曲牌。独具风格的米脂唢呐同样拥有相当丰富的曲牌,如用物名字命名的《急毛猴》,来源于历史文化的《三通鼓》。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唢呐文化的发展与沉淀,极其独特的音色和气质,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之一。
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绥米唢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独具地域特色的陕北传统器乐,唢呐自金元时期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之后从宫廷到军中,再到民间,这样由庙堂到民间的传播过程为唢呐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元素,生成自洽的形式风格,成为研究陕北历史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2.绥米唢呐的传播主体
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群体作为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艺是文化传播的权威内容,其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他们的传承才能得到有效延续。陕北绥米的唢呐从明代戚家军时期算起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绥德县和米脂县地处大明王朝的九大军事边陲之一,朝廷为了保证中原人民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专门派重兵在这里把守。每当人民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士,便奏响唢呐以示庆祝,这样一来,唢呐也就逐步从军营走向民间。
2.1 早期的底层声音
绥米唢呐的传承群体在不同时代的身份和地位各有差别,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地位逐渐提升的过程。早期的唢呐创作主要是来自于底层群体,过去的陕北人都听闻唢呐是由汉唐宫廷被贬的可怜人流落到民间而传下来的,所以那时唢呐吹手的身份地位极其低下,多是一些残疾人,或者一些“半堂”的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吹唢呐便成了底层民众养家糊口的谋生方式。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一代代陕北人的精心培育和呵护下,唢呐手的地位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同时,唢呐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由过去几个人的小团队发展为今天几十人、几百人的大乐队,单曲团队联合演奏把独奏、合奏、联奏融为了一体。唢呐那激扬高亢的声响,源自于世世代代的黄土高原的沟壑里,还有漫天黄沙的风暴里。经过数百年的传承,绥米唢呐日渐为人们所熟知,并成为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2.2 走过低谷,迎来复兴
唢呐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跌到谷底,被列为“四旧”而禁止。那个时期的婚丧大事严禁吹手,数年内都很难听到这种传统的乐音,令当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少了诸多乐趣。等到“文革”一过去,陕北唢呐马上迎来了反弹的机会,在文化复兴的整体语境下,唢呐的从业者日渐增多,新人辈出,传承有序,有的专注于唢呐曲牌的整理研究,有的重新延续了师徒承继的传统方式,将其一代代地传播下去。日常生活中,一切喜庆场合无不用唢呐,这使得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在黄土高原上再次绽放,娇艳胜过往日。整体来看,这种复兴景象为绥米唢呐的发展积累了稳定而可观的传播主体,为日后唢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知识和技艺上为唢呐文化的传播拓展了更深远的空间。
2.3 唢呐乐手的当代强音
时至今日,陕北出色的唢呐吹手凭借精湛的演出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承贡献了独特的分量,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验。绥米的唢呐文化培养出冯光临,李长春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都是唢呐文化的“大能”,是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冯光临的一曲《保卫黄河》更是将唢呐的明亮银色以及热烈粗犷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李长春在文化的继承中对乐器的制作工艺加以改进,改革后制作出的唢呐声音更加洪亮,这需要对乐器演奏和手工技术都精通才能做到。在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无比重视的当下,唢呐乐手们有机会走出陕北,走过北京人民大会堂,走出国门,走进英国爱丁堡军乐节,夺得了百花奖,俨然已成为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品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传统文化珍贵遗产。
3.绥米唢呐的传播路径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实践层面的探寻方向,对于绥米唢呐而言,其承载的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应有的理论格局和基本认知,但是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如何拓展大众层面的接受范围,进而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这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建构才能实现,这种建构既包括理论建构,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定位,例如对传播范围的分层划定,对传播主体的原创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多元化传播渠道的主动尝试与理性认知。
3.1 理论建构
绥米唢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样态之一,这种文化形式连接着整个“乡土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乡民的精神世界,同时勾连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既关乎生产实践,也关乎情感认知,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土壤。绥米唢呐是深深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的音乐形式,从器具工艺到演奏技艺,从曲牌到吹奏风格,都体现出绥米唢呐的兼容并包之艺术品格,不管是经典的《水龙吟》《柳青娘》《绣金匾》,还是解放后的《沸腾的黄土地》《闹元宵》等唢呐曲牌,都体现出传统民间音乐与戏剧艺术、舞蹈艺术相结合的实践可能。所以,对于绥米唢呐传播路径的建构,应建基于文化的、历史的维度,对其进行基本的理论建构。
3.2 传播范围“下沉”
传播的目标范围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范围太大会导致泛化而缺乏深度,所以对于传播的范围最好有一个层级性的划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水平的接受群体,设定差异化的传播方式。虽然与早些年相比,绥米唢呐的传播度和知名度有了质的提升,能够走出陕北,走出国门,但从受众范围来看,依然局限于专业群体和一些为数不多的音乐爱好者,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范围的拓展和下沉是必要的。具体来讲,要尝试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使绥米唢呐与当下的美育相关联,从小培养对这种传统民间音乐的审美感知,在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可以有规律地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实践授课,让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走进中小学课堂,尽可能拓展受众范围,下沉得充分一些,传播的受众面相对就会广一些,传播效果也会相应提升。
3.3 传播主体的原创能力
绥米唢呐的传播速度以及范围之广与传播主体有着很大关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播主体大多来自民间,他们在技艺传承方面有着相对权威的话语权,但是相对而言创作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原创能力关乎到音乐的生命力,对于绥米唢呐而言,这种能力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对唢呐经典音乐的领悟力以及现代转化的能力,转化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保留唢呐本身的美学韵味,而不是单纯追求热度甚至流俗;其二,是在文化认知基础上产生的创造力,这种创作力基于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所以,传承群体的文化素养越来越重要;其三,“技”与“艺”的相辅相成,技术虽然是硬道理,但是人文情怀则是决定音乐品味和艺术格局的关键因素,所以,原创能力既需要“技”,也需要“艺”,两者融合方能使绥米唢呐成为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的翘楚。
3.4 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在数字化时代,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新媒体独有的互动参与的便捷性为一个话题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传播方式比传统的言传身教要高效得多,当然,传统方式的严谨与细微也是无法超越的。在当下媒介跨越的语境中,有效利用不同媒介的传播作用可以为绥米唢呐获取更多元、更高效的传播渠道。但同时也要避免在信息化、碎片化的现实中良莠不分,走向浅表化、娱乐化的审美,将传统唢呐文化的美学意蕴消耗殆尽。此外,对于不同传播渠道的选择,要符合唢呐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并且形成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将唢呐的实用价值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得到持久的关注,避免断层。
综上,唢呐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迭代,在传统中革新,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寻找适合的存在方式。音乐是有生命的,唢呐用音乐表达了人的思想感情,营造了其它乐器不能代替的审美体验,乐音与情感良相融合,鲜明地体现了民间风情,深化了传统音乐的当代价值,使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民间风俗一代代充满活力地延续下去。绥米唢呐作为陕北民间文化的品牌,其与众不同的演奏方式和美学质地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历代的传承人以及传承群体对于绥米唢呐的发展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他们的坚持和执守使得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获得了当代生命力,在其之后的发展中,如果注重传播路径的建构,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借助技术的支撑为绥米唢呐开拓更多元的传播渠道,使得这种民间传统音乐样式为更多的人所熟知,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