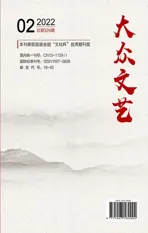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后启示录”风格游戏中的反乌托邦思想探析
——以《冰汽时代》为例
2022-02-18谈朱斐
谈朱斐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后启示录”(post apocalypse)作为一种特定的风格、主题与类型,最早出现于小说,之后逐渐延伸至电影领域,乃至电子游戏的世界中。这一概念来自“启示录”(apocalypse):“启示录”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揭露、显现、掀起面纱”。我们通常所说的“启示录”是一个宗教概念,指的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由基督教领袖圣约翰在流放期间创作。其中描述了“世界末日”与“最后的审判”的景象,旨在“指引世人改过忏悔”。从这一宗教典故而来,因此“启示录”风格的作品侧重于描述想象中“末日来临”的场景。
“二战”结束后,随着核问题、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日益凸显,以“后启示录”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在美国出现,其“故事背景主要设定在大灾难发生后的末日世界,重点关注浩劫之后的场景和生存者的思想与行动”。人们对于“末日”的想象不再局限于灾难来临时的瞬间,而是以“末日降临”为起点一直向后延伸,把笔墨用于浩劫之后的世界以及人类在末世中的求生与挣扎——“扭曲畸形的人性、废土求生的压力以及世界新法则的内容,正是后启示录风格的魅力所在。”简言之,“后启示录”风格的作品通常是某种“基于当前文明危机所造成的大灾难的延续性想象”。
在后启示录风格的电子游戏中,“反乌托邦”思想构成了游戏的精神内核:电子游戏通过视觉场景与互动体验的结合,生成了一个虚拟的“反乌托邦”世界。反乌托邦(英语为dystopia或anti-utopia,或译为恶托邦),一般被认为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词,如果说“乌托邦”是对一种理想中的完美社会的描绘,那么“反乌托邦”则是对未来生活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想象。
《冰汽时代》的主线故事发生于19世纪,随着“太阳的逐渐变暗”,气温逐渐下降,各国政府把目光放在了有着充足煤炭储量的北极。于是科学家们在北极修建了以煤炭驱动的能量塔,而玩家的任务是以首领的角色建立地球上最后一个城市——新伦敦,以保留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在这一设定下,“后启示录”风格作为游戏底色渗透进整个游戏之中。
因此,本文以《冰汽时代》为例,以此来探究“后启示录”风格游戏如何在游戏叙事和游戏机制的共同构建下,打开对末日的想象,将反乌托邦主旨表达并作用于玩家,进而实现社会批判的潜力。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游戏中的反乌托邦叙事是如何展开的;其次,游戏机制是如何实现社会制度的“游戏化”;最后,游戏给玩家带来了哪些批判的维度。
一、“反乌托邦”世界的展开:游戏中的反乌托邦叙事
在叙事学家眼中,游戏是可阅读和可解释的文本。下文根据叙事学的方法从“叙事结构、角色发展和情节等”分析《冰汽时代》后发现,游戏正是通过对灾难场景的书写展开了对于“反乌托邦”世界的叙事。
在《冰汽时代》中,游戏通过对于灾难场景的书写营造了“反乌托邦”世界的末日氛围。首先,游戏画面以及过场动画中的一系列视觉符号展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冰霜世界”。例如当玩家进入游戏的剧情《新家》时会有一段三分钟左右的动画,玩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原本色彩丰富的画面逐渐转为单调的黑白两色,并最终呈现为一种阴暗的“冷色”,这仿佛昭示着游戏中人类的命运被笼罩在冰雪的阴影下。通过对于“冰霜世界”的描绘,游戏中关于灾难场景的书写唤起了人类对于自然之力的原始恐惧,在末日来临之际,人类的无力与绝望营造了游戏中异常真实的末日氛围。
其次,游戏中“新伦敦”与“孤岛”的意象所勾连并且承载着“反乌托邦”叙事的展开。作为人类的最后希望之地,“新伦敦”就如同某种意义上的“孤岛”——冰雪与寒冷就像海水一般包围着整座城市,唯有依靠城市中心那唯一一座能量塔散发的蒸汽才使得它不被冰雪吞没。Nyman认为电子游戏的乌托邦主义最明显的借鉴方式之一便是重新使用传统背景——孤岛:岛屿几乎总是被视为独立的、孤立的实体,使它们成为想象中的乌托邦空间的主要背景。例如在《海岛大亨6》(2019)这一类型的模拟建造游戏中,“孤岛”作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点承载着理想世界的幻想,玩家可以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打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
但是在《冰汽时代》中“孤岛”这一意象突破了传统的“乌托邦”主题的限制,在“反乌托邦”思想下进行了重塑,这一重塑割裂了乌托邦与“孤岛”意象的旧有联系,将“反乌托邦”与“孤岛”并置以便于在一处封闭的空间中展开叙事:游戏中对于“新伦敦”的描绘并没有沿着“乌托邦”式的路径进行,而是逆流而上以一种残酷、绝望的“反乌托邦”式风格呈现出一座孤独的绝望之城,在灾难场景的书写中营造游戏出中的末日氛围。
二、“反乌托邦”世界的建构:社会制度的“游戏化”
游戏借助叙事向玩家打开了“反乌托邦”世界的大门,但是游戏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需要人们正确理解它的运行机制。因为游戏媒介的独特性与游戏的交互性有关,游戏的运行机制允许玩家“输入”一系列指令以重塑游戏世界,“换句话说,玩家可以凭借他们无法自由影响电影或小说的方式影响游戏世界。”在《冰汽时代》中,内嵌于游戏的组织逻辑、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创造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虚拟世界,游戏通过将现实制度或价值观重新安置在虚构的空间中,从而放大了这些问题来展示其内在的缺陷。下文对于《冰汽时代》的游戏机制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游戏通过对于社会运行的降维以及“选择导向”的玩法设定将社会制度进行了“游戏化”的处理,从而实现了“反乌托邦”世界的建构。
(一)社会运行的降维处理
《冰汽时代》中对于社会运行的降维处理则为社会制度的“游戏化”搭建起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使得“游戏化”的进程能够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可想而知,将现实世界原封不动的“移植”到游戏中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必须将社会运行的机制进行降维,所谓降维化的处理就是将现实中的社会系统拆解为独立的组成部分,并根据游戏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以及组合,以使其能够符合游戏的要求。
“反乌托邦”式的虚拟世界并不过分要求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冰汽时代》遵循基本的社会运行规律将原本庞大复杂的社会简化为资源、科技、生活、管理四个系统。这一闭环结构对于“生存”与“秩序”的强调,游戏试图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翻版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反常的“反乌托邦”式社会——它并不完整与合理,在末日之中某些并不需要的社会部门被舍弃了,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那些求生所必需的。“降维”处理后的游戏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合理性与现实性,但是在末日来临的背景设定下,游戏所追求的并非合理地复制现实,而是试图在这样的设定中放大并凸显可能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当社会系统中去除了那些与“生存”无关的枝蔓之后,人类将会面临怎样的一个社会。《冰汽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模板,而在它的模版之中我们所能看见的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残酷世界。
(二)玩家参与下的“选择导向”玩法
通过“选择导向”的玩法,游戏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玩家“选择”的自由,玩家能够根据个人的意愿进行决定游戏中某些事件的走向,所谓社会制度的“游戏化”也正是基于玩家的“选择”行为才得以最终实现,这也从而印证了“电子游戏是作为一门在叙事与游戏玩法之间进行妥协的艺术”,玩家作为游戏世界中的行动主体,游戏玩法保证了玩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的“输入”指令,而这些指令将会影响游戏中“反乌托邦”世界所呈现的最终模样。
游戏中“选择导向”玩法的关键在于游戏内的“数值系统”,它保证了游戏始终在一定的路径内进行而不至于偏离:游戏内存在“不满值”与“希望值”两个数值,玩家的选择会影响两个数值的增减,“不满值”过高或者“希望值”过低都会导致游戏失败。而“数值系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戏中的“法典”。法典的重要性在于其颁布会直接影响到“不满值”与“希望值”,例如玩家签署“应急班次”(要求工人24小时工作)或者“口粮减半”(将每人的食物配给减半)等法典时都会导致“不满值”增加,但是这些法律的签署能大大增加“生存”下去或者说“通关”的可能性,因此玩家始终在“求生”与民众“不满值”的增加这一矛盾中进行抉择。而游戏的吊诡之处在于玩家的目的本是为了文明的延续以及民众的生存,但是玩家不得不囿于游戏的机制从而签署那些过分的法典,这一矛盾使得玩家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亲手创造出了一个自己不愿看见的“反乌托邦”社会。
三、虚拟世界中的反思:游戏的文化批判维度
《冰汽时代》通过叙事与游戏机制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反乌托邦世界,同时后启示录游戏作为承载反乌托邦思想的容器,借助于这一思想的批判潜力延伸出许多可供讨论的批判维度,以此带给玩家关于“生存”以及秩序与自由之间界限的思考。
(一)对于“生存”意义的追问
“反乌托邦”思想作为后启示录游戏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于游戏对于“生存”意义的不断追问。在后启示录游戏中,游戏借助叙事与游戏机制让玩家暂时地离开现实世界,进入到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之中直面生存与死亡的抉择进而思考生存的意义:当现代文明被灾难所摧毁,尤其当人类面对危机似乎束手无策时,生存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冰汽时代》中的世界是无比残酷的,旧日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末日的废墟中也已经无法维系,所有的一切都屈服于生存的基本要求:为了维持城市的运作,所有人甚至是儿童都必须冒着严寒工作;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人们的口粮也可能会被添加木屑以增加饱腹感;为了给因冻伤而截肢的人移植器官,死者的遗体将一直在雪坑中保存而无法安葬。与此同时,随时有可能来袭的暴风雪在顷刻之间就能摧毁城市,能量塔也有可能会发生故障而无法运作。在这些危机面前,幸存者们的牺牲似乎毫无意义,失败看上去是唯一的结局,但游戏所传递给玩家的并未是消极的自我放弃,而是对于灾难的不妥协与抗争。尽管在游戏中并没有给出“生存”意义的确切答案,但是当幸存者们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并感叹道:“我又看到了太阳!”时,玩家们或许能够体会到生存的意义也许就在于生存本身,人类文明正是在毁灭与重建的宿命循环中延续到了今天。
(二)关于秩序与自由界限的思考
《冰汽时代》中的批判维度还体现于游戏对于秩序以及自由的思考,“选择导向”玩法下的“法典”系统似乎给予了玩家选择的权力,但是实际上游戏机制通过一种隐蔽而有力的方式将玩家整合到反乌托邦的虚拟世界中。这些有限的可能性限制了玩家的选择范围,不论玩家选择了“信仰”还是“秩序”,最终的法典都指向独裁与集权,因此随着玩家不断签署新的法典,秩序与自由的界限也在一步步模糊,游戏也借此引出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界限的问题。游戏借此给玩家设置了一个“陷阱”,所谓的“法典”系统似乎是玩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利器,其实这只是某种“金手指”一样的作弊手段。尤其是“最终法典”的签订,会让玩家几乎难以失败,只要签订了最终法典,游戏的通关难度就会降为最低。但是,那些依靠签订最终法典而通关的玩家在游戏结尾时将会遭到质问——“城市没有消亡,但这一切值得吗?”
这一质问使得某些玩家难以理解,但是回过头来可以发现“最终法典”就像是一瓶美味的毒药,游戏设计者并不鼓励玩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游戏,因为“最终法典”更像是游戏设计者为玩家所提供的一条捷径,而非正途。但事实上一旦玩家进入了游戏空间,所有玩家都符合反乌托邦设置的逻辑,并获得产生反乌托邦机制的亲密体验,玩家在游戏机制的作用下,难以避免地亲手创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由被绝对的秩序所取代,换来的是极权统治下的稳固社会。事实上,最终法典并未通关的必要条件,游戏给了玩家选择的权力。或许面对游戏通关后的评语,那些“取巧”的玩家也将重新思考自己在游戏中所做的选择——为了生存是否就可以选择打破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界限。
结论
本文通过对于《冰汽时代》这一典型的后启示录风格游戏在游戏叙事以及游戏机制的分析发现“反乌托邦”思想作为其精神内核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反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游戏中的反乌托邦世界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思与焦虑,游戏带给玩家并不是单纯的末日想象,更是一种对于现状的警醒:从启发玩家思考“生存”这一永恒命题的意义到关于“秩序”与“自由”的界限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电子游戏创造了一个可以呈现出反乌托邦无数维度的虚拟世界并且能够让玩家成为塑造反乌托邦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游戏的现实意义也正体现于游戏所能够引出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多维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