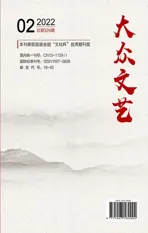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听郎朗《哥德堡变奏曲》
2022-02-18汪盛
汪 盛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太原 030000)
一、有感于郎朗谈“哥德堡”
2020年9月4日,郎朗的《哥德堡变奏曲》由德意志留声机(DG)唱片公司全球发行。包括2个版本、4张CD。第一个版本在巴赫工作多年、最后安葬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录制,弹到乐曲最后时,他潸然泪下。郎朗在巴赫的墓前献了一束花,坦诉着无限崇敬:“希望他能喜欢我的演奏,我尽力了”“感谢巴赫,我的学习是从巴赫开始的。不管我多喜欢肖邦和柴可夫斯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永远是我心里的前三位。巴赫是音乐之神,是我的重中之重”。第二个版本是在柏林一座静谧的录音棚中完成,这也是卡拉扬生前“御用”之处。在持续五天的录音期间,郎朗全神贯注地打磨作品,反复调整演奏状态直至甄选出最满意的一版。这也是他第一次以录音室和现场实况“双版本”模式发行全新专辑。
2020年3月1日是郎朗的首场“哥德堡变奏曲”音乐会,也是在录音之前的一次尝试,便于熟悉这匹“战马”的脾性,越来越有把握驯服好它。在德国威斯巴登接受的采访中,镜头下的他在后台的一些话语,一个小动作,一个呼吸,都难掩兴奋:“今天对我来说很特别,阔别三年回到这里,演绎这样一部伟大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是我梦想中的作品,原本是想在30岁生日时弹的,到七年以后才终于实现。现在梦想要成真了,但对我也是非常大的挑战。首先,它的长度是钢琴作品(实际上是羽管键琴作品)中最长的一首曲目,这场音乐会总用时接近2小时,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停顿。更是因为,当你从横向、纵向,各个维度不断地对它加以审视,可以从中学到太多的东西。它似乎给了人类一切,包括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所没有的。”尽管从10岁起就对《哥德堡变奏曲》情有独钟,是这些年每天都要练一会儿的曲目,也早就种下灌录唱片的愿望,但郎朗深知,这部作品的高深莫测,需要花很多功夫。直到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开始录音,因为“录不好的话,就把以前那么多年的基础一夜毁掉了,太危险了!”“这是一部‘高危’的作品,如果没弄明白巴洛克音乐是怎么回事,千万别录”。
现场观众座无虚席,演出圆满成功后,郎朗被山呼海啸的掌声包围。“我做到了,我实现了!”“我好累,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力气去吃饭,我从来没这么累过,精疲力竭。”郎朗捧着鲜花靠在墙上,随即和太太吉娜相拥,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他灌了一大瓶水,很久才能缓过来。像是仍沉浸于这场体验的历程中,回到现实后还有几分不可思议。他觉得演出结束的时候自己已和作品已经融为一体,不仅为其魅力迷醉,感到它无比浩瀚、无所不包,还会觉得自己是这部作品的拥有者之一,即成了能够驾驭这部作品的钢琴家之一。
在科隆,郎朗拜访了羽管键琴家安德雷斯•斯塔尔,在这六天的时光里做了有许多有益的讨论。“将柔版乐章做一些调整,使得听起来不那么冗长,比如变奏22。包括想象每一块地方像是哪种乐器,比如一些乐章更像是歌唱,甚至是合唱。这样大部头的作品每个部分都有从主题幻化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有些是独自在冥想,有些地方像是指挥给了个手势,从这里开始声乐进入。从整体律动来看,速度的把握和节奏的连接很重要。在力度上,要随时控制轻响的变化,尝试选择何种音色效果是最合理、最适当的。不必过多加入踏板,尽可能贴近最初的样子。每一个音符都要研究它,都需要考量作品的前后关系,慎重地对待。g小调柔版和卡农变奏15是最轻柔的,而有的地方需要大声地弹,甚至是钢琴可能弹出的最大音量。”大师的点化帮助他更贴近地理解、感受巴赫的思想情感,最终展示属于他个人的最本真的巴赫音乐。
在阿恩施塔特教堂,郎朗弹奏着巴赫曾经用过的管风琴,想象着这样一首作品最初是如何创作的。这架乐器四分之一都是1703年的原始的旧管子,那是巴赫的时代,他在羽管键琴和管风琴上基本上尝试遍了当时键盘上的全部技术,人们所能想到了,和想不到的,巴赫都试过。“它和当代管风琴是天壤之别。它的声音以及弹奏方式给我以很多灵感,让我知道哪个音是最主要的,也感受这个节奏和律动,感受巴洛克时代的演奏风格,有着无穷乐趣。我比从前更加了解巴洛克管风琴了,《哥德堡变奏曲》不仅是羽管键琴作品,也是用管风琴演奏的,当你知晓更多的背景后再回到作品中,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它们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我很珍视这个灵感,得到了很多启迪,拥有了许多有趣的新的想法,感觉自己离巴赫更接近了。”
“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咏叹调。一首如此美丽的作品,随着前八个小节的旋律缓缓流出,我们就深深被抓住,从一开始就是钢琴家与伟大的音乐之神巴赫之间的对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旋律,你不需要做太多,只需要跟着线条走,也就是低音的节拍。要弹出那种深度,你会感受到你的灵魂正在被建立起来,和低音的和声交融在一起,这里的低音带来一种上升的作用,而同时又把整个线条牢牢地保持住,给人一种由始至终的脚踏实地。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刻,随着曲子越来越艰难,随后是寂寞的到来……渐渐地,试图摆脱这个孤独的叙述,开始寻找出路。简单一点,后面还有整首曲子,精彩还在继续,后来将要走完一整段人生的旅程……当你弹完整首作品以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现主题),你已经经历了85分钟的美丽、挣扎、悲伤,而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你的身上,而且被赋予的新的意义。这时只需要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就像回放自己的记忆一样,跟从我们的本心,做最纯粹、最真诚的表达。”欣赏一部伟大的作品会令人高尚,不仅从神圣典雅的乐声中获得精神享受,还有对世界的宽恕和对自我的救赎。我们首先要感谢巴赫,尊重“和而不同”的声音,有益的讨论本身就如同多个声部的呼应与交织。当一切绚烂归于平淡,听众的心灵仿佛也被淘洗了一番,得到一种虔诚情感的召唤,这和作曲家最初以一段萨拉班德舞曲经妙手变幻的“疗愈”功能是一致的。尽管巴赫信仰的是上帝,但他的音乐能被我们东方人喜爱、推崇、理解,就是因为这种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与佛家讲的“慈悲”“放下”殊途同归。
郎朗心目中的巴赫也是生动有趣的:“我对巴赫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认为他就是非常宗教、与神灵们走得很近的一个人物,但后来发现大师的另一面,何尝不是炫技派?他演奏管风琴的时候,脚像跳舞一样。巴赫是巨能耍酷的,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为人处世有其灵活的一面。我总是在想,巴赫是不是有左右前后四个脑袋啊?就像李斯特,你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他和你我一样,不过一双手而已。”和记者的交谈中鲜明地透出他语言的幽默。然而,我们值得把自己的耳朵“交给”郎朗,在他的带领下走近巴赫音乐,还是因为他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古典音乐有其谱系,恰如大树的枝条绿叶之下,是‘根’,你要寻根,不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你弹得出色,就一定是最正确、最妥帖合适的。味道不对,或许白搭。”
郎朗还谈道:“对这部作品的和声、装饰音、音色、整体结构方面,我一直在学习。尤其是它有很多即兴的部分,实际上演奏巴赫有点类似爵士音乐,根音之外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上面加的,且每次在做反复的时候,可以完全不一样。巴赫从来没有非常清楚地写出力度,或是明确告诉你需要做什么表情……所以说,巴赫留给我们探索的艺术创作空间太大了,他的创作浓缩了人的一生。”
二、有感于郎朗弹“哥德堡”
郎朗试图用他朝圣般的虔诚信仰致敬巴赫,呈现这一部他研读了二十七年的旷世经典。从指尖下从容流淌出的主题,如此高贵而郑重的讲述,扣人心扉,直达灵魂,不疾不徐,娓娓道来。随后是千姿百态、包罗万象的变幻,魔法一般令人目眩神迷,广袤苍穹,灿烂星河,它们在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闪烁着光辉。那些音符颗粒透亮如水晶、圆润如珍珠的走句,倾泻而下,喷薄而出,充满着欢喜和希望,仿佛游心骋目于天马行空的浩瀚宇宙。而慢版段落亦能以极其深长的乐思线条贯穿其中,空灵缥缈,如诉如慕,又像海洋般深邃无垠,具有一种令人沉思之魅力。三首一组以卡农变奏作为小结,其音高差由同度逐渐扩展至九度,像两条始终彼此呼应、交流、对望的平行线,最终却归为统一,达到融为一体的和谐。而独自被划为一个部分的变奏25中情绪难以捉摸,你也许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可能是基督耶稣受难,又似乎是在悲悯人间的痛楚。也许每个人都会有想象,这是在表达着什么,但又无法说确切。这旋律叩人心扉,好像有千般愁绪,万种风情,却只有交织着美丽和痛楚的默默低吟。那黯淡纤弱,萧瑟如秋风,离尘出世,冷寂如寒冰,冥想式的半音进行预示着浪漫主义的源头。处理这样重要而艰深的乐段,他也能以整个身心的投入,达到忘我而难以自拔的境界,其中的哀痛和悲怆足以让听众身临其境。而紧随其后的变奏26立马要调整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从深谷中苦苦摸索一下子来到光芒耀眼的新天地,仅有几秒钟的调整时间,随即就是技巧高难的托卡塔,这是很大的挑战。在双手交叉目不暇接旋风般的激流中,暗礁涌动,险象丛生,处处都考验着演奏者的功力。郎朗的演绎不负众望,清晰、均匀而丝毫不见生硬。
爱乐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哥德堡”,对巴赫的解读以及对“Baroque Style”的认识,其乐评标准千万条。在得到业界总体肯定的同时,不乏争议声音,有人认为郎朗略显轻佻,不是巴赫,而是莫扎特。然公允而论郎朗的这张专辑堪称走心之作,没有流露半点炫耀式的浮夸,没有一丝油滑和玩世不恭。巴洛克的精神被呈现得悦耳又赏心,精致而深刻——它是崇高的,却不止于此,它生命的底色还是温暖的,充满向往的,有一种治愈力。当初凯瑟林伯爵期待的也是“既有安慰性质,又有愉悦气氛”的音乐,为自己带来内心的宁静。巴洛克时代乐器音色本身单薄,所以层次感并不能像现代这样丰富和立体,之前的钢琴家们做了很多模仿,试图在钢琴上弹出羽管键琴的效果。古尔德更醇厚,像一杯苦咖啡,尤其是1981版几乎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与被乐坛奉为圭臬的古尔德版本相比,郎朗的处理更加充满生命的活力。他将一些变奏中舞曲的性质表现得鲜明大胆,有一种小马驹儿的轻盈,飞扬,自信神气,潇洒华丽,容光焕发。连贯绵长的旋律部分仿佛是爱侣间轻柔缠绵的低语,点缀其中顽皮的装饰音跳脱如同林间松鼠,警觉,机动,成群结队,灵巧无比。低音声部则像牧羊犬细细的鼾声,满足,自在,松弛从容,又充满规律。郎朗的低声部弹得极其清晰,他能够在丰富的层次之下,始终维系着一种强大稳固的结构,管风琴音色式的坚实根音始终如支柱牢牢保持。在一些弹性节奏的处理上有个人的风格,但还是基本做到了变奏曲要求的形“散”而神“聚”,于多样性中孕育着统一。他曾说过,在面对净版乐谱很多“留白”的地方,必须要慎重,弹错了就是“灾难性的”。因此他探寻德国音乐传统,拜访了多位作曲、指挥,做了大量谱面之外的工作。在演奏时他对法式装饰音和意大利式装饰音的选择,以及运音法的采用都符合巴洛克审美原则。郎朗不仅触键控制能力极强,对踏板的把控比如柔音踏板的选择,以及保持音踏板配合制音踏板也十分注重,避免了声部线条的模糊和混乱。其完成度之高,让人感叹有时竟完全不像是一件乐器发出来的,而像是一个室内乐队。这种对古钢琴作品的再演绎,很好地体现出了现代钢琴更先进的技术手法和音响效果。他的精湛演奏彰显着21世纪的时代烙印,这是他音乐生涯中一个值得骄傲的里程碑,也会成为世界古典乐资料库中的宝贵记录。
品聆再三,愈发能感受到演奏者对作品的用心之深,以他极度的敏感细腻将音乐赋予了丰富的人生况味,同时,郎朗和巨匠巴赫,以及各位音乐家都有相通之处,汲取了多方养分。郎朗在2021年1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参考了古尔德、巴伦勃依姆、佩拉西亚、安德雷斯•斯塔尔等大师的演奏,并受过傅聪先生的指点。傅先生是将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精妙的人,如他曾说肖邦夜曲Op.62,No.2的结尾,就是“泪眼问花花不语”,波罗乃兹幻想曲op.61开头让人感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学习艺术的人,大多历经心随境转,执象而求,历尽磨难,百炼成钢,水穷云起,终得圆满。这些回响百年的旋律连接着神性和人性,跨越了宗教与俗世,沟通着东方与西方,也承载着历史与未来,仍将不断感动着全人类。“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一语道出了艺术与生命的交融、客体和情感的碰撞。众生芸芸如世间旅客,百态外壳的包裹下都掩着一片心灵花园,柔软的角落里住着孤独而私密的自我。也许只是在某一刻偶然裂开一丝缝隙,似“前世乡愁”般对某些旋律情有独钟。这前所未有,却早已契合灵魂的相遇,又怎能不让我们被瞬间击中,甚至被勾下泪来?
《哥德堡变奏曲》多像人的这一生哪,回望来时路,逶迤绵延,起落聚散,流连忘返。从出生到童年曾经的懵懂,在青春岁月遇到的那些人和事,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为人父母……走过一个个纪念日,送走一位位长辈离世,亲朋渐远,风华正茂的少年已是白发苍苍。或倚窗边孑然而坐,沉思往事忆前尘,感叹已成幻梦,悲辛交集,昏昏睡去;或二人相倚相偎听阵阵海浪拍打着沙滩,远处落霞苍茫,暮霭沉沉,近旁的爱人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一幅幅画面闪现,一幕幕场景回放之后,终于,主题再次出现,像疲惫地走向最后一站,只渴望舒缓疗愈,寂静简单。这次再现在时长上几乎多了一分钟,比起开头的平和与豁达,多了些领悟和透彻,也多了些不舍和温柔。仿佛寓意着告别前与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尽管颠沛流离,时过境迁,当初的心情宛在眼前,却又升华成了一份信念,一种情怀。朦朦胧胧间时空交错,亦真亦幻。这时的主人公,是对上帝慈爱崇敬感恩的巴赫,是对家族亲人充满眷恋的巴赫,也是你我……是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杨慎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也是弘一法师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