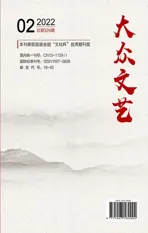断裂下的对抗与和解:英国移民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以《摇摆时光》和《白牙》为例
2022-02-18袁锟
袁 锟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457)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1975-)作为英国青年一代作家的代表,被推举为“种族、年轻、女性”的代言人。她的作品堪称“当代英国多元文化的代言书”,《白牙》(White Teeth,2000)和《摇摆时光》(Swing Time,2016)为其代表作。其作品当中的多元文化对话主题跨越了“种族、阶级、性别”,在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讨论有色移民的身份认知与建构走向。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多元文化对话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格局,但是自我和他者间的裂缝从未消失,作为“他者中的她者”,有色移民女性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意图与在主流文化体系中的“失语”与“缺席”之间形成矛盾。结合时代背景,本文以两部作品中两代移民女性故事为例,讨论英国黑人移民女性在建构主体性的道路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割裂与找寻,对英国文化的对抗与和解。文章在关注人物“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思考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困境和展望,讨论经由流动的、复合的“我”而进行的多元文化对话主题。
史密斯笔下的移民女性书写并非困在对黑人女性固有观念下,而是多层次展现身份建构的代际差异。史密斯透过世界上所有的肤色,展现共同拥有的“白牙”,也在“黑”“白”之间的不断“摇摆”中思考共同体构建的走向。
一、断裂下的抗争:一代移民的黑人母亲角色
《白牙》和《摇摆时光》中从母国来到英国的一代移民女性,在本族传统文化与本土英国文化的碰撞中,都在自我建构中走向极端:或是与文化之根彻底决裂,同化于英国文化;或是恪守母国文化,完全拒绝同化。无论走向哪个极端,其实质都是套上了种族主义枷锁,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Hedges Paul认为,“我是谁?可能是我们在不同时期都问过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身份问题从未远离。无论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族群、我的国家或我的世界,我们总是从不同层面的身份来思考。但是,正如我们将讨论的,这不仅仅是关于‘我是谁’或‘我们是谁’,而是关于‘你是谁’或‘他们是谁’。这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往往也被‘我们不是谁’所定义。”史密斯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建构,不仅关于她们本身,也为她们所处的环境所定义。
“她咧开嘴笑了,这一笑暴露了她的一个缺陷——整整一排上牙都不见了”,《白牙》中一代移民女性克拉拉以掉牙的形象出场,暗示着她与文化之根决裂的反抗。小说以“牙齿”为意象象征文化之根,在章节中以“出牙期”“牙根管”“臼齿”“犬齿”等牙科术语表现文化对话进行的不同状态。克拉拉的身份认知以“掉牙”为分界点,走向认知的两个极端。在此之前,克拉拉长着一口龅牙,服从母亲的安排,每日在学校散发教会传单,“为上帝服务”。在一次意外中摔掉牙齿后,克拉拉这位“脚穿中筒袜的黑种传教士”终于“身穿黄色喇叭裤和三角背心参加派对去了”,跳舞、抽大麻,并在派对上遇到了她的“救世主”:中年白人阿吉,从此“抛弃了教会和《圣经》上的一切教条”,完全同化于英国文化。与此相反的则是她的母亲霍藤丝,完全拒绝同化,坚守民族本真,仅仅因为克拉拉结婚对象的肤色原因,就直接将女儿逐出家门。
《摇摆时光》中“我”的母亲,是作品中一代移民女性代表。从这位牙买加裔黑人女性身上,几乎看不到本族文化之根的叶脉延展。作为经历过殖民的一代人,童年时期就经受着本族文化的苦难:读书就是罪罚。来到英国后,她将读书作为重塑自我的途径,终于成为英国下议院后座议员。她演讲着“我们拥有历史,拥有文化,拥有自己”,却在行为中忘记过去、割裂传统、否定真我;她教育“我”要像非洲的鸟“桑科法”(sankofa)一样回看过去,却警惕地防止家人“被拽回去”;她在政治参与中为族裔平等和女权意志努力抗争,却从未通过劳动自力更生,只能接受伴侣的经济庇护。“我”的母亲选择了与传统文化之根彻底决裂,将自我构建的理想完全寄托于西方知识体系,把原有的“自我”变为新的“他者”。
“所有这些角色都被置于英国伦敦的多元文化背景中,在那里,人物质疑他们的文化习俗和身份。”Thomas Matt认为,“《白牙》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寓言小说,主要人物被置于夸张的同化中”。比较《白牙》和《摇摆时光》两部作品中的第一代有色移民女性,有两个特点引起注意:其一,在文化认同上走向极端,无论是主动同化还是拒绝同化,都是单一选择,表象是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实质是套上了种族主义枷锁,导致身份认知迷失,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其二,都依靠“救世主”的拯救,或是依靠白人丈夫,或是寄希望于上帝,都把自己固化在“他者”的局限内,等待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宣判。因此,这种文化之根断裂下的抗争,注定是不彻底的反抗,其背后有着二战后特殊时代背景和意识深处种族记忆的深层原因。
移民是英国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通过对英国历史上的国籍法和移民法进行讨论,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对移民接收的心态演变,从而对一代移民进行“断裂下抗争”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再次被打破,英国发展走向也产生了重要转折,曾经的英帝国走向衰落,原有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大量有色移民如潮涌入。《1948年英国国籍法》规定“联邦公民”可以自由进入英国,在此之后,大量英属殖民地国家民众移居英国。然而在此开放的移民政策下,却充斥着来自英国本土的反移民态度。“尽管同属女王的臣民并被英国法律赋予同样的平等,但他们无论在外表还是习惯、宗教、文化上,都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于是在《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中,出现了收紧的移民政策规定:英联邦护照的持有者必须获得劳工部门签发的证明。1972年修订的移民法对政策进一步收紧,《1981年英国国籍法》更是从确认公民权的角度彻底限制移民。
以小说故事发生地英国伦敦为例。1851年,移民人口占伦敦人口的61.7%,但海外移民比例仅为1.7%。到1981年,伦敦的外国出生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18.2%,可见20世纪以来外国移民增长之快,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欧洲裔、亚洲裔、非洲裔、加勒比裔、地中海裔。Andrea Katherine在《当根不再重要》这一章节中表示:史密斯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虚构的、移民的和后移民的伦敦,在这个伦敦,英国多元文化既不新鲜也不值得注意,而只是一个“疲惫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下,相关政策也无法真正融合外来移民,缺失对流散族群权益的保障,一代移民女性虽然在地理空间上从边缘走向中心,但在社会群体中依旧是“他者”中的“她者”,凭借着非此即彼的决绝态度确立在社会中的身份归属感。
二、矛盾下的找寻与和解:二代移民的“混血女儿”身份
《白牙》和《摇摆时光》中在英国成长起来的二代移民女性,成长经历中充满着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作者在其身份建构中进行了混合性文化书写。她们经历了身份认知的迷失与文化之根的找寻,最终打破文化身份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在混杂的身份中融合,逐渐走向理性认同,成为多元复合的“我”,在文化对抗中达成和解。
对比两代移民的文化认同走向,可以看到史密斯的思考已不局限于某一种族或地区,身份问题让位于文化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文化多元逐渐更替二元对立,史密斯在作品中探索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复合的个体构成。“曾几何时,园丁们深信,自花授粉的植物比较可靠……如今,我们敢于冒险,高唱异花授粉的赞歌……”《白牙》中的艾丽,是继承了非洲卷发和一口龅牙的混血女儿,在学校被白人同学骂作“卷发肥臀的婊子”,渴望通过戴金属牙架、穿紧身内衣、拉直头发把自己从牙买加沙漏变成英格兰玫瑰。她模仿白人夏尔芬一家的英式做派,迫切地“要融入夏尔芬家,与他们成为一体,与自己家的混乱躯体分离,以转基因方式同另一个基因嵌合。一种独一无二的物种!新品种!”,早期阶段,艾丽完全将自我建构置于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在来到外祖母霍藤丝家后,艾丽探寻到了自家混血的历史,牙买加基因早已稀释,所谓的归属问题,好像成了一种假象,真实便是非此非彼、亦此亦彼。而她原以为具有纯粹英国味的夏尔芬一家,其实也是移民。对于二代移民而言,虽在英国的土壤中成长,但对英国的认知依旧作为自我认知的隐喻性表达存在于文化想象之中,二代移民尚需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完成自我认同、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班克斯认为:“在民主的多元文化国家当中,认同应该是复合的、变化的、重叠的和情景化的。”移民的文化认同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相比于《白牙》,《摇摆时光》中的混血女儿“我”更多了一丝文化认知上的理性色彩。“我”与不同文化有着情感联系,但同时又是文化归属中的局外人。在英国,“我”是黑人;在非洲,我却被视为白人。“我”没有热切融入英国文化的渴望,也没有主动寻根的冲动,哪怕身处西非部落最传统的面具舞蹈仪式“坎科冉”(Kankurang)中,也只想“逃离”(escape)。但当参观非洲当地的奴隶博物馆时,又感到“这就是我的遗产”。
对比两代移民女性,二代移民更多的突破了隐形的种族主义枷锁,打破二元对立局限,有着在“黑”“白”之间摇摆的选择,也充满对未来社会的多重想象。相比于只能在英国从事较低等工作的一代移民,成长在英国本土的二代移民有了更多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迅猛发展的交通和通讯也使得移民族群在居住国和母国之间往来更加便捷,从而可以拥有双重文化体验,进行更多文化认同思考,出现了向自我进发的“我是谁”主体觉醒。英国为推动种族关系平等而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也为流散族群的文化融入提供了社会土壤。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of 1965),是英国政府通过的第一部禁止在公共场合发生种族歧视的法案;1968年修订的《种族关系法》,禁止在住房、就业等领域产生种族歧视;《1976年种族关系法》规定任何认为自己受到种族歧视的个人都可以向地方法院起诉。在政策实施方面,英国也努力在经济、教育等方面推进移民融入当地。在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方面,威尔•金里卡认为,特别是在多民族聚集的国家中,教育具有培养双重认同的功能。“首先是在民族群体内部培养以共同语言和历史为依托的民族认同;继而培养能把国家中的所有民族群体结合起来的超民族认同。”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资本、文化、人才打破疆界快速流动,英国本土和各移民族裔间的融合更加混杂。21世纪伦敦的海外移民以青壮年为主,英国“全球性”呈现出新趋势。
关于族裔的身份认同上,威尔认为,族群认同是以血缘、地域、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而国家公民的认同感则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历史之上,通过国家政策和象征标志等,感受到自身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二代移民在双重的边缘体验之下,产生的身份认同是碎片化的、矛盾的。既对本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不深,又游离在英国主流文化体系之外,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双重断裂。散居族群只好选择建构一种新族性文化认同。对于二代移民女性而言,性别、爱情、婚姻等也是影响建构完整自我身份的重要因素,扎迪•史密斯笔下的“她们”,都产生过身份认同的困惑,也存在着两种文化间摇摆不定的身份迷思,或主动或被动地踏上文化寻根之旅,与“我是谁”的认同矛盾达成和解,构成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身份认知,展现跨越国家、种族、文化、性别的共同体意识。
对比两代移民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区别于一代移民女性的极端单一性身份构建,二代移民女性的身份构建更加复合多元。本文认为,形成变化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层面,共享的地域环境、互通的文化背景、多层次的交际联系,使在英国出生成长的二代移民女性能够拥有客观看待文化差异的可能性;二是政治层面,英国整体国际影响力衰减,相继颁布及修订的移民政策,也在逐步完善对已有移民的权利保护,从经济、教育等方面推进移民融入社会;三是经济层面,二战后英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大量有色移民劳动力的涌入容易激化种族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经济不断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方向转变,经济基础的夯实促进种族平等制度的完善,促进文化从单一孤立走向多元互通。
三、女性身份超越:文化困境与共同体想象
世界各族裔的文化根脉早已杂糅交织,史密斯将“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化,传递出她对文化分裂和全球化的焦虑。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扎迪•史密斯思考多元文化对话中的身份建构等方面的文化困境,同时也蕴含着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共同体展望。她的作品中有着漫长的历史跨度和对移民生活的全方位描述,在《白牙》和《摇摆时光》中,种族、肤色、阶级,都交织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多元文化对话。她借作品人物之口描绘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距今不太远的时代,到那时,根将变得无关紧要,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找出它,因为它太长、太盘根错节、埋得也太深了。”
《白牙》和《摇摆时光》由史密斯先后创作,两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对多元文化时代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在《白牙》结尾,作者借人物之口对被改写基因的“未来鼠”高喊“去吧,我的儿!”,展现出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期待和希望。《摇摆时光》则少了浪漫主义的乐观想象,多了对当前文化融合困境的现实思考,“我不愿相信非洲是欧洲的影子,仿佛没有欧洲支撑,非洲的一切都会在我手里化为灰烬。”然而非洲的事实却是:“这里,弱肉强食:形式各异的强(当地的、种族的、部落的、皇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经济的)欺凌形式各异的弱,无一例外,就连最小的女孩也不放过。可又有哪里不算这样呢?”通过作品中双重“他者”身份的女性书写,史密斯给读者展现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英国,有色移民女性的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之路。从作品中看到,人物的命运跨越了国家、地域、文化、种族、政治、经济,每个人都融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遭遇全球化困境,多元文化对话遭受质疑,文化之间能否实现平等对话、共存共荣?
当把目光移到作品《白牙》中孕育或初生的孩子们身上,也许可以察觉史密斯对共同体构建的复杂思绪。小说终章提道了孕育中的第三代移民:艾丽的胎儿。然而这是从孕育就无法分辨身份的一代——父亲既可能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迈勒特,也可能是“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的马吉德。然而他们是一对DNA相同的双胞胎兄弟,胎儿的身份也就注定无法精确定义。所谓“我是谁”的问题已经没有答案,也不再如此重要。在《摇摆时光》中,“我”震惊于“艾米能像订购日本限量手提包一样轻轻松松就买来一个宝宝,所有人都觉得合乎逻辑”,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面前,能否突破根深蒂固的传统二元对立呢?Katina Rogers认为,“尽管后殖民主义中的许多热门话题,如混合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常常被视为文化理想,但在《白牙》中,扎迪•史密斯拒绝延续这些话题,反而通过讽刺给这些主题增添了复杂性。对于希望歌颂混合性、世界主义等理论的作家来说,在伦敦这个聚集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昔日帝国中心似乎是一个理想的起点,但史密斯不是这样的作家。相反,她用更复杂的理解方式去描绘,史密斯的小说可以说是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在小说的最后,“我”的母亲临终前梦回家乡,真诚的嘱托“我”回到童年好友身边,照顾她的三个混血孩子。“她的孩子们围着她,大家都在跳舞”,也许史密斯在当前全球化困境下,仍然怀着共同体构建的美好憧憬。
结语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纪:褐色、黄色和白色人种,这是一个伟大的移民实验的世纪。”扎迪•史密斯是当代英国多元文化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史密斯也有着移民家庭背景。英格兰和牙买加混血的身份、伦敦和纽约轮换的居住地,她本人就是“多元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扎迪•史密斯为种族和女性代言,也通过作品为超越种族、性别、宗教的多元文化融合时代而努力。两代移民女性的故事,不仅展现了英国有色移民族群身份建构的历史走向,更讨论了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多元文化共生与共同体构建的美好愿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更应立足平等对话思维,秉持“和而不同”理念,促进文化和谐共存,推动文化星丛走向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