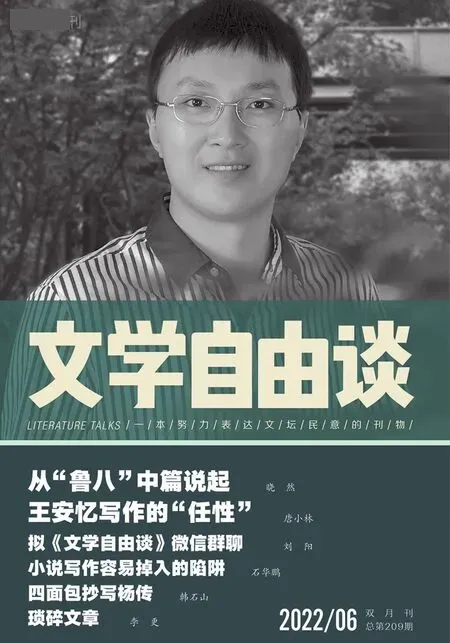路遥与《在中亚细亚草原》及其他
2022-02-17邢小利
□邢小利
一
五月的黄昏,我在二十七层楼上的书房,眺望着远山,听着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东京爱乐乐团演奏的,忽然想起了路遥。路遥当年,也喜欢《在中亚细亚草原》。而且他说,他非常喜欢。
想一想,路遥离去,已经三十年了。感觉,却是倏忽间的事。1992年11月,路遥因病去世。那一年,他还不满四十三岁。
路遥是喜欢音乐的。相当地喜欢。我听他说他喜欢《在中亚细亚草原》,是在王观胜那个宿办合一的半间屋里。
说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当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的情况。陕西作协大院,用的是1933年建的民国高级军官高桂滋的公馆。公馆大院占地十余亩,是请天津的建筑公司设计并建造的,前院是一座西式小楼,中院是花园,后院是三座相通相连的四合院,可称中西合璧。小楼所在的院子当年被称为“大楼院”,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曾在小楼东侧房里暂住十一天。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被称为一、二、三号院。四合院坐南向北,最初大门都开在北边街道。三个院落之间都有偏门相连,后来封了北边的大门,三个院落连成一体。四合院的平房全是砖木结构,院中铺满方形青砖,院中央植有花木。当年,《延河》杂志编辑部主要在东院,也就是一号院,王观胜就住在一号院东边平房北侧的屋子里;《小说评论》杂志编辑部是在中院,也就是二号院,我住在二号院北边的平房里。据史料记载,“西安事变”前夕,叶剑英前来西安会晤张学良时,中共中央曾派员和高桂滋进行联系,高桂滋同意中共代表住进自己的公馆,叶剑英就在二号院北房中住了近一个月。如此说来,我住的房子就是那时叶剑英住的房子。
话说当年路遥有一段时间,就住在二号院和三号院之间平房的北屋。他“早晨从中午开始”,常在几个院子里晃悠。我的房子坐北朝南,阳光好,门前有一株巨大的腊梅树,根深叶茂,几乎遮蔽了半个院子。树下有一个水泥台子的自来水管。路遥常常在外面街上买根黄瓜或两个西红柿,到水龙头下冲洗,洗完后就坐在我常年放在院子里的一个旧藤椅上,边吃边想着什么。白天我们多是打个招呼,晚上,我们经常聚在王观胜的房子里闲聊。
一个雪后的夜晚,王观胜敲我的门借录音机,说他刚从新疆旅行归来,带了不少新疆的音乐磁带,路遥要听。我就提着录音机和他一起去了他的半间屋。王观胜年轻的时候在新疆的北疆当过边防兵,对新疆情有独钟,一有机会,就往新疆跑。他是小说家,主要写中短篇小说,多写新疆、西部,如《放马天山》《各姿各雅》《汗腾格里》《喀拉米兰》《阴山鞑靼》《北方之北》等;五十岁以后,历时五年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遥远,遥远》,身后四年才出版,被《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称为“西部文明小说巨著”。他喜欢写孤胆硬汉“匹马西天”的故事,硬汉、骏马、女人、民歌、荒漠、草原、雪山,构成其小说的主要元素,是中国式的西部小说;艺术上讲究“惜墨如金”,作品风格独特,有“夸父逐日”的英雄情结,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征和抒情色彩。在王观胜温暖的小屋里,路遥、王观胜和我,围着火炉,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欣赏王观胜带回来的歌曲。歌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新疆好》《高原之歌》《冰山雪莲》《塔里木河》《草原之夜》等,距离现在都已很遥远,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但听起来既熟悉又亲切。路遥靠着椅背,仰着头,沉浸在歌曲的旋律中,不时随着歌曲唱起来。这些歌曲对路遥来说,或许有某种怀旧的意味,但更多的,是这些旋律符合他的心理、气质。路遥说他特别喜爱新疆和蒙古歌曲,那里边有一种深沉的感情。这个来自陕北黄土地的汉子,对雪山、大漠、草原这些能给人以严峻、辽阔的审美感受的自然景观,有一种天然的爱好是不奇怪的。他从严峻、忧郁、深沉而辽阔的旋律中,似乎听到了他的心灵的回声。
后来就聊起了音乐。王观胜提起话头,主要是路遥说,我听。
后来,路遥深情地聊起了陕北民歌。说到激动处,他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微闭着眼,不看我们,自顾自地用他浑厚的嗓音唱起来,《走三边》《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后来就聊起了外国音乐。路遥说,他喜欢老贝(贝多芬)的音乐,特别是“贝五”(《命运交响曲》)、“贝三”(《英雄交响曲》)。说到俄罗斯和苏联的音乐,路遥提到了苏联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提到了俄国作曲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听到这里,我有些惊讶。我喜欢听音乐,并以为我的音乐知识够丰富的,没有想到,路遥听的音乐以及关于音乐的知识也是丰富的。路遥谈到他对《在中亚细亚草原》的感受,王观胜也接了话;他对这部交响音画作品也很熟悉。王观胜于2009年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名字就叫《中央亚细亚的故事》,他在该书的前边还专门引用苏联专家的话,说明“中亚和中央亚细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他说:“中亚倾向于行政概念,专指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中央亚细亚的意思是:中部亚洲,范围更大一些,包括了中国西部的一部分。”(王观胜:《中央亚细亚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二天,天晴了。中午时分,阳光透进我在中院的北房,我在房子里用我的“先锋”音响放了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我的“先锋”当时买的是日本原装,电压还是110伏的,专门配了一个电压转换器才能放,音质非常好。记得当年,天津作家、《文学自由谈》编辑赵玫带着她的女儿若若来西安。她是应张艺谋团队之邀,为写作电影剧本《武则天》来西安,要到乾陵等地考察,我接待的她。她听了我的“先锋”音响,说“这个机器好”。《在中亚细亚草原》刚放了一会儿,我就看见路遥出现在中院,手里拿着一个蒸馍和一根葱,一边吃着,一边似乎在欣赏音乐。我出门请他进来听,他说就在院子里听。后来,他就靠在院子那个旧藤椅上,仰着脸,冬天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在中亚细亚草原》在院子里回荡。
《在中亚细亚草原》是一首交响音画,作曲家是十九世纪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波菲里耶维奇·鲍罗丁。鲍罗丁曾在这部作品的乐谱上注解道:“单调的,黄沙滚滚的中亚细亚草原上,传来了宁静的俄罗斯歌曲的奇妙旋律,接着听到渐渐走近的马匹和骆驼的脚步声,以及古老而忧郁的东方歌曲音调。一队土著的商队在俄罗斯军队的保护下,穿过广袤的草原和沙漠,又慢慢远去,俄罗斯歌曲与东方古老的歌曲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草原的上空长久地萦绕回荡,最后在草原上空逐渐消失。”
鲍罗丁的注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音画作品。
二
我是1988年4月底调到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后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到1992年11月路遥去世,算起来,我和路遥在一个单位共事约有四年半之久。路遥长我九岁。他是1976年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8月抽调、9月正式分配到当时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陕西文艺》(隶属当时的陕西省文化局)当编辑的。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延河》刊名。1978年4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恢复,《延河》归其主办,路遥也就一起过来。我来作协之前,和路遥也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我到作协陕西分会报到的当月,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其时,路遥已因《人生》等作品享誉全国。在作协大院,我和他之间,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工作上没有交集,私下里,彼此信得过,可以聊天,也可以合作。
路遥习惯晚上写作,白天——常常是中午或下午——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晃过来,然后懒懒地坐在我家门前的旧藤椅上,或休息,或若有所思。没事的时候,我也会拉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与他聊天。话题行云流水,国际形势,国内现实,下海,生活,书,音乐……但不谈单位的人与事,也很少谈当下的文学。有一次,聊到柳青。路遥视柳青为他的文学“教父”,他说了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做一件事,你认为有价值的事,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一定要经历全过程,你才会有深刻的体验,并对事情有全面的认识。”他这里所说,是从柳青当年为写作《创业史》下到长安县,住到皇甫村说起的。
1992年5月,中共咸阳市委宣传部组织邀请陕西五位著名作家写咸阳市的五位医疗、保健品生产方面的专家,号称“五神”。路遥选的采写对象是505企业的老总来辉武(来辉武当时的名气和影响最大),陈忠实写的是“神针”赵步长。路遥当时找我,要我与他合作写来辉武(其他四位作家都是自己写的),说他有些事情要办,抽不开身,让我先去采访,写出初稿,他再一起完成。我答应了。我当时在《小说评论》当编辑,并不很忙。经咸阳方面介绍与来辉武见面后,我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跟踪采访、了解、熟悉来辉武及其企业,写出了初稿,其中既有我的观察、印象和研究,也揉进了505企业给的一些材料。稿子写了一万多字,给了路遥。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文章初稿当时有没有起名字,总之,路遥看后,起了一个颇为大气的标题:东方新传奇。初稿是手写的,路遥在上面用笔对全文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和调整,有的地方还有充实——总之,经路遥之手最后完成。《东方新传奇》当年发表在全国很多报纸和杂志上(505企业配合这篇文章有广告赞助),记得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甚至《小说评论》这样的学术杂志也发表过。当时有人开玩笑,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路遥当年答应写这篇文章,我想,主要的还是缺钱。当年组织写作这篇报告文学的,是中共咸阳市委宣传部,组织方考虑的当然是宣传地方企业和人物,被写的对象考虑的是宣传本人和扩大企业的影响,而写作者,包括陈忠实在内(他后来跟我深入聊过他写关于赵步长报告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后来发生的故事),当年写作这样的报告文学,除了社会责任外,也考虑能挣一点高稿酬。1992年,陕西的作家普遍还很穷。那么当年的稿酬是多少呢?据我的记忆,写作报酬是由写作组织方付,大约每篇是500元吧(在那个年代也不算少)。
交稿以后,路遥于当年的8月6日乘刚开通的西安至延安的火车回陕北,刚去两天就病倒在延安。9月5日,重病中的路遥由延安乘火车回西安治疗,作协的几位同志和我一起到西安火车站接他。路遥还在延安的时候,我就把他病重的消息用电话告知来辉武。来辉武当时要去日本,他立即给路遥批了一笔医疗费,金额是6000元,要我从505企业代领后转给路遥。我后来到西京医院看望路遥时,告诉他这笔钱的来历,路遥说先放在我这里,他需要时会让人来取。我现在还保存着四张取款条子。第一张是张世晔的,条子上写:“张世晔在刑(邢注:应为邢)小利处拿走伍佰元交于路遥。”此条未注明日期。第二张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上写:“今领到小利处人民币(路遥存款)伍佰元正。”时间是9月29日。第三张条子上写:“小利:请将钱交远村处壹仟元,因他暂代我管理家务经济,此钱作为机动。”条子落款署名“路遥”,日期是“2/10”(10月2日)。我对路遥字体很熟悉,仔细辨认,认为条子用的是路遥的口气,但不是路遥写的,估计是路遥口授;而署名和日期确是路遥亲笔。第四张条子上写:“小莉(邢注:应为利):请将肆仟元正给远村,由远村转交金铮。”仔细看,条子上的这些字也不是路遥亲笔,但后边的署名“路遥”和日期“30/10”(10月30日),是路遥亲笔。后两张取款条子用的是印有“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红色字样的小号便笺。
由此,也可以见出路遥最后时刻的经济状况。
这四张条子涉及四个与路遥有关的人,需要说明一下。张世晔,笔名航宇,后著有《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远村,本名鲍世军,诗人,后来写有回忆文章《病中的路遥》。张世晔和远村都是陕北青年,他们当时都在作协陕西分会临时工作;远村是《延河》编辑部诗歌组的见习编辑,张世晔在作协陕西分会内部刊物《中外纪实文学》工作。由于他俩是陕北人,与路遥是老乡,平时与路遥关系也密切,路遥病重,他俩受作协陕西分会委托、安排,在西京医院看护病中的路遥。王天乐,是路遥的弟弟,在路遥诸兄弟中,他当年与路遥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金铮是路遥的挚友、铁哥们儿,当时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喜剧世界》杂志主编,路遥病重期间协调一些关系,照管路遥家。
三
作为作家的路遥和作为朋友的路遥,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去世后三十年来,有意无意,我会在心里反复琢磨这个人。
他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怎样的归纳才符合他的本真或者是全貌?
我觉得,“雄霸”这个词,也许更能概括我对他这个人整体的认识。路遥当然也有柔情甚至脆弱的一面,但如果要概括他性格的本质性特征,我觉得,“雄霸”可能更为接近——他有强烈的英雄气质,也有霸悍甚至霸道之气。在与路遥相处的日子,我能接触到的路遥的生活面,他都是风和日丽的、温和的,甚至是忧郁的;但我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以及了解到的一些材料(这些信息和材料都是真实的),又促使我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理解、去把握路遥。
反复掂量,“雄霸”,是这个词,才能反映我对路遥的整体认识。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只能谈出,但不可论证,也无法论证。
也许,“雄霸”是路遥作为男人的“外面”,“里面”则是作为个人和作家的温情、忧伤、孤独,以及寂寞。
我在陕西作协时的领导、路遥的同事和朋友刘成章(散文家,曾任陕西省出版总社副社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关于路遥有这样一些回忆和评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刘成章在延安歌舞团创作组(组长是诗人晓雷)做编剧,与闻频(时在延安地区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工作)等人“集体创作”,“虽然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成果,我们却可以得到生活补助,所以我们天天可以在东关饭馆吃饭,用闻频的话说,是‘享受共产主义好生活’。而闻频不忘他和路遥的延川之情,他深知路遥现在只是个穷学生(邢按:若按“穷学生”一说,路遥当时应该在延安大学读书),生活比我们艰苦多了,就时时关照着路遥,私下邀请路遥每天来这里改善伙食。”“路遥来吃饭的次数多了,免不了会出现些意见。一些人虽然不好当面说出,却故意对路遥视若无物,从不和他说一句话。而路遥,早已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在延川县曾经呼风唤雨,这时倒也能放下身段,只默默地吃着,一点也不介意。”“闻频和路遥从延川一路走来,到了省里之后,两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过去,闻频是领路人,路遥在后边跟着走;而现在,路遥成了长啸山林之虎,而闻频则成了喜欢在溪边饮水的一只麋鹿,还逗着蝴蝶玩儿。但他俩,以及我,还是要好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说是休戚与共。”“闻频和路遥的成就,很不一样。我以为,这是性格所致。路遥有雄心,能吃得下大苦,真像他所说,像牛一样劳动,残酷地折磨自己;而闻频则没有太大的目标,不求闻达,但求闲适。在现实生活中,路遥非常强势,他不管自己在组织里处于什么位置,总想而且差不多有能力掌控和左右一些重要活动。”“闻频呢,从来都不和别人争抢什么,是顺从强者的角色,和闻频共事,可以高枕无忧,心里不累,而他也因之烦恼不多,得以长寿,至今还如少年。”(刘成章:《闻频与路遥》,周至县泽明书院2022年9月2日网文)
刘成章(1937)、闻频(1940)、路遥(1949)三人年龄相差一些,但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后来又一起在陕西作协共事,是朋友,也是同事。刘成章在比较闻频和路遥时说的这些以事论人的话,应为知人之论。他认为“路遥有雄心”“非常强势”“成了长啸山林之虎”,似与我说的“雄霸”一词有相近之处。
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刘成章《闻频与路遥》一文后,我的大学同学强沫也转发了。他同时在前边加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其中一段叙述了他的一个经历:“1989年夏初,我与作家陈忠实老师从西安的钟楼东大街一路步行至建国路省作协院子,碰见作家路遥。那时候的路遥比陈忠实老师名气大得多。陈老师与路遥打了招呼,说了几句闲话。路遥一直躺在躺椅上,穿着白背心、大裤衩,扇着扇子,应酬了几句。这是我第一次见路遥。走过墙拐弯角儿,我问陈老师:这就是路遥?这人看着势咋这大的。”“势大”是强沫当时强烈的印象。这段经历,强沫以前曾给我讲过,我有笔记。他讲陈忠实“走过墙拐弯角儿”后,在强沫问“这人看着势咋这大的”时,陈忠实当时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原话不赘。
由强沫所述,一是可以见出他眼中的路遥确实有些“雄霸”之气,以致他感叹“这人看着势咋这大的”;二是也可以见出当年的路遥和陈忠实的关系,他们当然是同行、同事和朋友,但他们之间似乎也隐隐有那么一点“内在的紧张”。
陕西也称三秦(三秦的概念有两说,一说与历史有关,与项羽当年灭秦后裂地分封诸侯有关;一说是后来将陕西的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为“三秦”。这里用后一说)。陕西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三位大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又恰好分别来自陕北、关中、陕南,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代表性作品,也分别是叙写自己故乡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人与文的角度,称他们为“三秦三大家”。
“三秦三大家”的性格,各自不同。依我的接触与观察,结合阅读他们作品的印象,他们的作品也是他们性格与精神的映像,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路遥的性格总体是“雄霸”,陈忠实的性格是“正大”,贾平凹的性格是“鬼灵”。
2016年陈忠实去世后,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贾平凹写了一副挽联:“关中正大人物,文坛扛鼎角色。”这种挽联,一般来说,多少具有盖棺论定的意思。贾平凹对陈忠实其人的评定,用的也是“正大”二字;“关中”是指陈忠实是关中人,三秦中的关中。似乎也可以说,我与贾平凹对陈忠实性格为人的评定,乃“英雄所见略同”。
话再扯开来。我说陈忠实的性格是“正大”,并不是受贾平凹的影响,而是我的独立判断。2016年4月27日,也就是陈忠实去世前两天(陈于29日去世),陕西作协与西安石油大学在西安联合举办了王心剑的长篇小说《生民》研讨会,贾平凹等作家、评论家参加。我在会上发言说:“《生民》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关中平原原生态民生境遇和农业科技传播题材的小说。我把这个作品读了几遍之后,想到了一个词——题旨正大。小说的题材、立意、主题正大,主要人物性格也是正大,正而且大。这也是《生民》具有的独特性,少见,很震撼我。陕西几代作家写农村题材写得非常好,很难逾越。这部小说也写农村题材,但是整个视野和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写跟农业有关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个没人写过。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比如谷正春这个人物,关中平原有1934年创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发展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写这些人物有非常真实的历史依据。谷正春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代表,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精神是非常普遍的。谷正春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圣贤,光明正大的圣贤式人物。我们现在觉得做圣贤非常遥远,但是古代士人包括民国一些知识分子读书就是为了做圣贤。”(引自王心剑提供的《生民》研讨会发言纪要)
可以说,“正大”这个词语在陈忠实去世前后,分别由我和贾平凹用于不同对象。我现在再用“正大”来概括陈忠实,所以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说贾平凹的性格特征是“鬼灵”,也是一种印象式的概括,不可论证,无法论证。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其个体的原因,比如遗传和家庭;也有环境的原因,比如一方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乃至这个环境中深层的历史文化因素,所谓“集体无意识”。就大环境而言,路遥所处的陕北高原,历史上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叉互渗地带,游牧民族的铁蹄曾踏过这片土地,江南一些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宦人家也到过这里戍边。因此,路遥的性格中也多少体现了这种交叉互渗地带的历史文化特征,既有孙少安式的守护家园愿望,也有孙少平式的外出闯荡意识乃至“闯王”式的向外扩张特征。陈忠实所处的关中,是典型的平原、京畿与古都的结合地带。陈忠实说,他的家乡灞桥地区在汉唐时“为京畿之地,其后作为关中第一邑直到封建制度彻底瓦解”,封建王朝“在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陈忠实:《我说关中人——〈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序》,《陈忠实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这样的地方,也就是出“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地方,因此,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教授说陈忠实其人就是“朱先生”加“白嘉轩”,颇为中肯。其实,所谓“朱先生”加“白嘉轩”说的就是“关中正大人物”。贾平凹所处的商州,属于陕南秦岭山地,那里是中原儒家文化与楚巫文化的交叉互渗地带。贾平凹的“鬼灵”性格,颇能体现这块山地的地理文化特征。
评论家李建军也曾从地域文化的特点来分析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个人的精神气质。他说:“陕北的文化是一种我称之为‘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它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也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李建军在这里说的“高原型”“平原型”“山地型”精神气质,既道出了“三秦”的地理特点,也探讨了“三秦”人的精神气质;如果结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人的作品看,他的观点颇有让人深思的地方。而且,李建军在分析中所谈的路遥精神气质中的“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陈忠实精神气质中的“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贾平凹精神气质中的“轻飏、灵脱、善变”“有鬼巫气”,与我概括的路遥性格的“雄霸”、陈忠实性格的“正大”、贾平凹性格的“鬼灵”,虽不完全一样,但似乎也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
从时代背景看,陕西当代文学第一代的代表性人物,柯仲平、马健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戈壁舟、魏钢焰、李若冰、贺鸿钧等,都是从红色延安走出来的,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风景。第二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则大多是在党培养、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王晓新、李小巴、王蓬、冷梦等,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风景。时代洪流,大浪淘沙,惊回首,第一代多已谢世,第二代也纷纷凋零,文学的风景渐次变换。文学的山河重整,尚待来者与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