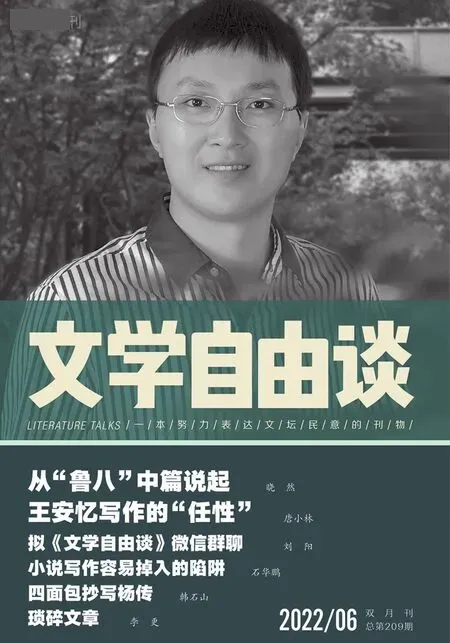当代小说经典化的一种路径考察
2022-02-17徐福伟
□徐福伟
《小说月报·大字版》有个“经典再读”专栏,每期选载一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小说。这些小说我以前零散读过,为了做好这个栏目,这次是系统阅读,时隔多年,有的甚至二十多年。在我经历了职业小说阅读工作的锤炼之后,对小说的审美要求明显提高了,并且对大量题材同质化、情感平淡化的作品深恶痛绝,有时甚至阅读得有点反胃;但当我重新阅读这些经典小说时,仍然会带给我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仍然会不自觉地被带入小说的叙事时空中,仍然会被人物的命运所感动,仍然会被温暖的细节所触动,虽然我反复告诫自己:注意,不要被带入进去,这是圈套,要保持理性的阅读。但是在这些经典小说面前,我对自己的告诫往往是徒劳的,我所依持的职业素养也是无效的。这些经典小说中就有刘醒龙的《凤凰琴》。
《凤凰琴》首发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小说月报》1992年第8期选载并荣获第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2010年被《小说月报》编选入《小说月报三十年》这一小说经典选本,时隔三十年后,《小说月报·大字版》又将其选入“经典再读”栏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说月报》参与并见证了《凤凰琴》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不能不说《小说月报》与刘醒龙,与《凤凰琴》有着极深的缘分。《小说月报》最先选载刘醒龙的小说是1989年第3期的《十八婶》,1993年第4期选载了《秋风醉了》,1996年第3期选载了《分享艰难》,等等。可以说,除了长篇小说,刘醒龙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都曾被《小说月报》选载过。
这促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经典小说为何能够永流传,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享受阅读所带来的有效情感慰藉。这是因为故事情节吗?是因为人物形象吗?是因为哲思内涵吗?是因为细节吗?似乎这些原因都有,但又似乎不全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着那个最为重要的着力点,无论是情节、人物、细节还是哲思都是从创作主体及文本本身出发的,但经典小说能够经典永流传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有很大的关系,从读者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应该是情感共鸣,也就是共情,这是阅读主体与创作主体在小说文本所构建的时空中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产生共同的情绪情感的深刻体验,这绝不是物理反应,而是有效的化学反应。因此我认为,情感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在,也是经典小说永留传的不二法门。我特别认同作家刘庆邦的那句话,“从本质上说,小说是情感之物。小说创作的原始动力来自情感,情感之美是小说之美的核心。我们衡量一篇小说是否动人,完美,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篇小说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挚、深厚、饱满。倘若一篇小说的情感是虚假的、肤浅的、苍白的,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就要求我们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以情动人,把情感作为小说的根本支撑。我们写小说的过程,就是挖掘、酝酿、调动、整理、表达感情的过程。”刘庆邦提出了“小说是情感之物”的论点,“缘情而作”的创作路径,他的创作实践也践行着这一标准。这与历史上刘勰之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李卓吾之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关系与印证。
诚然,考察当代小说经典化的路径不难发现,除了与读者共情之外,还依赖于文本本身所具有干预现实生活的能力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选刊、选本的“文选”促成路径,不断获奖的加深路径,影视化改编的“普罗大众”路径,等等。但这些路径的开发归根结底还是依赖于文本本身的情感因素,是否能够与最广大的读者“共情”。
小说是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尤其是带有普遍意义与价值的情感更是其所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是中国小说的典型传统与文脉,尤其是明清时更为注重“情理”。明代李渔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清代西湖钓叟则说:“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理也。”现代周作人说:“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当代钱谷融也曾说:“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经典小说《凤凰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情理”传统,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内化为情感体验,更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其并不是单纯着眼于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追求,而是更加注重对小说情感空间的开拓,执着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物理”和“世道人心”的深入开掘,强调情感的日常化、伦理化、传统化。这种对情感空间的深入开拓极易与读者产生共情的化学反应。《凤凰琴》就像是一个大的情感吸纳器,吸纳着一个人的情感,一群民办教师的情感,甚至一个时代的情感。从这个角度而言,刘醒龙是一位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与现实社会始终保持着“痛痒相关、甘苦与共的亲密关系”。刘醒龙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必须以笔为家,面对着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营造那笔尖大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此语道出了作家所坚守的“为人生”的五四文学传统以及关注“普遍人性”的价值立场。
《凤凰琴》的共情能力根源于“有意义”的小说品质。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叙事文体,尤其是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首先应该是能够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其次还应该“让读者能够一掬感动之泪、产生心灵的共鸣,而且还是最精确的社会-道德的地震仪,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苦难做出预报”,这是对哲思层面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有意义”。
韦斯坦因说,“‘意义’指文学作品中和问题或思想有关的方面,要言之,即作品的‘哲学-思想的主旨,道德的基础’方面”。小说是写给读者大众看的,总会不自觉地探求“意义”。布鲁克斯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生活的意义何在?要是一篇小说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望之至”。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由上述人的言论不难发现,小说一定要“有意义”,其指涉小说的思想、主旨,隶属于哲思层面,代表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一系列的看法和见解,此外,还关涉小说阅读者的代偿心理的需要。
《凤凰琴》以平实的笔调,书写两代乡村民办教师的悲欣命运故事,提炼出乡村民办教师身份转正这一有“意义”的社会话题并予以艺术呈现,从而让隐蔽在中国乡村角落里的四百万人之众的民办教师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持续关注。
《凤凰琴》中充斥着浓郁的情感因子,在界岭小学所形成的时空中悠扬飞翔。坐落在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只有五位民办老师,其中一位是因为急于参加转正考试而蹚冷水过河患病的明爱芬老师,还有一位是托舅舅万站长的关系想以此为跳板转正公办的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张英才,其余三位是界岭小学的教学主力团队,分别是余校长、副校长邓有梅、教导主任孙四海。正是这几位力量有限的民办教师保留住了乡村孩子们受教育的种子,并且在他们的细心呵护下发芽生根,甚至茁壮成长。教学环境和生存境况的恶劣,也是通过张英才这个外来者的叙事视角来呈现的,虽然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民办老师们依然在努力地维护着教育的尊严,兢兢业业地培养着学生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朝一日飞出大山。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民办教师的这种质朴的坚守与守护之爱温暖着大山里孩子们的心。如吹笛子升国旗的严肃场景,护送学生回家的场景,余校长家成为学生食堂兼宿舍的场景,等等,这些由温馨细节构成的场景无疑在强化着民办教师们身上善良质朴品格的坚守,这种坚守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的传统优秀文化因子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弘扬,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惑解也”的当代表达,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东方人伦情感的魅力。正是这种最为普通的司空见惯的情感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打动了人心,深化了人伦情感的认知。
诚然,界岭小学民办教师们的身上也各有缺点,并非传统意义上完美的师者形象,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其中最为重要的诉求就是期待转正名额,由民办教师转为带编制的公办教师。这种身份转换的诉求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重大目标,其迫切性、重要性可能是我们这些没有类似生活体验的人所无法体会的,但是这种身份转变的情感确是共通的,或许我们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在生活中遇到这种困境。这种身份的转正一方面是他们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一种心理情感上的社会身份认可的需要。他们虽然名义上是教师,但前面还有两个刺耳的字——“民办”,这种情感的困境并不是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老师,而是千千万万民办教师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这种困境由此导致了很多极端事件的发生,如明爱芬老师就是因为这种迫切的追求而葬送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张英才、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也都在暗中较劲,张英才甚至因看不惯他们的作风与行为而故意恶作剧捉弄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差点引发出大事件,邓有梅为此去偷树差点犯罪,孙四海无心送孩子回家差点导致孩子被狼群吃掉。是张英才这个关系户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变革的因子。作为外来的闯入者,张英才一方面担负着呈现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重任,另一方面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由对他们的隔膜,甚至厌恶,再到认同,甚至最终主动让出转正名额,决定在此扎根乡村教育事业,这种转变暗示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和解。正如刘醒龙所说,“我相信善能包容恶,并改造恶,这才是终极的大善境界。”
这里就涉及小说创作中关于情感的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了。《凤凰琴》一方面写出了乡村代课教师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共思的哲理,能够获得读者的普遍性共情,另一方面若对情感的处理极端化则会误入歧途。考察经典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情感的处理几乎都是在克制中走向和解的。这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能力和品质。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黑暗与光明、善良与邪恶、救赎与沉沦往往是并存的,作家们往往对人性之恶揭露得很顺手,而对人性之良善的书写则缺乏足够的信心。小说中的和解无疑关涉小说中的情感空间。就我观察而言,我觉得当下青年写作普遍存在拒绝和解的情感价值倾向,以为只有写的决绝、写得极端才能体现深刻,其实写好和解同样可以深刻。《凤凰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值得青年作家们关注并学习。舅舅万站长因为走婚姻的捷径而由民办老师转正成功但却陷于良心的谴责与婚姻泥沼中难以自拔,虽然买了凤凰琴送给明爱芬老师想以此赎罪,但最终事与愿违,成为了刺激明爱芬老师的导火索,最终在转正的问题上尊重了张英才和余校长们的意愿,将转正名额给了明爱芬老师,明爱芬老师才得以瞑目。舅舅和明爱芬都走向了情感的和解,虽然这代价是巨大的。余校长、邓有梅、孙四海,尤其是张英才,更是如此。张英才从进入界岭小学的第一天就梦想着转正,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张英才与环境、张英才与余校长他们、张英才与自身也达成了情感的和解。
《凤凰琴》创作至今已三十年了,还在被不断地经典化的过程之中。我每读一次感动一次,也许这就是经典永留传的不二法门:情感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在,而当下的许多小说恰恰丢失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