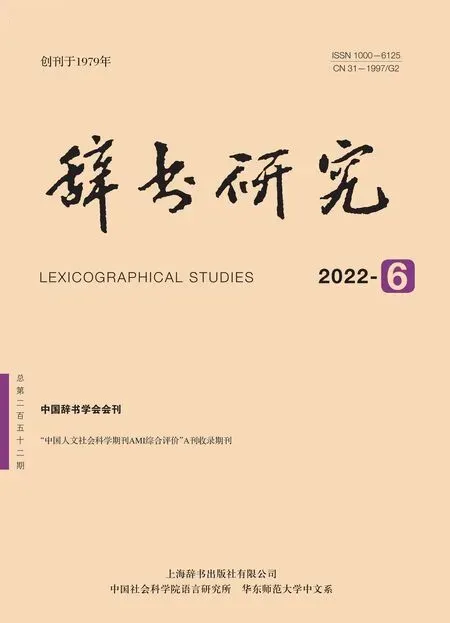再谈“吐蕃”的读音及其规范*
2022-02-17朱宏一
朱宏一
一、 引 言
“吐蕃”是七世纪在青藏高原兴起的古代藏族政权名,也是民族名、地名。关于“吐蕃”一词的读音到底读tǔfān还是tǔbō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争议不断。辞书中,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的《国语辞典》,“吐蕃”的注音是tǔfān;《辞海》《汉语大词典》则一直标为 tǔbō。《现代汉语词典》第 1—4 版标 tǔfān,第 5 版开始改标 tǔbō,这样“吐蕃”在辞书中的标音就完全统一了。就在大家以为“吐蕃”读音问题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之际,有好几位学者对“吐蕃”的读音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以《中国语文》2020年第2期发表的南小民、周志琴、孔凡秋《“吐蕃”音原》最引人关注。该文认为“吐蕃”应该读tǔfān,若“尊史从古”则应读作 tǔbiān 或 tǔbān;他们否认唐蕃会盟碑上“蕃—bod”的对音;认为“吐蕃”最初是“吐谷浑蕃部”或“吐谷浑的蕃国”的意思,“唐人所以用吐蕃二字称呼bod政权主要缘起吐谷浑:先简称吐谷浑为吐蕃,后阴差阳错将此简称施于bod政权”;认为历代文献中的“土波”“土钵”等“吐蕃”的译音词是“奇葩对音词”;否认立足当代、名从主人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审音原则,从而认为藏族人自己读“吐蕃”为tǔbō的观点“应是一个美丽错误”。该文转引自姚大力(2014)文章中提供的一则新材料尤值得注意,即元代蔡巴·贡嘎多吉用藏文写的《红史》里,提到它有关“唐-蕃史事”的叙述源于元初汉族译师胡将祖对《唐书·吐蕃传》的藏译,其中“吐蕃”的“蕃”依汉字读音译写,其今音应该读fān。
那么,“吐蕃”一词的读音到底读tǔbō还是tǔfān?这两个读音之间是什么关系?再往深里追究,“吐蕃”是汉语本有词还是音译词,“蕃”是否确实就是对音bod,汉语中“蕃”有没有今音读bō 的“薄波切”读音,这些问题也都需重新检讨。
笔者早年曾对吐蕃的读音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写成《“吐蕃”的读音》一文,发表在《语文建设》2001年第12期上。2018年,南小民等学者在《辞书研究》第5期发表《论“吐蕃”的辞书注音》一文与笔者商榷。本文是笔者对“吐蕃”读音若干疑难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也算是对南文的一个回应。
二、 “吐蕃”不是汉语本有词
“吐蕃”是汉语本有词还是音译词,这是上述问题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是音译词,则“吐蕃”的读音不难确定;如果是汉语本有词,那么“吐”“蕃”在汉语中的意义是什么?
南小民等(2020)坚持认为“吐蕃”是汉语本有词。他们指出:“吐蕃是上千年的汉语历史词而非藏语本有词。”“从词源看吐蕃的‘吐’当指吐谷浑,并非译音字。”认为“吐蕃”最初指“吐谷浑蕃部”,而且“早在bod政权首次通使唐朝之前汉地已简称吐谷浑为吐蕃”,“后阴差阳错将此简称施于bod政权”。果真如此吗?
其实南小民等学者文章中的这个观点和引证材料,基本都转引自姚远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的《唐以前“吐蕃”问题初探》。其引证材料主要有两个:第一,《太平寰宇记》中说的“叠州,……大业末陷入吐蕃”,又,《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资治通鉴·唐纪·高祖武德六年》:“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因吐蕃政权于634年才首次遣使唐朝并为汉人所知,隋末唐初吐蕃疆域尚远离叠州、芳州,所以姚远、南小民等学者认为这几个史料中的“吐蕃”不是“bod吐蕃政权”而是“吐谷浑蕃部”的意思。第二,《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二》:“则天长寿三年二月,西平大长公主还蕃。公主者,太宗族妹。贞观中,吐蕃遣使请婚,至是来朝,设归宁之礼焉。”因这个“西平长公主”就是出降吐谷浑的弘化公主,所以姚远、南小民等学者认为在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后,“还是有史官把公主出降国误为吐蕃,或者其眼中吐蕃即吐谷浑”。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两个证据的可靠性。
先看第一个证据。《新唐书·高祖本纪》和《资治通鉴·唐纪·高祖武德六年》在记载武德六年(623)四月侵陷芳州的民族这一问题上确实有异,前者说是“吐蕃”、后者说是“吐谷浑”。关于这个异文的辨析,史家是有定论的。著名吐谷浑史专家周伟洲(2017)186在《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中注释道:“据当时形势,《资治通鉴》所记为确。”当时形势就是:吐蕃还是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在位时期,吐蕃疆域还只限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土地肥沃的农业地区,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大可能侵陷大唐疆土;623年松赞干布才6岁,630年13岁的松赞干布才继承王位;而619年至634年的吐谷浑,是在不断遣使唐朝与之密切交往的同时,又乘唐政权初立之机,频繁扰犯唐西边的。所以,623年侵陷芳州的就是吐谷浑。而《太平寰宇记》中“大业末陷入吐蕃”的记载,在该书卷一百五十五陇右道六“叠州”:“隋初废州,以其地并隶同昌郡。大业末陷入吐蕃。唐武德二年,……上元元年,吐蕃入寇,密恭、丹岭二县杀掠并尽。”“大业末”是618年,如前所述,这时的吐蕃还不大可能侵陷大唐疆土势力;但“上元元年”是674年,这时的吐蕃正处于几可与大唐相抗衡的鼎盛时期,经常寇扰大唐边境。所以618年陷叠州的“吐蕃”,很可能是传抄之讹误,讹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与该记载相隔几行之后有“上元元年,吐蕃入寇”,而将前面本应是“大业末陷入吐谷浑”的误写为“大业末陷入吐蕃”了。因为叠州正处于吐谷浑东南边境,这时的吐谷浑常趁隋末社会大乱寇扰中原疆域。可见姚远、南小民等学者引证材料中的“吐蕃”都是“吐谷浑”,而非“吐谷浑的蕃部”,这是无疑义的。实际上,吐谷浑和他统治下的氐、羌各部,不是宗主(中央)与蕃属关系,而是统治者与臣属关系;吐谷浑的疆域主要就在今青海,比较小,其历史上并不存在“蕃部”,更不用说拥有“蕃国”了。
再看第二个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二》:“则天长寿三年二月,西平大长公主还蕃。公主者,太宗族妹。贞观中,吐蕃遣使请婚,至是来朝,设归宁之礼焉。”原注:“臣钦若等曰:‘按《唐书》,太宗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降吐蕃弄赞,至高宗永隆元年,公主卒。《实录》所载西平大长公主,检和亲事迹,未获。’”苏晋仁、萧鍊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注:“按《陇右金石志·大周西平公主墓志》: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之妻弘化公主,武周时赐姓武氏,改封西平长公主。则此‘吐蕃’乃‘吐谷浑’之讹,《实录》亦误,故王钦若检之不获也。”岑仲勉《唐史余沈·西平大长公主》认为《册府元龟》此条将“吐谷浑”误写成“吐蕃”,是因为“吐谷浑常省称吐浑,由吐浑而讹吐蕃,于文亦易”。夏鼐(1948)《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认为,这“盖涉上文‘还蕃’一语致误”。可见史家意见是一致的,即这个引证材料中的“吐蕃”是“吐谷浑”的讹写。南小民等学者(2020)却认为“或者其眼中吐蕃即吐谷浑”,这恐是主观臆测。因为《册府元龟》此条所据为《唐实录》,640年弘化公主出降吐谷浑王诺曷钵,641年文成公主出降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都是轰动朝野的大事;面对两年内的国家大事,作为朝廷实录史官怎么可能犯“其眼中吐蕃即吐谷浑”这种错误?可见姚远、南小民等学者的这条证据也站不住脚。
“吐蕃”的含义,不可能是“吐谷浑的蕃属/蕃部/蕃国”,也不可能是“吐谷浑的简称”,这还可以从“吐蕃”的异形词来证明。唐代时,“吐蕃”又写作“土蕃”。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婆罗吸摩补罗国》:“东接土蕃国。”陆贽曾亲历唐蕃关系,其《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云:“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土蕃。”李翱《进士策问》第二道:“土蕃之为中国忧也久矣,和亲赂遗之皆不足以来好息师。”唐代时,“吐蕃”还写作“土番”。如张鷟《朝野佥载》卷一:“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土番人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孟郊《新平歌送许问》:“早回儒士驾,莫饮土番河。”《元史·八思巴传》:“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吐蕃”还写作“土波”等,如元代王磐奉敕撰写的《拨思发行状》:“拨思发帝师,乃土波国人也。”无论“土蕃”“土番”还是“土波”,其前字都是“土”而不是“吐谷浑”的“吐”,这也都证明“吐蕃”的“吐”并非如南小民等学者(2020)所言是“吐谷浑”的意思。
退言之,如果吐蕃是“吐谷浑的简称”,也指bod政权,则大唐对这两个政权的称呼就混乱了。因为634年古藏族政权吐蕃就与唐朝往来,而吐谷浑329年建国直至663年才亡国(作为族名的“吐谷浑”仍存在)。那么,634—663年这近三十年间,唐朝用“吐蕃”这个称呼同时指称bod政权、吐谷浑?这显然不合情理。
而且从构词和语法功能看,“外族”“蕃属”义、读作fān的“蕃”,是从不单用作主语、宾语,也不用作民族名的;但“吐蕃”的“蕃”在古诗文和历史文献中常作为民族名单用,可做主语、宾语。这也证明“吐蕃”的“蕃”不读fān。
综上所述,“吐蕃”不是汉语本有词,其中的“吐”不是“吐谷浑”的意思,“蕃”也不是“蕃部、蕃国”的意思,不能读作fān。
三、 “吐蕃”是音译词
作为古藏族政权名、古地名和古民族名,“吐蕃”不是汉语本有词,那它就是外来词。“吐蕃”又称“蕃”,根据唐蕃会盟碑及敦煌石室中的藏汉对译材料,古藏族学者所著的《雍仲本教目录》《红史》《白史》等古藏族历史文献,《元史》《通制条格》等汉语历史文献中“吐蕃”的异形词,以及明清以来官方基于藏语语言调查的对译资料《西番译语》等可知,“吐蕃”是个音译词,今音应读作tǔbō。
藏汉对译材料,最著名的就是823年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唐蕃会盟碑。该碑正面盟辞中,“大蕃”出现3次、“蕃汉”4次、“蕃”1次、“蕃国”1次,其中的“蕃”均对应于bod。这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著名藏学家李方桂先生以及美国语言学家柯蔚南先生(2006)在《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中的结论,该书《碑铭文献词汇表》第316页记载有“Bod蕃,大蕃——古代西藏,吐蕃”“Bod chen-po大蕃——伟大的吐蕃国”“Bod-yul蕃国——吐蕃地域,吐蕃领土”“Bod-Rgya gnyis蕃汉二国——吐蕃和中国唐朝两国”。根据李、柯的研究,“蕃—bod”这个对音,也见于763年后不久立于布达拉宫南面的雪碑(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797年立于雅砻河谷吐蕃王室墓地附近琼结村一座桥上的琼结桥碑,以及赤德松赞统治时期(799?—815)立于拉萨西南若玛岗村的一座小寺附近的噶迥寺建寺碑。柯蔚南(2004)在该书《中译本序》中说,李方桂运用严谨的土著语言文本分析法,研究古藏语文献,“每一处细节,李方桂都会在原始材料允许的条件下对文献做尽可能详尽的校订,然后准备出精确注释、逐字翻译的译文。最后一步,也是非做不可的一步,是将文献全部音节目录汇编起来,其中的每一项都要加上注释,所有尚未确认的和尚未完全理解的词项都要清楚地标记出来”,“李方桂的研究在深度广度和分析说明的技巧上都无人能出其右”。可以说,李方桂先生的“bod—蕃”对音这一结论是相当可靠的。
无独有偶,在著名藏学家王尧(1982)的《吐蕃金石录》中,“蕃”也均对应于bod。该书第205页的英文内容简介中,“吐蕃”注音为Tubo。王尧(1986/2011)在其《〈红楼梦〉第63回的“土番”正解》一文中引敦煌石室所出的藏文写卷第1263号所列的藏汉对照的语词第7列有“bod特蕃”,第8列有“bod gyi btsan po土蕃天子”。这是787年吐蕃占领河湟瓜沙以后,在敦煌一带定居的藏人留下的手迹。王尧先生认为,其中“特蕃不过是土蕃的不同汉字译写而已”。此外,在王尧、陈践(1983)译注的《敦煌吐蕃文献选》的第48、第51—52页多处出现的“蕃苏”(bod sum),就是指“(吐)蕃化了的苏毗人”,其中“蕃”也是对音于bod。这些材料也都相当于为李方桂先生的结论做了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注脚。
“蕃”对音于bod,本是绝大多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藏学家的基本共识,但受到了郑张尚芳、巴桑的质疑和否认。郑张尚芳(2006)认为,“bod跟当时蕃字之音虽然声母相同,但韵母一为塞尾促声字,一为鼻尾平声字,也大不一样,因而不能说就对蕃字”,“甥国作Dbon之音正跟‘吐蕃’颇相近,或者即由此翻译是有可能的”。郑张尚芳的观点首先是基于他自己对“蕃(fān)”的中古拟音说的,这对讨论“吐蕃”的“蕃”字的读音来讲,就会因这个先入为主的做法而陷入循环论证。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王力先生(1939)在《论汉译地名人名的标准》一文中曾说过:“我们用汉字译欧音,并不能、亦不必求其声音完全相同”,“汉字没有代表纯辅音的,所以遇着西洋的纯辅音也不能译得很像”。王力先生虽讨论的是汉外翻译,实际上对汉藏对译来说也是如此。太纠结于尾音的相同与否,对对音来讲是过于苛求,也不符合实际。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汉文“巧克力(qiǎokèlì)”与英文chocolate尾音不同就否认二者的对音关系一样。根据李方桂、柯蔚南的研究,古西藏碑文中bod都对应于“蕃”,而dbon对应于“侄子、外甥”,dbon-zhang对应于“外甥与舅父”。又,根据唐大诏令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吐谷浑、奚、契丹、回纥与唐,均有甥舅关系。难道唐王朝也可以称吐谷浑、奚、契丹、回纥它们为“吐蕃”吗?实际上,除了古藏族政权,其他国并没有称“吐蕃”的。
巴桑(2020)认为,“如果一定要认为唐代吐蕃的蕃对音古代藏族地方政权自称的话,那么与其说蕃对音bod,不如说对音bon”。巴桑所言无史实根据。与“蕃”相对应,唐蕃会盟碑中只有bod,而没有bon。巴桑还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无轻唇音》“古读蕃如卞……卞、变、蕃皆同音”和王尧(1985/2011)《唐拨川郡王事迹考》为据,认为“吐蕃”的“蕃”唐音是pian,所以“蕃”应该对音bon。他对这两条材料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前者曲解了钱大昕的话,钱氏是说“甫烦切”(今音fān)的蕃古读如卞;后者误解了王尧先生的意思。兹将王尧(1985/2011)文中有关段落完整引述如下:“拨,古音作puat,与bod的发音最为切近。故赠以拨川君王,而且曰‘称故国’,说明这里的‘拨’即论弓仁的故国bod也。张说在碑文中用‘拨’而不用‘蕃’,可能是‘蕃’(pian)在对音上距bod较远,而且有蔑称之意。”很明显,王尧先生的意思是张说用“拨”来记古藏族政权,与bod音近;如果用“蕃”,其优势读音是“甫烦切”(中古拟音pian,今音fān),就与bod相去较远,就不能与bod对音。实际上如前所述,古藏语造诣极深的王尧先生是很明确地认为“蕃”对音于bod的。
“蕃—bod”对音,在藏族先哲用藏文写的《雍仲本教目录》《红史》《白史》等古藏族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格勒(2010)92《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认为,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最早的民族是“蕃”(bod)族。仁增·更珠札巴(1700—1769)《雍仲本教目录》载,藏族祖先悉补野蕃(spu-rgyal-bod)统治的地区就称蕃域索卡(bod-yul-sogska)。蔡巴·贡噶多杰(1309—1364)著《红史》(1988)中,称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约公元前二三百年)为蕃王(bod-kyi-rgal-po)。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Bacot,1873—1965)等编译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940)中,称聂赤赞普领导的部落为“蕃噶六牦牛部”[bod-ka-gyag-drug,ka是“白”的意思,所以格勒(2010)认为应该译作“白蕃六牦牛部”,因为“藏族自古崇信白牦牛为宝”]。根敦群培(1903—1951)著、法尊法师所译《白史》(2012)中说:“此复吾等此处,从最初时,在藏语中,即呼为‘博域’(bod-yul)。”
“蕃—bod”对音,在《西番译语》中也有反映。清乾隆年间四夷馆在充分的语言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汉藏对照双语教材《西番译语》分藏文(草书)、汉语词和藏文的汉字译写三部分,如(藏文)—番人(汉语词)—播迷夷(藏文的汉字译写,下同),—番僧—播板,—番汉—播儿甲,其中均用与“蕃”同音的“播”来译写(bod)。“蕃—bod”的对音,还反映在对现代本地人的读音调查结果上。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对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各地的藏语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语言调查,语言调查工作队队员将近百人,除汉族外,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区的藏族。调查的结果集中体现在著名藏学家、北京大学东语系金鹏教授(1983)主编的《藏语简志》中。《藏语简志》“概况”开篇就说:“藏族自称‘博巴’或(bod)‘博’”。其中均用与“蕃”同音的“博”来译写bod。
“蕃—bod”的对音,也反映在汉语历史文献中“蕃”或“吐蕃”的异形词上。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六·吐蕃》有“(吐蕃)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堤悉补野,因以为姓”;又《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有“(弃宗弄赞)自号吐蕃为宝髻”(“髻”是藏语“王”的意思),其《外臣部朝贡三》又有“宝王吐蕃赞府薨”。根据田晓岫(1997/2006),其中“悉补野”“宝”就是藏民自称“蕃”的不同译写。元王恽《玉堂嘉话》中有“吐蕃,土波”,指出“吐蕃”就是“土波”,即“蕃”读如“波”。1280年,元朝首任帝师八思巴(也写作“拔思婆”)去世,王磐奉敕撰写《拔思婆行状》,其中有“班弥达·拔思婆帝师,乃土波国人也”,而在宋濂(1310—1381)等奉敕撰写的《元史》中却是“八思巴,土番萨斯迦人也”,可见“土波”即“土番”亦即“吐蕃”。元代法典《通制条格》卷二十九僧道“汉僧红衣”条:“至元七年正月,尚书省。奏准圣旨条画内一款:‘汉儿和尚每,穿着土钵和尚红衣服,一迷地行有。’钦奉圣旨:‘那般着的拏者。’”可见“土钵”亦即“吐蕃”。综上,“蕃/番/波/钵”都读如bod。
在汉语中无对应字义,且有多种译写形式,这是汉语外来音译词的典型特征。“蕃”和“吐蕃”就是如此。如前所述,“蕃”又写作“拨、博”,“吐蕃”又写作“土蕃、土番、吐番、土波、特蕃”。这正说明了“蕃”和“吐蕃”的音译词性质。
音译词“蕃”的元语言,如前所述,自是古藏语bod。而bod在藏语中的意思,有不同的说法。王尧(1982)88推测“bod作为藏人自称,可能与农业生产有关”,但无文献记载。王忠(1958)《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格勒(2010)认为,作为藏人自称的bod源于本教(也写作“苯教”),根据本教史《格言宝库》,西藏未有王之前已有本教。bod最初指本教,后bod用于指古藏族名及古藏族政权,同时另新造俗字bon指本教。
音译词“吐蕃”的元语言,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认为是“大蕃”的意思,但“吐蕃”一词至少在634年就出现了,“大蕃”一词在安史之乱后吐蕃强盛后才出现;在唐蕃会盟碑中只用“大蕃”而并不堂而皇之地用之前惯常的称呼“吐蕃”;唐高宗李治《令举猛士敕》有“蕞尔(按:蕞尔,形容小)吐蕃,僻居遐裔”句,如果“吐蕃”是“大蕃”的意思,则此文句逻辑不通。可见,认为“吐蕃”是“大蕃”的意思不符合史实。
有的认为“吐蕃”是“上蕃”(stod-bod)的意思,但吐蕃的发祥地山南及其王都逻些其实属于中部,故也不符合事实。
多数学者认为“吐蕃”源于突厥语称呼古藏族人的tüpöt一词:在古突厥语中,u、ü不分,o、ö 常混淆,b、p 也往往不分,tüpöt是突厥语 tüp(宗族)和藏语 bod(蕃)的结合体,义为“蕃部族”,汉语从突厥语音译为吐蕃。但也有人认为tüpöt不符合突厥语构词规律;按构词规律,“蕃部族”突厥语应为pöt-tüp。常凤玄(1989)认为,鉴于“土蕃(吐蕃)”一词在唐初玄奘西天取经时已有记录,载于《大唐西域记》,“吐蕃”一词应是源于西域,传之突厥,再传入唐朝的。张云(1990)认为,吐蕃与西域之间,越过昆仑山、阿尔金山进行交往的道路,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经存在,囊日松赞曾派兵入据西域、统治突厥人,后丧失,但在松赞干布时又收抚、恢复了吐蕃对突厥某些地区的统治。可见吐蕃与突厥的联系比唐蕃间的往来要早很多。又据王钟翰(2011)《中国民族史》,突厥自隋朝到唐朝,都与中原王朝联系紧密;在唐朝,从王公贵族到将领,都有突厥族人,突厥族是各少数民族在唐朝中任职层次最高、人数最多的,融入中原社会也是最广泛的,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最大。所以,唐朝根据突厥语称呼古藏族人的tüpöt而译作“吐蕃”,顺理成章。
地名译写的基本原则是音译,且名从主人。所以亲属语言对“吐蕃”的译写是研究“吐蕃”读音的重要资料。说唐朝根据突厥语称呼古藏族人的tüpöt而译作“吐蕃”,能很好地解释“吐蕃”在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满语中的写法。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族的主要来源是突厥人的后裔,维吾尔文古籍中“吐蕃”写作Tübüt、Tibät、Tibet等;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成吉思汗西征时才开始“用畏兀尔字母记录蒙古语”,“吐蕃”在元代蒙文史料中写作Tibet;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人的主要来源女真人曾长期受蒙古人统治,所以“吐蕃”在清代文献中写作“图伯特”或“土伯特”等。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既可用于唐朝或他族对古藏族政权、古藏族的称呼,也可用于古藏族对自己民族或政权的自称。如弃隶蹜赞《请修好表》:“又西头张元表将兵打外甥百姓,又李知古亦将兵打外甥百姓。既缘如此违誓失信,所以吐蕃遂发兵马。”又弃隶蹜赞《请约和好书》:“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元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册府元龟·外臣部》“和亲二”:“吐蕃赞普献书曰:‘……且汉与吐蕃,俱是大国,又复先来宿亲,自合同和,天下苍生,悉皆快活。’”《资治通鉴·唐纪》:“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泚,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着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以上例子也证明,音译词“吐蕃”的“蕃”,与藏族一直自称的“蕃(bod)”,是音义皆同的,是同一个“蕃”。
反对“吐蕃”为音译词、反对吐蕃今音读tǔbō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古汉语字书中“蕃”没有今音为bō的读音。其实并非如此,举证如下: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蕃维司徒”,其中“蕃”是姓氏,也作番,齐诗作皮,韩诗作繁(按:此繁为姓,《广韵》“薄波切”),即“蕃”读如“姓氏”义的“繁”。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00卷汉书卷一“司徒皮”注:“师古曰:《诗》所谓蕃维司徒是也。蕃音婆,古读皮如婆。”(又见钱大昕《三史拾遗》)
又,《礼记·明堂位》:“周人黄马,蕃鬣。”王引之《经义述闻》:“蕃,读若皤。字又作繁。《尔雅·释畜》:青骊繁鬣,騥。”皤,义为“白”。“繁”的“皤,白”义,又见《广雅疏证》《故训汇纂》《汉语大字典》。
又,唐令狐楚《年少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钱锺书选唐诗》钱锺书注:“蕃,通‘皤’,白色。”
又,初唐“药王”孙思邈(581—682)辑《银海精微》卷一“久患虚冷”方中有中药“薄荷”,而在其名著《千金方》中则将“薄荷”写作“蕃荷”。唐李含光《本草音义》“蕃荷菜”注:“蕃音鄱”。值得注意的是,孙思邈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其著作中“薄荷”又写作“蕃荷”,说明“蕃”读如“薄”(《集韵》白各切)的这个音是当时标准语地区的一个读音。“薄荷”在华佗《中藏经》卷下“地黄煎解劳、生肌肉,进食活血养气”方中即有“薄荷汁一升”的用例。“薄荷”在西汉扬雄《甘泉赋》中作茇葀(guò),晋吕忱《字林》作茇䒷(guò)。茇,《广韵》蒲拨切。在《玉篇》中,“薄荷”写作“蔢(hè)”。蔢,《玉篇》傍个切,《集韵》步卧切。
由上述材料可知,“蕃”的古音同“繁、皤、婆、鄱”,在上古是並母歌部,《广韵》是“薄波切”。皤,《广韵》另有“博禾切”,今音读bō。“鄱”主要用于地名江西鄱阳。据《辞海》,江西鄱阳县秦代叫番县,西汉改名番阳,东汉始作鄱阳,1957年改名波阳。“鄱阳”之所以要改为“波阳”,就是因为:“鄱”本音如“婆”,属並母[b],浊音清化后,“鄱”在普通话中读 [p‘],但是与鄱阳当地人一直读[b]的语音实际不同,影响交流;按照“名从主人”的语音规范原则,又考虑到普通话中已经没有浊音[b]了,只得改找一个相近的声母即不送气清音[p]的字来描写。因此在1957年将“鄱阳”改为“波阳”。(谢仁友 2003)而为体现历史文化的传承,2003年波阳复改回鄱阳。可见,“蕃/鄱”在方言中至今仍有bō音。“婆”也一样。
此外,如前所述,“吐蕃”也写作“吐番”“土波”“土钵”,后三者都是“吐蕃”的异形词,异形词必同音同义。所以,“蕃”有“读如番(博禾切)/波/钵”的音。同理,《西番译语》中bod(蕃)译写作“播”;1935年底,红军长征时在西康甘孜建立的甘孜博巴(蕃人,藏民)政府,以“博”译写藏人自称。这也说明“蕃”读如“播/博”。
可见,汉语中“蕃”有“博禾切”或“薄波切”的音,所以唐蕃会盟碑用“蕃”对译bod。这个对译相当巧妙,因为蕃是个多音字,读“博禾切”时可同“皤”,有“白色”义,而藏人崇尚白色;“蕃”读“甫烦切”时通“藩”,有“蕃属”义,又暗合大唐“君王天下”的心理。
关于“蕃—bod”对音,还应注意:一是地名读音的保守性、存古性。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必赘述。所以唐蕃会盟碑bod以“蕃”对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藏语大规模调查时,bod对音“博”,读音完全一样。二是字典“蕃”未收“博禾切”或“薄波切”的音,其实也并不奇怪。字典收录单字和单字音的多少,受字典性质、规模、编者的学识以及当时汉字音义考释成果等诸多因素影响。《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噶gá伦”的“噶”gá音、“伽马”的“伽”gā 音,第6版中“戛纳”的“戛”gā 音,均未见于古代字书反切,《康熙字典》没有,甚至《国语辞典》也没有,但《现代汉语词典》中却有;“怼”的duǐ 音(义同“㨃”,用强硬的话顶撞、反驳别人),也不见于以往辞书,202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编写的《新编学生词典》则收录了。三是为什么《元史》《通制条格》中用“土波”“土钵”而不用“吐蕃”?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译音词词无定形,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蕃字是多音字(吐也是多音字),而且该字的优势语音是fān,与“吐蕃”的“蕃”的真实读音bō 相距甚远,所以作者另用两个常用的单音字“土”“波/钵”记音。
综上所述,“蕃”源自藏语,藏民至今读“蕃”为“bod(博)”。“吐蕃”是汉语中的音译词,今音应该读tǔbō。从来源上看,“吐蕃”一词是由突厥语传入唐朝的。
四、 吐蕃的正音和俗读音
认为“吐蕃”的蕃读fān的,有几条似乎很过硬的证据:
一是唐贾岛等所作诗歌中“吐蕃”的“蕃”押元韵。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中有“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何时霖岁旱,早晚雪邦冤”句,其中“蕃”与“魂、村、喧、冤、言”等字押韵。之后的元代耶律楚材《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明代欧大任《送胡宪使伯贤赴滇中六首》(之四),清代单隆周《秋怀十四》、沈德符《令公来》、彭而述《爨碑曲》、金甡《寄素山一百四十韵》,这些诗中“吐蕃”的“蕃”押韵情况也是如此。
二是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唐纪十一·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和“唐纪二十七·通鉴卷二百一十一”中,“吐蕃”下均有“(蕃)方烦切”的音注。
三是元蔡巴·贡嘎多吉用藏文写的《红史》里提到,它有关“唐—蕃史事”的叙述源于元初汉族译师胡将祖对《唐书·吐蕃传》的藏译,其中“吐蕃”依汉文读音译写,其藏文的拉丁文转写为thu hyen [ 综上,如果依据“吐蕃”在诗词中押元韵的情况等事实,“吐蕃”的“蕃”今音应该读fān;但如果依据“吐蕃”的“蕃”在《唐蕃会盟碑》等古西藏碑文中的汉藏对音等事实,则吐蕃的“蕃”今音应该读bō。那么,“吐蕃”为什么还有tufān这个读音,它和“吐蕃”的另一个音tubō 之间的关系如何? “吐蕃”的“蕃”有人读fān音的原因,除了fān是“蕃”的强势读音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吐蕃(bō)”也是“蕃(fān)”,是当时的外族,唐王朝域外的少数民族。它也是“八蕃”之一。《新唐书·西域列传》:“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 “吐蕃”也是西蕃(fān)之一。西蕃本指蕃居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或西方各国及其地区,如魏徵《隋书》卷六十七:“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高昌王、伊吾设等西蕃二十七国,谒于道左。”《旧唐书·王缙传》:“每西蕃入寇,必令韦僧讲诵仁王经以攘寇虏。”有时在“西蕃”后加上少数民族的名称,如《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武德三年正月三月,西蕃突厥叶获可汗遣使朝贡。”在唐代,西蕃中吐蕃的力量最强大,所以西蕃常用以特指吐蕃。如于公异《奏投降吐蕃表》:“独西蕃屡犯边疆,自为倔强,多从战败,少有生降,今者之来,实异于昔。”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时,当时朝中大臣李峤、徐坚、张说、薛稷、马怀素、赵彦昭等近20人都写有应制诗《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吐蕃(bō)”也是“蕃(fān)”,也是“八蕃(fān)”“西蕃(fān)”之一,并且“西蕃”还特指吐蕃,再加上“蕃”的优势读音是fān,很自然,这些都会对“吐蕃”的“蕃”的读音产生较强的类推作用,从而使部分汉民将“吐蕃”读作tǔfān。 “吐蕃”二音 tǔbō和 tǔfān 的关系,是正俗关系。 何谓正音、俗读音? 1. 官方承认、采用的读音为正音,民间个人注音、与官方正音不同的读音是俗读音。如前所述,《唐蕃会盟碑》等官方所立的碑文中“蕃—bod”的汉藏对音,王磐奉敕撰写的《拨思发行状》中吐蕃写作“土波”(官修史书《元史·释老·八思巴传》中写作“土番”),元朝法典《通制条格》中吐蕃写作“土钵”,清乾隆年间四译馆组织调查并编写的少数民族语言教材《西番译语》(藏汉对照)中吐蕃写作“土播”,这些都证明了官方关于吐蕃的“蕃”是承认、采用读如“波、钵、播”的读音的。金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持的大规模藏语调查,是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开展的,也属于官方性质的调查,结果是吐蕃的“蕃”的读音是“博”(bod);牙含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周总理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委托研究吐蕃的读音,其“吐蕃”应念作“吐播”(tǔbō)的结论得到周总理的首肯,这也是属于官方的结论。至于贾岛一首诗中“吐蕃”的“蕃”押元韵,以及其后几位诗人诗中沿袭前人的押韵,宋代史炤《通鉴释文》中“吐蕃”的注音,《红史》及其后几部著作中的“吐蕃”的注音(今音tǔfān),都属于个人作品,与官方正音有异,都属于俗读音。 2. 主人读音为正音,他人所读并与主人读音有异的读音为俗读音。“吐蕃”是唐代时藏族政权的名称,古藏族族名,也是“在历史上有某种特殊念法而现在本地音和它相合的”地名,根据《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地名》(文字改革出版社,1963)的审音原则:“凡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某种特殊念法而现在本地音和它相合的,一概‘名从主人’,不加改动。”如前所述,《西番译语》和《藏语简志》中“吐蕃”的读音(tubō)都是基于对藏人语言的大规模调查得出的官方结论,是正音。其他非藏族学者或个别藏人所读并与绝大多数藏人所读有异的读音(tǔfān),是俗读音。 3. 符合理据的读音一般为正音,不符合理据的读音一般为俗读音。如前所述,“吐蕃”是个汉语中的音译词,其中“吐”“蕃”二字在汉语中都无义。主张吐蕃是汉语本有词的观点和论据都站不住脚。“吐蕃”读tǔbō符合理据,是正音;而读tǔfān则不符合理据,是俗读音。 实际上,经对《全唐诗》的穷尽式调查,唐诗中“吐蕃”的“蕃”,真正明确押元韵(今音fān)的,只有贾岛诗一首。贾岛并没有参与过唐蕃事。参与过唐蕃事的,如张说、白居易等,其诗中并无吐蕃的“蕃”押元韵的情况。唐后直至清朝个别诗中“吐蕃”的“蕃”押元韵,当是沿袭贾岛等前人所致。至于以上诗词中“吐蕃”的“蕃”今读bō音而致不押韵,其实这并不影响古诗词学习和诵读,让学生知道“吐蕃”还有个俗读音tǔfān即可解决。 《红史》中引述的元朝汉人胡将祖译《唐书·吐蕃传》,是胡将祖译、喇嘛仁钦扎国师刊行的,并非南小民(2020)所言该藏文本是胡将祖、仁钦扎“合作”译为藏文的。胡将祖译《唐书·吐蕃传》乃非藏人的个人作品。依上述标准,其“吐蕃”注音属于俗读音。 “吐蕃”在文献中常写作“蕃”(bō),吐蕃又属于“蕃”(fān,“外蕃、蕃族、蕃地、蕃客”的“蕃”),这两个“蕃”的音义是不同的。但有时也不容易区别。如元稹《缚戎人》“蕃马膘成正翘健,蕃兵肉饱争唐突”中的“蕃”,按诗意指“吐蕃”,当读bō,但考虑到吐蕃也属于“蕃”(fān),似乎读作fān也无不可。但《唐蕃会盟碑》中的“大蕃、蕃汉、蕃国、蕃”中的“蕃”,都是国名,今音只能读bō,不能读作“蕃屏”的“蕃”(fān),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此时吐蕃正是鼎盛时期,自恃兵强,是要求与大唐平起平坐、绝不愿作为唐朝的外蕃的。《旧唐书·吐蕃传上》载:玄宗时,“吐蕃既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之礼,言词悖慢,上甚怒之”。又《新唐书·吐蕃列传下》载:“(德宗时,汉使崔汉衡见吐蕃赞普,)赞普猥曰:‘我与唐舅甥国,诏书乃用臣礼卑我。’” 作为唐代时藏族政权名、古藏族族名和古地名,“吐蕃”不是汉语本有词而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它有两个读音,一是tǔbō,它广泛存在于藏人的语言中,是官方承认、采用的读音;一是tǔfān,它是一个错误类推而成的读音,存在于一些个人撰写的古诗中和古文音注中。tǔbō、tǔfān 是正音和俗读音的关系;tǔbō 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规范读音。 南小民(2020)认为,要探索“吐蕃”千年历史真实语音,“与其问询现当代藏族人,不如向古代藏族人留下的藏文史籍求取”。这是错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丁声树先生(2020)在与《汉语大字典》审音组的谈话中曾指出:“地名,要尊重本地人的读法,可去调查当地人的读音。”现代汉语语音规范必须是基于大众的现代读音的规范。南小民(2020)反对“吐蕃”读音规范“名从主人”。其理由是:1.“藏族历史上并未主张并经常自称吐蕃”;2.“吐蕃历史上其地域变动不居”;3.“《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语文出版社,1976/1996)针对少数民族语言里的地名,吐蕃作为汉文历史专名并非藏语里的地名,不宜按该法规范读音”。这些理由是不符合事实的。如前所述,历史上藏族也可自称“吐蕃”;吐蕃历史上地域的扩大或缩小,完全不影响其作为政权名、地名的称呼,“吐蕃”还称“吐蕃”;“吐蕃”是藏族、藏语中的地名,其语源是突厥语,其汉文写法是“吐蕃”,所以《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适用于“吐蕃”的语音规范。五、 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