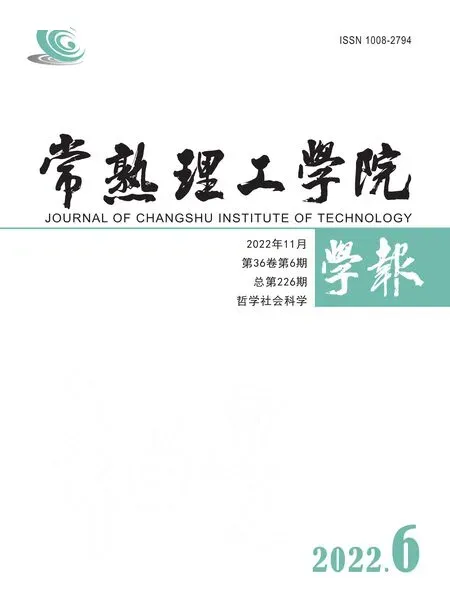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化俗”与“俗化”
2022-02-16尚丽新
尚丽新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 030006)
“宋元以来,俗文学积累了大量传统故事,题材广泛,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仙灵怪、才子佳人、家庭伦理、公案判断等,它们在民间戏曲、说唱文艺舞台上演唱,也以通俗小说、话本、唱本的形式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流传。清代民间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大量吸收了这类俗文学传统故事。”[1]10简单地说,俗文学故事宝卷就是那些自俗文学故事改编而来的宝卷。从传世的俗文学故事宝卷来看,大约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南北俗文学故事宝卷的数量开始激增,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第一个高峰。民国时期仍然持续增长,达到第二个高峰。俗文学故事宝卷留存的数量非常多,仅无锡今存的105种清至民国时期的宝卷[2]72-84中俗文学故事宝卷约有60种①60多种是笔者的粗略估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整理出版的河西宝卷中绝大多数也是俗文学故事宝卷。20世纪70年代,南北宝卷开始复兴,俗文学故事宝卷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很快于80年代走向衰落,到了90年代,它们就不再出现在南北宝卷的活态表演之中,仅以舞台展演或文本的形式存在。俗文学故事宝卷是宝卷中文学性最强的,因而学界很容易将之定位为“小说”,且把研究重心放在与通俗小说的对比之上。
是否可以将俗文学故事宝卷定性为一种通俗文学?在宝卷的信仰、教化、娱乐三大功能中,俗文学故事宝卷是否仅有娱乐功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宝卷一直走在复兴之路上,与民俗信仰密切结合的那部分宝卷一直活跃在民间,为什么俗文学故事宝卷却衰落无闻?显而易见的是,俗文学故事宝卷散发着非常浓烈的信仰教化的气息,有典型的“化俗”特征。
一、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化俗”特征
明清以来,劝善运动由上而下席卷了整个社会。明清的小说、戏曲以及通俗文艺都受其影响,或多或少都带有教化的意味。俗文学故事宝卷兼有俗文学和宝卷的双重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曲以及各种通俗文艺的普泛的劝善,而是被纳入宝卷的信仰教化系统之中,以信仰和教化来把控娱乐,带有明确的“化俗”目的。
俗文学故事宝卷里所有的故事都是自旧故事改编而来的,故事本身没有多少新意,有新意的地方是娱乐文本的信仰性、教化性改编,改编标准和改编方式比故事本身更值得关注。宝卷改编俗文学故事的标准,在题材内容上更偏爱有教化意义的,主题上要更加明确地宣扬善恶报应;对于那些极度流行,却偏离教化的俗文学故事则加以矫正和净化。一样的家庭伦理、侠义公案、历史演义,进入宝卷后比在其他俗文学形式中更加重视道德教化。例如,明万历到民国甚为流行的“正德微行”故事,在戏曲、小说、曲艺、民间故事中极为盛行,从文人雅士到草民俗众都加入这个故事的创作和改编之中,表达各自关于情爱、政治、社会的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需求;“正德微行”故事中以武宗情事最为发达,“武宗嫖院”“玉搔头”“游龙戏凤”各领风骚,但吴语区的正德故事宝卷于武宗情事却弃之不取,独取“周元招亲”故事。吴语区的“周元招亲”宝卷异名繁多,诸如《正德游龙宝卷》《游龙宝卷》《献龙袍宝卷》《割龙袍宝卷》《龙袍宝卷》《天缘宝卷》《周元招亲宝卷》《周元遇正德》《樵夫遇圣卷》《呆人得福》《游龙戏凤宝卷》①上海图书馆的民国十年(1921)抄本《游龙戏凤宝卷》、民国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游龙戏凤宝卷》、民国上海广记书局石印本《增像游龙戏凤宝卷》,皆冒“戏凤”之名,实际上仍是演述周元招亲故事。等。不管什么名目,故事讲的都是樵夫周元因以一只鸡招待正德皇帝而得到皇帝赐婚,娶了曹太史的女儿为妻。吴语区“周元招亲”宝卷里的周元是个呆憨滑稽、充满喜剧感的农夫形象,他将娶妻的梦想寄托在家中唯一的一只鸡上,鸡生蛋,蛋生鸡,卖了鸡买小猪,卖了猪买牛,卖了牛娶老婆,这种想法幼稚而又新奇,是符合庶民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宝卷选择“周元招亲”,而不选择武宗情事,显然是想呈现善有善报的主题思想。再如,据弹词《玉蜻蜓》改编的《玉蜻蜓宝卷》,同样也要表达教化劝善的主题。弹词《玉蜻蜓》因申贵升与众尼宣淫、尼姑志贞于尼庵产子被认定有伤风化,又因影射申时行而受到申氏家族联合官府的封杀。[3]按照常理来说,重信仰和教化的宝卷是不可能改编《玉蜻蜓》这种“有伤风化”之作的,但《玉蜻蜓》的主题是多元的,情节又极为曲折,在江南极受欢迎,称得上弹词里最经典的篇目之一,宝卷要改编《玉蜻蜓》就必须做净化处理。《玉蜻蜓宝卷》又名《瑞珠宝卷》②可参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郭腊梅的《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30—232页)相关记录。,瑞珠是状元徐元宰舅父张庭栋的女儿,与申贵升之子徐元宰奉旨完婚,瑞珠到故事结尾时才出场,虽然与整个故事几乎无关,但却是最纯洁的一个女性人物。《瑞珠宝卷》将弹词《玉蜻蜓》置于宝卷固有的善恶报应的模式中,申贵升、何志贞等人俱是天上众星,因过失而谪居凡间,最后在张氏(申贵升的原配)、志贞带动下满门修行,功果圆满之后升仙复位。
为了强化劝世功能,宝卷改编俗文学故事时还惯用修行模式和劝世模式。修行模式是俗文学故事宝卷,尤其是吴语区俗文学故事宝卷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模式,而且修行的发起者通常是女性。“周元招亲”宝卷的结局是周元母亲在富贵双全之后发愿修行,“周老太思想昔年苦楚,如今富贵双全,要想修行来世之福”,“日日焚香点烛,念佛看经。后来修得功成圆满,白日升天”。[4]《玉蜻蜓宝卷》是在张氏(申贵升的原配)、志贞带动下的满门修行。《琵琶宝卷》的结尾是赵五娘在荣华富贵正好之时发愿修行,最后赵五娘、蔡伯喈、牛小姐、张广才全家被观音度化升天。③光绪十二年(1886)宝树堂谢价藩抄本《琵琶宝卷》即是这种修行升天的结局。民国上海惜阴书局石印本《赵五娘琵琶记宝卷》结卷也是赵五娘修行:“五娘此时多好佛,起造庙宇佛装金。舍粥舍饭舍绵衣,修桥补路修凉亭。善人原是有善根,善孝二字有收成。”《斩窦娥宝卷》的结局是窦娥丈夫蔡廷文中状元后遵守与龙宫公主的约定一直修行,蔡婆、窦娥也跟着修行;功德圆满修成之后,蔡家人与龙宫公主及公主所生之子在龙华会上相见。④常州包立本藏清光绪十五年(1889)浦庚山抄本。修行模式的使用与佛教宝卷特别强调女性修行有关。女性修行是宝卷特别偏爱的一种题材,明代的佛教宝卷《香山宝卷》《黄氏女卷》《刘香女宝卷》就是典型。到了清代,以女性修行为题材的宝卷大量产生,并且向俗文学故事宝卷辐射,大量的俗文学故事宝卷也被套上了女性修行的模式。故事的结局通常被改写为由故事中的某一女性发起修行,然后全家修行,功果圆满后全家同登极乐。在神道故事宝卷中,修行包括在俗世的精神和肉体上修行以及名师指点下的远离红尘的高级修炼,如《香山宝卷》中妙善三公主的修行和《雪山宝卷》中释迦太子的修行。而对于凡夫俗子,修行实际上被简化为烧香念佛、持斋吃素和广行善事,如《女延寿宝卷》中的卜芙蓉、《男延寿宝卷》中的金本中,他们的修行主要是行善,不断行善使他们得到不断延寿的善报。修行并不是知识阶层那种理性的探讨和哲学的思辨,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践履。这样一来,修行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行善的道德实践,善有善报的践履就是实现信仰的最好方式,在劝善、行善中信仰与教化也合为一体了。
劝世模式一般是在结卷部分加点题的劝善总结,南北俗文学故事宝卷均有,北方俗文学故事宝卷使用更为频繁。如吴语区的“周元招亲”宝卷在结卷偈里对主题做了总结:“奉劝大众气量宽,但看周家好团圆。杀鸡留客一顿饭,一朝荣华得安然。小气不做大事体,大量倒有银子传。土地可能住大殿,小鬼何曾做判官。弥勒菩萨肚皮大,看见小气笑不完”①参见民国二十二年(1933)沈国兴抄本《献龙袍》,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第35册)影印本,第377—378页。笔者所见到的十余种“周元招亲”宝卷的结卷偈都大同小异。。较之吴语区宝卷,北方的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说教意味普遍更浓一些,例如,《佛说张瑞英寻仇救父鸳鸯绦宝卷》在结卷之后又附上大段的劝世文:“传是道非损阴骘,死在阴曹割舌根。与人方便开福路,暗箭伤人折子孙。奴仆也是人生就,何苦打的太无情。枕边言语切莫听,若要听时祸无穷。兄弟因他把心变,骨肉之情似仇人。邻里乡党须和气,忽(勿)因小可恨在心。你冤我恨仇益重,顷(倾)家败意生祸根。在世作恶人皆恨,死后家家贺太平。便有妇道真可恼,受人富贵说自穷。贵富本是前生定,莫要枉口怨夫君。嫁狗只的随狗走,嫁鸡就要随鸡行。配与官宦称奶奶,跟上乞丐叫贫婆。安分守己休埋怨,皇天不负好心人。翁婆父母家中佛,何用烧香敬泥神。妯娌姑嫂相亲近,切莫听人耳边风。背言背语休传递,当面致出羞杀人。世间有等不良辈,狼心狗肺不成人。姑嫂妯娌许他骂,翁婆父母不能尊。欺大压小只他好,自有皇天看的明。奉劝在世行善事,死后阎君看的明。常言行善有善报,作恶自有祸来临。”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嘉庆二十一年(1816)抄本《佛说张瑞英寻仇救父鸳鸯绦宝卷》。将结卷偈编成劝世文或在结卷之后附加劝世文在北方俗文学故事宝卷中很常见,而且部分俗文学故事宝卷还要在故事开始之前者或故事中间另加劝世文。
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化俗劝世特征,沿袭了佛教变文俗讲借用世俗娱乐方式传教化俗的传统。早在佛教、教派宝卷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改编文学故事以传道化俗。“早期佛教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讲唱的都是佛教传说;明代民间教派改编了少量俗文学故事宝卷,主要是为了宣传其教义,即改编者标榜的‘外凡内圣’。”[1]330到了民间宝卷时期,宣卷脱离了教派的控制,主要服务于民俗信仰,宣卷做会的目的是要解决民俗信仰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俗信仰,自然会吸收民间文艺中一些娱乐化、艺术化较强的因素。从道光年间起,民间宝卷中唱流行小调,讲流行故事越来越盛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娱乐是服务于信仰的,其中心目的是信仰而非娱乐,信仰可以把控娱乐,这也是大多数的俗文学故事宝卷会被套上修行模式和劝世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劝善运动与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化俗”
故事宝卷的“化俗”,除去宝卷利用世俗娱乐方式传教化俗传统的规约,更为重要的是明清劝善运动的影响。明清在三教合一背景之下展开了由上而下的社会各个阶层都积极参与的劝善运动,并且形成了对善恶报应的普遍认同。由此,善恶报应就成为劝善运动中最基本的法则。正如明清极为流行的《太上感应篇》所言:“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5]清李汝珍的《镜花缘》第七回唐敖功名梦碎,欲寻仙访道,被一老者用《太上感应篇》点醒:“要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信、仁为本。若德行不修,务求玄道,终归无益。要成地仙,当立三百善;要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6]《镜花缘》中宣传善报之处的确不少,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视为劝善之书,读者亦可从中窥见清代知识阶层对善恶报应的普遍认同。当然,在精英阶层中也不乏质疑者。明陈继儒的《读书镜》卷六载:“大尉韦俊为领军于忠所害,叹曰:‘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又宋詹事刘湛以义康党被收,谓弟素曰:‘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此即范滂临刑时语其子之言也。惟陆务观云:‘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后福报,若市道,吾实耻之。’吁!二子闻此言,可以瞑目矣。”[7]由此可见,精英阶层在遵奉善恶报应的表层之下流露出更为严谨深刻的思考。行善被视为士人的基本德行,而善报莫过于德行的圆满,而非现实的、具体的利益。这样一来,在部分精英知识分子那里,善恶报应既超越了功利,也超越了神的控制。不过,“为善自是士人常事”是精英阶层的标准,而“市道”“邀身后福报”则适用于庶民。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法则仍然意味着今生和来世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平安以及信仰的实现都要从善行中获取。明清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艺被卷入教化思潮中,善恶报应成为通俗文艺中被普遍使用的创作模式,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结局也彰显了善恶报应:李甲郁成狂疾,终身不痊;孙富受惊卧病,奄奄而逝;柳遇春则因慷慨得到了杜十娘的宝匣。[8]
在庶民社会中,以善恶报应为基本法则的明清劝善思潮成功地把信仰和教化联系在一起,并且把教化变成了扬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宝卷扎根于基层社会中,它是民间劝善运动和民众劝善实践的典型代表。基层社会的教化既有乡绅为代表的亚精英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教化,又有庶民阶层的自我教化,宝卷的教化更多地属于庶民阶层的自我教化。基层社会里的娱乐本身就是和信仰教化合一的,拿唱戏来说,戏肯定不是随便唱的,通常会由亚精英阶层来决定唱什么戏,唱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教化。不可否认,一个民风淳朴的乡村离不开亚精英阶层的教化,而居于亚精英阶层之下的庶民阶层的自我教化往往是被忽视了的。宝卷,尤其是俗文学故事宝卷的教化功能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宣卷先生(通常也是编卷者或改编者)和相关执仪者无疑是主导者。他们是庶民阶层中的文化人,至少他们是识字的人,又因为他们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和普通民众一样,但他们在普通民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对基层社会也会有一定的把控能力。作为庶民阶层的文化人,他们有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感;作为宣卷人和执仪者,他们本身又是宝卷信仰教化功能的传播者和执行者。因此,当宣卷人从当地盛行的民间文艺中改编各种流行的俗文学故事时,他们会自觉加上教化模式;且这个模式频繁出现,反反复复地强调着善恶报应。加之在基层社会的信仰中,信仰与教化是合二为一的,人的种种行善修行的努力要得到神灵认可方能兑现善有善报的承诺。出于对掌握报应大权、主宰着今生来世命运的神明的敬畏,民众自然会对善恶报应产生虽然被动却不容置疑的认同。今天来看俗文学故事宝卷中的修行模式,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套路。但站在当时庶民俗众的立场上来体会一下,对于那些信奉神明、对善恶报应格外关心的民众来说,一个因为行善修行而得到完美果报的故事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宣卷人和执仪者又是庶民中的一员,他们会根据底层生活实践和生活经验对自上而下发出的教化教条进行调整,甚至反拨,加入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情感好恶。例如,吴语区光绪十二年(1886)宝树堂谢价藩抄本《琵琶宝卷》中的蔡伯喈形象与南戏《琵琶记》中的形象有别。蔡伯喈既自私又功利。他在牛府招亲之时,偷偷算了几卦,得知牛小姐命中“犯着冠带有三子”,不禁“心中得意喜洋洋”地遵命了。入赘牛府后“一心常伴牛小姐,丢却家中结发情。一心孝养牛丞相,不想家中老年人”。这样一个颇有些反面的蔡伯喈的出现,从深层次来说,大约流露的是编卷人那种市井小民精于算计的心理。清代流行于北方的《白马宝卷》改编自“熊子贵休妻”故事,被穷命的丈夫无故休掉的妻子杜金定选择了天婚再嫁,任由白马将其带到乞儿张三的破窑前。杜金定的天婚再嫁与正统封建伦理要求女性从一而终是相悖的,再嫁其实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民间伦理对这种再嫁是有一定宽容的,《白马宝卷》保留再嫁情节也是这种宽容的表现。总之,较之其他民间文艺,俗文学故事宝卷表现出来的教化思想更为浓重而严密,同时又因其扎根于底层生活之中,减少了精英、亚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教条式说教,保持了淳朴自然的本色,虽然有着粗鄙、功利等明显缺憾,但却是鲜活的。
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劝善是以庶民阶层的自觉劝善为主流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俗文学故事宝卷在基层社会所发挥的强大的教化功能。直到20世纪80年代,“河西人还把宝卷当作教育人的特种手段。谁家子女不孝父母,谁家媳妇不敬公婆,庄上比较权威的人(一般是长者),即可通知在他或她家念卷。他或她就要按念卷场的惯例,把炕上炕下打扫干净,擦亮炕桌,摆上好吃的,专候念卷开始。念卷时,他或她得细心耐心地听着;必要时,还可叫他或她跪着听。念卷先生有什么问话,他或她眼泪和着鼻涕,只能战兢兢地回答说:‘是。’或‘知道了。’不准强辩,也不敢强辩。”[9]
三、庶民的娱乐需求与俗文学故事宝卷的“俗化”走向
宝卷首先应该是信仰、教化合一的神圣文本,相对于这种“神圣”,“俗化”指的就是世俗的娱乐化和艺术化。宝卷的“俗化”以俗文学故事宝卷为代表,它充分发挥了宝卷的娱乐审美功能。
宝卷自身就具有故事化、娱乐化、艺术化的基因。艺术起源于宗教的论点并不陌生,民族史诗、祭祀神歌等具有信仰特质的神圣文本都有故事化的特点,宝卷亦是如此。佛教宝卷、教派宝卷时期,改编故事、吸收民间艺术以传教化俗颇为普遍,到了民间宝卷时期,宝卷和乡土社会的泛神信仰结合在一起,大量神灵故事宝卷产生了,诸如吴语区靖江的圣卷,常熟的素卷、荤卷和冥卷,都以讲述各种民间信仰神灵的故事为主。当然,这种故事化的目的是化俗而不是娱乐,但不可否认客观上却契合了民众的娱乐需求;而且,也为神灵由圣而凡、宣卷由娱神到娱人、俗文学故事进入宝卷埋下了伏笔。
宝卷吸收俗文学故事,从内因上来说,并非出于娱乐的目的,而是出于信仰、教化之需要。宝卷借用民间文艺形式传教有两种形式:一是唱民间流行小曲,二是讲俗文学故事。一个重音乐,一个重文学。宗教性强的教派宝卷侧重吸收民间音乐,用在科仪上;而与民俗信仰结合紧密的民间宝卷偏重讲故事,对音乐和故事都有借鉴。所以教派宝卷时期,故事宝卷是最不发达的。进入民间宝卷时期,信仰与教化合一,为了劝善化俗,宝卷的娱乐化、故事化大大增强,同时也因为做会时间加长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俗文学故事被改编为宝卷。吴语区将之归入“闲卷”“草卷”“小卷”“凡卷”(与之相应的是和神灵信仰相关的“神卷”,诸如靖江的“圣卷”,常熟的“素卷”“荤卷”“冥卷”),以示其与满足信仰的“神卷”有凡俗之别,同时也肯定了它的娱乐功能。宝卷吸收俗文学故事,从外因上来说,是明清时期庶民通俗文艺的大发展为俗文学故事进入宝卷提供了客观条件。明清是通俗文艺大发展时期,社会各阶层都卷入通俗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大量的俗文学故事被创作出来。较之雅文学故事,俗文学故事有着多元的传播和繁殖方式。它可以被置换到不同的形式里,被各阶层的民众寄以各种不同的理想、愿望。在雅文学里,故事成型之后不再接受再创作;而在俗文学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故事有多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没有定型的故事,可以被不断改编。俗文学故事的这种易于变形的特点,为宝卷改编俗文学故事提供了可能。
民众的娱乐需求是不可扼杀的,但对于基层社会的普通民众而言,娱乐需求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的。看戏是奢侈品,小说之类的故事文本是给识字的人看的,能较大限度地满足当地百姓娱乐需求的就是当地盛行的民间文艺(当然这些民间文艺中有很多品种是和民间信仰有瓜葛的)。并非民间文艺的宝卷恰恰就在宝卷盛行的地域扮演了这种角色。尽管俗文学故事进入宝卷的初衷是信仰教化,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极大地发挥了娱乐的功能,满足了基层社会的娱乐需要,成为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吴方言区民间宣卷的大发展是在清咸丰以后、太平天国被清政府镇压之后。饱受战火之苦的普通民众,在精神上更加信仰掌握着‘善恶报应’的神佛。而恰恰在此时,清政府以净化道德的方式重整封建社会的秩序。同治六年(1867),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查禁 ‘淫词小说’(所列作品多为弹词)、‘淫戏’(指花鼓、滩簧等地方戏)的命令。宝卷由于其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且以劝善为主,不在查禁之列。弹词、花鼓、滩簧等被禁断,客观上给宝卷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趣的是,宝卷不仅满足平民、乡绅的信仰、教化需求,而且将弹词、花鼓、滩簧的娱乐功能也接替过来。宣卷艺人开始大量改编那些消闲、娱乐的弹词,将之置于宝卷固有的善恶报应的模式之中。所以,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民间宣卷人的手抄本宝卷的品种和数量都大量增加起来。”[10]太平天国之后的道德整肃运动导致弹词的大量篇目被改编到宝卷中来,这是对吴语区宝卷娱乐化发展的一个大促进。北方没有类似查禁“淫词小说”“淫戏”之类促进俗文学故事宝卷大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但从存留的大量的清代、民国时期的俗文学故事宝卷文本,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河西走廊仍以宣俗文学故事宝卷为主来看,俗文学故事宝卷在北方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迅猛发展,把宝卷的娱乐功能凸显出来,娱乐功能不仅与信仰教化功能完美地合一,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挣脱信仰、教化把控的迹象,娱乐甚嚣尘上在某个时期的某些地域里一度喧宾夺主。诸如苏州的苏派宣卷已成为一种接近弹词的说唱文艺、杭州的宣卷发展成“杭剧”、民国上海石印本故事宝卷的大量印刷又将宝卷等同于纸本的通俗小说。当然,这些属于个别现象,且都发生在商业繁荣的江浙沪地区。
总体来看,俗文学故事宝卷的俗化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而是受信仰教化把控的娱乐,娱乐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信仰和教化;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娱乐又完美地融入信仰教化中,满足了当地民众的娱乐需求。
四、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衰亡和价值
20世纪七八十年,宝卷开始复兴,但从90年代起,俗文学故事宝卷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南北宝卷都很少再宣俗文学故事宝卷。吴语区的宣卷活动明显地与民俗信仰结合在一起,祈什么愿、禳什么灾,就宣什么卷,加之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宣卷仪式省略、时间紧缩,现在用不了一个白天就可完成全部的宣卷,以往在夜晚宣唱的俗文学故事宝卷自然被省去不宣了。河西娱乐故事卷的宣演也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衰微,但在政府非遗工作的保护之下,那些教化、娱乐色彩浓厚的故事宝卷仍出现在舞台展演中。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为舞台表演艺术而做的努力与宝卷的初衷早已南辕北辙。
俗文学故事宝卷的消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变文的消亡。变文的消亡是因为变文已经完全脱离了佛教信仰,嬗变成被官方禁绝的通俗文艺。近代宝卷中也有一小部分脱离了民间信仰,沿着商业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变成了曲艺。不过这只是少数。宝卷之所以能长存,恰恰在于它是扎根于信仰之中的。一旦脱离了信仰环境,宝卷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这也就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大量吸纳俗文学故事和民间文艺的乡村宝卷尽管俗化得非常严重,却仍然没有脱离信仰本质的原因。俗化不能决定宝卷的存亡,决定宝卷性质和生存的是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河北宝卷、青海宝卷和洮岷宝卷里几乎没有俗文学故事宝卷,它们却一直存在着。当然,信仰会随着时代变迁,宝卷经历了佛教信仰、教派信仰和民间信仰三个时期。从清代康熙年间到如今,宝卷中的民间信仰也几经变迁。1949年之前的民间信仰的特点是通过善恶报应把信仰和教化合二为一。1949年之后的民间信仰受到意识形态的干预,大部分宣卷活动自行消亡或转入地下,还能公开存在的宣卷活动则有意识地淡化信仰色彩,例如靖江宝卷在政府的引导下向民间文艺转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民间信仰的动因主要是求助神灵来把握不确定的人生,消解生活中的焦虑,即又回归到祈福禳灾之上。善恶报应的历史局限性展露无遗,信仰与教化分离,同时新兴的娱乐方式兴起,俗文学故事宝卷已经不可能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既是劝善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庶民文艺大发展的时期。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庶民文艺大发展带来的道德滑坡表现出担忧。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中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末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11]但另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却发现可以借助民间文艺来推进劝善运动,王阳明的《传习录》云“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2]。吸纳俗文学故事服务于宝卷的信仰教化和王阳明的观点不谋而合。精英阶层和亚精英阶层对庶民文艺的整肃总是过犹不及,行政高压、过分净化的结果只能产生刻板的劝善书,未必真正能有益风化。而庶民阶层自发的、自觉的劝善,因冷暖自知而倍显亲切。宝卷本质是信仰,由于明清的劝善运动通过善恶报应把信仰和教化合二为一,使得宝卷成为民间劝善运动和民众劝善实践的典型代表。宝卷的娱乐是民俗信仰和乡村教化掌控之下的娱乐,它贴近生活,在辅翼教化的同时又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达到了信仰、教化和娱乐的完美结合,在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劝善维稳的作用。
俗文学故事宝卷是民间劝善运动与庶民的文艺思潮在宝卷中合而为一的产物,是教化、娱乐的双重文本。对俗文学故事宝卷的价值作出客观的评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众所周知,俗文学故事宝卷不是原创的,而是改编俗文学故事而来;那么,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改编问题。一个俗文学故事会存在于多种文艺或文学形式之中,只要故事的基本母题不改变,它的形式和思想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社会各阶层都有参与创作的权力,都可以表达各自的不同理想和多元需求。这样一来,宝卷改编俗文学故事时就会有多元的选择。一般来说,改编哪部作品就意味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认同。这也是同一地域内的最为流行的曲艺、地方戏是最有可能被改编的原因。虽然通俗小说是庶民文艺中传世文本最多的,但宝卷不会一味地改编通俗小说。例如吴语区的俗文学故事宝卷改编自弹词的最多。据车锡伦先生考证《中国靖江宝卷》中18部小卷中有9部改编自弹词,它们是:《十把穿金扇》《独角麒麟豹》《彩云球》《白鹤图》《回龙传》《八美图》《九美图》《香莲帕》《文武香球》。[1]331李萍认为今存的清末民国无锡地区的105种故事类宝卷中有39种是与弹词、地方戏共享的俗文学故事宝卷。[2]267而且,宝卷改编俗文学故事有时候是非常随意的,可能会把某些说唱文本直接搬过来,连形式都不作改动,仅将题目命名为“××宝卷”。俗文学故事宝卷的改编既有规律性,也有很大的随机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部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艺术水平多取决于被改编作品的原初水平,同时也受改编者的创作水平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编卷先生的文化水平不会太高,俗文学故事宝卷改编往往是粗线条的改编,思想上的粗鄙、艺术上的粗糙随处可见。那些改编自弹词的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艺术水平通常要比弹词低。不过有一点不容忽视,俗文学故事宝卷的个性和创新性往往体现在宣卷人临场发挥的表演之中。宝卷只是文本,当这种文本被宣演的时候,它就不再是静止的,而是变得鲜活起来。一个好的宣卷人可能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但未必是个好作家。时至今日,俗文学故事宝卷的宣演已从民众的信仰生活中退出,变成了非遗保护下的舞台展演,对原生态的俗文学故事宝卷的表演进行研究确有难度。学术界把俗文学故事宝卷研究的重心放在文本上。它拥有数量众多的抄本、木刻木和石印本,例如吴语区的“周元招亲宝卷”就有66种抄本、3种石印本①此数据来源于对以下资料的统计: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吴瑞卿的《傅惜华藏宝卷手抄本研究》(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郭腊梅的《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孔夫子旧书网相关书影及友人提供给笔者的资料。,这个数据说明它曾经在吴语区是非常流行的。不过,它的大多数的文本都大同小异,版本的比勘和文本的细读终归是收获甚微、劳而少功。当这些俗文学故事宝卷以静态的文本的形式存在时,很容易把它们和通俗小说联系起来,因为这些宝卷中绝大多数的故事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直接从小说中改编过来的。如果要研究宝卷对小说的改编,首先需要对“通俗小说”有个清晰的界定,然后判断所研究的每一种宝卷具体从何处改编,和小说有无瓜葛。在俗文学故事宝卷的研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得出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
结语
俗文学故事与宝卷的离合,展现出民间信仰和庶民文艺从清代到近现代的变迁。明清的劝善运动通过善恶报应把信仰和教化合二为一,这种合二为一使得宝卷成为民间劝善运动和民众劝善实践的典型代表。俗文学故事宝卷是宝卷化俗的产物。它是信仰、教化的副产品,但客观上又满足了民间社会的娱乐需求,因而成为教化、娱乐的双重文本。俗文学故事宝卷的研究,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和更为多元的视角下更好地理解近代俗文学和俗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