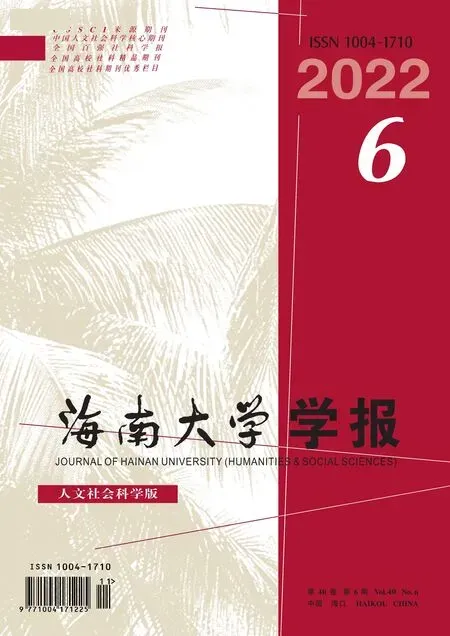论欧阳予倩对《桃花扇》的改编
2022-02-15朱东根
朱东根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古典名剧改编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书写方式之一。古典名剧不仅给现代戏剧写作提供了叙事材料,也在艺术创作方面提供了借鉴。同时,古典名剧历经时间的洗礼,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往往是其现代改编作品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但如何改编古典名剧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数度改编孔尚任名剧《桃花扇》,堪称古典名剧现代改编的先驱人物。他的改作不仅曾轰动一时,令人瞩目,也为古典名剧的现代改写进行了有益的艺术探索,树立了光辉典范。那么,《桃花扇》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而欧阳予倩改编名剧又有哪些成功的秘诀呢?
一、孔尚任的创作过程
《桃花扇》乃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精心结撰、打磨的传奇剧本。他曾这样自述剧本的创作过程: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少司农田伦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1]5
孔尚任出仕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四年清圣祖南巡北归的1685年,时因皇帝祭孔,在御前讲解《论语》而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桃花扇》完稿之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上距其出仕已在十四年之后,可见剧作家为了写好这部剧作是如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他既阅读了有关史料,同时也深入实地展开调查,遍访遗民旧闻,力求把剧本创作建立在充足确凿的史实基础之上。其求真求实之切,致有《桃花扇考据》的写作,以示其故事的情节乃至细节皆有根有据,可以查考,不妨当作信史看待。“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1]11也就是说,《桃花扇》在创作方法上走了一条和一般戏曲剧本不同的道路——写实求真,在古代戏曲剧本中堪称异数。
《桃花扇》不仅创作方法与众不同,其剧本结构也非常独特。虽然采用“爱情+政治”的传统叙事模式,“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1]1,但这种爱情与政治的结合却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生硬地扭合在一起的。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他既是本剧中男主人公,“爱情”的必然当事方,同时又是晚明、南明的重要政治人物,倾向于东林党(其父侯恂为东林名士),亲身参加过复社文人反阉党的斗争,并入职史可法幕府,亦可谓“政治”的必然当事方。李香君也是如此。她是“秦淮八艳”之一,和侯方域有深入交往,侯曾为之作《李姬传》,称她“侠而慧”,又因其身份,和晚明、南明的达官贵人们有诸多周旋,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故此,她亦是本剧“爱情+政治”叙事的另一个最佳候选人。在这一叙事模式中,《桃花扇》的叙事基点放在政治而非爱情上:政治为主线,爱情为副线;政治为主,爱情为宾,爱情乃是剧作家用于表现政治的切入点和手段。关于本剧以政治为创作重心的动机,剧作家不是予以掩饰,而是反复申说,昭告于天下: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1]1
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1]3
为此,剧作家将剧中人物按其政治属性等作了部伍分类,有所谓左右正色、间色、奇偶中气、戾气等名目,如侯、李为正色,史、左为中气,弘光、马、阮为戾气,等等。又据以安排全剧的整体艺术结构:
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
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①《桃花扇》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桃花扇本末》:“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夺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有人甚至说这些批语是孔尚任自己写的。且不论真假,但至少,孔尚任是赞同这些批语里的看法的,他视读者们的这些批语为“知己之爱”。
剧中著名的却奁、骂筵等关目设置亦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爱情的动机。因为写实求真,并以政治而非爱情作为剧本写作的出发点,所以孔尚任在剧本结局的安排上也摆脱了窠臼,让男女主人公分道扬镳,出家入道。为什么呢?现实中侯、李并无团圆毕姻之事,一如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人的遭际那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2]。现实生活并不总是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美好。而更为重要的是——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
(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
(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1]258
政治上的因缘变局才是孔尚任决定打破传奇俗套、另创新局别开生面的主要原因。而时人顾彩未睹孔尚任此举的深意和价值,改写侯李故事为《南桃花扇》传奇,将孔尚任所写李香君、侯方域双双入道的结局改为以生旦团圆收场。因此孔尚任说:
顾子天石,读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其词华精警,追步临川。虽补予之不逮,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1]7
这种“快观者之目”的改写并没有取得观众的认同和良好的效果,今顾彩的改本已佚失不传。孔氏所谓“形予伧父”“敢不避席”云云,实乃自谦之辞耳!清代曲评家梁廷枏对此品评道:
《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脱尽团圆俗套。乃顾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优孰劣,识者自能辨之。[3]
可谓眼光不俗,评论精到有识见。
二、欧阳予倩的改编
以上这些创作情况成为《桃花扇》一剧撞击现代时代脉搏和扣响今世观众心弦的基本条件,也是著名戏剧、电影工作者欧阳予倩反复改编、乐于改编《桃花扇》的主要依据。
(一)三度改编
民国时期,欧阳予倩凡三度改编《桃花扇》传奇为现代戏剧。第一次是1937年的京剧改编:
1937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仅仅演出两场就被迫停演了。……当时观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4]171
之后,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桂林剧团团长,于是有了第二次的桂剧改编:
1939年,我把它改成桂戏,在桂林上演的时候,曾经加以某些删改,但也曾根据当时的一些感想有一些补充。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敲起警钟;对勇于内争,暗中勾结敌人的反动派,给予辛辣的讽刺。这个戏在桂林曾经轰动一时,最后被明令禁演。[4]172
1947年,欧阳予倩在中国台湾对《桃花扇》作话剧改编,是为第三次:
1946年,我和新中国剧社到了台湾,最初演出了三个戏:《郑成功》《牛郎织女》《日出》。此后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节目,大家认为最好演一个历史戏,就让我把《桃花扇》写成话剧本。我就躲在一个有温泉的旅馆里,用十天工夫把剧本改好,排了七天,演出了四场。[4]172
欧阳予倩对三次改编过程的自述透露了《桃花扇》被现代人青睐的个中消息。1937年和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到处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文艺工作者们也积极投身于其中,以手里的笔作为匕首投枪,创作、宣传、鼓动,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激发抗敌救国的热情。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编和他的桂剧《木兰从军》《梁红玉》,话剧《青纱帐里》《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等作品一样,可谓文艺界抗战救亡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不难想象,立足政治、贴近现实,在剧中弘扬爱国主义、对敌斗争和民族气节等主题,是欧阳予倩此一时期选择题材与创作构思的主要着眼点,我们很容易看到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和欧阳予倩此时的创作诉求之间有着深度的契合,他可以极方便地把孔尚任的创作内容转换成时代所需。换言之,只要稍加取舍,孔尚任《桃花扇》就能成为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的戏剧作品。而其取舍之道也一如原作,突出现实的、政治的方面,弱化乃至虚化爱情因素,以彰显其时代意义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阳予倩继续关注《桃花扇》的改编,并将它搬上了电影银幕。。
(二)欧阳予倩改编的着眼点
首先,他只截取了《桃花扇》中矛盾冲突、思想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几个场景来叙事,表现了美忠刺奸、激浊扬清的主题。《桃花扇》原著是一部体制庞大的历史剧,以侯、李爱情为切入点,包容了整个南明弘光王朝的兴衰史实,其线索、事件和主题皆是多样的,以寄寓作者的兴亡之感。如写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写正派文人的生活与情趣、写下层社会状貌、写史可法、左良玉等将领的情怀……读者、观众可以从中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并不限于单一的主题。简言之,《桃花扇》采用了“全景式”的叙事方式。
反之,欧阳予倩从“打阮”开始写起②1963年的改编本在“打阮”之前还有“教歌”的一场戏。,连缀“题扇”“却奁”“修札”“辞院”“画扇”“骂贼”等情节,以“撕扇”剧终,可谓主题鲜明而专一,场景紧凑而集中。他说:“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辈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4]171他要通过《桃花扇》的改编,歌颂爱国英雄,痛斥汉奸卖国贼,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为此,他大幅度删削了原著中无关宏旨的情节、段落、人物、场景,而只截取了其中最为切要的部分,体现在篇幅上,《桃花扇》原著凡二本四卷四十四出(含上本试一出、闰二十出、下本加二十一出、续四十出),欧阳予倩改编本则八九个场景而已,相当于一部现代话剧作品的长度。
很明显,这种以鲜明主题为指导分场分幕的写法乃是受到了话剧写作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中,选取几个典型场景来写作的手法也很常见。司马迁叙写蔺相如的时候,不是写蔺相如的一生,也没有写蔺相如的方方面面,而是选取了特别能表现蔺相如个性精神的三个场景(“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来细致刻画、详尽描写,起到了纲举目张、画龙点睛的效果[5]。李渔主张剧本写作须“立主脑”[6]16“减头绪”[6]21,即是要求写剧本时主题明确,线索清晰,不要贪多务得,贪大求全。近代以来,京剧等戏曲剧种在进行戏曲改编的时候,通常也只截取部分的情节段落来表演,如一些三国戏、水浒戏所显示的那样。换言之,欧阳予倩是在借鉴了中、西文学之长后改写《桃花扇》的。
其次,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欧阳予倩突出了主要的人物、主要的矛盾冲突,从而予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无疑,李香君是欧阳予倩所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虽是一个烟花女子,但其见识、气节则远在一般人之上。他设定香君是东林党人李宗林之后,因遭党祸而沦落倡家,所以,她能有着令人钦敬的见识和气节。她看到杨龙友无缘无故地为她置办彩礼,便很警觉地想道:“他为我送来缠头锦,他为我送来百宝箱。他本是罢职赋闲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这烟花巷?”当得知是阮大铖所为时,尽管有杨龙友、侯方域在旁为阮做解释打圆场,她还是毫不容情地拒绝了:
李香君:官人,你太老实了。【唱】你思一思来想一想,莫学那东郭先生救黄狼。阮大铖攀权贵廉耻丧尽,他是臭名到处传扬。妇人孺子皆唾弃,你为何反与他来消祸殃?你要做青松耸立在高山上,莫学那杨花柳絮随风扬。休为妆奁把私情讲,还他银两退回百宝箱!香君虽是青楼女,哪肯名节付汪洋?!戴荆钗,穷不妨,穿布衣,名自香,还他绫罗还他锦帐,金钟休想罩凤凰!!(欧阳予倩1963年电影剧本《桃花扇》)
在香君的激发之下,侯方域也醒悟过来,和阮大铖划清了界限。阮大铖挟恨捉拿侯方域,侯方域不知如何是好,且留恋柔情,又是香君晓之以理,指点迷津:
李香君:【唱】生生离别苦透心,香巾揩泪诉离情。男儿应有四方志,休要为我多劳神。此去江北多报国,拯救黎民水火中。人生聚散何足论,脉脉相连一条心!奴家虽是青楼女,此心决不负郎君!(欧阳予倩1963年电影剧本《桃花扇》)
后来,权贵田仰逼娶香君,香君以死相对,血染桃花。又当面痛骂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数落他们祸国殃民的罪状,表现了凛然正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表现香君的民族气节,欧阳予倩还改变了原著的结局,写侯方域降清,香君义斥他的变节行为,撕掉了象征二人爱情的桃花扇,触阶殉节。
香君和阮大铖的斗争是欧阳予倩所突出的主要矛盾冲突,“却奁”“辞院”“骂贼”等场次对此有浓墨重彩的描写。
为了衬托李香君,欧阳予倩对剧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侯方域作了大幅的“改造”:(1)他性格软弱,在政治斗争中走调和路线,没有表现出东林党人应有的斗争精神,缺少是非观念。他不仅没有像吴次尾、陈定生等人那样痛恨阮大铖,而且对阮大铖的“收买”无动于衷,心安理得,还和杨龙友这样的圆滑狡黠之人关系很好。(2)他过分迷恋情色,甚至把它置于大义之上。在斗争形势紧张的时刻,他却迎娶香君,贪图享受;在需要他表现出精神和气节的时候,他却以夫妻团聚为借口,悍然变节,最终害死了香君。(3)他最终变节投降,令人不齿。这是对《桃花扇》原著的重要改造,是很有现实针对意义的改造。总之,欧阳予倩在写作的时候,处处将侯、李二人相互对照,态度鲜明。
(三)欧阳予倩改编中的“现代元素”
欧阳予倩善于把“现代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本改编之中,以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礼教,究其实,乃是一场关于人的自身的解放运动。封建时代加诸人们身上的种种教条束缚被一一打破,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个人在国家、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和重视,个体生命特别是“小人物”的命运,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话题,被讲述、被刻画、被讨论。然而,由于封建秩序力量的强大和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虽然有一波波的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推动,个体价值的论述始终都未能完成。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便以戏剧的方式来表现他对此问题的关注。
李香君是地位低下的歌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本无所谓地位与人格可言,是受人欺凌的对象,是受到侮辱与损害的人。确实,达官显贵如马、阮、田仰辈把她当作蝼蚁一般地对待,呼来喝去事小,更要抢她做妾,否则死路一条。即使是“正派的”文人,也不过拿她当作消遣,或者情感的慰藉。在孔尚任写作《桃花扇》的时代,理学思想和专制主义横行,根本谈不上“人的觉醒”的问题。可欧阳予倩却赋予了李香君这一形象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意义。换言之,欧阳予倩笔下的李香君与其说是旧时代的歌妓,毋宁说更像一个“新女性”。平等意识是她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是如此。
虽然马、阮、田仰辈是达官显贵,地位、权势上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这帮祸国殃民的奸贼败类,李香君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们,鄙视他们的人格,痛骂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向她伸来的魔掌黑手,则不惜以死报之,表现了不屈的精神。在客观条件上,李香君是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子,可其人格的光辉却远超马、阮、田仰辈,照耀千古。这是我们读了欧阳予倩《桃花扇》之后的一大感受。同样是却奁、骂筵,原著与改作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此不同即改作中于表现大义、气节之外,更增加了人格平等的意识。这是一个“现代元素”,是五四新女性走向独立的一大标志。人们不能忘怀李香君的“我要作人”的那声呐喊(欧阳予倩1963年电影剧本《桃花扇》第四场)。侯方域在无意中用了阮大铖的钱、受了他的恩惠,李香君知情后并不像侯方域、李贞丽那样以为无伤大雅、无可无不可,而是严词拒绝,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
尽管你们把我看成下贱的女子,可是我心还没有死,是忠是奸我还分得出来。就把我凌迟碎剐,我也不会随便接待一个奸贼的走狗!(欧阳予倩1963年电影剧本《桃花扇》)
很显然,正像香君对假母贞丽所说的那样,她是欧阳予倩所要着力塑造、着力书写的“大写的人”。贞丽代嫁情节也是香君平等意识觉醒的体现——“不自由,毋宁死”。香君以死相抗,贞丽则屈从于田仰的淫威。
平等意识还表现在侯、李的交往与爱情之中。李香君不是侯方域失意的寄托,不是爱情的被动接受者。她爱侯方域,但这种爱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正义的力量和果敢的精神。侯方域为东林党人之后、复社文人领袖,这受到了李香君的敬重,也是其爱情的根据和基础。当侯方域和阮大铖发生瓜葛,有些纠缠不清的时候,香君并不因为顾惜爱情而有所宽贷,也并不因为侯方域的地位而对他高高仰视。当侯方域做出失节之事的时候,爱情基础便不存在了,香君毫不犹豫地斩断情缘,痛斥侯的无耻,殒身明志。在侯的面前,香君同样表现得不卑不亢,正气凛然,人格高洁。
三、欧阳予倩改编的其他方面
所谓“现代元素”,在欧阳予倩的《桃花扇》中,还表现在他对“小人物”的关注及对平民百姓的“发现”上。《桃花扇》是政治题材,写明清鼎革易代之际,涉及的“大人物”很多:弘光、马、阮、史可法、左良玉、东林名流……原著里确实有很多由“大人物”演出的戏。可欧阳予倩差不多把“大人物”从舞台上全“赶跑”了——除了东林人物及阮大铖等必不可少的“大人物”在场之外,舞台上全是“小人物”活动的身影:院中的李贞丽、李香君、郑妥娘、寇白门;老曲师苏昆生;说书艺人柳敬亭;官府衙役……甚至还有不知名的民众:
民甲(指墙内)你看这里不是阮大胡子的庄园吗?当初靠着马士英的势力,无所不为,千方百计把老百姓的田弄成自己的产业,恨不得把所有人的饭弄到一个人的嘴里。
民乙所以他们就要抢官做,做了官,有了权才好借着各色各样的题目霸占百姓们的土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他们成群结党,一天到晚耍的是这一套把戏,弄得大家的钱都积在他们一群人手里。
……
民甲要不是他们,明朝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
民乙平常看起来,好像只有他们像人,老百姓都不是人;现在看起来,老百姓始终还像人,他们才真不是人。妈的!
民甲可怜,眼看见他们起高楼,又看着他们楼塌了!(1947年新中国剧社话剧版《桃花扇》第七场)
原著续四十出“余韵”借渔樵(柳敬亭、苏昆生)之口写兴亡之感,给人以言近旨远、回味无穷的感觉,自然是巧妙的剧情设计。欧阳予倩继承了这一做法。但其间是有不同的。渔樵虽说是“小人物”,是“民”,在中国传统的创作语境里,却别有所指,别有特殊的意涵。“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①杨慎:《临江仙·〈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该词被后人录入《三国演义》小说中,成了它的开篇词。[7]他们不过是许由、巢父、长沮、桀溺等世外高士的代名词罢了。如果欧阳予倩沿用这样的人物意象,那么,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跟时代不相匹配。五四时期提倡“劳工神圣”,五四以后,工农运动兴起,工农阶级、普通百姓成为了重要的革命力量,影响力越来越大。抗战时期,全民支持抗战、参与抗战,则进步的剧作家眼中更须有普通民众、平民百姓。从来人们都持英雄史观,20世纪的社会实践颠覆了它,并把工农大众推向了历史前台。这是时代的现实。欧阳予倩在抗战之后改编《桃花扇》,把渔樵变成了民甲民乙,通过百姓对话、街头议论,揭示了官民对立,抒写了兴亡之感,其实是对于“人”的发现,是平民情怀,是进步的体现。
于描写忠奸斗争之外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情怀,于表现香君的精神气质之外书写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于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之外提升“小人物”、平民百姓在历史上的地位,乃至把他们推向了中心的位置。就这样,欧阳予倩敏锐地体察到时代的律动和变迁,并把这种律动和变迁融注于《桃花扇》的改编中,使之成为一部“创作”,适合了新时代的观众的需要。欧版《桃花扇》之所以能一次次地被要求改编、修订,并跨越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战争动乱、和平建设的两种环境,常演常新,其魅力正在于此。
其实,欧阳予倩的改编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在戏剧形式上尽量吸收现代元素,以便现代观众的接受和欣赏。在这方面,欧阳予倩可谓驾轻就熟、经验丰富。他长期从事剧本创作和舞台实践(包括组织、指导、表演等),既熟悉话剧又谙习戏曲,从“春柳社”时期开始,直到20世纪后半叶,戏剧活动时间横跨半个多世纪,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和创作大师。他还勇于探索创新,不断地推动戏剧的发展进步,早年积极引进话剧,后来参与话剧、京剧、歌剧、地方戏的改造改革,成绩斐然,成果丰硕,晚年又涉足戏剧教育和电影,拓宽自己戏剧活动的领域。他乐于接受新事物,大胆尝试,并不故步自封。他的这些经验和探索同样体现在《桃花扇》的改编上。大体有这几点:
第一,作品结构采用话剧体制。传奇创作以“出”为单位,一般说来,以人物的上下场为依据,并不太注重情节段落的发展节奏。有的出目情节紧凑集中,有的出目则重在以曲抒情,抒写人物的内心,情节叙事的成分较少。传奇的“出”近似于杂剧的“折”,跟曲牌组织体制即音乐元素相关。因此之故,明末清初以来,传奇还发展出了折子戏(单出戏、出头戏)的表演形式,情节叙事性更被弱化了。话剧与之不同。话剧没有曲唱抒情,剧作的叙事性很强,情节发展紧凑,故而适合采用分场分幕演出,在剧本写作的时候,非常注重情节结构的均衡安排。传奇分出,话剧分场,无所谓优劣好坏,都是依据各自的历史和特点所形成的。但现代读者、观众已经逐渐习惯了话剧的以情节叙事为主要依据的分场分幕的体制,欧阳予倩改编《桃花扇》,无论是改编成话剧、电影还是改编成京剧、桂剧,他都须考虑到这一变化,对原著体制作出调整。简言之,他给《桃花扇》分段的依据主要是故事发展,而不是人物或音乐等传统戏剧因素。
第二,传奇创作既有曲词又有宾白,但两者在剧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曲词远比宾白更为重要。看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出的写作即不难知之。欧阳予倩在京剧《桃花扇》中大幅调整曲唱、说白的比例,显著增加了人物对话的分量,使之更适合现代人欣赏。故此,传奇中称之宾白,京剧《桃花扇》中须改称说白或对话。这可以看作是较早的“话剧加唱”的尝试。另外,根据京剧的写作要求,他把原著的曲牌体改为板腔体,对话语言也更加地通俗化、口语化、平民化,增强语言的鲜活度和表现力。
第三,他借鉴了话剧的一些叙事技巧,如田仰其人,和女主角李香君有重大关联(逼婚香君,以致香君血溅扇面,而贞丽代嫁),欧阳予倩把他作为暗场人物处理,让人只见其威不见其人,这不由人不想起《日出》中的金八,虽没有出场,却始终挥不去他的阴影,并最终把陈白露逼上了绝路[8]。这种暗场处理方式有时却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渲染环境气氛,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四、结语
总之,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编,不仅是他本人从艺生涯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一次改编(他创作、改编、修改过的戏曲剧本不下五十部,如《卧薪尝胆》《黛玉葬花》《晴雯补裘》《人面桃花》《木兰从军》《孔雀东南飞》等),而且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写树立了典范,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方面,他尊重原著,依托原著,并不把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完全推倒了重来,另编故事,另起炉灶。这是改编者对于原著所应该抱持的谦逊的态度,和今日大话、戏说经典之风形成了鲜明对比①目前戏剧影视节目中有一种歪曲原著,诋毁、丑化原型的不良风气,如戏说唐僧、孙悟空,诋毁、丑化阿庆嫂、杨子荣等,这是不尊重经典、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试想,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东西,怎么能够让别人去尊重和接受呢?也许能一时轰动,却不能传之久远。应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为改编而改编,对原著照搬照抄,依葫芦画瓢,而是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结合在一起,在改编中体现时代变化,表达时代诉求,为时代观众而改编,适合时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并启其深思。刘勰说过,“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9]321;“变则堪久,通则不乏”[9]331;“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9]331。戏曲改编应该既通又变,既要学习、借鉴原著又要成为一次真正的“创作”。欧阳予倩的《桃花扇》改编,留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
经典阅读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一个热门的生活事件和学习事件。它是涵养心灵、提升品格、丰赡精神、传承文化、倡明风气的重要路径[10]。《桃花扇》既是历史的题材、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应在改编中与时俱进。它是历史和社会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