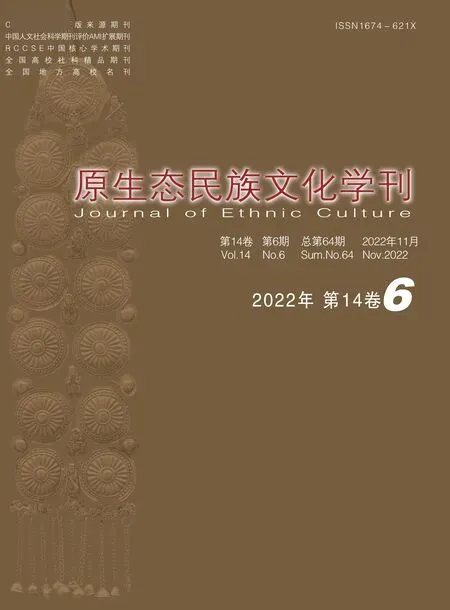天地会传说叙事的文化渊源
2022-02-11陈宝良
陈宝良
一、引论
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颇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据报载,一度声称天地会诞生地和创始人已被确认,即福建省云霄县高溪村为天地会的诞生地,创始人为提喜和尚,创会时间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这一结论,甚至被称为20世纪“我国历史学的重大发现”[1]3,云云。这足以说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相当复杂,于是才不断有新说涌现。
其实,关于天地会的起源,过去即有争论。据有的学者统计,其起源已有13种说法。据笔者看来,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提喜和尚在高溪村创立天地会一说,作为史学界的共识,似乎为时尚早,甚至有点强人所难。笔者借助于对明代秘密社会状况的深入探讨,再综合参考前人对天地会的研究成果,曾经提出过“天地会起源于明代”一说[2]1-10。这是从史实的角度对天地会的起源稍作蠡测。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秘密会社组织,天地会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钱穆曾就帮会的起源做过一个推测,认为那些帮会“主要是由元、明以来,由杭州到北通州运河上的运输工人发展而来”[3]72。尽管钱氏的推测并无实际的史料依据,且帮会与运河上运输工人的关联,亦仅仅涉及天地会起源的一个侧面,但将帮会的起源追溯至元、明,至少说明天地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形塑过程。
进而言之,天地会起源历史的形塑过程,显然关乎两大渊源:一是天地会的历史渊源。这需要从真实的历史记载出发,根据充分的历史依据加以推断。为此,笔者曾认为天地会源自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亦即由宗教结社转化而来。二是天地会的文化渊源。作为秘密社会的天地会,在其传说的“西鲁叙事”中,理应存在着一个文化符号系统。就天地会的文化渊源而言,至少有下面三点属于天地会的文化符号系统来源:一是唐人关于万回的记载,与天地会叙事传说中的万大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二是传统数字文化中的“五”数,与天地会的“五祖”传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三是传统数字文化中的“三”数,以及宗教文化中的“三官”之说,同样与天地的起源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
二、万回其人与天地会万大哥之关系
在天地会文献的历史叙事中,无不把万云龙认定为天地会的创始人,亦即所谓的“万大哥”。这位传说中的万大哥,从文化符号系统的渊源而论,疑源自唐人“万回”,或称“万回哥哥”。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记其事云: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巾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居常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懼焉。万回望其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4]141-142。
万回其人及其故事,同样载于郑綮《开天传信记》,内容与钱易所载相同,仅仅文字叙述稍有差异而已。这则记载至少说明下面两点:一是万回具有“惊人神异”的功能,万里旅程,日夕之间即可来回,甚至具有许多预见。这符合天地会传说的附会、神化意蕴。换言之,万里行程如此急速,唯有云行于云中方可实现。这或许就是“万回”转为天地会传说中的“万云龙”的佐证。二是早在唐代,万回已是妇孺皆知的名人,甚至集贤院中也有其画像。这符合天地会传说中张大其事的意蕴。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万回故事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人物角色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万回成为佛教大师,其事迹开始进入《释氏传灯录》与宋代无尽居士张商英所撰的《护法论》中。据此两书记载可知,万回俗姓张,在进入佛教符号系统后,已成为法名“寂感”的佛僧,又称“张万回法云公”。所谓的“法云公”,显指万回的法号为“法云”[5]136-137。在天地会传说中,万云龙是僧人身份,这正好与万回的身份若合符节。二是在历史的传衍中,一至宋代,民间已将万回塑造成“和合神”。如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持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来回,故曰万回。”[6]335清代诗人无锡张步瀛有诗云:“西风刀尺一灯凉,塞外寒多妾自伤,只恐衣成难寄远,万回哥处暗烧香。”诗中“万回哥”三字,或不能解。其实,根据很多史料记载可以推测,所谓的“万回哥”,其实就是指“和合神”。张步瀛之诗,所用就是这个典故[7]315。当然,有史料指出,和、合一般以二神并祀,而万回仅为一人,两者应有所差别。如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有人以此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有误[8]900-910。其实不然。和、合均有团圆之义,相合成万回一神,显在情理之中。至于其中和、合之义,则无疑与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有着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唐人“万回哥哥”或许就是天地会传说中“万大哥”的文化原型。
至于天地会叙事中将创立人定为“万云龙”,究其原因,无非出自以下两点:一是以“万”为姓,显是为了表达天地会兄弟人数之众。从已有的史料记载可知,至少在汉代的民间谚语中,已经把“物多”称为“无万数”。此谚语出自《汉书·成帝纪》[9]4163。二是至迟自宋代以后,民间隐语已用“方”暗寓“万”。据载,宋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多有其例[10]142-143。至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拆字的方法,仍然流行于官场。如明初苏州知府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得钱一千,则改称“一撇”[11]845。正德时刘瑾擅政,官场贿赂风行,凡行贿钱钞,说馈“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12]81。入清以后,以“万”作“方”仍不乏其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科场事发,正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均被处以腰斩。有人将此事编为《万金记》。所谓的“万金”,就是拆“方”“钱”两字之半而来。此外,又拆“方犹”二字为“一万刀狗酋”[13]114。
以“方”作“万”,则至少有两点与天地会的起源有关:一是在天地会传说中,五房之一为方大洪。其中万、方之间的关系,足以为解读天地会起源提供足够的文化符号依据。二是早在明代,著名学者焦竑有君子“成名立方”之说[14]765。这与黑道上所说的“扬名立万”之说如出一辙。
三、“五”数与天地会“五祖”之关系
在天地会传说叙事中,存在着一个由“五房”演变为“五祖”的说法。这种分房之法,显然也有一个文化渊源可以追溯,且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
首先,“五”数久已融入儒家文化之中,且成为一种文化内蕴。儒家立教,喜欢采用自然界之数,诸如“五常”“五礼”之类。其中所谓的“五常”,显然是效法“五行”而来。换言之,在儒家文化中,“五星”是“五行”之精;而“五常”则为“五行”之用[15]153。在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士大夫群体中,同样存在着一种对“五”数的内在理解,即从“天数五”“地数五”中,推导出“五”数是“无极”的结论。①陈仁锡:《无梦园集》马集《吴音序》,明崇祯六年刻本。这就是说,在“天成象”或“地成形”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来自自然的“道”,亦即“用奇不用偶”的准则。儒家文化对“五”数的重视,无疑已经渗透到民间文化中,其结果则是,在民间的观念中,“五”数为君象,是老百姓禁止使用之数。如在中国民间,一向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为月忌,“凡事必避之”。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三日属于河图数中的“中宫五数”[16]490-491。
其次,“五”数与民间的鬼神信仰密切相关。按照儒家的鬼神观念,《易》即已有了这样一种说法:“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数是变化之源,又可以“行鬼神”[17]409。换言之,天地之数“五”,唯有“五位相得”,方可“各有合”。这个“合”字,与天地会分支的“三合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值得玩味。至于在道教的信仰世界中,更是存在着一种“地上主”的说法,这一“地上主”分别掌管着五岳、四渎与名山大川[18]92-93。
进而言之,在民间的信仰世界中,在有关神灵的建构上,诸如“五显”“五圣”“五通”“五猖”“五道将军”之类,更是大多与“五”数相关。所谓“五显”,全称应作“五显灵顺之神”。根据一般的说法,五显之神,发祥于婺源,时间大概在唐代,或称是唐贞观之初,或称是唐光启之际。至宋代,朝廷给以加封,分别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总称“五显”。明初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南京钦天山之阳设立“五显灵顺祠”,由官方加以祭祀。②宋讷:《西隐文稿》卷5《敕建五显灵顺祠记》,清乾隆三年刻本。所谓“五圣”,或作“五通”,是江南地区普遍信仰的神灵。如杭州灵隐寺后北高峰上,有一座华光庙,“以祀五圣”[19]25。杭州西泠桥,一名西林桥,又称西陵桥。桥畔有一座五圣祠,俗称西陵五圣。凡是经商的商人,无不在此祠“祭献不绝”[20]765。关于“五圣”的出典,存在着两种说法:一是五圣是“五方之神”或“五方之帝”,即东方勾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中央后土,其后演变为白、青、黄、赤、黑五帝。二是五圣是“五行之神”,“与日月并行,与四时错序,伦符五常,道备五德,散于物则为五气之精”。至于神灵的偶像,同样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一母所生五子,而后成为“五方之神”,故后世存在“太母庙”,其中的“太母”,有的记载又称“太妈”。另一种认为五圣之神只有一个神主,即崔刚,又作崔江、崔纲,是宋代四川人,或称清溪人[21]511-512,[22]3342。所谓“五猖”,所祀则为“不祥之气”与“五方恶气”,亦即属于“凶神”,民间专立“五猖庙”加以祭祀。民间所指五猖,从庙中所供神位来看,则为中央黄帝、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23]308。这无疑与天地五方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值得指出的是,“五猖”信仰与天地五方,以及民间“五通”“五圣”信仰,确乎又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关于此,清末人许学诗《素壶便录》有如下详细考辨:
又徽宁凡祈福酬神,辄祀五猖。或谓五猖为五方正神,犹天之五纬,地之五行;或谓乃五通之类。然五纬、五行,未可言猖,惟五通近似,而要皆非也。按猖为猖獗,乃强也。五猖泛言五方强干之神,初无指实。考明《祀典·旗纛之祭》,其神有曰旗头大将、曰六纛大将、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战船正神、曰金鼓角铳炮之神、曰弓弩飞枪飞石之神、曰阵前阵后神祇五猖等众。则五猖乃军营所祀,其曰“等众”,初非五纬、五行之谓,而亦非五通,盖皆浑称无所指名也。况五通五显,实亦正神,唐、宋尝列祀典,无与战阵之事。至若今俗所谓五通,乃吴下淫祀,军营安得聚之?大概徽宁人行商远贾者多,五猖之祀,以资捍御,亦犹军行冀无往不利耳。故亦有称五福者。又俗于神前割鸡沥血,曰剪生,此亦军营之礼。凡大征伐,天子祭军牙六纛,刺五雄鸡血于五酒碗,以酬焉。亦见明典礼[24]611-612。
此段记载颇有价值,大抵可释读出如下意思:一是“五猖”信仰,既非传统的天之“五纬”,与地之“五行”,又有别于“五通”“五显”信仰。究其原因,“五通”“五显”自唐、宋以来,直至明代,均列于官方正祀。二是“五猖”信仰起源于商人外出行商,“以资捍御”,而其来源则是模拟军营所祀。商人外出经营,类同于行走江湖。这种“五猖”信仰,与作为江湖秘密社会的天地会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显然值得做进一步的考释。三是“五猖”信仰中,有在神前“割鸡沥血”之举,这与江湖秘密会社之“刺血”拜盟之举,若合符节。最为值得玩味的是,许学诗所引祀典之例,多出自明代礼典,这又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提供了足够的文化渊源旁证。
通观民间的“五”数神灵信仰,其中有以下两点显然与天地会存在着文化渊源关系:一是“五”数与盗贼信仰之关系。如扬州有“五子庙”,所祀为五代时五位结义兄弟。这五人曾经为盗,“流劫江、淮间”[25]1716。又民间所祀“五道将军”,同样属于“盗神”。按照明朝人田艺蘅的推测,所谓的“五道”,其典出自《庄子·胠箧篇》“盗亦有道”之义。至于“五道”,则指圣、勇、义、智、仁。细言之,即“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26]925。二是“五”数与天地会茶碗阵之间的关系。在民间的“五圣”信仰中,每当遇到冠、婚之类的大礼时,通常会用“茶筵奉上”[27]293。这一“茶筵”,无疑与茶碗阵存在着一定渊源关系。
四、“三”数、“三官”与天地会之关系
在天地会的传说叙事中,与“三”数颇有渊源关系,诸如“三点会”“三合会”之类即是。就文化的符号系统而言,这无疑也是渊源有自。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三”数与天地会之关系。有一个现象需要加以关注,即传统儒家立教,多喜采用“天叙”“天秩”之法,亦即按照自然法则立教。其结果则使立教之人,在“取义”上,或用“三”数,或用“五”数。就“三”数而言,有“三纲”“三德”;就“五”数而言,有“五常”“五礼”“五伦”。“五”数的文化意蕴已如上述,在此不赘。以“三”数而论,诸如“三纲”“三德”之类,其中之“三”,已被清代学者朱一新一语道破,实则效法“三光”之说[28]153。据《史记·天官书》,三光原指日、月、五星,仅限于天象。但在随后的传衍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一是作为天象的“三光”,与地形开始相合,亦即天地并称。如汉代班固《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二是三光之说开始渗入道教的文化符号系统,并进而天地并列。如晋葛洪《抱朴子·仁明》云:“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载无穷者坤也。”三是三光之说渗入佛教的文化符号系统,进而形成“三光天子”之说,并被民间传为“三光菩萨”。三光原是佛家所指大罗金仙(佛)头上的金光、佛光、灵光,后又衍申为“三光天子”,分别为日天子、月天子、明星天子。按照三光的本义,三光理应均作菩萨之形,但据《学海余滴》卷4所载,造佛工匠所造三光之像,仅将明星天子塑为菩萨之形,日、月二天则取天、人之形。
若是以道教文化符号系统为例,其中的“三茅”之说,以及由此而来的“三茅观”,就文化符号的传承而言,与天地会显然存在着诸多的符号联系。如在杭州吴山西南,有一座“三茅观”。三茅观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观中所祀之仙,其原型是三兄弟。据载,这三兄弟之名,依次为盈、固、衷,是秦初咸阳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司礼监太监孙隆重修三茅观,并在观中建“三义阁”,足证在民间的知识系统中,将“三茅”断为结义的三兄弟。假若这一结义形式属实,那么“三茅”结义明显早于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而这种结义形式,恰恰符合秘密社会的结拜特点。二是所谓的三茅,即兄弟三人,其后得道成仙,从汉代以后已经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崇祀。观中三茅之像,一立、一坐、一卧,其中的意义很难解读。但据明末清初人张岱的猜度,其意或许是一种修炼功夫,即行立坐卧,均属修炼,教人不可“蹉过”[29]98。
其二,“三官”信仰与天地会之关系。传统中国民间,广泛信奉“三官”。就经典而言,传世的有《三官经》。据《三官经》所述,有一陆氏之子,娶龙女之后,生有三子,均有神通,后得道受封,成为天官、地官、水官。据明末清初史家谈迁所言,这部《三官经》属于“妄人”所撰,但也有一种传说,认为《三官经》是明英宗在南宫幽居“无聊时所作”[30]503,[31]351①吴翟辑撰、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卷7《外神祀考证》,第293页。。就庙而言,民间到处立有三官庙、三官祠。就习俗而言,民间又有上元、中元、下元三节,将此三节作为祝祷三官之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祝祷天官;七月十五为中元节,祝祷地官;十月十五为下元节,祝祷水官。在东南地区,每年的正月、七月、十月,民间均有斋素之俗,称为“三官素”。更有意思的是,在民间三官信仰的传衍中,其知识累积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将原本属于道教信仰系统的三官信仰,转而建构为佛教信仰系统的“三官菩萨”;二是民间三官信仰的俗化,即民间认为三官菩萨有大量,人若持“三官素”,可以不忌荤腥之物,只要不吃“特杀之物”,即属斋素,故民间又有“假吃三官素”之谚[32]14。
关于“三官”的出处,宋濂《跋三官祠记》有云:
按汉熹平间,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盛。盖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昉于此也[33]205。
宋濂的这则记载,同样可以从刘基的记述中得到印证,且足以证明在元末,三官信仰已经遍布江淮地区。如刘基所著《郁离子》中有一篇《神仙》,其中记载:“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而致斋以邀祥焉。满三年计之,多不得祥而得祸。”[34]52云云。
在宋濂所载三官传说中,若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观察,显然存在着不合情理之处。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至高者是天,至厚者是地。水即使很大,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物而已,显然很难与天、地相抗衡。如明人陆容曾就此提出以下质疑:“水为五行之一,生于天而附于地,非外天地而为物也。今以水与天地并列,已为不通之论。若其使民服罪之书,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既云上之天,则置之云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则山非地乎?其诬惑蚩蚩之民甚矣。”[35]110这种质疑无疑出于儒家知识人的正统之论,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忽略了民间信仰具有一种混合众说的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与儒家文化精神相合。就此而论,将天、地、水三者并称为“三官”,宋濂的追溯与阐释,显然“足破群疑”[36]。
当然,三官信仰的文化符号价值,并非仅仅限于此,而是逐渐融入天地会起源的文化符号中。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观之:一是在三官信仰中,将天、地、水视为“三官”,以天、地并称,固然与“天地会”之名相合,即使是天、地、水并称,也与“三合会”之名若合符节。如其中所云水官的起源,将符“沈之水”,无疑与天地会传说中将秘密文书藏入铁箱,沉之海底,而后称为《海底》(或称《海底金经》),其中文化符号的传承关系亦揭若昭然。此外,加入一个水官,其影响更是及于天地会符号中多三点之水的文化传统。二是据前述刘基的记载,在民间的三官信仰中,多“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其中斗星所指及其相关干支寅、申、亥,与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拜斗钻刀”之间的关系,更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解读。进而言之,儒家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三皇本纪》,所称天皇、地皇、人皇“各一万八千岁”,其中相传之数,显然本于邵雍演绎易理的《皇极经世书》,书中所云“一万八千岁而天开于子,又一万八千岁而地辟于丑,又一万八千岁而人生于寅”,其实就是“三皇之数”。①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85《引瑯琊漫钞》,第1797页。这一记载中的子、丑、寅三天干,其中与天地会传说文化符号同样不无关系。三是三官信仰的传说中,其中有“始皆生人,而兄弟同产”之说,即由龙女所生。即此一点,明人归有光就已敏锐地察觉到,与“汉茅盈之类”存在着相似之处。归氏所言“茅盈”,即指“三茅”信仰中的盈、固、衷三兄弟,尽管仍被归氏斥为“其说诡异,盖不可晓”[37]402,但其间的兄弟甚至结义兄弟关系,更是成为天地会传说中的文化符号渊源。
五、余论
综上所述,在追溯天地会的起源中,必须关注天地会传说叙事中的文化符号渊源。稍加归纳,天地会的文化符号渊源,大致有三:一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有一位“万大哥”,其文化原型显然源出于唐代的“万回哥哥”。至于所用的“万”字,既不是姓,而是属于隐语系统的数字符号,这又影响到后世天地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传统,即“以万为记”或“以万为姓”。二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存在着“五祖”之说,且有以五分房的传统。这同样源出于传统中国的“五”数文化符号。三是在天地会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分化“三点会”“三合会”,这显然与传统中国“三”数文化符号,尤其是“三茅”“三官”信仰存在着文化传承关系。概言之,天地会传说的文化符号相当复杂,既有来自儒家易理中的数字符号,又有来自道教、佛教的文化符号。自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一出,儒家的数字符号开始羼杂了道教的文化因子,更使秘密社会在叙事中找到了文化共鸣。当然,相较而言,天地会的文化符号传统,更多的是来自道教与佛教文化,甚至是儒佛道三教文化符号合流的产物。
尽管“万”“五”“三”之类的数字文化符号体系,早在汉唐以来即已出现,但其定型及其广泛流行,则无疑是在明代。不止如此,将天地会的起源定为明代,尤其是源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天地三阳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大多融合儒佛道三教,而明代尤其是晚明正好是三教合流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