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字改革,一部民族自强史
2022-02-10吴尚蔚
吴尚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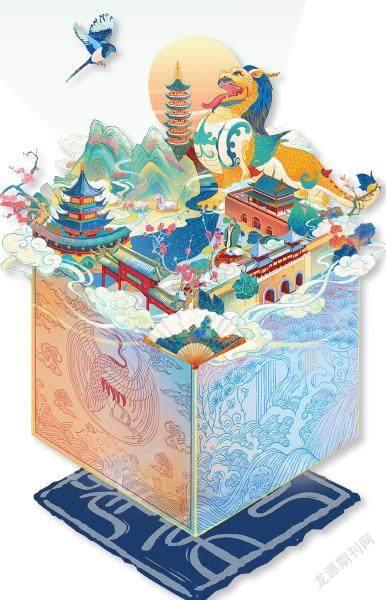
对今日的多数人而言,学习汉字、拼音、普通话,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大体上奠定今日之格局的,正是“国语运动”。
我们可能会惊讶于这个运动中那些极为激进的主张,例如废除汉字。我们可能会觉得意外:一些我们在今日越来越多地思考的问题,例如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之间的张力,原来早在民国时期就被热烈地论辩过了。只不过,国语运动中那些参差多态的观点与论述,很少进入今人的视野。
如果没有普通话,两个中国人能否自如地交流呢?
1905年刊载于《南洋日日官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不同通商口岸的人相遇时,由于方言不通,常常以英语交流。
另一则事例来自民国元老颜惠庆的回忆:20世纪初于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一个福州籍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
在还未确立国语或普通话的年代,作为“殖民工具”的外语,已渗透进中国。1900年代,维新派人士汪康年注意到,日本在福建、浙江开设了一些日文学堂,俄国也在东三省和直隶省推广俄语。在他看来,此举“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
1920年代,一篇名为《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的文章提到,在中国,不同外语的分布范围与列强的势力范围重合:英语盛行于沪宁铁路一代,法语在云南颇有影响力,日语是在南满铁路沿线和山东,俄语则是在北满和新疆的一部分。
且不论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真的能用外语交流,以上事例的讲述者无疑都经历过一种不安:列强环伺,国人亟需团结一致,而若是没有一门共通的语言,人们如同一盘散沙,无法沟通协作,又谈何富国强民?
在时人眼里,方言林立并不是民智开启、人心团结的唯一障碍。另外两个阻碍,还包括难学的汉字和佶屈的文言。于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国语运动(广义)得以产生,在文字、文体、语言三个层面展开,从1890年代绵延到新中国建立。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们普遍认为,强国需先智民,普及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当时,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国人识字率太低。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
改造文字,便成了一项重任。有的方案较为温和,例如创造一套与汉字并行的拼音文字,辅助汉字的学习。最为激进的方案,则要求废除汉字。
废除汉字的理由大同小异,既有实用性的考量,又有学理上的支撑。
实用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难记、难写,浪费时间。二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便于检索和机械化,特别是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
学理上也存在着一种推崇拼音文字的态度。清人介绍的斯宾塞学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学说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二是文字由图画而来,经过象形,进入拼音阶段,从象形到拼音是进化的必由之路。
在那个人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年代,被放到进化论的滤镜下进行考察的,不仅是语言文字,更是它们所关联的社会。野蛮和文明,被认为是社会进化的两个端点,而与“文明”的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是“野蛮”的。许多人认为,文字应当为此负责。
鲁迅就说过:“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或许此观点颇为偏激,但鲁迅的观点表明了在中华民族经历动荡之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反思,急于寻找出路。
汉字被废的理由,还包括其阶级属性。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提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但一度被诸方嫌弃的汉字,终究没有被废除。
同汉字一样,汉语也曾经历过“至暗时刻”。根据西方学者早期提出的语言分类法,汉语因为“没有语法”或“语法简单”,被归入人类语言中的“落后”部分,被视为“东方黑暗”的绝佳案例。
看似“科学”的语言分类,实质上充斥着欧洲中心主義的偏见。王东杰教授论述道:
“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资料,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这是在知识上对世界的驯化。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
所幸的是,国语运动时期,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胡以鲁就批判过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等人,说:“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语,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
有趣的是,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语言“进化”程度的判断标准在发生改变。一些人认为,一门语言也可能从复杂进化为简单,这种由繁趋简的态势在英语的发展历程中就有所体现。
一旦采用“简单”作为进化标准,汉语便具有了优势。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据此力争,以至于到1930年代末期的时候,陈梦家底气十足地说:“中国语法的简单,没有‘时’‘数’‘性’‘人称’等变化,正是中国语进步的优点。这已渐渐为人所公认了。”
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而是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王东杰教授认为,这种关怀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若一定需要用词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除了对外谋求民族独立自强,对内实现民主平等也是国语运动的政治考量。
然而,对于如何保证“民权”,人们莫衷一是,在哪种语言有资格成为国语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国语语言标准而言,影响最大的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另一派要求会通“异言”,另成一套标准。
支持北京话的人认为,以首都方言为国语,是各国通例。有人力证北京话是各地语言交融的结果,通行地域最广,通晓人数最多,因而符合民权主义者所在意的“多数”原则。
但在当时,北京话会让人联想到清廷、君主、专制,令许多民权人士反感。京话反对者认为,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须尽量隔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北京话仍然是一种方言,强迫大家都说,就是不公。
于是,会通派呼声日高。会通派大致主张参考古代韵书,兼顾南北,专门制定一套标准音。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便以参会者投票决定的方式,确定了一套语音标准,即今天所谓的“老国音”。不过,在这套“老国音”当中,京音其实也已占相当的比重。
国音标准的确立被不少人视为一个塑造理想中国的手段,不仅要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还要在保留汉语传统和适应现代需求之间求得平衡。
但人为筛选、制定出来的“老国音”,后来被批评为“死语言”。而北京话因其是一门“活语言”,又受到了支持。终于,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以北京话为国音的标准。这便是所谓的“新国音”。
1930年代,左翼文化兴盛起来,为批判式地看待“国语”加入了新的视角。例如,代表人物瞿秋白认为,“国语”是多民族国家中统治民族“同化异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确实,自“国语统一”的口号提出以来,许多讨论者都自动将汉语视为“国语”,少数民族语言基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才来应对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定位的问题。
左翼语文革命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也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所谓的“国语统一运动”,反对“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他们主张以各大方言区为单位,制定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让大众先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他们并不反对共通语,但坚决反对“强迫”“侵略”。
保护方言的主张
面临汉语方言林立的现实,国语运动需要处理好“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运动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明确宣称,国语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统一国语的同时,也应容许甚至鼓励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语统一不能以方音湮灭为代价。
在民主、個性、反专制的价值引导下,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运动一直存在对语言“过度统一”的警觉,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
这种追求体现在知识分子对于所谓“标准口音”的态度上。在刘半农看来,只要他见了广东人不需要说英语,国语普及的目标就达到了。钱玄同认为,好国语绝不是“音正腔圆”,若“硬要叫他统一”,就只能“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
实际上,方言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可以说地位较高。王东杰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取向与此也有关联。
在传统的社会伦理观里,抛弃原籍言语可能被视为“卖祖宗”、忘本。相应地,游子归来能否“乡音如故”,甚至成为判别品行高下的标准。
当然,知识分子对方言的支持,除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恐怕包含了情感的因素。提倡方言文学的俞平伯就说:
“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热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
俞平伯的话,今人未必完全认同。母语一定有助于我们流露自己的性情,表达自己的感受吗?
总之,反对废止方言可以说是国语运动的共识。国语与方言并行的“双语”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虽然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运动主将们主张保存方言,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担心得更多的,或许还是国语是否能成功推行。
具有语言学知识的他们,定是知道语言总是在不停地流变。他们不一定料到的是,在媒体众多、互联网发达、人口快速流动的今天,方言的变化速度会如此之快,一些方言甚至出现消失的趋势。
我意识到,作为一个90后四川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经历了普通话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对四川话的面貌的改变。
学校自然是一个重要情境。尽管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不少老师还用四川话教课,但同学们仍在课堂上学到大量的书面语词汇,在生活中也就倾向于不使用它们所对应的方言词汇。
若一些词汇并不是从日常的四川话语境中习得,大家也习惯凭借其普通话发音去推测四川话发音,很容易就偏离了“正确”的四川口音。
互联网则是另一个重要情境。如果说广播、电视是让人学会“听”普通话,那么互联网和新媒体则让更多的人学会“说”普通话。
我家原本在一个小镇上,后来搬到县城里,在日常生活中,我和爸妈都不说普通话。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普通话,是在家里买了电脑以后。那时他玩起了语音聊天室,跟天南海北的网友聊天,自然要用普通话。最近两年,爸妈常刷抖音、快手,而他们的四川话,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了。
现在的许多长辈认为,就算教四川话,也要教“标准一些”的四川话,这里所谓的“标准”是指跟普通话接近。随着父母这代人逐渐变成祖父母,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也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向普通话靠拢,试图摆脱一些“土音”。
自十七岁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来,我的四川话像是放进了冷冻室,从没变过。今年春节在老家县城的街头放耳一听,只觉得年轻人口中说的,并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四川话。
在电影院里观看《刺杀小说家》时,北京演员董子健说的重庆话让我觉得亲切。他学的重庆话,可能比影院里众多年轻观众们的四川话要“地道”得多。
古人说,少小离家,乡音无改。而今日的故乡,可曾还有不变的乡音,等着游子的归来?
(摘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