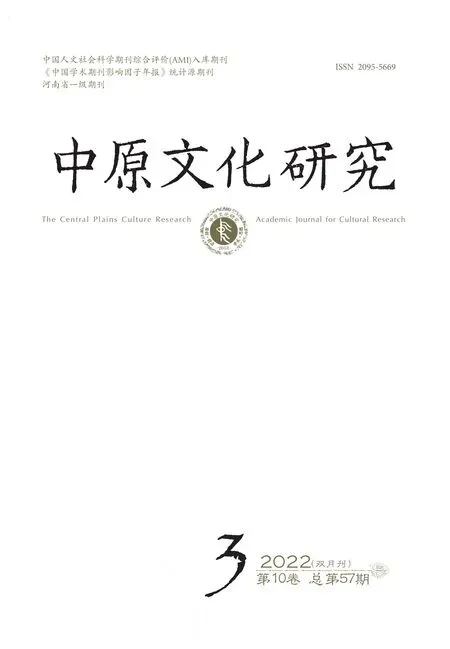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2022-02-09袁延胜
袁延胜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荆州博物馆在胡家草场墓地发掘了18 座古墓葬。其中,西汉墓M12 出土了一批简牍,简4636 枚,牍6 枚,简牍总数量4642 枚,保存状况总体良好。经过初步整理,这批简牍可大致分为岁纪、律令、历日、日书、医杂方、簿籍、遣册等7 类。其中岁纪简共160 余枚,按照竹简形制分为两组。第一组简长约27.5 厘米、宽约0.5 厘米,所记内容为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时期的大事,每年一栏,通栏书写;第二组简长约27.5 厘米、宽约1 厘米,该组简有卷题《岁纪》,所记内容为秦二世至汉文帝时期的大事,每年一简,按月分栏书写。综合器物形制和竹简内容,M12 应为汉文帝时期的墓葬,下葬年代不早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1]20。
胡家草场西汉墓的整理工作进展很快,《考古》杂志2020年即刊出了发掘简报和出土简牍概述①,2021年出版《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公布了192 枚简牍[2],其中公布的《岁纪》简共有9 枚,为我们研究战国秦汉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公布的这9 枚《岁纪》简中,其中1 枚为标题简,只有“岁纪”二字,其他8 枚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始皇、汉高祖、吕后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正史、补史。本文就以公布的这9 枚《岁纪》简为基础,对其中涉及战国时期韩、魏的历史,秦国的历史,西汉初年的历史做一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岁纪》所见秦昭襄王时期对韩、魏的攻取
公布的9 枚《岁纪》简中,秦昭襄王时期的简有3 枚,年代分别为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四年(公元前303年)、十四年(公元前293年),内容主要是秦攻占韩、魏之地的记载。下面按照简文的时代顺序进行探讨。
(一)秦昭襄王元年“取宜阳”的年代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事始于秦昭襄王元年,该年记事为:“取宜阳。”(简1532)[2]图版第3 页,释 文 第191 页
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是韩国西部防御秦国的战略要地,地位重要。早在韩烈侯九年(公元前391年)和韩昭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39年)的时候,秦就攻打过宜阳②。经过秦惠王时期的发展,到秦武王即位时,秦的国力已经很强大了。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3]2311,但“车通三川”,必然要经过韩国的宜阳,因此秦武王就与丞相甘茂商议伐韩之事。甘茂认为宜阳是韩的大县,韩国又长期经营,攻取难度大,担心一旦战争胶着会招致秦国亲韩大臣的非议。为了消除甘茂的担心,秦武王与甘茂在息壤结盟,表示坚决支持甘茂伐韩。“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3]2312由此可见,秦国攻打宜阳的过程很艰难,历经数月才占领宜阳。
秦攻打宜阳是秦武王三年秋天,而攻取宜阳则在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上半年。《史记·秦本纪》载武王三年“其秋,使甘茂、庶长封③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3]209。秦攻占宜阳后,秦武王就亲往东周,以窥周鼎,并自恃力气大,与孟说一起举周鼎,结果“绝膑。八月,武王死”④。八月秦武王死,则秦攻占宜阳肯定在八月之前。结合甘茂五月未拔,增加兵力后才攻取宜阳,则秦攻打宜阳历时应在半年以上。从时间上推算,秦武王三年秋天攻打宜阳,经过半年,则秦攻取宜阳可能在秦武王四年的春天或者夏天。不论攻占宜阳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在史书中多有印证。如《史记·周本纪》载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秦攻宜阳,楚救之。”[3]161《史记·六国年表》韩襄王五年(公元前307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拔宜阳城,斩首六万。”[3]735但胡家草场汉简《岁纪》却把秦“取宜阳”的时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秦武王无子,立异母弟,是为秦昭襄王。但“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3]209。武王八月死,昭襄王从燕国回归,可能需要一定时日,则昭襄王继位可能在九月。但不管昭襄王几月继位,其改元应在第二年,即秦武王四年之后改元。如果是这样,则发生在秦武王四年的“取宜阳”之事,就不会系于秦昭襄王元年。
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性质相同的是睡虎地秦简《编年记》⑤,《编年记》记载秦昭襄王以来的部分大事,时间上与《史记》也有一年之差。对此,黄盛璋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可能和各国用历不同有关。《编年记》和同出其他文书都确证秦在统一六国前早就采用颛顼历,即以十月为岁首,而其他各国皆不用十月为岁首。因此,发生在十月到十二月间的事件,秦与他国可能有一年之差。”⑥由此我们推测,因秦用颛顼历,秦武王四年十月,即为秦昭襄王元年。从以正月为岁首的夏历来看,秦“取宜阳”是发生在同一年的事,因此把此事系在秦昭襄王元年。《岁纪》系年的不严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岁纪》可能是西汉人整理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秦代史书。
(二)秦昭襄王四年攻取韩、魏之地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秦昭襄王四年攻打韩国,夺取韩国、魏国之地的事。简文为:“四年,攻(韩),取蒲反、武(遂)、阳晋。”(简1437)[2]图版第4 页,释文第191 页
对于秦昭襄王四年之事,《史记·秦本纪》载秦“取蒲阪”[3]210。《史记·韩世家》载韩襄王九年(公元前303年)“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3]1872。《史记·六国年表》载韩国该年“秦取武遂”[3]735。《史记·魏世家》载魏哀王十六年(公元前303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3]1852。《史记·六国年表》载魏国“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3]735-736。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秦昭襄王四年“攻封陵”[4]“释文”4。
由这些记载可知,秦昭襄王四年,秦不但攻打了韩国,而且还攻打了魏国,并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漏记“封陵”,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只记载“封陵”来看,《岁纪》类简牍在记载国家大事时,是有所取舍的,并不全面。另外,从《岁纪》记载的“阳晋”来看,《史记·魏世家》记载“阳晋”正确,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晋阳”是错误的。张守节《史记正义》“阳晋当作‘晋阳’也,史文误”[3]1852的解释,是不对的。另外,从《岁纪》“蒲反”一词来看,“蒲反”应是通行的写法,而“蒲坂”可能是通假使用。
综合来看,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秦昭襄王四年之事并不严谨,如把攻占韩国、魏国之地混在一起记载,对攻打魏国之事也没有记载。如果严谨一些,《岁纪》简文内容应调整为:“四年,攻韩,取武遂。(攻魏,取)蒲反、阳晋。”下面就简文中涉及的几个地名做以补充。
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南),是韩国的重要战略之地。早在秦武王四年攻占宜阳后,就“涉河,城武遂”[3]209。但不久之后,即韩襄王六年(公元前306年),秦把武遂归还给韩国,史载“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3]2316,“秦复与我武 遂”[3]735。但 过 了三年,秦又攻占武遂。对于秦反复攻占武遂,杨宽先生认为:“是年(笔者注:指秦武王四年)秦拔韩宜阳,并北上渡河占武遂筑城,次年秦又归武遂于韩,此乃当时震动各国之大事。武遂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以北,正当宜阳以北,为韩重要之关塞,并有重要之通道,南下渡河可通大县宜阳,北上可直达韩之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隧’常用以指山岭、河流上以及地面下穿凿之通道,武遂即利用黄河与山岭穿凿而成,用以贯通韩南北之通道。《史记·秦本纪》与《史记·六国年表》皆谓秦拔韩宜阳之后,即渡河占有武遂而筑城防守,绝断韩贯通南北之通道,以此作为威胁要挟韩国屈服之手段。”[5]586-587秦昭襄王四年再次占领武遂,是对韩国安全的再次威胁。
蒲反、阳晋、封陵,这三个地方都是魏国的战略之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秦昭襄王四年“攻封陵”,五年“归蒲反”[4]“释文”4。整理小组注:“封陵,魏地,《水经注》作风陵,即今山西芮城西南风陵渡。”“蒲反,魏地,古书或作蒲阪、蒲坂,今山西永济西。”[4]“释文”8阳晋之地不详,但应该在今山西永济西南的濒临黄河一带⑦。杨宽先生说:“蒲阪、晋阳(笔者注:应为阳晋)、封陵皆为河西通往河东之重要渡口,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武遂与封陵为韩、魏防守之要地。”[5]630,587由此来看,秦昭襄王四年攻占的武遂、蒲反、阳晋、封陵,皆为韩、魏的战略要地,是秦削弱韩、魏实力的重要步骤。
(三)秦昭襄王十四年秦与韩、魏伊阙之战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秦昭襄王十四年大胜韩、魏联军,取得伊阙之战胜利的事。简文为:“十四年,大胜(韩)、(魏),杀公孙喜伊(阙)”(简1415)[2]图版第5 页,释文第191 页
伊阙之战,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大战,史书多有记载。《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3]212《史记·穰侯列传》载:“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3]2325《史记·白起列传》载:“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3]2331《史记·韩世家》载韩釐王三年(公元前293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3]1876《史记·魏世家》载魏昭王三年(公元前293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3]1853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秦昭襄王十三年“攻伊〈阙〉”“十四年,伊〈阙〉(陷)”⑧。
对于《史记·白起列传》所载秦昭襄王十三年“击韩之新城”的新城,《史记索隐》曰:“在河南也。”《史记正义》曰:“今洛州伊阙。”[3]2332《史记·秦本纪》“新城”,《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云:“洛州伊阙县本是汉新城县,隋文帝改为伊阙,在洛州南七十里。”[3]214伊阙,即今河南洛阳龙门,新城应在龙门附近。杨宽先生结合秦简《编年记》的记载,认为“盖新城为韩新建之城,用以防守与保卫伊阙之要害者,故此新城,既名新城,亦可统称为伊阙。白起于昭王十三年所攻者为新城,《编年记》统称为攻伊阙,白起于十四年又大破韩、魏于伊阙,是役相战两年,白起先攻克韩之新城,继而韩得魏之助,退守伊阙,白起又大破之。”[5]707
伊阙之战持续两年,秦国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是对韩、魏两国,尤其是对韩国的沉重打击。杨宽先生说:“伊阙为韩在中原重要之关塞,因而伊阙之战成为秦与韩、魏之决战。”“从此削弱韩、魏二国之战斗力,范雎谓‘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5]721伊阙之战,秦军主帅是白起,韩、魏联军主帅是魏国的司马喜。《史记·秦本纪》《史记·穰侯列传》等记载秦军俘虏了公孙喜,但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却记载“杀公孙喜”,与《史记》记载有异,而与《战国策》《韩非子》等记载一致。《战国策·西周策》载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6]55杨宽先生认为犀武“当即公孙喜之称号,犹如公孙衍之号称犀首也”。同时认为“伊阙之战又称周南之战”[5]721。《韩非子·说林下》“周南之战,公孙喜死焉”[7]204,《岁纪》“杀公孙喜伊閒(阙)”的简文,印证了《战国策》《韩非子》的记载,明确了公孙喜的结局,也为伊阙之战抹上了又一层悲壮之色。
《岁纪》“大胜韩、魏”中的“大胜”两字,显示了秦在伊阙之战中取得的重大战果。《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3]1729《史记·楚世家》用的也是“大胜”两字,由此可见伊阙之战影响之大。
二、《岁纪》所见秦王政对韩国的攻占
公布的《岁纪》简中,秦王政时期的简有2枚,年代分别为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容主要是秦灭韩过程的记载,以及秦国的其他大事。
(一)秦王政十六年“破韩”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作丽山、初书年、破韩等大事。简文为:“【十六年,始】为丽邑,作丽山。初书年。破(韩),得其王,王入吴房。”(简1538)[2]图版第6 页,释文第191 页
对于秦王政十六年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十六年(公元前231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3]232《史记·六国年表》“秦”栏载:“置丽邑。发卒受韩南阳。”“魏”栏载:“献城秦。”“韩”栏载:“秦来受地。”[3]754综合《史记》记载,该年秦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在丽山营建秦始皇陵;二是命令秦国男子申报年龄,这在秦简《编年记》有体现⑨;三是魏国献地于秦;四是韩献南阳之地于秦。
与《史记》所载相比,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内容多出了对韩国和韩王的记载,这丰富了秦灭韩过程的记载,极为珍贵。首先,《岁纪》“破韩”记载,揭示了秦占有韩南阳之地是经过战争手段夺取的,而非韩的自愿献出。《史记·六国年表》所载秦“发卒受韩南阳”,是建立在秦武力威胁基础上的,或者是秦击溃韩的抵抗后获得韩国土地。其次,《岁纪》“得其王”记载不见于《史记》,简中的“王”,应是指韩王安。结合“破韩”的记载,应该是秦在攻打韩国南阳的时候,韩王安亲临前线,结果兵败被俘,也可能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韩王安主动献地求和。“得其王”的“得”可以理解为“俘虏所得”,也可以理解为韩王主动请降。似以后者更为符合历史实际。最后,《岁纪》“王入吴房”,记载了韩王安该年的去处。吴房,故房子国,春秋后期以封吴,故曰吴房。汉初属于南阳郡,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别属汝南郡,治今河南遂平县西[8]263,425。对于“吴房”,孟康注曰:“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槩奔楚,楚封于此,为堂谿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堂谿亭是。”[9]1562汉初曾“封杨武为吴防侯”[3]336,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国除为县。周振鹤等认为吴房原属南阳,文帝十二年“割南阳之东部西平、郎陵、阳安等数县及吴房、慎阳、成阳等侯国置汝南郡”[8]421。从郡县沿革看,吴房在战国晚期应属于韩国南阳郡所辖。尽管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置南阳郡”[3]213,但并非占有全部南阳之地,当时秦可能只占有宛城以西地区,南阳东部之地还被韩国掌握⑩。
从《岁纪》来看,秦王政十六年,秦国占领了韩国所辖的南阳之地,但可能还保留了南阳东部的“吴房”县,供韩王安暂住。从“王入吴房”一语来看,是指韩王安来到吴房。但究竟是韩王安流亡到了吴房,还是秦国安置他到了吴房,还不易判断。但考虑到韩国的统治中心是在颍川,则“王入吴房”似乎是韩王安被迫流亡到了吴房。
(二)秦王政十七年灭韩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太后死、韩国灭亡等大事。简文为:“十七年,十二月,大(太)后死。五月,(韩)王来。(韩)入坨(地)于秦。”(简1535)[2]图版第7 页,释文第191 页
对于秦王政十七年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3]232《史记·韩世家》载:“(韩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3]1878《史记·六国年表》“秦”栏载:“内史腾击得韩王安,尽取其地,置颍川郡。华阳太后薨。”“韩”栏载:“秦虏王安,秦灭韩。”[3]754-755综合《史记》记载,该年秦的两件大事:一是华阳太后死;二是灭韩,在新占领的韩国之地设置颍川郡。而对于韩国而言,韩王安被俘,韩国灭亡。韩国的灭亡,拉开了秦统一六国的大幕。
韩国灭亡的时间,《史记》系于秦王政十七年,但具体的月份则不清楚,《岁纪》明确为该年五月,丰富了我们对该历史进程的认识。但《岁纪》所载的“五月,韩王来”,则又与《史记》所载的“秦虏王安”“得韩王安”有所不同,似乎韩王安是主动投降的,而非抵抗后被俘。但结合《史记》“内史腾攻韩”“内史腾击得韩王安”,以及秦简《编年记》“(秦王政)十七年,攻韩”[4]“释文”7的记载,秦灭韩是经过武力夺取的,而非韩的主动纳降。由此来看,《岁纪》所载的“五月,韩王来”,应是在韩国抵抗失败后,韩王被迫向秦纳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可能是“韩王来”的又一种表述。“得韩王安”是指秦俘虏韩王,“韩王来”应是指韩王战败后主动向秦表示臣服。可能秦俘虏韩王安之后,韩国之地还没有全部被秦国占领,这些地区可能还存在零星的抵抗,需要韩王安投降后,去招降这些地区。因此《岁纪》在“韩王来”之后,就记载“韩入坨(地)于秦”。这表明,韩地全部入秦,应该有韩王安的招降之功。同时结合《岁纪》上年“王入吴房”记载看,韩王安可能在吴房一带组织了对秦的抵抗,失败后被俘,才去招降韩国其余地区的。
韩国是秦灭亡六国中的第一个国家,秦国可能为了减少统一进程中的阻力,就对投降的韩王进行了宽大处理,把他安置在一个“□山”的地方,韩王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去世。秦简《编年记》载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7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⑪
三、《岁纪》所见刘邦、吕后时期历史
公布的《岁纪》简中,西汉早期的简有3 枚,年代分别为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九年(公元前198年)、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内容主要是刘邦平定关中、立赵王以及吕后施政措施等事,这些记载有的不见于史书,有的与史书记载不一致,深化了对西汉早期历史的认识。下面按照简文的时代顺序进行探讨。
(一)汉高祖元年“杀章邯”等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高皇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王汉中、杀章邯等大事。简文为:“高皇帝元年,十月,王汉中。立十二年,孝惠皇帝立。十二月,王举汉中兵入武关,杀鄣(章)邯。”(简1539)[2]图版第8 页,释文第191 页
该条《岁纪》所记高祖元年之事,《史记》《汉书》也有记载,但时间、地点有所差异。如高祖“王汉中”的时间,《岁纪》记为“十月”,史书记载刘邦正月立为汉王,四月就国。《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3]362,365,367《汉书》记载与《史记》略有不同,把刘邦封汉王时间记为二月。《汉书·高帝纪》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9]22,28,29但结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元年“正月,分关中为汉”[3]776-777的记载,刘邦立为汉王,应在正月。因为汉初沿用秦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汉代史家把十月作为汉元年的开始。如前引《史记·高祖本纪》就是以十月,沛公刘邦至霸上为汉元年的开始。由此来看,《岁纪》所载“十月,王汉中”,应是在十月为汉元年的基础上来记述的。把刘邦“王关中”的时间前移,可能意在强调汉元年的合法性。只是这种记载与历史事实有些距离,因此,《岁纪》刘邦“王汉中”时间记载与其说是错误,毋宁说是汉代人维护汉朝法统的一种表达。
除了“王汉中”记载外,《岁纪》“十二月,王举汉中兵入武关,杀鄣(章)邯”的记载也与史书不一致,不一致包括时间和地点。关于刘邦出汉中,还定三秦之事,《史记》《汉书》都有记载,出兵的地点是故道,时间是五月或者八月。汉灭章邯的过程,《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四月,刘邦到关中,“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3]368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3]369,37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汉元年八月“邯守废丘,汉围之”,汉二年五月“汉杀邯废丘”[3]783,787。对于 刘邦出汉中袭击章邯的时间,《史记》记载为汉元年八月,而《汉书》记载为五月⑫。《汉书·高帝纪》:“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9]31对于章邯被杀之月,《汉书·高帝纪》系于汉二年六月。综合以上记载,汉王还定三秦有汉元年五月、八月之异,章邯被杀有汉二年五月、六月的不同,但都与《岁纪》中的“十二月”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岁纪》中的“十二月”,并非汉元年十二月,或者汉二年十二月,而是指首尾十二月之意,是指一个时间段。如果取信《汉书·高帝纪》汉元年五月从故道出袭章邯,以及《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二年五月“汉杀邯废丘”的记载,则章邯从被袭到被杀,首尾一年,刚好符合“十二月”之数。
《岁纪》记载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汉王出汉中的路线问题。《史记》《汉书》记载刘邦还定三秦的路线是出“故道”。《史记集解》:“《地理志》武都有故道县。”[3]368孟康曰:“县名,属武都。”[9]31另外,从韩信和曹参作战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汉军是从陈仓故道进军,还定三秦的。《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元年“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3]2613。《史记正义》注曰:“汉王从关北出岐州陈仓县。”[3]2613《汉书·韩信传》曰:“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9]1866《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斄。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3]2024故道,严耕望先生认为即陈仓散关两当略阳道⑬。东汉《石门颂》有“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10]49之语,其中的“出散入秦”,指的就是刘邦从陈仓散关故道进军关中。
汉军是从陈仓故道,也就是今天陕西宝鸡一带出兵的,但《岁纪》却记载为从“武关”进军,与史书记载不同。但在刘邦与章邯作战的一年中,确实也有出武关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的同时,“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3]368。《汉书·高帝纪》载汉元年:“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9]32从记载来看,汉王刘邦遣兵出武关,主要是从南阳到沛县迎接太公、吕后,而非攻打章邯。当然,也不排除刘邦曾派兵从武关攻打章邯,但考虑到项羽“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3]316,如果汉王从武关进兵关中,首先面对的是塞王司马欣,而非咸阳以西的雍王章邯。因此,刘邦还定三秦之初就从武关攻打章邯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在塞王司马欣降汉后,从武关出兵攻打章邯是有可能的⑭。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汉兵从陈仓故道进军的记载。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岁纪》的编写者混淆了刘邦从武关进军灭秦的历史与刘邦灭章邯的历史。刘邦西入武关灭秦,是西汉立国的大事,而刘邦统一天下面对的第一个劲敌是章邯,因此《岁纪》编写者误把汉王刘邦灭章邯的路线记为“入武关”也是有可能的。
(二)汉高祖九年“立赵王”等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高皇帝九年(公元前198年)立赵王、大疫等事。简文为:“九年,正月,立赵王。丙寅,(赦)殊死以下。二月,大伇(疫)。七月,以丙申朔=(朔,朔)日食,更以丁酉。”(简18)[2]图版第9 页,释文第191 页
《岁纪》所记高祖九年之事,“立赵王”“赦殊死以下”两件事史书有记载。而“大疫”、改朔日二事不见于记载,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正月,立赵王”之事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3]386。“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9]67从记载来看,赵王张敖被废和刘如意徙为赵王,都在正月。《岁纪》所载与《汉书》相同。
2.“赦殊死以下”之事
《汉书》有记载:“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9]67《岁纪》与《汉书》记载的正月丙寅赦罪诏书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汉书》记载的内容详细,《岁纪》简略而已。
3.二月“大疫”之事
此事史书未载,史书该月记载了刘邦召见赵臣之事:“二月,行自洛阳至。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9]67《岁纪》所载“大疫”,应是指范围很大的一次瘟疫,必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可惜史书缺载。查《汉书》“大疫”的记载有两次:一次是吕后时期派兵攻打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领”[9]3848;一次是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五月“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9]1305。如果加上《岁纪》所载高帝九年这一次,则西汉时期的“大疫”有三次。
4.改七月朔日之事
此事史书没有记载,但却记载了与七月朔日紧密相连的六月晦日的干支。《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九年“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9]67。《汉书·五行志》亦载“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9]1500。按照“六月乙未晦”推算,则七月的朔日应是“丙申”,七月二日是“丁酉”,但《岁纪》记载日食发生在丙申日,因此把七月朔日更改为丁酉。而六月的晦日则变成了丙申,这比《汉书》所载晚了一天。学者认为“因为发生日食而更改朔日的记载,此为首见,扩展了人们对于古代朔日设置的认识”[11]22。
(三)吕后元年“予吏仆养”等问题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记载了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予吏仆养、赐天下户爵等事。简文为:“高皇后元年,十月辛卯,以庸(傭)平贾(价)予吏仆养。二月乙卯,赐天下户爵。·减老增傅。·大(太)后立号称制。七月,令复五大夫。·钱八分乃行。”(简37)[2]图版第10 页,释文第191 页
《岁纪》所记高皇后元年之事,共有六项,除了“赐天下户爵”“太后立号称制”“钱八分乃行”三事史书有载外,其余三项均未见记载,弥补了史实记载的不足。下面分别叙述。
1.“予吏仆养”之事
汉初沿袭秦历,仍以十月为岁首,因此十月是吕后元年的首月。该月吕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以庸(傭)平贾(价)予吏仆养”,就是官府按照市场的价格雇佣人员作为吏仆、吏养。郑威认为这与“赐天下户爵”一样,都是吕太后称制时的善政。该事反映出:“与秦代不同,西汉初期的吏仆养来源发生了变化,至少从吕后元年十月开始,政府使用雇佣劳动力作为吏仆、吏养。这一变化的背景,大概是由于汉初政府对普通百姓的管控不再如秦时严苛,一方面导致汉初徒隶数量锐减,人员数量方面已无法满足服务官府的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民间的自由劳动力增加等。”⑮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同时笔者也认为,吕后这一举措,可能与惠帝初年赐爵、赐吏钱、优待官吏的做法一致,都是安定天下,笼络人心的措施。惠帝时期谈及优待官吏的原因时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9]85-86按照惠帝诏书的说法,优待官吏的目的是让他们尽心尽力,为朝廷、为百姓服务。按照这一思路,吕后“予吏仆养”,优待官吏,目的也是让他们更好地为朝廷服务。至于“予吏仆养”中“吏”的爵位与禄秩的标准,还不清楚。但从桑弘羊所言“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12]219-220来看,他据“卿大夫之位”而有“仆养”,说明有“仆养”是高级官吏的一种待遇。
2.“赐天下户爵”之事
此事史书有记载,《汉书·高后纪》元年:“二月,赐民爵,户一级。”[9]96而《岁纪》明确了赐爵诏书的具体时间为“二月乙卯”,“赐天下户爵”则是对“赐民爵,户一级”的概括。吕后的这种做法,与惠帝即位之初“赐民爵一级”[9]85一样,是一种恩惠天下的举措。此后,文帝、景帝、武帝即位之初,都有赐民爵之举。
3.“减老增傅”之事
此事史书未载,郑威指出“减老增傅”是缩短役期的方式,是吕后的善政⑮。“减老”是指减少免老的年龄,“增傅”是指增加傅籍的年龄,但增减的具体年龄不详。“老”“傅”的年龄标准汉代是有变化的。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9]37如淳注引《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9]37-38颜师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9]38又《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⑯从《汉仪注》和《汉旧仪》所载看,汉民23岁傅籍,56 岁或者60 岁免老。但这可能是西汉后期的情况,西汉早期并非如此。《二年律令·傅律》载:“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简356)[13]57“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简364)[13]58从《傅律》来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时期免老和傅籍年龄是根据爵位的高低而有差异,这可能就是吕后元年“减老增傅”后的结果。而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9]141,可能是取消了爵位的限制,傅籍年龄统一为20岁了。
4.吕后“立号称制”之事
此事史书有记载,《汉书·高后纪》载:“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9]95《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八月惠帝崩,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3]399。从记载来看,似乎吕后从元年冬十月年幼的太子立为皇帝之后,就“临朝称制”,但《岁纪》却系吕后“立号称制”时间为二月,与史书记载不同。如果《岁纪》所载属实,则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太子即位后“号令一出太后”,但应该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吕后还需要假借皇帝之名行事,因为丞相王陵时常提出反对意见。十一月吕后废王陵,夺之相权,而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典客审食其为左丞相,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吕后才“立号称制”,彻底摆脱年幼皇帝在名号上对自己的束缚。而只有在吕后“立号称制”的情况下,诸吕封王才具有合法性。
5.“令复五大夫”之事
五大夫是第九级爵,所谓“令复五大夫”,即是以诏令形式免除五大夫爵位者的赋税徭役。此事史书未载,但考虑到惠帝即位时曾对五大夫以上的爵位者在司法上予以优待,即“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9]85,则吕后对五大夫爵位者予以赋役上的减免,可能与“予吏仆养”一样,是对高级爵位者的一种优待和恩惠。而五大夫爵位比吏六百石,如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9]287。张家山汉简中,五大夫爵位在不同的情况下,比秩并不相同,有比八百石、比五百石之别。如《二年律令·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简291)[13]49;《二年律令·传食律》:“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简236)[13]40尽管五大夫爵位比秩不同,但其属于高级爵位者则是无疑。吕后“令复五大夫”,就是对高级爵位者的一种优待。
6.“钱八分乃行”之事
此事史书也有记载,只是时间在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七月,与《岁纪》所载相差一年。《汉书·高后纪》载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9]97从记载来看,《岁纪》“钱八分乃行”,应即《汉书·高后纪》所载“行八铢钱”,二者所记应为同一件事。“钱八分”乃是“八铢钱”的另一种称谓。“行”,即为“通行”之义,实际上就是“改铸”或“新铸”[14]37。“行八铢钱”时间,《岁纪》与《汉书》所载相差一年,不易判断孰对孰错,如果以《岁纪》为是,则吕后改铸八铢钱时间应为吕后元年。
“行八铢钱”之事,涉及汉初钱币政策的变化。《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9]1152对于吕后“行八铢钱”,应劭注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9]97-98钱剑夫认为,秦半两钱重12 铢,汉初的榆荚钱实际上就是“三铢钱”,也就是只有秦半两钱四分之一重的既轻且薄的“轻钱”,其文仍为“半两”[14]30,35。吕后二年“行八铢钱”,“这就是较重十二铢的秦半两为轻,而较三铢荚钱为重的一种折衷的币制,其文仍为‘半两’”[14]37。由此来看,吕后改铸八铢钱,是汉初一次重要的币制改革,只是这次改铸没有持续太久,到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行五分钱”[9]99,就是改行五铢钱了。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又改行四铢钱。武帝时期币制多有变化,一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后,币制才稳定下来。
注释
①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M12 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2 期,第3-20 页;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 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0年第2 期,第21-33 页。②分见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62、2263 页。③杨宽先生认为“封”当为“寿”之形讹。“寿”即“向寿”。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 页。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4 页。另外《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第2175 页)。⑤李零先生根据江陵汉简称“编年记”为“叶书”,即“牒书”。见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第73-80 页。⑥黄盛璋:《云梦秦简〈编年记〉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1 期,第1-22 页。马雍先生也从历法角度对《编年记》与史书记载的年代不一致的情况进行了阐述。见马雍:《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1 页。⑦杨宽先生认为阳晋在封陵之北,与蒲反、封陵之地,相距不过百里。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4 页。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4 页。学者认为简文脱“陷”字,正确的简文应为:“十四年,伊阙陷。”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 页。⑨《编年记》载秦王政十六年墓主“自占年”,即自己申报年龄,登记户籍。简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7 页。⑩郑威教授对韩王入吴房的真实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吴房当属秦南阳郡,未曾属韩。虏韩王入吴房,是将韩王置于附近的秦国边境据点,确保在秦人强有力的管控之下,以防生变。有关观点见郑威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胡家草场岁纪简初读》学术讲座的纪要(见“华大古史”公众号2021年11月4日),又见郑威:《〈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岁纪简初读》,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3 页。但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韩献南阳之地于秦,说明之前南阳之地并非全部为秦占有,尤其是南阳东部的吴房,可能仍在韩国控制之下。⑪简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7 页。关于这两条简文,学者解析颇多。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 页,注释67、68。又陈侃理认为简文“有死□属”,应为“有(又)死。为属。”见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第47-50 页。⑫梁玉绳认为,汉王定三秦,当以八月为是。见(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5 页。⑬严耕望:《汉唐褒斜道考》,《新亚学报》第八卷第一期,第104 页。⑭郑威教授对刘邦由武关入关中杀章邯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见郑威:《〈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岁纪简初读》,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26 页。⑮郑威:《〈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岁纪简初读》,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1 页。⑯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 页。但周天游把“年六十乃免老”中的“老”,据孙星衍辑改为“者”,似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