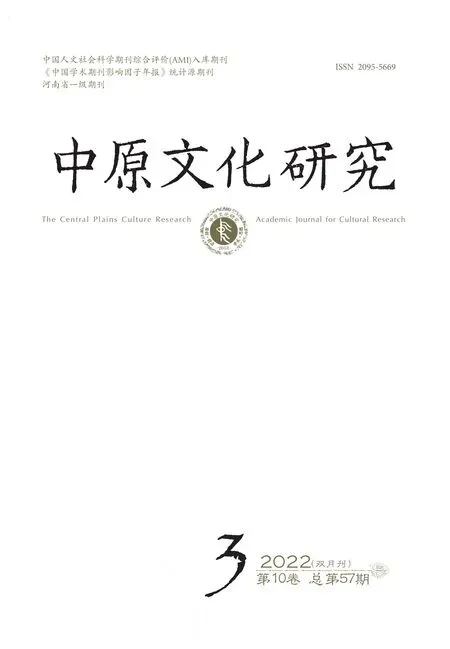从“知其不可而为之”论孔子的经世智慧
2022-02-09吴先伍
吴先伍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享有“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从以往对其形象探究的成果来看,人们普遍接受的是《论语》中石门晨门所作“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概括。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说道:“‘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1]52蔡尚思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以激赏的口吻说道:“‘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对孔子尽人事以应天命的态度的最好说明。”[2]92这些都明确表达了对于晨门概括的肯定,将孔子看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虽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直被当作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被当作孔子光辉人格的铭文,但是笔者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一概括虽然给人们树立起孔子为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形象,让人们感受到了孔子锲而不舍的坚毅品格,却抹杀了孔子的经世智慧,让人们在对孔子心生敬意的同时,难免会产生“愚不可及”的悲叹。因此,我们需要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说法进行反思,以便准确理解孔子的经世智慧。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误读与经世智慧的遮蔽
“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论语·宪问》,原文如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年代最为久远的解释,是何晏所引证的东汉经学家包咸的解释,“言孔子知世不可为而强为之也”[3]383。包咸基本采取了一种直译的方式,“知其不可”的解释中只是将“其”明确为“世”,将“可”后因为避免后文重复所省略的“为”重新释出,不过在“而为之”中增加了一个“强”字,这一增加则为后世带来了解读上的歧义。
“强”在先秦时代乃至在古代汉语中,含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意的。“强”在先秦时代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勉力、勤勉,如《墨子·天志》曰“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又如《孟子·梁惠王下》曰“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这种“强”是褒义词,是一种值得阐扬的正面价值。万事皆有度,勉力、勤勉固然值得赞扬,一旦过度就会变为勉强,也就成了老子所说的与无为相对的强作妄为,也就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勉强从事,结果“过犹不及”,“强”则成了一种负面价值。正因为“强”包含歧义性,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对于晨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概括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晨门嘲讽孔子“愚不可及”,孔子明知世不可为非要勉强从事,结果四处碰壁。宋代学者胡寅就持此种观点:“晨门知世之不可为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4]158另一种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晨门的讥笑转换成变相赞美,将晨门不怀好意的嘲讽变成孔子一生努力而行的真实写照。康有为曾对此评价道:“知不可为而为,晨门乃真知圣人者,不然齐景、卫灵公之昏庸,佛肸、公山之反畔,陈蔡之微弱衰乱。此庸人之所讥笑,圣人岂不深知?而恋恋徘徊,其愚何为若是哉?”[5]223尽管两种态度相反,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晨门对孔子的概括是准确的,因此这两种理解最终被奇妙地结合为一。儒家后学们认为晨门对于孔子的讥笑恰恰是对孔子的高度赞美,晨门的讥笑实际上正好从反面为孔子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经世精神做了注解,“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6]387。
虽然以上解释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却都赞同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在这样的赞同当中,包含了对孔子“勉强从事”“强作妄为”的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因此赋予孔子以入世情怀、执着精神、理性精神、责任伦理等各种荣誉徽章①,但也使其不得不背负“枉顾现实”“强作妄为”的形象。学者董楚平对于前人的解读提出异议,认为孔子并不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是一个“知其可而为之者”,认为赞同将孔子看作“知其不可为之者”是由于现当代学者为迎合西方老庄玄禅的偏好,从而援道入儒,利用道家来阐释儒家思想,把孔子想象得像道家学者一样超凡脱俗,“认为孔子的确‘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实这是认识的倒退,是西学东渐引发的援道入儒所致”[7]。
笔者虽然反对前人的以上解读,但也并不因此而赞同董楚平的论断。首先,董楚平认为赞同将孔子看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近现代的特有现象,这与事实不符。黄式三在《论语后案》中说:“曰‘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指圣人周游列国,知道不行,而犹欲挽之,晨门知圣也。”[8]422其明确肯定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这也是现当代学者的解释之所由来。其次,虽然晨门的论断未必完全符合孔子的本来面目,但是董楚平彻底推翻晨门论断,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论语》作为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这件事被记录下来至少说明:晨门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肯定与孔子的真实形象之间有些契合之处。晨门是《论语》所涉隐者当中的一员,虽然隐者的思想主张与儒家之间多有不合,但隐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批评往往能够切中时弊,这说明他们对于现实或现象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概括能力。因此,他们对于孔子的概括一定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凭空杜撰,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最后,如果孔子是一个“知其可而为之者”,即使我们像董楚平那样承认孔子的“知”也确实存在不可靠的问题,那么孔子就与常人没有任何区别,更谈不上有任何智慧可言,甚至我们因此可以将孔子看作一个事事都看效果的功利主义者,这显然与孔子的思想主张之间存在尖锐对立。
综上所述,无论是坚持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还是反对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实际上都犯了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错误。在笔者看来,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既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也有不符合事实的一面。因此,无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都只具有片面的合理性。如果我们认为孔子确实是“知其不可”却勉强“为之者”,那么,就必然会陷孔子于迂执的境地,这既不符合孔子作为“圣之时者”的形象,也否定了孔子的经世智慧。如果我们认为孔子不是“知其不可”而勤勉地“为之者”,那么孔子就变成了一个知难而退的人,这也不符合孔子“为而不厌”的形象。为了准确地把握孔子的精神气质,洞悉孔子的经世智慧,我们需要对“知其不可而为之”进行深入分析。
二、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毋我智慧
前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以“知其不可而为之”来概括总结孔子的时候,其间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忽略了对晨门的身份分析,从而忽视了由此导致的晨门与孔子在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上的重要差异。当笔者这样说的时候,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驳,因为宋代胡寅强调了晨门与孔子之间的差别:“晨门知世之不可为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现代学者李零也说:“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和隐者不同,隐者是‘知其不可而避之’和‘知其不可而逃之’。”[9]265两者虽然都强调孔子与晨门之间存在差别,但是又有所不同:胡寅强调的是孔子认为天下是“可为”的,而晨门认为天下是“不可为”的;李零强调虽然孔子与晨门都认为天下是不可为的,但是二人对此处置方式不同,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晨门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实际上,“为”与“不为”是一个客观的区分,其间的差别一目了然,人们通过孔子与晨门的所作所为就能知道他们到底是“为”还是“不为”。而孔子与晨门之间区别的关键在于,他们到底是“知其可为”,还是“知其不可为”,也就是他们到底是否能够“知”“可为”与“不可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持不同观点者都一带而过,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显而易见的事实,直接将之作为立论的前提,从而使自己的论断无法经得起推敲。如果孔子“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那么就是将孔子看作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论语》当中多次记录了孔子对于现实的无可奈何,甚至产生了“乘桴浮于海”的退隐想法,否则孔子也不会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下文引《论语》只注篇名)。如果孔子和晨门一样“知其不可”,那么问题在于:“知”的问题乃是一个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晨门怎么能够知道孔子是“知世之可为”还是“知世之不可为”呢?既然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主观的论断,我们就有必要去讨论这个论断的合理性,讨论孔子到底是否“知世之为可”或者“知世之不可为”。
正如钱穆在《四书释义》中所说,晨门与微生亩、荷蒉者、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一样,都属于隐者[10]29-31。孔子虽然偶尔也会产生退隐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并未付诸实施,因此孔子始终在求道行道,济世救民,不属于隐者行列。因此,孔子与隐者在思想观念上,在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上,必然会存在巨大差异,隐者如何能够“知”孔子之所“知”呢?因此,晨门所做出的“知其不可”判断中的“知”并非孔子的“知”,而是其自身的“知”,他不过将自己之所“知”强加给孔子而已。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历史记载所做出的合理推论。
正如钱穆所言,晨门是隐者当中的一员,我们可以通过隐者的言论来推论他们对于世之所“知”。楚狂接舆在经过孔子的门前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我们从接舆与桀溺的言论当中可以看出,隐者对于社会现实具有一个共同的“世不可为”的认知:当时社会道德败坏,从从政者到整个社会风气,都已经处于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凭借个人的微薄力量已经无法力挽狂澜,使社会重回正轨。隐者作为志行高洁之士,既然觉得“世不可为”,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他们只能从现实当中退隐,逃离纷纷扰扰的现实。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隐者的“知”是否也是孔子的“知”呢?孔子是否也“知世之不可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经常说这个“可”,那个“不可”,但是他在“世之是否可为”问题上承认自己的“无知”,拒绝给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与那些隐者存在明显差异,“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这里讲孔子“无知”,不是指孔子没有任何知识,对于世之可为与否没有任何了解,而是指孔子要超越认知,就像孔子说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这并不是说孔子没有知识,不能获得关于他人的认知,而是拒绝将其当作认知的对象,从而对其做出认知上的判断,这实际上是对于“知”的一种超越。回到“知其不可”这个问题上,晨门还停留在认知层面,试图将这个世界看得一清二楚,拘泥于世界可为不可为;而孔子则超越了对世界的认知,超越了世界可为不可为的问题。显然,晨门并不理睬孔子对于“知”的超越,而是将自己之所“知”强加给孔子,将孔子认定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为何会发生这样一种强加?晨门作为隐者,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孟子所说的伯夷、叔齐这样的“圣之清者”,孔子把伯夷、叔齐说作“逸民”,也就是隐逸之士。隐者之所以会从现实中退隐,是因为他们志行高洁,立身行事都高标准严要求,且以此为标准检视自己与社会,要求整个社会都必须符合自己的标准要求,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可为的”。否则,社会就是“不可为”的,就应该退隐与远离,如果滞留就必然会对自己的高尚德行造成污染。因此,隐者对污浊的社会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向现实妥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正因如此,晨门才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和对孔子的观察,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对于孔子的“知”,还是对于现实的“知”,都不过是晨门的一己之见。晨门“知世之不可”,“可”与“不可”是与“知”联系在一起的,是由“知”出发而做出的一个判断,而“知”往往带有自我的主观性、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我们的认知水平受到生长环境、接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影响,这些构成了我们认知的“前见”,即庄子所谓“成心”。虽然这些“前见”“成心”阻碍了我们客观全面认识事物,但是它们又构成了认识的前提条件,正是借助这些现有的知识框架,我们才能对事物展开认知,并依其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所做的认知总是从自我需要、自我好恶出发,我们在做出认知之前,心中总是已经装着自我,会从自我需要出发判断事物是“可”还是“不可”。因此,在这种认知当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将自我与他者放在主客体的地位之上,他者作为认知的对象已经失去了自性,成了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和工具,等待我们做出有价值与无价值、可与不可的判断,从而接受我们的处置。
当孔子说“我无知也”的时候,实际上就主动放弃了对他者的认知,拒绝将他者作为认知的对象与有待处置的客体,而是将他者尊为完整的生命,有其自身的自性、尊严,无需我们赋予他们以价值,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对其保持敬畏之心。这种放弃背后实际上就是对于自我中心的拒绝:拒绝从自我的“成心”“成见”出发,将其作为一个认识框架,强迫他者适应这个框架;拒绝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强迫他者来满足自我的利益需求。这也就是孔门后学概括的“毋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朱熹解释道:“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至于我又生意,则物欲牵引,循环不穷矣。”[4]109-110从朱熹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孔子之所以要戒绝意必固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都是从一己之私出发,从而使自我被封闭在私己的内部循环之中,他者永远在我之外,无法进入自我的生命当中,与自我本身发生真实的生命关联,自我无法与他者共情同感,无法将他者当作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来对待,而只是将他者看作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孔子“毋我”实际上就是对于私己、自我中心的放弃,不再将他者看作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和工具。虽然站在私己的角度来看,他者可能有不尽我意的地方,因此需要我们对其加以征服与改造,而一旦他者摆脱了手段和工具的地位,每一个他者都必然有其可取之处,有其价值之所在,都有值得我们推崇的地方。这就像庄子所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11]61
正是因为孔子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者的认知,不再将他者看作一个认知的客体,所以,他才会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强调他者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强调他者的独特价值,而不是关乎自我的相对价值。正是每种事物、每个他者都有自身独特价值,都有其独特之处,所以他们都有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的地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正是在对于自我放逐的过程中,我们超越了对他者的认知,他者不再作为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作为他者自身与自我交往。因此,他者不再接受自我的认知评判,无所谓“可”与“不可”,我们不能依据自己所谓“可”与“不可”来决定自己“为”或“不为”。《论语·子张》记载,子夏认为交友之道应该“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从而在“可”与“不可”的问题上出现了教条化倾向,执着于依此区分来决定自己所作所为。子张指出,这种做法偏离了孔子的教诲:“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根据自我认知在人们之间做出“可”与“不可”的区分,认为“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孔子实现了自我放逐,从而使自己的内心空明如镜,“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子罕》),从而使他者在自我内心当中无所阻碍地自由出入,而不是要求他者被动适应自我的认知框架。因此,对于孔子而言,任何他者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无所谓“可”与“不可”的问题。
正是因为肯定了他者的内在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将他者当作手段与工具,我们要把他者当作目的本身,我们就要放弃对于自我价值标准的执着,要敢于承认他者与自我的不同,并大方地宽容他者与自我的差异,以契合他者的方式来对待他者,从而与不一样的他者和谐相处,即孔子所谓“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十三章》)。当孔子“毋我”,并要求“以人治人”的时候,实际上就肯定了他者的优先性,他者优先于自我,我们在与他者相处的过程中,要把他者放在自我之先之上,承认他者的优越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都自以为是,“自是而相非”,但孔子并不是这样,孔子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总是说自己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特殊的知识才能,自己之所以“多能鄙事”,也不过是因为“少也贱”,因为生活所迫学了一些生活技能。即使面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没有以老师自居,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学生,“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淮南子·人间训》)因此,即使我们执着地要对他者进行认知,要对他者进行“可”与“不可”的价值评判,那么,我们到底是抓住“可”的方面认为其“可”,还是抓住“不可”方面认为其不可呢?显然,我们抓住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有片面性。个人也好,社会也罢,都会有“两端”,因此,我们只能超越“两端”,超越“可”与“不可”。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先“知其不可”然后而强为之者,孔子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可与不可的问题。孔子超越的基础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在中国古代,这种自我实际上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小我”,也就是肉身性的自我。由于这种自我与物质欲望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自我而言,就有所谓得失问题,就有“可”与“不可”的问题。孔子在“毋我”基础上对于可与不可的超越,实际上也是对于功利主义的超越,我们没有必要做什么事情都首先思考是否有利可图,而是首先听从自己的良心,听从自己的仁欲。正是因为超越了利益算计,达到了“毋我”状态,孔子能够从他者出发,从社会现实出发,根据对象本身与之相处,来加以作为,从而做到了“可于可,不可于不可”。
三、“为之不厌”的实践智慧
虽然晨门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中“知其不可”是对其误解,但是他强调孔子“为”这一点则是正确的,因为孔子一生勤勉有为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而且孔子也曾多次评价自己是一个终生勉力而为的人,“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当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中的“为”到底作何解释?根据杨伯峻的统计,《论语》中“为”字出现了170 次,有是、帮助、替、被、做、干、治理等多种含义[12]285。在这里,意思比较接近的是做、干、治理的意思。关键是做什么、干什么、治理什么呢?在《论语》中有为仁(为仁由己)、为义(见义不为,无勇也)、为礼(为礼不敬)、为国(不能以礼让为国)、为邦(善人为邦百年)、为政(为政以德)等,这里到底所指为何呢?我们在前面已经将晨门归入隐者的行列之中,而隐者认为当时世风日下,政治腐败,整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所以,任何想要重振道德、清明政治、挽救现实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绝无实现的可能,而这也就是晨门所说的“不可”,像隐者接舆有“今之从政者殆而”之叹,认为当时的从政者都处于危殆之中,不仅无法挽救社会,而且还会使自己身陷险境之中。因此,隐者们奉劝孔子放弃拯救社会的想法,远离政治,成为一个“辟世之士”,从而过上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子路面对荷蓧丈人对于孔子的劝谏,曾经为孔子做过辩护:“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从子路的辩护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出仕”问题,也就是干政的问题。因此,这里的“为”应该就是为政。这种说法,确实具有自身合理性,孔子周游列国实际上就是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过,我们也不能将政治狭隘化,从而将其理解为直接的干政活动。实际上,为政的“政”应该是一个广义概念,为仁、为义、为礼等,都可以被纳入为政的范围之中。《论语·为政》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虽然热衷于政治,而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但却生不逢时,获得治国理政的机会并不多,一生中有很长时间都远离政治。因此,有人询问孔子,你怎么不参与政治活动呢?——“子奚不为政?”这个“政”显然是狭义的政治,孔子则在回答中将“政”的外延加以扩充。“《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同样有益于社会和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活动。
“政”被泛化以后,使得孔子的所作所为都能够进入政治当中,都可以看作治国理政的活动。不过,这种说法的局限在于把孔子置于一个普通政治家的行列,孔子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放大了政治的范围,使得个人的自我修养、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活动都被看作政治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得孔子成为了一位实干家,而忽视了孔子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理想之维。孔子的理想在《礼记·礼运》中得到具体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对于孔子的大同理想,我们以前主要关注其和谐的人际关系。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大同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种和谐人际关系的实现则依赖于“大道之行”,只有大道畅通无阻,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变成现实,也就是说,“大道之行”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此,对于孔子来说,为政为学都不过是践履推行大道罢了。不过孔子的“大道”不是老子的“大道”,老子的大道是自然之道,孔子的大道是人道,是仁义之道。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晨门所讲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直接地说是为政,而追根穷源地说是为道、为仁、为义。
中国人讲道与西方人不同。在西方,无论是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还是基督教《圣经》中的“道”,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人无关,与人的所作所为无关,即使我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大道,也不会对道造成任何损害。因此,对于西方人而言,道是宇宙的创造主或上帝创造出来的,人所要做的只是被动地遵守大道,而不能参与大道的创生过程。中国人讲道与西方迥然有别。中国人并没有预设一个完成性的“道”,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天地周行不殆,世间万物生生不已,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易道,道处于变易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自身并不仅仅是世间万物变化的旁观者,而是世界变化的参与者,人要“参赞天地之化育”,我们不仅投身于世界大化洪流之中,甚至还是世界变化的枢轴,因为世间万物都不过是被动顺应世界变化,而人类却主动地参与变化,人类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于儒家而言,无论是讲道、讲仁、讲义都离不开人类的所作所为,因为仁道、仁义都不是自然之道,而是人道,人道不体现于自然世界之中,而是通过人的活动、通过待人接物等人事来展现自身,这也就是说“道在事中”,只有在事中才能体现大道,而“事”就离不开人的所作所为。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的就是人之所为在道之展现、道之弘扬当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正是因为人与道之间这种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十三章》)。
儒家所讲的仁道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长而为人的,也就是说人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有关这点,中国与西方表现出巨大不同。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成人,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就是一对夫妻;在古希腊传统中,爱神所代表的同样是成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西方文化把人看作独立自主的成人,否定了人的成长过程,高度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中国文化则高度重视人的发展过程,认为人是从身体和心理都不成熟的幼儿慢慢成长为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的成人。因此,中国人讲爱并不像西方人那样高度重视爱情或情爱,而是高度重视对父母亲人的爱亲或亲爱,这从有子把“孝弟”看作“为仁之本”就可见一斑。“孝弟”就是一种孩提之童爱亲敬长的朴素情感,人们从具有朴素道德情感的儿童逐渐成长为具有仁心善性的仁人志士。人如何体现仁道,人如何成长为人?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而是在学中成长,在为中成人,学就是学习如何做人,学以成人。这种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学习书本知识,孔子讲学实际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在做中学、为中学,孔子的弟子子夏就曾说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为什么要在做中学,“为”中学做人?因为儒家的人是仁人,也就是道德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道德不是字面或口头上的学问,而是一种实践智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品格,才能真正成为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也并不是体现在一时、一地、一件事情上,而是体现于时时处处每件事情上。这就像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曾经因为英雄壮举而被评为道德楷模,结果他利用自己的名声走向违反社会公德、违法乱纪的道路,结果不得善终,沦为道德败坏之人。因此,我们要想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就必须为之不已、为之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个人修养需要持续不断的道德实践,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呈现为不断的道德实践过程。实际上,一个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的建设同样也是如此。一个道德的国家不是凭借君主的一声号令、一纸文书、一次行动就能建成的,任何作为本身都只是过往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即使它过去曾经甚至现在仍然具有价值,仍然对现实产生影响,但是它的价值是有限的,无法确保这个国家永远都是道德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号令、文书、行动总是具有时空的局限性,它们的价值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控制方方面面、世世代代,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面对与解决,因而我们必然需要发布新号令、新文书,做出新的行动。另一方面,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要想让我们的行为产生预期效果,就必须不断铲除前进道路上遭遇的各种障碍,永远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因此,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的建设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始终处于过程之中,人始终要在此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使得仁政建设始终行走在“未济”—“既济”—“未济”过程之中。也正因为政治、社会的建设表现为生生不已的过程。所以认可有关“可”与“不可”的判断都是与此不相应的,只有通过“为而不厌”的持续作为才能参与到绵延不绝的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才能对理想社会、仁政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孔子来说,我们之所以为了推行仁道而为之不厌,是因为只有在为之不已的过程中才能成仁成人。这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实现自身本质的过程不断提升境界,让自己脱离动物世界而变成道德之人。成人是自我成就,是完全就着自己本身来说的。不过,自我成就却并不是在自我内部就能完成的,成就自我离不开他者,因为道德本身就是处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仁”字从“人”从“二”的构造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人是社会中的人,不能脱离与他者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成仁成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正是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明确了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身份与地位,才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使自己真正“立”了起来,在此世界中安“家”了。社会关系对于自我的重要性意味着需要建构和维护好社会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承担起社会责任。任何社会关系都意味着社会责任,如果身处社会关系之中而又不能承担相应责任,那么这种社会关系就会随之解体,我们因此而丧失了在此特定关系中的特定身份。孔子的“为”实际上就是对于责任的承担,而这种责任不仅是对于亲人的责任,更是对于社会、对于天下的责任。因此,当长沮、桀溺劝孔子放弃改变社会而退隐江湖的时候,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实际上就是强调自己要承担起为天下推行仁道的责任,并且要为此而为之不已,为之不厌,不会因为遭遇困难而退缩。正是因为受到孔子的影响,曾子高度重视推行仁道的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在儒家的影响下,勇于承担责任并为此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进而出现了大量为了社会责任抛洒热血的英雄人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关心的并不是“可为”与“不可为”的问题,而是自己“为”与“不为”的问题,并且他们始终坚持要“为之不厌”。
结 语
虽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孔子是晨门概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明知世不可为但却勉强为之,从而把孔子变成愚不可及的迂执之人。实际上,晨门对于孔子的概括并不符合孔子的真实形象,因为孔子不是隐者,晨门的概括实际上是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强加给孔子。任何认知都存在主客区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从一己之私出发,而孔子则是以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他对所有生命都保持敬畏之心。因此,孔子已经超越了“知”。对于孔子来说,并不存在为自身利益“知其可”与“知其不可”的问题,他的心里装的只有仁义之道,只有他者。因此,为了成仁成人,为了他者,自己只能为之不已,为之不厌。也就是说,要努力地推行仁道,从而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从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辨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真正做到了对于功利主义的超越,做到了义以为先,义以为上,“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为了世人能够享受仁道的惠泽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尤其值得学习与弘扬。
注释
①参见孙海燕《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发微》,《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 期;李波、赵丽《孔子入世情怀与执著精神的现代价值——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中心》,《社科纵横》2014年第9 期;宋晓宇《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理论界》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