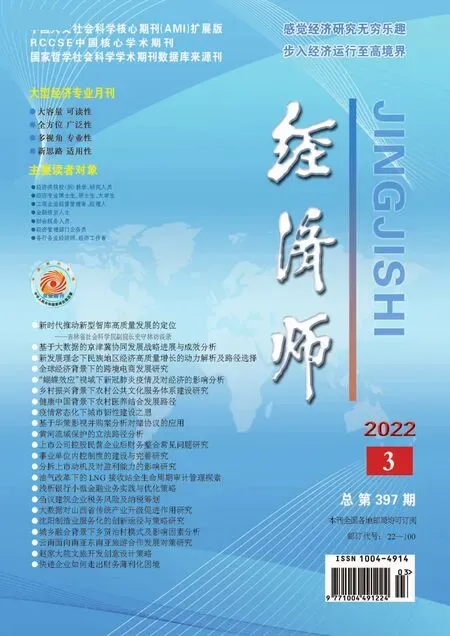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治理的基本经验
——以杭州市为中心的考察
2022-02-06范虹邑
●范虹邑
城市作为国家基本组成部分,其善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彰显的重要方面,是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铭记历史,追溯源头,不忘来时路”是接续奋斗征程的基础。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的重心由农村转为城市,探索城市治理,杭州作为南方大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了接管与改造,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政权认同、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对南方其他城市管理提供一定经验借鉴。在新时代下,注重治理多元主体的共同发力,合理运用数字化媒介、法律法规、具体制度等载体,对作为治理客体的人、事、物实现统一的治理三个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一、治理主体:党和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齐头并进
城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由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构成,中国共产党是治理的当然核心,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在获得革命胜利后,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领导组建新的人民政府和其他机构,在治理各项事务中承担主要任务,成为城市治理的主体。杭州在被接管后,8000多名干部南下到达浙江与300多名地下党员、当地干部、军队干部共同形成城市工作的主体。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坚持党的治理主体地位,在党的核心领导前提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是城市实现善治的保证。党根据国家总体计划,制定适合地方的目标与政策,充分发挥党在治理各项事务中的掌控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权、主导权,保证城市治理沿着总体正确方向前进。党员干部积极承担责任,在治理各个环节发挥示范作用、服务群众,与其他干部共同将党和政府的决策变为居民自觉行动,使得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其他政治机关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杭州市治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形成、作为群众自治机构探索的居委会的成立成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在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中选出主席1名、副主席4名、委员35名首次选举成立了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共同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时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生活需求,对政府的政策等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展开监督。杭州以居委会的创建开启最先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探索,发挥社区内建设服务等作用。“1950年底,杭州有507个居民委员会和3283个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委员会包括150至200户家庭。”[1]社区是前言阵地,是国家、省、市政策执行的领域,落实的具体范围,同时是城市中党和政府政策实行效果反馈之地。人民代表会议、政协、居民委员会在杭州接管与改造中作为城市管理的实体,在城市建设各方面发挥各自作用。当今国家的权力机关、政协、基层群众自治机构,包括随着时代发展日益完善的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党的宏观领导下,在合乎法律与制度约束中,坚守各自领域,参与城市发展各方面,从而发挥更多作用。
普通居民是党和政府政策的接收者和实行者,是城市治理的主体之一。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具有能动性、社会性等特质,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需要以普通市民为动力和前提。在杭州的接管初期,特务分子的势力依旧活跃,产生了社会的混乱,影响城市稳定。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控诉、反映、举报,主动揭发反革命组织及其分子。为了城市良好治安环境,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群众性冬防组织委员会,建立纠察队、联络队等组织,协助公共部门的城市治安保卫工作。在进行城市市容市貌整治过程中,群众自行组成清理队,筹集垃圾箱等。“1950年春季进行一次大型清洁大扫除运动,动员14万群众参加,历时14天,扫除垃圾6000余吨,自制公共垃圾箱640余只。”[2]归根结底,人民的具体实践是治理的原动力,是治理取得应有效果的起始点。在城市中,市民是进行城市治理底层的、广泛的实践者和依靠的坚实主体。城市治理任务与内容由时代变化而产生变迁,新时代下,市民群众同样需要以主体姿态加入城市治理队伍,对政府决策建议提供、政策运行监督等方面发挥主体性作用,同时在面对正确的政策时,进行拥护与支持,并积极实行。民众治理主体地位的实现是要党和政府在价值观、行为方面的总体引导,在合理的领域与规则体系下,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推进城市治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由单一主体转为多个主体,各主体需共生共存,相互调适,实现良好互动。
二、治理客体:人、事、物的和谐统一
人、事、物是城市治理的客体,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是治理的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存在党员干部、各界代表人士、普通民众等主体。党员干部面临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和党性修养任务。中央和浙江省委极其注重干部党员的纪律问题,建立统一集体组织生活制度,开展干部培训。党员干部是城市治理的推动者及实践者,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任何时期,需要进行自我革命,提高治理城市的能力,在环境变换、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加强理想信念的塑造。在新政权的稳固阶段,实现公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认同尤为必要。党和政府在就业、社会环境改造等过程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开展组织工人参加训练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任何一个取得政权的政治集团或阶级都必须为取得自身合法性而继续斗争。”[3]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合理性建设在城市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城市治理中起着“粘合剂”作用,政治认同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宣扬,达到对群众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在城市接管与改造过程中,对不同事件的处理体现党和政府的智慧。一方面,不同的时期,需针对城市生活中不同事件进行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立足唯物史观,着力恢复经济发展和工人重新就业。在社会生活上政府组织防疫委员会,进行霍乱、白喉等疫苗的接种以及环境的消毒。城市治理是为了人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感受的美好实现。城市治理根据具体城市情况,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日常居住环境优化、居民资源享受等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完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治理过程中总会出现突发事件,妥善的解决是城市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一步。在杭州治理中货币混乱、物价上涨事件发生。杭州市政府以干预交易市场等形式肃清银元黑市。在对各公私企业、学校等实行基本物资平价、定额销售,辅以“折实储蓄”制度中平抑物价。针对抗美援朝战争所进行的增产节约、物资募捐等活动。突发事件的处理考验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完善程度,事件处理中反应能力与恢复能力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在危机的状态下,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和干预成为迫切需要。党和政府的调控和及时措施应对能够引导紧急事件向良性方向发展,规避事件继续发生,从而实现城市的善治。城际间、社会上进行资源调配与补充、社会恐慌心理克服、日常预防与监测机制、针对常见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事件解决后的追踪是突发事件得以有效解决的途径。
城市的独特自然风光及文化设施是特色城市特色建设的有力资源,是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其一,蕴含有历史底蕴建筑构成城市风貌,兼具经济、政治带动作用。杭州城市内有大量以佛教为主的寺庙是宗教文化圣地。“早在11世纪,杭州有400多座寺廊,20世纪初达到2000多所。”[4]寺庙周边的商铺、茶馆、手工业品等一系列与宗教文化及旅游相关的设施及物品出现,提供就业岗位,繁荣之相形成。西湖是杭州独有的自然风光,党和政府对西湖进行清理,对各景区加以修缮。在城市治理中,需要依托于具体物质体,挖掘深层经济、政治、文化意义,实现联动发展,形成完整的链条治理。其二,城市不仅作为国家所属部分,同时处于世界体系中,城市需要注重国际影响力塑造及竞争力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及科学技术等不够发达,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扬长避短,以文化为切入点拓展在东南亚等地的影响力。戏曲尤其是越剧是浙江省独特传统文化,杭州市政府将其融入政治内容进行国际传播。城市治理基于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深入的背景,城市的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国家国际形象的展示,城市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世界性活动筹办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世界的接轨,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在与全球国家、地区的接触中,吸收有利于发展的因素,积极探寻城市进步的资源与机会。
三、治理载体:法律、制度、媒介的多管齐下
载体是城市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互动的中介。法律条例、体制、大众媒介在建国初期杭州治理中成为有效载体,为城市问题的解决及秩序建立产生深刻影响,新时代城市治理中运用的载体应与时俱进。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5]法治具有防御性、可操作性高及规则性强的特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保障底线,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经过程与形势之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对杭州各方面进行接管与改造过程中,依据中央的总体条例结合城市具体情况出台各项的法律条例,多以布告、指示、条例形式呈现,开展城市管理。诸如经济、卫生、市容面貌等方面出台条例。法律条文的设计基于城市现实情况及为市民服务的理念,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当时管理问题的解决。法律的制定以“他律”的行为导向出发,改变传统社会注重道德修养的价值导向,建立并完善现实、务实、不交叉的法律条文,为应对城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基础。在城市治理中将行政性法规、地方法规、国家法规协调运用。
城市治理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实现,有利于实现治理效能提高和善治的实现。在杭州接管中党和政府对于前政党管理下的工厂、机构及其事业接管实行请示报告制度。对党员干部有工作生活报告制度,党员干部集体领导制度及个人负责制度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领域中,各项具体的制度进行创制。在宏观顶层制度设立中,通过与各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城市治理中进行初步尝试并取得成效。城市治理坚持宏观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同时在具体的生产生活领域进行具体的制度完善。城市治理中,制度的建立者具有问题意识,在对问题产生缘由、形式、危害等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尊重治理主体的建议,集思广益,制定符合历史规律、与现实条件相匹配的制度。同时制度随时代的发展演化、吸收新因素实现再造。制度的设立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制度的实行过程需法律的保障及各方面的监督,在实践中不断调试,使制度符合城市长久发展的需求,让不同的制度在城市中发挥解决冲突的效用。
媒介作为治理内容与任务的传播渠道是重要支柱,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不同时期有不同媒介对城市治理政策的制定、实行、监督等过程提供宣传平台与渠道。建国初期,杭州巧妙运用媒介开展工作主要为广播、报纸、宣传漫画,诸如:对一贯道等迷信教会的取缔中党和政府以漫画形式揭露其性质,宣扬新政府主张。党和政府关注媒介对于城市管理的地位及作用,以当时现有媒介发挥政策传播功能,促进市民对政策的认同,加快政策的实施进程。新时代下,大数据、全媒体、云计算等加快信息传播速度与范围,而且资料的传播呈现地毯式、扁平化、交互性。通过手机、网络等平台,党和政府进行信息的传播,为民众的意见及时反馈、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提供载体。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同时空范围的市民沟通交流,平台公开透明及评议渠道畅通保证市民知情权与监督权。各媒介在政策宣传中对市民的浅层及深层价值进行认同引导,人民以平等、及时有效的方式认知执行政策。现代城市治理中政策、数据的完整精确公开克服信息的片面性与不对称性,党和政府挖掘数据背后的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对民众起到服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