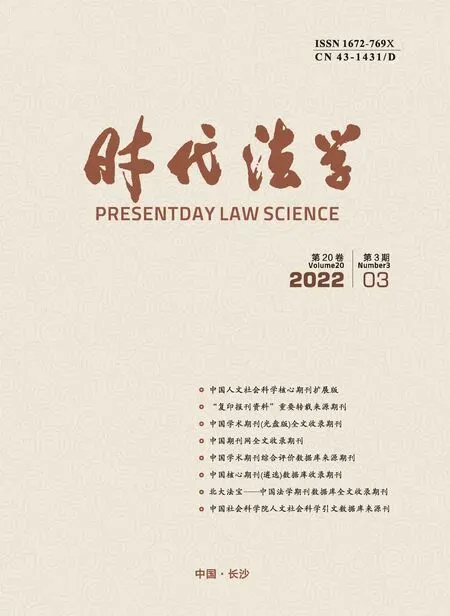论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的优先顺序
——以《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的司法适用为中心*
2022-02-05李鸣捷
李鸣捷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担保制度设计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兼顾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使得各类型担保权利虽形式上分离,但实质上却由统一的核心规范(以登记为基础的统一顺位规则)将其串联(1)王利明.担保制度的现代化:对《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的评析[J].法学家,2021, (1):37.,《民法典》第414条系该统一顺位规则的一般规定。作为特殊规定,《民法典》第768条(2)《民法典》第768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针对应收账款多重保理场合保理人的优先顺序构建了“登记—通知—比例清偿”的三阶判断体系。鉴于质押和让与在法律构造上相类,故为贯彻“类似法律关系类似处理”之理(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55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4)《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规定:“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768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同一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保理、质押及债权转让)的优先顺序予以统合,一律准用《民法典》第768条。
在解释论层面,《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有以下方面尚待澄清:首先,如何理解“同一应收账款”?就应收账款担保而言,《民法典》将质押或保理的客体范围扩张至“现有的及将有的应收账款”,那么具备同一性的应收账款可否跨越将来与现实两种样态?其次,若前述问题答案为肯定,将来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或保理客体的识别标准如何?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可否被处分?如何基于有无基础关系之别分别拟定应收账款同一性的判断进路?再次,尽管依该款中“债权转让”之文义,竞存权利似涵括所有类型应收账款让与,但根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2条,可得登记的应收账款让与仅限于以保理为代表的担保型让与,故囿于登记能力的不均衡,《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事实上仍未打破应收账款让与优先顺序“双轨制”(5)所谓双轨制,是指在担保型让与场合,受让人的优先顺序依登记先后确定;在非担保型让与场合,由于优先顺序规则阙如,实践中法院通常以让与先后或通知先后为据确定受让人的优先顺序。的现状。那么既有立法实践对于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的规定是否合理?有无必要赋予所有类型应收账款让与以登记能力?最后,在将来应收账款质押或让与的情形中,处分行为与处分效果通常相分离,以保理为例,在应收账款预先让与至受让人实际收取债权这段期间,若让与人破产,此时保理人可否藉登记对抗让与人的破产管理人?让与人的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在竞存权利顺位体系中应如何排序?笔者拟对关涉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优先顺序的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应收账款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二、“同一应收账款”的法理阐释
(一)“同一应收账款”能够跨越将来与现实两种样态
《民法典》将质押或保理客体范围扩张至“现有的及将有的应收账款”后,就某一应收账款而言,其客观上存在将来与现实两种样态。从内在演进角度看,将来应收账款与现实应收账款构成“前世今生”的关系,二者系应收账款于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故就某一应收账款,其将来与现实的两种样态应作同一性评价。
(二)将来应收账款的识别标准
1.将来应收账款应当具有确定性
关于“将来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或让与客体是否需要设限”这一问题,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分:前者如德国学者莱赫曼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85条第2款系规定非权利人所为的处分,该规定可适用于所有将来债权,因此对将来债权事先预定加以处分,应当认定有效(6)方新军.现代社会中的新合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6.;后者认为,将来应收账款可以被质押或叙作保理,但需施以一定限制。笔者支持肯定说,且适格将来应收账款应以可确定为限。理由如下:首先,从法理角度看,法谚有云“处分一个尚不存在的债权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7)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00.。一般认为,应收账款的质押或让与系对权利的处分,而权利在被处分时需能够确定。由于法律安定性,债权应适用特定性原则,被处分的债权必须由当事人准确地描述,以致这些债权可以被个体化(可以被确定)(8)[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M].沈小军,张金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93.。其次,从期待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将来应收账款质押或让与的实质是对具有经济价值的期待利益之处分。然而并非所有民事主体之期待均受法律保护,期待如缺乏确定性,则民事主体不能因此种期待而生相应期待利益,其行为效力不应被法律所承认(9)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640号民事判决书。。最后,从比较法层面看,《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应收账款质押及让与采“担保交易”的统合立场,其客体涵括将来应收账款。对此,Adkins等担保法学者指出,尽管让与将来应收账款是被准许的,但是这些应收账款应当在产生时能够被识别为特定让与的客体(take specific assignments at the time when the accounts are created)(10)Leonard D. Adkins , Walter Chandler, Harry S. Gleick & James A. MacLachlan, Report of Panel Discussion at Convention, 9 Bus. Law. 11, 33(1954).。此外,《国际保理公约》第5条第1款和《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第8条第1款(b)均认可将来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客体的适格性,但同时均要求该将来应收账款是可确定的。
2.将来应收账款的类型划分
在德国民法学理上,将来债权分为有基础之债权与无基础之债权,前者如附停止条件或附始期之债权,以及基于继续性债之关系(租赁、劳务)所生之债权;后者如有待订立之买卖、租赁所应生之债权,因无基础关系又被称为“纯粹将来债权”(11)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C.H. Beck 1987, S. 584 ff. 转引自朱晓喆.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转让与“将来债权”让与——评“平安凯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执行异议案[J].财经法学,2019, (4):15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黄立教授也采此种区分方式。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16-617.。那么,前述两类将来债权是否皆可成为质押或让与的客体呢?对此笔者持肯定立场:一方面,由于有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其基础合同已成立,“将来债权转变为现实债权”的要件及所附条件已由基础合同所确定,担保权人对于将来应收账款具有合理期待,故有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的适格性应无疑问。另一方面,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只要在产生时可得确定,其亦可成为质押或让与的适格客体。原因在于:其一,将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纳入适格客体范围,能够极大地拓展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适用范围,提升“获取信贷便利度”,从而为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作出应有的制度贡献;其二,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确定性的判断时点可延伸至该将来债权产生时(12)参见[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93-394;[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M].沈小军,张金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93.。因此,只要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在产生时能够被识别确已为先前订立的融资合同所涵及,则可落实对其确定性之审查(13)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403.。
(三)应收账款同一性的判断
基于前述分析可知,作为质押或让与适格客体的应收账款涵括三类:一是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二是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三是现实应收账款。该划分依据与其称之“类型”,不如谓为“阶段”;易言之,就某一应收账款而言,其于上述三阶段皆存在被质押或让与的可能,若债务人于该应收账款的不同“生命阶段”分别设定权利负担,则此多项权利的顺位安排仍须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但问题是,如何鉴别处于不同阶段应收账款的同一性呢?笔者认为应当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对于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与现实应收账款的同一性,由于此二类应收账款均存在基础关系,故可直接通过登记系统内已公示的对担保财产的描述内容加以判断(14)实务中对于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其作为担保财产于登记时通常借助编号将其特定化,如某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中,担保财产被描述为“《平潭综合实验区政府采购合同》(采购编号为[350190]XRD[GK]2021001)项下的应收账款”。登记证明编号:11691071001397427773,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另一方面,对于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与有基础关系应收账款的同一性,由于前者虽无基础关系,但质押或保理合同中当事人会就其未来产生期间及其他限制作出约定,使得该类将来债权于产生时能够被识别是否为先前订立的融资合同所涵括,因而同样具备确定性。故于此场合,查阅内容除登记系统内已公示的对担保财产的描述外,通常尚需涵括作为登记附件的融资合同(15)如实务中某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中,担保财产被描述为“质押人销售产品给某石油公司产生的应收销售货款”,登记证明编号:03638698001269962500,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依文义,此处“应收销售货款”涵括现有及将有的应收账款,由于担保财产描述部分未言及将来应收账款的产生期间,故需另行审查作为登记附件的融资合同以作出判断。当然,在某些涉及将来应收账款的融资登记中,担保财产描述部分已明确将来应收账款的产生期间。如在某保理登记中,担保财产被描述为:“让与人已产生及未来(2020.5.19—2022.5.18)产生的与其核心企业的所有应收账款,核心企业包括某食品公司…等。” 登记证明编号:08151577000973604461,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由于在此场合,以担保财产描述部分为据已然可以甄别无基础之将来应收账款,故可不必另行审查融资合同。。
三、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之辩
(一)既有立法实践之检讨:限于“以融资为目的”并不妥当
如前所述,以登记为基础的统一顺位规则,系我国《民法典》在担保制度设计上兼顾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核心举措,《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即是该统一顺位规则在应收账款担保层面的具体体现。该款在描述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时将保理、应收账款质押与债权转让并列,而保理的核心系应收账款让与,故依文义,该款所规制竞存权利应为应收账款质权、保理及所有非保理应收账款让与场合中受让人的权利。但问题是,某项权利可否采用登记这一公示方法,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登记能力(16)参见王利明.登记的担保权顺位研究[J].比较法研究,2021,(2):19;何颖来.《民法典》中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构造[J].中州学刊,2020,(6):65.;就此规定而言,《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34条将可得登记的应收账款让与限于“以融资为目的”,而其修订后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较前者范围更窄,仅限于担保型让与。这就导致实然层面《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中的“债权转让”面临着“限缩解释”的窘境。笔者认为,将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适用范围限于“以融资为目的”并不妥当(17)鉴于从范畴上看,担保型让与可为“融资目的应收账款让与”所吸收,故基于“举重以明轻”之法理,笔者此处以“融资目的应收账款让与”为论述对象,以阐释不论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抑或是作为其前身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其就应收账款让与登记适用范围所作之限定皆存缺陷。,理由如下:
1.“以融资为目的”界限不明
就“以融资为目的”的理解而言,立法者在释义文献中曾以抵债式应收账款让与为示例(18)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417.,试图借此厘清其与融资式让与之界限,从而为“以融资为目的”划定藩篱。但在笔者看来,该做法颇值商榷。理由有二:
一方面,从商业实践角度看,何谓“以融资为目的”?界限并不清晰。前述示例中的“让与应收账款抵债”即实践中债务重组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会计实务上,就债权人让步场合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而言,债务人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最终增加企业当期净利润(19)企业期末结转利润时,应将各损益类科目的金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平各损益类科目。结转后“本年利润”科目的贷方余额为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223.。利润的沉淀增厚企业的权益资本,此恰可为企业的内源融资创造条件,怎能否认该情形下的融资目的?细思之,前述观点欠周延之处在于:其将融资局限为“资金积极增加”这一种情形,却忽略了“资金消极增加”亦能竟融资之功。在文义上,“融资”并不排斥“资金消极增加”(20)《现代汉语词典》对“融资”的定义是:“通过借贷、租赁、集资等方式而使资金得以融合并流通。”该释义亦未将“融资”限于“资金积极增加”这一种类型。;而在上市公司破产实务中,重整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将企业打造成一个无资产及负债的净壳,以便后续融资(通常是非公开发行股份)并购置优质资产,此过程充斥着大量的债务重组(21)如著名的ST天颐重整案。该案基本情况如下:ST天颐是一家生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制造业企业。2007年10月11日,法院裁定受理ST天颐的破产重整申请。10月20日,三安集团通过股权拍卖获得ST天颐大股东席位。11月23日,法院批准重整计划,重整中ST天颐与其债权人进行多次债务重组,最终使ST天颐成为一个无债务负担的净壳。2008年3月3日,ST天颐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大股东三安集团的注资方案:ST天颐向三安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三安集团控制的子公司三安电子的LED外延芯片及其他芯片经营性资产。随后,ST天颐更名为ST三安。次年,ST三安“摘帽”,重整成功。参见S*ST天颐:躲过退市风险零对价便宜借壳者(EB/OL)(2008-03-04)[2021-12-01].http://stock.hexun.com/2008-03-04/104184020.html.。可见,抵债式应收账款让与并非必然与融资目的绝缘,“以融资为目的”界限不明。
另一方面,从比较法角度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将应收账款买卖纳入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这种功能主义立法进路为新近诸多统一法所效仿(22)新近统一法或以“让与”一词涵盖担保交易,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2条a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9.1.1条、《欧洲合同法通则》第11:101条第4、5款;或以“担保”一词涵盖债权让与,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1条、第2条。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J].法学研究,2019,(1):59.。尽管《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109(d)将以收款、偿债等非商业融资目的之应收账款让与剔除于登记制的适用范围(23)See UCC§9-109(d)&cmt.12(2010).,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并不以“融资目的”作为甄别某项应收账款让与得否适用第九编的标准。譬如在Bramble Transp., Inc. v. Sam SenterSales, Inc案中,特拉华州法院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109(d)意在剔除“无商业实质”的交易,而非排斥所有情形(包括“非融资目的”)下的应收账款让与(24)Bramble Transp., Inc. v. Sam SenterSales, Inc., 294 A.2d 97, 101 (Del.Super.1971).。又如在Matterof Biloxi Prestress Concrete, Inc案中,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指出,与建立和完善担保利益相关的交易(transactions relating to the creation or perfec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s)均可适用第九编,无需考虑应收账款让与的具体目的(25)Matter of Biloxi Prestress Concrete, Inc., 98 F.3d 204 (5th Cir.1996).。
2.限于“以融资为目的”不利于维护保理人的交易安全
退一步讲,即使认为“以融资为目的”界限清晰(将其限定为“资金积极增加”),双轨制的运作亦对交易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7年修订)》新增“以融资为目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参照质押登记办理”之规定,其核心目的系保护以融资为目的应收账款转让场合中受让人的交易安全(26)对于新增“以融资为目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参照质押登记办理”之规定,起草者阐释理由如下:“转让和质押是应收账款融资的两种形式,但我国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立法缺失,使得实际业务中交易一方…面临一笔应收账款…被重复转让的风险。…转让登记虽为非强制性规定,但有助于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开展登记与查询,保护交易安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7年修订)修订说明(EB/OL)(2017-11-01)[2021-12-01]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11/01/content_5236146.htm。由此可归纳出,上述修订的核心目的乃保护以融资为目的应收账款转让场合受让人的交易安全。。但笔者认为,双轨制的运作与该目标背道而驰,以保理人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例:
一方面,从商业实践角度看,实践中很可能出现“非融资目的让与发生在先,融资目的让与发生在后”的多重让与情形。双轨制下,由于前者无需登记亦无法登记,故于后者场合保理人即使查询相关登记,也难以知悉其所受让应收账款有无被在先让与;又因为私人合同不具权利外观,保理人无法善意取得该应收账款(27)债权原则上不存在善意取得,因为这里取得人不能主张与占有或土地登记簿中的登记相似的权利外观,通过这种权利外观无权让与人可能被正当化。Larenz, Schuldrecht I, §34 I;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I, Rn. 758.,而前受让人依让与在先(如采让与制)或通知在先(如采通知制)之事实业已取得应收账款,故此时保理人除追究让与人违约责任外,只得“望款兴叹”。质言之,双轨制看似给予保理人优待,实则乃“头痛医头”之举,对保理人交易安全之保护无丝毫助益。
另一方面,从金融监管角度看,保理业务中银行保理占有很高比重。为管控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保理人的交易安全,银监会明令商业银行在受理保理融资业务时必须对应收账款的出质、转让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28)参见《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并禁止商业银行基于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发放保理融资款(29)参见《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然而,在将应收账款让与登记限于“以融资为目的”的情形下,商业银行即使查询相关登记,也无从知晓所受让应收账款是否确无在先设定的权利负担(如在先被用于非融资目的让与),进而无法确保融资业务的交易安全。此际,金融监管的目标亦难达致。
(二)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一元化之提倡
1.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一元化之证成
笔者认为,应当对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适用范围作划一处理,不论让与目的为何,皆应允许当事人藉登记获得保护。理由如下:
首先,从权利客体理论上看,权利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当一项权利成为另外一项权利的客体时,它最好能够通过有体的载体(外部定在)表现出来。否则以它为客体的权利的不确定性就非常明显(30)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J].法学研究,2010,(2):42.。在债权让与场合,受让人所受让之债权系第三层次的权利。为了使第四层次的权利尽可能地确定下来,作为其客体的受让债权最好能表现为某种可观察的外部定在,登记是最佳路径之一(31)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J].法学研究,2010,(2):58.依作者观点,另一种路径是证券化,但由于证券化并非是确定优先顺序的方法,故此处不作讨论。。
其次,从商业实践角度看,交易安全保护是基于各类应收账款让与场合均存在的普遍问题,非因让与目的之别而异。若将登记制的适用范围限于“以融资为目的”,则在其余场合,应收账款让与只能以签约或通知的先后来确定优先顺序;但签约本身无公示效力,让与通知亦难堪公示之任(因为债务人并无回复查询之义务),故此际受让人的交易安全几无保障(32)在四川某法院审理的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案涉应收账款让与系为抵扣投资款所为,法院依让与时间先后确定受让顺序。参见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1896号民事判决书。后受让人称其无从知晓应收账款被多重让与,且其已先于前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并主张取得该应收账款。该案历经二审、再审申请,均被驳回。参见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9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申4955号民事判决书。可见,在非融资目的应收账款让与场合,公示制度的欠缺对受让人交易安全的危害亦不容小觑。。事实上,登记制作为法律创设的“公共品”,应向所有主体开放,而不应成为特定行业的专属品,进而剥夺其他主体藉登记获得保护的机会(33)参见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J].法学研究,2019,(1):67-68.我国学者亦指出,尽管依现行法,债权转让未被赋予登记能力,但出于权利顺位保全的需要,对于交易数额较大的的债权让与而言,受让人亦应有权办理登记。参见程啸,高圣平,谢鸿飞.最高人民法院新担保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420.。将登记制的适用限于融资场合,将导致非融资情形下应收账款受让人无法依登记确定受让顺序,以防范交易风险,此亦悖于“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基本法理。
最后,从成本收益分析角度看,登记制的普遍适用具有效率价值。法经济学家White教授指出,在优先顺序的制度设计上,一项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规则确定。确定性使规则适用结果更易预见,减少讼争。第二,促进社会所需的交易。第三,制度运行成本低廉(34)See James J. White, Reforming Article 9 Priorities in Light of Old Ignorance and New Filing Rules, 79 Minn. L. Rev. 529, 533(1995).。据此检讨:首先,在规则确定性方面,让与制、通知制与登记制分别以让与时点、通知时点与登记时点作为确定优先顺序的依据,规则本身均明晰确定,故在此维度三项制度并无高下之分。其次,在促进信贷方面,登记制更胜一筹。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不对称催生了充斥着逆向选择的“柠檬市场”,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随之加剧(35)See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J. Econ. 488, 488-500 (1970).;在此背景下,资产的可担保性能够促进信贷,因为企业可借助担保向潜在贷款人释放资金安全的积极信号(36)Efraim Benmelech&Nittai K. Bergman, Collateral Pricing, 91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9, 341(2008).,以增强债权人的放贷动因。然而,让与制对欺诈让与的纵容使前述所传递的积极信号收效甚微,且会增加不菲的信贷成本(37)Akseli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发达资本市场,银行或可依借款人的陈述,了解其偿债能力与诚信水平,因为这些市场(如德国)通常配有健全的反欺诈立法,对借款人重复让与应收账款的惩罚超过其潜在可得收益。但对于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让与制对登记的豁免促进信贷”是存疑的,尤其是以任何方式(包括证人)证明让与时间将是一项挑战。See Orkun Akseli, International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facilitation of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instruments, Routledge, 2011, p.214.;至于通知制,其在诸多场合(如大宗或将来应收账款让与)(38)在大宗或将来应收账款让与场合,通知制无法回应受让人的问询诉求,因为此时债务人可能数量众多且身份未知,受让人客观上很难借通知查明应收账款的权属;即便可以,该做法在经济上亦颇不划算。See de Lacy, J, the Priority Rule of Dearle v. Hall Restated, 63 Conv. 311, 311-325 (1999).无助于受让人抵御交易风险,此亦将明显增加信贷成本,使中小企业藉应收账款融资窒碍难行(39)See Orkun Akseli, International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facilitation of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instruments, Routledge, 2011, p.217.。Lacy教授指出,Dearie v. Hall规则(通知制)不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确定优先顺序的要求,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建立一个集中式的公共登记系统,用以存储、公示顺位信息(40)See John De Lacy, Reflections on the Ambit of the Rule in Dearle v. Hall and the Priority of Personal Property Assignments—Part Two, 28 Anglo-am. L. Rev. 197, 214 (1999).。最后,在运行成本方面,登记制并非处于劣势。一方面,诚如前述,让与制虽省略公示,看似节约成本,但其实质是将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一边倒”地分配给潜在受让人;在法经济学上,如欲实现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交易风险及成本应分配予更有能力抵御风险之人,否则将徒增制度成本。让与制下让与人实施欺诈让与的成本极低但受让人审查在先让与的成本极高,该制将风险全部分配给受让人无疑将激励让与人实施欺诈行为,此时制度运作趋于低效甚至无效。另一方面,通知制下由于债务人无回复查询之义务,故受让人藉通知获取优先顺位信息很可能只是“缘木求鱼”,目的尚不能至,遑论节约制度成本。反观登记制,尽管登记系统的运行与维护需花费不菲,但我国已建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可登记范围覆盖保理在内的多种担保交易,这样就能够有效摊低制度运行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于去年底发布《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对作为其前身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予以修订,其中就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适用范围而言,其删除了原先的“以融资为目的的应收账款让与准用质押登记”之规定,并于第2条明确了保理及其他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场合登记的适用性。就此,可得登记的应收账款让与范围被进一步限缩,即由原先的“以融资为目的让与”缩窄为“担保型让与”。笔者推测,该修订或为契合规章名称中“动产和权利担保”一词,以凸显所规范对象的“担保”共性。然就其“保障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之实现而言,该变动恰有南辕北辙之嫌:一方面,诚如前述,旧规对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范围限于“以融资为目的”之规定,造成了保理及非保理场合“受让人交易安全之保障”双双落空的局面,而又因新规在应收账款让与登记的适用范围上较旧规更为限缩,故旧规之弊于新规中非但未能矫正,反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旧规下,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中的受让人可藉登记获得保护;而新规将登记范围限于“担保型让与”后,资产证券化便丧失登记能力(41)之所以认为新规下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丧失登记能力,是因为资产证券化通常无法设计为质押形式。在资产证券化场合,发起人须将其应收账款让与给特殊目的实体,方可满足“真实销售”与“破产隔离”的要求;如果设计为质押,则发起人保留对应收账款的控制,资产证券化交易将彻底失败。参见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J].法学研究,2019,(1):65-66.,这种规制模式所存在的逻辑矛盾在保理商开展保理和非保理两种交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实践中,保理商在向客户提供融资的同时自身亦需从其他渠道获取融资,保理资产证券化即是保理商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该交易的具体流程为:保理商作为发起机构,将其受让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特殊目的实体,而由后者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得融资(42)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J].法学,2019,(12):43-44.;于此场合,同笔应收账款,同以融资为目的,受让人均有交易安全保护的需要,但依新规,在保理场合可得登记,在资产证券化场合却无法登记,这显然在法理上难以自洽。
2.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一元化的制度设计
那么,赋予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一元化的登记制度应如何设计呢?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行方案:一种方案是登记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系统,如此,可于以后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时增设非担保型应收账款让与登记之准用条款。或有观点认为,《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旨在规制担保权益的登记,在其中规定非担保型让与登记之准用似有欠协调。笔者认为该顾虑并无必要。因为诚如前述,资产证券化与质押在构造上存在根本冲突,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34条仍然规定了资产证券化可得登记的准用条款;同理,在名为担保的规章中规定非担保型让与登记之准用亦无不妥(43)如我国学者指出,对于交易数额较大的债权让与而言,为保全权利顺位,防止权利冲突,受让人亦可在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平台上登记其对应收账款的权利。程啸,高圣平,谢鸿飞.最高人民法院新担保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420.。另一种方案是借由特殊动产、权利登记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让与登记,同时在该登记系统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系统间建立电子链接。互联网时代,在两大登记系统间创建电子链接并无技术障碍(44)高圣平.《民法典》视野下同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的构造[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9):42.。该做法的优势在于:既尊重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系统登记“担保权益”的纯粹性,又能够使交易相对人一次性查询特定应收账款上的所有权利负担,尽可能降低征信成本。不过,该构想的实现尚需我国既有的特殊动产、权利登记系统完成电子化的改造(45)高圣平.统一动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J].环球法律评论,2017,(6):66-83.。
四、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优先顺序的体系建构
(一)登记对抗范围的扩张: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3条
前已述及,《民法典》于应收账款担保领域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将担保客体扩张至将来应收账款。将来应收账款让与的特殊之处在于,让与之际其客体尚不存在,处分行为与处分效果相分离。那么,在将来应收账款的让与合意达成后至其实际产生的这段期间,若让与人破产,由于应收账款尚未产生,故原则上应归入债务人财产,那么作为保理人,其可否藉登记对抗破产管理人呢?
对于这一问题,《民法典》第768条未予回应,从文义上看,该条仅赋予应收账款让与登记对抗保理中其他受让人的效力,系不完整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规则。笔者认为,《民法典》第768条在让与登记对抗范围上存在明显漏洞,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3条将其扩张至包括破产管理人在内的所有第三人。理由如下:
首先,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赋予让与登记对抗破产管理人的效力能够较好地衡平保理人与让与人的普通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一般认为,经登记的将来债权让与,可视为对所有相关人员已作推定通知,并可对后续债权人与受让人产生对抗效力(46)[美]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下册)[M].王卫国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03.。我国目前已建立了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机制,保理被明确纳入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保理人可借助登记加强对其自身利益的保护,同时,让与人的普通债权人可基于登记事项合理评估交易风险,其交易安全亦得保障,双方利益均有顾及。诚如克茨教授所述,对未来债权让与的慷慨接受亦有其弊:它可能会不公平地损害让与人的其他债权人之利益。然而,避免这些不利后果的方法不是简单地禁止对未来债权的让与,而是使它们作为担保手段必须满足特定的形式要件方可产生对抗效力,如登记(47)[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95.。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看,尽管《美国统一商法典》在1972年修订前未承认“将来应收账款上可设立担保利益”,但实践中已有法院前瞻性地认可将来应收账款作为担保客体的适格性,并认为该担保利益经完善可对抗破产管理人(48)Norman H. Nachman, Developments in Commercial Bankruptcy Law, 24 Bus. Law. 1369, 1372(1969).。应收账款浮动担保权在破产程序中具有优先效力的观念已被牢固确立(49)See William M. Burke, Secured Transactions, 30 Bus. Law. 893, 919(1975).譬如在DuBay v. Williams案中,应收账款担保登记远早于让与人破产前四个月,故受让人对于应收账款可主张的担保权益不受破产管理人偏好考验的影响(immune from the trustee’s preference challenge)。See DuBay v. Williams, 417 F.2d 1277(U.S. Court of Appeals 9th Cir.1969).。在对竞存担保利益及应收账款让与作规制时以登记作为完善(perfection)要件,将来应收账款让与不区分有无基础关系,原则上只要经登记均可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此处第三人包括多重让与中的受让人、担保权人、强制执行申请人及破产管理人等(50)参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204(a),9-317(a),9-322(a)。。受美国法影响甚深的《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均设有类似规定(51)《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29条、第37条、第44条第2款;《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规定担保性让与适用担保编的规则,而担保编的优先顺位规则(第九编第4:101条)类似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相关规定。参见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J].法学,2019,(12):38.。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该漏洞填补方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以登记为核心的优先顺序规则,其规范目的在于通过构建一个清晰明了的权利顺位体系,鼓励权利人藉登记维护交易安全,从而鼓励融资,优化我国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诚如前述,在“保理场合让与登记得否对抗除重复受让人之外其余第三人(如破产管理人)”这一问题上,《民法典》第768条付之阙如,这会引起将来应收账款受让人极大的“不安全感”,削弱其提供融资的动因,不利于“提升获取信贷的便利度,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因此,《民法典》第768条存在明显漏洞,基于“实质担保观”理念,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3条(动产抵押登记对抗规则)对该漏洞加以填补。
(二)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的优先顺序
此处需要讨论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关于“登记—通知—比例清偿”顺位体系的理解。一方面,位居顺位末次的比例清偿方案颇具争议,其合理性有待证成;另一方面,当数个通知到达债务人但先后顺序不明时,受让人的顺位应如何安排?第二,在对质押或让与登记可得对抗的权利人范围予以扩张后,“新增权利人”(主要是破产管理人、扣押债权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在既有的优先顺序体系中应如何安置?以下逐一讨论:
1.比例清偿规则的法理阐释及类推适用
位居三阶判断体系最末的“比例清偿”颇为学者诟病。批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比例清偿下债权归属不明。申言之,应收账款让与系处分行为,于首次转让时权属即已发生变动,很难想象该权利可同时归属于后续受让人。其二,该方案彻底无视当事人意思,甚为不妥(52)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J].法学,2019,(12):49.。笔者认为上述意见值得商榷,比例清偿规则的合理性可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证成:
第一,债权让与的意思主义与公示对抗相结合,使得应收账款让与呈过程化,而非一蹴而就。经典民法理论认为,民事权利依其效力可划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前者具有对世性,而后者仅对特定主体产生效力(53)Vgl. Stadl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8. Aufl, 2014, S.50.;物权是绝对权、支配权,债权是相对权、请求权。然商业实践中日益普遍的“物权债权化”“债权物权化”现象引起了学者对前述经典理论的反思。代表性观点认为,物权与债权概念可拆解为支配权、请求权、绝对权与相对权四种要素的两两组合,而我们通常理解的物权系绝对的支配权,债权系相对的请求权(54)金可可.物权债权区分说的构成要素[J].法学研究,2005,(1):29.;其余组合下的权利样态虽不具典型特征,却仍冠名以“物权”“债权”,这就引发了上述实践中出现的物债界限模糊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物权、债权之效力并非囿于其概念本身,而是系于公示手段有无的制度设计;于对抗效力角度观瞻,应收账款让与的过程如“沙漏”般呈现出流动性,随着公示手段的逐步完善,受让人所得债权的对抗力趋于圆满(55)蔡睿.保理合同中债权让与的公示对抗问题[J].政治与法律,2021,(10):135.。准此以解,于应收账款多重让与场合,倘若第一受让人未办理公示,则其取得的债权效力尚欠完整,除对让与人外,不能对抗公示后效力始及之第二受让人,后者自可藉公示“后来居上”,取得应收账款之完整权利。至于比例清偿,由于数位受让人均未办理公示,相互之间均处于“不能对抗”之境地,故只能平等受偿。
第二,比例清偿规则的确立根基是债权平等理念。债权平等最初是破产语境下的一项程序法原则(56)Vgl. Brehm/Berger, Sachenrecht, 3. Aufl., Mohr, 2014, S. 487.,然晚近以来域外判解学说多有将其作为确认实体权利归属的一种进路。典型者,如日本最高法院在1993年审理的某债权转让案件中,案涉债权可分且被重复让与,然由于让与通知到达债务人的时间顺序不明,债务人只得向指定机构提存以消灭债务。后数位债权受让人均向提存机构申请受领提存标的(57)最判平成5年3月30日民集第47巻4号3334頁。。学者评析该案例时指出,前述情形中提存的法律效果不仅在于消除债务负担,而且使得数位受让人对债权之主张转化为比例清偿的实现程序,此为债权平等原则之彰显(58)森田修『債権回収法講義第2版』(有斐閣、2011年)32、102頁参照。。从债务人保护角度看,鉴于应收账款系可分债权,比例清偿规则适用下数个受让人间成立按份债权关系(59)北居功「指名債権の二重譲渡において残された論点は何か」椿寿夫編集『債権総論(講座現代契約と現代債権の展望)』(日本評論社、1990年)174頁参照。,债务人按照确定的份额履行债务,亦无负担增加之虞。
此外,在数个通知到达债务人但先后顺序不明的场合,数位受让人于“通知”位阶上处于相互“不得对抗”的状态,故此际类推适用比例清偿规则明显最为合理。尚存疑问的是,依《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的反对解释(60)《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通知到达债务人后债权让与即对其发生效力;尽管数个通知先后顺序不明,然其均确已到达债务人,在对债务人的关系上均具对抗效力(61)[日]我妻荣著.新订债法总论[M].王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81.。那么于清偿期届至倘某受让人向债务人请求全部履行,此时债务人是否须按照比例清偿之结果仅得向其为部分履行呢?对此笔者持否定立场。因为该项要求实则课以债务人调查各受让人间债权比例状况之负担,过于苛重(62)尤其是应收账款作为金钱债权,具有可分性,故可以对其进行分割而部分让与。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57.此际,各受让人间比例之计算很可能相当繁复。;基于债务人保护的理念,应当承认该情形下债务人可根据自身判断,向任一受让人为全部履行的有效性。至于比例清偿结果之落实,其余受让人自可向已受领清偿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之返还(63)域外法上,日本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当债务人对以双重通知进行的债权让与抱有疑问的情形下,应认为其可拒绝对任何一方的清偿。债务人。参见[日]我妻荣著.新订债法总论[M].王燚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82.此时债务人可向提存机构办理提存,以消灭债务。潮見佳男『新债権総论 II』(信山社、2017)471頁、472頁参照。不难发现,尽管日本法做法与我国形式上有别,然其亦旨在将债务人从“调查受让人债权比例”中解脱出来,其背后仍然是债务人保护理念之彰显。。
2.“新增权利人”对应收账款权利的顺位检讨
前已述及,在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3条对《民法典》第768条漏洞予以填补后,破产管理人、扣押债权人等亦纳入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的主体范围,其于“登记—通知—比例清偿”三阶判断体系中的顺位安排殊值检讨。由于在优先顺序上,扣押债权人与破产管理人顺位相同(64)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J].法学研究,2012,(5):15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M].台北:作者自版,2010.163.,可比照破产管理人处理。故以下仅就破产管理人的顺位安排予以探讨:
(1)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与未登记未通知担保权
就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与未登记未通知担保权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前者优先于后者,理由如下:
首先,从规制隐形担保角度看,该优序安排有助于消除隐性担保,维护交易安全。债权人设立担保的根本目的并非在于处理其与债务人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借助优先顺序安排解决其与其他现实及潜在债权人的利益冲突问题。正因如此,担保的设定须经公示,否则构成隐形担保,产生破坏第三人合理预期、无法防范当事人倒签合同虚构担保的道德风险以及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65)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J].法学研究,2020,(6):24.。《民法典》对担保制度的修改目的之一正是消除隐性担保(66)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J].法学研究,2020,(6):27;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力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J].法学家,2021,(1):52.,关键举措即为构建以登记为核心的担保权利顺位规则。赋予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优先于未公示担保权,主要是为解决未公示担保利益所涉表面所有权的问题。申言之,债权人基于对权利表象的信赖,会以为债务人的资产池(pool of assets)比真实情况要大,从而与债务人进行交易,故当债务人破产后前述信赖仍应予以维持。法律通过合理设计优先顺序,阻止那些持有秘密利益的主体行使其权利而损害被权利表征所误导的债权人的利益(67)[美]查尔斯·J.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册)[M].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520.。
其次,从比较法角度看,为解决未公示担保利益在破产程序中的顺位问题,1910年美国国会在颁布的section 47a(2)中赋予了破产管理人于破产申请时司法担保债权人的地位,基于该地位,管理人可针对未公示担保利益行使“强臂撤销权”(68)管理人的这项权力在1978年《美国破产法》中被极大地扩张,在不动产交易场合,其甚至享有在破产时业已完成登记的善意买受人的权利。John C. II McCoid, Bankruptcy, the Avoiding Powers, and Unperfected Security Interests, 59 Am. Bankr. L.J. 175, 181 (1985).,该规定为后续的《美国破产法》§544(a)(1)所承继。《美国破产法》§544(a)(1)的适用要件较为宽松:一方面,管理人的主观状态是拟制的不知情,其对债务人财务状况的任何实际知悉都不影响管理人“强臂撤销权”的享有与行使(69)譬如,在债务人自行管理场合,尽管秘密担保的设定系债务人所为,经管债务人对此必然知情,但是其仍然被拟制为不知情,可行使强臂撤销权。参见[美]查尔斯·J.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册)[M].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520-521.。另一方面,该款的适用不要求实际存在受秘密担保损害的无担保债权人,即管理人无需证明实际存在无担保债权人对未公示状态的信赖。尽管有少数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上述赋予管理人“强臂撤销权”的规定存在过分拟制之嫌(70)John C. II McCoid, Bankruptcy, the Avoiding Powers, and Unperfected Security Interests, 59 Am. Bankr. L.J. 175, 190 (1985).,但理论(71)理论界观点,如Cuevas教授认为,破产管理人的“强臂撤销权”能够通过禁止秘密担保进一步强化表面所有权原则,以保障交易安全。See Carlos J. Cuevas, Bankruptcy Code Section 544(a) and Constructive Trusts: The Trustee’s Strong Arm Powers Should Prevail, 21 Seton Hall. L. Rev. 678, 701 (1991).类似观点,See David Gray Carlson, Trustee’s Strong Arm Power under the Bankruptcy Code, The , 43 S. C. L. Rev. 841, 915 (1992).及实务界(72)实务界观点,如在Benedict v. Ratner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Brandeis指出,表面所有权问题在应收账款让与场合同样存在,担保利益未经公示不得对抗破产管理人,否则秘密担保引发的欺诈问题将对交易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See Benedict v. Ratner, 268 U.S. 353 (1925).类似观点,See Loup v. Great Plains W. Ranch Co.38 Bankr. 899, 904 (Bankr. C.D. Cal. 1984).多肯认其在阻遏秘密担保、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重要功能。
最后,从与破产法规范目的相协调角度看,破产法的规范目的系当债务人面临“公共鱼塘”困境时,通过公权力介入统一债权人行动,以实现分配公平(73)Thomas H. Jackson, Bankruptcy, Non-Bankruptcy Entitlements, and the Creditors’ Bargain, 91 Yale. L.J. 857, 857-864 (1982).;准此,集体清偿与平等分配是破产程序的重要特征。而赋予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优先于未公示担保权助益于担保制度与破产法规范目的之协调:一方面,该制度安排能够维持未公示担保权人与无担保债权人的“平等地位”(74)John C. II McCoid, Bankruptcy, the Avoiding Powers, and Unperfected Security Interests, 59 AM. Bankr. L.J. 175, 191(1985).。Tabb教授认为,在非破产场合,未公示担保权人与尚未取得司法优先权的无担保债权人会就优先顺位展开“竞赛”,只有先下手者才能取胜;申言之,如果未公示担保权人在其他无担保债权人取得司法优先权之前完成公示,那么其将获胜,反之则败。但在胜者尚未确定时,破产申请中断了这一“竞赛”。在破产申请之后,担保债权人不得再对其担保物权进行公示,无担保债权人也无法再取得司法优先权。《美国破产法》§544(a)(1)实际上宣布上述未决竞赛的结果是“平局”,其结果是:担保财产归入破产财团,未公示担保权人与所有无担保债权人取得平等的清偿地位(75)[美]查尔斯·J.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册)[M].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522.。另一方面,该制度安排契合破产程序集体清偿的属性。Jackson教授指出,通常情况下,无担保债权人的数量远超未公示担保权人,故其利益在破产法集体清偿程序中应被投以更多关照,立法政策得向其倾斜(76)See Thomas H. Jackson, Avoiding Powers in Bankruptcy, 36 Stan. L. Rev. 725, 734 (1984).。
(2)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与未登记已通知担保权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在优先顺序的安排上,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应置于未公示担保权之前。因此,对于“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与未登记已通知担保权顺位关系”这一问题的解决,其关键在于厘清“通知能否成为公示方式”;申言之,若承认通知为适格公示手段,则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劣后于未登记已通知担保权,反之亦然。
笔者认为,通知不构成公示方式。理由有二:一方面,公示涉及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无法以合同约定妥为安排(77)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J].法学研究,2019,(1):58.,通常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78)物债区分下公示原则上仅涉及物权,而就“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否包括公示方式”而言,尽管部分学者持否定立场,但他们大多并非排斥“公示方式由法律明确规定”,而是指出“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系两项各自独立的原则,并非成立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参见张志坡.物权法定,定什么?定到哪?[J].比较法研究,2018,(1):56;常鹏翱.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J].法学,2014,(3):89.。而《民法典》第768条以通知时点而非让与时点作为确定优先顺序的次标准,主要是基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考量(79)对此,立法者在释义文献中写道:“对于保理人都未进行债权让与登记的情形,考虑到通知在先虽然较之登记在先的社会成本要高,但较之合同成立时间仍然成本较低,因此,此时采取通知在先的顺位确定方式,即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顺位在先。”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417.,而非将其作为公示手段。另一方面,从法律效果上看,通知本身并不能起到公示的作用。因为通知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其实质不过是在让与人之外另行增加一个关涉让与情况的私人信息来源(债务人)而已(80)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J].法学研究,2012,(6):110.;反言之,倘若将通知作为公示机制,则无异于置债务人于应收账款受让人间对抗关系的漩涡中,使之沦为“情报中心”,接受各方问询并负担回复义务(81)石田剛『債権譲渡禁止特約の研究』(商事法務、2013)19頁参照。。其结果是,债务人因无需基于其同意的债权让与行为而陷于更为不利之地位,此明显悖于债务人保护的基本理念(82)债权让与不得恶化债务人地位,此际债务人不应负担回复问询之义务,否则会加重其负担。白石大「債権譲渡の対抗要件制度に関する法改正の日仏比較」安永正昭=鎌田薫=能見善久監修『債権法改正と民法学Ⅱ 債権総論·契約(1)』(商事法務、2018)214頁参照。。
由于通知无法作为公示手段,故破产管理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应置于未登记已通知受让人之前。综上,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优先顺序体系为:已登记受让人、质权人>破产管理人、扣押债权人>未登记已通知受让人>未登记未通知受让人。
结语
以登记为基础的统一顺位规则,系我国《民法典》在担保制度设计上兼顾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核心举措,《担保制度解释》第66条第1款即是该统一顺位规则在应收账款担保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优先顺位规则为论述中心,从竞存应收账款所附着应收账款同一性的判断、应收账款让与登记能力与对抗范围、应收账款上竞存权利优先顺序的体系建构等角度,对该规则于解释论层面所涉系列重要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同时,为司法适用提供有益参考,服务于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