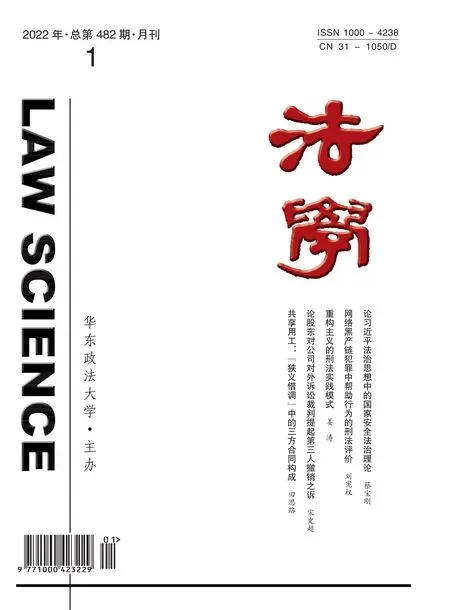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的落实
2022-02-05曾皓
●曾 皓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但是世界各国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立法、行政、司法活动的纲领性原则,还是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等多个国际人权条约所确立的儿童权利保护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12月29日批准我国加入《公约》以来,我国坚持在保障儿童权益的相关立法中转化、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1〕例如,我国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实到收养法律制度之中。我国在2020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时新增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相关内容,为此学者认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质上就是对《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概括提炼”或“本土化表述”。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第6版;宋英辉、刘铃悦:《〈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111页。我国教育部于2020年9月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学前教育法草案》)第13条也明确规定:“对学前儿童的教育应当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2〕教育部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七个月之后,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审议。根据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624号建议的答复来看,《送审稿》并未修改《征求意见稿》第13条。因此,在国务院暂未公布《送审稿》的情形下,本文仍以《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为研究对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2009/t20200907_485819.html,2021年6月7日访问;《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624号建议的答复》,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zfs/202107/t20210721_545957.html,2021年9月17日访问。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公约》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我国有关儿童事务立法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亮点。而儿童最大利益是一个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的动态概念。“从历史上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从英美判例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路径先天地使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成为了一个弹性极大的自由裁量概念。”〔3〕何海澜:《善待儿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在教育、家庭、刑事制度中的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这进而加剧了在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活动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难度。而在当前的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实现“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的着力重点。那么,我国应当如何在当前的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呢?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求教各位方家。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之合理内涵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原本是英美法系国家家庭法中确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的法律原则,该原则是西方国家摈弃“父母本位”立法思想,将儿童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的产物,其核心内容是由法官通过综合考虑子女利益和父母各自的条件来指定儿童的监护人,以确保儿童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照料。到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儿童的法律地位在世界各国得到实质性提升,“儿童权利本位”被世界各国确认为有关儿童事务立法的价值取向,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有关一切儿童事务立法的指导性原则,并被联合国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与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多个国际法律文件,确立为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首要原则。〔4〕See Lynne Marie Kohm, Trac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Standard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 Journal of Law & Family Studies, Vol. 10, No. 2, 2008, pp. 337-354.
《公约》在第3条第1款集中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各国的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及立法机构,在执行一切涉及儿童的行动中,均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条约的生命力在于缔约国的遵守与执行。因此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下文简称“童权委”)在“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措施”的第5号一般性意见中,敦请各缔约国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将《公约》第3条第1款纳入或转化为本国国内法,并确保国家在立法时将维护儿童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5〕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art. 3, para. 1), paras. 14-15,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1999年召开的第21次年会中也提出,各会员国在教育立法时应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首要考虑。可见,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我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必然要求。要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首先就应当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包含的合理内涵。
然而,何谓“儿童最大利益”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命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以下争论:儿童最大利益中的“儿童利益”究竟是指儿童个体利益,还是指儿童群体利益?儿童最大利益究竟是儿童基本利益,还是儿童全部利益?儿童最大利益究竟是儿童短期利益,还是儿童长期利益?〔6〕See Michael Freema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 Is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the Family, Vol. 11, No. 3, 1997, pp. 360-388.笔者认为,应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文本分析,从分析“儿童”“儿童利益”“儿童最大利益”等法律术语的基本涵义出发,来探讨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合理内涵。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适用主体的双重属性
对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对象“儿童”,学者基于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等不同方法论,有着不同的解释与界定。
个人主义者认为,在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主要适用领域——儿童抚养与监护制度、儿童收养制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被理解为保护个体儿童权利的法律依据与标准。因为,倘若不将“儿童”这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活生生的“个体儿童”,“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就会沦为一个空洞无物的口号;保护个体儿童的权利或福祉,才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最终价值源泉,才能使得该原则有存在的意义;一些经济发达且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是通过制定尽可能彰显儿童自主性、个性,凸显保护个体儿童权利的法律或政策,来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7〕See Philip Alston, The Best Interests Principle: Towards a Reconciliation of Culture and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the Family, Vol. 8, No. 1, 1994, pp. 2-5, 10-11, 21.然而,持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却认为,在解释儿童最大利益究竟是个体利益还是群体利益时,虽然不能以“群体性要求”覆盖或否定“个人权利保护”的诉求,但国家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集团之中的,这个社会集团的各种行为规范存在的基础是:形成并维护一定社会连带关系。〔8〕参见[法]莱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0页。因此,在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将儿童群体作为考虑对象。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持折中的观点。例如,帕克就认为,应当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对象作扩大解释,它既包括作为群体的儿童也包括作为个体的儿童。尽管在司法审判中,法官考察的是如何实现个体儿童的最大利益,但公私社会福利机构、行政当局与立法机关在作出有关儿童事务的决策或决定时,经常将维护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在这种情形下,立法或行政决策者考虑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公平地在儿童群体之间,及儿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分配诸如资金、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9〕See Stephen Parker,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Principle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the Family, Vol. 8,No. 1, 1994, pp. 36-37.
帕克的观点得到了弗里曼等权威儿童法学者的赞同。并且,童权委在2006年关于“在幼儿期落实儿童权利”的第7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明确提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对象,既包括单个儿童,也包括作为一个群体或团体的儿童。童权委还认为,适用于个体儿童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教师、保育者和其他负责照料儿童的个人或机构,在作出所有涉及儿童照料、健康、教育等相关行动与决定时,都必须以确保个体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适用于儿童群体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则要求所有与儿童福祉或儿童权利有关的立法活动和政策制定、行政管理,及相关的公共服务,例如直接影响儿童的卫生保健、幼儿看护照料及学校教育等,以及间接影响儿童的环境、住房、交通等,都必须以保障某一特定儿童群体或一般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10〕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7 (2005)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in Early Childhood,para. 13,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7%2fRev.1&Lang=en,last visit on May 7, 2021.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为了保障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机会均等,先后制定《提前开始法》《入学准备法》《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等一系列学前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应当利用公共资金为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学习障碍儿童、少数种族儿童等社会经济处境不利及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群体,优先提供补偿性学前教育服务,以保障这些儿童群体的受教育权,进而推进教育起点公平乃至整个美国教育公平。〔11〕参见庞丽娟主编:《国际学前教育法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二)以利益权衡法来确定儿童最大利益
儿童最大利益,是从英文术语“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ren”翻译而来。从语法而言,英文“the best”与中文“最大”都属于比较级。可见,确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就是一种比较与权衡各种利益的结果。那么,何谓儿童最大利益?由谁来评判儿童的最大利益?确定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是什么呢?
1.何谓“儿童最大利益”?按照“权利利益论”的说法,权利以利益为基础,受益是享有权利的表征。〔12〕See J.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 167.因此,可以把儿童利益看作儿童权利的基础,作为确保儿童在健康安全和不受歧视的环境中生存,并获得全面发展所需的各种便利和机会的总称。但儿童最大利益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相对性的概念。2013年,童权委在其“第14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儿童最大利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
(1)一项实质性权利。儿童有权要求国家机关在权衡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时,优先保障他或她的最大利益。(2)一项基本的解释性法律原则。如果可以对一项法律条款作出多种解释,则应当适用有利于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那种法律解释。(3)一项行事规则。在国家机关或成年人在作出涉及儿童事务的决定时,他们应该先评估自己的决定会对儿童最大利益产生什么影响。所有主体都应当做对儿童最有利的事。并且,国家应当制定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保障性程序。”不过,童权委还指出:“儿童的最大利益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涵盖了各类不断演化的问题。其‘一般性意见’只提供了一个评判儿童最大利益的参考工具,而不是要确定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一种情况下的儿童最大利益。”〔13〕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art. 3, para. 1), paras. 6, 11,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last,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
由此可见,相关法律所列的一切儿童权利均为“儿童最大利益”,不得对儿童最大利益进行负面解释或限缩解释,以否定或限制儿童应享有的任何一项法律权利。〔14〕同上注,para. 4.联大通过的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就明确提出,儿童最大利益应当是指儿童在健康和正常的状态下获得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且,儿童最大利益既是儿童个体的最大利益,也是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对于个体儿童,应当参照所涉儿童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其最大利益;当立法、行政等国家机关针对一般儿童事务作出集体性决策时,就必须参照具体儿童群体和一般儿童的情况,来评判和确定他们的最大利益。譬如,一国政府决定缩短义务教育学时,以节省教育资源,从而让更多的儿童接受教育。这个决定针对的就是作为群体的儿童的最大利益。〔15〕See Philip Alston eds.,The BestInterests of the Child, Clarendon Press, 1994, p.28.
2.应当由谁来认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儿童能动自治论者认为,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当由儿童自己来决定。〔16〕同上注,pp.42-61.但是,这在现实中窒碍难行。将儿童能动自治论绝对化,对儿童的决定或言论“惟命是从”,将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笔者认为,由于儿童年龄太小,或处于弱势的境况,既不应剥夺他们表达其本人意见的权利,但也不应在判定儿童最大利益时,赋予他们意见过重的分量。只能允许儿童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一些风险不大的决定,以增强儿童的能力,培养他们的自治潜能,而不能任由儿童来确定儿童的最大利益。〔17〕See Jane Fortin, Children’s Right: Are the Courts Now Taking Them More Seriously?, King’s College Law Journal, Vol. 15,2004, p. 259.并且,《公约》也只是一方面在第3条第1款中规定,要由成人或相关国家机关来确定儿童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又在第12条中要求决策者从儿童的眼光和视角出发确定儿童最大利益。因此,应当由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公共或私人或社会福利机构、第三方专业机构来确定儿童的最大利益。但是在儿童达到法定年龄、有权对影响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权益发表意见时,相关国家机关、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确定儿童最大利益时,应当参考或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另外,有关国家机关有权监督父母的决定,并且在父母的决定或行为损害儿童利益时,有权干预家长的决定,以保障儿童“过有尊严的生活”并获得全面发展。
3.确定儿童最大利益的标准是什么?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因人而异,难以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与解释,因此不宜制定一个固化的或刚性的标准来认定何为儿童最大利益。〔18〕See Micheal Freeman, A Commentary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Martinus Nijhoあ, 2007, pp.27-28.一般而言,如何界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取决于立法者、行政决策者或司法裁判者的价值观,及他们更关注儿童利益或福利的哪个层面,这是一个不同法律标准或利益博弈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确定儿童最大利益是毫无客观规律可循的。笔者认为,确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当以确保儿童全面和有效地享有各项法律权利,及获得全面发展为指引,在具体的环境中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综合权衡评估儿童最大利益所需考虑的各种要素,逐个、逐案地认定儿童最大利益。〔19〕See Geraldine Van Buer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Martinus Nijhoあ, 1995, p. 45.
基于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国家当局既把儿童视为与成年人平等的权利主体,尊重儿童的自主权;又要在儿童利益与其他主体利益或者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儿童实施合理的差别待遇,首要考虑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但“首要考虑”并不意味着将儿童利益视为唯一的或最高的考量因素。因为,儿童的最大利益可能与公共利益或监护人利益等相冲突。相较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保障等因素,儿童最大利益就并不必然具有优先性。儿童利益也并不一定比其他主体的利益更重要。〔20〕参见段小松:《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56页。而且,儿童的利益与其监护人或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具有同构性。因为,儿童是弱小的,只有成人社会从各个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照顾和保护,儿童的权利才能得以实现。甚至在幼年时期,唯有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履行其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义务,儿童才能得以存活与成长。因此,即使儿童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司法机构、教育机构等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也不能奉行儿童利益至上论,而应以衡平的理念来协调“儿童、家庭、国家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可见,奉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是要将儿童置于成年人的对立面,而是为了鼓励所有行为方参与,以全面维护儿童身心、道德和精神健全并增强他或她的人格尊严为目标,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和光明的未来,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一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益权衡工具。〔21〕参见朱晓峰:《抚养纠纷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评估准则》,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87页。这正如童权委所强调的,在存在权利冲突的情形下,实施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时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从个体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与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之间潜在着冲突,应当逐案加以解决,审慎地实现所有当事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达成适当的折中。倘若其他人员的权利与儿童的最大利益形成了冲突亦须同样处置。若达不成协调,主管当局和决策者就得铭记,应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列为首要考虑,在合理的限度内优先保障与实现儿童的合法权利。”〔22〕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art. 3, para. 1), para. 39,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 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
综上所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国家对儿童权利进行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纲领性原则,它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家庭成员、教育者和保育工作人员等所有个人,在涉及儿童事务的一切作为或不作为中,均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儿童个体或儿童群体的利益、福祉。儿童最大利益是一个灵活且可调整适用的概念,这也使得其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儿童境况。应由相关主体根据所涉儿童个体或儿童群体的具体情况,兼顾个人的状况、处境和需求,来界定何谓儿童最大利益。但是,鉴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存在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立法者不宜在相关法律中具体地规定什么是儿童个体或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而应致力于形成一个用于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要素清单,并制定一系列落实该原则的程序性保障。〔23〕See David Archard, MaritSkivenes, Deciding Best Interest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ases of Norway and the UK, Journal of Children’s Services, Vol. 5, No. 4, 2010, pp. 43-54.
二、评判儿童最大利益的各项要素之立法列举
虽然各国的法律都要求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处理相关儿童事项的基本准则,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明确阐述了何谓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了避免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沦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工具,一些英美法系国家试图通过在立法与司法中列举评估因素或标准的方式来界定“儿童最大利益”,以克服该原则的不确定性。例如,英国《儿童法》规定,法官在评判“儿童最大利益”时必须考虑以下事项:儿童的情感成长,儿童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儿童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等。〔24〕See Susan Nauss Exo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Going beyond Legalese to Empathize with a Client’s Leap of Faith,Journal of Juvenile Law, Vol. 24, No. 1, 2003-2004, pp. 4-6.又如,美国明尼苏达州法官在审理儿童监护权纠纷时,除了适用美国联邦政府《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还会依据“儿童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儿童的生活环境”“当事人给予儿童爱护、影响、教育的能力”“发生在父母间暴力行为对子女造成的影响”等因素,来“推定”如何作出裁判才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25〕参见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童权委也建议《公约》缔约国在相关法律中“拟订一份并非详尽无遗、不分层次等级的考量要素清单”,再由行政当局或司法机关在具体个案中依据所涉儿童的具体情况,对拟作出的决策或判决所涉的各个对立矛盾的要素和利益进行综合衡量,以判断特定状况、特定处境与特定需要的儿童最大利益是什么,最后作出决定或行动。〔26〕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4 (2013)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Have His or Her Best Interests Taken as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art. 3, para. 1), paras. 32, 50,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这些经验与建议,为我国在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为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我国的学前教育法有必要规定一套评判儿童最大利益须考虑的要素清单。儿童最大利益的评判要素,应当是能凸显所涉儿童或儿童群体特征的事实性构成。而这种事实性构成之所以能够成为儿童最大利益的评判要素,是因为它们是儿童受教育权的表征,是保障学前儿童身心健康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不过,想要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穷尽一切儿童最大利益的评判要素是不切实际的。笔者建议,我国学前教育法可以考虑列明以下几项儿童最大利益评估要素。
(一)保障儿童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
确保生存和身体健康是有关儿童权利保护的优先事项,是儿童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保障儿童的生命、健康、尊严与安全,是儿童最大利益的核心内容。《公约》第6条与第19条规定,缔约国不但有义务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和成长,并应当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增进所有幼儿在其学前时期这一人生关键阶段的福利;而且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教师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性侵犯。童权委还指出,儿童的生命、健康、尊严与安全涵盖儿童成长的所有方面,应当从整体上保障儿童生存权和成长权。可见,评判一国立法是否保障儿童最大利益,就必须考察该国相关立法是否有效尊重并保护儿童生命、健康、尊严与安全等。〔27〕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7 (2005)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in Early Childhood,para. 10,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4&Lang=en,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
因此,虽然儿童是学前教育的对象,且是稚嫩弱小的个体,必须依靠成人的精心照料、保护与教育才能得到健康成长,才能实现他们的权利。但是,为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就应当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视为一个与成人平等的权利主体,而不应将他们视为“受塑造的对象”或“被支配的客体”。相应地,一国的学前教育立法一方面应当明确规定,教师有义务尊重和促进儿童的人格尊严及身心健康,在保教过程中以儿童为本的态度,尊重他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要求和愿望,听取他们的意见,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尊重他们个人的看法,使儿童意识到他们是有价值、有能力、不可缺少的“人”,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获得良好的自我概念,为他们自身的继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应当禁止教师随意呵斥、责备、惩罚儿童,让儿童免遭一切形式人身或精神暴力、伤害或虐待,免遭因幼儿园或教师未能为儿童配备基本必需品而导致的生理忽视,及教师或其他照料者缺少对儿童的情感支持和爱而导致的心理或情感忽视等,不能让儿童一进幼儿园便失去了人权。〔28〕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3 (2011)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Freedom from all Forms of Violence, para. 13,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C%2fC%2fGC%2f13&Lang=en, last visit on May 7, 2021.
此外,环境是学前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幼儿园开展各种保教活动的物质条件。而且,与其他阶段的教育比较起来,环境对学前教育的作用与影响更强,学前教育对环境的依赖性也更大。保障儿童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还要求为儿童提供一种安全且舒适的教育环境,以保护儿童免遭一切生理、心理的侵害,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29〕参见王承绪、顾明远主编:《比较教育》(第4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所以,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还要求学前教育法能够推动国家、社会办好普及、普惠、安全与优质的学前教育。比如,在学前教育法中设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学系统、全面规范、职责明确的幼儿园安全风险预防体系、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安全事故处理和风险化解机制等法律制度,以切实维护师生人身安全,保障校园平安有序。
不过,保障儿童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并不意味着要禁止教师对学前儿童进行必要的、合法的、适度的教育惩戒。因为,教育惩戒源自教师的教育权。没有教育权,受教育权便无从谈起——只有承认教师拥有适度、有限的教育惩戒权,才能实现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30〕参见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法或教师法也赋予了教师教育惩戒权。但是,教师的教育惩戒并非没有边界,不当的、过度的教育惩戒只会破坏学前儿童的发展潜能,甚至是毁掉他们的美好人生。因此,只有目的正当、措施适当、程序公正,并且在尊重学前儿童人格尊严的前提下,教师教育惩戒权才具有合法性。超出这个边界的教育惩戒则属于法律禁止的体罚行为。〔31〕参见刘冬梅:《论教师惩戒权的法律边界》,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7-90页。为了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我国的学前教育法既应当确认并规范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又应当确保幼儿园及教师执行纪律的方式应符合儿童的人格尊严,并明确规定体罚行为的认定标准,体罚的预防、预警与惩治措施。〔32〕参见赵阳、孙绵涛:《学前教育立法必须明确虐童行为法律责任》,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11-13页。综上,是否有效保障儿童的生命、健康、尊严与安全,是评估我国学前教育立法是否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二)保障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平等是人权的核心内容。每个儿童都应能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享受相关权利。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个人不得基于任何理由歧视一般儿童或特定儿童群体、个人。例如,不给予儿童充分照料和关注;限制儿童游戏、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禁止儿童自由表达感情和看法等。《公约》第28条第1款还规定,确保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首先就是准入的问题,即国家应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确认、实现儿童的受教育权。因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必然要求,将是否保障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列为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要素。
法律上的平等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含义。消极意义上的教育平等,是指国家应立法确认每个儿童在享有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受教育权方面,都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并保障所有儿童不会因户籍、民族、地域、性别、家庭出身、父母、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家庭财产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在受教育方面受到歧视,亦即“同样情况同样对待”。〔33〕参见刘作翔:《权利平等的观念、制度与实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82-84页。例如,《公约》第2条与第28条都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学前儿童在受教育机会、教育标准和素质及教育条件等方面被平等相待,而不管学前儿童或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种族、性别、宗教、民族、出身、财产、伤残或其他身份等方面有任何差别。芬兰、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但将保障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它们的核心教育政策,而且将“教育平等”列为它们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日本、韩国等国还将这一权利载入宪法。
积极意义上的教育平等,是指国家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为每个儿童能获得入学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而提供保障或创造条件。〔34〕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2页。如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为了从积极方面保障学前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国家必须承担物质性、服务性和制度性等三方面的给付义务。〔35〕参见莫静:《论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3期,第43-44页。其中,物质性给付义务主要是指,国家为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对学前教育给予适度比例的财政投入,对幼儿园提供一定金额的生均经费和生均财政拨款;为保证处于困境的学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给予他们财政支持与物质保障等,从而保障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机会进入同等条件的幼儿园就读。这里强调的是教育系统的投入平等。服务性给付义务主要是指,国家就幼儿园录取、入园、收费、保教等事项,向学前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提供通知、咨询、指导等公共服务;为幼儿园设立、审批、撤销等事项提供公共服务,向学前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有关行业准入、督导、评估、培训与权益保障等公共服务等。〔36〕参见庞丽娟等:《关于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思考》,载《教育发展研究》2018第23期,第48-49页。制度性给付义务主要是指,国家就学前教育办园体制、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学前教育财政保障、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保教的内容及其开展等事项,制定有利于维护儿童最大利益的法律制度等。〔37〕参见湛中乐、李烁:《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45-51页。国家在学前教育领域承担服务性给付义务与制度性给付义务,旨在为学前教育提供优质的师资队伍、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活动方式方法与教育环境等,以确保幼儿园的管理与运行、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内容、幼儿园的环境与条件、幼儿园的安全工作等因素,能全面提高学前儿童的各种能力素质,最终实现国家预先设想的学前教育目标。
然而,国家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在履行社会权保障的给付义务时需要区分层级进行差别履行。对于未被列为义务教育范畴的学前教育,国家只能有条件地履行给付义务。因此,评估我国学前教育法是否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就必然要考察我国学前教育法是“如何制定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怎样向公民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如何设立、发展和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38〕劳凯声:《论受教育权利的国家义务》,载《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期,第43-44页。等。
(三)以儿童为中心开展学前教育
童权委在关于教育目的“第1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儿童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儿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才智和能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儿童为中心,对儿童友善并维护儿童的各项权利和固有尊严。”〔39〕Se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General comment No. 1: The Aims of Education, para. 2,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5&DocTypeID=11, last visit on December 7, 2021.
儿童中心论是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与理论内核,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所提出的“种子说”。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儿童中心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公认,该学说承认儿童具有与成年人一样的独立人格,要求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并尊重儿童的意志、自由和选择,科学地制定儿童教化养育方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就开始在儿童教育中践行儿童中心论,使得欧美国家的儿童教育“经历了一场类似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成了各种教育设施都围绕着他们旋转的‘太阳’,成了各种教育设施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的‘中心’”。〔40〕[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因此,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就要求立法者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学前教育的理念由教师或课程本位转变为儿童本位,将儿童在保教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依附地位转变为主动地位、主体地位。这实质上就是要求以满足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需求为指引,用国家、幼儿园与教师责任术语来构建学前教育法律制度,将以儿童为中心作为学前教育的教育目的。〔41〕参见卜玉华:《解读“儿童中心观”》,载《学前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页。是否立法保障以儿童为中心开展学前教育、如何立法保障以儿童为中心开展学前教育,自然成为了考察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否在学前教育立法中得到落实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考虑儿童个体/群体的差异多样性
儿童并不是一个完整划一的群体。因此,在评估学前教育法是否有效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时,必须考察立法是否充分考虑了受教育儿童的个体差异,例如儿童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个人性格、智力发展水平、身体情况、家庭情况等,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并优先保障处于困境或弱势的儿童接受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从而实现教育公平,亦即“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就应适当地考虑到他们的民族、宗教、文化和言语背景。又如,为了保障残疾幼儿的最大利益,我国的学前教育法还应当明确规定,普通幼儿园有义务招收具有接受普通学前教育能力的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与孤独症儿童,并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学前教育;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有义务建立、加强公办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育机构,以保障学前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42〕参见彭兴蓬:《全纳教育与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204页。另外,我国还应立法保障处于弱势或困境的儿童获得接受补偿性学前教育。譬如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以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接受免费学前教育等。
不过,处于弱势境况的个体儿童或群体儿童的最大利益并不一定相同。因此,在学前教育立法时,立法机关还应当考虑到每位儿童或每种儿童群体的不同类别、不同经历、不同处境和不同的困难程度,作出个体化的评判。最好能由跨学科小组进行定期的复审,并在儿童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因此,国家在学前教育立法中,是否尊重且有效保障特殊儿童的权益,也是评判该法是否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所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
综上所述,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由于受教育权具有社会权的性质,公民受教育权的确认与实现,又取决于国家对资金、物质等教育资源的分配。〔43〕参见胡锦光、任端平:《受教育权的宪法学思考》,载劳凯声主编:《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这正如一名学者所说的:“教育是一个利益场,教育法是调整教育利益关系的基本法律手段。教育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用法律手段分配教育利益,调整利益冲突,保障、促进教育利益的实现。”〔44〕褚宏启:《教育利益的界定甄别与法律调整》,载《教育学报》2013年第4期,第23-29页。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最关键的就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国家给付义务,以实现以下目标:首先,国家应在其境内为所有的学前儿童提供足够多,且良好运作的学前教育机构;其次,国家应消除儿童在获得和享有学前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确保所有的学前儿童都能获取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的学前教育;再次,国家应确保学前教育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得到学前儿童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认可,并保证学前教育不得违反最低的教育标准;最后,国家应确保学前教育与国情、社情与民情相适应,并能与时俱进地满足学前儿童成长、发展的需求。〔45〕See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1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rt. 13), 8 December 1999,E/C.12/1999/10, para. 6,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8c22.html, last visit on November 21, 2021.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上文列举的各项评估要素,在内容、依据、适用范围与作用等方面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时的分量也不相同。一些要素对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影响较大,属于重要的要素。如要求国家在建立教育体系和确保教育准入方面负担给付义务,确认、尊重与保护学前儿童享有各种合法权利,优先保障弱势儿童获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等。一些要素对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影响较小,属于不太重要的要素。如“学前儿童的性别”“学前儿童的年龄”“父母的身份”等。此外,一些要素是在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一切场合都要加以考虑或权衡的因素。例如,尊重儿童人格,保障学前儿童受到平等对待等。而一些要素只能用于评估特定个体儿童的最大利益或特定群体儿童的最大利益。例如,考察是否建立“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补偿机制”,及该机制的运行效果如何,只能作为评估“国家采取措施支持‘革民边贫’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是否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所需考虑的因素。因此,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权衡、比较各要素的分量,充分考虑儿童与儿童之间、儿童群体与儿童群体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差异,并依据国家的财政情况、教育目标、教育现状等现实情况,作出妥善安排。
三、程序性机制: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之重要保障
(一)建立儿童最大利益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在学前教育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关键在于以立法的形式解决好以下问题:如何明确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处理有关学前教育的速度与质量、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46〕参见管华:《学前教育立法应处理好十大关系》,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6-7页。等。要理顺这些复杂关系,就必须协调与平衡不同儿童及儿童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儿童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囿于专业知识有限且要处理的事项过于复杂,仅靠某一国家机关,可能难以准确地评估儿童最大利益。并且,完全交由某个政府部门评估儿童最大利益,还可能造成立法为部门利益“背书”,或者因“部门争利”而使“立法无果而终”等负面结果。
由第三方——既具备从事与儿童相关事务的经验,又熟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情况,且能以客观方式审视所收集到信息的专业人员,在良好和稳定的氛围下来确定、评估儿童的最大利益,最后由立法或行政机关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或决定。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我国的学前教育法,可以考虑建立儿童最大利益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包括:第三方评估主体的遴选机制,即明确第三方专业人员的资格条件;第三方评估的启动机制,即明确第三方介入儿童最大利益评估的条件与方式;第三方评估机制,即明确第三方评估机构调查搜集用以评判最大利益的信息和数据,并对任何会对儿童及其享有儿童权利产生效应的拟议政策、立法、条例、预算或其他行政决策的影响进行评估、监测与分析的程序;对第三方评估报告的审查与监督机制,即明确评估报告的内容、作用及其公开、审查与责任追究程序。
(二)建立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程序
要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保障儿童最大利益,就必须把尊重和保障学前儿童的各项合法权益作为学前教育立法的宗旨,在学前教育法中确认学前儿童得享有“自我成长”“教育自由”等具有防御功能的权利,以及“获得受教育物质帮助”“接受补偿性学前教育”等具有受益功能的权利。〔47〕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0页。
设立相应的权利保障程序,是确保学前儿童的上述实体性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机制。为了保障实现防御性的受教育权利,我国的学前教育法一方面有必要在学前教育法中设置保障学前儿童受教育权不受非法剥夺或侵犯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应当制定国家机关依法干预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行使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程序,要求国家机关在作出任何限制学前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行使具有防御功能的受教育权利的决策或行动时,都必须依法列明动因、理由和法律依据。
为了保障实现受益性的受教育权利,我国的学前教育法一方面要规定国家履行给付义务的法律程序,包括学前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维持程序、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国家与地方财政投入与分担程序、幼儿园的规划与设置程序、学前教育质量督导与评估程序等;另一方面,要建立保障儿童行使其合法权利的程序,包括尊重学前儿童表达他或她本人意见的程序,保障学前儿童受到平等对待的程序等。
(三)建立多元化的学前儿童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程序
西方法谚云:“有权利则必有救济。”无法诉诸法律救济的权利,根本就不是法律权利。因此,只有在学前教育法中设置多元化的权利救济程序,才能确保儿童要求将其最大利益列为首要考虑的权利得到实现,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实落地。
在我国,如果学前儿童的人身权、财产权在幼儿园受到了侵犯,学前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诉诸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但是,由于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权利,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基本权利具有直接司法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受理违宪案件;受教育权属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不属于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故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48〕参见尹力:《儿童受教育权:性质、内容与路径》,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我国的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且幼儿园与学前儿童之间的关系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所以,学前儿童及其法定监护人很难仅因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被侵犯,而对幼儿园或相关国家机关提起行政诉讼。〔49〕参见聂帅钧:《我国学前儿童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载《河北法学》2018年第8期,第152-153页。具体而言,在我国,如果幼儿园以学前儿童患有乙肝或轻微的视力、听力残疾为由拒绝其入园(侵犯幼儿的受教育机会权),或者因地方人民政府对幼儿园布局规划不合理而导致一些学前儿童入园困难或无园可上(侵犯幼儿的受教育条件权),或者学前儿童父母想为幼儿选择一个保教质量较好的公立幼儿园入学而遭无理拒绝(侵犯幼儿的受教育自由权),或者因幼儿园教育“小学化”而影响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挫伤幼儿的学习兴趣(侵犯幼儿的受教育收益权)等,学前儿童及其监护人就难以寻求相应的法律救济。〔50〕参见何善平:《3-6岁儿童受教育权保护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75-177页。而受教育权是宪法法律赋予学前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权的实现不但要求国家为学前儿童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与条件,还要求国家在相关法律中设置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程序。〔51〕参见龚向和:《受教育权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唯有如此,受教育权才能得以实现。也只有这样,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才能真正在学前教育法中得以落实。
构建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程序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可以考虑在学前教育法中设立教育行政救济制度,把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学前儿童之间的管理关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例如,在学前教育法中规定:如果学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认为,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行为侵犯了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或者幼儿在接受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受到身心伤害、不合理对待,有权向幼儿园及幼儿园主管部门或举办者投诉;如当事人对幼儿园及幼儿园主管部门或举办者的处理不服,还有权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于公民的申诉申请,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学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有在申诉过程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如学前儿童及其监护人认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幼儿的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还有权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52〕参见兰岚:《学前教育立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146页。为保护受到侵害的儿童群体或个体儿童的受教育权,我国还可以考虑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设立“教育公益诉讼制度”,规定:如果存在侵犯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行为,例如,幼儿园的保教方式与保教质量较低,或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课程内容、教育方式或教学环境“小学化”;幼儿园拒绝接受适龄且具备在普通幼儿园随班就读能力的残疾儿童;第三方扰乱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破坏幼儿园环境等,为保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公益诉讼。当然,这必须以我国采用修改法律或进行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为前提。〔53〕参见崔玲玲:《教育公益诉讼:受教育权司法保护的新途径》,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第145-148页。此外,为解决学前儿童在幼儿园受到人身侵害举证难的问题,我国还可以考虑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设立“幼儿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如发现幼儿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或者发现幼儿面临其他危险情形,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如强制报告的主体未履行报告义务,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可采方案
我国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将学前教育法的价值取向确定为儿童权利本位,将“最大限度地维护学前儿童的最大利益”树立为学前教育法的根本宗旨。而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在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就要求我国立法机关在修改学前教育法草案时做到以下几点。
(一)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条款放入“总则”部分
将集中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条款设置在学前教育法“第一章总则”靠前的位置。维护儿童的最大利益,既是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学前教育法时的首要考虑,也是保障、实现儿童受教育权及其他合法权利的准则,因而其内容具有本源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贯穿学前教育法的全部内容,能全面、深刻地反映该部法律的各项具体制度,能高屋建瓴地指导该部法律的适用,因而其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使其他标准合理化并予以澄清的依据,是一种协调儿童与成年人或社会机构之间权利冲突、儿童个体与儿童群体之间权利冲突的利益权衡标准,是比较和评价所有涉及学前教育的社会法律和实践的重要标准,因而其功能具有指导性。〔54〕参见张爱宁:《国际人权法专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因此,学前教育立法应当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确立为学前教育法的基本原则,并将该原则规定在学前教育法“第一章总则”之中。而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只是将该原则规定在“第二章学前儿童”,这明显弱化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有的法律地位与作用。
(二)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替代儿童优先原则
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中是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儿童优先原则”相提并论的。在我国过去的立法实践中,我国的法律主要使用的是“儿童优先原则”一词,而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虽然这两个法律术语都有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的内涵,我国一些学者甚至把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3条第1款中规定“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视为我国首次在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55〕参见柳华文:《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国内实施》,载柳华文主编:《儿童权利与法律保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但是这两个法律术语在理论内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儿童优先原则”是指,国家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应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发展需求;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一切有关儿童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活动的指导性原则,它既是儿童的一项实质性权利,也可以作为一项解释性法律原则与国家机关的行事规则。因此,在内容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比“儿童优先原则”更丰富、更先进;在本质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比“儿童优先原则”更符合儿童权利本位论、更能体现儿童中心主义;在适用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比“儿童优先原则”更灵活、更有利于保护儿童。〔56〕参见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下),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第114-115页。可以说,“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儿童优先原则”之间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本身就蕴涵着儿童优先的理念。因此,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儿童优先原则”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为了让我国严格遵守国际公约、与国际社会接轨,并让学前教育法体现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理念与宗旨,笔者建议,我国的学前教育立法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在法律文本中提出“坚持儿童优先原则”,而应效仿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单独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因为,不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涵摄儿童优先原则,而且,无论世界各国关于儿童事务的国内立法还是国际人权条约,使用的法律术语与适用的法律原则都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儿童优先原则”。
(三)充实用于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要素清单
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遵循外国的立法体例,没有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只是列明了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考虑的几个因素:尊重儿童人格,保障学前儿童的游戏权与平等受教育权。但是,这些考量要素还不足以有效评估与确定学前教育领域的儿童最大利益。因此,我国学前教育法应当在各章中充实评估儿童最大利益时所应考虑的要素。
“这个要素清单所列明的内容不必详尽,但它应能够给每一个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决策者提供一个指南,以帮助他们在任何有关具体的儿童利益的事项上进行正确地评估和判断。”〔57〕David Archard, MaritSkivenes, Deciding Best Interests: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e Cases of Norway and the UK, Journal of Children’s Services, Vol. 5, No. 4, 2010, pp. 53-54.比如,在学前教育法“总则”部分,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与普惠性,强调保障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确保实现幼有所育;在“学前儿童”部分,明确国家应当健全学前教育机构举办体制,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基本实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保障弱势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与质量;在“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部分,增加国家“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给付义务,规定各级政府有职责科学规划幼儿园布局,调整办园结构,增加公办资源,扩大普惠性民办资源等;在“保育与教育”部分,强调推进科学保教,全面改善办园条件,完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健全教学质量评估监测体系,尊重并保护学前儿童的尊严与安全,根据学前儿童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开展保教活动等;在“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部分,要求严格依标配备幼儿园教职工,依法保障并逐步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任职资格、地位和待遇,考虑解决幼儿园教师的编制问题,完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培训制度与监管机制;在“管理与监督”部分,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加强源头监管,完善过程监管,严格依法监管;在“投入与保障”部分,要求各级政府有义务逐年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和生均学前教育经费数额,基本实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完善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大力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为实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与“普惠性”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在“法律责任”部分,明确要求强化法律刚性,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园行为、侵害儿童权益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及执行制度。〔58〕参见庞丽娟:《学前教育要发展加快立法很关键》,载《光明日报》2018年3月29日,第14版;肖玉等:《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载《学前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第87页;刘悦、姚建龙:《学前教育立法的亮点与若干争议问题——以〈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22-123页。
(四)制定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机制
没有规定权利实现程序与权利保障程序的法律权利,是难以得到实现的。我国只是在《学前教育法草案》中规定了要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没有规定应当如何落实该原则的程序。这有可能会使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变成“纸面上的法条”,而难以得到落实与执行。因此,我国在修改完善《学前教育法草案》时,应当设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明确第三方评估主体的遴选,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启动、运行及监管程序;建立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程序,例如,在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要保障每个中国儿童都能接受学前教育,特别扶助那些由于身心残疾、经济条件差、家庭环境不利、处于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而形成的弱势幼儿群体;〔59〕参见沙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法律研究及启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设立多元化的学前儿童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程序,规定学前儿童及其监护人可以通过申诉、行政复议、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来维权。
五、结论
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涉及儿童事务与儿童福祉领域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我国在学前教育立法中也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过,由于“儿童最大利益”的概念充满了广泛性与模糊性,“儿童利益最大化”又是一个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的动态性概念,不宜制定一个固化的或刚性的标准来认定何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而应当通过制定评判和权衡儿童最大利益所必需的要素清单,以利益权衡法来确定某一特定儿童的最大利益或某一特定儿童群体的最大利益。〔60〕参见陈苇、谢京杰:《论“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第37-39页;王洪:《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32-34页。因此,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首先,要求立法机关在国家财政资金与公共资源总量都有限的背景下,从宏观层面协调“逐步推进学前教育全面普及”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之间的利益冲突,找到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科学制定国家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比重,合理、恰当地规定与规范国家为“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而承担的给付义务,从而为实现“幼有所育”提供法治保障。其次,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将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作为学前教育立法的首要考虑,充实儿童最大利益评价要素清单,在学前教育法中科学合理地制定儿童权利保障制度、幼儿园规划与举办制度、科学保教制度、师资队伍建设制度、监管机制、投入与保障制度等内容,从而保障儿童能获得公益、普惠、公平、优质学前教育的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学习成功权。〔61〕参见龚向和:《论新时代公平优质受教育权》,载《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第54-57页。最后,在学前教育法中制定确保落实儿童最大利益的程序性机制,规定公民、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有权通过法律救济程序来维护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
我国的《学前教育法草案》虽然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没有把该原则确立为学前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充分列举评判儿童最大利益所需考量的各项要素,更没有制定确保落实儿童最大利益的程序性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了学前教育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学前教育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构成了学前教育法的灵魂,决定着学前教育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考虑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学前教育法》的基本原则,在该法“总则”部分予以规定,充实评估儿童最大利益时所应考虑的要素清单,并制定确保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保障,从而真正在学前教育立法中遵循儿童本位观、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