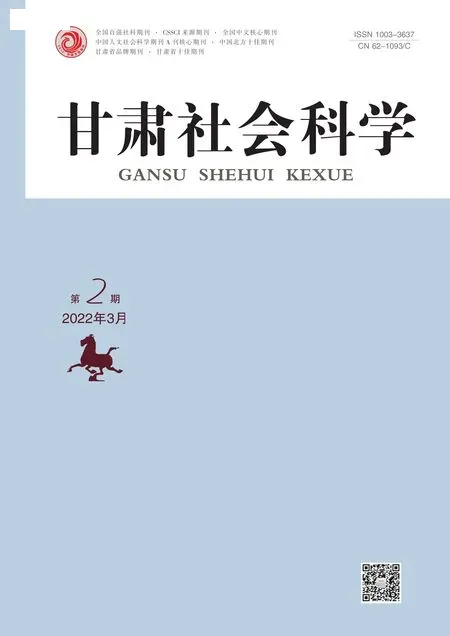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
2022-02-04康倩
康 倩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提要: 自八九世纪始,“桃花源”传说与“桃源图”即体现出紧密的共出关系,“桃花源”意象的形塑,很早便以文字和图绘的两种形式共同完成。从“桃花源”语义流变入题,对苏轼题画诗的创作活动、美学精神呈现进行全面、系统的场景还原和史论结合的分析阐释,借助“桃花源”之幽径,探胜苏轼之文艺精神与生命境界。
苏轼受到老庄影响而实践心隐,故山水画及题诗成了苏轼在心灵上归隐林泉的最佳载体。《李颀秀才善画山水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从此北归休怅望,囊中收得武林春。”[1]528《惠崇芦雁》:“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1]2770苏轼的这些题画诗句正道出了他的心声,诗句中出现的诸如渔舟、云泉、烟雨、潇湘等意象,无不寄寓着苏轼意欲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心结和愿景。在这些题画诗篇中,苏轼将画中山水图景作为真山真水来观览赏玩品味,正是典型的“卧游”。如同进入真的山水佳境悠游行乐一样,苏轼通过观画和题画,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这正是苏轼山水题画诗的美学品格之所在。苏轼之观画、题画,以及他所题写之画作中的山水景象,共同指向“桃花源”这一核心审美意象,而“桃花源”是一个在思想价值和美学精神方面衍生能力极强的文学命题,苏轼以其题画诗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学、美学中的“桃花源”母题、意象的美学内涵和审美维度,本文主要围绕“桃花源”这一关键词,来解读分析苏轼在山水题画诗中所表现出的林泉归心及其美学特质,并希望由此而窥得中华美学精神之一斑。
一、“桃花源”语义流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艺术中,“桃花源”是一个蕴含着社会理想、政治伦理道德、价值美学并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和理想价值意义的文化、审美符号,且在传统诗文创作和绘画中得到了彰显,成为古典诗、文、画中的一个从母题、主题、意象三个层面充分展开,具有强盛美学生命力的审美范式或曰审美共同体。因此,对中国传统诗画中的“桃花源”主题、意象进行历史语义层面的梳理和阐释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古代诗画中,“桃花源”主题、意象以文字描述和图像描绘两种形式呈现,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和题画诗中是以山水和人物等图像与诗词题咏方式予以呈现,常是文人用以寓涵理想世界、太平盛世的一个“象喻”符号,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美学意义,诗人和画家们在使用这个符号时无不将自我主体安置在这一理想的家园之中,或强化桃花源的隐逸生活形态,或以仙境视之,无不蕴含着避世的志趣。在历经累代集体创作与阅读后,桃花源意象内涵日益衍生、叠加、异化,演变成一个复杂、丰盈的文化景观。
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中的“桃花源”母题、主题之形成和成熟,以及以此为主题的喻象、意象、文本化世界之完型呈现,以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桃花源记并诗》为标的,《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之序言,记和诗两种文体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如果按照传统诗歌文本的普遍情况来衡量的话,这个文本的重心应该是诗而不是起导言性质的记,但是由于记写得太精湛出色,所以对后世之“桃源”审美意象的发展影响最大、经典化程度最高的是记而非诗。陶渊明在此记中以“武陵渔人”之行踪为线索,穿越于现实和历史之间,回到了他所寻觅到的或曰他心象中的那个理想世界,通过对桃花源诗意化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乌托邦世界的愿景,以及对当时的现实生活强烈不满的批判意识。当然,如果要对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文本世界形成之历史成因和思想文化基因进行追溯,必须要回到先秦时代,并且密切联系《诗经》《庄子》及《楚辞》中屈原的相关作品以及东汉后期的隐逸思想及其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对一些重要的节点性思想观念和关键词进行历史语义学的考释,由于篇幅的关系,学界已有相关论析,这里不予展开。
作为诗文和绘画的价值美学主题和意象,其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向和批判精神,在唐代以来得到了全面展现,意涵更加充盈丰富。唐代文人对桃花源的题咏倾向于从仙境和人境两个层面进行两种生命基调的建构。如王维《桃源行》“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2],具有浓厚的神仙意味。然而,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则充满了人世化的色彩,其对“桃花源”的美学叙事并不以描绘仙境为能事,而更加接近于陶渊明范式的“寓意”之文,或甚而如陈寅恪辨之为“纪实”之文[3]。对于苏轼而言,桃花源最吸引他的地方,应该是那种无政治存在的完全自由,这种书写对于处于党争倾轧之中而饱受其苦害的苏轼而言,最能带来超越和抚慰作用。苏轼对“桃花源”本质的描述,带来了对“桃花源”意象进行“人世化”诠释的美学新风。苏轼在《和桃源诗序》一文中有言: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4]765
起头便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如此断然立论的依据当然不是舒元舆、韩愈等唐人所见的桃源仙境图绘,而是在摒弃了那些传闻异本后,独尊陶潜版传说为正本之后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苏轼便回归到陶氏《桃花源记》的文本,辩称文中“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又以村人“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1]2196,来否定其为仙人之说。苏轼在文中积极地举证其可实存于人世的高度可能。他特别指出南阳之菊水、蜀中青城山老人村以及颍州之仇池等地,都属同类境地,而且“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苏轼虽将桃花源看得如此“人间”,但他也认同了陶潜的诠释,以为此“避世”之地的前提在于不“使武陵太守得而至”,不使之“化为争夺之场”,亦即保持其“无政治”的绝对自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非桃源题材的绘画题咏中,无论画面的景物为何,或烟江叠嶂,或细雨扁舟;绘画的风格或金碧山水,或青山绿水,或水墨云山,或浅绛山水,苏轼观画的心灵是相通的。苏轼在有意无意之间,均将眼前有限的山水风景画,与桃花源的文化意象相涉。最直接的引用是将桃花源的故事简化浓缩成“桃花”“桃源”“武陵”等语言符号。也就是苏轼喜欢略去桃源背后的文化记忆,而仅以桃源来形容优美的山水风景画。苏轼的题画诗中有着丰富的“桃源”意象,对这部分山水画中的桃源意象分析,会加深我们对苏轼山水画题咏的认识。
苏轼将桃花源“人世化”之举,充满了个人人生经历的寄寓与感慨,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乐观与期待,也为失意的知识分子憧憬了一个可以摆脱现实中的世俗纷争而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以此来疏解政治上的压抑与悲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意象的语义有两种解释途径:一是可以逃避政治倾轧的自由之地;二是期盼在生活中找寻到这样自然纯净的家园。某种程度上,苏轼通过赏读山水画作并且题咏,达到了这一目的,使他即便身在庙堂,也可以在观览山水画和题咏过程中寄托以上两种情思,从而达到精神上疏解的目的。
二、诗画内容的互文性——元祐年间苏轼的“桃源”想象
我们可以援用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这一理论工具对苏轼题画诗中“桃源”意象的审美生成机制进行解析。比如,宋代王诜率先开创了“烟江叠嶂”这一绘画题材与主题,苏轼及时跟进,通过诗歌唱和对王诜的“烟江叠嶂”画作进行题咏,就“烟江叠嶂”这一艺术主题和审美意象而言,苏轼之题画诗与王诜之画作便形成了两种不同体裁间的互文阐释,诗境与画境相互投射、相互映照、相互“观看”。因此,正是通过题画诗这“互文性”产物的纽带作用,王诜的画作和苏轼的题画诗作共同确定了“烟江叠嶂”这一画题的含义与功能,使“烟江叠嶂”这一文本性景观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符号叙事功能的审美喻象、意象,其所蕴涵的价值美学思想就是隐逸思想——“隐于朝”,而不是“隐于市”。苏轼与王诜之间关于“烟江叠嶂”山水画的题咏唱和,作为“书信式山水画”,它在知音间传递,起到了传达信息、叙说故事、倾诉情感、交流经验、增进友谊、劝慰鉴戒等多种功能。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烟江叠嶂图》①,系由王诜(1036—1093)所作,在水墨卷拖尾上,书有四首苏轼与王诜的唱和诗,共分两次唱和。为了便于释读,兹录如下:
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右书晋卿所画烟江叠嶂图一首,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书。”[1]1608元祐三年(1088年)王诜第一首唱和诗:“帝子相从玉斗边,洞箫忽断散非烟。平生未省山水窟,一朝身到心茫然。长安日远那复见,掘地宁知能及泉。几年漂泊汉江上,东流不舍悲长川。山重水远景无尽,翠幕金屏开目前。晴云幕幕晓笼岫,碧嶂溶溶春接天。四时为我供画本,巧自增损媸与妍。心匠构尽远江意,笔锋耕偏西山田。苍颜华发何所遣,聊将戏墨忘余年。将军色山自金碧,萧郎翠竹夸婵娟。风流千载无虎头,於今妙绝推龙眠。岂图俗笔挂高咏,从此得名因谪仙。爱诗好画本天性,辋口先生疑宿缘。会当别写一匹烟霞境,更应消得玉堂醉笔挥长篇。右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1]1607其中第一次唱和的内容,被学者认为属于《烟江叠嶂图》的青绿卷。通过诗画互文解读,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苏轼心中的桃花源意象的勾勒,另一方面可以得知,苏轼想要做的其实是将画艺的境界提升到与诗艺同等的水平。苏轼是在告诉我们,画师不应仅仅是“摹仿”技巧的匠人,他们可以和诗人一样,通过笔墨绘出的纸上烟云媒介,来传达和展现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特质。《烟江叠嶂图》青绿卷在北宋时藏于苏轼和王诜的朋友王巩(字定国,约1048—约1117)之手。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里涉及的几个人物,苏轼、王诜、王巩三人是“朋党”,时在神宗朝元丰二年(1079年),贵为驸马并擅长画山水的王诜在“乌台诗案”中因受苏轼牵连而坐罪,被削去驸马都尉,贬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并于次年赴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安置,元丰七年(1084年)获赦移颍州(今安徽阜阳)安置,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才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苏轼本人则是在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获罪下狱,侥幸被释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之后即在元丰七年(1084年)才奉诏离开黄州而赴汝州(今河南汝州)任团练副使。这样算来,苏轼在黄州谪居五年,王诜在均州也是差不多谪居了五年,更为恰巧的是他们两人又同于元丰八年被朝廷召回京师。这幅《烟江叠嶂图》画的收藏者王巩,长于诗画,他在“乌台诗案”中也因与苏轼的关系而受到牵连和责罚。王诜与王巩在文学上是苏轼的追随者,但是在北宋“党争”中,这就属于“朋党”,因此在“乌台诗案”中二王与苏轼这三个人就同命相连而共进退,都被贬谪出朝流放外地,实际上在这场“文字狱”中受苏轼牵连者不仅仅这二王两人,而是总共有二十多人受到牵连被责罚,苏轼在题画诗中“东坡先生留五年”一语,正指此而言。以上所述构成了苏轼与王诜以《烟江叠嶂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画而题诗唱和的创作背景。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评苏轼此题画诗云:“起段以写为叙,写得入妙,而笔势又高,气又遒,神又王(旺)。”[5]所谓“以写为叙”,是指这一段实质上是叙述《烟江叠嶂图》的内容,但是没有用抽象的叙述方法,而是用形象的描写方法。如果既不看诗题,也不看诗歌下面的内容,就不会认为这是一首题画诗,只是感觉到在客观地描写自然风景。前四句,着眼于高远之处,写烟江叠嶂的总貌。“江上”,点明“千叠山”的位置。“愁心”,融情入景,以扩展艺术境界。“浮空积翠”,是“积翠浮空”的倒装,主语为“千叠山”,“积翠”言翠色之浓。在古典文学的语境中,“积翠”分别指代两种意象,一是远望之浓密的绿色;二是指人间佳境。首先,苏轼在此使用“翠绿”这一语汇,是在点明画面上的由树木葱茏景色所呈现出的山水审美意象。在传统诗文中,“积翠”一词出现频率较高,一般用来形容草木茂盛,翠色重叠,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审美意象的词汇。在南朝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就喜欢使用“积翠”这个意象,比如南朝沈约《留真人东山还诗》:“连峰竟无已,积翠远微微。”[6]1002到了唐代,“积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在诗作中出现的就更加频繁了,如李白《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诗中有句云:“远山积翠横海岛,残霞飞丹映江草。”[7]王维《送李太守赴上洛》中有句:“商山包楚邓,积翠蔼沉沉。”[8]不一而足。而苏轼在题画诗中用“积翠”一语,也正是形容所题《烟江叠嶂图》画中绘写的树木之浓密茂盛和翠绿深邃。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冯应榴在其《苏文忠公诗合注》中对苏轼的这一句诗有“松柏重布云积翠”[1]795之注语,正是言此。其次,苏轼使用“积翠”又用来表达他观赏画面上呈现的山峦叠峰、烟云朦朦、树木葱茏的画境时内心所唤起的对人间仙境的向往。“积翠”这一词汇,在传统诗文中往往被用来指代山川景色之美臻于极致的人间仙境,尤其是较多地出现在宫廷应制诗的景物描写之中。比如,前蜀太后徐氏的《丈人观谒先帝御容》诗中有句:“日照堆岚迥,云横积翠间。”[9]86刘宪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诗:“商山积翠临城起,沪水浮光共幕连。”[9]780而在苏轼的这首题画诗中,他笔下的“积翠”意象呈现为“千叠山”峰峦堆绿叠翠,云烟缭绕,弥漫无边的翠色在天地间浮动,像烟如云。苏轼笔下着意突出的是“积翠”,而不是云烟,所谓“浮空积翠如云烟”,一个“如”字表明了他重点突出的是“积翠”。苏轼在诗中继续顺着自己的意绪写到,那在寥廓的天地间浮动的究竟是“千叠山”的“积翠”呢?还是升腾不已的水气云烟呢?然而对面此情此景,又实在难以让人辨别清楚,因为千叠山之景色实在是太深邃旷远了,并且变化无穷,当人在观看时,画面就产生了变化,但突然间又烟消云散,呈于目中的依然还是那“千叠山”。这里反映的其实正是苏轼内心意绪的变化,不管是“积翠”或“云烟”以及它们相互间的画面切换,都是苏轼在观画时内心意绪升腾、峰峦叠起、云烟幻化之写照。因此,苏轼在诗句中着意渲染之“浮空”的“积翠”,其实是通过诗歌语言从不同的角度、从拉近又推远的不同的镜头,来观赏画面所描绘的变幻无穷并且充满了仙味的玄远之境,而这种境界也正是他内在的一种精神向往。
“积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苏轼在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的《〈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引)》的第七首之中也出现过:“烟雨飘渺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1]795诗中所言之“海市”和“绛宫”都指幻出人间的仙境,苏轼在此题画诗中从首句开始,便将画中之景喻为仙境,诗中相继对画卷中的叠山、积翠、云烟、泉水、林麓、渔舟等一系列意象进行了诗语再描述,这种再描述,既是一种还原也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再创造。如果我们再联想一下苏轼给王诜的诗中所言之“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之语,便可以充分说明虽然画面所描绘的是山水画中常见的自然山水景色,但无不可以成为苏轼所向往的超然之境。继“东坡先生留五年”之句,苏轼又叙写了他在黄州流放中度过的四时,并且流露出在诸般景色中他最为向往的是武陵桃源的春景,诗中“虽有去路寻无缘”一句,语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10]由此句,我们可以联想到苏轼在前文中所言之“仙境”即为他心目中的武陵桃花源,而“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则指的是正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三、诗画体裁的互文性——苏轼题画诗中桃花源的音乐性
左思有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6]386在苏轼的山水题画诗中,经常出现对画中的景象通过音乐化来表现的情况,这是一种由观及听、以听代观、即观即听的“通感”审美过程,其中所体现的互文性关系值得分析。如他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说:“山苍苍,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1]872雨后空林,泉流钟鸣,水天一色的江面上,映衬着夕阳的余晖,传来一声悠扬的渔声炊乃与无边的江天、山林、烟霞融融相和,仿佛它们原是与自然界一体的声响,不是某个人在演奏,而是大自然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文人以音乐为山水的精魂,视山水之音为天籁,两者呈互文关系,通过视听转换来领略品味之,可以更得山水美景之神韵与气机。山水与音乐结合、将山水音乐化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文人对山水图像的解读,在绘画的山水风景中出现音乐的境界,即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结果,山水题画诗的幽空之境也源此而生。中国诗画是动静互补的艺术,绘画是静寂无声的图像,题画诗创造出“声”的听觉想象,以诗境的“声动”补画境的“色静”,声动色静之对比与反差反而强化了山水画境之空与幽,引领着观者的思绪心灵浸润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空与幽中,而将空与幽引入桃源之境,则是对作为价值审美共同体之“桃花源”范式的一个美学跃升,这种对“桃源”喻象、意象之虚化,无疑是一种庄禅美学质性之赋格,而这又无不强化了其在文学表意方面的虚涵性及其审美叙事功能,因此可以视为是对“桃花源”主题、意象及象喻功能的一个新的拓展。
苏轼题画诗中的音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文性的渔歌、清歌、琴、笛、钟声;二是自然性的响泉、鸟声、风声。在苏轼山水题画诗的空幽之境中,意味悠长的各种音色,不仅仅作为“声动”以补充衬托画面的“色静”,而且这两类东西又具有传统“道”的承载,所以赋予了山水图像以更深的文化意蕴。继而我们对苏轼山水题画诗的形制加以分析,如在宋迪所画的山水小品中,苏轼分别题写了三首五言律诗,来表现画面的轻快、笔墨的省净,这与我们在前面看到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图中所用的排律,给人的感觉不同,前者是一首小调,后者则更像是一部协奏曲,前奏、高潮、尾声层次分明,转换、变奏的轨迹体现得相当鲜明。苏轼在山水题画诗中,非常注重“随物赋形”,根据画面的形制特征,选取不同的诗歌体式,通过无声画与有声诗之间的互文性转化,充分调动“通感”审美方式所能带来的多层面、多维度的感悟与穿透,既可以目观,又可以耳观、鼻观,从而实现诗与画、诗人与画家、笔墨与文辞在互文性关系中营造美学共同体这一目的,就审美极致和所体现出的美学精神而言,这是中国传统文艺创作发展到北宋时期所追求并且达到了的一种极致之境,我们把这种审美范式名之为中国传统文学、绘画创造、营构出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桃花源”,如之何?
如此种种音乐画的山水意境,是绘画无法用笔墨表达出来的。苏轼对山水画的题咏中,再次创造出“声动”的听觉意象。这既是中国山水诗的文化传统,也与苏轼观照山水画的致思方式有直接关联。诗人题咏山水画,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与画家情感的互动、对绘画艺术的鉴赏、绘画批评理论的观照,同样是用画面中的素材,在内容形式上通过诗画互文,将画境当作真山水来表现、歌咏,其实质则是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精神与山水题咏融为一体。因此,我们看到,苏轼的山水题画诗与山水诗往往相差无几。在山水题画诗音乐意象的背后,则是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文人集团想要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符号,构造出同志同趣的精神世界的栖息之所。
四、遥“远”的桃花源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将中国山水画中“远”的观念,以“远的自觉”称之,认为其与庄子的逍遥精神、魏晋玄学相通,是山水画形与灵的统一。徐复观认为,“远”是山水形质的延伸。此一延伸,是顺着一个人的视觉,不期然而然地转移到想象上面。由于这一转移,而使山水画的形质,可以明确通向虚无,由有限直接通向无限;人在视觉与想象的统一中,可以明确把握到从现实中超越上去的意境,在此一意境中,山水的形质,烘托出了远处的“无”。这并不是空无的“无”,而是作为宇宙根源的生机之意,在漠漠中作若隐若现的跃动。而山水远处的“无”又反过来烘托出山水的形质,乃是与宇宙相通相感的一片生机。由远处见灵气,把不可见的与可见的统一起来。而人类心灵所要求的超脱解放,也可以随视线之远而导向无限之中,在无限中达成了人类所要求于艺术的精神自由解放的最高使命。魏晋人所追求的人生的意境,可以通过艺术的“远”而体现出来,中国山水画的真正意味乃在于此[11]。
北宋画家、画论家郭熙绘画偏爱平远山水②,苏轼也有诗歌题咏,郭熙之画和苏轼之诗,诗画合璧相得而益彰,可以近乎同步地将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引向既“远”又“淡”的境地,遥山远水,淡岚轻施,乃适宜林泉之士的性灵之居,是山水画成熟的境界,也更适合于艺术家心灵的要求。在这远景里仿佛无数景物隐没于轻烟淡霭,看不见刻画显露的凹凸及光线阴影,只有一片明暗的墨色,表象着包蕴天地之间细温的气韵与节奏,此正符合中国传统绘画、诗歌美学所追求之心灵潇洒空明的意境。所谓山水画与山水诗,以及山水画题诗,都生发和成长于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因此,在崇尚平远山水构图的画风之下,苏轼的山水画题诗也以“远意”为主要表现面向。在郭熙秋山平远的画作中苏轼这样描述:
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巘。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为画龙门八节滩,待向伊川买泉石。[1]1509(《郭熙画秋山平远》)
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1]1540(《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一)
木落骚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要看万壑争流处,他日终烦顾虎头。[1]1540(《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二)
苏轼对画面景物的描述无一例外,均是从宏观的景物着笔,取其远势,如白波青嶂、漠漠疏林、孤鸿落照、万壑争流,等等,所谓“近取其质,远取其势”,远势是山水形质的延伸,对远势的表现构成山水画题诗“远意”之基础。苏轼在题画诗中体现的观照方式也是纵目极望,“离离短幅开平远”,“目尽孤鸿落照边”,等等。在苏轼山水题画诗中这种远望取势的山水意境非常普遍,宛如题咏的公式,影响所及就连后世追和,似乎也“墨守陈规”,从“远处”着墨,突出“远观”“观远”之旨意。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如此这般地体验一番:顺着我们的视觉尽量延伸而远望,从画面一角推出而至广袤,以小景移向远峰云外,以近迫远,以小见大,在青山白云、远水平沙的虚实之境神游远观,内心升腾出超脱尘嚣之感,这应该是必然。中国画历来讲求“咫尺应须论万里”[12]的“远势”,文人画家对咫尺万里的远势已然形成一种自觉的追求。望远,必远思,无所至极。在空间上,“大曰远,远曰逝”③,由近及远,由质实转向空灵,由有限归入无限。因此,水天苍茫、烟云飘渺的远境,也是心灵的远境。如王之道《追和东坡郭熙秋山示王觉民》:
平生最爱烟水间,不知岁月磨江山。干戈七载厌奔走,清湘夜人飞蓬间。我家山水擅平远,未向郭熙见秋晚。惊鸿断处抹微云,野水尽头横翠献。林塘绿净明拒霜,似与枫叶骄秋阳。东坡山谷妙言语,珠玉倍增山水光。乱离记得承平日,政出多门事如发。伤心北狩归何时,园苑荒凉万年石。[13]
诗人将画面向画外推进一步,走向江天之外的虚空。画中远意不再是画面中的具象描绘,而是借着画内的实景,暗示着画外的虚境,表达了对仙隐之志的向往。平远山水因其画面中心聚焦点的后退与消失,令观者的视线由眼前有限的山水风景生发无所定止的远意。远的尽头就是“无”,但是此处之“无”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宇宙之间生发不已的万物之源。以“无”衬“有”,反转来烘托山水的具象,这正是中国传统诗画在虚实相生的图像空间里引发虚无空明之感的美学肌理所在。
中国诗境讲究言外之意,而无声诗——画,也讲求画外之音,艺术家想透过绘画表达的情感往往不在画面中的具象描绘,而是借着画内的实景,暗示着画外的虚境,画面内的实空间主要表达画外的虚空间,这个画外的虚空间其实就是心灵的空间。清人笪重光《画荃》有云:“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4]因此,山水题画诗中无论平远之意或迷远之境,均是由眼前有限的山水风景,生发出一种意之所游而情脉不断的远意。这一远意,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将画面延伸向空无,走向心灵。一言以蔽之,山水题画诗中“远”的自觉,其实质由远意而引发出想象空间,由质实转向空灵,由有限归入无限,最终泯灭现实与图像之间的虚实差异,而回归渺渺一统的境界,以图达到消解现实困境的目的。从价值美学的层面来分析,我们也能将苏轼山水题画诗中的这种讲求远近、虚实辩证转化关系的诗艺和画理与陶渊明的“桃花源”主题和喻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并且发现苏轼山水题画诗中的这种“桃源”笔法,不但体现出了他在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层面追慕陶渊明没有“忘言”之“真意”,而且更将陶渊明所追寻之“真意”具体地技术化到诗艺、画理之中,呈现为一种兼容诗法画技的艺理之说,由此大大地拓展了传统文学、美学中“桃源”主题、喻象之美学表现空间和张力。
结 语
其实,就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而言,“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绘画艺术就是制造视觉的盛宴,成功诱使人们远离现实生活。苏轼无论是作为一个山水诗人及山水画题画诗人,还是一个画家,抑或只是一个观画读画者,他钟情于题咏山水画,或者自己也绘写山水枯木怪石图,创作的动机与目的终究还是为了寄情山水,传达自己希冀置身其间,脱离俗世的牢笼,归返自然,从而在价值混乱与精神纷抗的时代,止息不安灵魂,回归自然而自如、没有党争、没有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纷乱不已的“桃源”世界,这种境界无论是对陶渊明来讲还是对于苏轼而言,均具有终极性的意义。苏轼在《与子由弟十五首之十四》中有云:“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4]77这段话正好用来为此文作结。
注 释:
①上海博物馆藏有两卷北宋王诜所画的《烟江叠嶂图》,一为水墨卷,一为青绿卷。本文讨论的题画诗文本出于水墨卷,但是内容指向是青绿卷,故在此特加以说明。参见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按:《烟江叠嶂图》青绿卷曾入北宋的宣和内府收藏,卷首有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题签“王诜烟江叠嶂图”,题签上钤有宣和七玺。在《宣和画谱》卷十二“王诜”条中有著录王诜画作“今内务府所藏三十有五”。(参见俞剑华标点注释:《宣和画谱》,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南宋时由贾似道(1213—1275)收藏。入清经孙承泽(1593—1676)、宋荤(1634—1714)、清乾隆、嘉庆至宣统内府收藏,俱钤有藏印。此后为近人张伯驹(1898—1982)所藏。卷后有元代姚枢(1201—1278)、明代宋濂(1310—1381)的题跋,明代黎民表的观款。姚枢的题跋:“乾坤有清气,赋予诗人身。君作无声诗,谁谓非诗人。胸中黄子陂,浩汗无涯津。烟江一万顷,写出胸中真。秋光倚叠嶂,玉树霜色匀。定应神仙游,中有云气新。温然琢玉润,老宽削铁皴。正笔参颜苏,俨然即之温。爱事论骨髓,吮笔摇吟魂。丹青亦堪老,富贵俱浮云。观画见天趣,眼子如车轮。相马取神骏,未暇骊黄分。此意久寥阆,世俗难并论。掩卷午窗静,烟炉正轮困。雪斋姚枢敬题。”明代宋濂(1310—1381)的题跋:“王晋卿画烟江叠嶂图,余见数本,其布置广狭皆不同。内一本有东坡亲笔所赋诗者尤为精绝。此卷签题乃徽宗所书,盖尝入宋内府矣,可宝也。翰林学士宋濂识。”黎民的观款:“嘉靖丙辰(1556年)夏六月领南黎民表观。”
②郭熙在《林泉高致》之《山水训》一篇中这样说道:“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飘渺。……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澹。”参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页。郭熙对平远的体会是“冲融”“冲澹”,他认为这样更接近人从容悠游的状态,更贴近艺术家的心灵追求。
③《老子》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