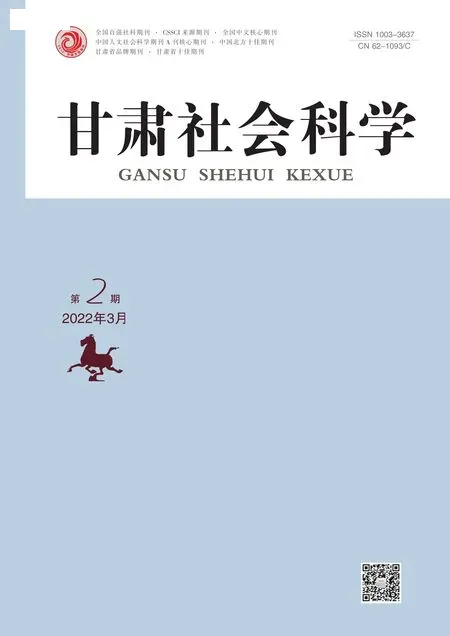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最终形成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思想实验研究
2022-02-04张一兵
张一兵
(南京大学 a.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b.哲学系,南京 210023)
提要: 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发生的经济关系(货币、资本)场境,在事物化颠倒后的变异权力对于个人现实行为的超验先在性,即经济的社会历史先验。资产阶级社会独有的市场交换中的货币关系,在盲目的交换活动中无形地重新建立了一个外部的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生成的关系场境没有指向个人主体的内在必然性,而是由商品交换关系和货币流动建构起来的外在的、偶然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勾勒了自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构式。经济拜物教理论是阐释逻辑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马克思自己新的经济学论著,不再是简单的一般“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对资本的批判。《资本论》由此得名。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中实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在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十分艰辛的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对他所面对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赋型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858年,马克思开始思考自己的理论成果如何向公众表述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后继第二分册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这既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革命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在这一重要思想实验中,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最终得以确立。本文中,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作前后发生的重要思想实验,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最终确立。
一、经济学理论叙述前的思想实验与表述话语
1858年初,马克思同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签订了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合同。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自己经济学理论构式的定位,还没有上升到对资本关系的直接聚焦上来,在这个意义上,《大纲》并非后来的《资本论》的草稿,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初稿。其实准确地说,马克思不久后写下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二分册的初稿,之后才逐步转换为新的学术构境。不久,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第一分册。我们先看到,马克思在1858年6月写下了一个《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Index zu den 7 Heften[dem ersten Theil],以下简称《索引》),这一索引写在了写有“导言”的笔记本M的最后十一页(即第23至33 页)上。这是马克思完成《大纲》后,为了从研究的思想生产转向面对公众的理论表述的思想实验。可以明显感觉到,马克思的表述话语显然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即重新回到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上,而没有坚持他在《大纲》中已经完成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全新观念上来。这应该是他一直到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和定稿这一过程的主基调。
在《索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首先关心的还是货币的历史发生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定在(Dasein des Capitals)是在社会的经济场境(ökonomischen Gestaltung der Gesellschaft)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1]308①。资本的定在不仅是一种关系,而且是统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弥漫性场境存在。这个ökonomischen Gestaltung der Gesellschaft(经济的社会场境)是一个重要的新概念,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它将支撑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概念。Gestaltung(场境)一词,已经从具体的劳动塑形和构序关系赋型中上升到社会宏观场境的指认上。因为这是理解资本关系的入口,在提法上,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尽量避免哲学话语的痕迹。
其一,货币的本质是事物化(Versach-Lichung)的劳动交换关系。《索引》的第二稿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货币是与商品并存的独立的商品交换价值”,并且,“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1]305。相比之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货币是价值关系异化的复杂讨论,这显然是过于简略的概括。马克思说,可见的货币实在,其背后隐匿着商品交换关系场境,其本质是抽象劳动时间,这种抽象的劳动时间成为商品在用地性的使用价值之外获得的“一般社会生存(allgemeine sociale Existenz)”[1]307。这个与社会定在不同,马克思并不常用的社会生存,倒真是一个隐喻式的东西,因为,这个妖魔化的金钱仿佛是有生命的生存。有趣的是,马克思在《索引》中,还提及“货币的先验权力(Transcendentale Macht des Gelds)”[1]307。这个Transcendentale(先验)当然是重要的哲学范畴,也许马克思觉得在康德之后,这会是一个能够被理解的概念。但是,这个先验性肯定不是康德在认识论上使用的那种知性构架上的先验性,而是社会历史先验,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发生的经济关系(货币、资本)场境,在事物化(Versachlichung)颠倒后的变异权力对于个人现实行为的超验先在性。索恩-雷特尔曾经认真关注过这一问题②。具体说,如果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指认了先在于个人感知和认知活动统摄机制,那么,马克思这里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奇异的现象:所谓货币的先验权力,即作为人的劳动交换关系,在商品—市场经济活动颠倒地为事物化的先验社会力量,它表明“社会过程第一次表现为同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r Zusammenhang)”[1]308。当然,货币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联场境,并不是人与人的直接关联,而是颠倒为商品与商品之间“事物化的社会纽带(versachlichtes Band der Gesellschaft)”[1]311。在这里,马克思没有使用《大纲》已经发现的货币的异化权力,而是指认这种金钱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先验统摄作用。这一点,当然也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现象学的重要观点,它也构成批判认识论中社会历史先验塑形观念先验构架的原则。这是康德认识论革命的现实基础。
其二,是货币关系发生的历史作用。1858年8月至10月底,马克思先在笔记本C、笔记本B′和笔记本B″上,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笔记本C没有保存下来,据判断,它应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的初稿;笔记本B′和B"包含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后半部分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的初稿。因为笔记本C的遗失,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笔记本B′中第二章后半部分的内容了,可以看到,这里马克思正在讨论封建制度的后期,货币场境关系取代传统社会关系的巨大历史作用。马克思说,当封建社会末期属于不同阶层的两个人开始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时,“两者是作为彼此只代表交换价值本身的抽象的社会的人(abstrakt gesellschaftliche Personen)而发生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结(Nexus),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1]315。假如这两个人一个是属于有品封建贵族阶层的高贵的地主老财,一个是属于平民阶层穷得叮当响的农民,那么,在这个交换关系中,“两者[交换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一切特殊性(Besonderheit)都消失了(在这种关系中只涉及交换价值本身,即社会流通的一般产物),而且从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的、宗法的(patriarchalischen)和其他的关系也都消失了”。这里社会关系特殊质性的消失,不同于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使用价值在对象化过程中的那个“消失的对象”,而是商品交换场境中发生的第二层级“消失”,即以抽象的劳动时间夷平(席美尔语)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什么呢?马克思告诉我们:
货币是“无个性的”(unpersönliches)财产。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联,社会实体(allgemeine gesellschaftliche Macht und den allgem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die gesellschaftliche Substanz),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物(Ding)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关联(Zusammenhang),社会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同它的所有者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因此,他所运用的这种权力也表现为某种完全偶然的,对他说来是外在的东西。[1]316-317③
当然,应该加以说明的是,这里马克思所列举的货币关系并非一般封建社会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买卖关系,而是特指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经济交换关系开始成为普遍“社会关联”的特定历史场境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在这种特殊的货币关系中,原来在等级制下,人所具有的所有政治阶层和家族的血缘关系特性,才会在金钱关系面前都统统消失。与封建关系中的天子专有的龙袍和官员的乌纱帽不同,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物相化结果出现的金钱本身,是“无个性的”,也就是没有任何专属性和个性的,作为一个可以支配所有具体财富的“一般权力”,无论什么人将它“揣在我的口袋里”,他都能“运用这种权力”,这种偶然的流动性的权力进入第三等级的平民的口袋,也就会挑战皇权,进而夷平平民与贵族的阶级等级质性。这就会造成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的政治革命。后来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也讨论过货币的这种特性。只是他的观点是抽象和非历史的。马克思说,一方面,这“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persönlicher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的解体,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通过现金赎买摆脱妨碍其发展的桎梏而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从浪漫主义方面来看,这一过程表现为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代替了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结合手段”[1]316。一是资产阶级通过货币关系的“现金赎买”,消解了封建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既解放出自由的劳动力,也创造了无孔不入、无往不胜的资本力量;二是六亲不认的单一金钱关系场境,替代了所有“丰富多彩”的亲情关系。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过的观点。马克思说,“正是这种把人和商品投入炼金炉而炼出黄金的黑暗的理财术,同时把一切阻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ctionsweise)的关系和幻想统统蒸发掉了,而只把货币关系即一般的交换价值关系作为沉淀物保留下来”[1]316。这是可以蒸发所有旧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幻想的“黑暗理财术”,它像一个货币场境关系铸成的“炼金炉”,有质性的人与物在进入这个魔幻般的交换场境之后,一切都只剩下“钱眼”这一唯一的通道。我以为,这当然也是历史认识论与历史现象学中的批判认识论的分界处,批判认识论正是要透视在“黑暗理财术”中消失的社会定在本质。
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中,他都退回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样的表述上去,而没有使用他在《大纲》后期已经发现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这样新的话语。我推测,这应该是马克思对观念传播和被接受程度的考虑。还有一个方面的差异,是在马克思准备公开发表的文本写作中,他也克制了一些深奥的哲学概念,比如异化和外化一类术语,他更多地使用了关系事物化颠倒这样的表达,比如在货币关系中,“个人相互间的这些关系表现为事物的社会关系(Diese Beziehungen der Individuen zueinander erscheinen aber als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en der Sachen)”[1]332④。可能在他看来,事物化颠倒的关系会更容易被接受一些。然而,异化关系与事物化颠倒关系虽都是历史现象学透视中的重要观点,但异化关系表征的是货币—资本关系的本质是劳动的自我异己化结果;而事物化颠倒关系,则是经济物相化的成因。二者并非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对哲学话语的这种压抑,最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特别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是被打破了,而在《资本论》中,开始马克思仍然坚持了这种表述话语中的压抑,最后还是有限地解除了。
其三,独立的个人与外在的事物性社会关联。与上述的货币关系解构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共同体的作用相关联,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即“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只是由生产中的相互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般的各个私人(atomistischen Privatpersonen)”[1]377。显然,这是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通过市场交换关系生成非直接的需要体系的构境。不过,这一切都在马克思对经济物相化的透视棱镜中重新认识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看起来独立的原子化的个人,通过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市场交换中的货币关系重新联结起来。
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共同体(Gemeinwesen)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事物的必然性(sachliche Nothwendigkeit),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Unabhängigkeit),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1]334-335⑤
不同于深嵌在血缘宗法共同体中的奴隶,资产阶级社会的确使人获得了根本的独立性,然而,彻底原子化的个人之间失去了内在的必然关联性,当他们走向市场的商品交换时,他们有具体目的的商品生产的gesellschaftliche Dasein(社会定在)则变成了市场总体发展中的无序返熵运动,只是通过事物化颠倒的货币这样“可以捉摸的”等价物,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中介性手段式的“对象性的定在(gegenständliches Dasein)”,并且,所有个人都“在交换行为中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和彼此漠不相干(Gleichgültige)的人。等价物是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1]359⑥。可以看到,只要马克思悄不留心,哲学话语就会流露出来,此处的“社会定在”“对象性定在”和Gleichgültige(漠不相干性),可能都是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话语。特别是这个Gleichgültige,直接就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重要逻辑构序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独有的市场交换中的货币关系,在盲目的交换活动中无形地重新建立了一个外部的经济共同体,相对于传统社会中基于血亲关系的可见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不可见的无形关系场境,这个共同体中生成的关系场境没有指向个人主体的内在必然性,而是由商品交换关系和货币流动建构起来的外在的、偶然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个在市场中用货币购买了商品的人,他与生产和销售这一商品的人是“漠不相干的”,但他们之间却由市场交换关系外在地、偶然地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说,“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事物的东西(Sachliches)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这正是他们作为独立的私人同时又发生某种社会关系的条件”[1]335⑦。在商品—市场经济中,个人是独立的主体,可他们通过货币建立起来的事物化的关系场境却是外部的统治性的先验权力。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在交换关系中自发生成的“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这一点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中,而且是表现在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义、最难捉摸的形式——扬弃了一切中介的形式中”[1]377。这种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盲目和无序活动中自发生成的“固定的、压倒一切的”的货币的社会先验力量,自发地调节着无序的生产和商品变卖中上下摆动的市场价格,这也就是斯密所指认的“最难捉摸”的“看不见的手”以及黑格尔用思辨唯心主义伪装起来的“最抽象”的“理性的狡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批判认识论中最难捕捉的认知对象之一。
二、市民社会话语IV与事物化颠倒
1858年11月,马克思才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当时他已经决定,第一分册不再包括原来计划的三章,而只包括前两章,并改称为《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马克思在第一分册结尾中说:“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们将在论述资本的第3章即这一篇的最后部分中加以研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从11月底开始誊抄付印稿。1859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定稿⑧。
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一上来就使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制度(System der bürgerlichen Oekonomie)”和“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样的传统表述,显然,这是一种表述话语中的理论定位。有趣的是,也是在这种传统的话语方式中,马克思首先谈及自己的“市民社会IV”⑨理论。他在回顾自己研究经济学的起因时,提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在那里: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materiellen Lebensverhältnissen),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Gesammtheit),黑格尔按照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412
这是对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之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黑格尔所指认的市民社会,是斯密(法国经济学家)已经揭示出来的经济关系系统(“市民社会II”),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中,才能找到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然而,马克思这里所讲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不直接指狭义的斯密—黑格尔的资产阶级需要和交换市场经济(市民社会II),而是链接于他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的市民社会IV,即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现实经济基础。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bestimmte,notwendige)、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bestimmten Entwicklungsstufe)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Ueberbau)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ßtseinsformen)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reale Basis)。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das ihr Sein,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vorhandenen)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Entwicklungsformen)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sozialer Revolution)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ökonomischen Grundlage)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12-413
这个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最早出现在《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对毕莱《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的摘录中⑩。在此,马克思原先是想概括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观点,可由于他这时还没有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所以,他并不知道经济结构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在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必然使这一概括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传统教科书体系将这一可以理解的失误凝固化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社会基本矛盾”时,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误解。好在马克思在文本中也做了一定的限定,即这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只是适用于经济的社会赋型(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即存在经济结构与政治法律关系的社会。这个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马克思已经多次使用过的概念。他还专门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赋型(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演进的几个时代”413。当1877年以后马克思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时,这一从“市民社会IV”转化而来的观点,就会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定直接变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适用于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社会定在本质和运动规律。
此外,继续揭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事物化颠倒机制。在面对公众所宣讲的经济学成果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进程里,暂时放弃了自己已经获得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一类概念,用学界可以迅速了解的“市民社会”和“布尔乔亚”等范畴,来介绍自己的第一个公开出版的经济学论著。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研究话语与表述话语的差异。
在第一篇《资本一般》(Das Kapital im Allgemeinen)的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了《大纲》和遗存初稿中都没有出现的“商品章(Die Waare)”。这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表述更加接近后来的《资本论》的阐释性理论逻辑构式。我体会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写作中制定的阐释性理论逻辑构式,明显不同于他自己在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实验(笔记与手稿)中自然呈现的生产性理论构式,这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话语形式上的差异,也表现在思想的不同深浅把握之中,可以看到,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实验中形成的深刻学术思想都会进入公开的理论阐释之中。这是我们面对马克思不同类型文本时,需要格外留心的一个重要构境原则。在这里,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财富谈及商品,并且,明确指认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双重属性。以后他会进一步区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
第一,他直接说,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商品“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gesellschaftlicher Bedürfnisse)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关联(gesellschaftlichem Zusammenhang)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ß)”420。有如椅子“可坐”这样的用在性场境存在,可以出现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场境之中,但它并不直接映现奴隶制或封建制特定的生产关系质性。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一般社会关联与生产关系,前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的具体用在性内容(Inhalt)规定,椅子“可坐”、粮食“可吃”的用在性社会关联,直接面对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后者则是深刻反映一定社会定在性质的形式规定(Formbestimmung)的关系,有如奴隶制中人与物中体现的直接强暴的场境存在与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商品—市场交换中椅子和粮食的可变卖性。在马克思看来,他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透视这种不可直观的生产关系,或者说,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是建立在现象学逻辑构式之上的批判认识论,所以,它必然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说,在他所关注的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则是商品的社会定在形式——交换价值,如果政治经济学关注使用价值,也只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第二,“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是对斯密—李嘉图以来的劳动价值论的坚持。这当然不是指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透视的一般物相化,即从木制椅子中看到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椅子的“可坐”的用在性使用价值,而是要在去除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后,透视出对象化在作为商品的椅子商品可交换(变卖)关系中的一般劳动时间量。显然,进入资产阶级经济王国中的可变卖性场境,已经是在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了,但这只是历史现象学透视的第一层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比《大纲》中的思考更加成熟和全面一些。马克思再一次强调指出,这种在不同商品中出现的量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发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历史性的客观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1]423。这种从劳动交换关系到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进而从商品际价值等价物到货币的抽象,并不是人们的主观经验抽象为观念,而是每天发生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经济交换活动的客观抽象场境。这一观点,自然也会涉及康德认识论革命中那个“先天综合判断”的现实历史基础。
第三,作为商品交换价值,它是对象化劳动结果,但与那种特殊性的劳动,即“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不同,商品(交换价值)生产的劳动,是无质的抽象的社会劳动。其实,这里的“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就是直接塑形和构序商品使用价值特殊用在质性的具体劳动,而“无质的抽象劳动”,则是商品交换关系中体现的抽象劳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1]429。这是说,通过劳动“有目的地”直接塑形和构序物品的用在性,是人类生存不变的“自然条件”,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原则的体现,而为了生产用于变卖的商品的劳动,则是一种只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才出现的劳动的历史性的“特有的社会形式”,这则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定观察点。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深化为价值形式理论,以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劳动二重性理论。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突然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的社会联系(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der Personen)仿佛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gleichsam verkehrt darstellt),就是说,表现为事物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 Verhältniß der Sachen)。”426这是《大纲》中已经涉及的方面,这是指证商品本身包含的交换价值的事物化关系场境颠倒。也就是说,由抽象劳动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本身,是劳动者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商品效用性的交换关系,可是它在交换活动中却颠倒地表现为商品的社会形式。椅子可坐、面包可吃的用在性,颠倒地表现为作为商品的“可变卖性”,这种可变卖性不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颠倒地表现为金钱这样的另一个(他性)“事物的社会关系”。这是经济物相化迷雾中最重要的神秘性发生。因为,在历史现象学第一层级透视中捕捉到的那个交换关系客观抽象而成的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价值),现在不再是它自己,而颠倒为一个与自己“漠不相干”的物性他者。意识和觉识到这种经济关系场境的颠倒,是历史现象学透视的第二层级。可以看出,如果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在用异化概念来表示历史现象学构式中透视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关系颠倒的本质,而在这里,他更想用事物化颠倒这样较为实证的科学话语表达出来。马克思说,“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Verhältniß zwischen Personen)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dinglicher Hülle)之下的关系”[1]426。交换价值是在金钱这种dinglicher Hülle(物的外壳)之下遮蔽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场境。因为,我们在任何一张英镑或者美元的纸币上,是看不到人与人的关系场境的。看到这种经济物相背后的劳动关系场境,当然也是历史现象学之上批判认识论的功能。在后来的《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说明过这一现象,他说,“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人劳动表现为一般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Verhältnisse von Dingen und Dinge)并表现为事物(Sache)——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存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表达事物的用语中”147。个人的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虽然这种转换本身是不可直观的,但它们并不是观念中发生的想法,而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矛盾的现实关系场境,历史现象学发现,只是这种矛盾性的关系采用了事物化颠倒的方式呈现出来。马克思说,资本家作为生产当事人,“他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本身,那些他借以进行生产并且在他看来是既定的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是这一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经常的产物,并只是由此才成为经常的前提,不同的关系和因素不仅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并取得一种奇异的、似乎彼此无关的存在方式,而且表现为物的直接属性(unmittelbare Eigenschaften von Dingen),取得物性的场境(dingliche Gestalt)375-376。这里有历史现象学中一种新的复杂的双层构境:一是资本家当作“既定的自然关系”的货币和资本,其实是特定生产关系事物化颠倒后生成的“独立的东西”(事物),这是上述历史现象学第二层级透视的结果;二是这种经济关系场境事物化的颠倒,却被当成商品和金钱“物的直接属性”,这就是特定的物化(Verdinglichung)误认场境,这里的dingliche Gestalt(物性场境),已经是经济拜物教的前提。这既是历史现象学第三层级的批判性透视,也会是批判认识论的丰富内容。
我发现,也是在这里面向公众的经济学成果宣示中,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勾勒了自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构式。显然,经济拜物教理论是阐释逻辑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直接使用《大纲》中已经出现的Fetischismus(拜物教)这一术语,但他所分析的三重经济物相化的表层误认,却正是经济拜物教批判话语的逻辑构式内核。
一是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本身是不可直观的,可是一旦它以商品的方式在场,那么,它仿佛就成了某种可见的事物。这恰恰是商品不可捉摸的神秘性(Mystifikation)成因。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列举了我们刚才所提及的不神秘的“可坐”木椅与作为可变卖的商品木椅的神秘性。马克思说:
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对象(Gegenstandes)的形式,以致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Verhältniß der Personen in ihrer Arbeit)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Dinge sich zu einander)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427
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所指是常识中现成对象的自明性一样,马克思这里历史现象学第三层级的透视,正是针对了人们在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故而变成“平凡的、不言自明”的经济物相。这是由抽象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经过商品交换的事物化关系颠倒之后,再以商品的物性方式呈现出来,人们把这种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关系场境,或者说在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一般劳动(价值)的社会关系畸变,直接当作商品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物化式的误认,正是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所在。
二是马克思说,等到交换价值通过一般等价物生成货币的时候,货币拜物教中出现的事物化现象就会表现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Form eines Naturdings)”[1]427。当然,货币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不是前述劳动生产中的用在性形式规定,而是流通领域中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结果了,当贵金属和纸币这样的“自然物的形式”在场时,则看不到劳动交换关系的遗迹了。从深层理论逻辑构序上看,这是从Versachlichung(事物化)向Verdinglichung(物化)误认的转换。然而,马克思却直接使用了Naturdings这样的表述,而刻意遮蔽了事物化颠倒这一复杂的内在机制。马克思说:
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Gegenstand),这些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有属性(specifische Eigenschaften eines Dings),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加夺目而已。442
可以感觉得到,马克思在这些表述中,尽可能压抑了自己在《大纲》中不时表露出来的哲学话语,在《大纲》中直接使用异化概念来批判的现象,这里通常是用平实的话语来展现其科学的实证描述。这里就会出现一样重要的文本学解读构境中的不同视位之间差异:在过去简单的客体视位中,我们会将时间线索上后出现的文本看作更加作者更加成熟的思想构序度,此处,就可能判断Naturdings(自然物)的话语实践会比《大纲》中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颠倒关系场境要成熟;而如果转换到文本解读的主体视位上来,则会体知到,马克思在公开阐释自己的经济学成果时,有可能考虑到读者接受程度和传播性限度所做出的逻辑退让和刻意深度遮蔽。由此,这里出现的Naturdings(自然物),则可能是省略了Versachlichung(事物化)颠倒环节的可直观表达话语。甚至,马克思忍不住说,“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1]519。表面上,这几乎回到了《穆勒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近构境层,可是,马克思却通过注释援引了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性质》等经济学论著的相近讨论[1]519。货币“从手段异化为上帝”这句话,都能感到马克思是硬咽了回去。
三是马克思还告诉我们,如果再到以后的资本拜物教,将会出现更加复杂的“物性”颠倒。以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对资本时,“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Ding)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 Verhältniß),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1]427。这是一个复杂的话语构境。李嘉图与所有资本家把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机器和厂房看作是物的时候,他们无法知道这正是资本关系事物化颠倒后的结果,而当他们用作为资本的货币去支配生产和交换关系的时候,市场本身的盲目返熵状态却使他们的逐利目的消解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物的力量“嘲弄他们”。显然,这里马克思没有使用有特定构境意向的经济事物(Sache),而直接使用了“物”(Ding),依我们此处文本解读的主体视位,这不是批判话语更加成熟和深刻的表现,而是一种刻意的逻辑退让和深度遮蔽。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一批判话语的简要构式生成为完整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
三、一个重要的思想实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之后,1859年1至2月,马克思在自制的笔记本“B"”的第21至27 页上写下了一个《引文笔记索引》(Verzeichnis zu dem Zitatenheft),显然,它是为了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而对自己之前的读书摘录笔记中的材料重新组合后所作的概括性索引。首先,马克思利用了《伦敦笔记》第VIII 笔记本以后的各笔记本的摘录,接着,他补充进了形成于40 年代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的摘录索引,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自己在不同时期中的三次经济学研究的笔记文献总括,其中,他可能会仔细分辨自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的不同入境程度和文献摘录的全景。最后,马克思把他记入1858年写经济学手稿时用的第VII笔记本后面的摘录部分中的材料(这个笔记本的前64页是《大纲》的结尾部分,64页以后的空白页被用作摘录笔记)加了进来。《引文笔记》共92页,包括多种著作、报纸杂志的摘录线索,约700多条。这一引文线索的重新梳理,自然会塑形起马克思自己的一种综合性思想构境,也是他下一步写作和思考的支援背景。应该是在1859年春天,马克思写下了《资本章计划草稿》(Planentwurf zum Kapitel über das Kapital)。其实,一直到此时,“资本”都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章的主题,马克思还没有真正形成把资本关系当作自己全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的观点。这一文本包括在一本单独的(既无号码也无字母编号的)小笔记本中,没有总标题。这个计划草稿的内容,是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即第三章(资本章)所拟的结构。这个草稿是上述《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第III项(资本一般)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因为这两份材料,都是马克思用作自己下一步写作的准备,所以,一旦没有了面向读者和外部学术场的压力,马克思立刻在生产性学术构境中恢复使用了自己在《大纲》原有的一些新术语。在《引文笔记索引》一开始(笔记本B"第21页),马克思就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的标题下,写下了“在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Bedingungen der 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消失了”[1]597,这里,马克思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刻意逻辑退让中改成的“资产阶级生产”,而是自如使用了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之后,他又在第24页上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Schranken der 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这样的表述[1]601。在第27页,马克思没有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直接写到,“以往的生产方式转化为资本主义中的生产方式(Verwandlung früherer Productionsweise in capitalistische)”[1]603-604。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Productionsweise in capitalistische这样的表述。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之后写下的《资本章计划草稿》中,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的自我扬弃的限制”[1]589这样的表述。显然,此时在马克思的内心里,他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以资本统治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即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久,马克思通过一个重要思想实验巩固了这一全新的重要想法。这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1861年6至7月间,马克思在自制的笔记本B"的最后9页即第28至36 页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Referate zu meinen eignen Heften,以下简称《提要》)。该笔记本前面写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以及《引文笔记索引》。从内容上看,《提要》是对笔记本“M”、I-VII、“C”、“B′”和“B″”中所包含的材料的概述。然而,从我们这里关注的研究线索上看,这里却发生了一个理论上的场境突变。马克思对自己已经完成的《大纲》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进行了要点提炼和重新定位,在确定自己下一步研究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之后,经过反复推敲,正式确定了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重要表述,并且,我推测马克思决定,自己新的经济学论著不再是简单的一般“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本的批判。其实,《资本论》才由此得名。
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实验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的构序逻辑。它是从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已经用过的笔记本C开始的。新的提纲中,马克思很快他指认了“资本来自流通。交换价值成为内容”,当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时,就出现了“流通向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的过渡”[1]608。这里,环环紧扣资本关系在流通领域中以交换价值为内容的货币形式的出现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正生成。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后,马克思极为精准地标识出,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资本从物质上看是对象化劳动。资本的对立面是活的生产的(即保存并增殖价值的)劳动”[1]609,这是历史现象学解蔽中物的本质剖析——对象化劳动与劳动对立的劳动—生产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der 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的目的是价值(货币),不是商品、使用价值”[1]616,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事物化为物性对象的对象性劳动对活劳动价值创造力的吸纳,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商品的用在性实在,而是作为一般财富的金钱。马克思明确标定这样的关键性要点,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不能用交换来说明”,因为流通并不创造财富。在流通领域发生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平等交换的实质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当作交换价值,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当作使用价值”,当“工人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出去”时,资本家恰恰在形式上的“平等交换”之后的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了这种创造力量的全部成果(保存价值和新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说,工人的“劳动并不是再生产出(reproducirt)它所加工的材料和它所使用的工具的价值。劳动保存(erhält)它们的价值,这只是通过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把它们当作劳动的对象性的条件(gegenständlichen Bedingungen)来发生关系。这种起死回生力和保存力不费资本分文;相反,它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力量”610。
这是一个很细的解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工人的劳动保存了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价值,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也创造了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价值和一个新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地得到剩余劳动和把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保存下来”[1]611。也在这里,马克思提点说,“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的所有条件现在表现为(雇佣)劳动本身的结果。劳动变为现实性的过程(Verwirklichungsproceß),同时是劳动丧失现实性的过程”[1]613。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资产阶级的生产”,他这里十分确定地使用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这样的概念来组织自己的思考提纲,这也为下面更大规模的手稿写作提供了基本方向。比如,在《大纲》中没有明确指认的对史前不同生产方式的分析,这里马克思直接标定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 vorhergehen)”[1]614。也正是在这里,他也突然会想到必须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sweise)同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区别(普遍性等)”[1]615。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sweise这一科学概念,来直接说明原先他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的最终形成,正是在此。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实验完成了他将近20年的艰辛理论探索。
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公开发表的理论表述话语的压抑之解除,马克思也开始轻松地使用自己内心里奔涌的哲学话语,面对新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资本的发展,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Entfremdung,颠倒,Verkehrung)。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sweise zu Grunde),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基础。”[1]622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说明,包括了狭义历史唯物主基础上历史现象学批判中的两个构境层: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配和流通领域里,已经出现了商品和货币的异化,即对象化劳动时间和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商品物的自然属性和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这是《大纲》“货币章”的基本内容;二是马克思想突出强调,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异化(颠倒)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机制就发生于这种劳动本身的自我异化关系中。这一点,马克思在《大纲》“资本章”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分析,这也将是马克思在后面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完整的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构式缘起。
注 释:
①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91.
②关于索恩-雷特尔的相关思考,可参见拙著:《发现索恩-雷特尔——先天观念综合发生的隐秘社会历史机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20.
④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33.
⑤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53-54.
⑥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57.
⑦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0,S.54.
⑧马克思在1859年1月26日把书稿寄给柏林的出版商。同年2月23日,马克思把序言寄给了出版社。《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 分册)于1859年6月在柏林敦克尔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卡尔·马克思”。
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从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下沉到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场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II,再由黑格尔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III。这于这一观点,我已经有过初步的讨论。参见拙文:《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
⑩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六笔记本中,直接摘录了这段样的文字:“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形态——即是用人类的思考,在只有大自然埋下的基础(Grundlage)之上,树立起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Karl Marx,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