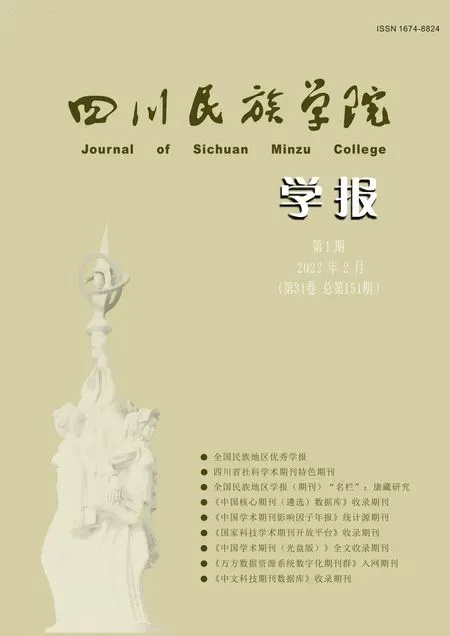二十世纪上半叶康藏研究译著述评
2022-02-04袁利
袁 利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中国现代藏学萌芽晚于西方,康藏研究是中国现代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姚乐野,石硕曾指出“康区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现代藏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发端”[1]。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要塞与历史背景决定了康藏研究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1911以前有关西藏方面的外国著作已达百余部、论文100余篇,而同期国内有关涉藏地区研究的文章和著述寥寥无几。康藏由于地势孤悬,交通阻隔,民族文化多元,国内研究者甚少,而抗日战争使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西迁或南迁,为康藏研究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近代,随着英、日、德、法、俄等国家的科学家、传教士、领事官员等主要从境外的印度和境内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进入西藏,国外对该地区的研究大量涌现,其窥探、觊觎西藏地区,在我国边疆妄图进行军事扩张与干预的目的昭然若揭。国内相关研究论文和著述随着藏事紧急的政治环境而迅速增加,其研究不得不借鉴和学习西方藏学研究成果以形成追赶之势。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关藏事研究的代表刊物《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系列,《蒙藏旬刊》《蒙藏月刊》等蒙藏系列《边政》《边政公论》系列和《禹贡》的《康藏专号》(1)二十世纪上半叶康藏或边疆问题研究学术刊物众多,康藏系列被整理为《〈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下文简称《全本》), 主要研究康藏问题;蒙藏系列包括《蒙藏旬刊》《蒙藏月刊》等11种刊物, 主要研究蒙藏问题;边政系列包括《边政》《边政公论》等7种刊物, 主要研究边疆问题,其中《边政》主要研究康藏问题;《禹贡》主要研究古地理和边疆问题,曾在1937年第6卷第12期出了《康藏专号》。等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康藏或边疆时政、人文地理、经济教育等近万篇论述和近百篇译述。根据《康藏书录题解》(2)参见《康藏月刊》1942年第3卷第12期第23-31页,第4卷第1期第12-28页,第2/3期第1-20页;1943年第5卷第2/3期第62-70页,第4期第46-55页,第7/8期第47-57页。所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康藏研究开始独树一帜并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催生了大量的专门论著和译述,康藏系列期刊作为特色内容刊载了大量知名学者的译述,“中国发表的关于藏区人文地理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作品”[2],相对其他汉语论著,这些译作似乎微不足道,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它是进一步了解康藏、治理康藏的基础,为后世康藏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和必要的文献、史料参考,也促进了藏学整体研究。
然而,过去的康藏研究中,这些译文只是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作为重要史料被提及,诸如后文提及的学者赵艾东、王川、向玉成、霍仁龙、姚勇、王启龙、邓小咏等都曾参考《川滇之藏边》《西藏东部旅行记》等译文内容从各自研究领域对西方人在康藏地区的情报收集、传教、外事、游历考察等活动及其外文史料价值方面进行探讨,虽然这些译文史料价值影响深远但至今没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对其深入探讨。笔者对上述康藏系列期刊近20年的译文刊载情况及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结合二十世纪上半叶重要史实文献对这一时期译作进行深入探讨,因《全本》中《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所刊译文的数量,影响力以及价值,故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些译作虽不可与同时代其他经典文学译作比肩,但其藏学研究价值不可忽视。分析其独特译风,纯粹的体裁以及以译述为主的翻译方式,旨在从历史语境下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共融关系中探讨译者主体性对译作语言、翻译策略的影响。
一、二十世纪上半叶康藏研究翻译概述
关于康藏研究,国外早有关注,一些学者在其著述中早有提及并整理,《关于研究康藏问政中外参考书目举要》(3)参见何璟《举要》,载于《康藏前锋》第2卷第10/11期第23-49页、第3卷第3期第17-32页。(下文简称《举要》)全面而详细地整理了关于康藏研究的中、英、日等文献目录。《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民国边政史料汇编》(4)参见徐尔灏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 1945年编,内部发行资料;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录了民国时期边政方面的史料,即蒙藏院及蒙藏委员会相关史料;吴传钧《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上、下),载于《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5期第54-60页、第6期第52-58页。等书籍中对90多个西方人在中国西部或西南边疆地区游历、考察、测量等文献目录进行整理,同时收录了部分西方人所撰写的康藏研究文献。近年来,王启龙、邓小咏从地理研究角度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文论文和书籍译述进行详细梳理,语种涉及英、法、日语,其史料参考性较强,但有些文献内容及出处仍有一些疏漏,需要完善。《举要》辑选了1800年至1927年约130年间与康藏研究有关的英文著作160多部,论文近70篇,日语著述高达269篇(部)但主要研究内容为大藏经、藏传佛教和梵教等,译著少且主要涉及西藏概观(5)参见太田保一郎著《西藏》,1907年四川西藏调查会译刊;山县君著《西藏通览》,1913年陆军部译;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1931年唐开斌译。。英语、法语类著述较多,但译著大部分是以卫藏研究为主,正如《西康之神秘水道记》(6)参见Francis Kingdon Ward著,杨庆鹏译,The Mystery River of Tibet《西康之神秘水道记》,1931年蒙藏委员会出版。译者序言所言“吾国关于康藏两地记载特少,又皆详于藏而略于康”,足见研究者的选择。《举要》中大部分著述除了某些章节涉及康藏问题研究外,专门以康藏问题研究为主的译述不过40篇(部),相对几百篇(部)的涉藏地区外文文献翻译这并不多。译作包括外文书籍和科研论文翻译,主要涉及实地考察、探险和旅游,如研究者所熟知的《西藏东部旅行记》(7)参见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此书民国时期多次被节译,详见吴墨生译《西藏东部游记》,载于《边政公论》1931年第8期第69-83页,1932年第9期第142-158页;朱章译《西藏东部旅行记》,载于《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季刊》1933 年第81-106页,后以笔名‘之通’续译并刊载于《蒙藏月报》1935年第4卷第2期第38-43页、第3期第36-41页、第4期第48-59页;高上佑译《西藏东部旅行记》,载于《康藏前锋》1934年第2卷第1期第29-37页、第3期第24-29页、第8期第59-68页、第9期第39-47页、第10/11期第23-28页、第12期第33-38页,1935年第2卷第7期第33-39页、第8期第41-47页、第12期第33-38页、第3卷第2期第31-36页、第3期第41-46页、第4期第23-26页,1936年第3卷第8/9期第22-29页;余生译《西康游记》,载于《再生》1941年第63期第10-12页、第64期第11-12页、第68期第12页。《川滇之藏边》(8)参见古纯仁著,李思纯译《川滇之藏边》,载于《康藏研究月刊》1947年第15期第5-13页,1948年第16期第2-11页、第17期第18-26页、第18期第21-28页、第19期第26-31页、第20期第20-29页、第21期第18-24页、第22期第10-16页,1949年第23期第22-28页、第26期第22-32页、第27期第28-32页。原文详见Francis Goré, Notes Surles Marches Ttibétaines du Sseu-Tch’ouan etdu Yun-Nan, Bulletin de l’cole.Fran aised’Extrême, Orient, 1923.《西康之神秘水道记》《旅居藏边三十年》(9)参见杨华明,张镇国译《旅居藏边三十年》,载于《康导月刊》1943 年第5卷第6期第36-41页、第9期第32-35页,1944 年第5卷第11/12期第40-44页、第6卷第1期第41-45页;全文共三编:西藏鸟瞰、西藏天主教、汉藏边境。《藏人论藏》(10)李安宅译《藏人论藏》,载于《边政公论》1942 年第1卷第7/8期第98-105页、第9/10期第70-80页。原文详见G.A. Combe,A Tibetan on Tibet,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26.《康藏故事集》(11)原文详见A·L· Shelton,Tibetan Folk's Tales,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5; 作者常见中文译名为“史德文”,著作为胡仲持首译,此后出现多个译本,胡仲持译《西藏故事集》,1930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程万孚译《西藏的故事》,193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甘棠译《西藏民间故事》,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敬祥译《西藏故事集》,1937年上海开明书局;李敬祥译《七个王子》,1941年上海启明书局。等,主要涉及康藏地区的地理、气候、植物、民族 、宗教、民俗等。其中针对康藏问题的全译本很少,80%译作属于著作节译。一些涉及康藏问题的科普论述、游记以及研究论文,诸如源泉所译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陈告佳所译《西康东部高原游记》以及洛克(Joseph F. Rock)所撰的游记译作(12)参见源泉译《西康人文地理述略》,载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7/8期第155-163页。陈告佳译《西康东部高原游记》,载于《旅行杂志》1940年第14卷第11期第3-14页。约瑟夫·洛克多篇游记被翻译刊载,例如吴墨生译《经过亚細亚的奇伟河峡》,载于《边政》1931年第5期第190-215页;李伯谐译《雄伟壮丽之明雅贡噶山》,载于《边政》1931年第8期第159-183页;金飞译《木里游记》,载于《边政》1932年第9期第159-174页。等,这些译文多载于康藏《全本》和《边政公论》,而《边政》、蒙藏系列以及《清华周刊》等期刊偶有拾遗。
与《边政公论》等期刊相比,《全本》刊载康藏研究的译作数量最多,针对性也更强,独具特色,其史学和学术价值受到学者和专家的普遍认可。“对国外学者关于康藏地区考察报告的翻译与刊载,更反映了当时学者广阔而独到的学术视野和视角。”[3]其中《康藏研究月刊》刊载量最为突出,该期刊所共刊载65篇学术文章,译述13篇,约占总篇目的13.8%,属三种康藏期刊之最。这些节译主要包括李思纯所译法国天主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é)的《川滇之藏边》之主要篇目,译文总计约七万字,这些译文对后世研究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反映外国人在康区考察活动的文章中,最具价值,所反映的康区内容最为详细和丰富”[4]。虽然杨明华、张镇国后来也选译了古纯仁所著的另一部短篇游记《旅居藏边三十年》连载5篇刊载于《康导月刊》,但内容主要涉及西藏宗教和外交事件。故“《川滇之藏边》在同时期外国人所著有关康区的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和独特价值”,其译文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高上佑所译英国人台克满(Eric Teichman)的著作《西藏东部旅行记》刊载于《康藏前锋》。该著作早期被吴墨生翻译过两章,之后有其他译者选译过,但高译篇目最多,居所有期刊之最,连载14篇,包括4篇藏史序言之藏边各方之关系史略与10篇康藏旅行记事,以史料的形式详细呈现康藏地区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状况,对当时康藏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素材和佐证。值得一提的是《康藏前锋》等刊物的译述改变了康藏研究模式——以译促研,在康藏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中,大部分学者都从事过外译。外文著述“具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学术撰写规范,其体系和理论都更加科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某种科学论著的范式。”[5]对国内相关研究从学科体系、行文特色、语言组织上都有一些影响。通过翻译,让国人了解到外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和研究远比我们深入,从而激发国人从更广阔的视野去了解康藏研究的焦点、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对比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认识自身研究特色与优势。
二、康藏问题著述翻译的特点
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有关康藏地区的典籍文献甚少翻译作品中探险、游记方面的内容比重大。早期国内学者为了进行深入研究康藏不得不参考这些国外文献,因而所选译文具有一定主题性和针对性,如上文所提及的《西藏东部旅行记》《川滇之藏边》等著作以及一些国外地理杂志的科考、游记译文,主要涉及当时康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因此这一时期译文、译风上具有如下特点,一方面,翻译体裁以科研考察、实地探险和游记居多,翻译风格以写实、科普为主,语言形式多以半文半白。另一方面,翻译策略多采用译述,译注常被用以作文化或语言注解或诠释。
(一)文风朴实,多为游记
文风朴实符合科考、探险等文献的要求。二十世纪初边藏研究译作延续清末“学西人”,“广民智”[6]的思想。科研论文,考察报告,游记探险文献的翻译是康藏译作突出特点。这个时期西方人在康藏地区科考、探险、旅行活动主要通过游记形式记录并流传[7],内容与康藏地区社会的基本情况有关,如《川滇之藏边》的作者古纯仁,一位法国天主教士,通英语,会汉、藏文,长时间滞留考察,其著作较为全面翔实地记录了作者游历考察康区各地之情形;该书分社会和地理两部分,著名学者李思纯选择了该书的11篇内容节译并刊发于《康藏研究月刊》包括《川滇之藏边》《川边之打箭炉地区》《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理塘与巴塘》《维西》《旅行金沙江盆地(1922年)》和《察哇龙之巡行》《康藏民族杂写》,内容涉及人文地理、社会,民俗等;译文朴实,可读性强,多次被学者引用。一般而言,写作目的决定了内容,同样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风格。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大部分西方人进入西南边疆进行考察、探险和游历达到高潮,固然一方面是因为东方文明的吸引,但大部分人根本的目的还是觊觎我国西藏,有所图谋。这一时期,大量西方政客、传教士、探险家和科学家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入境,对藏边进行考察、调研、游历和资料收集。他们是早期康藏的研究者,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西藏的探路人和情报收集者,例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古柏(T.T. Cooper),博物学家普拉特(A. E. Pratt),外交官川边领事台克满和美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W.W. Rockhill)等(13)这一时期,西方人进入中国边藏地区从事游历、考察等活动可从其著述中窥知一二。古柏,第一个在川西和滇西北一带探路的英国人, 撰写考察文章和《身穿汉装的商业先驱之旅》《藏东游记》等著作,为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扩张提供情报;普拉特,英国博物学家,收集动植物标本记录于《西藏踏雪记》及《两访打箭炉游记》等著述中;柔克义,曾到打箭炉做人类学和民族学考察并采集标本,著有 《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等著作;古伯察是最早进入康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以传教和考察之名进入西藏,著有《鞑靼西藏旅行记》;史德文曾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康区情形和其在康区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游历者是西方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他们到康区除了“传福音”外,还在该地区进行地理考察、植物采集、文化交流等活动。例如,法国传教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美国传教士史德文(A. Shelton)等。在这样历史背景下,而游记考察成为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许多学者曾通过翻译深入研究过这些科学家、传教士在藏边考察和游历背后的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探索等目的。[8]翻译这些游记可知康藏研究之概貌,窥西方学者之意图,例如《西藏东部旅行记》作者台克满,曾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熟悉中国,特别留意研究西藏,1918年奉英国政府之命赴藏调节西藏纠纷,事后著书。其游记则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英在西藏问题的立场和外交关系,其政治立场鲜明,另一部分才是赴藏日记,同为游记,古纯仁的《川滇之藏边》立场更为客观。另外,从1888年到1929年刊载于《皇家地理学会月刊》等专业学术期刊上40多篇有关康藏地区科考或游记文章,如普拉特就刊发过《两游藏东边境之打箭炉》,古柏四篇考察记录则发表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文集》。部分论文在当时被国内学者翻译,如上文提到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西康东部高原游记》等。游记表达方式多样,记叙、描述、论述作者所见、所闻、所感,其内容主要涉人文地理,社会面貌等。也包括很多专业科学知识如地理测量、动植物,水利等,因此译文的体裁也如其科普文章一样简洁朴实而流畅,例如《贡噶各寺院探奇记》:“五月二十八日,自木里出发,四周森林,尽属松橡,林际外瞩,遥见里塘河,峡谷在其南,风景甚美…… 翌晨极早出古德村,冒雾行,过广漠森林中,丰恬不飓,万籁俱寂,仅杜鹃啼鸣,稍解清晨之沉寂而已。”[9]58
虽然这些考察游记有些观点带有主观性,但其著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记录了其考察游历时期康藏社会发展情况,有一定翻译价值。另外,民国时期,国内囿于研究条件的局限,而西方人使用了现代科学的考察方法和测量技术在西南边疆进行游历和考察,故翻译这些图情资料是一种深入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即使近几年,学者要研究康藏边境的历史也要参考这些史料,而对西南边疆游记资料的利用近年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期”[10]。
(二)译为主体,述为补充
从翻译角度看,“译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康藏译作另一大特点,此术语常见于民初的翻译或版权页中,该语词在明朝开始使用,传教士高一志曾自谦称其译作为“译述”。译界熟悉的《天演论》就是一部译述,“如果说译述形成于严复,那么林纾则把这种方法发扬光大”[11];因此严复、林纾等实际掀起了译述史上的一次高潮。何为译述?学界并没有统一定义,但意思大抵相似,译述中“译”是基础,“述”是补充,“一般指译者仅仅表达出原文的主要内容或大意,而不是那么完全忠实于原文。”[12]然而,这一时期的译述呈现方式并不一样,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其一,译者根据原作,并不按照原文的顺序和语言逐一译出,只是译出其主要意思,如《猴岛交涉记》(14)详见黄明信译《猴岛交涉记》,载于《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第145-160页。,译者在序言已说明“原书版本不佳,而且错字极多,好在前后行文连贯尚无大碍,就略去未译”。其二,依托原文进行翻译,翻译过程中常有增删,其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者通常在篇首或篇尾以“译者按”的形式进行补充说明,例如,《藏人论藏》(见上文注释)在开篇洋洋洒洒几百字补充了一大段原作者和翻译背景与内容等相关信息,“译者案:此文译自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之藏人论藏一书……首末两章为孔贝自传,一论佛教,一述打箭炉之跳神,其余各章均藏民智慧保罗旅行与观察所及…”。而杨明华、张镇国所译《旅居藏边三十年》,译者不仅在篇首对翻译内容、目的及风格进行简要概述,在篇末还补充对翻译背景和译事作了必要的介绍,“结语,本篇脱稿后,发生二件大事,影响西藏之前途必巨……谁能逆料此次战争如何结局乎,虽然,西藏绝无不受影响之理。”
另外,这一时期的译述中的“述”有时也发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句子或段落进行翻译介绍、补充、说明和评述,看起来与“译注”类似。“加注”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二十世纪上初,译注不像如今翻译那么规范。任何语言都有其特殊性,译者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总会有言而未尽或言过其甚,加注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完整地传达原文的语义和风格的一种补偿方法,是为了尽可能达到翻译等值而采用的辅助性手段”[13]。李思纯在其《川滇之藏边》中大量地使用“文中述”,译者常采取两种形式进行,一是翻译内容后加括号补充注释信息,二是以“译者按”提示后增加解释内容,这两者略有区别,前者通常对时间、人名地名等进行解释与说明,后者常对康区宗教、社会习俗、史事、事件等进行必要的阐释与补充。
三、译者视角下的康藏研究著述翻译
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至今,各种理论和流派层出不穷。从翻译语言学派到文化派的发展,从以“原文中心”翻译观到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的多种思潮,其研究主体越来越指向译者方向。霍姆斯(James S. Holmes)1972年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框架中虽没有在纯粹的翻译研究中考虑对译者的研究,但在翻译应用研究中通过translator training明确了译者的重要性。[14]翻译的外延不断扩大,但翻译的本质依然是“换易言语使相解”;直译、意译和忠实、通达等问题始终是评价翻译实践绕不开的问题,但其研究的切入点和范式早已不同。除了对原文与译文讨论外,学者也从译者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早期有如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尽量让读者安居不动,使作者靠近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就已经开始讨论译者的状况与活动。列文(S. J. Levine)认为“翻译应该是一种批评行为……产生疑问,提出问题,对原文的意识形态重新语境化”[15]表明了译者在翻译中立场与作用。韦努蒂(L.Venuti)对文学译者的“隐身与显形”研究,提莫志克(M. Tymoczko)的“译者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霍米觝巴巴(Homi Bhabha)的“第三空间”等表明了译者的立场和定位在翻译研究中的日益重要性。[16]
相对民国时期笼统地称为“译述”,现代翻译中对这类翻译方式描述更为具体,“转译、译写、创译、变译”等常被学者们使用。译述是什么样的翻译?国内学者常用“translating and reviewing,reviewing,transwriting”等英语术语,反映了学者对其不同的理解。印度翻译家拉尔(Purushot Lal)曾定义译创为“具有可读性、不严格忠实的翻译”。[17]大部分学者认为“译创”应该在一定的翻译基础上改编,增删甚至再度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译创亦可称创译,这和译述有相似之处;不管采用“先译后述”还是“夹译夹述”的方式,译是主体,这里的“述”既有综述又有评述之意。如上文提到朱章所译的《西藏东部旅行记》,在其卷首“译者附识”,相当于译者序,简要概述该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对其内容进行简短评述:“民念一年下(即1932年),余读该书一过,觉其议论见解,虽不无偏颇之处,然大体尚能持之稳健,堪供参考,日记部分,更多珍贵材料,爰即从事移译…”。有些学者认为译述之“述”更多体现为“撰写”,或“创作”。译述和译创主体都是译,但呈现方式上,前者有综述、评论之形,而后者有撰写、创作之意。相对而言,上文提到的译文,其体裁和翻译目的决定了“述”原比“创”更实际,更符合读者的需求。近年来,“译述”随着翻译外延的拓宽其定义也有些改变,国内学者黄忠廉把这种翻译方式又称之为“变译”,他认为“述,即转述,是在译文中转述原作相关内容,与‘述’相应的变译方法是译述,即译者用译语转述原作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的变译活动”[18]。因此译述更强调译者的作用,译者不但要吃透原作内容,领悟其要旨所在,用目的语准确再现,还要对原作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评述,如译者在《贡噶各寺院探奇记》“按”中述评道: “余以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自云南省城出发,挈随从多年之纳书(藏书)人偕行,由大理抵丽江,作探奇之筹备,添雇随从,部署行装,一切既妥”乃复北发,行十日而抵木里土司境,(15)木里土司译作木里,在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处,系雍正八年归附,授安授司印,所管皆番僧,清时隶属会监营。当地人民,称土司为大王,故西籍常译作kingdom,实不过一族之酋长而已,(16)笔者注:原文无此句,属于译者评。拟晴土司护送往贡噶,乡城,即定乡县。”[9]58
“译述”中译者除了将原文主旨内容尽量译出,还会以译者身份对其加以介绍和评论,韦努蒂根据自己翻译意大利实验派诗歌和小说经验提出译者将译文译成流畅、地道、可读的语言,创造出一种“透明的幻觉”可以使其“隐身”,译文看上去不是译文,而是“原创文本”,受到更多的青睐[19]。如上面的译者评述的一句,文中并无明显提示和译文融为一体。为此“译者要先对原文了然于胸,下笔时不要太拘泥于一字一句 ,主要在把意思表达出来 ,可以增 ,可以减 ,可以夹译夹述。”[20]即译者要把作者的真实意思表达出来可以对原文的信息进行适度的创造或加工,译述能给予译者一定的求真务实的空间与适度的自由[21]。然而,在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语境中,这种强调内容顺畅通达,述评具有点睛之笔的译述,让译者不能完全“隐身”,在译文中,译者通过不同的“述”得以“显形”,当然这里“显形”不同于韦努蒂针对文学翻译者的“行动号召”方式,因为它并非原文本身的翻译。根据费尔斯蒂纳(J. Felstiner)对译者“隐身”的理解,他认为“新诗歌一旦定稿,翻译时投入的工作就‘隐身’了,其中包括译者背景、研究,翻译构思等”[22],而这里的译述,除了对翻译的补充、说明和评述外,还包括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上文提及《川滇之藏边》,文中大量的“译者按”就是作为研究者学者译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
“译述”立足于“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一个崭新的切入点”[23];译者是纽带和媒介,“译”到“述”的过程复杂多变,在其对原文深入理解后并结合读者情况对原文进行注解和述评,从原文到译文,再从译者到读者,以译者为出发点建构“译者——译文——读者”新三元关系。译述内涵决定了其所指可以是上面提及的“转译、译写、创译、变译”任何一种,这由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来决定。忠实畅达,直译意译等二元对立关系有时无法更好地解释诸多的翻译现象,诸如康藏译著翻译中译者身份、社会因素、读者因素等对翻译内容、语言,翻译方法的制约。近年来,国内对译者及其行为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如胡庚申从“译本、译者、译境”[24]三者相互关系讨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周领顺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讨论,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是既不同于以二元对立式判断的译文与原文忠实度静态研究范式,也不同于社会背景下对文本和译者理性批评的研究范式,它强调译者行为与译文品质的相互作用,充分考虑了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性、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25]民国时期康藏译著中“译述”的名与实比较复杂,诚如李奭学谈及明清之际天主教的翻译文学史时指出的那样“这期间耶稣会士的翻译,很少列出原作者和原书名,也不会在书中告诉我们有多少成分是‘译’多少是‘撰’”[26]。这表明译述中,译者主体性在“译者——译文——读者”三元关系中贯穿整个翻译过程,译者在材料选择、翻译策略,语言使用等都具有一定抉择权。从译者身份来说,上文提及的学者李思纯是民国时期四川大学教授,现代藏学开拓者之一,而高上佑是康藏前锋社社员,后来的西康省代议长,政府官员,其选择的材料亦有所不同,《川滇之藏边》出自学者、教士古纯仁,而《西藏东部旅行记》则出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川边领事台克满;所译内容,前者翻译与康藏地区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状况,民风民俗等内容,后者翻译与外交军事、边疆冲突等;从翻译策略和语言使用上,李思纯在《川滇之藏边》翻译策略采取“注”多于“述”皆因目的语读者鲜有法语习得者,故注释较多,这也成为该译文一大特色,据统计其每一篇译作至少四五十个注释,而高上佑则反之,李思纯作为学者的严谨性体现无疑。在语言使用上高在《西藏东部旅行记》译文中保留了康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域特色给读者以新鲜感,由于其涉及三种语言的转换,文中大量转译的英语和藏文化新词汇,如恶魔舞(devil dances),黑帽舞(dance of the black),西藏蓝皮书皮纸(The Tibet blue book),皮纸(pichils),银卓卡(trangka)庄酒(chang),西藏雍(dzong)(17)藏语文化词“黑帽舞”是指恶魔舞,西藏戏剧的表演形式;“皮纸”是指既硬又粗的西藏纸;“银卓卡”指西藏货币;“庄酒”指清淡之啤酒,大麦所酿成;“雍”指堡及官吏之住地;另外,Pichils,trangka,chang,dzong均为音译词。等直接采用英语或藏文加注,不作更多解释,突出了文化差异,作为年轻编辑的高上佑用词尚算大胆新颖。
另外,同一译本不同译者,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也显示了其不同的立场。《西藏东部旅行记》中关于第一部分藏史序言之藏边各方之关系史略的翻译,有三位译者都翻译过这部分,除高上佑外其他两个背景不详,但从其翻译可以审视其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对英帝国的野心可谓见微知著(18)英国人在康定的活动显示其觊觎西藏的野心。1868年英国人首次进入打箭炉(1908年后称康定),出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阴谋1913年英帝国在康定设领事馆分馆,1922年撤馆。前两任领事Louis King(金路易),Oliver Coales(郭立实),台克满(汉名赵锡孟)为第三任,插手并干预1917年“康藏纠纷”,《西藏东部旅行记》记述了台克曼担任领事期间考察并插手康藏军事纠纷的经历。。在翻译时,一方面,译者吴墨生、朱章(后用“之通”之名)都翻译了原文第一章序,交代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历史,在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上做了改译,而译者高上佑却直接将原文第一章序言删掉。另一方面,具体翻译上也能体现,例如对该书第一章的标题翻译来看,原文“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Up to the Time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Lhasa in 1904”三位译者分别翻译为“1904年英军到拉萨以前中藏之关系”(吴墨生译),“1904年英国远征拉萨前之中藏关系”(朱章译),“1904年之中藏关系”(高上佑译),对台克满使用的“China and Tibet”并未作说明,这和当时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有莫大联系,这里暂不作讨论。单说翻译,标题中作者把军事干预和侵略说成Expedition,从英语释义上看该词条中大都和“journey”有联系,具有“考察、探险,远足”之意,而“远征”相对来说比较符合该词的意义和英国真实意图。审视各译者的翻译,只有朱章翻译到位,其他两译者要么没有翻译出来,要么直接删掉不译,其立场和态度跃然纸上难免让人猜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译者为切入点的译者行为研究并不等于不研究文本和其社会性,上文中译者对文本中语言的处理实则具有一定社会性。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具有语言和社会双重性,因此有译者主张翻译内外结合来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不断。这时期外语原著选择少,局限性大,懂外语且对康藏研究感兴趣的不多,且翻译的专业性不强,对康藏研究不深,这种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不仅影响了译述的数量和质量,还影响了译者对文本的体裁,内容,语言与风格的选择。例如上述译述源语言多为英语,偶有法语,译者正确解读原作的风格与语言定位,这是由文本的所处时代决定,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故译文体现了原文的风格,语言简单明了,用词准确,专业术语使用恰当,虽是半文半白,但可读性强,即使现在读起来也不觉晦涩。《西藏东部旅行记》多种译本,虽大都文白相伴,细读不难发现其语言略有不同,例如同一句译文,朱译“十八世纪初叶,准格尔蒙古人侵略西藏,满清皇帝派两路军队援助藏人。”吴译“十八世纪之初,准格尔犯藏,清帝派救兵两路援藏。”此两句简洁顺畅,正如巴斯内特和勒费弗尔(S. Bassnet & A. Lefevere)谈及译入语文本所实现的功能时所说“有些文本主要用于传递信息,那么这类文本的翻译应该力图传递该信息才合理。”[27]而高译“方十八世纪之始也,准格尔蒙古人(19)三位译者的译文在现在来看有些用词并不恰当、不严谨,这也同时说明了特定的译外环境对当时翻译的影响。(Dzimgarian Mongols)侵入西藏,清帝发兵二路助藏攻之。”较之前两者译文更偏文,且使用原英文注释,在其选译文本中此现象比比皆是,对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要么意译加注,要么音译加注,要么直接用英文,保留了一些异域特色,正如其编者开篇介绍其译文时这样评价道“其内容详确而精美,词句新颖而畅达”。三译文所用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阅读不是非常顺畅,但不至于佶屈聱牙,就译者当时的社会性和语言性而言,该译文确实通俗易懂,表达流畅,符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后文白参半的社会需求。另外,就读者群来说,译作受众大多是康藏研究的学者或政界要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对译入语基本要求就是语言雅致畅达,但如果对普通读者,“语欲简雅,意欲明易”的译文,其可读性会增强。
四、结语
中西方对翻译的讨论是以文本为主体,对直译与意译,忠实与通达这些二元对立命题讨论一直呈螺旋式推进。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与康藏有关的译述,总的来说,其主题明确,针对性强,语言畅达,意思清楚,译评结合,风格突出。在人们关注这一时期有关康藏研究的翻译时,注重其译文内容多于其呈现形式与翻译策略,也许有人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的译作对当下翻译似乎没有很好的参照,但在笔者看来,从译者的视域下从翻译外问题到翻译内问题重新探讨这一时期著述翻译,既有史料研究意义,也能对当下部分缺乏译者深度理解的译作有一定反思。译者是联系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重要纽带,其翻译行为受时代、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读者群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外国有关康藏问题研究著述翻译问题的讨论,客观地分析和认识译作内容和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其译文内容进行批判性认识和接受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史料价值。另外,这一时期的译者多采用译述,他们或评,或撰,或改再现了原作内容和意义以达到译者追求译文的“真”,其背后体现了译者在具体语境中对译文的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务实”,最终达到吸引读者并使其获取通达的史料信息。这种“译述”的方式对研究新的语境下的变译、创译等翻译形式仍有一定借鉴,对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译者群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