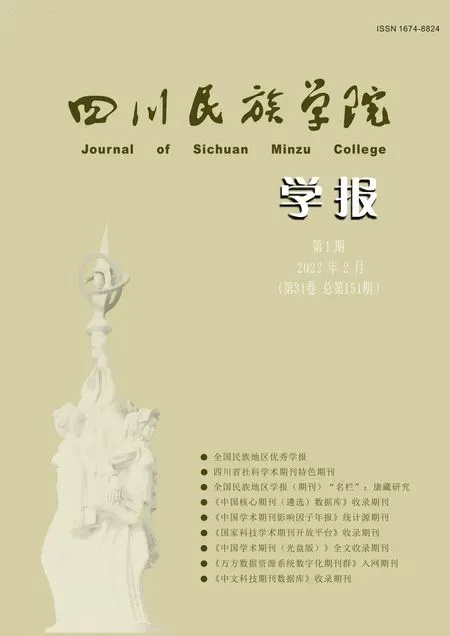成都地区五代十国音乐图像研究综述及反思
2022-03-31苏俊
苏 俊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纵观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唐末北方战乱导致经济和文化重心历史性向南转移。距离长安(今西安)数百公里外的成都以政治安定、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吸引晚唐文人雅士和乐工舞伎入蜀,促使唐风乐舞和巴蜀本土音乐文化在该时期的高度融合,成都成为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北进中原与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枢纽。此时的成都不仅保存唐代音乐文化的精髓,更为宋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成都现已发掘五代十国前蜀、后蜀大量手持乐器的陶俑、石棺刻画的乐舞图、石窟中雕刻的演奏者。因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前蜀高祖王建墓石棺上二十四张音乐图像,其他较为稀少,故本文对该区域五代十国墓葬、石窟音乐图像研究成果统一梳理并探讨。
一、音乐图像乐器考辨研究
1939 年秋,宝天铁路工程队在成都市区西门建防空洞时发现一处古墓。1941 年春,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四川大学成立四川博物馆,遗址发掘工作正式启动。1943 年 9 月,在中央研究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协助下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修筑在中室的棺床背面雕大朵莲花,其余三面均为浮雕女伎乐。其中东、西面各有十尊伎乐,正面两尊乐女和两尊舞女,每副石雕音乐图像高度约25厘米,因石雕共有乐者22人、乐器23 件、舞者2 人[1],学界也称“二十四伎乐”,现公开展示在成都市永陵博物馆内。王建墓石棺上的音乐图像研究主要集中在石棺乐器考辨:1955年,考古发掘者之一的杨有润在《王建墓石刻》中图文并茂地对石棺中每件乐器批注名称[2];1956年,杨有润参与日本召开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公布该组音乐图像照片,日本东亚音乐研究学者岸边成雄根据照片予以一一定名, 1979年,翻译《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寄王建墓管理所。1988年,樊一译《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乐妓》在国内公开发表,并认为乐器编排非常接近唐、宋宫廷燕(宴)乐乐队编制[3];1957年,本次考古发掘的主持者冯汉骥在《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指出“这部器乐浮雕属于唐代燕乐(宴乐)系统,归属龟兹乐和清乐乐器”,根据音乐史料相关论述对图像中的乐器种类及名称定名[4];1982年,俞松云《永陵乐舞石刻》认为王建墓石刻中的音乐图像描绘的是唐五代宫廷中的“燕乐”形态,也对每幅音乐图像阐述了乐器定名原由[5];1992年,李成渝《王建墓浮雕——乐器研究》首次对前面学者关于王建墓音乐图像中的乐器定名诸说整理性研究,并提出自己对乐器名称的观点[6];2012年,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依据敦煌中的伎乐图像和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冯汉骥,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前期乐器定名深度剖析,同时提出自己命名及原由[7];2019 年,永陵博物馆王建墓研究院刘仕毅《永陵棺床鼓类石刻乐器刍议》针对鼓类分歧较大的乐器命名重点阐释,并对永陵博物馆展览区乐器标注说明[8]。从上可见,王建墓从挖掘者、音乐学者、考古专家、博物馆研究者等相继对石棺上音乐图像乐器种类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均未达成共识,主要分歧代表如下(见表1)。

表1 王建墓石棺音乐图像乐器分歧代表性观点
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对成都市彭山观音乡后蜀宋琳墓进行挖掘。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任锡光为代表的考古队发布《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其中提及棺座正前方有三个乐舞伎[9],暂无该音乐图像的研究成果;2011 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对成都市东门十陵镇五代十国后蜀宋王赵廷隐墓进行挖掘,考古报告没对外公布。后续彩绘乐俑研究成果闫佳楠在《赵廷隐墓出土乐舞伎俑音乐文化研究》一文从乐器命名、舞蹈种类等方面详细介绍出土乐俑分男女乐俑,男乐俑 2 件,女乐俑 20 件,其中一女乐俑的乐器遗失无考,男乐俑所奏乐器皆为笛。女乐俑所奏乐器有方响 1 件、排箫 2 件、笙2 件、笛 2 件、筚篥2 件、四弦曲项琵琶 1 件、拍板 1 件、都昙鼓 2 件、正鼓 2 件、答腊鼓 1 件、鸡娄鼓并鞉牢鼓 1 件、细腰鼓 1 件、大鼓 1 件,共计 22 件、14 类乐器。[10]该文的乐器命名和数量与成都博物馆展览厅的赵廷隐彩陶伎乐俑批注有少量出入,因考古报告没有公布,无法考证;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乐至县文物管理所发布《四川乐至县报国寺摩崖造像踏查记 》考古报告图文并茂描述该摩崖石刻一共8窟,其中有2个石窟有丰富的音乐图像,对窟1的十二种乐器做了详细的说明,窟5仅手绘图阐释第二层左右各五名伎乐,其下有两名乐者、顶部有多个乐器,[11]并没有文字性说明该石窟不同区域乐器的具体名称及数量;2019年,林戈尔在《 当代古蜀乐乐队建制构想》以乐至县报国寺石窟乐俑为历史来源点构想建立古蜀乐乐队数据库[12],但该研究中的十七件乐器数量与考古报告并不一致。
二、承唐启宋音乐历史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成都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艺术氛围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入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五代成都艺术文化圈,为中古歌舞伎乐向近古戏曲音乐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1984年,何昌林《唐五代西川音乐之一瞥》列举唐五代时期四川的各种音乐形式,说明当时四川音乐的繁荣景象源于盛唐遗风[13];1986年,杨伟立、胡文《前后蜀宫廷中的音乐歌舞初探》对前后蜀教坊机构、歌舞种类进行研究,粗略地勾画了前后蜀宫廷音乐歌舞的基本轮廓[14];1988年,秦方瑜在《五代南方艺苑的奇葩——王建墓石刻伎乐与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王建墓和《韩熙载夜宴图》中石雕乐舞的音乐历史价值和美术史意义分别予以阐述[15];1992年,赵为民在《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从《宋史》关于教坊记载中乐工来源和数量阐述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在音乐上对宋教坊的重要影响[16];1994年,秦方瑜、朱舟在《试论王建墓乐舞石刻的艺术史价值》一文中从王建墓石刻史阐述唐代乐舞的流布轨迹和艺术史学价值[17];2009年,包德述在《唐五代时期南北朝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在成都的传播与交融》中以《南诏奉圣乐》在成都完成过程史料记录与王建墓乐舞石刻遗物来说明成都在五代十国时期担负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重要枢纽作用[18];2010年,罗天全《前后蜀是唐宋音乐传承的纽带》从宋初教坊乐工来源考、宋初教坊体制来源考、蜀派教坊乐工技艺记载说明该时期宫廷音乐编制和乐工在宋初宫廷传承中的重要作用[19];2014年,谢艾伶在《后唐宫廷音乐兴衰之缘由考》一文中过,以盛唐遗风和民族风俗文化两个方面阐述五代十国时期成都音乐的风格特征来源和现存遗物的历史价值[20],该类研究主要通过考古中出土的音乐图像佐证和丰富史料记载。
还有少量关于舞蹈名称研究,如秦方瑜先后在《王建墓石刻伎乐与霓裳羽衣舞》,《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认为王建墓中的其中两舞伎所跳正是唐代流行的霓裳羽衣舞,乐队反映了唐代宫廷坐部伎演奏燕(宴)乐的风貌和编配形式[21-22];2017年,闫琰《后蜀赵廷隐墓出土花冠舞俑与柘枝舞》一文阐述其中舞伎的姿势是唐五代时期最流行的柘枝舞,柘枝舞与胡旋舞、胡腾舞并称为“西域三大乐舞”,后蜀乐舞形式与唐代宫廷配置形式一脉相承[23]。该类研究主要是图像学常用的“看图说话”,通过外在舞蹈姿态和装扮对该时期乐舞形态的初步猜测。
综上所述,成都地区已出土的五代十国前蜀高祖王建墓、后蜀宋琳墓、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及后蜀乐至县报国寺石窟均有较丰富音乐图像。不同学科专家从不同视角对音乐图像进行研究,极大的推动了成都地区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研究价值。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单一考古地址中音乐图像的个案性研究,并无对该区域音乐图像整体性研究。研究方向集中在音乐图像乐器考辨和音乐史学价值研究两大板块。如:五代十国前蜀高祖王建墓石棺音乐图像中的乐器命名占据了10篇论文/专著,多运用目前世界通用演奏性功能乐器分类法命名,其中分歧最集中在鼓类乐器,表1已列出具有代表性争议观点。其次研究数量较多的是从出土相关音乐图像结合史书记载阐释唐五代时期成都在承唐启宋的历史地位和音乐史学价值,该类研究多运用考古学中常用的“二重证据法”,即史料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互相佐证;后蜀宋王赵廷隐墓没有公开考古报告, 三篇论文分别从乐器命名、舞伎的舞种和衣着头冠与道教文化交融上猜测,其中《赵廷隐墓出土乐舞伎俑音乐文化研究》该文的乐器命名和数量与成都博物馆展览厅的赵廷隐彩陶伎乐俑批注有少量出入,因考古报告没有公布,无从考证;后蜀乐至县报国寺石窟的音乐图像研究仅考古报告,一篇古蜀乐乐队建设构想的论文提及该石窟伎乐,但乐器种类和数量同样没有达成共识。总之,成都区域王建墓、赵廷隐墓及报国寺石窟研究成果争议问题都涉及音乐图像的乐器考辨。
三、研究反思
笔者认为,研究结果没有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参与发掘的一线考古工作者、文物管理人员及少量艺术学研究者仅对单个墓葬中的陶俑、石砖浮雕、地面遗存石窟雕塑乐器命名或分类等个案性研究,缺乏对该区域音乐图像整体性研究。例如:从王建墓浮雕中争议最大的鼓类来看,墓室石棺雕刻中的“鼓”不仅是对当时某种音乐场景的模仿,也是一种美术创作加工后的“鼓”,更是丧葬仪式中墓室文化的“鼓”。王建墓25厘米高的石棺浮雕作品中的“鼓”从形态上已经与实物有了新的创新,音乐图像呈现的形态和现实中的乐器必然存在一定差异,仅个案性研究是不能满足音乐图像发生规律,唯以区域性音乐历史研究为中心,建设五代十国考古发掘和地面遗存的音乐图像数据库为基石方可缓解研究过程中的这些争议问题。通过选择一定区域相关的事物的共性,获得普遍性历史发展规律,并把有着相似形态特征的音乐图像组合在一个音乐文化时空之中,最终找出成都地区在唐宋衔接关键时期音乐文化变迁和发展动力中的本体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变异动态走势图。从整体的数据库走向个案性多学科研究,并以科学怀疑精神图文互佐,弱化音乐图像研究中的二度创作带来的考辨问题。这也是本文以成都地区五代十国音乐图像研究整体综述的出发点。比如:王建墓音乐图像中的十五种乐器与唐代史书记载龟兹乐比较,没有五弦、侯提鼓、檐鼓,但又新增加了羯鼓、鞍牢鼓、拍板、叶等新的乐器种类,这到底是唐乐在五代十国时期成都地区新发展还是美术工匠笔下的偶然事件。又如:王建墓石棺上的箫显示十管,唐史书记载多是十六管或二十三管[24]。王建墓中的箫到底是汉代十管箫在成都区域的乐器形态遗存,还是工匠在尺寸限制下美术作品的二度创作?音乐图像个案研究还不足以真实反映音乐景象,唯独建立区域性数据资料库方可弱化工匠二度创造性,最终为研究唐宋时期音乐的承传转变及五代十国社会生活、丧葬礼仪、文化思想等提供更为准确的参照依据。
纵观西方图像学研究发展史,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美国德裔犹太学者,著名艺术史家。在图像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影响广泛。其中《图像学研究》(1939)和《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它们对图像学这一艺术史领域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是较早探讨美术作品中的图像,他把音乐图像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依照常识辨认音乐场景中的对象和基本形态;第二层是参考史料记载发现与音乐形象相关的文化或习俗含义;第三层是通过视觉中的图像去研究形成这种音乐图像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个体心理特征,最终探索音乐图像背后的深层意义。罗斯基尔(2)罗斯基尔: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男,1903年生于俄国,抽象派画家,抽象派运动早期领袖之一。在著作《图画的阐释》中也指出音乐图像的阐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图说”;第二个层次是“诠释”;第三个层次是“估测”。按照以上图像学经典理论来看,目前针对成都地区五代十国王建墓或赵廷隐墓中的音乐图像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第一层“图说”,即依照常识辨认音乐场景中的对象并进行分类。对音乐图像中乐器名称的考辨、舞蹈名称猜测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作者认为,中国的音乐图像是古代雕塑家或者美术家通过作品创作让音乐景象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体现的是文化中的音乐,此刻的音乐景象主旨是丧葬文化、礼乐文化、民俗文化等直接表现手段,不同于影像资料记录音乐表演场景或者拍摄具有演奏功能的乐器。中国的音乐图像从诞生之初就以音乐景象展现音乐文化为目的,反映该区域生命形态的精神面貌,展现历史中区域文化的基本社会特征。从古文献所载“河图”“洛书”(3)“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洛书”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收录于《尚书》,其次在《易传》以及诸子百家亦有收录。到战国“按其图以想其生”(4)出自《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 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乃至宋代形成并传承至今的“金石学”(5)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中国音乐图像自古都展示的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综合体,体现区域群体共同认知、审美和哲学思想,与西方美术作品中的图像学研究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起源和社会结构,这恰是中国音乐图像研究价值所在和特殊性质。由此可见,中国音乐图像研究不仅需要从区域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弱化美术工匠者的二度创作,更要打破西方图像学常规研究中的三层次顺序关系,从中国历史文化出发,多学科、多视角中准确解读音乐图像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建立符合中国气派的音乐图像学研究体系和方法。
四、结语
成都区域相继出土的五代十国音乐图像在音乐史上的意义及其对宋文化的影响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942年,成都市一环路出土的前蜀皇帝王建陵墓石棺上二十四幅音乐图像完美地呈现出前蜀宫廷乐舞的盛大规模及壮阔场景;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对成都市彭山城北观音乡后蜀宋琳墓进行发掘,棺座正前方有三副石刻乐舞图;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发现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共计二十余件彩绘乐俑;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乐至县文物管理所对四川乐至县报国寺摩崖造像公开发布考古报告,其中2窟有大量音乐图像遗存。成都地区不断涌现的五代十国考古成果让我们更加清楚意识到该区域音乐文化历史价值,但大多墓葬和石窟中的音乐图像“后发掘”并不充分,研究成果较少,这无疑是对整个五代十国音乐文化研究的重大缺憾。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文,对如何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做了重要指示: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25]。本文意在梳理成都地区五代十国音乐图像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前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相信通过诸多学者不断努力,必将有更加完善的中国气派音乐考古图像研究体系和更丰富的图像研究成果诞生,在传承、保护与创新音乐图像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基础上找到文化研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