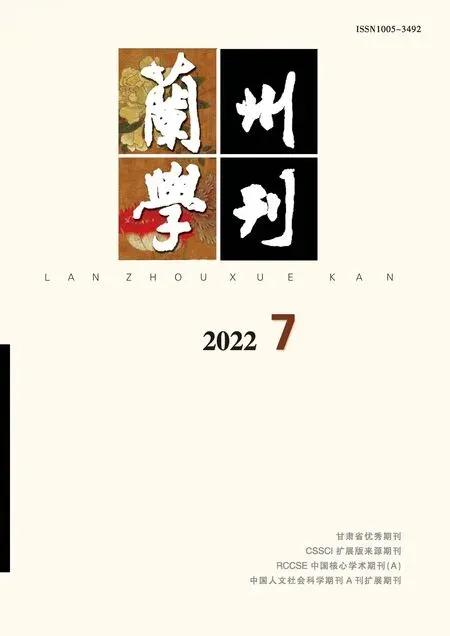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文化功能与诗体建构
2022-02-03吴大顺
吴大顺
宫廷仪式乐歌,指朝廷各种仪式活动中产生的礼乐歌辞。宫廷最重要的仪式有祭祀天地山川诸神的郊祀仪式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仪式歌辞;其次是朝廷重大的节庆仪式,如元会等节庆中天子燕飨诸侯及群臣的仪式;再者如出兵征战、庆功封赏仪式等。这些仪式都要用乐,相应地则有音乐歌辞,如郊庙歌辞、宗庙歌辞、燕射歌辞(1)沈约:《宋书·乐志》载:汉章帝元和二年,“食举乐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8-539页。、军乐歌辞,以及用于这些仪式的雅舞歌辞等。本文重点探讨西汉郊庙乐歌《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的体式生成与建构问题。
一、汉武帝立乐府、定郊祀与汉代仪式乐歌的文化功能
(一)汉武帝立乐府与重定郊祀之礼
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活动是其“修郊祀”等礼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概括来说,汉武帝在礼乐文化建构方面重点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重定郊祀之礼。西汉之初,刘邦“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2)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030页、第1043页。开始了汉代的礼乐建设活动。在制定郊祀礼乐方面,汉高祖刘邦也多有建树,秦代帝王一般郊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刘邦增立了“黑帝祠,名曰北畤”(3)。汉文帝十五年夏四月,“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第二年又“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4)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8页、第1382页。。汉武帝重定郊祀之礼是汉代礼乐文化建构中的一件大事。
《汉书·武帝纪》对“祠太一于甘泉”之事载录曰: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诏曰:“朕以眇身讬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脽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陲,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禅。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5)班固:《汉书·武帝纪》,第185页。
《汉书·礼乐志》记载曰: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6)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45页。
汉武帝重定郊祀之礼中,新增了“泰一”神,并将之置于其他众神之首,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要通过提高“太一”神在国家祭祀中的核心地位,以确立汉王朝大一统的地位和尊严。(7)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8-74页。班固《武帝纪》《礼乐志》重点记载了元鼎五年武帝“立泰畤于甘泉”“祠太一于甘泉”的事件,标志着元鼎五年汉武帝重定郊祀之礼的完成和此事的重大意义。
二是扩大乐府的功能。“乐府”作为朝廷的音乐机关,本始于秦代,(8)乐府始于秦代的最重要证据是刻有“乐府”二字的秦代错金甬钟的考古发现。寇效信:《秦汉乐府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班固《汉书·礼乐志》载,至汉武帝“乃立乐府”,主要指“扩充”汉乐府的规模和职能。(9)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第69页。武帝时期的音乐机构有太乐和乐府两个部门。传统的宗庙祭祀雅乐主要由太乐掌管,但是当时雅乐已残败不堪,“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10)。武帝时期,诸如定郊祀祭礼、采集地方歌谣、召集文人写作歌辞、为歌辞配乐等重大的礼乐活动,都是依托乐府机关进行的,乐府机关的规模和职能因此得到极大拓展,不仅掌管《安世房中乐》《郊祀乐》等宫廷和郊祭礼乐,还负责采集和整理各地的娱乐音乐。扩大乐府是汉武帝礼乐文化建构的需要,即需要从朝廷立场出发,通过礼乐文化构建一套体现儒家精神的政治伦理话语。
郊祀之乐重在祭神娱神,通过对天神和四方之神的膜拜,宣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权威性,宗庙之乐重在宣言祖先之“功德”,以达到“上下齐同”而“壹于正”的目的。而其他各种礼俗活动之用“乐”,如“朝聘”“燕享”之乐,均能达到“教化黎庶”之作用。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应该具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通过采集赵代秦楚之风,作为祭祀乐歌的素材。所以《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1)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43页、第1045页。。其立乐府,采诗夜诵与李延年作十九章之歌放在一起叙述,足见乐府“采诗夜诵”之用意。二是通过“立乐府采歌谣”达到音乐的移风易俗目的。(12)关于汉武帝“定郊祀”“立乐府”的礼乐文化建构活动,又见拙文《论汉武帝礼乐文化建构与汉代乐府学的价值取向》,《乐府学》2018年第1期。汉代的仪式乐歌是汉武帝礼乐文化活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仪式功能。
(二)祭神颂瑞之歌:汉代《郊祀歌》的仪式功能
汉代的《郊祀歌》是祭祀、颂瑞歌辞,其功能依次为:《练时日》迎神曲,《帝临》祀中央黄帝之曲,《青阳》祀东方春季青帝之曲,《朱明》祀南方夏季赤帝之曲,《西颢》祀西方秋季白帝之曲,《玄冥》祀北方冬季玄帝之曲,《惟泰元》祀太一之神,《天地》祀天地之神,《日出入》祀太阳之神,《后皇》祀后土,《华烨烨》祀后土毕济黄河作之曲,《五神》云阳始郊见太一所作之曲,《赤蛟》送神之曲,以上为山川诸神的祭歌。其他如《天马》颂得天马,《景星》颂得宝鼎,《齐房》颂产灵芝,《朝陇首》颂获白麟,《象载瑜》颂获赤雁,《天门》武帝祷颂天神祈得长生作,以上诸曲是歌颂祥瑞的乐歌。(13)张永鑫:《汉乐府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相较之下,叙写祖先功业的内容很少。正如《宋书·乐志》所言:“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14)这种状况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活动有很大关系。通检汉武帝时期的郊祀活动,几乎没有见到祖先配飨天地、山川诸神的情况。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南郊天地之神时,才出现以太祖高皇帝配天、高皇后配地而祭的情况。东汉建武帝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15)沈约:《宋书·乐志》,第550页、第538页。汉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16)范晔:《后汉书·祭祀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1页。明堂祭祀天地之神是东汉以后才恢复的。
(三)祭祖颂功之歌:汉代《安世房中歌》的仪式功能
汉代的宗庙乐,《汉书·礼乐志》等文献多有记载。如《汉书·礼乐志》载: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17)
惜其众乐歌辞现已不存,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仅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存于班固的《汉书·礼乐志》,但关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作者及音乐性质,学术界存在分歧。
《汉书·礼乐志》有关《房中乐》记载曰: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18)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43页。
从这条材料我们可以得知三方面信息:一是汉“房中乐”与周“房中乐”、秦“寿人”乐有密切联系;二是“房中祠乐”是汉代宗庙乐一部分,作者是高祖唐山夫人,用楚声演唱;三是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更名“安世乐”,备其箫管。
对于《汉书·礼乐志》涉及的三个问题,近年,钱志熙、王福利等学者结合《仪礼》《周礼》和《毛诗传》等相关文献进行了较深入考证。钱志熙据《仪礼·燕礼》《诗经·毛传》等汉前文献关于周“房中之乐”“国君有房中之乐”的记载,认为周代确实存在“房中乐”。又通过对郑玄《仪礼·燕礼》《周礼·春官·磬师》《毛诗谱》等注中有关“房中之乐”文献的梳理考证,认为周“房中乐”为国君夫人燕娱之乐,其中也有房中祭祀之乐。“房中”之义兼有后妃夫人之“房中”与“祖庙”祠堂“房中”两义。周代的“房中乐”是对路寝、后妃房中、祭祀房中之作乐的通称。
汉代唐山夫人以后宫材人身份作《房中祠乐》,是以周房中乐上述意思为依据的,唐山夫人以“房中乐”为其所作歌诗的专名后,房中乐便由周代各类房中乐俗称,成为唐山夫人《房中祠乐》的专称。文章对周“房中乐”的燕乐和祭祀两重性质和功能及唐山夫人《房中祠乐》的得名依据的论证堪称灼见。(19)钱志熙:《周汉“房中乐”考论》曾发表于《文史》2007年第二辑,收入其《汉魏乐府艺术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王福利则认为,唐山夫人《房中祠乐》是在说明汉之能够有天下、备宫悬并具万世鸿业的真正原因,是在祈求所得后向神明的“报福”“还愿”,并在还愿的过程中,面向神灵歌颂当今主上的丰功伟业,以对后继者的宣导昭示之意。(20)王福利:《论汉代的“房中乐”“房中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萧涤非根据歌辞文本,认为《安世房中歌》“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2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沈德潜认为:“《房中歌》近雅,古奥中带和平之音……首言‘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22)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4页。据首章如“高张四悬,乐充宫廷”,次章如“神来宴娱,庶几是听”,第三章如“乃立祖庙,敬明尊亲”等诗句,可以推测这些歌辞当是宗庙祭祀的内容。
《汉书·礼乐志》殿本《考证》齐召南云:汉《安世房中歌》,直是祀神之乐,故曹魏初改名《正始之乐》。后因缪袭言,又改名《享神歌》也。丘琼荪曰:“齐召南云《安世房中歌》直祀神之乐,其言良是。诗中多称孝述德,歌功颂烈,敬祖荐神之语,绝无人伦夫妇、《关雎》后妃之说。”(23)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5页。
一般认为唐山夫人《房中祠乐》作于汉高祖五年。(24)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8页。叔孙通所制宗庙乐也大致在高祖五年至七年间,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载,高祖五年,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汉代的元会朝贺礼仪。高祖七年,长乐宫修建完成时,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元会朝贺礼仪开始使用。其仪如次: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汉高祖经历了这番仪式后,感慨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3页。因此,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常,主持初汉礼乐之事。
叔制宗庙之仪已见上文《汉书·礼乐志》。问题是叔的宗庙仪式中,演奏的是《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五首歌乐,而不见《房中祠乐》。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二十八家歌诗中有“宗庙歌诗五篇”,陆侃如先生以为这五篇歌诗就是自《嘉至》至《永安》的五篇《宗庙乐》歌诗。(26)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9页。虽然这种结论是一种直觉判断,没有充分的证据,但至少说明《房中祠乐》与汉初叔制之《宗庙乐》关系不大。
《汉书·礼乐志》载:“高庙奏《舞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27)班固:《汉书》,第1044页。在西汉高祖、孝文、孝武庙乐中不见有《房中祠乐》存在。那么,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到底在什么场合表演呢?郑樵《通志》曰:“房中乐者,妇人祷祠于房中也,故宫中用之。”(28)郑樵:《通志·乐一》,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年影印万有文库本,第一册,第635页上。陈本礼《汉诗统笺》云:“诗名《房中》,当是宫中之庙,非祫祭大享之太庙也。”(29)陈本礼:《汉诗通笺》,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03页。
周代“房中乐”也有用于宫中祭祀的。如《采蘩》,《左传·隐公三年》载:“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3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7-28页。《毛传》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31)又《采苹》,毛传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32)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284页、第286页。可见,汉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早期当也是宫中祭祀之用的。西汉初、中期,皇帝的宗庙大致有京庙、陵庙、郡国庙三种类型,宗庙数总计约一百七十六所,远远超过了天子七庙的古礼规定。如汉高帝十年(前197),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去世,“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33)班固:《汉书·高帝纪下》,第68页。惠帝“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34)景帝谥文帝庙号为太宗,“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35)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392页、第436页。
又《汉书·韦贤传》载:“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36)汉代宗庙情况非常混乱,不能排除宫中庙祭的可能。《汉书·礼乐志》关于高祖沛宫原庙的祭祀就是一个旁证。《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37)班固:《汉书》,第3115页、第1045页。这当是郡国庙祭。又《后汉书·桓帝纪》载:“坏郡国诸房祀。”注曰:“房谓祠堂也。”并引《王涣传》曰:“时唯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令王涣祠。”(38)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页。可见,郡国庙也称为“房”。
到汉元帝下诏罢郡国庙,“因罢昭灵后、武哀后、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39)班固:《汉书》,第3117页。建立“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的宗庙祭祀制度,作出“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40)班固:《汉书·韦贤传》,第3120页。的决定,基本完成汉代宗庙祭祀的“七庙”制度。(41)郭善兵:《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汉书·礼乐志》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42)班固:《汉书》,第1043页。可见,汉《房中乐》不在叔孙通作为太常管辖的太乐中,而是在乐府中,乐府所管多为燕乐俗曲,这与汉《房中乐》的楚声音乐性质相符。班固《汉书·礼乐志》收录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未署名唐山夫人。歌辞“多称孝述德,歌功颂烈,敬祖荐神之语”,其文辞“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与楚声多口语虚词的语言习惯不同,其语言结构与汉武帝时代的《郊祀歌》非常相近。又郭茂倩《乐府诗集》“郊庙歌辞”解题曰:“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43)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陈旸《乐书》曰:“汉高帝时,叔孙通制宗庙礼,有《房中祠乐》,其声则楚也。孝惠更名为《安世》,文、景之朝无所增损。至武帝定郊祀礼,令司马相如等造为《安世曲》,合八音之调,《安世房中歌》有十七章存焉。”(44)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第745页。
由上举文献可见,《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当不是唐山夫人《房中祠乐》的始辞,而是汉武帝定郊庙时的新作。正如逯钦立所言:“《汉书》仅谓唐山夫人作乐,乐与辞非一事。此质之汉志可知,似不得即署唐山夫人。”(4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7页。
下面从歌辞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安世房中歌》第五章曰:“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颜师古注曰:“谓匈奴。”(46)翻检《汉书·高帝纪》,仅一次出与匈奴作战的记载,其起因是韩信降匈奴。文帝、景帝时期匈奴寇边的记载逐渐增多,记载最多的是汉武帝时期。因此,歌辞“海内有奸,纷乱东北”当不是指高祖时期,这样看来,歌辞为高祖姬唐山夫人所作的可能性不大。第十一章曰:“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晋灼注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广远安固也。”(47)班固:《汉书》,第1047页、第1050页。
综上可见,汉代的“房中乐”是唐山夫人沿袭周“房中乐”后妃夫人女乐,身兼宾燕、祭祀性质的一种乐歌。汉代早期的《房中乐》当以燕娱为主,隶属乐府机关,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对之进行加工,增加了箫管乐器,并改名为《安世乐》。汉武帝定郊庙礼乐时将之纳入国家宗庙音乐,并创作了《安世歌》十七章歌诗,配合宗庙祭祀演奏。班固《汉书·礼乐志》结合前后二名,称之为《安世房中歌》。如萧涤非所言:“班固以《安世》既出自《房中》故录此歌时,乃合前后二名题曰《安世房中歌》。此《房中歌》以楚声而用周名及其更名之故也。”(48)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武帝以后,《安世房中歌》在宗庙祭祀和朝贺燕享中兼用。如汉哀帝罢乐府前,包括《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在内的一百二十八鼓员,“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49)
二、汉代宫廷仪式乐歌的诗体形式
现存的汉代宫廷仪式歌辞有《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鼓吹铙歌》十八曲等。在此主要讨论《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的体式结构。
(一)汉《郊祀歌》十九章的体式
《郊祀歌》十九章,多撰制于武帝时代。《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0)班固:《汉书》,第1073页、第1045页。“十九章”之歌,实为二十首,其中《天马》一题二首,多是祭祀、颂瑞歌辞,作者涉及汉武帝、司马相如、邹子等数十人。现对每章的句式及篇章结构描述如下:
《练时日》:“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48句。
《帝临》:“4,4”四言结构,齐言,凡12句。
《青阳》:“4,4”四言结构,齐言,凡12句。
《朱明》:“4,4”四言结构,齐言,凡12句。
《西颢》:“4,4”四言结构,齐言,凡12句。
《玄冥》:“4,4”四言结构,齐言,凡12句。
《惟泰元》:“4,4”四言结构,齐言,凡24句。
《天地》:“4,4”结构8句,“7,7”结构4句,“4,4”结构4句,“7,3,3”结构3句,“7,7”结构8句,凡27句。
《日出入》:“5,6。5,4,4,4。6,6。4,4,4,4。7”杂言结构,凡13句。
《天马》其一:“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12句。
《天马》其二:“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24句。
《天门》:“3,3,3,3”三言结构8句,接“4,4,6,6。3,3,3,3。5,5。6,6。5,5。6,6”杂言结构16句,结尾“7,7”结构8句,凡32句。
《景星》:“4,4,4,4”四言结构12句,接“7,7”七言结构12句,凡24句。
《齐房》:“4,4,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后皇》:“4,4,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华烨烨》:“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38句。
《五神》:“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20句。
《朝陇首》:“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20句。
《象载瑜》:“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12句。
《赤蛟》:“3,3,3,3”三言结构,齐言,凡28句。
汉《郊祀歌》中,“3,3,3,3”的齐言结构,有《练时日》《天马二首》《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8首;“4,4,4,4”的齐言结构,有《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齐房》《后皇》8首;《天地》《日出入》《天门》《景星》4首属于杂言结构。其中,《天地》《景星》2首由四言和七言结构组成;《天门》以三言结构为主,间杂四言、六言和五言;《日出入》以四言为主,间杂六言、七言和五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结构的句子在汉《郊祀歌》中仅有6句。
(二)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的体式
汉代宗庙歌辞仅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存于班固《汉书》中。《汉书·礼乐志》载:“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51)班固:《汉书》,第1043页。“房中”兼有后妃夫人之“房中”与“祖庙”祠堂“房中”两义。周代的“房中乐”是对路寝、后妃房中、祭祀房中之作乐的通称,唐山夫人以“房中乐”为其所作歌诗的专名后,房中乐便由周代各类房中乐俗称,成为唐山夫人《房中祠乐》的专称。(52)钱志熙:《周汉“房中乐”考论》,《文史》2007年,第二辑。班固《汉书·礼乐志》收录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未署名唐山夫人。歌辞“多称孝述德,歌功颂烈,敬祖荐神之语”,其文辞“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与楚声多口语虚词的语言习惯也不类,而与汉武帝时代的《郊祀歌》非常相近,当是汉武帝定郊庙时的新辞。
《大孝》:“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七始》:“4,4”四言结构,齐言,凡10句。
《我定》:“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王侯》:“4,4,4。4,4。4,4”四言结构,齐言,凡7句。
《海内》:“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大海》:“7,7。3,3。3,3”杂言,凡6句。
《安其所》:“3,3”三言结构,齐言,凡8句。
《丰草葽》:“3,3”三言结构,齐言,凡8句。
《雷震震》:“3,3”三言结构,齐言,凡10句。
《桂华》:“4,4”四言结构,齐言,凡10句。
《美若》:“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硙硙》:“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嘉荐》:“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皇皇》:“4,4”四言结构,凡6句。
《浚则》:“4,4”四言结构,齐言,凡4句。
《孔容》:“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承帝》:“4,4”四言结构,齐言,凡8句。
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4,4”齐言结构占多数,有《大孝》《七始》《我定》《王侯》《海内》《桂华》《美若》《磑磑》《嘉荐》《皇皇》《浚则》《孔容》《承帝》13首;“3,3”齐言结构有《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3首;杂言结构仅《大海》1首。《安世房中歌》无五言句。
三、汉代宫廷仪式歌诗的体式渊源与生成方式
汉代《郊祀歌》祭神颂瑞、《安世房中歌》祭祖颂功的仪式功能,决定了其内容的庄重严肃性。这种庄重严肃的内容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歌辞的体式选择。汉代宫廷仪式歌辞以四言为主的体式结构,其实是对《诗经》体式的继承和延续。《诗经》“颂”类诗歌“祭祖颂功”的功能及其仪式咏诵活动,对《诗经》四言体完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汉代宫廷仪式歌辞在继承《诗经》传统中选择四言体,就不难理解了。汉代宫廷仪式歌辞“三言”体式的生成机制则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现存汉代宫廷仪式歌辞《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中,除四言体外,还存在大量“3,3”结构的三言体。究其渊源,主要来自楚辞,当是省略楚辞体“3+兮+3,3+兮+3”句式的句腰虚词“兮”而形成的。
明郝敬《艺圃伧谈》曰:“汉《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辞》‘九歌’而变其体。”(53)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898页。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曰:“汉《郊祀词》幽音峻旨,典奥绝伦,体裁实本《离骚》。”(5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52页。
关于汉《郊祀歌》的生成方式,《汉书·礼乐志》有一段文字记载可值注意: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5)班固:《汉书》,第1045页。
这里提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可见“十九章之歌”是李延年在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诗赋”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史记·乐书》载: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聘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56)司马迁:《史记》,第1178页。
《汉书·艺文志》载,《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皆为“邹子乐”,其句式为四言结构;而《天马》二首为“三言”结构,此录如下:
太一況,天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權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57)《汉书·礼乐志》载,歌辞后有“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的备注。班固:《汉书》,第1060-1061页。
两相比较发现,《史记·乐书》的《天马歌》是“3+兮+3,3+兮+3”的骚体结构,《汉书·礼乐志》的《天马歌》是“3,3,3,3”的“三言体”结构。其次,歌辞内容及语词上也有不少变化,《史记》两首《天马歌》的歌辞均只有四句,而《汉书》的歌辞篇幅要长得多,《汉书》中的歌辞语词也比《史记》更显典雅。
关于歌辞的篇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史记·乐书》不是以载录歌辞为主,而是在叙述《天马歌》来历时“略举”了汉武帝原初歌辞的部分内容,并非“全篇”。(58)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歌辞略举之,非全篇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8页(上)。《汉书·礼乐志》著录的当是汉代《郊祀歌》仪式唱诵歌辞,所以内容完整,语词典雅庄重。至于骚体变成“三言”体,是乐工配乐时的加工,还是班固《汉书·礼乐志》载录歌辞时的省略,则不得而知了。但《史记·乐书》有载,汲黯向武帝进言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59)司马迁:《史记》,第1178页。《汉书·礼乐志》也有载,“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韵,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60)班固:《汉书》,第1070-1071页。。
又,汉武帝乐楚声,所作《瓠子歌》《秋风辞》与《天马歌》均为楚歌,其体式结构以“3+兮+3,3+兮+3”为主,西汉其他帝王、王子所作杂歌,也主要是楚歌体,其句式也以“3+兮+3,3+兮+3”结构为主。看来,汉《郊庙歌》的仪式唱诵辞,应较多地保留了在西汉王宫和上层社会流行的楚歌体式。(61)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楚歌体《灵芝歌》一首,署名《汉郊祀歌》,见《乐府诗集》,第9页。徐坚《初学记》题班固《汉颂论功歌》,见《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7页。当是班固《汉颂》之“系歌”,颂美元封二年甘泉宫生九茎连叶灵芝的祥瑞事件,后来是否被收入《郊祀歌》不得而知,郭茂倩署名《汉郊祀歌》不知何据。
现存汉《郊祀歌》的“三言体”结构,是对楚歌体句腰“兮”字的省略,当是可信的。班固《汉书》中,省略楚歌体“兮”字的情况还有多处,如贾谊《鵩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著录的文本句末有“兮”字,而《汉书·贾谊传》句末“兮”字全被省略了。值得注意的还有贾谊《吊屈原赋》文本的“兮”字,在《史记》和《汉书》中的区别。总体看,《汉书·贾谊传》是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改定而成的,《吊屈原赋》的“兮”字在二传中均有保留,但仔细比对发现,《汉书·贾谊传》很多句中的“兮”字与《史记》的位置有了变化,如: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鲈,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62)司马迁:《史记》,第2493页。
《汉书·贾谊传》: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馿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屦,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63)班固:《汉书》,第2223页。
通过比较发现,《史记》的“兮”字多用在句腰,而《汉书》将句腰的“兮”字放在了句尾。《汉书》中还有个别句子直接将句腰的“兮”字省略,如《吊屈原赋》“独堙郁兮其谁语?”(《史记》)“子独堙郁其谁语?”(《汉书》)又如司马相如《长杨赋》:“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谺。”“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64)司马迁:《史记》,第3055页。“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操行之不得,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65)班固:《汉书》,第2591页。第一句中,《汉书》将第二分句的“兮”改成了“乎”;第二句中,《汉书》直接省掉了第一分句末的“兮”字。此类情形,还有如汉武帝《瓠子歌》:“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66)司马迁:《史记》,第1413页。“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洋洋,虑殚为河!”(67)班固:《汉书》,第1682页。《汉书》直接将第二分句句腰的“兮”省略了。
可见,《汉书》对楚辞体句式“兮”,特别是句腰“兮”字是有意识的一种省略,班固在《汉书》中习惯于将句腰的“兮”字用“逗点”替代。“3+兮+3,3+兮+3”结构的楚歌体,一旦句腰的“兮”省略,便成了“3,3,3,3”结构的“三言”体式。省略楚歌体“兮”字成汉《郊祀歌》“三言”体的行为,是李延年等宫廷乐工所为,还是班固所为,抑或是在歌辞文本传抄中形成的呢?因文献失传,已无从得知了。
综合来看,应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而不是班固的个人喜好所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时,是在广求“遗书于天下”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七略》是刘歆“总群书”而成的目录提要。也就是说,《汉书·艺文志》所录书籍及篇目是刘向、刘歆目睹其书而成的,有文本依据。那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的包括《宗庙歌诗》五篇在内的三百一十四篇歌诗都是有文本依据的,《贾谊赋》七篇也是有文本依据的。这些文本具体样态不得而知,但班固写《贾谊传》时应该是能见到的,《汉书》中贾谊“赋作”与《史记》中的文本区别,特别是《鵩鸟赋》的“兮”字全部省略,当不是班固所为,而是另有省略“兮”字的文本。说明楚歌一旦离开口语和歌唱环境,其文本中的“兮”字已经没有音乐上的意义,仅仅起到停顿的作用,在文本传播中成为可有可无的存在,于是在辗转传抄中,便逐渐被省略了。
此外,《郊祀歌》十九章中的五言句有:“日出入安穷”(《日出入》),“故春非我春”(《日出入》),“幡比翄回集,贰双飞常羊”(《天门》),“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天门》)等6句。这些诗句的句式结构均为“1+2+2”结构,若二分则为“3+2”结构,与相和歌辞“2+3”结构的五言句式有明显差别。从这些诗句在诗歌句群中的位置更能清楚其结构特点,如“故春非我春”(《日出入》)的“故”字,是领起“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四句的。“幡比翄回集,贰双飞常羊”(《天门》),王先谦以为“翄”“飞”下皆有“兮”字,(68)王先谦:《汉书补注》,第489页(上)。若依王先谦的理解,这句诗应是“幡比翄兮回集,贰双飞兮常羊”的省略。“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天门》)两句则是承“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两句的句式结构,为了避免重复,中间省去了“以”字,当是“3+虚词+2”结构的省略。这种句式在《楚辞》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曼余目以流观兮,翼壹反之何时。”(《哀郢》);“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抽思》)可见,汉《郊祀歌》中的“五言”句应是楚辞体句式的某种变形,与相和歌辞中的“2+3”结构的五言句式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