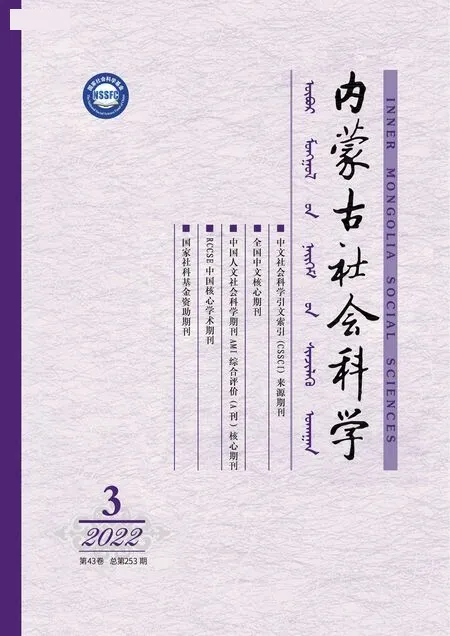高车诸族称来源及关系探析
2022-02-03王石雨
王石雨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始见于《魏书》。《魏书·高车传》记载:“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1](卷103P.2308)《新唐书·回鹘传上》亦称:“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2](卷217上P.6111)《魏书·高车传》又称:“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1](卷103P.2307)可见,“高车”并不是该族的唯一族称,而是另有“敕勒”“丁零”等称谓。但《魏书》对“北方”“诸夏”所指代的对象并没有作出明确解释,这也导致了研究者们观点各异,从而影响了对高车族称的准确理解。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史文进行重新释读,以理清高车不同称谓的来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敕勒”为自称,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漠北各族对敕勒的称谓
由“北方以为敕勒”可知,“敕勒”是“北方”对该族的称谓。周伟洲通过分析《魏书·孟威传》中的“北土”“北人”等词汇,认为“北方”在南北朝时应指塞外鲜卑、柔然等族聚居之地。[3](P.3)段连勤根据《魏书·崔浩传》中北魏君臣自称“今居北方”,认为“北方”包括云中、平城等地,是拓跋鲜卑的政治统治中心。[4](PP.12~14)尽管以上二说均不无道理,但要想更为准确的理解“北方”一词,需要具体分析“北方”在《魏书》中的各处记载,综合判断得出结论。
据《魏书·燕凤传》记载,前秦君主苻坚在同使臣燕凤讨论代王什翼犍及代国军政时曾提出:“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1](卷24P.609)燕凤回答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常胜也。”[1](卷24P.609)苻坚所称之“北人”显然为包含燕凤在内的代人,燕凤所指的“北方”也主要是代国统治地区,并以盛乐为中心。代国以南,包括关中在内的地区则皆称“南方”。然而,《魏书·序纪》中的“北方”又明显与《燕凤传》不同。《魏书·序纪》载:“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1](卷1P.1)考虑到拓跋毛时期拓跋鲜卑仍然居住于大鲜卑山一带,生产力相对低下,交通不够发达,史文所谓的“威震北方”之范围当不宜过高估计。另据《魏书·慕容白曜传》,北魏献文帝时期慕容白曜奉命出师攻打刘宋统治下的淮北地区,他在劝降冀州刺史崔道固的书信中称,“猥总戎旅,扫定北方。济黄河知十二之虚说,临齐境想一变之清风,踟蹰周览,依然何极。故先驰书,以喻成败”[1](卷50P.1118)。作为魏将,慕容白曜所扫定的“北方”肯定不能指代北魏统治地区,而是应指包括青州(治所东阳)、冀州(治所历城)在内的淮北诸州,也可称作“齐境”。有研究者对此处史料提出质疑,并援引《册府元龟》将“北方”改为“此方”[5](卷416P.4956),又称“按慕容白曜率军从河北进平青齐,似不得言扫定北方”[6](卷50P.1239)。然而从以上诸例中可以发现,《魏书》中的“北方”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域,而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含义或指代地域往往需要结合所在史料的历史背景来确定。此外,《册府元龟》往往对前出史书的原文进行改动,而《魏书·慕容白曜传》并未散佚,故仍应以《魏书》原文为准。
鉴于《魏书》中的“北方”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域,因此,想要准确理解“北方以为敕勒”,只能从记载该句的《高车传》中寻求答案。据《魏书·高车传》可知,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高车斛律部部帅倍侯利在与柔然首领社仑交战失败后,率残部投奔北魏,被赐爵为孟都公。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之人畏婴儿啼者,语曰‘倍侯利来’,便止。”[1](卷103P.2309)也就是说,倍侯利归魏后,在作战中勇猛过人,使得“北方之人”非常惧怕,故此处“北方”当不包括北魏统治地区,而应是指代以柔然为代表的漠北各族聚居之地。由此来看,“北方以为敕勒”当可理解为“敕勒”是大漠以北各族对这部分人的称谓。鉴于敕勒族包含在大漠以北各族之中,所以,“敕勒”应是该族的自称,或者是其自身习惯性认可的称谓。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漠北各族并不使用汉语,故典籍中的北方各族名称实际上多为根据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而来的汉语词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7](PP.48~53)加拿大学者蒲立本 (E.G.Pulleyblank)提出“坚昆”与“黠戛斯”译写自同一个语词。[8](PP.124~134)而“敕勒”“铁勒”则被日本学者羽田亨、小野川秀美等认为均是音译自Türk。[9](PP.1~61)[10](PP.1~39)根据汉语音韵学,隋唐以前汉字“敕”字的声母为透母,可构拟作*t‘ǐěk,又与“铁”读音相近。自隋唐起,“敕”字的声母变成了彻母,构拟作*t‘ǐk,其读音已不能再音译敕勒族名,只能换用透母字“铁”来代替。这也导致了隋唐时期史书中的“敕勒”普遍被“铁勒”取代。[11](P.1)而《新唐书·回鹘传上》所记载的“或曰敕勒,讹为铁勒”正是反映了这种读音变化。[2](卷217上P.6111)
此外,今本《魏书·高车传》及《北齐书·神武帝纪》《北齐书·斛律金传》等篇目又将“敕勒”写作“勑勒”。陈世良认为,“敕”与“勑”本非一字,“勑勒”即高车,其族源为丁零,“敕勒”则是高车别种,本为月氏族。[12](PP.71~79)陈氏忽视了其他正史中的相关记载。如北齐神武帝高欢病重时嘱咐其子高澄曰:“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13](卷6P.230)《北齐书·斛律金传》亦称:“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也。”[14](卷17P.219)故“敕勒”“高车”“勑勒”所指称的对象明显相同,“勑”只不过是“敕”的异体字。
二、“高车”为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的称谓
由“诸夏以为高车”可知,北魏时期“高车”这一称谓出自“诸夏”。周伟洲认为,“诸夏”指自古以来称为华夏的汉族;在南北朝时期,诸夏不仅指南朝的汉人,而且也指北朝的汉人和汉化了的鲜卑等。[3](P.3)段连勤则认为,《魏书·崔浩传》中“诸夏”既与“北方”对举,当指云中、平城以南北魏统治下的汉族居住区,又泛指淮河以北之中原地区;淮河以南的南朝是必须排除于“诸夏”之外的,他们一向被魏人称作“岛夷”。[4](PP.13~14)
通过分析《魏书》各处出现的“诸夏”,可以认定“诸夏”当指代中原地区。除《崔浩传》外,还有多篇传记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如《魏书·僭晋司马叡传》在卷末论及偏安江南的东晋朝廷兴亡之时称:“自叡之僭江南,至于德文之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1](卷96P.2110)此处“诸夏”与“夷狄”相对,明确“夷狄”所指称的对象对于理解“诸夏”的含义十分重要。而该处史料中的“夷狄”极易被误解成指代北方各民族,这样就会导致对“诸夏”理解的偏差。事实上《魏书》成书于北齐时期,以北魏、东魏为正统,是绝无可能将建立魏政权的拓跋鲜卑视作“夷狄”的,反倒是北朝将江南地区的南方诸政权称作“夷狄”或“岛夷”,因此与“夷狄”相对的“诸夏”无疑当指代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政权统治中心所在的中原地区。这既反映了魏收对东晋朝廷的批判,也体现了《魏书》的中原正统观念。《魏书·天象志三》记载:“自五胡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1](卷105之3P.2389)此处“诸夏”又与“五胡”相对。自西晋末年起,匈奴、慕容鲜卑、羯、氐、羌等先后进入中原地区活动,建立政权,史书所谓“五胡入华”。因而这里的“诸夏”当是指中原地区,东晋所统治的江南地区无疑不包括在“诸夏”之内。另外,北魏宣武帝时期,源怀曾上书朝廷称,“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1](卷41PP.926~927)。源怀指出,以沃野镇为代表的北部边镇情况与“诸夏”不同,但之前设置官职时却完全没有差别,边镇冗官严重,导致“黎庶怨嗟,佥曰烦猥”。显然,这里的“诸夏”当指不同于六镇的北魏后期统治中心中原地区。
尽管可以确定“诸夏”即中原地区,“高车”也毫无疑问源自该族人善于制造、使用高轮车这一生活特征,但“高车”这一称谓出现于何时,由何族最早使用尚无定论。段连勤认为,“高车”作为敕勒人的族称源自中原汉族[4](P.14),然未具体说明中原汉族开始称呼敕勒人为“高车”的时间。从拓跋什翼犍第一次征讨高车至拓跋焘完全据有中原的五六十年间,中原地区曾先后被北方民族建立的前燕、前秦、后秦及汉人建立的刘宋等多个政权占领,假使中原汉人在此期间即已称呼敕勒人为“高车”,那么记载这些政权历史的《晋书》《宋书》不应毫无只言片语。如果北魏统治中原后汉人才将敕勒人称为“高车”,又无法解释“高车”这一称谓为何自北魏后期开始逐渐消失。包文胜认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前,可能称呼高车为qaŋlï或qaŋlïn,即搬运货物的大车;入主中原后,才将原来的称谓意译为“高车”。[15]这一说法无疑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
结合史实分析,拓跋鲜卑多次攻打高车,其中天兴二年(399)掳获车辆二十余万乘。毫无疑问,拓跋鲜卑对高车非常熟悉,更了解他们善于制造并使用高轮车的风俗。从高车与拓跋鲜卑的密切关系,以及北魏灭亡后“高车”作为族称逐渐消失来看,“高车”应为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其所使用的称谓。只不过由于“敕勒”产生在前“高车”产生在后,史书中难免出现二者杂用的情况。
也有少数研究者否定“敕勒”等同于“高车”。如钟兴麟称“在某种意义上敕勒是柔然的别名”[16](PP.54~61)。这一观点不仅忽视了《魏书·高车传》中的记载,而且仅凭敕勒与柔然联系密切就认定二者为一族也缺乏证据。冯承钧认为,高车十二姓与六种之间为主部与客部的关系,其中十二姓为主,即高车,六种为客,即敕勒、铁勒。[17](PP.32~33)但高车“六种”中有斛律氏,据《北史·蠕蠕传》可知,柔然首领匹候跋诸子在其父被执后投奔高车斛律部。[13](卷98P.3250)若以“六种”为敕勒,敕勒又不等同于高车,显然与《蠕蠕传》记载不合。事实上史书中绝不乏“敕勒”与“高车”换用之例。如《魏书·京兆王传》记载:“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1](卷16P.401)同书《高祖纪下》则记载:“十有二月甲寅,以江阳王继定敕勒,乃诏班师。”[1](卷7下P.184)又如《魏书·广阳王传》载:“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1](卷18PP.430~431)同传又载广阳王元深奏疏称:“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不必制敌。请简选兵,或留守恒州要处,更为后图。”[1](卷18P.431)综上,“敕勒”即“高车”当无疑问。
三、“丁零”是北魏以前中原汉族以及南朝对敕勒的称谓
由点校本《魏书·高车传》中“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可知,除“高车”外,中原地区也曾称呼敕勒为“丁零”。然而,史学界对“高车”与“丁零”之间断句却不无争议。早在20世纪初期,白鸟库吉即已将“高车丁零”连为一词使用。[18](P.44)周一良在分析《魏书·高车传》史文时也称:“疑狄历、敕勒、丁零一声之转,高车丁零者,以其乘高车,故冠此二字以形容之,又省称曰高车耳。”[19](P.230)段连勤明确提出,《魏书·高车传》从头到尾与丁零并无一字一语相关,如断句为“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势必导致高车亦可称丁零,与全部北朝文献矛盾,故“高车丁零”应作连用,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高车传》此处断句有误。《魏书·太宗纪》中的“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及《魏书·古弼传》所载“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也可作为其说的文献支撑。[4](PP.2~3,13~15)随着该观点被诸多研究者所认可,史书中又缺少丁零与“车”相关的记载,以至于汉魏时期丁零为南北朝时期高车族源的说法也开始遭受质疑。
从丁零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丁零”(又作“钉灵”“丁灵”“丁令”等)就已出现在我国汉文典籍中。《山海经》记载:“有钉灵之国,其民从厀已下有毛,马蹄善走。”[20](卷18P.398)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卷17《五行篇》引《尚书大传》亦称:“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21](卷17P.13)虽然《山海经》等书所载丁零史事常被认为属于“附益之语”(1)参见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但两汉三国时期“丁零”已经较多出现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如《汉书》载:“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22](卷54P.2463)《后汉书》载:“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 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23](卷90P.2981)
尽管并未有任何文献明确提出丁零人可以制造、使用高轮车,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据《资治通鉴》记载:“丁零翟斌,世居康居。”[24](卷94P.2977)元代康里驻扎在汉代康居旧地,岑仲勉即曾提出康居、康里本为同族之说。[25](P.746)而根据《史集》,“康里”这一称谓的产生与其善于制车相关。[26](PP.136~137)此外,两汉时期与丁零人交往频繁的匈奴人同样善于制造车辆,《盐铁论》即载“胡车相随而鸣”[27](卷6P.348);东汉顺帝阳嘉三年(134),汉军在西域车师附近的间吾陆谷大破北匈奴,缴获车千余辆。[23](卷88P.2930)从丁零与善于造车的康居(康里)、匈奴的紧密关系来看,其造车、用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丁零早年远居于贝加尔湖一带,与两汉、曹魏政权的接触远少于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没有被中原史官所了解。因此,不能仅凭史书中缺少丁零与车相关的记载,就简单否定丁零与高车的族源关系。实际上,正如周一良等学者所论,丁零与敕勒均是音译自Türk。否定丁零与高车的族源关系即等于否定敕勒与高车的族源关系。
自东汉中后期开始,丁零逐渐分散。一部分丁零人逐步内迁至河北、河南、山西等地,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从事农耕生活;十六国时期,其贵族翟氏甚至建立了“翟魏”政权。另有一部分丁零人则从贝加尔湖地区迁徙至漠北,从事游牧生活,并与匈奴等族不断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部族。尽管这两部分人群在生活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但在北魏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仍然习惯于沿袭传统,将他们统称为“丁零”。直到北魏时期,才开始重视二者的区别,以“丁零”原音Türk的另一种译法“敕勒”来称呼丁零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部族。北魏入主中原后,又因敕勒人“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称其为“高车”。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汉书》《三国志》《宋书》中较多出现“丁零”而没有出现“敕勒”与“高车”。总之,“敕勒”与“高车”为同一民族的两种不同称谓,而敕勒虽曾被中原地区称作“丁零”,但实际上与丁零又有所区别。
综合上述分析,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高车传》中“诸夏以为高车、丁零”的断句是合理的,如将此句断为“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则不能解释“高车”之称产生以前中原对敕勒的称谓。此外,据宋人校语可知,正史中唯一将“高车丁零”连用的《魏书·太宗纪》实际上已非魏收原本,而是魏澹《魏书》残卷。[1](卷3P.64)《魏书》中也只有《古弼传》将“高车敕勒”连用,不仅属于孤例,且更像是《魏书》编纂者的疏漏或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有鉴于此,二者均不能作为证明“高车丁零”可以连用的文献依据。
尽管江南地区不包含于“诸夏”之中,但由于南朝各政权在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汉、魏、西晋等中原政权一脉相承,因此,在记载南朝历史的典籍中,同样没有将敕勒与丁零加以区分。如《宋书·芮芮虏传》称:“(芮芮)去北海千余里,与丁零相接。常南击索虏,世为仇雠,故朝庭每羁縻之。”[28](卷95P.2357)“丁零”当指代5世纪末高车副伏罗部在西域地区建立的“高车国”政权。同书《五行志二》载:“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兖、豫,鲜卑寇河上。”[28](卷31P.910)此处之“丁零”即与《芮芮虏传》所指不同,当是翟斌兄弟所率领、后迁入内地的丁零。一般情况下,若南朝史书中记载“丁零”与柔然或西域各国交流、交往情况,那么该处“丁零”大概率即为北朝史书中的“高车”;反之,则指代内迁至河北、山西等地的丁零。
综上所述,“敕勒”为自称,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漠北各族对敕勒的称谓;“高车”为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的称谓。“敕勒”与“高车”在史书中常有换用之例。“丁零”是北魏以前中原汉族以及南朝对敕勒的称谓。敕勒虽然曾被中原地区称作“丁零”,但实际上又与丁零有所区别。而《魏书·高车传》中“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一句的准确解读当为:大漠以北地区称敕勒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以前,中原汉族称敕勒为丁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后,又称敕勒为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