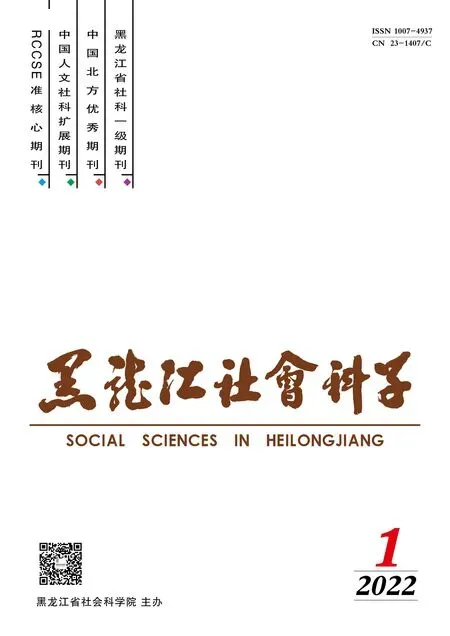吴兴华拟古诗的叙事性研究
2022-02-03樊嘉亮
樊 嘉 亮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吴兴华的拟古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在力图规范新诗形式思想指导下所创作的“绝句”诗,这一类诗具有整饬的外形、和谐的音节、仿古的意象以及深婉的情调;另一类是在其认定的想象力作为诗的本质、“理性之美”(intellect)作为诗的内容要求以及美感判定标准思想下所创作的“古题新咏”诗,这一类诗以自由体为形式,借用古代典故的故事背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在“化古”上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和艺术性。这些诗内容上是对古代故事的一种重新演绎,思想内涵上却包含了很深的现代思绪。学界对于吴兴华拟古诗的分析和研究,由于受到“新诗如何更好发展”问题的影响,多集中在这类诗中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辨析上。在前代学人的不断努力开掘下,明确了吴兴华拟古诗仿古、化古、融汇中西、结合现代与古典的特色以及吴兴华在探求新诗发展上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特殊地位。随着新诗的发展不断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力求拓展其书写范畴,叙事性也作为一种新诗谋求扩大书写边界的手段被诗人学者引入进来,并一度成为新诗写作、理论创建和发展研究的一门“显学”。本文意在以吴兴华的“特殊文本”拟古诗为例,以叙事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开掘,力图在特殊的文本形式中,以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探寻这类诗歌尚未引起过多关注的美学意味。
一、现代性与叙事
“现代性”的叙事,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现代性手法对诗歌文本的展开与叙述。实际上,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备受推崇。这里面少不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传入和接受的推动,同时也少不了当时历史环境下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的影响。吴兴华作为那个时代的诗人,难免会受到时代的裹挟而接触到现代主义理论。学界有不少关于吴兴华对于里尔克思想接受的研究。吴兴华自己也曾在文章中这样说道:“在我未提笔之前,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关于黎尔克说几句中肯的话是一桩多么困难的事。想起来够多容易,他的诗篇,散文及信札多年来就是我欢乐与忧愁中最亲切的伴侣,仿佛把我对它们的印象大略描述一下,就可以算尽了介绍的责任。”[1]但笔者以为,可能通过吴兴华自身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关注更能说明其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他在1947年12月16日给宋淇(林以亮)的信中这样写道:“最近杂志上常登一个叫穆旦的诗作,不知道你见到过没有?从许多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最有希望的新诗人。”[2]其后他还和宋淇谈到了穆旦诗歌语言欧化的现象,以及他对于穆旦这种英国牛津派风格突出的高等知识分子的诗能否在国内走得通的担忧。从这一个细节上就大概能够看出吴兴华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注和了解。这种关注和了解自然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同时,在其诗歌创作之中也有很深的体现。
梁秉钧曾指出过吴兴华的“古题新咏”诗是“对众所周知的题材加以陌生化的技法(the device of defamiliarization of well-known subject matter)”[3]。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众所周知的题材”以及“陌生化的技法”。这种“陌生化的技法”实际上是通过有别于传统古典线性叙述的现代性叙述来实现的。可以说,此类诗歌在选择题材的“古典化”和表现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恰恰就是此类诗歌张力产生的动力之源。时代沉积所产生的时间上的落差以及熟悉故事之中所迸发出的能引发现代人情感共鸣的情调,给予了“古题新咏”诗一种沉淀之中闪现出新奇的“再发现”的美感。
下面以《吴王夫差女小玉》为例进行分析,该诗采用了吴王夫差幼女小玉和童子韩重的故事为原型,原文讲述了二人偶然相识,并通过私通书信相互了解互定终身;此后韩重因求学而去国离乡,期间嘱托其父母向小玉求婚,吴王震怒不允,小玉气结身死;三年后韩重学成归来,得知小玉已然身死,去其所葬江边悼念的完整故事。
在叙述策略的陌生化表现上,首先是重新调整叙述结构从而造成叙述的陌生化。原故事是一个有起因、经过、结果的整体,而在吴兴华的诗中,省去了故事的起因和发展过程,直接将故事发生的地点限定在江边,将原故事中的高潮和即将到来的结局作为诗歌叙述的主体情节。诗的开头便是:
他们俩相遇在大江日夜的流声
沉落的地方
这就将原来纷杂变换的场景和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同时原故事中预设的叙述视角很高,而且是客观中立的视角,并在此视角下安排二人相见后以对话的方式互诉衷肠。而在吴兴华的诗中虽然有对于小玉的描写,但大都停留在动作和体态上。同时诗人刻意把叙述视角推得很低,并主要框定在韩重一人身上,通过对韩重心理和情绪的精致刻画来从侧面展现出二人之间的情感羁绊和命运对于二人的捉弄。更有意思的是,在诗中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直接的语言交流,有的只是二人的动作的描写以及韩重细致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的刻画。这种无言的展现毫无疑问地加强了诗歌所展现出的故事的悲剧化效果——所有的悲凉凄恻、所有的苦楚压抑都被埋没在了这没有对白的无言的叙述之中,只有“远处大江声,狗吠着山下的行旅”。也正是这样全新的故事编排和叙述使得原有的为人熟知的故事成了诗歌叙述的背景板,既定的旧有期待视野被新的故事叙述和编排打散、重组,使得读者在接受之时有了获取新期待的可能,也给予了这首诗一种叙述结构上的“陌生化”。
其次,以情感流动的叙述代替故事情节的叙述从而营造出陌生感。吴兴华的诗歌叙述过程中几乎完全抛却了原有故事的完整情节,而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了小玉同韩重的情感流动上,尤其是对韩重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地刻画:
在他脑子里频频敲击着的思想,
临近于恐怖,却更临近于失望:
……
或许死亡并不是,如他所梦想的,
一切生命的最高点,完满的终结。
这样,故事的推进就不再依照传统叙述中情节发展的逻辑一步步推进,而是依照人物情感和心理的变化起伏来发展。随着韩重情感上对于小玉的思念,对于现实的恐惧、失望,对于小玉离世的悲伤,以及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最终推动了情节向着二人再度相认并携手步入坟墓的结局发展。情感从某种程度上代替情节作为叙述的主线,使得这首诗整体上有了一种幽怨悲伤的氛围和基调。虽然仍然是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但叙述手段的不同,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爱情故事。通过细微的情感和心理叙述,作者想要展现给读者的一种全然不同于原故事的、符合现代人审美预期的、新的情绪,是那种散发着浓重现代主义气息的、有关爱与死亡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说是吴兴华的一种对现代情绪的内化,也可以认为是其受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的旨趣上选择了“理性化”的方向。也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叙述同现代情绪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叙述上的“陌生化”效果。
再次,通过有意抓住某个细节并延长叙述时间的叙述手法营造陌生化。莱辛在《拉奥孔》之中阐述了艺术创作在有限篇幅内选取表现时间的原则:“既然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了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个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4]这样的艺术裁剪和加工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更好地展现作品的艺术性。吴兴华对于原有文本进行裁剪和再编排也是为了能够突出其想要发掘的精神内涵。同时由于受到了里尔克的影响,其创作还出现了一种有意抓住某个细节并延长叙述时间的特点。他在文章中以里尔克的《奥菲乌斯·优丽狄克·合尔米斯》为例,表达了这样的艺术倾向:“这个故事,像许多其他的希腊神话一样,几乎像是生来就是为作诗的题材而设的。但是它‘最丰满,最紧张,最富于暗示性’的一点到底在哪里?恐怕大家所见不见得相同。粗粗看起来,似乎奥菲乌斯在地界王面前奏琴那一段最为感人,但黎尔克抛弃了这显而易见的一点,而选择了这短短的一瞬:在奥菲乌斯将要回头而尚未回头时。在这短短的一瞬里,他放进了整个故事。”[1]在《吴王夫差女小玉》这首诗中诗人就花了两节二十多行的篇幅着重描绘韩重再次见到小玉时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起伏。从最初的恐惧、失望到深深的悲伤,从暂时摆脱强烈情感的冲击到再度陷入了回忆的泥淖,眼前小玉和记忆之中小玉的对比产生的虚幻感令韩重错愕,也使其一时间陷入了对于生与死的思索。这种对于叙述时间的延长处理,突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形成了人物情感波动上的张力表现。将故事的焦点集中在了诗人想要展现给读者的“美妙的瞬间”之中,并通过这一精心选择的焦点瞬间将诗人对于整个故事叙述的匠心营造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放缓了叙述节奏的同时也使得诗歌情感的节奏骤然加快,一快一慢之间产生的戏剧性张力也使得诗歌的叙事充满了一种现代气息十足的陌生感。
最后,吴兴华“古题新咏”诗在叙述上所展现出的陌生化实际上是一种以真实性为前提的陌生化。在什克洛夫斯基阐述“陌生化”理论的文章《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对于“陌生化”的本质有着这样的阐述:“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我们可以将这段话总结为两个方面——艺术的真实和手法或形式的困难。这就是说,究其根本,“陌生化”的目的还是要“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是要追求一种艺术上的真实。“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与展开也脱离不了对于事物的真实描写。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首诗上来,这首诗的结尾相较于原故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动。原故事是“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之夜,尽夫妇之礼”。如果诗人完全按照原故事进行再加工,在故事发展和叙述逻辑上似乎没什么不妥,但是这里面却又隐隐存在一种与现代价值不相符的情况,如果“夫妇之礼”出现在这首现代诗里,未免会产生一种违和感。这就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价值观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的行文逻辑和价值导向进行改写,难免会出现“不真实”的感觉,既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又和全诗的基调明显相悖。所以诗人在这里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述:
坟墓缓缓的张开他石头的牙颚,
吞食下他俩,只余下蜡泪和残灰。
这种处理,在保障了作品艺术真实的同时延长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感受,交代了故事结局的走向又给了诗歌融合古典审美的“留白”延伸,从而完成了艺术上的真实性和形式上的陌生化。并且,也使得现代人的现代感官和现代思想同古典故事很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具有张力的“现代性”叙述。
二、形式与叙事
这里说到的“形式化”叙事实际上更偏向于形式对于诗歌叙述的影响这一层面。如果我们把形式也看成是诗歌叙事的一个重要层面,那么毫无疑问,不同的形式的选择会对哪怕是相同的诗歌题材的内容和叙述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文学革命的初期,作为新诗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如此看重诗歌的形式开拓,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口号,力图打破旧有形式加在中国诗歌上千百年未变的束缚。因为有了“诗体大解放”,新诗才没有形成统而划一的形式,而也正是因为新诗未能像古典诗词那样形成一套或几套固定的形式,新诗的形式问题就成了一直伴随着新诗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吴兴华的拟古诗包含两大类,其中“绝句”一类的诗歌就体现了吴兴华对于新诗形式规律建设的一种尝试。吴兴华的“绝句”诗每行固定为十二个字,分为五音步,第一、二、四句押韵,音步相等,不讲求平仄。与传统古典五七言诗相比,在格式上不那么严谨,但大致遵循了古典诗歌的格律原则。此外,他吸取了“五四”以来对于音组的实验改良结果,运用音节组合来停顿,在诗歌内部带来一种节奏的变化。这就使得“绝句”形式写成的诗歌形式齐整、结构紧凑、音韵和谐、意象幽婉,有着非常浓重的古典气息。下面以林以亮、卞之琳和张建松分别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吴兴华的同一首诗歌为例来说明:
绝句
仍然 等待着 东风 吹送下 暮潮
陌生的 门前 几次 停驻过 兰桡
江南 一夜的 春雨 乌桕 千万树
你家 是对着 秦淮 第几座 长桥[5]
经过林以亮的断句我们不难发现,在这首诗中绝句的形式为诗歌的叙述提供了很好地帮助,在清楚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带动下,诗中的意象、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基础,又同时兼有强烈古典风格韵味的特殊诗篇。中国香港学者冯晞乾认为,这首诗的原型来自于明代林初文的诗:“不待春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冯晞乾同时认为,相较于林诗,吴诗是对其的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误读,他认为这首简短的诗中包含了诗人吴兴华四层诠释:化用七绝形式写一首古香古色的新诗;依照旧诗传统“次韵”一首渡江名作;既要对原诗亦步亦趋,又要改头换面,改换诗文主旨意趣;这种创造性的误读是在新的时代和语言环境下对于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有益的延续[6]。冯晞乾的解读实际上也是由表及里、由想象到本质的,正因为有了相应的形式,才能以此为基础展开诗歌叙述进而升华诗歌的内涵。所以可以这样说,由于形式的特殊使得“绝句”类的拟古诗在叙述中产生了一种古典化的叙述节奏,也使得吴兴华的“绝句”诗有了不同于其他形式新诗的深厚古典主义色彩和韵味。
同时,由于字数的限制,像古典五七言近体诗一样,为表达一种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事件,也是为保证在有限的篇幅内包含更多的内容,用典和大量引入相关意象成为了这类诗歌一种必不可少的叙事技巧。高友工和梅祖麟就对近体诗用典的必要性作出过这样的分析:“近体诗的最大容量也只有七言八句五十六个字,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很难把某一行为的动机、环境解释清楚,而一个没有环境和动机的行为,就不能算是道德行为,这样,近体诗的作者在表现道德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更加尖锐。然而,典故的运用使本来不可能的事成为不必要的事:由于环境、动机、人物关系等背景材料都已蕴含于典故之中,详细的解释就被简略的暗示所取代。当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地点时,所有与之相关的意义和事件都会随之俱出;而当典故运用于现实的题材之中时,就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活动的环境。”[7]以单音节词为主且未在诗行中加入大量虚词的文言文尚存在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在以双音节词和虚词大量介入从而拉长了句子长度的现代汉语作为语言基础创作时,要满足每一句都限定在十二个字,这种技巧就显得更为重要。如这一首:
绝句
尚记得行吟泽畔憔悴的孤臣
国家有如此烈士怎能够沉沦
骊山一火竟不灭离骚的光耀
阿房三月终伸复武关的怨心
垓天美人泣楚欲定陶泣楚舜
沛中高帝的大风,汾上的白云
诗篇慷慨更不惭流传下万古
饮水思泉时还须俯首对灵均
这首诗中就包含了很多典故,诸如屈原行吟、火烧阿房宫、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刘邦赋《大风歌》等等,几乎每一句中都有古典意象或是人物典故的加入。虽然整首诗读起来依旧音韵和谐、节奏清晰,但是在如此繁复的意象和典故的加持下令人有些目不暇接。如上文所言,想要用词汇音节更长、句法结构更加严密、句式较文言文更长的现代汉语在每行一定的字数内表达更多的内涵,这种叙述手法是不可或缺的,但固定字数诗句的承载力终究有限,加入了太多内容就会让人产生不堪重负的感觉。过多的典故意象安排不仅会打乱叙事节奏,也会影响作品整体的艺术美感。也正如卞之琳所分析的那样:“在一首新诗的有限篇幅里实在容不下那么多意象,拥挤了一点,少了一点回旋余地……少了一点中国诗传统常见的一种雍容或潇洒的风姿。”[8]虽然这种形式的诗歌在叙述之中会存在意象典故过于繁复的问题,但是这种尝试依然是一种沟通新与旧、古典与现代的有效途径,也为新诗的发展,尤其是新诗的形式建构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吴兴华重视诗歌形式的原因是他认为“形式仿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公有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就都是作者的了。我们念完了一行诗,绝没有方法知道第二行将要是多长,同时也不知道第二行将要说甚么东西,因为新诗现在越来越‘简洁’了,两行并列时,谁也看不出其间有甚么关系”[9],同时他认为一定的形式,并不会影响诗意的,反而有时候会更好地表现诗歌的内涵,并举例说明,“当我们看了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春如短梦方离影,人在东风正倚栏’、‘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等数不尽的好句之时,心里一点也感觉不到有甚么拘束,甚么阻止感情自然流露的怪物。反之,只要是真爱诗的人立刻就会看出以上所引的诸句,和现在一般没有韵,没有音节,没有一切的新诗来比时,哪个是更自然,更可爱。”[9]这可能是形式带给叙述者的一种便利,但这种便利同时又需要作者和读者产生一定的默契。
在吴兴华看来,正是由于新诗失掉了旧诗那种形式上勾连起作者与读者的“红利”,使得诗人、诗歌相较于旧诗而言天然地与读者产生了隔膜。所以新诗人在创作新诗时要更加小心,因为诗人此时肩负了更为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其看来是教育大众的责任,让读者能在新诗之中产生新的真善美的体验,从而一步步努力建立起以往那种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这里就又存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依照吴兴华所言,新诗不应该去求大众化,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其最终想要达成的那个“新诗化”的目标却是一种类似于古典诗词生态环境那种晋升了的有固定审美范式并能使读者与作者相互理解的“大众化”。而这一切的基础,应该就是诗歌的形式。那么在旧有传统未完全被取代之时,古典主义的审美相较于新诗在这百年以来做过的新的尝试,哪一个更能为大众所接受,什么样的“新诗化”是更为讨巧的方式,想来吴兴华应该并不是没有预见到,不然他也不可能选择一条更新传统同时努力化古纳新的折中道路。至于形式,依照上文分析,确实可以影响到诗歌的叙述,但想要以一定的形式再次达成近体诗那种沟通诗人与读者的模式,在新诗发展到如今的地步,恐怕不只是诗人,读者可能也并不买账。
三、抒情与叙事
在传统诗学审美之中就有“诗缘情而绮靡”[10]的论述。“缘情说”也和“言志说”一起被称为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与美学表征。在吴兴华的拟古诗中,由于深受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带有很浓重的抒情性色彩。吴兴华自己也在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提到:“事实上是中国人一提起‘诗’这个字来,就容易联想到抒情诗,这足以珍贵的、从中国人发展到极高峰的艺术。在抒情诗的领域里,丰溢的想像力是缺不得的。”[11]在吴兴华看来,抒情诗“有一个坚不可拔的古典文学的基础”[12]。因此有研究者这样认为:“不仅吴兴华早期的诗歌几乎都是抒情诗,即使在其诗歌写作的过渡时期和成熟时期,抒情诗也是他进行诗歌创作的首选。”[13]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吴兴华的拟古诗中又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叙事意味极强的“古题新咏”类诗歌。
最早为这一类拟古诗命名的是美国学者耿德华,他将这一类诗歌称为“叙事史诗”[14]。但这一概念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极不准确的。余凌(吴晓东)就认为:“‘叙事史诗’是不十分准确的概念,因为吴兴华的这一类带有叙事成分的诗作尽管大都择取历史上的某一人物或事件,但作者关注的不是叙事,也不是故事本身。吴兴华只是在初始故事的原型中找到了一个规定情境,凭藉这个情境和框架,吴兴华着力传达的是具有鲜明的诗人主体性的感性体验和哲理思索。”[15]解志熙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评论者称之为‘叙事诗’或‘叙事史诗’,以为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现代叙事诗的稀缺。这种说法未必妥当。诚然,这些诗作确有较强的叙事性,但除了较早的《柳毅和洞庭龙女》着重铺叙那个浪漫传奇的故事之外,其余都是取古典人事的一点、一刻或一面而已,并且作者的心思并不在发怀古之幽情或炫耀其拟古之才藻,所以也不同于传统的怀古、咏古、拟古之作。即使说是咏古、使典,吴兴华的兴趣也不在历史与典故所蕴涵着的那些亘古常新的人生经验与人生况味,且予以别有会心的现代性拟想与创造性重构。”[16]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都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吴兴华诗歌的旨趣,认为不能仅凭形式上的叙述样貌就将吴兴华拟古诗中这一类诗歌称为“叙事诗”,而应更加关注诗歌之中想要表现的一种人生经验和作为人的主体思考。
那么这种经验性的内在观照究竟属于什么范畴呢?高友工在其文章中有这样的论述:“抒情美典显然是以经验存在的本身为一自足之活动,不必外求目的或理由。它的价值论亦必奠基于经验论上,经验本身有何种价值,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观察:即是感性的、结构的、境界的。”[17]吴兴华的拟古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内观性的和经验性的对于人物的心理描绘和情感描写。对于细微心理变化的刻画和微妙情感流动的描写已经成为吴兴华诗歌中的一大特点。梁秉钧就把“心理洞察力(psychological insight)”以及“与众不同的人物刻画(unusual perspective on characterization)”[3]作为吴兴华诗歌的特点。同时在主题上,如同上文提到的两位学者所言,诗歌的主题也显现出了极富现代主义意味的对于人生经验的感悟和人生况味的体察。由此可以看出,吴兴华的拟古诗是符合高友工所提到的“抒情美典”的范畴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在吴兴华哪怕是表面最具叙事性特征的“古题新咏”一类拟古诗中,这些诗的内涵依旧是深度抒情的。
但同时,由于现代人情感的复杂性,在诗文中想要表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以及更加丰富的符合现代审美的内涵,在同一文本之中存在多个美学范式也是可能的:
不但兼有两种美典是可能的,而且更须认清美典绝不限于此两种。
这两种(指抒情和叙事,笔者按)对美的态度好像是不可能兼容并蓄的。但事实上正因为二者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解释,因此任何人都必须视其环境而有不同程度的抉择与适应[17]。
简单地讲,在吴兴华的“古题新咏”诗中存在着外在形式上的叙事性和内在情感与旨趣上的抒情性,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抒情与叙事这两者背后所代表的内涵时,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果我们将抒情理解成是一种建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共情性美感之上的美学原则,而且其具有很强的情感和道德上的内驱性冲动,那么与之相对的叙事则是一种建立在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逻辑性美感之上的美学原则,并且其具有很强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外延性冲动。这也就是说,当我们采取这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去关照文学文本的时候,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抒情性更注重的是主观经验的投射,即主观的情感道德同投射对象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以一种内向发掘的递进性推动力达成主观经验同客观投射物间的统一,从而展现文本的美感。而叙事性则倾向于将投射物(客观事实描写)同投射的经验分置,以一种更为跳脱的视角来审视文本的肌理运作,并通过不同客观事物间、事件间或是事物、事件与主观经验间的张力来展现美感。同时,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外在的客观目的往往臣服于内在的主观经验”“内向的(introversive)的价值论及美典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外向的(extroversive)的美典,而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17]的现象。
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诗人的吴兴华还是作为评论者的前代学人,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文化倾向的影响。吴兴华在诗作中哪怕采用了极为叙事化的外在叙述方式,其诗歌的内涵依旧有着浓郁的抒情性特质;而评论者的评论也都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吴兴华诗歌更加具有抒情性的内涵而不是叙事性的形式上,甚至在为这一类诗歌命名时,不约而同地认为形式上的叙事性不足以概括这类诗歌的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称其为“叙事诗”。但是实际上,抒情与叙事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隔膜,上文中也曾提到,有时作者想要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情感或者主题,或者想要给予读者复合式的审美体验时,这两者同时出现在同一文本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固然,我们有着抒情压倒叙事的文化传统,同时在吴兴华的文艺思想之中也对诗歌的抒情传统情有独钟,但这些都不影响抒情与叙事这两者在吴兴华的实际创作当中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平衡表现在,叙事性作为一种明显更具外延性和逻辑性的美学范畴,无论是作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在文本之中运用时,文本所展现出的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符合逻辑叙述要求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就使得文本在叙述上有了很好的外延性空间,可以根据作者对于文本的需要创造出合适的叙述时间和空间。反映在吴兴华的拟古诗上就是对于原本故事背景以及故事发生环境的重新裁选,如在《褒姒的一笑》中,诗人就独具匠心地仅截取褒姒因烽火戏诸侯而露出笑颜这一画面展开叙述,省去了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对故事情节的重新编排甚至改写以达到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艺术真实性效果,则体现在《柳毅和洞庭龙女》中,原故事是柳毅听从龙女嘱托,直接前往洞庭湖请来了龙女的父亲钱塘君救出了被困的龙女,而诗歌中故事在柳毅离开洞庭龙女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同时在柳毅的去向上吴兴华也作了改写:
该死!
我还不快走干什么?
用脚向马腹一踢,
可是他糊涂了,应该往东的,他往了西……
这样的改写体现出了柳毅内心的纠结和踌躇,细致的心理刻画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延长叙事时间、放慢叙述节奏以达到凸显人物性格的目的,则体现在《盗兵符之前》中,诗人花了大段笔墨来演绎原故事中没有展现出的信陵君说服如姬帮其盗取兵符的内容。同时加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
她不言语,暂时被这新的知识
击昏,如何在狂风与疾驰的险流中
才有真实的生命。她裹在锦绣里,真想
把一生只换一天,像他这样的一天。
这样的描写增加了叙事的时间,放缓了叙事的节奏,同时也更好地展现出了如姬在和信陵君对谈以后发生的变化。
而抒情性作为一种更具内向性和经验性的美学范畴,当作者将其运用在文本之中时,文本所展现出的就是一种灵魂上与历史上的内省和沉淀,这种向内的开掘使得文本在唤起读者一种基于经验积累的共情的同时也赋予了文本向更为深刻思想探寻的可能性。表现在吴兴华的拟古诗上就是文本中带有的厚重的历史沉淀感,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情感流动和心理变化,如在《褒姒的一笑》中对于周幽王见到褒姒笑颜后的心理描写:
他觉得他的心像要跳到她手里
霎时间悲愁的空气向四周散布
微笑出现在她唇边。他闭上眼睛
觉到有死亡的神祇在与他耳语
柔顺的却不含恐怖,他向他倾听。
此时的周幽王已经抛弃了作为一国之君的身份,只是以陷入爱恋的男性的身份接受了褒姒那倾国倾城的一笑。诗人如此描述其内心感触,使其感触和普通人别无二致,拉近了历史人物与现实的距离,使得文本内外的情感在一瞬间达到了一种共通,体现出了一种现代的审美以及极富“理性之美”的有关国家、社会、人生、死亡、爱情等一系列主题的深入思考。而上文提到的《吴王夫差女小玉》也反映出对于爱情和死亡的思索,《盗兵符之前》则承载了家国愁思,是一种对个人和国家乃至历史的观照的思考。可以说,吴兴华的拟古诗在把握抒情和叙事二者精妙平衡的同时,达到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