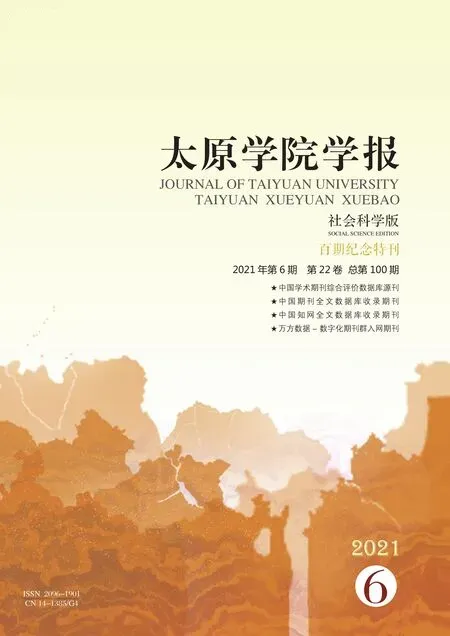论古代乡贤道德的超越性和实践性及其当代价值
2022-01-19刘硕伟
刘硕伟
(临沂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近年来,乡贤文化成为媒体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话题。古代乡贤文化的发掘也就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古代乡贤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文化。它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的哲学品质。古代乡贤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古代乡贤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文化
古代乡贤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文化。这从字源即可见一斑。在甲骨文中,“乡”写作“”,两人相向跪坐,共食一簋。《国语·齐语》之《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篇载,桓公向管子请教治国之术,管仲对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桓公又问:“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匠和商人六乡,军士和农民十五乡,由桓公掌管五乡,国子掌管五乡,高子掌管五乡。这里的“乡”,指把国都为成不同的功能区域,在不同的功能区域内,以二千家为一乡。显然,“乡”已经具有了一定空间范围的含义。在汉代,“乡”正式成为行政区划概念,但它仍然保留着“关系密切”的原始意。许慎《说文解字》:“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段玉裁释“离邑”曰:“析言之则国大邑小,一国之中离析为若干邑。”又特别地解释了汉代基层治理结构:“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1]303段玉裁在《经韵楼集》说:“相友、相助、相扶持亲睦名曰乡者,取其相亲,礼莫重于民之相亲,故乡饮、乡射原非专为六乡制此礼也。而必冠之以‘乡’字、‘乡大夫’‘乡先生’者,谓民所亲近者也。”[2]311可见,“乡”的本意及引申义都包含着人际关系密切的意思。乡饮、乡射之礼制,乡大夫、乡先生之称谓,都着重于人伦道德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乡”的行政区划概念,实际已经包含了道德共同体之内涵。在甲骨文中,“贤”写作“”,左边为顺从的眼睛,代表善良,右边为举起的手,代表能力。小篆作“”,从贝。《说文解字》:“贤,多才也。从贝,臤声。”杨树达先生认为:“以臤为贤,据其德也;加臤以贝,则以财为义矣。盖治化渐进,则财富渐见重于人群,文字之孳生,大可窥群治之进程矣。”[3]37也就是说,“贤”字包含了能力(“财”或“才”)与品德(“臤”)之意。《荀子·哀公》载孔子回答哀公之问,对“贤人”作出如是定义:“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富有天下、布施天下,是财;行中规绳、言足法天下,是德。行动符合礼义而不伤本性,说话堪为表率而不伤自身,富有天下却不蕴积私财,广泛布施却不担心自己贫困,这样的人,德财俱备,人伦和谐,可称贤者。贤者必须首先具备能力(多财,多才),并且以这种能力为道德共同体作出为众人认可的行动。质言之,“贤”隐含了能力超群的标准,而强调道德品质之突出。
乡贤是道德共同体之权威。这里的“道德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村、一乡、一国,皆可为道德共同体。管仲相齐,成就桓公霸业,其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将一国视为一个经济体、军事体,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四维学说。他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4]3礼指符合社会等级制度的礼节仪式等;义指行为不自私自利,合乎社会规则;廉指廉洁方正,不隐匿真相;耻指保有羞耻之心,不追随邪恶。如何强化四维,管子提出了具体意见:“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4]32从这些繁复的议论来看,管子不仅重视生产力,也重视生产关系,不仅重视经济基础,也重视上层建筑,四维之说的提出,把一“国”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且强调道德之于此共同体,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所以“乡贤”,不必拘泥理解为“一乡之贤”,更不是今天城乡对立意义上的“乡村之贤”,而是特定的道德共同体之权威。正如欧阳修所说:“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渎,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贤于一乡者,一乡之望也;贤于一国者,一国之望也。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5]267必有“达”的过程性,才有“望”的权威性。总之,乡贤是道德权威,权威之形成,须为道德共同体作出贡献且为此共同体所认可。
从道德共同体之权威的意义上说,乡贤文化实际产生于汉代。学者一般认为乡贤祭祀是乡贤文化之始。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汉献帝时孔融任北海相,“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以弘扬儒家道德为己任。为了培育德性文化,他刻意地褒扬德业学行皆著称于世的郑玄,认为“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孔融又引东海于定国为例,为郑玄建“通德门”。孔融弘扬儒家道德的第二件事就是追祀甄子然。《后汉书》本传说:“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清代梁章钜认为,这是服膺儒术、德高望重者称“乡贤”之始。其《称谓录》云:“东海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按:此误,应为甄子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6]465实际上,西汉已有祭祀循吏之载。《汉书·循吏传》载,召信臣曾任上蔡长、零陵太守、南阳太守等,所在好为民兴利,推行教化,“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召信臣于南阳,可称名宦,于其家乡,可称乡贤。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之祀于西汉已有。梁章钜以孔融祀甄子然为“乡贤之始”,可能就其未曾入仕而以德行祔庙的角度来论说的。
乡贤在道德共同体中的权威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纵向的国家治理网络中,乡贤发挥着神经末梢的重要功能。在横向的乡土自治网络中,乡贤是网络的编织者和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力作用。
首先从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网络来看,古代乡贤发挥着沟通乡土社会与政府机构、协助政府进行治理的重要社会功能。汉高祖刘邦刚入秦地,即“与父老约法三章”,“至栎阳,存问父老”,以稳定关中民心。这里的“父老”即为乡土社会的精英人物(汉末始有乡贤之称)。汉二年,又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高祖本纪》)三老不是政府官员,不领取俸禄,但有一定的待遇(免除徭役、每年十月赐酒肉)。此举遂在地方政治中建立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并行的二元格局。费孝通说:“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的。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7]288三老制度的设立,正是实现双轨形式的一项创造。汉高祖之后,文帝、武帝皆有三老之设。如《汉书·文帝纪》:“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此外《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及《百官志》都有“三老掌教化”的记载。此后历代统一封建王朝多承汉制,各地乡贤也在沟通乡土社会与政府机构、协助政府治理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明朝洪武五年(1372)诏令各乡各里建造“申明亭”(惩治奸恶之所)和“旌善亭”(表扬先进之所)。洪武二十一年(1388)颁布《教民榜文》(又称《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了强化社会治理,朱元璋“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里置一人,谓之耆宿,俾质正里中是非,岁久更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里老不仅负责教化,也担负着一定的调解纠纷的司法职能。清顺治九年(1652)颁布的《圣谕六条》,即将朱元璋所颁《教民榜文》重新颁行八旗及各省。各地乡贤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沟通乡土社会与政府机构、协助政府治理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明代乡贤邹守益、清代乡贤郭大昌,都是担当社会事务的典范。乡贤有时会发挥政府机构难以达到的作用。例如崇祯年间,灾荒频繁,地方官设立的粥厂,打出“奉宪赈粥”的旗帜,聚集灾民排队等候,等到中央派出的“勘荒官”到来后才开始施粥。“勘荒官”走后,施粥工作往往立刻宣告结束。这种表演式的赈灾不仅不能使灾民受益,且因大量灾民聚集,极易发瘟疫或民变。鉴于此,嘉善乡贤陈龙正发明“担粥法”以济流民。所谓“担粥法”,就是雇人挑着担子,流动地赈济灾民,无定所,无定额,随到随救,量力而行,且因其流动性,不易发生疫情或民变。不仅如此,陈龙正还在施粥的同时,发表“讲语”,宣传儒家伦理道德。由于切实可行,“担粥法”一直传承至清末。
其次在乡土自治的横向网络中,古代乡贤发挥着敦睦宗族邻里、维持乡间秩序、促进乡村教化的重要社会功能。乡贤对家族、宗族的有效管理,使儒学深厚、门风敦睦的“望族”大量出现。例如,郓州寿张县张氏家族,“立义和堂,制典则,设条教,以戒子孙”,门风敦睦,为地方望族。隋文帝派人送“孝友可师”之匾。唐高宗封禅泰山,归途绕道寿张拜访张氏族长,询其治家秘诀,并亲书“百忍义门”匾额。正如钱穆所说:“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8]309-310乡贤还常常通过乡约、义庄、耆老会等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北宋蓝田人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成文乡约。吕大钧在返乡守父丧期满之后不愿复出为官,而是留在家乡推行道德教化,制定《吕氏乡约》。其核心精神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约组织超越了宗族组织,是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自治组织。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修订,化繁为简,贴近生活,还特别加入了“畏法令,谨租赋”六字。这是民间组织向国家政权的表态。由此,乡约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王守仁于正德十三年(1518)颁布《南赣乡约》,影响巨大,嘉靖年间,由朝廷推广。乡约是乡贤规范乡里的组织,义庄则是乡贤敦睦宗族的形式。范仲淹在六十余岁时将自己多年积蓄拿出购田千亩,建设“义庄”,救济族中贫困者。义庄之外,还创办义学、义宅。(义学为族内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义宅为族中公共住房。)直到清代,范氏义庄仍然存在。耆老会主要是致仕乡贤恢复传统礼仪、维持乡间秩序、促进乡村教化的组织。如,史浩是南宋著名廉吏,辞官归隐后,组织耆老会,恢复四明的乡饮酒礼,目的在于敦睦乡里,引领向善风气。他还与当地其他望族联合创立义田庄,设立书院等,并亲自撰写了《童丱须知》,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变成深入浅出、琅琅上口的韵文。除史浩外,皆曾为台阁重臣的汪大猷、楼钥、陈卓等致仕后亦结耆老会,通过复乡礼、置义田、办书院等活动,维持着乡村秩序,节约了官府的治理成本。
二、古代乡贤道德的超越性
古代乡贤秉承儒家“以天论德”传统,其道德具有形上超越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将“性”“命”与“天”紧密相连,认为天命是人性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儒家以“天”作为道德的形上根源,使其道德具有类似宗教的超越性。乡贤秉承儒家文化。一方面,以儒家孝悌之爱为根本,将血缘亲情扩展于社会群体甚至天地宇宙;另一方面,古代乡贤又将对于形上天道的体悟和证认贯彻落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具有主观的精神修养与客观的形上天道双向实现的超越性。
一方面,儒家文化将基于血缘的孝悌之爱扩展于整个社会群体乃至天地宇宙。《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孝、悌等基于自然情感的爱是“仁”的根本。也就是说,爱人须从亲始。不亲亲者,何以泛爱众?乡贤作为儒家道德信念的坚守者,不仅爱亲、爱家,更具有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博大情怀。乡贤就是实践着的人际关系的中心,他以家庭为精神之旅的出发点,在不断扩大的关系层次中全面地实现人性:一是与自己的和谐,通过个体的人伦践履及精神修养,实现个体的内在超越;二是与他人的和谐,注重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仁者爱人;三是与群体的和谐,重视协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重视群体价值;四是与社会的和谐,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为个体的追求,有利于促进公平和正义;五是与“天”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伦理。还应指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又不限于自然伦理。儒家之“天”不仅仅指自然之天,更具有伦理之天甚至神明之天的内涵,是修为之目的,是价值之来源。
另一方面,乡贤又将对于形上天道的体悟和证认贯彻落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也就是孔子所谓操存之法。《孟子·告子上》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心”之“出”“入”没有定时、没有定向的特点,更决定了操存的重要性。它要求个体生命“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贤将对天道的感悟和体认化作一种生活方式,坚信与身边人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史记·公孙弘传》谓之:“养后母孝谨。……后母死,服丧三年。”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琐事,但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对形上天道的贯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乡贤文化体现了主观精神修养与客观形上天道双向实现的道德哲学品质。
三、古代乡贤道德的实践性
古代乡贤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对人的重视,对人伦关系的强调,使得乡贤文化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体现在个体的道德践履与群体的伦理规范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乡贤将群体的伦理规范变成个体的道德践履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乡贤的个体道德践履又作用于道德共同体,维持基于道德信念的秩序安排。
首先,乡贤将儒家伦理规范变成个体道德践履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追求是儒家文化的内在要求。孔子有所谓操存之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贤坚信与身边人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例如,房彦谦十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隋书》本传称“事所继母,有逾本生”,对伯父也是竭尽心力、十分孝顺,“每四时珍果,口弗先尝”。遇上亲戚家的丧期,他一定茹素食以尽礼节。诸如此类的生活琐事,史不乏书,因为修史者同样相信,这些点点滴滴,是对形上天道的贯彻。《论语·阳货》中宰予与孔子讨论三年之丧的问题,被孔子严厉批评,并且事后对其作了苛刻的议论:“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实际上把一个礼仪问题转换成了一个情感问题。李泽厚说:“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溶为一体。”[9]20《汉书·王吉传》记载,琅邪人王吉的邻居家有棵枣树,枝条扶疏,垂到王吉家中。有一次,王吉之妻摘了些枣子给王吉吃。王吉吃完之后才知是擅自从邻家枣树上摘的,认为妻子不贤淑,打算休了她。邻居得知,深感不安,要砍掉那棵树。众街坊觉得砍树可惜,纷纷劝阻,并劝王吉接回自己的妻子。在众人劝说下,王吉原谅了妻子。时人谣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琐事,在当事者看来,是对儒家道德的遵守和实践,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加强主观精神修养,可以达到对天道的体悟和认证。
其次,乡贤群体基于道德威望维持着法理权威所难以达到的乡土社会的优序良俗。乡贤之“乡”,是具有相对意义的道德共同体,具体表现为特定时期与特定地域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它具有相对意义,小可指家族,大可至国家。乡贤之“贤”,是在个体意义上对抽象道德精神的表达,是生命个体与道德共同体的合一。乡贤之“贤”的显著标准是道德,隐含标准是能力。能力的突出表征是学业,更具体地说是儒术。如果只具备德行而无能力做基础,往往埋没蒿莱,不以“贤”著称乡里。而那些能力出众者,加以孝悌友善的个体道德实践十分突出,往往成为一乡(相对的道德共同体)之“望”。也就是说,乡贤一方面是“乡”的道德共同体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又对这一共同体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乡贤作为道德权威,维持着伦理共同体的秩序安排,具有非同寻常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质言之,乡贤是个体生命与伦理实体良性互动的产物,乡贤文化的道德哲学本质就是道德主体与伦理共同体的互动。西汉兒宽在任左内史时,表奏开六辅渠,在征收租税时,不急征收,假贷与民,以故田租多不入库。后有军役征发,左内史因欠租课名列末,当免官。“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这种从垫底到第一的戏剧性变化,并不是凭借法律的权威,而是兒宽道德的力量。东汉琅邪人童仲玉,在灾荒年代把全部家产拿出来救济灾民,亲属和乡里数百人得以保全。其子童恢在任县令时清廉勤谨,当吏民有违禁令时,他总是根据情况给以指正;如果官吏称职,或者有人做了好事,他都要赏赐酒肉以示鼓励。“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吏人为之歌颂。”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四、古代乡贤道德文化的当代价值
古代乡贤文化的积极成分,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可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培育新型乡贤提供榜样。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又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古代乡贤据道尊德,其崇奉的儒家伦理的积极成分,至今不失价值。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主)、“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不偏不易,中正和合”(和谐)。“为仁由己,百家争鸣”(自由)、“列德尚同,爱无等差”(平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公正)、“礼法共治,德刑合一”(法治)。“临患不忘,将死不忘”(爱国)、“敬业乐群,惟精惟一”(敬业)、“诚者天道,言信行果”(诚信)、“上善若水,仁者爱人”(友善)。古代乡贤所秉持和倡导的道德信念在国家、社会、个人的不同层面契合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资源。我们必须主动地汲引这种文化资源,培养公民道德人格。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充分调动农业、农村、农民的活力,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也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特别是道德失范的问题。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农村仍然面临严峻的道德滑坡现象。这种滑坡表现在个人、家庭、村社等各个层面。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丧失诚信、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家庭层面,主要表现在养老问题、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方面;村社层面,表现为集体观念淡化、邻里关系冷漠等方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冲击、基层行政力量薄弱等。前文已及,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张由血缘、地缘、学缘等共同编织的社会关系网。乡贤,就是这张网的重要节点,是道德信念的坚守者和示范者。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0]3这种说法受到一定的质疑,但就其强调以乡绅(乡贤)为主导的伦理道德秩序对传统社会的重要性而言,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农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也已经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家族规训的制约。同时,国家法律法规等普遍性规则并不像传统的家规族训那样关注道德性,制度上的规定远不能达到对人心的规约。因此,随着社会转型,原来乡土社会中所存在的积极的、低成本的控制机制便趋向解体,道德维护机制不能得到及时修复,社会规范和价值不能得以有效维持和再生产。学者认为,在处理风俗民情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种理解路径:“移风易俗并改造国民性以适应和追求现代法治社会;顺应并适合国情民情以调整和建立相应体系与特色的法律制度”。[11]47事实上这两种路径不可偏废。加强法治建设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法律条文中增加吸纳优序良俗的弹性条款,以作为引入传统道德要素的“接口”。另一方面,要借鉴传统乡贤对于强化礼治秩序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在沟通乡土社会与政府机构、协助政府治理社会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努力做到将乡贤文化的积极因素融入或渗透法治建设,构建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效融合。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培育,说到底是道德建设问题。培育新型乡贤,是满足这一历史性诉求的重要途径。古代乡贤可以为培育新型乡贤提供榜样。“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意思是说,如果想成为“善人”,一定要以前人为榜样,否则,不能达到“入室”的地步。比如“曾三颜四”就是对榜样的精炼概括。(《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颜渊》:“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为什么说传统乡贤是培育新型乡贤的榜样呢?学者指出:“榜样示范的基本条件有四:榜样本身必须具有真实性的特质;榜样与模仿者在德性方面存在位势差;榜样与模仿者人格的同质性;模仿者对榜样的心理认同。”[12]传统乡贤曾经名著乡里、造福一方,为当地百姓景仰,经过世代流传,成为特定伦理实体共同的精神财富。李东阳说:“彼生于斯,学于斯,闻其姓名,睹其庙貌,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岂能已于俎簋尸祝之间哉?”[13]1012文天祥少时即受乡贤榜样的激励:“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嗣‘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文天祥传》)古往今来的事例证明,理想的范例是道德人格培养的温暖阳光,传统乡贤的榜样示范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方式。